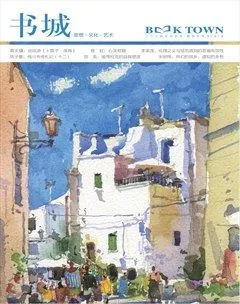彼得拉克的自我塑造
陳英
選擇一種“純凈”的語言
在最初締造意大利語的幾個(gè)文化巨擘中,但丁(1265-1321)是敞開的、包羅萬象的,代表了某種混雜和無限;彼得拉克(1304-1374)則曲徑通幽、向內(nèi)探索,用一種純凈的語言表露了內(nèi)心世界的小小顫動。在語言方面,一個(gè)很小的例子就可以展示兩者的差異。但丁在《地獄》第二十八章中對挑撥離間者的處境進(jìn)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寫:
那人竟被劈成兩半:從下巴一直劈到屁眼:
大小腸掛在兩腿中間,
心肺肝脾全都暴露在外面
……
(黃文捷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
但丁是寫實(shí)的,不會用文雅的詞匯替換那些略顯粗俗的詞語;而彼得拉克的詩文中連“腿”這個(gè)詞都可能會回避,頂多寫到“美麗的腳”(bei piedi),根本不會出現(xiàn)“屁眼”和“糞便”如此刺眼的詞語。若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彼得拉克是典型的“內(nèi)斂型”人格。在《歌集》的開頭,詩人就呈現(xiàn)出一個(gè)孤單的身影在曠野漫步的形象,躲避愛神糾纏的同時(shí),沉迷于一個(gè)萬分敏感豐盈的內(nèi)心世界。
彼得拉克建立的語言典范無疑是成功的,在他離世后一百多年,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威尼斯語言學(xué)家本博(Bembo,1470-1547)提出將彼得拉克的語言作為詩歌語言的典范:因?yàn)橐阉渍Z提升為一種文學(xué)語言,就要杜絕“俗氣”的詞語。彼得拉克用佛羅倫薩語言寫作,但他和但丁一樣,是一個(gè)被流放者,他從小大部分時(shí)間都生活在法國的阿維尼翁,又在蒙彼利埃學(xué)習(xí)法律,后來也在意大利北部生活過幾年。彼得拉克幾乎沒有在佛羅倫薩生活過,他用拉丁語工作,在教皇那里謀了一份差事,他的佛羅倫薩語是一種“流散”者的、書面的語言。當(dāng)代古典文學(xué)學(xué)者桑塔伽塔(Marco Santagata)認(rèn)為:
彼得拉克的語言是現(xiàn)代的。他對于用詞格調(diào)統(tǒng)一的堅(jiān)持是對的,一方面排除了過于口語的表達(dá),另一方面減少了對過于艱深的專業(yè)詞匯的運(yùn)用,這樣產(chǎn)生了一個(gè)相對“封閉”的詞語表。彼得拉克會優(yōu)先選擇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詞匯,也就是在語義上有多種涵義、內(nèi)涵豐富的詞語。總之,他的做法是對的,就是凸顯一種遠(yuǎn)離日常的語言,并強(qiáng)調(diào)其抽象和形式。
除了詞語上的嚴(yán)格標(biāo)準(zhǔn),彼得拉克當(dāng)然也傾向于思想上的嚴(yán)肅、優(yōu)雅,他的詩句定然不會出現(xiàn)同時(shí)代錫耶納詩人切科·安焦列里(Cecco Angiolieri,1260-1313)那種直言不諱、褻瀆主流價(jià)值的詩句:“把美女都給切科,瘸子丑婦歸他人……”或者“世上有三樣?xùn)|西最合我意:骰子、女人和酒館……”本博不推崇在今天看來引人入勝的“多語體”《神曲》,認(rèn)為只有《歌集》里嚴(yán)格選擇用詞的語言才是完美的典范。事實(shí)是,在《歌集》出現(xiàn)后的兩三百年,“彼得拉克主義”在歐洲盛行無阻。
享受世俗聲望的愛國者
彼得拉克其實(shí)在生前就備受追捧,他一三四○年在羅馬被加冕為桂冠詩人,這是他世俗聲望的頂峰。一九○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意大利詩人卡爾杜奇(1835-1907)在他的文章《在彼得拉克墓前》中,講述了這種空前絕后的盛譽(yù):
不僅僅是那不勒斯國王、法國國王欣賞他,為他的才華感到驚異;皇帝和教皇也在追捧他;同時(shí)意大利各地暴戾、粗魯?shù)馁灾饕脖凰Z服。比如殘暴的米蘭城主威斯康蒂希望他能當(dāng)自己的兒子的教父……他當(dāng)然也不乏民間的追隨者,有目盲的老先生由兒子攙扶著,在意大利半島上追隨著桂冠詩人的腳步,還有工匠用鮮紅色和金色裝點(diǎn)房間來招待他……
彼得拉克是一個(gè)“現(xiàn)代人”,他大部分時(shí)間都在歐洲各地旅居,曾經(jīng)渴望過古羅馬的輝煌能重新回歸,甚至指望過先于時(shí)代的狂想家,“最后一個(gè)羅馬平民保民官”—科拉·迪·里恩佐能開創(chuàng)一個(gè)新局面。他的夢想太過于超前,很快陷入幻滅,意大利在十九世紀(jì)才勉強(qiáng)實(shí)現(xiàn)了統(tǒng)一,輝煌卻談不上。彼得拉克是一個(gè)世界人,但民族身份卻是鮮明的,當(dāng)時(shí)意大利各城邦相互作戰(zhàn),同室操戈,請的都是德國雇傭兵。他和同時(shí)代的很多文人都意識到了雇傭兵的害處,在《歌集》里第一二八首就收錄了一首愛國詩歌,呼吁意大利人停止內(nèi)斗,當(dāng)心德國人的陰謀。
我的意大利,望見美麗的身體上
驚心的瘡痍
雖然言語對致命傷
無濟(jì)于事
但至少我的哀愴
是臺伯河、阿爾諾和波河的期望
現(xiàn)在我所處的意大利
痛苦而沉寂
天主啊,我懇求
憐憫讓你降臨到人間。
眷顧你喜愛的高貴土地。
慈悲的主,你看
一些細(xì)小的仇隙
都會引起血戰(zhàn);
殘酷而高傲的戰(zhàn)神
讓人心冷硬,一意孤行
天父,請感化、打開人們的心結(jié)
……
在各城邦殘酷斗爭,甚至城邦內(nèi)部也不斷分裂的局勢下,彼得拉克一句深情的“我的意大利”彰顯了他的身份歸屬,也為幾百年后“塑造意大利人”開啟了道路。
唯美的自然世界
彼得拉克在拉斐爾(1483-1520)之前就用文字營造出了優(yōu)美、祥和的古典主義風(fēng)格的自然風(fēng)光。《歌集》最廣為流傳的第一二六首:
清涼、透亮、甜美的水
我眼里唯一的女人
曾把嬌美的身體浸泡其中
她喜歡把美麗的身軀
(我?guī)е鴩@息憶起那一幕)
靠在那溫柔的樹干上
天神般的裙裾
她輕盈漂亮的衣裙
覆蓋了鮮花和綠草
晴朗、圣潔的氣息
……
從美麗的樹枝間
(在記憶中那么溫柔)
陣陣花雨,落在她的胸懷;
她坐在樹下
謙卑而又充滿榮耀
愛的輕煙籠罩著她
有花落在她的裙裾上
有花落在她金色發(fā)辮上
如同珍珠和黃金
這就是那日我見到的
有的花落在地上,有的漂在水面
花瓣在空中飛舞
仿佛在說:這是愛神的領(lǐng)地。
這是《歌集》中最著名的篇章了,場景靈動,三個(gè)形容詞的連用(清涼、透亮、甜美)也最能凸顯彼得拉克的語言特點(diǎn),這也在無形中塑造了意大利的文學(xué)語言。他對于愛神領(lǐng)地的呈現(xiàn):清澈的流水、碧綠的草地,花雨落在艷麗的衣裙上,與其說是一種真實(shí)自然的描寫,不如說是一種“幻象”。這種理想化的自然場景,在文藝復(fù)興盛期阿里奧斯托的文本中會時(shí)時(shí)浮現(xiàn),不過語氣已經(jīng)改變,彼得拉克凝重、深情的調(diào)子會被一種輕盈、調(diào)侃的語氣所取代。
第二七九首,類似的場景會再次浮現(xiàn):
在開滿鮮花的清澈河水邊
如能聽到鳥兒啁啾,綠葉
在夏天的微風(fēng)中沙沙地響動
還有清涼的河水汩汩地流動
彼得拉克的自然世界是理想化的、唯美的,既和古典作品中的自然描寫相互照映,也是后期文藝復(fù)興畫作中祥和、靜謐的自然。花瓣雨下的美麗女子,似乎已經(jīng)呈現(xiàn)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精神相貌,不一樣的是審視者帶著一顆現(xiàn)代的心,一個(gè)不安的靈魂。
隱秘的內(nèi)心世界
彼得拉克在《內(nèi)心的秘密》(Secretum)中虛構(gòu)了他與圣奧古斯丁的對話,坦白說自己的最大的罪責(zé)是慵懶(accidia),這種慵懶當(dāng)然不是白天睡覺、無所事事,而是道德上的不作為:雖然感覺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有罪惡感,但沒有心力去采取行動,最終是一種意志的缺失。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現(xiàn)代人的靈魂寫照,一種類似于抑郁的情緒。奧古斯丁在這場對話中承擔(dān)“心理分析師”的作用。他問:
“告訴我,對你來說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我見到的周圍的一切,我聽到的,接觸到的。”彼得拉克回答說。
“啊呀,你什么都不喜歡?”奧古斯丁驚異地問。
“特別少,幾乎沒有什么我喜愛的東西。”
對于彼得拉克來說,所有一切都是折磨。奧古斯丁對他的診斷是“慵懶”,當(dāng)然如果是現(xiàn)在的語境,“抑郁”是最合適的詞語。在彼得拉克塑造的“自我”身上,欲望的實(shí)現(xiàn)遇到了重重阻隔,首先是世俗的眼光,其次是死亡。彼得拉克在一三二七年四月六日在阿維尼翁的圣基亞拉教堂見到勞拉,這是他生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歌集》第六十一首用禱詞的方式講述了這次“致命的邂逅”。
我見到你的那日那時(shí)是有福的,
我見到你的那國那地也是有福的,
那讓我心系一處的明眸,
還有初戀甜美的憂愁,
我接納愛神的利箭,
那抵達(dá)心窩的傷也是有福的。
阿維尼翁的勞拉死于一三四八年,她是一位侯爵夫人。這也讓我們瞥見中世紀(jì)的愛情觀:有些愛情是在婚外的,比如當(dāng)時(shí)廣為流傳的亞瑟王圓桌騎士的故事,第一騎士蘭斯洛特和王后桂妮維亞的愛情故事。《神曲》中弗蘭杰西卡和保羅的叔嫂禁忌之愛,也是在閱讀蘭斯洛特和王后的故事中催生,并非一種“原創(chuàng)”的欲望。彼得拉克對于勞拉的欲望也并非自發(fā),之前有但丁的《新生》,他對貝阿特麗切的深情凝視和死后的惦念,還有“溫柔新體”詩派中,女性帶來救贖的種種書寫。
這份熱望并沒有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而消逝,或許正是因?yàn)楝F(xiàn)實(shí)的重重阻隔,《歌集》第七十九首展示了在初見十四年之后,一切執(zhí)念都沒有改變。
假如我嘆息的第十四年
中間和結(jié)束只是一個(gè)開始
我再也逃不過那熱念
時(shí)時(shí)被微風(fēng)的氣息換起
《歌集》中從開始第一首就是在回顧,一種在“自我”的深淵中的漂流,一種主觀的、憂傷的情緒在四處蔓延:
我現(xiàn)在清楚看到,
長久以來我曾是眾人的笑料,
我常為我自己感到慚愧
我荒廢時(shí)光收獲的是后悔
是悲憤,是清楚地知道
塵世所貪戀的是一場短暫的夢境。
值得一提的是,《歌集》的第一首十四行詩《請你們傾聽這散亂的詩行間》,其中原文第十一句采用了“押頭韻”的手法(di me medesmo meco mi vergogno),一句中出現(xiàn)了四次“我”的不同表述。整個(gè)詩集中的“自我”經(jīng)常超載,我的痛苦、眼淚、焦慮、懊悔、自我憐惜無處不在。韓炳哲認(rèn)為憂郁癥是一種自戀性病癥,病因往往是帶有過度緊張和焦慮的自我中心主義。彼得拉克定然沒有想到,他的情緒慵懶會成為一種世紀(jì)病癥。
彼得拉克的文本中自然重點(diǎn)贊美了勞拉的美,里里外外,靈魂深處的美,“勞拉”(Laura)這個(gè)名字也是彼得拉克對自己“欲望對象”的命名,并在其中加入了很多的雙關(guān)之意,這里面還包含著神話中“阿波羅與達(dá)芙妮”的傳說,達(dá)芙妮在變成桂樹(Lauro)之后,“桂冠”與詩歌榮耀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勞拉”的名字中蘊(yùn)含著金色、晨曦和微風(fēng)。這個(gè)欲望對象被塑造得如此誘人,以至于當(dāng)世之人去阿維尼翁窺探究竟,也只是感嘆:不過爾爾。
彼得拉克對于世俗聲望的追求和他對于勞拉的愛意在《歌集》中形成兩條并行的軌道,都是在矛盾和遲疑中向前,兩者都代表了易逝的世俗之物。
博爾赫斯作為但丁的擁躉,在《但丁九篇》也調(diào)笑過彼得拉克的不切實(shí)際,說:“他的筆下婦女的頭發(fā)總是黃金似的,水總是清澈得像水晶;那種機(jī)械似的、粗糙的符號文字破壞了語言的嚴(yán)謹(jǐn),似乎基于觀察不足而造成的冷漠。但丁卻不允許自己犯這樣的錯(cuò)誤。”然而彼得拉克筆下的金發(fā)還是那么奪人心魄,散發(fā)著MTV般群眾喜聞樂見的氣息。比如在《歌集》第九十首:
金色的頭發(fā)在微風(fēng)中飄散
纏繞成攝人魂魄的發(fā)卷,
美麗的眼睛,秋波流轉(zhuǎn)
迷人的光芒,如今不再閃耀奪目
在陽春四月,美麗女子的金發(fā)在煦暖的春風(fēng)中飄散,還有比這更輕盈、靈動的書寫嗎?這些句子在幾百年之后依然是活的。彼得拉克以男性的視角打造了一個(gè)女性的神話,這個(gè)神話在后來的幾百年會一次次被重寫,留下難以抹去的烙印。只有女性作為主體出現(xiàn)之后,這個(gè)神話才會漸漸變得黯淡。
自我形象的塑造
彼得拉克塑造的自我形象—憂傷憔悴的詩人,后來在浪漫主義時(shí)代成為典型,比如說歌德筆下憂傷的“維特”,意大利詩人福斯科洛(Ugo Foscolo)小說中殉情殉國的“雅可波”。《歌集》膾炙人口的第三十五首就是作者的自畫像:一個(gè)心懷愛火,落落寡歡,離群索居之人。
獨(dú)自一人,心事重重
我行走在曠野,步履沉重
緩慢,目光仔細(xì)回避過
人跡所到之處
我無處可藏,落落寡歡
的言行,昭然流露出
內(nèi)心燃燒的火焰
也無法躲過他人之眼
……
這種狀態(tài)在第一六一首會重現(xiàn),只是多了眼淚和渴望:
噢,散亂的步子,隨時(shí)都浮現(xiàn)的凌亂心思
頑固的記憶,熱切的期頤,
強(qiáng)大的渴望,柔弱的心,
我的眼睛,已不是眼睛,而是泉眼!
在《歌集》第七首,彼得拉克彰顯了自己清高的志向:對詩歌的追求高于其他一切。
追求桂冠、愛神木有何用?
哲學(xué),赤裸而貧窮,
精于算計(jì)的市儈們會這樣嘲諷。
你在這條路上會孑然而行;
所以我請求你,高貴的靈魂,
不要放棄高貴的使命。
《歌集》的第八十二首每一行都有“我”,他說出了作為人和自己惡習(xí)搏斗的疲憊:
我被那古老的訓(xùn)誡束縛
我的罪過、惡習(xí)讓我疲憊
我萬分害怕在半途倒下,
落入我仇敵的手中。
彼得拉克的自我也經(jīng)常被分離出來,從外部審視自己。比如在《歌集》第三○二首中,他看著自己的心思去往渴望的地方,終于在第三重天見到了心心念念的女人,她在那里更加謙卑美麗。
她握著我的手說:在這一重天
若初心未變,你依然會和我在一起,
我是那個(gè)讓你不得安寧,
在夜晚降臨之前結(jié)束了時(shí)日的女人。
你凡人的智慧,無法理解我的好:
我只等待你,你摯愛的
我美麗的身軀,已經(jīng)留在下界。
……
自我愿望的達(dá)成也在內(nèi)心進(jìn)行,然而這一切還是會被懊悔淹沒,在《歌集》第三六五首,可以說是全書的終曲,作者的絕望也抵及最深處,只期望得到死亡的接納。
我為我失去的時(shí)光痛苦
我把生命耗費(fèi)在對凡俗之物的愛上,
雖有雙翼,卻沒有飛起,
讓自己成為一個(gè)不凡的表率。
……
彼得拉克在詩歌中除了呈現(xiàn)愛欲帶來的甜美、焦灼和不安,也時(shí)時(shí)在表達(dá)時(shí)光流逝帶來的痛苦和焦慮,比如在《歌集》第二七二首中,時(shí)間的維度被打開,但無論過往、現(xiàn)今和未來,都沒有讓人安寧的時(shí)刻:
生命在逃離,一刻也不停歇。
死亡緊跟其后,過往之事
現(xiàn)今之事都讓我不寧,
未來之事也同樣。
回憶和期待都讓我不安
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都是如此。
《歌集》收錄的三百六十六首詩歌也是精心構(gòu)思,似乎像日記一樣,代表了一年或者一生的時(shí)日(勞拉在提到自己時(shí)說:我是在夜晚降臨之前結(jié)束了時(shí)日的女人。在這里“一天”引向了“一生”),富有深意。彼得拉克的創(chuàng)新之處就在于對自我意識的審視,對自我欲望、痛苦和頑念的分析,這種審視有“為賦新詞強(qiáng)說愁”的一面,但正如卡爾杜齊所言:彼得拉克第一個(gè)做出了古代詩人沒有做的事,那也是基督教不允許的事(除非是以苦修為目的),也就是每個(gè)靈魂都能像人類社會一樣,擁有自己的故事,生命的每個(gè)時(shí)辰,都可以像一首詩一樣展開,一個(gè)小小的內(nèi)心的事件,如果在人心里響起了回音,那在詩歌上也會響起回音。彼得拉克是第一個(gè)剝開自我意識的人,對它進(jìn)行審視、分析;他在審視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他所寫的哀歌的深層意義就是:特定的人和他無限的可能之間,感受和理想,人和神之間的矛盾。
文中所引《歌集》皆為本文作者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