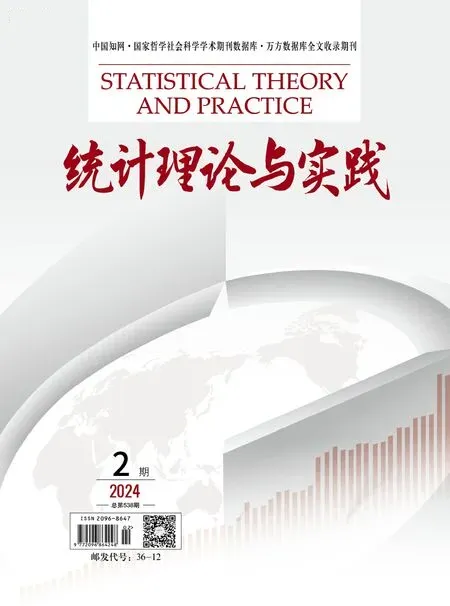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分工與對接關系的測度分析
楊海深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廣東 廣州 510635)
一、研究背景
區域內部或區域間產業主體之間的發展存在差異,促使產業合作不斷深化,產業也向著利潤最大化的方向和地區擴展,這符合主體利益的選擇,也是市場調節的必然結果。區域產業協作主要有四種形式,即商品貿易、生產要素流動、產業轉移和產業對接,這四種形式是一個分工合作不斷深化的過程,從商品貿易到要素流動,再到產業的整體轉移,最后到產業的緊密對接,這是區域產業專業化和分工的必然規律。因此,產業對接是區域產業協作模式的深化,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區域經濟協作方式。一方面,產業對接源于區域內或區域間的比較優勢和產業發展的差異化;另一方面,產業對接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區域內或區域間的互動,鞏固合理的分工和合理的利益分配。徐遠征(2007)認為,產業對接是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為實現某種共同利益和利益互補為目的的跨地區產業合作的總稱。信虎強和李建(2007)則認為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自然可以通過理性科學的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決策,促進產業的合理布局和融合發展。姜澤華(2012)認為,產業對接是由政府參與的,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按照產業鏈的順序,實現跨區域間產業緊密銜接,以達到提高跨地區產業合作效率和效益的目的。本文比較認同姜澤華的觀點,尤其對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區域產業協作,更應該注重產業對接。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作由來已久,總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和兩個層面。兩個階段分別是改革開放的頭20年和最近20余年,兩個層面分別是港澳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以及內地城市之間的產業分工與對接。
第一個階段主要以港澳地區的制造業向內地城市轉移為重心,港澳企業通過在內地城市投資設廠,形成港澳為“前店”、珠三角城市為“后廠”的粵港澳大灣區別具特色的產業合作形態,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紛紛通過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港澳資本和企業,表現出激烈的產業競爭,再加上各城市資源稟賦相當,最終造成了產業發展重疊、產業結構高度趨同的狀況。
進入第二階段,港澳地區制造業基本轉移完畢,逐步建立起以金融、航運、物流、專業服務和旅游休閑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在三次產業方面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相比表現出明顯的結構差異。同樣,內地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強調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產業呈現一定程度的分工,尤其是經歷了“十二五”和“十三五”先進制造業規劃的調整,深圳、東莞、惠州逐步向珠江東岸高端電子信息產業帶方向發展,珠海、佛山、中山、江門、肇慶向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領域拓展。這一時期隨著分工與對接政策的進一步落實,特別是行業內分工的逐步細化,城市間的產業同構現象正在減輕,產業差異化程度正在擴大。
綜合兩個階段看,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作除商品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作為長期的合作方式外,起初主要是進行產業轉移,先是大規模地接納從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到本地區的加工制造業,經過制造業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改造和升級,形成強大的制造業能力。隨后,為了產業整體的轉型升級,開始將部分低水平的制造業向區外轉移,以騰出空間發展更高層次的產業。經過持續的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產業分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的互補性日益提升,成為一個更緊密、關聯度更高的經濟體。至此,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轉移的轉入和轉出已基本達到預設的目標。繼續深化區域產業協作的重點將是有序的產業對接,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產業協作的主要模式。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不同產業發展的現狀和基礎不同,產業分工與對接的協同發展選擇的模式也不盡相同。具體包括產業間的分工和對接、產業內的分工和對接、產業鏈的分工和對接,最終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全面融合。其中,產業間的分工和對接是前期階段的產業分工和對接形式,不同的地區根據自身優勢發展不同的產業;產業內的分工和對接是基于比較優勢、規模經濟,生產種類不同產品,為實現專業化目標,在同一產業內部的協同發展模式;產業鏈的分工和對接是屬于同一產品不同環節上的分工,關聯性更強,是生產不同環節、工序甚至模塊上的分工與對接;產業的全面融合則包含研發、生產、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等多方面的融合。因此,同一產業不同分支的發展,是城市間產業合作深化的表現,也是產業對接的基點。
鑒于此,本文利用專業化指數、分工指數和區域競合關系指數對粵港澳大灣區專業化分工及競合關系演變態勢進行探討,分析當前產業分工特點和規律,提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分工與對接的對策建議,以期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專業化及演變分析
(一)產業專業化指數的測算
專業化指數是通過衡量地區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和集中程度來反映行業的相對發展水平和優勢行業的地區分布,表示地區在高層次區域的地位和作用,進而揭示區域分工的基本格局,公式如下:
其中,qij為i城市制造業分行業j的增加值,qi為i城市全部制造業增加值,即qi=∑jqij,因此,為i城市的分行業j占全部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qj為全區域制造業分行業j的增加值,即qj=∑iqij,q為全區域全部制造業增加值。本文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區域比較對象,來反映各城市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地位及專業化程度。
(二)粵港澳大灣區優勢行業特點演變分析
參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 4754—2017),將制造業的大類代碼13—43作為行業類別,使用專業化指數公式(1),測算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2009年、2013年和2018年的優勢行業分布(一般認為,專業化指數大于1的行業為優勢行業),并依照高技術產業(制造業)分類代碼(2017),將優勢行業劃分為傳統優勢行業和高技術優勢行業,通過近十年專業化指數測定的傳統優勢行業和高技術優勢行業變化來判斷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的演變趨勢。
表1給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2009年、2013年和2018年傳統優勢行業和高技術優勢行業代碼分布情況,從中可以發現:

表1 2009—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優勢行業變化
一是粵港澳大灣區優勢行業分布覆蓋了制造業所有大類。總體看,粵港澳大灣區優勢行業囊括了制造業代碼13—43共31個全部行業大類,既涵蓋傳統制造業領域,也包括高技術制造業領域。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乃至全球工業門類最為齊全且具有相對優勢的區域之一。
二是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制造業結構正持續改善。對比2018年和2009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傳統優勢行業具有一定的延續性,高技術優勢行業變動較為顯著。就傳統優勢行業而言,絕大多數城市行業變動不太明顯,說明其已形成具有比較優勢和較為持續的競爭能力。從高技術優勢行業變動看,珠三角核心城市中,廣州從4個增加到5個,深圳從2個增加到4個,珠海從5個增加到7個;其他城市除肇慶和澳門外,數量也基本持平或略有增加,反映出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內部結構正在進行調整和升級。
三是粵港澳大灣區優勢行業同構正趨于舒緩、行業間分工水平正在提升。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優勢行業同構的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地理臨近性和產業鏈分工不足所導致,如廣州和佛山擁有相同的優勢行業代碼13、15、18、21和26,深圳和東莞擁有相同的行業代碼35、39-41,珠海和中山擁有相同的行業代碼26、27、38、40和43;另一方面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產業轉移所引起,如江門和肇慶作為產業轉移地,在傳統優勢行業領域與廣州、珠海、佛山和東莞有較多的行業代碼重合。但是整體看,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行業分布有較為清晰的主線,珠江東岸形成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代碼39)、儀器儀表制造業(代碼40)為行業主體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珠江西岸形成以通用設備制造業(代碼34)和專用設備制造業(代碼35)為主體的裝備制造產業基地,有力提升了行業間分工水平。
三、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競合關系及演變分析
(一)產業競合關系的測算方法
產業競合關系指數是從行業結構的差異性出發,利用歐式經濟距離公式測算產業同構或互補的程度,是表達區域經濟競合關系性質的重要指標。
首先,采用制造業各行業增加值比重所構成的指標向量來描述城市制造業結構狀態,計算城市間指標向量的歐式經濟距離,通過距離值的大小來判別城市間競爭與合作關系。歐氏經濟距離公式如下:
其中,Dik指i城市與k城市的歐氏經濟距離,x'ij、x'kj為i城市和k城市制造業分行業j標準化后的數據,計算公式為:
其中,xi(k)j為i或k城市的行業j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為全部城市行業j的平均值,M為研究地理單元的總數,粵港澳大灣區共有11個城市,故M=11。
其次,通過歐式經濟距離公式(2),可計算城市間的競合關系指數,進而判斷競合關系。競合關系指數公式如下:
其中,N為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配對樣本數,即N=55。若該指數為正,則表示城市間存在互補合作關系,且值越大,互補性越強;若指數為負,則說明城市間存在競爭關系,絕對值越大,競爭性越強。
(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競合關系特點
城市間的產業合作和生產要素流動均建立在行業發展異構與互補的基礎上,行業間的分工深化有利于強化城市間的互補合作,但行業同構將帶來惡性競爭。本文采用競合關系指數來判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產業競合關系。若競合關系指數Iik≥0.5,表示兩城市是強互補合作型;若0≤Iik<0.5,則是一般互補合作型;若-0.5<Iik<0,表示為一般競爭型;若Iik≤-0.5,則是強競爭型。由此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競合關系狀態進行類型劃分,結果見表2。

表2 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競合關系
1.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競合關系以競爭關系為主,“深莞惠”和“珠中江”經濟圈內競爭尤為嚴重
從表2可以看出,在粵港澳大灣區55個配對樣本城市中,競合關系指數為負數的有32對,占58.18%,側面反映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制造業同質化較為嚴重,潛在的產業競爭壓力較大。從珠三角三大經濟圈看,“深莞惠”經濟圈中,“東莞-惠州”“深圳-惠州”“深圳-東莞”競合關系指數分別為-1.25、-0.49、-0.66,絕對值均接近或大于0.5;“珠中江”經濟圈中,“珠海-中山”“中山-江門”“珠海-江門”競合關系指數分別為-1.83、-1.38、-1.31,絕對值均大于0.5,可見“深莞惠”和“珠中江”經濟圈內均為強競爭型關系;“廣佛肇”經濟圈中,“廣州-佛山”“廣州-肇慶”“佛山-肇慶”競合關系指數分別為-0.42、-0.37、-0.97,雖都處在競爭關系中,但程度與其他兩個經濟圈相比,競爭關系稍為緩和。
2.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間以互補合作關系為主,但節點城市之間以競爭關系為主
廣州、深圳、香港、澳門4個中心城市之間的競合關系指數(除“香港-澳門”外)均大于0,表明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已經形成各自相對獨立而又相互支撐的產業體系。但是對粵港澳大灣區7個節點城市而言,彼此間競合關系指數(除“佛山-惠州”外)均小于0,某些城市之間為強競爭關系,說明節點城市之間制造業的行業同構程度較高,產業存在較為嚴重的競爭關系。中心城市與節點城市之間的競合關系出現分化特征,廣州和香港分別與佛山、中山、江門、肇慶表現為競爭關系;深圳與東莞、惠州表現為競爭關系,與佛山、中山、江門、肇慶呈現互補關系;澳門與全部節點城市表現為互補關系。可見中心城市要成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輻射帶動功能還有待加強。
3.粵港澳大灣區競合關系呈現出動態性特征,但總體上相對穩定
與2009年城市間競合關系對比(見表3),競合關系指數呈現出一定的變化趨勢和動態特征,主要表現為中心城市的互補程度在加強,大部分節點城市的競爭程度在下降。競合關系演變的本質原因在于城市之間的產業差異化程度高低所引發的產業合作與市場爭奪行為,從粵港澳大灣區競合關系演變結果看,經濟發展有助于改善城市間的分工與合作。但從整體看,競合關系狀態依然與上述兩點基本相同,說明短期內改變城市間的競合關系比較困難。

表3 2009年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競合關系
四、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分工及演變分析
(一)分工指數的測算
城市分工指數是基于城市間產業結構的差異度來衡量城市分工的重要指標,產業結構差異的背后是城市間分工的結果,表達式為:
其中,Sik為i城市與k城市之間的分工指數,qij與qkj分別指i城市與k城市產業j的增加值,qi(k)=∑jqi(k)j指城市產業部門的總增加值。Sik越大,則產業結構差異越大,區域分工程度越高。當兩個城市間的產業結構完全相同時,Sik為0;當兩個城市間產業結構完全不同時,Sik等于2。可見,城市分工指數衡量了兩個城市間的分工狀況。
(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分工特點及演變分析
本文利用城市分工指數公式,測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分工指數,以反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分工程度,結果見表4。

表4 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分工指數
1.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間的分工程度明顯高于節點城市間的分工
廣州、深圳、香港、澳門4個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間的分工指數均大于1,珠海、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和肇慶節點城市間的分工指數(除“佛山-惠州”“珠海-肇慶”“惠州-江門”“惠州-肇慶”外)均小于1,可見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間分工程度要高于節點城市間。說明中心城市已經形成具有各自特點的產業定位和產業結構體系,而節點城市仍然面臨著行業間的定位重疊和分工不充分的境況。
2.粵港澳大灣區節點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的分工顯著高于節點城市間的分工
以佛山為例,其與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的制造業分工指數均大于1,與珠海、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分工指數均小于1,說明佛山與中心城市已經形成良好的產業分工體系,但與節點城市的產業分工有待進一步優化。
3.“廣佛肇”經濟圈內的分工程度稍高于“深莞惠”和“珠中江”兩個經濟圈
“廣佛肇”經濟圈內(除“佛山-肇慶”外)的分工指數均大于1,而“深莞惠”和“珠中江”內部分工指數均小于1,說明“廣佛肇”經濟圈已經形成較為合理的“中心-外圍”形式的產業結構異質性和整體性分工。
4.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的分工程度在不斷提高
對比表4和表5可以發現,上述3個分工關系依然保持不變,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分工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可能是產業結構在一定時期內難以改變,有一定的結構“黏性”造成的。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的分工指數大部分有所提升,表現出較高的同步性,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分工演變是一個同步的過程。但也有例外,如“東莞-惠州”“珠海-江門”“珠海-中山”分工指數略有下降,反映出這些城市間產業結構有繼續同質化的趨勢。

表5 2009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分工指數
五、粵港澳大灣區加強產業對接的建議
綜上所述,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形成優勢行業覆蓋面廣、行業同構現象趨緩和產業分工水平不斷提升的產業對接基礎,在產業對接中形成中心城市間互補合作、節點城市間競爭角逐的格局,呈現出珠江東、西兩岸間產業互補趨勢逐步增強,東岸城市之間、西岸城市之間各自競爭仍然激烈,特別是“深莞惠”“珠中江”“廣佛肇”三個經濟圈內部的競爭有更為明顯的產業對接特點。基于此,粵港澳大灣區要以城市間的產業對接作為主要協作模式,促進產業深度合作。
(一)強化優勢行業集聚,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建設有序分工與對接的產業鏈條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走向深入,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融合的新要求,必須從簡單著重區域間的產業轉移變為強調城市間的產業對接;既要堅守并充分發揮傳統優勢行業,又要推進正在迅猛發展的高技術優勢行業,促使這些行業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行業龍頭或打造重要生產基地,從設計、研發、整體制造和市場拓展等方面形成核心,將中心城市行業配套與節點城市的配件加工、生產能力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優勢行業發展的梯度合力,進而形成產業鏈集群。充分利用港澳現代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促進其與廣東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從戰略頂層設計、產業鏈協同招商等方面構建多層次產業協同分工體系,建立產業鏈供應鏈協同保障機制,合理打造先進制造產業集群,協調謀劃未來產業發展,增強粵港澳產業協同能力、安全發展能力和產業國際競爭力,積極主導RCEP區域產業鏈重塑,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在RCEP供應鏈網絡中的核心節點地位,推動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產業合作和競爭。
(二)加強城市間分層次對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間點對點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節點城市應把握與中心城市分工程度持續改善的良好趨勢,加強與中心城市的產業對接,特別是要多方位對接深圳先行示范區以及廣州“老城市、新活力”規劃,積極發展成為傳統優勢產業的重要合作創新源頭。推進“廣佛”“港深”和“澳珠”極點產業輻射帶動節點城市產業發展,以技術要素和金融要素為產業對接的突破口,以“產業鏈—資金鏈—創新鏈”為對接體系,調整節點城市之間的產業對接形態,通過產業鏈演進過程中分工層次增加、生產環節分工細化,實現各節點城市精準的生產環節層次對接,緩解節點城市的產業同構壓力。鼓勵產業結構趨同前提下的產品差異化發展,將面上的產業同構轉化為產業鏈條內的合作協同。發揮橫琴、前海、南沙和河套4個重大合作平臺作用,切實加強其與港澳產業協同、科創資源承接,強化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并在產業對接領域強化制度設計和機制創新,共同構建密切的開放經濟合作空間,促進產業集聚發展和科技成果轉化,筑牢粵港澳全面深化合作的基石。
(三)以產業升級為契機,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產業數字化對接
產業升級是解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同構和產能過剩的有效治理手段。粵港澳大灣區應抓住產業升級機遇,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完善數字經濟與制造業融合發展機制,推進傳統優勢行業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以智能工廠、機器人應用、“互聯網+”等為重要手段加大技術改造投資,加快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中的標準體系建設,促進產業向價值鏈兩端躍升,通過產業數字化轉型推動數字產業鏈關聯協同發展,推動建設數字產業集群,共建國際數字新技術新業態策源地,培育數據要素一體化大市場,推動產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同時,加大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激勵和支持力度,充分調動企業融入參與數字化轉型升級的積極性,引導社會資本向數字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創新研發方向傾斜,支持企業巨頭和優勢行業聯盟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應用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資訊技術融入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幫助企業“上云上平臺”,引導行業定制流程生產方式向智能制造方向轉變,形成錯位和梯級發展的抱團式產業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