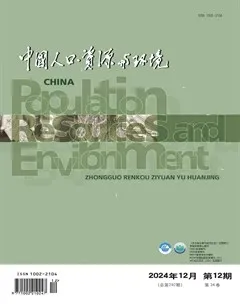整體性治理視域下生態保護規范法典化的邏輯與進路
摘要 近年來,中國環境法治逐漸從要素治理向系統治理轉向,以解決傳統治理模式對生態系統整體性關照不足之弊。在此背景下,整體性治理進路成為生態環境法典中生態保護規范的重要依循。這不僅要求在理念層面呼應可持續發展的邏輯主線,也需要從文本邏輯和法律制度等方面遵循整體性方法,健全中國生態保護法治體系。基于適度法典化的編纂模式,生態環境法典的自然生態保護編可遵循以下編纂理路:①在理念上,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融入法典內容中,以整體性、系統性方法構建以生態環境法典為核心的生態環境法治體系。在自然生態保護編中,應秉持貫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將維護生態系統整體功能作為根本目的,依此構建生態保護法律制度體系。②在內容上,基于環境、資源與生態一體三面的關系,明確自然生態保護編中生態保護法律規范的重點與核心,采取“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模式。同時,根據適度法典化的編纂要求,實現自然生態保護編與污染控制編、綠色低碳發展編之間的融貫與銜接,以及生態環境法典與單行法的有效協同,從而明確同一生態要素基于“環境”“生態”“資源”的不同側重在法典不同編的具體體現。③在框架結構方面,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邏輯線索,生態保護的主要內容應涵蓋生態系統保護、物種保護和遺傳資源保護等方面,并在此基礎上就生態退化治理、生態修復和生態補償等方面作出規定,以實現從生態系統、物種間到物種內的整體性保護。同時,生態環境法典可基于類型化邏輯安排自然生態保護制度,構建“事前預防-過程監管-損害救濟-恢復治理”的規范體系,從而為生態保護提供完整、健全的規范依據。
關鍵詞 生態環境法典;自然生態保護編;整體性保護;生態安全;生物多樣性
中圖分類號 D922. 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12-0014-11 DOI:10. 12062/cpre. 20241103
生態保護關乎人類生存和永續發展,不僅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進路,也是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核心領域。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納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提出,積極研究推進環境(生態環境)法典和其他條件成熟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編纂生態環境法典”。這些重大決策體現了新時代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對“生態”和“環境”一體化的回應,遵循了整體性保護理路,突出了生態保護在生態文明法治建設中的重要地位。目前,中國的生態保護法律規范缺少充分的系統整合和整體性保護的規范依據,對生態系統整體功能關注不足,這也成為影響生態文明法治效能的重要方面。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利契機。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整體性視角作為編纂自然生態保護編的方法論基礎,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基本邏輯脈絡,構建自然生態保護編的制度體系和協同方案。
1 整體性治理視域下生態保護法治的理念遵循
當前,中國生態保護法治正在經歷從要素保護到生態系統整體保護的理念更迭,在價值層面體現為生態保護法治更加重視安全價值。這要求生態保護法基于生態系統整體,以系統整體觀為根本方法,從整體層面保障生態安全。
1. 1 生態保護法治的理念更迭
中國早期的生態保護法律規范主要嵌入在自然資源立法之中,強調生態要素的區分保護。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出現并為世界各國認可,中國作為這一理念的堅定支持者和踐行者,在1994 年發布的《中國21 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中,明確提出了促進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在環境保護法治發展過程中,中國逐漸將可持續發展原則內化為生態環境保護的基本精神。環境資源一體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內容之一,也對中國生態環境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中國環境法治體系的不斷完善,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性保護理念也反復體現在中國生態保護立法之中,尤其是對于生態系統的區域性保護愈發重視。在此背景下,中國陸續制定和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濕地保護法》(以下簡稱《濕地保護法》)和《國家公園管理暫行辦法》等生態保護法律規范。
當前,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環境法治發展的價值指引,并且在各國環境法典編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2]。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過程中,應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貫穿始終,以確保法律規范能夠有效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與此同時,作為邏輯主線的可持續發展在法典各編中發揮著不同面向的作用:在污染控制領域,可持續發展所體現的是“以人為本”的面向,強調以保障環境健康為目標的社會可持續;在綠色低碳發展領域,可持續發展所體現的是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面向,強調在生產、流通、消費全環節的經濟可持續[3-4];而在生態保護領域,可持續發展所體現的則是資源可持續利用與生態保護一體化的面向,強調對生態的整體性保護。
具體而言,自然生態保護編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應著重強調以下3個方面:一是聚焦于生態保護。“生態”是與生物有關的各種相互關系的總和,生態保護的主要目的在于增進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保障生態利益。與此不同的是,自然資源利用強調生態要素的經濟屬性,保障可持續的經濟收益。二者在根本目標方面存在顯著區別。二是堅持“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目標。由于生態環境要素和資源要素往往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即使在利用層面,也要強調可持續利用中的生態保護需求。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生態保護密切關聯。一方面,生態系統的功能維持是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資源開發利用方式會導致生態環境退化,加速資源耗竭,破壞生態系統。因此,資源可持續利用也應當貫徹生態保護要求。三是以整體性路徑實現生態保護,摒棄原有的要素分別保護立法模式。要素立法體現了立法上的“還原論”進路,將整體的生態問題還原為不同生態要素受到的破壞,通過對遭受破壞的不同生態要素立法規制整體生態問題。但是生態系統并非生態要素的簡單加和,要素分別保護立法的加總難以替代整體性保護的立法功能。為此,需要從規制對象、管理體制、區域協調等多方面確立整體性路徑,采取跨領域的綜合措施,才能有效應對復雜的生態環境問題。
1. 2 生態保護法治的價值基礎
生態保護法治的核心是安全價值保障,這不僅是生態安全保障的根本需求,是法的安全價值的體現,也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生態保護法治中的落實。
1. 2. 1 作為生態保護法治內核的安全價值
安全價值是法的核心價值之一。法的價值體現了法與人的關系,是法對人需求的滿足和人對法的期待[5]。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生態安全是當代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將傳統法律的個體安全價值拓展為包含“生態安全”的公共安全,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置于生態安全的中心地位[6]。這不僅回應了風險社會對法律價值的需求,同時也表明,生態文明法治的安全價值體現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因此,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應當基于整體安全,將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的哲學觀念轉化為法的價值取向[7]。這也要求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核心邏輯。
從系統視角來看,應對生態風險是法律系統性保障生態安全的內容。當前,中國生態保護法治面臨著雙重風險的挑戰:一方面,生態系統作為一個生態要素交疊的復雜系統,一旦產生損害,就會引發系統性、不可逆轉的負面后果;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在回應生態環境問題時為了化約復雜性,可能在此過程中產生不可控結果,其中可能性既包括穩定的、有益的向度,也包括潛在的危害,即風險[8]。面對這種雙重風險,生態保護法治應當構筑一套穩定運行的體系,以其相對穩定性對抗風險的不確定性。生態保護法治通過調整社會關系,使生態系統不過分暴露在風險之下,保障其面對人類活動時的韌性和復原力,使之保持一個相對的穩定狀態,進而保障生態安全[9-10]。同時,生態風險的普遍性要求生態保護法治不能固守損害填補或權益救濟的傳統法律邏輯,而應構筑相對“主動”的風險應對機制和法律制度體系,以系統性思維應對生態風險[11]。
就國家戰略而言,生態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內容。2014年4月15日召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12],明確將生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內容。隨后,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30條規定:“國家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加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強化生態風險的預警和防控,妥善處置突發環境事件,保障人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大氣、水、土壤等自然環境和條件不受威脅和破壞,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一規定亦表明生態安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的重要地位[13]。
可見,保障生態安全既是生態保護法治核心價值的體現,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路徑。生態安全只有通過生態系統整體功能的實現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此整體性視角和方法應當在生態保護法治中得到充分重視和貫徹落實。
1. 2. 2 作為生態保護方法論依循的系統整體觀
整體性保護是符合生態保護基本特征的方法論,對于生態保護法治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整體性保護方法論為生態保護法治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促進了生態保護法治體系的形成和發展[14]。在生態保護法治中,整體性保護方法論體現為系統整體觀。
系統整體觀是中國學者在西方生態整體主義基礎之上,結合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系統觀方法論總結升華的理論方法[15]。其體現出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為核心、以“協同論、整體觀”為要義的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價值論,符合生態保護的基本需求和生態保護法治的基本邏輯。基于系統整體觀的生態保護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特征:整體性和系統關聯性。
系統整體觀要求以整體主義方法保障生態保護法治的形式理性。以生態安全為核心,意味著生態保護法需要涵攝生態系統整體,結合生態系統復雜性特征調整諸多類型的人與自然互動關系類型,覆蓋從事前到事后的生態環境利用活動。從自然界中的人、動物、植物等各個要素本身出發的個體主義方法是一種分離式的方法論,注定只能關注生態系統的局部[16]。與之相對,整體主義的方法論是聯系的、系統的思維方式[17]。生態保護法治應以整體性作為法秩序的線索,以整體系統思維保障生態保護法的形式理性。一方面,生態保護法治的秩序狀態本身為社會帶來安全。這是因為,面對復雜的生態保護需求和生態環境利用情況時,成體系的生態保護法具有生產性,可以填補因法律關系變化導致規范制度不完備而產生的漏洞[18]。另一方面,生態保護法的整體性秩序邏輯可以對抗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和偶在性帶來的系統風險[19]。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的確定性內容和程序在實踐中預見行為后果,繼而以相對安定的狀態開展生態環境開發利用活動。這一體系正是法律價值的體現[20-21]。
系統整體觀要求生態保護法治著眼于生態系統的系統關聯性和法律規范的體系性。目前以污染防治為主的生態環境立法存在要素分立的思維慣性,未充分重視整體生態系統的功能和價值。基于生態保護的客觀規律,生態保護法治應當重視生態系統的關聯性[22]。為此,生態保護法典的自然生態保護編首先應當貫徹法典的邏輯主線,即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性思維,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為邏輯主線。自然生態保護編應將分散的生態保護法規整合為具有邏輯性和系統性的法律文本,保證篇章的秩序一致,提高生態保護法律的適用性,繼而更好地應對生態風險,為保障生態安全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
2 基于整體性保護理路的自然生態保護編邏輯結構
基于整體性保護的內在要求,自然生態保護編的邏輯結構應考慮整體篇章體例的設置,在微觀上明確“生態-資源”一體化的具體安排,同時與適度法典化的編纂模式相適配。
2. 1 自然生態保護編的內在邏輯
自然生態保護編作為生態環境法典的一編,與總則編、污染控制編、綠色低碳發展編、生態環境責任編共同構成法典的主體內容,對于這一點已經基本達成共識[23-26]。其中,自然生態保護編應以保護生態系統、保障生態資源可持續發展為目標,著重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功能保護,對現行的生態保護法律規范進行優化整合,以整體性方法實現生態保護目標[27]。
目前,學界關于自然生態保護編的框架結構設計存在不同觀點。有觀點認為應當基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基本思路將生態保護法律規范納入各部分之中,從規劃、管控、防治、保障4個方面構建自然生態保護編[28]。還有觀點認為,在遵循“事前-事中-事后”基本思路的同時,應以“總-分”的思路構建自然生態保護編的整體結構。即,在自然生態保護編內設置通則、自然區域保護、野生生物物種和遺傳資源保護、行政法律后果4個分編[29]。也有觀點認為,應當在處理好要素保護與區域保護關系的基礎上,基于“要素+區域+生態系統”的思路構建自然生態保護編[30]。另外的觀點認為,可借鑒《法國環境法典》的編纂思路,以生態空間管控作為自然生態保護編的體例邏輯[31]。這4種觀點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包含的內容范圍,以及各部分制度體系的邏輯劃分依據等方面。
參考典型國家的生態環境法典,其中關于生態保護的規定亦呈現出不同的篇章結構。有的國家設立了自然生態保護編,集中規定生態保護的相關內容。例如,《瑞典環境法典》專設第三編“自然保護”,規定了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區域和禁獵禁伐區、水域保護區等生態區域,還特別規定了動植物物種保護[32]。有的國家采用“生態系統保護-各子系統保護”的總分模式,分別將生態系統保護和子系統保護規定在法典總則和分則中。例如,《德國環境法典(專家委員會草案)》在第245至第285條專門規定了生態系統整體保護的內容。該部分以“保護生態系統功能”為核心,呈現“整體生態系統保護+重要群落生境保護”的基本結構。除此之外,該草案在分則部分分別對野生動植物、森林、土壤、水體要素的生態保護作出規定[33]。有的國家法典采用較為分散的文本結構,并未設置自然生態保護編,而是將生態保護法律規范和制度分散規定在法典的不同部分。例如,《意大利環境法典》以環境影響評價、資源利用和污染防治為主體,在有關土地資源和水資源利用的規定中附帶規定了土壤保護和抗沙漠化、水體保護等生態要素保護的內容[34]。《法國環境法典》在第二卷“自然環境”、第三卷“自然空間”和第四卷“自然遺產”中都規定了生態保護的內容。其中,第二卷主要規定了不同生態要素的污染防治內容,附帶規定了各生態要素的生態保護;第三卷側重規定了海岸帶、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等特殊生態區域保護;第四卷主要規定了生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其中在狩獵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要求中規定了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保護的相關內容[35-36]。可見,這些國家生態環境法典有關生態保護內容的結構布局差異較大,生態保護法律規范樣態呈現多元化特征。一些國家并未制定自然生態保護編,而是將生態保護的相關內容放置于其他與之相關的部分,這也與法典化過程中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本土法治資源和法典編纂模式不同有關。
分析中國學界關于自然生態保護編的篇章結構的研究可見,在自然生態保護編應包含的內容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定共識,即應充分重視要素保護、區域保護與系統保護。但是,對于應當以何種邏輯實現對生態要素與生態系統的保護存在一定的差異。如前所述,設置自然生態保護編的目的在于梳理生態立法的邏輯主線,構建完整、系統的生態保護法律制度體系,為生態系統整體功能保護奠定法律基礎。而無論是生態要素保護還是生態系統保護都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內容。以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自然生態保護編的邏輯框架,既符合生態學原理,也能同時實現對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保護。具體而言,在價值層面,生物多樣性強調生態系統的豐度和穩定狀態,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核心的自然生態保護編的篇章結構回應了生態安全的價值需求。在內容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層次包含了系統內的所有構成要素的特征和關聯性,符合生態保護整體性的要求[37]。在邏輯層次上,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遺傳資源多樣性分別從系統內、物種間和物種內3個層面涵蓋了生態系統的整體,可避免生態系統保護和子系統保護的重復規制與交疊。
2. 2 “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框架安排
整體性保護的方法論要求自然生態保護編在貫徹生態環境法典基本理路的基礎之上明確本編側重規制的對象和路徑。生態環境法典的自然生態保護編應明確“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基本框架,并據此作出相應制度安排。
2. 2. 1 “生態環境”的一體三面
環境法通過法律手段協調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調整對象不僅包括了“影響人類生產、生活、生存及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組成的自然環境[38],也包括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進言之,環境法的規制邏輯是法律作用于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繼而反過來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呈現出“人-環境-人”的傳導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基于人類活動的不同類型,法律規制體現在3個層面。其一,法律對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經濟活動的規制,將“資源”這一范疇納入規范視野。因此,對資源的法律規制強調自然環境要素的經濟屬性,對其價值判斷主要關注資源的稀缺性。其二,法律規制人類利用不具有稀缺性的自然物的活動催生出“環境”這一法律范疇。法律上的“環境”范疇側重環境要素對人類非經濟性的利用價值,尤其是與人類生存和生命健康密切相關的環境利用行為是法律上的“環境”的主體內容[30]。其三,生態學將人類視為生態系統的物種之一的視角為法律規制提供了視界基礎。法律中的“生態”范疇強調人的生物物種屬性,側重維持生態系統內部、物種之間、物種內部的平衡狀態[39] 。“資源”“環境”“生態”共同構成了“生態環境”這一環境法律規范的基本范疇,在體系化整合環境法律的過程中,其也成為生態環境法典的基石概念[40]。
“資源”“環境”“生態”分別體現了“生態環境”的不同側面,但在不同的語境下三者可以相互轉化。“資源”與“環境”的區別在于是否著眼于單一的經濟價值。當對“資源”的“利用”活動作擴大解釋時,并非純粹基于經濟價值衡量的資源利用活動將進入“環境”的范疇。例如,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活動可能涉及土壤污染,產生環境健康問題。而提高“資源”“環境”的視角,將其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要素或一個環節看待,則會進入“生態”的范疇。例如,林草資源和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同時也是森林生態保護、草原生態保護、水生態保護的重要環節。與之相對,在“生態”范疇中更多地考慮“人”的需求價值,則會進入“資源”或“環境”的視野。例如,在自然保護地法中規定生態旅游的相關內容時,生態保護與資源利用合而為一。可見,“資源”“環境”“生態”呈現出“一體三面”的特征,它們都是“生態環境”這一范疇在不同視角下的投射。因此,在生態環境法典中,“資源”“環境”“生態”是貫穿整部法典的范疇,只是在不同的規范需求中有不同的側重體現。在污染控制編強調對環境污染的預防和治理,在綠色低碳發展編強調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自然生態保護編強調對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保護。
2. 2. 2 “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理論基礎
自人類步入工業社會以來,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被愈發重視,這使得其本作為商品的經濟屬性被突出強調,直到世界范圍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的不斷加劇,資源所蘊含的生態價值才逐漸被各國所關注和重視。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各國經濟發展模式之中,資源的生態價值的外延也在不斷拓展,甚至由生態價值轉化成為經濟價值,使得“資源”的內涵愈發豐富,資源與環境的邊界也愈發模糊。在法典化視域下,綜合生態系統管理理論所蘊含的生態系統整體性保護方法和一般系統理論所關注的元素與系統的辯證關系為我們結合資源與生態的不同面向、在自然生態保護編中實現“生態-資源”的一體化保護提供了理論支持。
在生態學視角下,綜合生態系統管理(integrated eco?logical management,IEM)理論認為,應將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整體,從長期和可持續的角度看待自然資源,強調自然資源與生態功能之間的關聯,并實施綜合性的生態系統管理[41]。這要求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應考慮生態環境現狀,采取綜合性的措施實現生態保護的目標。以生態功能保護為代表的公共利益逐漸被納入自然資源利用的規制考量中,這導致自然資源法的規制從私益范疇擴大到公益范疇,利用管制的規制理念成為自然資源法的底層邏輯[40,42],生態保護要求被內在地納入資源利用規制之中。
一般系統理論認為,系統整體大于系統部分之和,即整體系統具有部分不具備或不能解釋的特征和性質,只能通過整體視角觀察整體的功能[43]。就生態系統而言,其作為一個復雜系統所具備的特征符合一般系統論的描述。首先,生態系統是圈層構成的。生態圈層既包括生物群落,也包括巖石圈、水圈、大氣圈這些非生物環境。不同圈層相互嵌套和重疊,客觀上不能割裂。其次,生態系統具有尺度性。一個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穩定性,往往依賴于更大尺度上生態系統。這表明,從保護目的出發,生態系統的穩定狀態是資源要素得以持續利用的前提。最后,生態系統具有涌現性,即生態要素聚集成生態系統時會產生新的功能[44]。例如,樹木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森林會涌現出樹木不具備的特征和功能,反之樹木減少一定數量后森林的功能不復存在。這意味著評價資源數量帶來的價值無法剝離生態系統功能的影響。就社會系統而言,人類社會是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的系統,其中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人類社會的存續價值、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無法也不能割裂衡量[45]。因此,資源價值與生態價值不可孤立評價,只有通過一體化保護才能充分保障生態系統的整體功能實現。
將“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作為自然生態保護編的基本思路具有合理性。首先,生態保護與資源利用在理念上存在本質區別,但在規制措施上存在關聯。雖然生態保護的“去中心化”結構和“非人類中心”價值與資源利用的“人類中心”價值傾向存在差異,但在規制邏輯方面,生態破壞與資源破壞具有共性,都是人類向生態環境的過度索求導致的消極后果,指向的客體范圍也存在交疊。例如,對森林資源的破壞也會導致同一區域森林生態的破壞。因此,生態環境法典的資源利用制度同樣以可持續性為根本追求。法典通過規制性和(或)激勵性措施,結合不同資源品種的特性,規定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同樣追求實現生態保護的效果。其次,現行立法中已經規定了“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相關內容。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第14條將資源利用狀況作為制定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的條件,第41條規定了應對氣候變化時區域生態系統、水資源、野生動植物的統籌保護體系。而在實踐中,資源價值也是衡量生態價值的重要依據。例如,自然資源資產核算是生態補償計算和生態價值評估的重要基礎[46]。
因此,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以“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為基礎,在基本范疇方面區分“生態”與“資源”;在理念方面側重“生態保護”而非“資源利用”;在規制措施方面將資源可持續性利用作為生態保護的實現手段。
2. 2. 3 “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的制度安排
在自然生態保護編中,“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可以從規制對象一體化和保護機制一體化兩個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規制對象的一體化。在基本范疇的文本表述方面,立法不應刻意區分資源要素與生態系統。事實上,“生態”與“資源”的外延基本重疊,對某一自然資源的保護就是對該自然資源所在生態系統的保護。因此,立法應盡量減少使用“資源保護”這一術語,代之以更凸顯整體性的“生態保護”。例如,用“水生態保護”代替“水資源保護”。在制度邏輯方面,立法應將規制重點放在維護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上。一方面,貫徹整體性思維應當避免割裂同一區域內的不同生態要素保護。一個區域內的生態系統是天然的地理單元,其系統本身具有局部的穩定性。因此,可以優先以區域為基本單元構建保護機制、管理體系和制度措施。另一方面,基于生物圈的科學特征,應當圍繞生物群落及其棲息地構建保護機制,將制度重點放在維持生物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穩定互動關系上。這進一步要求立法考慮將“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遺傳資源多樣性”邏輯結構納入制度體系中。
保護機制的一體化。“生態”“資源”在立法中需要區分但不能割裂,在具體制度安排中,立法需要更加辯證和精細地處理二者的關系。在原則層面,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確立綜合管理原則,強調生態環境保護、資源可持續利用、特殊區域保護的整體推進,綜合采取各種手段、措施對治理單元內各種自然因素進行統一管理[47]。在具體制度層面,“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應當著重體現在以下幾個制度中。其一,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由于資源與生態系統共處于同一空間,若這一空間的生態遭到破壞,依附于其上的資源將面臨巨大風險。因此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應當考慮納入對該空間內資源開發活動的限度,例如建立占用生態保護紅線區的戰略礦產資源勘探開發、油氣管道基礎設施建設等活動的正面清單[48]。其二,生態環境監測制度。應當從生態系統角度開展生態資源調查和監測,并將其作為實施生態保護和修復的參考指標之一[49]。其三,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的目的是合作共治和共享生態與經濟效益[50]。如前所述,資源價值是生態補償的重要評價標準。因此應當構建資源價值和生態價值的定量機制,充分保障生態價值在法律上的落實。需要注意的是,基于自然生態保護編“生態優先”理念的考量,以資源利用為主的法律制度,例如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能開發利用相關法律規范等不宜納入自然生態保護編。
2. 3 適度法典化模式下的整體性治理進路
目前,適度法典化已經成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模式選擇,這使得自然生態保護編需要綜合考慮適度法典化的立法目的、需求和編纂技術,來構建自然生態保護編的整體框架、作出制度安排,從而實現法典與單行法的有效銜接、法典內部融貫協同的目標。
2. 3. 1 適度法典化的要求
法典化是指將分散的法律規范整合成一部或幾部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的法律文本的過程[51]。這一過程不僅涉及法律文本的編纂,還包括對法律原則、規則的系統化表達,以及對法律關系的全面調整[52]。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是一項宏偉、繁復、艱巨的系統工程,為了更好地契合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實踐現狀與現行生態環境法律體系,采用“ 適度法典化”的編纂方案已經基本成為學界共識[53-56]。
然而,在“適度法典化”具體如何落實方面學界尚未提出統一的完整方案,不同的方案分別有不同的側重點[57]。但是,在整體上采取“雙法源”,即“生態環境法典+單行法”的編纂模式已成基本共識,這也與中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相契合。在此基礎上,就需要對現行生態環境法律規范的基本價值、基本原則、基本制度等內容進行整合提煉,改變分散立法、分別立法帶來的法律沖突和重疊等問題。同時,也需要適當保留部分單行法,對法典中的相關規定予以補充、完善和細化[58]。在“雙法源”模式下,如何厘清適度化邊界,則需要法典具備根據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目標而調整內容的能力,保障法典內容詳略得當[59]。就適度法典化的“體系性”而言,“適度法典化”的重點在于通過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系統性,確保法律體系的適應性[60]。在此基礎上,“體系性”意味著法典編纂在滿足穩定性需求的同時,也要滿足開放性需求,即法典不僅要涵蓋現有立法的主要內容,還需要對其內容進行適時的調整和完善,以適應當下及未來一定時期內生態環境保護的實踐。具體來說,適度法典化應包括內部的體系融貫性和外部的體系協同性兩個方面。
2. 3. 2 法典內部的融貫性
理論上講,法典化的目的在于科學地整理和完善一個領域內的法律材料,形成清晰的表述和邏輯結構[61]。法典應具有內部融貫性,保證法律規范的系統性和體系性。自然生態保護編的內部融貫性不僅是法典編纂的規范性體現,也是生態環境保護整體性思維的體現。內部融貫性體現在理念和內容兩個方面。
在理念方面,自然生態保護編編纂的融貫性體現為將可持續發展和整體性保護的方法論與具體的生態保護法律規范實現有機融合。一方面,可持續發展作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核心價值導向應在生態保護、污染防治、綠色低碳發展的規定內容中貫穿始終。可持續發展要求以生態資源辯證統一的整體自然觀為基礎進行立法。例如,在處理污染防治與生態資源保護的關系時,認識到環境污染是生態與資源面臨的重要威脅,生態破壞是資源開發利用的極大制約。另一方面,自然生態保護編的核心目標是構建契合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法律體系,整體性方法是自然生態保護編編纂的基本方法。整體性治理要求不僅僅關注單一要素或局部區域的保護,而是著眼于整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將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為終極目標追求[62]。因此,為了從更宏觀和全面的角度進行生態保護,避免只注重局部而忽視整體的問題,自然生態保護編的法律規范應當納入生態系統整體的安全、穩定和多樣性保護的相關內容。
在內容方面,自然生態保護編應實現內部自洽,特別是規范內容的完整性和規范對象的不重復性。在整體上,盡可能周延地涵攝生態系統整體,同時避免對生態系統及其子系統的重復規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除了前文所述以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體系邏輯之外,自然生態保護編還應當明確整體生態系統保護的內容。生態系統保護不簡單地等同于各生態要素的簡單疊加。首先,生態系統及其構成要素具有顯著的尺度性特征。例如,在宏觀尺度上,流域是大生態系統,而山水林田湖草等是流域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生態要素;然而,當研究尺度降低時,山水林田湖草等均可視為具體的生態系統。若以各類具體的生態要素類別進行篇章安排,可能會忽視了這一尺度性特征。其次,生態系統的界定并非基于構成要素,而是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生態功能。各生態要素的簡單累加無法全面涵蓋生態系統的功能。因此,生態要素保護的法律規范的加總無法替代專門的生態系統保護法律規范,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納入生態系統保護規范,強調生態系統整體功能的重要性。
2. 3. 3 法典與單行法的體系協同
自然生態保護編的“雙法源”特征,使其編纂的過程中需要著重考慮法典與單行法的協同與銜接適用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大量的生態保護規范規定于自然資源相關法律法規之中,并且由于“生態”與“資源”二者一體兩面的辯證關系,使得適當處理自然生態保護編與單行法的關系尤為重要。在“雙法源”模式下,每部單行法內容都應當具有獨立性和完整性,法典模式不需要特別考慮單行法的領域歸屬,而應著重考慮在內容不重復的前提下如何將單行法的有關內容在不同分編中側重體現[63]。在宏觀層面,自然生態保護編需要考慮在實現生態安全價值的前提下,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式歸納和整理現行法中的共同原則和共性制度,并著重對生態環境法典與保留的單行法和未來的生態保護立法之間有序銜接作出制度安排。在具體法律規范層面,應實現法典與單行法的功能協同,保證法典的形式融貫性和內容完整性,在規范選擇上注意繁簡適度。從法典調整范圍來看,適度法典化強調在確保法典能夠全面覆蓋特定領域的同時,避免過度擴張導致的復雜性和冗余性。這就要求自然生態保護編應聚焦于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落實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治理進路。在法典中主要規定涉及生態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規范,而不細化規定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法律規范。在此基礎上,發揮單行法對法典的補充和細化功能。例如,關于長江、黃河和青藏高原等重點區域的保護,可以通過在法典中設置轉致條款直接適用現行法,從而發揮“雙法源”模式在保障內容的全面性和法律靈活性等方面的優勢。
3 生態環境法典中自然生態保護編的規范路徑
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在“事前預防-過程監管-損害救濟-恢復治理”的制度體系基礎之上,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目標,以“生態系統保護-物種保護-遺傳資源保護”為基本框架,并在制度設計中貫穿生態系統整體治理的理路。
3. 1 自然生態保護編的體例安排
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編纂邏輯可以較為全面地涵蓋生態系統整體,科學地回應生態系統中物種數量和相對豐度的動態變化,避免單一要素層面的保護帶來的漏洞,也可有效規避系統無限細分帶來的重復規制,符合生態系統保護的科學基礎和體系邏輯[64]。因此,構建以“生態系統保護-物種保護-遺傳資源保護”為邏輯線索的自然生態保護編框架,再結合“事前預防-過程監管-損害救濟-恢復治理”的制度脈絡,是自然生態保護編較優的路徑選擇。具體而言,自然生態保護編可劃分為一般性規定、生態系統保護、物種保護、遺傳資源保護,以及生態退化治理和生態修復與補償5部分。
在一般性規定部分可規定以下3方面內容:其一,自然生態保護編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基本理念即實現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基本原則包括生態優先原則、風險預防原則、綜合治理原則等。其二,通用于自然生態保護編的共性制度,例如生態保護規劃、生態標準、生態監測評估等。這一部分可以與總則編生態環境一般性制度相銜接。其三,自然生態保護編與污染控制編、綠色低碳發展編之間的適用關系,明確同一生態要素基于“環境”“生態”“資源”的不同側重。
在生態系統保護部分,可以規定包括生態系統整體保護和現行立法中關于森林、草原、水、荒漠等生態系統子系統保護的相關內容。本部分應特別注意規定關于生態系統整體保護的措施,厘清生態保護與生態退化防治的區別。以荒漠生態系統保護與荒漠化防治為例:荒漠生態系統保護的重點在于從整體上保護荒漠生態系統內在的生態服務功能,關注其間接利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65],相關制度內容直接指向荒漠生態系統功能。而荒漠化防治基于“事前-事中-事后”的邏輯,以人類活動為中心開展沙化土地預防和治理。現行立法側重強調荒漠化防治,出于生態系統保護的整體性要求,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在此基礎之上規定荒漠生態系統保護的內容。體現在制度設計上,可以在本部分內規定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及限制人類活動、荒漠生態補償等具體制度。同時,還應特別關注重點區域保護,即自然保護地、自然生態空間、流域、濕地、水土流失重點防治區域、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高原保護區等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態功能區域。相較于一般區域而言,重點區域的生態問題更為突出,治理要求也相對復雜,因此需要在立法上予以特別關注。在生態區域治理方面應發揮生態環境法典的基本法功能,建立區域協調機制,明確跨行政區域的合作機制,從而為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同時,基于適度法典化的編纂模式和法典容量,這方面內容可以通過設置引致條款的方式,與自然保護地立法(包括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其他自然公園有關立法)、流域立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立法等相銜接。
在物種保護部分,主要強調種群保護,包括外來物種入侵防控、生物群落、放生規制及其棲息地保護等內容。物種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方面,也是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對保障生態系統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法典應當綜合考慮目的符合性、與本編其他制度的關聯性、法制基礎是否成熟等因素,在自然生態保護編中選擇性地納入物種保護的內容[66]。值得注意的是,本部分規定的棲息地保護內容應著重于野生動物植物和生態系統中具有生命成分的自然要素,與關于生態系統保護的內容區分、銜接[67]。
在遺傳資源保護部分,可主要規定遺傳資源惠益分享、數字序列信息規制、生物遺傳資源申報備案和專家評審制度、生物遺傳資源技術來源披露及授權等內容。遺傳資源作為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基礎。遺傳資源保護有別于物種保護,它所關注的重點是生物的遺傳材料和信息,通過對生物遺傳材料和信息的保護來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在此,應注意本部分內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等立法的銜接。
生態退化治理和生態修復與補償在生態保護實踐中密切關聯。生態退化治理的目的在于預防、治理以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為代表的負面生態后果,保障生態安全。水土保持部分的規定應以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以下簡稱《水土保持法》)為基礎,包括水土保持規劃、水土保持方案、預防和減輕水土流失措施、水土流失監測等內容。荒漠化防治部分的內容可以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以下簡稱《防沙治沙法》)為基礎。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制定的時間較早,其中許多制度,例如營利性治沙等,已不適應當下的生態環境保護需求。同時,水蝕荒漠化與風蝕荒漠化在管理體制和制度體系方面存在內在聯系,這一部分內容應綜合考慮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的制度內容,實現制度銜接。生態修復與補償部分的內容應包括生態修復責任的界定與實現機制、生態補償主體的范圍、生態補償的公私關系、生態效益補償費征收、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生態恢復責任形式等。
3. 2 以規范類型化為基礎的自然生態保護制度安排
為了預防生態風險和實現保障生態安全的目的,生態保護規范應包含預防生態損害風險、生態保護、生態修復、救濟保障等方面內容。在明確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主線的篇章框架結構的基礎上,按照功能不同可將生態保護法律制度劃分為預防型、監管規制型、補救保障型、恢復型4類,從而形成以規范類型化為基礎的制度安排方案。
預防型法律制度是自然生態保護編落實風險預防原則的重要路徑,通過制定生態規劃、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明確生態標準以及科學規范資源要素使用等方式,有效防范生態環境風險。預防性方法不僅適用于單一事件的應對,也適用于長期的風險管理以生態保護規劃為例,目前,中國生態保護規劃有40多種,其中包括水土保持規劃(《水土保持法》第10條)、防沙治沙規劃(《防沙治沙法》第10條第1款)、海洋生態修復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保護法》第42條)等生態風險應對類的規劃,也包括全國海島保護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第8條、第9條)、濕地保護規劃(《濕地保護法》第15條)、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相關保護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1款)等生態要素保護類規劃。除此外,落實事前評估機制和區劃制度等規范資源要素利用的機制措施是預防性制度的重要內容。事前評估機制統籌考慮生態要素、生態區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可以系統性研判潛在風險,便于提前制定針對性措施,配合實施生態標準制度,既防范“黑天鵝”事件,也防范“灰犀牛”事件。又如,區劃制度(例如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等重要控制線)可以實現生態保留的目的,為人類活動明確劃定邊界。
監管規制型制度是自然生態保護編落實整體性保護方法論的重要手段,通過對生態狀況、生態利用活動、生態信息等進行全過程監督和管理,避免或者降低生態風險,有利于在生態利用的全程預防生態破壞,確保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監管規制型制度主要包括生態監測制度和生態信息管理制度兩方面內容。其中,生態監測制度是主管部門開展監管活動的基礎。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明確自然生態要素和空間統一確權登記制度,在此基礎上加強統計監測和信息共享,建立覆蓋所有資源環境要素的天地水陸海一體化監測網絡體系和質量預報預警機制,為監管、決策提供準確、完整信息。在此基礎上,生態信息管理制度應當細化規定關于環境信息制度的內容,側重規定有關生態風險、生物多樣性的信息的管理。除此之外,過程監管應明確事權劃分,構建突破行政區域邊界的生態區域協同管理機制,例如城鄉一體監管和執法制度,區域、流域執法聯動機制、協作機制等。
補救型法律制度旨在填補已經發生或可預見的生態損害,避免損害的現實化或損害進一步擴大,例如禁止令制度、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等。補救型法律制度源于民法的停止侵害、消除危險,基于對生態破壞行為的“定價”督促行為人理性開展活動以避免造成生態損害,有利于保證生態風險預防。補救型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證是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生態保護補償是由國家對導致生態功能減損的資源開發利用者收費及對為改善、維持或增強生態功能為目的作出特別犧牲者給予補償,其目的在于恢復、維持和增強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通過對“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的調節,生態保護補償制度不僅以更正義的方式衡平了生態保護責任分配,也有助于激勵生態保護活動。
恢復型法律制度旨在恢復生態系統功能,其核心在于堅持以自然恢復為主,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統治理的理念,分區分類開展受損自然生態系統修復。其中,除傳統的經濟罰和自由罰之外的生態修復法律責任對于生態恢復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破壞生態的行為不是僅僅造成某一環境要素的損害,也造成整體生態環境的不利改變以及提供生態系統服務能力的破壞和損傷。然而,通過一般侵權案件中通常使用的“差額”方法(即通過比較損害前后被侵權人財產數額的差距來確定侵權損害數額)確定的罰款金額和生態補償金額無法充分彌補具體環境要素的不利改變與整體系統服務功能的退化。另一方面,恢復型補救有利于繞開經濟罰的復雜程序,及時補救生態損害。例如,對于未經批準擅自采伐經濟林的行為,除對行為人進行罰款、拘留外,還可要求其對破壞的林木進行更新,履行看管、保護林木的責任;要求行為人研發并向相關部門提供生態恢復或治理新技術來抵扣部分賠償或補償款等。
3. 3 自然生態保護編與其他編的協同
為了實現生態保護規范在法典篇章結構和內容層面的融貫性,實現生態保護的整體性治理,自然生態保護編的生態保護規范需要與總則編、污染控制編、綠色低碳發展編以及生態環境責任編等部分的內容相銜接,從而使生態環境法典各編各司其職,相互銜接配合,形成關于生態保護的全面系統的規范體系。
在總則篇章中,應就生態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作出規定,以此作為自然生態保護編規范展開的基礎。污染控制編主要關注對單一生態環境要素質量下降的預防和治理,并吸收現有的污染防治法,其中可就由環境污染引起生態破壞的相關事項作出原則性的規定,以便自然生態保護編呼應與銜接。自然生態保護編集中就生態保護作出規定,是法典中關于生態保護的主體內容,同時需要與其他編中與生態保護相關的內容實現又與自然生態保護編對生態保護的關注視角不同。在生態環境責任編中,應充分觀照生態保護篇章“雙法源”的特征,在納入適合作為法典法律責任規范內容的同時,為生態保護單行法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留下適度的空間。
4 結 論
生態保護規范在生態環境法典中的適當安排不僅是法典編纂過程中應予重視的重要方面,也是體現新時代生態文明背景下新興法典創新性的重要方面。在基本理路上,自然生態保護編應依循整體性治理進路,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融入其中,將生態系統整體功能保障作為根本目的——由此區別于污染控制編應對生態環境要素質量下降問題,以及綠色低碳發展編關注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和涉碳相關內容。在內容安排上,自然生態保護編應當在明辨“生態”“環境”“資源”三者關系的基礎之上,基于生態保護之主旨,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基本目標,構建基于“事前預防-過程監管-損害救濟-恢復治理”的制度體系。由此,自然生態保護編可基于整體性保護理路,形成系統而完整的生態保護規范體系,全面回應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在生態保護方面的規范需求,為生態文明法治建設提供充分、堅實的法典規范依據。
參考文獻
[1] 呂忠梅. 發現環境法典的邏輯主線:可持續發展[J]. 法律科學
(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2,40(1):73-86.
[2] 李延瑾,徐琳. 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
由之路[J]. 理論月刊,2001(7):50-52.
[3] 朱炳成. 公私法交融下的環境健康權保護[J]. 吉林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2023,63(3):60-70.
[4] 張忠民. 環境法典綠色低碳發展編的編纂邏輯與規范表達[J].
政法論壇,2022,40(2):32-43.
[5] 卓澤淵. 法的價值論[M]. 3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45-51.
[6] 呂忠梅.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最嚴法治”論[J]. 法學,2024
(5):3-20.
[7] 呂忠梅. 環境法典編纂視閾中的人與自然[J]. 中外法學,2022,
34(3):606-625.
[8] 尼克拉斯·魯曼. 生態溝通:現代社會能應付生態危害嗎?[M]. 湯
志杰,魯貴顯,譯. 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19-26.
[9] CHERP A,JEWELL J. The concept of energy security:beyond the
four As[J]. Energy policy,2014,75:415-421.
[10] 寧天琦. 論“雙碳”目標下能源法的秩序價值及其實現[J]. 江
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5(5):46-59.
[11] 曹明德,馬騰. 風險社會中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的變遷[J]. 國外
社會科學,2021(3):58-70.
[12]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EB/OL]. (2014-04-15)[2024-11-06]. https://www. gov. cn/
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 htm.
[13] 唐瑭,王普. 生態環境風險預防原則的法律構造及其功能闡釋
[J].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4(1):72-83.
[14] 于文軒. 習近平生態文明法治理論指引下的生態法治原則
[J].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1(4):5-13.
[15] 劉彤彤. 整體系統觀:中國生物多樣性立法保護的應然邏輯
[J]. 理論月刊,2021(10):130-141.
[16] 戚建剛,蘭皓翔.“中國第二代環境法的形成和發展趨勢”之反
思[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5):52.
[17] 霍爾姆斯·羅爾斯頓. 環境倫理學[M]. 楊通進,譯. 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48-253.
[18] 舒國瀅. 法學的知識譜系[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919.
[19] 尼克拉斯·盧曼. 法社會學[M]. 賓凱,趙春燕,譯.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3:71-73.
[20] 王利明. 法治:良法與善治[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1-13.
[21] 羅伯特·阿列克西,宋旭光. 法的安定性與正確性[J]. 東方法
學,2017(3):134-141.
[22] 于文軒,馮瀚元. 生態文明視域下自然保護地法治體系的完善
[J]. 城市與環境研究,2024(1):41-51.
[23] 呂忠梅. 環境法典編纂研究的現狀與未來[J]. 法治社會,2023
(4):1-11.
[24] 呂忠梅,田時雨,王玲玲.《環境保護法》實施現狀及其法典化
“升級”[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3,33(1):1-14.
[25] 王燦發,陳世寅. 中國環境法法典化的證成與構想[J]. 中國人
民大學學報,2019,33(2):2-14.
[26] 徐祥民. 關于編纂“自然地理環境保護法編”的構想[J]. 東方
法學,2021(6):83-98.
[27] 呂忠梅. 環境法典編纂的基本問題[J]. 荊楚法學,2022(1):
25-40.
[28] 呂忠梅. 環境法典編纂論綱[J]. 中國法學,2023(2):25-47.
[29] 汪勁. 論中國環境法典框架體系的構建和創新:以中國民法典
框架體系為鑒[J]. 當代法學,2021,35(6):18-30.
[30] 鞏固. 環境法典自然生態保護編構想[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
大學學報),2022,40(1):96-105.
[31] 張百靈. 生態空間管控的立法模式與制度體系[J]. 政法論叢,
2022(3):151-160.
[32] 瑞典環境法典[M]. 竺效,丁霖,田時雨,等,譯. 北京:法律出
版社,2018:27-40.
[33] 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和核安全部. 德國環境法典:專家委員
會草案[M]. 沈百鑫,李志林,馬心如,等,譯. 北京:法律出版
社,2021:137-154.
[34] 意大利環境法典[M]. 李鈞,李修瓊,蔡潔,等,譯. 北京:法律
出版社,2021:75-159.
[35] 法國環境法典(第一至三卷)[M]. 莫菲,劉彤,葛蘇聃,譯. 北
京:法律出版社,2018:135-347.
[36] 法國環境法典(第四至七卷)[M]. 莫菲,丁汀,張肖,等,譯. 北
京:法律出版社,2020:3-117.
[37] 秦天寶. 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系統性法律規制[J]. 法學論壇,
2022,37(1):119-128.
[38] 鞏固. 環境法典基石概念探究從資源、環境、生態概念的變遷
切入[J]. 中外法學,2022,34(6):1523-1542.
[39] 郭曉虹.“生態”與“環境”的概念與性質[J]. 社會科學家,2019
(2):107-113.
[40] 呂忠梅. 生態環境法典中的“環境污染”概念辨析[J]. 政法論
叢,2024(2):13-27.
[41] 馬爾特比. 生態系統管理:科學與社會問題[M]. 康樂,韓興
國,譯.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2.
[42] 艾琳·麥克哈格,巴里·巴頓,阿德里安·布拉德布魯克,等. 能
源與自然資源中的財產和法律[M]. 胡德勝,魏鐵軍,譯. 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05.
[43] 馮·貝塔朗菲. 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M]. 林康義,魏宏
森,譯.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30.
[44] 奧德姆. 生態學:科學與社會之間的橋梁[M]. 何文珊,譯. 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24-28.
[45] 王如松,歐陽志云. 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與可持續發
展[J]. 中國科學院院刊,2012,27(3):337-345.
[46] 郭韋杉,李國平,王文濤. 自然資源資產核算:概念辨析及核算
框架設計[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1,31(11):11-19.
[47] 鞏固. 生態系統方法視野下的環境法典編纂:方向與思路[J].
法治研究,2023(3):49-64.
[48] 闕占文,鐘昕益. 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環境法典表達[J]. 法治
論壇,2023(2):199-213.
[49] 陳善榮,董貴華,于洋,等. 面向生態監管的國家生態質量監測
網絡構建框架[J]. 中國環境監測,2020,36(5):1-7.
[50] 潘佳. 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的法典化塑造[J]. 法學,2022(4):
163-178.
[51] 陳金釗. 法典化語用及其意義[J]. 政治與法律,2021(11):
2-16.
[52] 吳勝利. 論我國生態環境法典內在體系的立法融貫[J]. 法學
評論,2024,42(4):171-181.
[53] 張梓太. 中國環境立法應適度法典化[J]. 南京大學法律評論,
2009,(1):239-245.
[54] 李艷芳,田時雨. 比較法視野中的我國環境法法典化[J]. 中國
人民大學學報,2019,33(2):15-28.
[55] 于文軒,牟桐. 生態文明語境下環境法典的理性基礎與法技術
構造[J].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49(6):11-16.
[56] 李摯萍. 中國環境法典化的一個可能路徑:以環境基本法為基
礎的適度法典化[J].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2(5):18-30.
[57] 羅麗. 論我國環境法法典化中的若干問題[J]. 清華法學,
2023,17(4):92-105.
[58] 呂忠梅. 中國環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選擇及其展開[J]. 東方法
學,2021(6):70-82.
[59] 張梓太,包婧. 中國需要一部怎樣的環境法典:再論環境法的
適度法典化[J]. 探索與爭鳴,2024(6):34-45.
[60] 程飛鴻. 環境法適度法典化:立法限度、規范表達與教義學構
造[J]. 政治與法律,2023(6):110-126.
[61] MANFRED W,丁曉春. 民法的法典化[J]. 現代法學,2002,24
(3):137-138.
[62] 岳小花. 環境法典編纂背景下區域性生態保護立法的體系化
路徑[J]. 河北法學,2022,40(11):119-138.
[63] 胡靜. 土壤污染防治規定的法典表達[J].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24,54(3):113-123.
[64] DíAZ S,MALHI Y. Biodiversity:concepts,patterns,trends,and
perspectives[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22,47:33.
[65] 劉玉龍,馬俊杰,金學林,等.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方法
綜述[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15(1):88-92.
[66] 于文軒,胡澤弘. 論生態文明視域下的生物多樣性法制體系化
[J].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49(5):
37-45.
[67] 魏世婧,柯堅. 試論生物安全“入典”之立法選擇與規范表達
[J]. 中國環境管理,2022,14(5):104-111.
(責任編輯:閆慧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