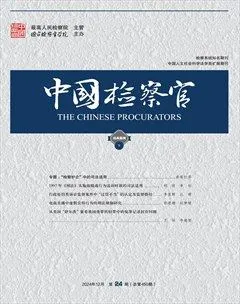電商直播中虛假宣傳行為的刑法規制研究
摘 要:隨著電商直播帶貨的迅猛發展,虛假宣傳等直播亂象也日益突出,嚴重損害了消費者權益。虛假宣傳行為大多體現為宣傳行為的夸大、欺騙,在認定上存在行政違法行為還是刑事犯罪行為的重大區別,但因入刑標準尚未統一,司法實踐中極易混淆。同時,針對新興行業電商直播中的帶貨行為能否認定為廣告行為,也具有較大爭議。為此,要綜合考察電商主播等人員的主觀認知、虛假宣傳內容、虛假宣傳程度等,把握電商直播帶貨過程中虛假宣傳行為的本質屬性,準確區分虛假宣傳行為類型,以罪與非罪考察為基礎,此罪與彼罪審查為重點,對電商直播中虛假宣傳行為予以精準定罪量刑。
關鍵詞:電商直播 虛假廣告罪 詐騙罪 違法所得認定
一、基本案情
2023年5月,因珍珠直播行業火爆,余某組織周某某、舒某、林某等人從外省趕至浙江省諸暨市山下湖鎮,出資組建網絡直播團隊以“開盲盒”方式銷售珍珠,客戶下單后即在直播間現場為客戶開蚌取珠。為提升銷量,余某安排林某采購統珠(稱重計價的珍珠)和不含珍珠的肉蚌后,讓周某某、舒某等主管安排主播用無珠肉蚌冒充珍珠蚌,在直播過程中利用手法將事先準備好的珍珠塞入肉蚌后現場開蚌取出珍珠,并在直播過程中宣稱珍珠是盲剖所得。為提高直播間利潤,余某又讓周某某在其負責的直播間安排人員偽裝貨主,在直播過程中虛構貨主回收的場景,同時反復制造盲開珍珠蚌獲得大直徑珍珠的情形,并讓“貨主”在直播間承諾回收,通過上述方式進一步提高所謂“珍珠蚌”的價格,變相達到高價銷售珍珠的目的。至2023年7月被查獲時止,余某、舒某、周某某等人以上述虛假宣傳方式直播銷售得款共計人民幣約130萬元,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50萬余元。最終,法院判決認定余某等人構成虛假廣告罪。目前判決已生效。
二、分歧意見
電商直播指的是互聯網直播技術,在網絡上將商品進行展示、推廣和銷售的過程。它是傳統電商和直播技術相結合的產物。[1]隨著電商直播帶貨日益火爆,直播亂像頻發,其中以虛假宣傳現象最為突出。因直播帶貨是近幾年崛起的新興產業,相關理論研究、司法實踐均處于初級階段,故如何界定電商直播過程中的虛假宣傳行為也成為當前司法實踐中的新難點。關于本案的定性,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余某等人在直播過程中使用虛假營銷模式,但余某等人銷售的均是真實的珍珠,并非是假冒珍珠。故余某等人的直播帶貨行為并非是全部的虛假、欺騙,故余某等人的行為應當屬于《民法典》中的不誠信行為,是一種行政違法行為,而并非是刑事犯罪行為。
第二種觀點認為,余某等人在直播間內以蚌內含有珍珠為由進行銷售,客戶下單的核心理由是蚌內開出高價珍珠的概率,類似于賭博。而事實上因為蚌內沒有珍珠,余某等人實際上可以百分百控制開蚌結果,類似“殺賭”,客戶完全沒有開出高價珍珠的可能性,故余某等人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涉嫌詐騙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余某等人客觀上交付了有價值的珍珠,其主觀上的非法占有故意不明顯,但鑒于余某等人直播銷售珍珠有虛假宣傳的行為,情節嚴重,破壞了廣告經營的管理制度,涉嫌虛假廣告罪。
三、評析意見
分析上述三種觀點,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表現為電商直播帶貨過程中的虛假宣傳行為是否應當入罪,以及能否認定為刑法中虛假廣告罪的“虛假宣傳”以及詐騙罪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筆者認可第三種觀點,余某等人在直播銷售過程中存在虛假宣傳行為,嚴重損害了正當的商品交易活動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破壞了廣告經營的管理制度,應當予以嚴厲打擊。但余某等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故意不明顯,其行為不宜認定為詐騙罪。結合余某等人直播過程中的虛假宣傳行為,應認定為虛假廣告罪。具體分析如下:
(一)行為違法性判斷:區分過失型、夸大型、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類型,判斷行為有無違法性
當前,電商直播帶貨中存在的虛假宣傳行為大部分是依據《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予以行政處罰。《廣告法》第28條、《反不正當競爭法》第8條中關于虛假廣告、虛假宣傳等內容的描述與虛假廣告罪中的虛假宣傳行為、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等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處,司法實踐中極易混淆。
在司法實踐中,直播帶貨中的虛假宣傳行為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過失型虛假宣傳行為;二是夸大型虛假宣傳行為;三是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對于過失型虛假宣傳行為,因電商主播等行為人在宣傳過程中不具備明顯的虛假宣傳的主觀故意,很可能其本身也是被欺騙的,故一般不認為其構成違法,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夸大型虛假宣傳行為、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的行為人均具有明顯的主觀故意,在造成社會危害的情況下,應當認定其行為具有違法性,需要予以行政或者刑事處罰。本案中,余某、舒某、周某某等人以“開盲盒”形式博取流量,虛構蚌內含有珍珠并利用手法將珍珠塞入不含珍珠的肉蚌內,并對開蚌所得珍珠的年份、品質進行夸大宣傳,欺騙和誤導廣大消費者,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損害了正當的商品交易活動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破壞了廣告經營的管理制度,具有違法性,應予以處罰。
(二)入罪必要性考察: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具有刑法意義上的社會危害性,需納入刑法規制范圍
在肯定虛假宣傳行為具有違法性之后,就需要探討此種虛假宣傳行為是否應當納入刑法規制。大部分虛假宣傳行為均為行刑交叉行為,既有可能構成行政違法,也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升格為刑事犯罪行為。筆者認為,考量具體的虛假宣傳行為是否應當入罪,應當結合虛假宣傳行為的本質屬性進行實質判斷。
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是指對電商直播所售賣產品的性能、功能、質量等本質、關鍵性內容進行欺騙、誤導的一種行為;夸大型虛假宣傳行為主要是指對產品的銷售情況、用戶評價、品牌效力等非關鍵性信息進行夸大、虛假宣傳的虛假宣傳行為。一般而言,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對于產品本身有不同程度的虛假宣傳,其虛假宣傳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并非是廣告本身的虛假性,而是在于虛假宣傳的產品有極大可能對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對某一行業的發展造成嚴重損害,足以撼動產業的誠信體系;而夸大型虛假宣傳行為則是對產品的用戶評價、品牌、產地等非關鍵性信息進行夸大、虛假宣傳,雖然會對消費者造成一定的誤解,但上述誤解的產生并不會對消費者的身心健康、行業發展等造成嚴重損害。
故筆者認為,夸大型虛假宣傳行為中均是圍繞產品非關鍵性信息展開,主觀惡性較低,并未嚴重影響人民群眾身心健康、行業發展,社會危害性不大,不具有刑法學意義上的社會危害性和應受懲罰性。而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緊緊圍繞產品本身,其虛假內容往往針對是消費者核心需求,極易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應當予以嚴厲的刑法打擊。本案中,余某等人通過虛假開蚌、虛構大直徑珍珠回收等固定直播營銷方式吸引客戶眼球獲取不正當利益,余某等人的虛假宣傳行為對珍珠品質、來源等等多個關鍵信息予以欺騙,本質上屬于欺騙型虛假宣傳行為,屬于刑法犯罪行為,應當納入刑法規制。
(三)罪名辨析:電商主播虛假宣傳行為構成詐騙犯罪還是虛假廣告犯罪
虛假廣告罪與詐騙罪在主客觀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區別關鍵在于詐騙罪是無中生有,即通過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欺騙被害人,從而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財物;而虛假廣告罪則是通過廣告對真實存在的商品或者服務進行虛假宣傳。筆者認為,本案中余某等人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虛假廣告罪,不宜認定為詐騙罪。具體分析如下:
1.余某等人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首先,客觀方面,余某等人的虛假宣傳行為并非是詐騙罪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本案中,余某在直播銷售珍珠過程中虛構的事實主要為虛構蚌內含珍珠以及所銷售珍珠來自于蚌內,但其交付給消費者的仍然為珍珠,并不存在以淡水珠冒充海水珠、將十分劣質不具有價值珍珠冒充精優珍珠等其他詐騙行為。故余某等人在直播銷售珍珠過程中僅存在部分虛假宣傳的行為,而若認定余某等人構成詐騙罪,則要求余某等人對于交易的核心內容予以虛假宣傳,從而騙取客戶財物。但余某等人實際銷售是真珍珠,這與客戶花錢開蚌購買珍珠的本質目的相吻合。故筆者認為,余某等人的虛假宣傳行為并非是詐騙犯罪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
其次,主觀方面,余某等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明顯。本案中,余某等人直播所銷售的珍珠均系通過正規途徑批發采購,系有價值的真珍珠,案發時珍珠的進購價已經累計至33萬余元。主觀方面,余某等人采用虛假宣傳方式是為了提高直播間流量,促成交易,并非是為了騙取客戶財物,故余某等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故意不明顯。
最后,犯罪數額方面,詐騙金額難以認定。本案中,余某等人雖然能完全控制直播間開出珍珠的好壞概率,但其交付客戶的珍珠確實屬于有價值的珍珠。若認定余某等人的虛假宣傳屬于詐騙行為,在計算余某等人詐騙金額時則存在難點。珍珠作為一種飾品,珍珠的定價系依據珍珠的顏色、光澤、質地、性狀等綜合制定,沒有統一的市場定價,且隨著市場行情起伏較大。故無法簡單依據珍珠銷售價格與進購價格的差額直接認定余某等人的詐騙金額。
2.余某等人的行為構成虛假廣告罪。虛假廣告罪是指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行為。電商直播帶貨中虛假宣傳行為頻發,但因傳統刑法理論限制,電商直播能否認定為廣告以及電商主播是否符合虛假廣告罪的主體身份存在較大爭議。但筆者認為,余某等人的行為構成虛假廣告罪。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電商主播帶貨行為符合“廣告”的本質屬性,應認定為“廣告”。目前,虛假廣告罪的刑罰規制仍然停留在傳統形式廣告上,無法有效規制新型電商直播帶貨主播的虛假宣傳行為。對于電商主播帶貨行為是否屬于“廣告”的法律性質爭議,主要集中在商業廣告論、導購論、新行為模式論和不確定論方面[2],爭議較大。筆者認為,判斷電商主播帶貨行為是否屬于”廣告”,應當從廣告的本質屬性出發來予以探討。“廣告”是指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者承擔費用,通過一定媒介、形式直接或間接地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或者所提供服務的商業活動,故“廣告”應當符合傳播性、商業性、介紹行為三個屬性。傳播性指的是廣告傳播需要借助媒介。商業性指的是傳播人員以獲得商業利益為目的。介紹行為建立在傳播性的基礎上,指的是對相應受眾有介紹產品或者服務的行為。電商主播的直播帶貨行為是電商主播利用自身影響力、觀眾基礎,通過直播對商品進行介紹、推銷的商業推廣行為。電商主播在直播平臺帶貨期間,直播平臺對外公開,符合“廣告”要求的傳播性;直播帶貨需要電商主播對商品、服務進行介紹、測評等,符合“廣告”要求的介紹行為;同時,電商主播帶貨會獲取提成、推廣費等商業報酬,符合廣告的商業性。綜上,筆者認為應當認定電商主播帶貨行為屬于廣告。本案中,余某等人在公開的直播平臺銷售珍珠,在銷售過程中對珍珠的年份、光澤等性狀進行介紹,且能通過珍珠銷售獲得相應報酬,應當認定為“廣告”。
其次,電商主播屬廣告經營者,系虛假廣告罪的適格主體。虛假廣告罪是身份犯,包含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三個犯罪主體,單位也可構成本罪。“廣告主”是指為推銷商品或者提供服務,自行或者委托他人涉及、制作、發布廣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廣告經營者”是指接受委托提供廣告設計、制作、代理服務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廣告發布者”是指為廣告主或者廣告主委托的廣告經營者發布廣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本案中,余某等人系在某購物平臺上店鋪并開通直播間,招募主播團隊委托其在直播間對珍珠進行將介紹、推廣、銷售,而主播接受委托獨屬于其個人的直播間或直播頻道內進行商業推廣,該直播間的所有直播內容由該主播控制和產生,主播在直播間的商業推廣行為使得直播內容成為實質上的商業廣告。故余某等人符合廣告主身份,余某等人團隊內的電商主播符合廣告經營者身份,均系虛假廣告罪的適格主體。
最后,虛假廣告犯罪的違法所得數額應當扣減必要支出,且應達到“情節嚴重”要求。依據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67條的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實務中,違法所得認定是否需要扣除生產、銷售成本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在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時,應當扣除購買原材料等直接用于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必要支出。本案中,在認定余某等人的違法所得時,扣除了余某等人進購珍珠、肉蚌等必要支出,但對于余某等人為提高直播間流量等支付的引流費用等非必要支出則不予扣除,最終認定該案的違法所得數額為50余萬元,達到虛假廣告罪的情節嚴重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