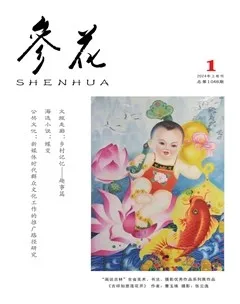鑼鼓咚咚鏘
侯健康
鄉人婚喪嫁娶,每每要把鑼鼓班請進門來,喜慶熱鬧一番。一套鑼鼓班一般由七至八人組成,圍一張方桌,坐四條板凳,各執一樂器,咚鏘咚鏘咚咚鏘,邊打邊奏邊演唱,并不化妝,一人演幾個角色。唱的劇目多半是傳統小戲,諸如《樊梨花》《薛仁貴征東》《劉海砍樵》之類,有段時期,也盛行過《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現代京劇。若辦喪事,有人來吊孝,則停戲奏哀樂,一個個煞有介事,靈前有戚戚之容,戲前存融融之意。
說起來,我跟鑼鼓有些緣分。記得小時候,我們村有鑼鼓班,當時村里沒有電視,聽不到歌曲,半年也難得看上一場電影,那鑼鼓咚咚鏘聽起來便覺新鮮。出于好奇,我跟著一幫孩子常湊了去,里三層,外三層,圍得滿滿的,口里不時也跟著“鏘鏘嘁鏘嘁,鏘鏘鏘鏘嘁鏘嘁”地念叨。因爹是我們村這塊小天地的頭,鑼鼓班的人都認得我,有位唱小生的大哥,還常把我拉到他的身邊,手把手地教我打鼓、拉胡琴,還教我唱些花腔小調。
上了中學,圍觀鑼鼓班就不是單純的好奇了,聽著那鏘鏘之聲,就仔細琢磨其跌宕起伏的節奏;欣賞那悠悠的小調,便細細地品味其優美動聽的旋律;聽著那一環套一環的韻白,便努力去融會唱本的情節和故事,一聽就是大半夜甚至通宵。于是,心里頭就萌發了長大學打鑼鼓的念頭。與幾個伙伴一商議,大家都極感興趣,并推我為頭,定好誰當鼓手,誰吹喇叭,誰唱花旦小生。無意間將我們的打算透露給了爹,沒想到他老人家很贊賞。可學鑼鼓得置樂器,要花好幾百塊,錢從哪里來呢?村后有塊荒地,水源方便,爹叫我們就在這塊荒地上打主意。我們明白了,這塊荒地可開墾成水田,開成水田后就可以種糧食,收了糧食賣了不就有錢了嗎?從此,每天放學后,我們八九個伙伴把時間都花到了這塊荒地上。
可是,田還沒開成,我就進城念了高中,落下的活兒就只得由伙伴們干了,這牽頭的任務我也交給了德林哥。我在城里念書的日子里,不時要給德林哥去信,問起開荒造田的事。當年寒假回去,只見德林哥已帶領伙伴們把田開成了,方方正正,有五分多的面積。翌年他們就在開荒的田里種了水稻,打了百多斤稻子。第三年,打了九百多斤。這千多斤稻子賣出去,也有四百多塊錢,按當時的價格,這就夠買一套鑼鼓班的樂器了。
我高中畢業前,要迎接升學考試,一學期沒回過家,也沒跟德林哥他們聯系。大概是離高考還有個把月的時候,德林哥進城來,說是錢夠了,特意來購買鑼鼓器材,還說請師傅的錢村里面答應出,理由是成立鑼鼓班也是為了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 也是宣傳工作的需要。至于那開墾的新田,已經交給村里了。為紀念鑼鼓班的娃娃們,田的名字定為“鑼鼓方丘”,寫入了田冊簿。德林哥還捎來爹的話:“打就的草鞋生新的命,讀書莫霸蠻,別傷了身子,爹當了一輩子的農民活得一樣痛快,考不上大學就回家學打鑼鼓。”當時,我為爹的處世哲學困惑過好一陣子,這樣一位農民為何在他三十多年村干部的生涯中,竟然維系了全村千多號人的生存與安定。當然,現在我開始明白,那其實是一種普通人的信仰在支撐著爹的事業,這是題外話。
遺憾的是,命運并沒有安排我去學打鑼鼓,而是將我差使到了一所市里的師范學校。這時我想:恐今生再也沒有進鑼鼓班的福分了。讀了幾年書,被分配到一所鄉村學校當了“孩子王”。于是,我人生的步履也就固定在了辦公室至教室這條五十米的小道上,周而復始地往返。可是,德林哥們偏沒有把我這個老伙計忘懷,有時附近有人家請鑼鼓班,總要三番五次地將我邀了去,幫他們添個鈔唱個小生什么的,湊個熱鬧。但我終究不敢放肆,本來教務繁忙,無暇應酬,自己畢竟得以教為本,報效祖國。所以,他們的盛情還是常被拒絕,一個學期也難得湊上一次熱鬧,實際上我與鑼鼓幾乎絕緣。
眨眼幾十年過去了。前一陣,社區組織開展文明創建活動,說是要成立一個鑼鼓班子,一則配合社區開展各項宣傳教育活動,二則社區里有人籌辦紅白喜事可以就湯發面,不用另請鑼鼓班子了。社區人才濟濟,這鑼鼓班說成就成了,但少個鼓手,我這昔日與鑼鼓的緣分便派上了用場。早些天,社區舉辦“文明創建文藝會演”,我們鑼鼓班登臺獻藝,臭美得還真有點飄飄然。由此我聯想到,百姓自有百姓的快活,事業上銳意進取為上,心態上順其自然、隨遇而安為好,心里頭又多了幾分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