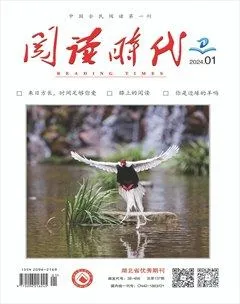來日方長,時間足夠你愛
劉慈欣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個炎熱的傍晚,大人們都在外面搖著扇子聊天,家里只有我一個人在流著汗看書——我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說,凡爾納的《地心游記》。如癡如醉中,書從我手中被拿走了,是父親拿的。我當時有些緊張,因為前幾天看《紅巖》被他訓斥了兩句,還把書沒收了。但這次父親沒說什么,默默地把書還給了我。
就在我迫不及待地重新進入凡爾納的世界時,已經走到門口的父親回頭說了一句:“這叫科學幻想小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影響了我一生的名詞,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驚訝,我一直以為書中的故事是真的!凡爾納的文筆十分寫實。“這里面,都是幻想的?”我問道。“是,但有科學根據。”父親回答。就是這三句簡單的對話,奠定了我以后科幻創作的核心理念。
以前,我都是把1999年發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說作為自己科幻創作的開端,其實,我自己的創作歷程要再向前推20年。在1978年我寫了第一篇科幻小說,是一個描寫外星人訪問地球的短篇。在結尾,外星人送給主人公一件小禮物,是軟軟的可以攥在手中的一小團薄膜,外星人說那是一個氣球。主人公拿回去后向里面吹氣,開始是用嘴吹,后來用打氣筒,再后來用大功率鼓風機,最后把這團薄膜吹成了一座比北京還大的宏偉城市。我把稿子投給了《新港》,然后石沉大海沒了消息。
在發表《鯨歌》前的這20年中,我斷斷續續地寫作。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由我和父親那三句對話所構成的傳統科幻理念已經開始被質疑,然后被拋棄,新的觀念大量涌入。
我感覺自己是在獨自堅守著一片已無人問津的疆土,徘徊在空曠的荒野中,偶爾路過一處野草叢生的廢墟,那種孤獨感仍記憶猶新。在最艱難的時候自己也曾想過曲線救國,寫出了像《中國2185》和《超新星紀元》這樣的東西,但在意識深處仍在堅守著那片疆土。后來我放棄了長篇小說的寫作,重新開始寫短篇,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幻理念上來。
開始在《科幻世界》上發表作品后,我驚喜地發現,原來這片疆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空曠。科幻文學在中國有著不尋常的地位,作為一個類型文學體裁,它所得到的理論思考,所受到的深刻研究和分析,所承載的新觀念新思想,都遠多于其他的類型文學。沒人比我們更在意理論和理念,沒人比我們更恐懼落后于前衛,于是,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
獲得雨果獎后的一個月里,我有機會與更多領域和階層的人談科幻,更感覺到這件怪事的存在。科幻界和學術界談的科幻,與界外的人們談的科幻,幾乎不是同一種東西。
曾經有一位著名作家說過,以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是一塊磚一塊磚地壘一堵墻;而現代文學和后現代文學則是一架梯子,一下子就能爬到墻頭的高度。這種說法很好地描述了科幻界的心態。我們總想著要超越什么,但忘了有些東西是不能越過的,是必須經歷的,就像我們的童年和青春,不可能越過這些歲月而直接走向成熟。
經過一個由偏執走向寬容,由狂熱走向冷靜的過程,我后來意識到科幻小說有許多種,明白科幻小說中可以沒有科學,也可以把投向太空和未來的目光轉向塵世和現實,甚至只投向自己的內心。每一種科幻小說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能出現經典之作。
但與此同時,那三句對話所構成的核心理念在我心中仍堅如磐石,我仍然認為那是科幻文學存在的基礎。雖然走了一百年,中國科幻文學至今也是剛啟程,來日方長,時間足夠你愛。
(源自“青年博覽”,王傳生薦稿)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