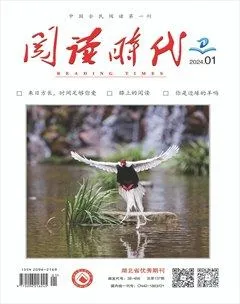踏著月光上路
李文山

萬籟俱寂的深夜,只有我踏著月光上路。
鄉(xiāng)村的曠野歸于平靜,房屋的燈火也不再眨巴眼睛。我一個人從徒有四壁的斗室出發(fā),孤零零地走在興隆河堤上,手里拿著一封信,盡顯旁若無人的恣意。
準(zhǔn)確地說,我不是在投遞一封信,而是要去與一個夢中的詩人幽會,這個詩人就是何其芳。當(dāng)然,在這個1978年的秋夜,我根本不認(rèn)識何其芳,也不知道這個可敬的詩人已在一年前溘然長逝。
“幽會”源于我的初戀。我和當(dāng)時的女友同窗四載,但她屬城鎮(zhèn)戶口,我是農(nóng)家子弟。同樣是高考落榜,她能進入城鎮(zhèn)謀一份比較體面的工作,而我卻只能回到搖搖欲墜的人民公社種田打土塊,我們只得忍痛分手。
女友掏出一支鋼筆和一本薄薄的舊書,在舊書上方留白處龍飛鳳舞地寫了幾筆,遞給我說是作個紀(jì)念。我接過來一看,書沒有封面也沒有封底,書頁已經(jīng)泛黃,只不過上面多了她那熟悉而雋秀的字跡。這是一首四行新詩,帶有那個時代的明顯特征:“茫茫大海任友行,大風(fēng)大浪好征程。不做燕雀學(xué)鯤鵬,展翅高飛入九重。”
如果我不甘心成為一只蓬間雀,我就必須練就一番直入九重的本領(lǐng)。而正是捧讀這一本女友留給我的舊書,讓我做起了一個鯤鵬夢。
彼時的中國,“文化啟蒙”思潮成為主流,詩歌創(chuàng)作也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期。躬耕壟上之余,在昏暗如豆的煤油燈下,我捧讀這本無頭無尾的舊書,讀到了一首題為《預(yù)言》的詩:“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于來臨!/呵,你夜的嘆息似的漸近的足音/我聽得清不是林葉和夜風(fēng)私語,/麋鹿馳過苔徑的細(xì)碎的蹄聲!/告訴我用你銀鈴般的歌聲告訴我,/你是不是預(yù)言中的年輕的神?……”
詩人說這是他19歲時寫下的對自己愛而不能得的初戀的“預(yù)言”,而讀到《預(yù)言》時我只有16歲,總覺得這是詩人寫給我自己愛而不能得的初戀。
沐浴著詩人的《預(yù)言》《季候病》《夜歌》《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和《我們最偉大的節(jié)日》,我開始了自己展翅高飛的夢想。
一份份帶著原始沖動的稿件,就這樣一夜夜地踏著月光上路。夜雨連綿不便出行,月黑風(fēng)高我也不會投稿,我總是等待著皓月當(dāng)空的子夜或是繁星滿天的三更出發(fā)。
這是一段幾乎渺無人煙的僻路,皎潔的月光透過樹丫枝葉的縫隙篩落在地面上,儼然躍動的片片銀箔。松軟如毯的路旁,多是鳴唱的蛐蛐,偶爾還有土蛤蟆之類的小活物跳出來助興。
踏著月光上路,這便是我鄉(xiāng)村生活中最美妙最愜意最幸福的時光。
月華如水,如冰雪之色。我的肩頭有一片月,我的腳下也有一片月,我的前方依然是一片月,我就在月光下做著我癡癡的夢。
異想天開是要付出代價的。家里窮得常常揭不開鍋,做詩人夢也沒有溫床。稿紙匱乏,真正是“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我就把別人扔掉的煙盒當(dāng)成寶貝;買不起一分錢一個的信封,就用別人丟棄的水泥袋紙自己糊,或者在接到編輯部回函后將信封翻轉(zhuǎn)過來反復(fù)使用;八分錢的郵資在我看來比天還大,好在當(dāng)時向大小報刊寄發(fā)稿件都不需要粘貼郵票,郵政工作者的無私付出,讓我的思想天高地闊。
最初的寫作,都是那些稚嫩而粗糙的文本。因此,我癡癡的詩人夢,總是在早晨醒來時破滅,當(dāng)然也有再踏著月光上路的夜晚。
“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也許是經(jīng)歷了太多的失望,上蒼給予了我些許慰藉。1980年3月,有感于“林業(yè)部門今天栽,水利部門明天毀”的亂象,我以《盲目治水園林荒蕪》為題寫了一封“農(nóng)村來信”寄往北京。后來無意間發(fā)現(xiàn),我的這一篇報道綻放在了《人民日報》的枝頭。
“有心栽花花不發(fā),無心插柳柳成蔭。”從此,我的新聞作品一發(fā)不可收拾,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開始小有斬獲。大隊黨支部發(fā)現(xiàn)我是一個能寫材料的筆桿子,就在當(dāng)年金秋讓我當(dāng)上了民兵連長,繼而改任團支部書記。次年7月,我的一個記者朋友將我在文學(xué)道路上的努力記載下來,發(fā)表在地區(qū)黨報副刊上,標(biāo)題是借用的歌德的一句詩:“如果是玫瑰,它總會開花的。”
這篇文藝通訊登載不久,鄰縣撤縣設(shè)市繼而升格為地級市,草創(chuàng)的報社求賢若渴,馬上向我伸出了橄欖枝。但后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還是沒有去成,他們給我寄來了袁枚的絕句相勉:“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xué)牡丹開。”
秋風(fēng)蕭瑟的時候,人民公社走到了盡頭。也就是在這年冬天,我因為“還能夠在報刊上寫幾句話”奉命組建鄉(xiāng)文化站。1989年初,鄉(xiāng)鎮(zhèn)機關(guān)要在村干部中招聘國家干部,我從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是年7月,我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0月,我終于如愿以償進入國家干部序列。
借助書籍的羽翼,我飛過了茫茫大海;在鋪滿月光的路上,走了將近11年。回過頭來,我才弄明白,那首題為《預(yù)言》的詩歌作者名叫何其芳。何其芳——何其芬芳,何其美好,何其令人陶醉啊!他的名字本身就散發(fā)著詩意。難怪這個出生于重慶萬州的“公子哥”會不負(fù)眾望,由新月派詩人成長為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摷遥梢粋€學(xué)者而崛起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
詩人有幸,我當(dāng)時讀到的是他的論文集《詩歌欣賞》,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付梓,而我恰巧是在這一年呱呱墜地。何其芳為什么會選擇在這個時候?qū)懴逻@么一本書?是不是在冥冥之中他的命運與我也有一種別樣的交集?
五年后又是一個春天,我奉調(diào)進入復(fù)刊不久的市報,從普通記者做起,兩年后以“全省十佳”業(yè)績競得記者部主任,而后躋身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屆記者節(jié)表彰之“百名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龍虎榜,出任報社副總編,再任副社長,成為本地新聞界首屈一指的“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
聞歌生悲,我的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為詩人祝福,為自己祈禱。雖然與何其芳失之交臂,我卻覺得自己是他神交已久的嫡傳弟子。
踏著月光上路,月光為我照亮了我與詩人幽會的路:
“如今我悼惜我喪失了的年華,/悼惜它如死在青條上的未開的花。/愛情雖在痛苦里結(jié)了紅色的果實,/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難撿拾。”
月華如水,如冰雪之色。我的肩頭有一片月,我的腳下也有一片月,我的前方依然是一片月。與何其芳先生幽會,我還在月光下繼續(xù)做著我癡癡的詩人夢。
責(zé)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