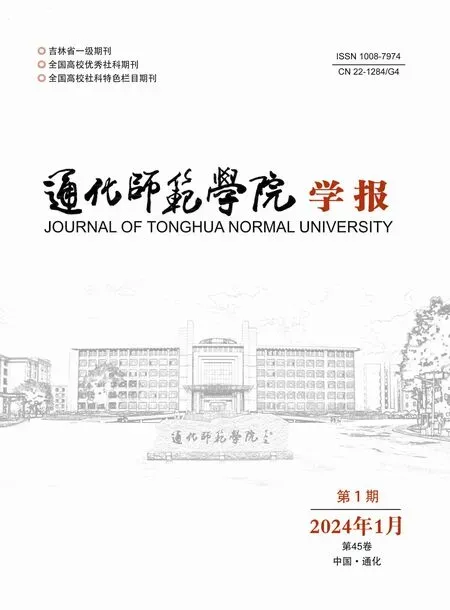長白山滿族刺繡特征與流變研究
王 紀
一、滿族刺繡溯源
長白山是滿族的發祥地,這里至今留存著滿族原生刺繡。公元1125年,女真族滅掉遼國,建立后金。女真人冬季穿皮衣御寒,在與漢族經濟文化的交流中,畜牧業、紡織業不斷發展,用布作為服裝面料逐漸成為主流。《大金國志》記載:“金俗好衣白,……土產無蠶桑,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粗細為別。非皮不可御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纻絲、錦衲為衫裳。亦間用細皮、布。秋冬以貂鼠、狐貉或羔皮,或作纻絲綢絹。貧者春秋并衣衫裳,秋冬亦衣牛、馬、豬、羊、貓、犬、熊、蛇之皮,或獐、鹿、糜皮為衫,褲襪皆以皮”[1]553。從這些記載可以知道金代女真人皮革制衣十分普及,也已經開始使用布帛縫制的服裝。
皮革服裝、器物上縫繡,在今天的滿族人生活中已經罕見。而生活在東北的少數民族鄂倫春族因1953 年才下山定居,食肉衣皮的習俗延續時間較長,所以還保留著皮革縫繡工藝。該工藝以皮革剪縫作為紋飾,采用釘線繡的方式固定。線是用鹿、狍子等動物身上的筋捻搓而成,結實耐用,也有用動物毛做成的線條,用筋線釘縫。至今滿族大量留存著用布帛剪、縫的服裝及掛飾,也都體現出了釘縫的方法和思維(見圖1、2)。

圖1 鄂倫春族積攢搓線用的狍筋

圖2 鄂倫春族保存的熏皮子防蛀用的黃色朽木
皮革縫的典型工藝是點縫。點縫即上下走針,形成點狀痕跡,隨縫制疏密產生節奏變化。該方法在狩獵民族服飾上仍可見到,如鄂倫春人皮衣上經常可見此種仿生針跡,這也是一種仿生學觀察方法的體現(見圖3、4、5)。比如,鄂倫春族老人見到鼠足在雪地上留下的清晰腳印,就會聯想并說到縫制的針法。滿族在今天的布帛刺繡中對該方法有大量沿用,并形成了種類豐富的表達方式。

圖3 鄂倫春族狩獵皮革服裝衣邊采用“仙任”點狀針腳的繡法

圖4 “仙任”繡法來自于對山林動物腳印的觀察
在滿語發音中沒有“繡”這個詞,只有“縫”,滿語發音為“yi he me bi”,縫的表達很豐富,與縫相關的詞有縫補、縫納、縫連。縫補滿語發音“nia ca me”,意為衣服上的補丁,強調加縫的動作。縫納滿語發音“a ba xin”,強調縫的針跡。縫連滿語發音“ka bu ca mu”,則指把兩者之間進行連接。①關于滿語發音闡述,出自《滿語字典》及滿族研究專家富育光老先生及田野調查中的滿族老奶奶口述。縫連、縫納強調工藝,縫補側重動作,是滿族刺繡原生狀態的一種表達,以加固為原則(見圖5)。

圖5 鄂倫春族“開啟上”的以補繡方式制作的皮質紋飾
在滿語中有棉線一詞,滿語發音為“tong gong”,強調的是線絲,有粗細之別。滿語中沒有絲線、金銀線等詞匯,可見滿族人用棉線刺繡是十分普及的事情。
從以上滿語詞匯可以看出,滿族的刺繡是用棉線進行縫的工藝。而縫的方法多樣,工具材料則以棉線和布為主(見圖6、7)。

圖6 鄂倫春族樺皮圍子上以補繡方式制作的樺皮紋樣

圖7 滿族服飾中以補繡方式制作的布帛紋飾
滿族人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間,生產方式上經歷了漁獵、農耕和現代文明。滿族刺繡的發展從材質上經歷了皮革、棉布、綢緞三個階段。漁獵時代刺繡以皮革、樺樹皮、筋線為主要原料,以剪、貼、縫為主要方法,圍繞信仰和仿生來確定造型和針跡。進入農耕時代后,材料不斷豐富,以棉布和棉線為主要材料的刺繡成為地域特色,既美觀又耐磨洗,受到廣泛歡迎。
今天我們見到的光彩艷麗的滿族刺繡則是滿族入關后受漢文化影響所致。而作為滿族文化發祥地的長白山區,是以縫補工藝為核心,在材料、色彩、造型等方面兼容并包,在繼承中延續發展,從而形成了今天具有原生文化特征的滿族刺繡。其中以布帛和棉線為材料形成的補繡、線繡構成了今天的原生滿族黑白繡,成為滿族地域具有代表性的刺繡技藝。在由黑白向彩色的過渡中,形式豐富的作品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痕跡。
二、滿族刺繡的日常應用
滿族刺繡之所以精彩紛呈并能留存至今,與滿族婚俗息息相關。以前,滿族姑娘從7 ~8 歲起就開始拿針學習刺繡,定情信物和新婚嫁妝涉及到刺繡的,均要自己準備,直至出嫁。枕頭頂是新婚女子嫁妝中的重要部分,嫁妝抬到婆家的過程中,要將出閣前繡好的幾十對甚至上百對枕頭頂繃在一塊大笘布上,這個繃滿五光十色枕頭頂的“枕頭簾子”上端穿在木桿上,枕頭簾子一路展示,街坊四鄰邊欣賞邊品評。婚禮當天,男方要將這些枕頭頂作品展示于新房最顯眼的地方。“紅男綠女咸來瞻仰,不夸刺繡好,只稱活計高”(《海龍縣志》)。婚禮次日,新娘要將最好的枕頭頂繃在夫婦二人枕頭之上,之后由大嫂領著去“認大小”,即拜見其他男方親屬。作為見面禮,新娘要按輩分將枕頭頂送給長輩們,甚至還要送給和婆家交往親密的朋友,妯娌姊妹間也要相互交換,而親友也往往會將枕頭頂的刺繡功夫作為評價新婦是否賢惠靈巧的標準(見圖8)。

圖8 新房中布置的枕頭簾子
滿族刺繡在日常生活應用中以服飾和炕飾為主,服飾包括肚兜、旗袍、氅衣、馬褂、木質高底旗鞋、踩堂鞋、馬蹄底鞋、水鞋、毛皮棉靴、靰鞡鞋,以刺繡為裝飾的主要為前四類,繡鞋也是滿族繡品的重要載體之一,后三類多以動物皮革為材質,鮮有刺繡裝飾(見圖9、10、11、12、13、14)。

圖9 姑娘之間互相學習繡花

圖10 滿族補繡旗鞋

圖11 皮質軟底繡花鞋

圖12 馬蹄底繡花鞋

圖13 布腰靰鞡20世紀初

圖14 牛皮靰鞡20世紀初
滿族服飾刺繡中以圍裙刺繡最為精彩。圍裙有大小之分,大圍裙帶肚兜,小圍裙只有下半身。在吉林四平、九臺,遼寧清源、西豐,黑龍江黑河的調查和收集工作中了解到,這些地區均有使用圍裙的習俗,只是在風格、色彩、紋飾上有所區別。滿族姑娘的圍裙是嫁妝之一,也是姑娘婚后必備之物,一般媽媽給女兒做,數量多為兩條,一條要有豐富的花飾,一條則素面(見圖15)。花圍裙在年節和外出做事時穿,素面圍裙平日在家干活時穿。所以現在收集到的花圍裙都很干凈,磨損也不大。

圖15 姑娘結婚出嫁時制作的補繡圍裙
廚子幫忙干活的圍裙則是要婆婆來做。鍋頭是祭祀中為神制作貢品的重要神職人員,掌握很高的廚技,滿族人家祭祀的時候鍋頭通常也要系圍裙,圍裙的紋飾很莊重(見圖16)。

圖16 鍋頭在儀式中穿著的圍裙以壽、福等掛飾為其主要紋樣
長白山區冬季漫長,滿族人在屋內設置對面炕來解決取暖問題,也因此產生了炕文化。女人圍繞炕創造出大量滿族刺繡藝術,有遮擋對面炕的幔子、幔軸穗、幔帳套,有帶枕頂刺繡的方枕、扁枕、二人枕、脈枕、耳枕,還有炕柜上的被格褡、枕頂檔簾、柜底檔簾等。
屋內一般還有掛飾喜貼、壽貼、結發貼、門簾、被簾、信插、桌簾、柜簾等等,而掛飾中最精彩者是喜貼、壽貼、結發貼,多掛在中堂或者家中顯眼之處,以欣賞為目的。多數人家南炕有窗,西炕供神,北炕是整面墻,用于掛畫,過年則掛喜貼、過壽掛壽貼、結婚掛結發貼。這種掛飾一般由四件組成,中間幅面較大,左右兩邊各有條幅,上有橫批。有錢的滿族大戶人家常用布藝制作,平常人家則多以紙材制作(見圖17、18、19、20)。

圖17 過年墻上掛的補繡喜貼

圖18 祝壽墻上掛的補繡壽貼,中間團花為“龜”紋

圖19 結婚墻上掛的補繡結發貼

圖20 結婚墻上掛的結發貼
喜貼滿語發音為wu la ben ta qi lie。在過年時會掛上喜貼簾,上面有字有畫,過完年后取下來。結婚時,婆家做結發貼,掛于北炕上,中間是喜字,兩邊是對聯,均用布縫制。平時墻上貼畫,畫的內容是歷史故事,一般3 ~5 張,標有編號,是民間延續的風俗習慣。在北方墻上有掛畫的傳統,兼具美觀、表達愿望及教育功能。從圖案上看,過年以家訓、四季平安類紋樣為主;祝壽以壽字、萬字、蝙蝠等紋樣為主;結婚以喜字、蝴蝶、盤腸等紋樣為主。筆者2005年調研時,滿族倪友芝老人講述她的剪紙“龜”含義是長壽,“以前老人過壽時,墻上貼龜的剪紙”。在夾布的喜貼中也可常見此類紋飾,造型莊重大氣。圖中龜頭與龜尾相對,四腳分開,龜背上呈現壽紋與蝙蝠的紋樣。
三、滿族刺繡的造型體系
滿族刺繡在發展過程中,有不同的方法和功用,呈現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化形態。民間老人會根據材料、實用性、用途來選擇制作工藝。為了能夠更加清晰地辨識滿族刺繡的藝術特征,本文分別從方法、材料、制作工藝角度出發,在對滿族刺繡的地域民族特色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梳理滿族刺繡的造型體系。該體系構架與思維方式相關,總體歸結為剪紙思維、刺繡思維、繪畫思維。
1.以補繡為主的剪紙思維造型
補繡是滿族刺繡的早期存在形式。最初以皮革、樺皮為原料進行縫補,剪技是縫制技藝的基礎,剪的造型決定了紋飾的造型。布帛補繡出現相對較晚,在布帛刺繡的內側均有一張紙裁剪出底樣,經過粘貼、剪裁、窩邊、縫制等工藝,形成布帛刺繡。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剪紙造型,它決定了繡技最后呈現的形式(見圖21、22)。

圖21 運用剪紙的對折手法制作的補繡作品

圖22 運用剪紙的手法剪制紋樣,以刺繡的方式自由組合成的補繡作品
剪后縫是補繡的主要工藝。縫是滿族刺繡工藝的基礎方法,不復雜,重熟練,是當時女人必會的技藝之一。而剪則只有心靈手巧者才能夠掌握,水平高者剪出的紋樣在紋飾組合方式和造型上往往能夠形成個人風格,會在村中廣為流傳并不斷重復使用。剪技影響著滿族補繡的造型,梳理后發現以下規律:
(1)紋飾對稱。補繡前要先剪紙,剪紙的特點是可折疊,事半功倍。補繡的紋飾中有大量的團花、對稱圖形。
(2)注重連接。繡是通過縫使紋飾結實地與底布連為一體,無需考錄連接,但補繡因始于剪的動作,所以造型與連接性相關,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點。
(3)線條均勻。補繡縫的工藝在紋飾的邊緣,為增強牢固性,紋飾形成以細線條為主的造型,該造型方法增強了紋飾的牢固性,使繡品更加耐磨。
(4)復合型紋飾組合。這種剪技特征與滿族剪紙的區別較大,是根據刺繡的連接、組合特點造型,而不是剪紙的連接組合特點,二者區別在于剪紙要靠紙張本身連接,刺繡則靠縫紉工藝連接,各圖形之間最后組合成復合紋飾。
2.以線條為主的繪畫思維造型
以繪畫的方式表達事物是原始思維的特征之一,在刺繡中運用較多。目前傳世最早的是戰國時期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的兩件繡品,采用辮子股針法,這種方法以線條的方式呈現事物。這種線條方式的傳達在滿族有多種針法:索線、水線、釘線,這些是針法的體現,表達的均是線條,滿族老人稱其為“擰花梗”,該名稱可以涵蓋所有的針法。用自然界植物生長的姿態來形容針法造型,如花梗生成具有韌性、生命力、外張力(見圖23、24、25)。

圖23 以擰花梗方式縫繡的襪底花

圖24 以擰花梗方式縫繡的幔帳套

圖25 以擰花梗方式縫繡的檔簾
擰花梗使用的材料是棉布,以白色為主,也有使用黑色底布,刺繡線使用棉線。該技藝造型是繪畫思維,善繪者分為觸覺型、知覺型。觸覺型藝人追求比例準確,知覺型藝人注重情趣。從大量實物可以看出,這兩類畫稿民間流傳較廣。不擅畫者借用描樣后刺繡,繡技單純,成品耐磨,存世量大,大量適用于襪底花、桌布、幔帳套、荷包等。
3.以繡技為主的刺繡思維造型
滿族刺繡的技法隨著手法的豐富,不斷產生著變化,色彩是影響其技藝發展的主要因素。生活在荒寒域北的通古斯語系諸民族,自然崇拜最高的神祗是光芒萬丈的太陽神。太陽熾熱的光是白色,白色被視為生命的顏色,是媽媽的顏色,是最高貴、最純潔、無可征服的顏色。[2]88-89她也是英雄之色、吉祥之色、光明無瑕之色,是最高尚的顏色。
《金史》中記載:“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3]26
在滿族祭祀的譜書《吳氏我射庫祭譜·色經》云:尚白為祖風,尚黃為美風,尚紅為獵風,尚黑為雄風。……黑色是大地的顏色,象征威懾、搏擊、根絕。[2]88
從以上史料中看出,白色和黑色對于滿族人來說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白色象征光明,黑色象征大地;白色象征生命,黑色象征力量,他們是萬物生命的源泉。所以早期滿族的服飾、掛飾多由黑白構成,后來逐漸受中原文化影響,開始有了色彩的運用。
刺繡技法是在面料、針、線三者之間建立的語言方法。該方法對造型的表達要用繡技加以呈現,在刺繡過程中以最大限度實現針與線在面料上形成的專有語言方法為佳作,以刺繡方式效仿油畫、國畫等作品,體現的不是刺繡語言而是繪畫語言。因此本文強調的是民間淳樸的繡技語言。
滿族民間剪紙主要特征為:注重外部造型,內部少打扮;外形是多視角個性化特征的綜合表達。彩色刺繡在長白山區出現較晚,源自中原,也經歷了本土化改造,這種改造主要表現在外形的繼承和典型紋飾的延續,增添的是色彩和針法。在彩色刺繡出現之前是以黑白線、藍白線進行平面刺繡的階段。該階段作品是黑白刺繡向彩色刺繡在技法上過渡的重要時期。
從圖26作品中可以看出滿族剪紙人物造型重輪廓,內部打扮主要在臉部。圖27幔帳套刺繡是補繡線造型向面造型刺繡過渡時期的作品,該作品繼承了剪紙語言注重人物外輪廓的藝術手法,臉部細節造型與剪紙同,特別是藍白線繡作品,以一組組短線繡出大塊的面造型。而此后出現的彩色刺繡從人物服飾中可以看到增添了云卷等紋飾打扮,與環境中呈現的云卷紋相同。從這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到滿族刺繡中的面造型延續了剪紙的造型語言,在不斷發展中增添了繡技和色彩變化。

圖26 滿族剪紙注重外輪廓,突出形的個性特征

圖27 幔帳套刺繡中人物造型簡潔整體、輪廓清晰,注重形體特征
四、滿族民間刺繡的傳承發展
滿族發祥地從清代以來有多次大的移民潮,移民主要來自于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移民帶來的文化與當地文化的融合,對滿族刺繡的演變、傳承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長白山區滿族原住民刺繡最大的特點是剪縫的技藝以補繡、線繡為主,色彩單純,包括黑白及棉、麻、筋的原色。從今天滿族地區遺存的刺繡技藝和作品看,存在多種類型,如納紗、編紗、絨繡、打籽繡、盤金繡等是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產物。除滿族入主中原成為執政王朝,吸納中原優秀繡技外,本土居民刺繡更多受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移民文化影響。其中山東魯繡地域特色鮮明,對滿族刺繡影響較大。魯繡繡線大多是較粗的加捻雙股絲線,俗稱“衣線”,也叫衣線繡,曾流行于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在滿族地區有大量衣線刺繡方法存在,該方法在吉林烏拉街、長春九臺、四平等地流行。該工藝將滿族的色彩崇尚、造型特點與漢族的技藝方法緊密結合,形成了白布做底,彩色大花鳥刺繡的平面紋飾。在用色上,魯繡注重色彩明亮而濃麗,紅、黃、藍、綠、紫、黑等色彩使用飽和度較高,形成色相對比明快的視覺效果,這種色彩的使用與山東地域民俗心理和審美相關。造型上保留了滿族刺繡的特點,該特點可以概括為:穩、浪、滿。端莊大氣即為穩,直爽、艮氣為浪,大而豐富為滿。滿族刺繡產生于白山黑水,這里的人們在與自然的相處中為生存而創造藝術:高蹺秧歌、滿族民歌、滿族繪畫、滿族剪紙、滿族刺繡等。民歌的清爽高亢,秧歌的豪放浪漫,繪畫的靈動飽滿,這些因一方水土養育的文化之間氣脈相連。因此我們能夠綜合地感知滿族刺繡的精神內涵,也因此才能夠理解它的形式美。
滿族刺繡原本色彩較單一,如幔帳套,這是滿族對面炕文化必不可少之物。同樣是制作幔帳套,滿族人用補繡、線繡的方式在其上承載信仰中象征生存繁衍的蝴蝶、云子卷、龜等紋樣,漢族人則在幔帳套上用色彩艷麗的棉線、毛線、絲線繡制漢族地區流行的圓光、抱角等形式的喜鵲登梅、鳳戲牡丹等紋飾。
外來文化的色彩、紋飾結合滿族當地的風格、民族代表性符號構成了長白山地區滿族刺繡的又一風格特征。白底大花鳥是典型代表。
以上方法是長白山滿族地區20世紀30—50年代比較流行的刺繡方法,這些方法與傳統黑白刺繡同時并存在同一個村莊里。到了20 世紀50—80 年代,這些地區最為流行的刺繡方式為割繡,割繡又稱“割絨納繡”,系河北、山東兩地流傳的一種民間刺繡。在新疆羅布泊曾出土西漢時期打結栽絨地毯殘片,這是最早的栽絨地毯實物。栽絨和堆絨是割絨的雛形,流傳到河北和山東一帶,該種技藝隨著移民不斷融入東北刺繡技藝中,在20 世紀50—80 年代,開始得到普及發展,成為家喻戶曉的流行刺繡方法。門簾、窗簾、電視蒙子、洗衣機簾、枕頭蒙子等等,今天能夠見到眾多的運用割繡技藝制作的物品。這種技藝與傳統相比最大的問題是,樣稿來源及文化內涵。傳統的刺繡樣稿來源于民間生活體驗的創作和傳承,而割繡的樣稿多為批量印刷品,題材和造型受漢文化影響較大。如今在遼寧省桓仁縣洼子溝村,整村的婦女都在用絨繡的方式制作鞋墊。大家都知道該技藝是20世紀80年代一個回鄉探親的山東人回來后將山東的絨繡技藝帶進了村莊,從此這個村中的滿族和漢族婦女都利用閑暇時間割繡各種色彩豐富的鞋墊。這是滿族人接受了漢族人的刺繡技藝,同時滿族人在運用這種技藝的過程中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創作回撥鹿、山花等滿族題材的作品。滿漢文化的融合更多的是工具材料、工藝的融合,對于承載文化的紋飾、符號是伴隨著生產方式、信仰而存在和改變的。
(一)繪畫造型刺繡的傳承發展
線繡的發展經歷了由筋線到棉線,由黑白到彩色的過程,圖28中人物為典型的線條繡,中間的盆花是彩色線條繡和彩色刺繡的結合體。圖29 作品《蓮開并蒂》中“云”沿用黑白線條繡,龍身采用彩色刺繡,兩端的花枝還留有彩色補繡的造型語言。從這些發展階段出現的各種繡法中我們能夠看到滿族刺繡的發展演變過程,它經歷了由黑白到彩色,由線造型到面造型的一個漫長而有趣的發展變化過程。

圖28 王美榮觀花

圖29(1) 黑白線繡和彩色刺繡結合使用

圖30(1)-(4) 補繡紋樣在發展過程中由黑白向彩色過渡,做工也由勻凈向尋求變化過渡
(二)剪紙造型刺繡的傳承發展
1.補繡色彩由單一向彩色過渡
滿族地區的補繡最初材料為皮革,色彩以天然植物染黑、黃為主。在布帛流行的時期,長白山區普遍使用的布料包括:家織布、花旗布、斜紋布,他們出現的時間早晚不同。下組圖第一幅是20世紀初作品,紋飾勻凈端莊,后三幅是20世紀中期出現的作品。第二幅紋飾在線條的粗細上變化過大,欠缺端莊之氣。第三幅圖依然采用補繡的方法,面料改為彩色,色彩的深淺會使人產生輕重、虛實之感,但隨著色彩在民俗中含義的變化,人們對色彩的需求不斷提高。這種只換面料不換技法的方式在民間流行一時。
2.用彩線繡出補繡造型
圖31 彩色枕頂刺繡組圖中的碟紋,其造型方法是補繡線條造型的沿襲,其中第四幅是彩色刺繡中常見的蝴蝶繡法,該方法是面造型,強調色塊之間的深淺、大小關系。前者紋飾更加抽象,帶有符號的特征。后者更加接近于自然,追求形似。在梳理清楚補繡造型觀念的前提下,才能夠讀懂這些彩色刺繡為何如此造型。色彩和刺繡針法的多樣性,結合補繡的紋飾造型,推動著滿族刺繡的發展。

圖31(1)-(4) 彩色枕頂刺繡組圖
從圖32中我們能夠看到完整的補繡線造型方法在彩色刺繡中的完整體現。

圖32 線造型表達外輪廓,內部填充色彩,該階段是補繡向彩色刺繡的過渡時期
這與彩色刺繡成熟以后的造型觀念完全不同。在兩者之間還產生了一個過渡時期,彩色刺繡造型依然遵循補繡線條造型的原則。如下圖是完整的彩色刺繡,該作品中造型均有寬邊,這條邊以里的造型填充了豐富的色彩,該手法是補繡向彩色刺繡過渡的第三個階段。
通過以上梳理,對補繡的發展可以整理為:黑白補繡、彩色補繡、彩色線仿補繡。
3.以彩色的絲線襯托補繡造型
補繡作為一種剪形,完整而漂亮,在向彩色刺繡發展的過程中還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以色彩來襯托這種形的單純,以白當黑、以虛當實,這種觀念構成的方法,成為彩色刺繡的一個特殊品種。這種底色的方法是受日本刺繡影響,紋飾上保留了滿族補繡的造型語言,成為滿族刺繡發展過程中的獨特品種(見圖33、34)。

圖33 補繡由單一顏色向彩色過渡

圖34 彩色線繡效仿補繡造型方法
4.滿繡的剪繡語言向刺繡語言過渡
補繡線造型表現和彩色的面造型兩種方式的過渡時期恰是造型語言結合的發展階段,該階段的作品中恰是抽象和具象造型的結合。這種方法是對傳統補繡在色彩和造型上的繼承和發展,該造型的典型之處是云卷紋、壽字紋的變化,該紋樣隨形而變,長短、疏密、與其他形體的結合等都別出新意(見圖35)。

圖35 剪繡語言與刺繡語言同時存在的滿族刺繡作品
(三)刺繡造型的傳承發展
滿族黑白繡向彩色過渡形成剪紙、刺繡、繪畫三種語言的結合。這也形成了滿族的面造型刺繡特殊的發展階段,該階段針法的豐富性達到了一個新高度,色彩由生硬開始向自然柔和過渡。題材由原來以信仰為主開始兼容并蓄,出現文人畫、書法、篆刻等內容,這種內容形式的發展也促進了滿族刺繡技藝的發展(見圖36、37)。

圖36 花、鳥色彩過渡生硬的作品

圖37 花鳥運用插針、參針,色彩過渡柔和自然的作品
五、結語
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間的滿族人在農耕時代創造了獨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滿族黑白刺繡藝術,這些作品中承載著該民族厚重的歷史、文化遺跡,在不斷的民族融合發展中,色彩、技藝方法都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當我們了解了該民族的刺繡技藝的演變,也才能夠明白滿族刺繡不斷發展形成的歷史軌跡,也才能夠從今天紛繁復雜的眾多的刺繡藝術中體會了解滿族刺繡藝術的魅力。這些梳理和研究更大的意義在于其對民族刺繡技藝的傳承發展,只有理清根系,才能在繼承中發展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