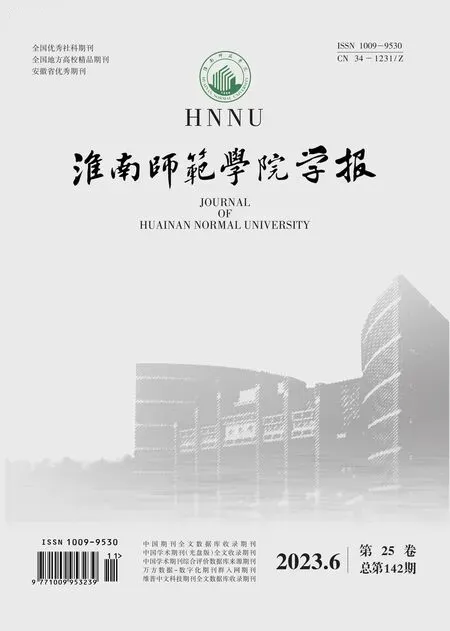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呈現
——以潘玉良繪畫為中心的考察
范本勤
(淮南師范學院 美術與設計學院,安徽 淮南 232038)
現代人文語境下的女性意識,包含了女性的性別意識和自我意識。前者是女性在生理、心理和社會學層面的自我認知和體驗;后者是女性在性別意識的前提下,作為主體,以自主的途徑和方式參與社會生活、實現自己的價值和滿足自己需求的意識。女性意識既是對男性權力和男性經驗的積極否定,也是對自身價值的覺醒、體悟,甚至自我批判。
賈方舟將中國現代女性藝術的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即女性意識的萌動、女性經驗的展開、女性主義的崛起,并認為,“女性意識的萌動就是從潘玉良開始”,“潘玉良的意義在于她是一個較早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藝術家,……從女性藝術這個角度看,潘玉良這個角色很符合中國女性發展的最初階段。”[1](P12)所謂女性藝術,并不泛指“女性的藝術”,而是出自女性的視角,以女性的身體感覺、體驗,呈現出的文字畫面,這是女性藝術的前提。潘玉良在20世紀早期的“洋畫運動”中成長起來,與當時活躍在畫壇的女性畫家(如方君璧、關紫蘭、丘堤等人)類似,從寫實性的繪畫基礎起步,嘗試探索各種現代性畫風,形成相對穩定的繪畫風格。從繪畫本體的造型技巧看,潘玉良并不能獨占鰲頭,但是,潘玉良有著其他女畫家所沒有的曲折傳奇的人生經歷,而她的繪畫又與自身經歷息息相關,時時透射出對自己性別身份和人生際遇的思考,彰顯了其性別意識的覺醒,這是活躍在民國畫壇的其他女性畫家難以媲美的。也因此,潘玉良的繪畫,在溯源中國美術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男性圖式體系的解構、女性主義的萌發時,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
一、鏡中人:自我審視與自我認同
肖像畫的功能在19世紀中期以前大致相當于現代的照相,所以肖像作品大多是由贊助人及其家族私藏的,一些畫家也創作自畫像,但也基本限于自藏。19世紀下半葉以來,包括自畫像在內的肖像畫逐漸成為公開的展品和流通的商品,在這種情形下,畫家的自畫像就不再只是“自我欣賞”的私密性作品了,而是兼有了與觀眾對話的中介功能,這樣,畫家在創作自畫像時,必然就要考慮向觀眾展示什么樣的自我形象。畫家通過自我形象設計——包括姿態、角度、神情、服飾和道具,以及光線、背景、色彩、線條等等藝術要素——最后形成的,是帶有各種象征性符號和意味的、重塑性的自我敘述,而這種自述,往往是(或期望是)直面觀眾的審讀的。“我是誰”“我希望我是誰”“我期望你認為我是誰”——畫家內心的自我形象、自我意識、自我身份的認知,都會通過自畫像流露出來。換言之,自畫像的這一特性使其成為研究藝術家內心世界的最好文本。
潘玉良(1895—1977)出生在揚州,本名張世秀①,未滿周歲父親去世,8歲母亡,由親戚撫養,后流落到安徽蕪湖,寄身妓院,以婢女或藝伎的身份活到18歲,直至遇見陳獨秀和潘贊化,在陳獨秀的撮合下,潘玉良嫁與潘贊化為妾,人生命運由此轉變。 22歲時,跟隨安徽籍畫師洪野學西洋畫,開啟了艱辛而絢爛的藝術生涯。“雖然潘玉良的社會地位與個人身份隨著其藝術道路的開闊而逐步提升,但是悲慘的出身、諱莫如深的經歷與為妾的現實,還是成為了阻礙其得到更大發展空間、收獲平等友善關系的根本性因由。”[2](P19)在遇見潘贊化之前,潘玉良的人生是卑微的,而在嫁與潘贊化后,雖然丈夫疼愛有加,物質上也有保障,但“妾”的身份仍是不愿與外人道的。這種“諱莫如深”的隱痛不僅伴隨終生,且不時地被揭開傷疤,遭受冷眼甚至粗暴的對待。
潘贊化在1955年寫給她的家信中所說:“你一生不解(講)究裝飾,更有男性作風。少年騎馬射箭,都是好手。”[3](P23)與潘玉良交往過的友人們對潘玉良的性格特征也有一致的印象:“此人豁達大度,性格豪放,說話大嗓門,能喝酒,會劃拳,愛唱京戲,女唱男,唱黑頭,須生……她這個人在當時是屬于思想解放的一類,爽朗的很。”[4]這種性格表現,既是天生所賦,也與其早年寄身青樓、見識太多的人情世故有關,更不容忽略的是,其間有自我保護、刻意男性化,以及積極躋身男權社會、獲取身份認同的復雜心理因素。在人前的喧囂,無法掩蓋獨處時的痛楚。時常面鏡而觀,自我審視“我是誰”,并通過自畫像呈現出來,借此達成自我認同。在潘玉良的存世作品中,可以查閱到繪于不同時期的自畫像至少有19幅,其中多數創作于異國他鄉。容貌平平的潘玉良如此熱衷于創作自畫像,除了對自己容顏的自憐之外,上述心理訴求應是可以蠡測的重要誘因。

圖1 《自畫像 》潘玉良 1924年圖2 《自畫像 》潘玉良1940年
圖1、圖2兩幅自畫像分別作于1924年、1940年。潘玉良創作前者時,尚在法國跟隨西蒙學畫,繪畫手法還較為稚嫩;而潘氏創作后者時,已是再次回到法國寓居的16年之后了,歷經歸國10年教學和創作生涯,藝術水準已有長足進步。共通之處是,兩幅作品中,作者對自己的容貌都有一定程度的美化,尤其后者,刻意潤飾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溫暖柔和的光線下,濃妝艷抹,姿態優雅,嬌艷盛開的瓶花更加襯托出人物的嫵媚。

圖3 潘玉良肖像 (攝于1920年)圖4 《自畫像 》潘玉良 1945年
潘玉良年輕時的照片(圖3)中呈現的容貌,與影視作品中的演繹相差很遠。旅美畫家林藹是潘玉良的摯友,她在回憶潘氏的容貌時說:“真正的潘玉良,外表是丑得不能再丑的女人,她的身材矮胖,她的臉龐既不白里泛紅,也沒有酒窩,而是黧黑,而五官的奇特,令人注目,她的聲音,不是鶯聲嚦嚦,而是像虎嘯猿啼,她那過厚的嘴唇,使人懷疑她的祖先好像來自非洲。”[5]林藹的說辭并不是為了揶揄潘玉良,也不是完全客觀的描述,其真正用意是提醒世人,勿以為潘的人生成就是靠美貌帶來的。不過,林藹的言語可以側證,潘玉良的容貌即使不很丑陋,也與“漂亮”無緣。
這兩件跨越16年的自畫像表明,潘氏在此期間是欲以世俗美感示人的,這種心態與傳統社會中的普通女子并無二致。然而,在此后若干年的幾幅自畫像表明,潘玉良的內心世界有很大轉變,不僅在形象上從附庸男性審美觀轉變為真實地展示自我,而且在精神上有刻意呈現堅毅冷峻、孤獨沉思的自我狀態之趨勢,女性主體意識的表達逐漸明晰起來。圖4、圖5兩幅自畫像作于1945年,畫面構思異曲同工。人物立于窗前的自然逆光下,身體的姿態已無柔弱溫婉之感,上肢與手的動勢甚至有些男性化傾向,衣著樸素,膚色沉著,容貌平庸,自我美化的匠心已了無痕跡。與1940年所創作的自畫像相比,瓶花、半身人像的素材組合幾近一致,但畫面所呈現的視覺感受判若云泥,作品已從“被觀賞”(尤其是男性的觀賞)的預設情境轉向女性“自我訴說”的精神圖式。圖6是兩年后(1947年)的自畫像,取胸廓以上形象,軀體、動態等反映性別的特征似乎已無關緊要,去除了瓶花,背景做平面化處理,用特寫的方式,對人物的面部作重點刻畫。怪異的發型、寬廣的額頭、深陷的皺眉紋、折疊的下巴不僅真實反映了50歲出頭的年齡,更著重刻畫出了紛亂而凝重的情緒,尤其是直面觀看者的眼神,帶著凜冽的審視意味。如同赫倫·謝夫貝克、凱綏·柯勒惠支那樣,用 “不美”的自我敘述,模糊了性別界限,突出了精神表達和思想張力。

圖5 《自畫像 》潘玉良 1945年 圖6 《自畫像 》潘玉良 1947年
造型果敢、用筆剛勁,潘玉良的繪畫很早就呈現出男性繪畫的氣質,但她早年在創作自畫像時,卻小心的將自己包裝起來,以溫婉示人,這種矛盾體現了復雜的心態。一方面,生活的經歷使其缺乏安全感,潛意識里處處模仿男性以獲得某種心理補償;另一方面,在描畫自己的形象時,又把自己回置到男性觀眾的對面。這種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失。20世紀40年代以后,自畫像中性別特征的逐漸弱化、精神面貌的著意表現,體現出潘玉良已形成不受觀看者左右的主體意識。
二、女人體:叛逆與隱喻
縱觀潘玉良的存世遺作,人體畫占有最大篇幅。早在上海美專學習時期,潘玉良就已開始人體題材的繪畫創作,雖然石楠在《潘玉良傳》中關于潘氏以自己為人體模特創作油畫并公開展出的說法缺乏證據支撐,但劉海粟主持的美專西畫教學中,注重人體模特寫生的訓練方法,初步培養了潘玉良對人體題材的興趣,應是題中之義。爾后,潘氏又出洋學畫,西方學院里的訓練更是以人體寫生為中心,長期嚴謹的訓練使得潘氏具備了扎實的人體畫寫生、創作的能力。但是,這些并不是潘玉良終其一生堅守人體題材的充分理由。以人體為媒介,對自己的情思進行隱喻性表達、對男性權威進行無聲的反抗,是在實踐藝術技巧和表達審美觀念之外,促使潘玉良專注于人體畫的重要因素。
色粉畫《顧影》是潘玉良早期人體畫的代表作,在1929年全國美展中展出。畫中描繪一女子正向而坐,手持鏡而自顧,面部流露出的憂郁的神情。李寓一評曰:“女士此作,于愁苦悵惘、愛惜、郁悶等,似與惆悵相近,而亦未曾明示于觀眾,蓋亦人間之大迷也。女士心性耿直,胸無點塵,……無一幅一筆一點之間,不為其忠誠心靈之表白。”[3](P102)顯然,這是一件有隱喻意味的作品:其一,畫中女子容貌普通、身材健碩、膚色沉著,與民國早期通俗繪畫(如布景畫、月份牌等)中體現出的流行審美觀不同,而與潘氏自己,倒是十分相像;其二,顧影自憐,面露悵惘之色,與其說是精心設計的藝術構思,倒不如說是潘玉良在那個時期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潘氏1928年回國,隨后即受聘于上海美專,擔任西畫系主任,開始了10年教學生涯。上海美專是潘玉良學畫經歷中的重要一站,但潘氏在美專學習期間遭遇的歧視,讓她對美專有著復雜的情感,加之現實之中又受到丁遠(美專總務長)等人的排擠,歷史的隱痛和現實的艱難疊加在一起,使得潘玉良的內心壓抑苦悶,這種情思在《顧影》中可見一斑。潘玉良在此次畫展中的參展作品,除《顧影》外,還有《黑女》《歌罷》《酒徒》《燈下臥男》,共五件之多。積極地公開展示自己的作品、參與社會活動,是潘玉良一貫的作風。其在歸國后精心策劃了大型個展,引起了文化界不小的轟動。歸國后,參加的畫展不計其數,各大藝術社團、組織,也常見其身影。這些社會行為,一方面是出于對藝術的酷愛,如潘氏自己所說:“生性喜歡美術的我,對于音樂、雕刻、繪畫都曾經做過相當的練習,但自繪畫上的色彩把我引誘成了一種嗜好之后,音樂、雕刻在事實上就只得犧牲了。”[3](P94)另一方面是要雄心勃勃地在男性社會爭取成功,以繪畫的成就證明自己“不讓須眉”,讓人們淡忘自己的出身,最終獲得平等的對待和公允的評價。理想主義的和功利主義的目的糾結在一起,不易分辨,但其中“平權”的女性意識之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潘玉良作為女性,其出身和作畫題材,使得那些堅守舊(道德)觀念、對潘氏頗有微詞的人,自以為獲得“呈堂證供”,更加肆無忌憚地予以攻訐。這種廣受非議的情形應是潘氏可以預料的。然而,正是這些攻訐激發了她的叛逆心理,越是困難越要堅持,將人體畫當作回擊舊道德、彪炳新觀念的宣言;同時,她在藝術理想上不愿妥協,在現實功利和藝術理想之間,寧可犧牲前者而成就后者。人體畫題材的堅守,生動體現了潘玉良作為特定女性個體的反抗意識以及堅貞不屈的品格。
“潘玉良以女體做對象的作品,似乎都有一種‘自畫像’的隱喻,潘玉良不一定是一個刻意表現潛意識隱喻的畫家,但是,她的隱喻卻耐人尋味。”[3](P114)如《顧影》中,無論是肉體還是精神,都有觀照自身的意味。若將潘玉良的人體繪畫分為寫生與創作兩種類型,可以明顯地看到,在創作型的人體畫中,人物形象的營造,包括面部形體和妝容、人體的整體性特征,甚至膚色都有以自己為藍本的傾向。這一傾向,在其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彩墨畫中愈發明顯。如果說寫生中的人物形象會較多受到客體(模特)的掣肘,對于潘玉良(所能駕馭的繪畫技能)來說,主觀化的改造存在一定困難,那么,在離開模特進行創作(或在寫生的基礎上再創作)的時候,潘玉良的造型是相對自由的。恰是這種自由狀態下的造型,最真實地反映了潘氏的某種藝術觀:追求真實之美、健康之美,強調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意識,否定了男性對女性的“物化”。這其中,也暗含了對自身——一個有著類似形象的普通女子——的積極肯定。《著上衣的女人體》(1959年)、《海邊浴女》(1959年)、《坐姿雙人體》(1963年)、《戴帽女人體》(1963年)等,是這類繪畫的代表性作品,從中不難發現,畫中人物有著幾乎千篇一律的飽滿臉型和五官、細長眉線、偏暗的膚色、健碩的體型。
三、多彩情節:溫暖的女性世界
在跨越半個世紀的藝術生涯中,在純粹的用于訓練繪畫技能的寫生以外,潘玉良通常都會在畫面中精心營構情節,以實現自己想要表達的主題。潘氏寫實的、文學性的繪畫,是古典藝術傳統的延續,與她所處時代的“先鋒”藝術理念有較大出入。對潘氏繪畫的評價,新舊各派褒貶不一。蔡元培、徐悲鴻對其贊許有加,而有現代派色彩的“決瀾社”先鋒龐薰琹對其卻不以為然:“一九三○年,……她在上海美專時教油畫,在藝苑畫模特兒,屬于法國學院派的畫法。她似乎沒有想追求什么新的創作風格,她只是規規矩矩地畫,沒有顯示出特殊的才氣。”[6]無論如何認定潘玉良的藝術才能,其文學性的繪畫都是作為女性畫家(用以重建現實的)較有價值的選擇,同時,也為我們在今天探幽其心靈世界打開方便之門。如西蒙娜·波伏娃認為:“當她們用自己的話語重建現實時,她們才能獲得表達個人經驗的權力。而女性藝術家一旦將探尋的目光轉向自身、轉向個人經驗的呈述和心靈事件的表白,這些深潛的情感領域便成為建構女性話語的理想境地。”[7](P99)家庭、母愛、思鄉、閑逸等都是潘玉良情節性繪畫中常見的主題,圍繞這些主題展開的具體情節,呈現出了豐富多彩的女性世界。
《我的家庭》創作于1931年,自傳式的描寫了家庭生活:潘玉良坐在畫面的中心位置,一副知識青年的模樣,對鏡寫生,在她身后站立的是潘贊化和兒子(正妻之子),他們專注地看她作畫,看起來,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和諧美滿。張道藩稱贊道:“一張很有趣很難得的畫……觀眾們能不羨慕潘女士家庭的快樂嗎?整幅畫的結構和色調的分配都很好。”[8]其實,將家庭以美滿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只是潘玉良美好心愿的傾訴方式而已。這一時期,雖然潘玉良的公開社會地位不斷提升,但在家庭中,潘氏卻尷尬地在教授與侍妾的身份之間不停轉換,所受屈辱是一言難盡的。將潘的正妻排除在畫外,體現了潘玉良對傳統婚姻關系和道德觀的反抗。新舊觀念相互糾纏、身份錯位而無力改變,是促成潘氏再度遠赴歐洲的深層原因,只有“出埃及”才能擺脫現實痛苦、維護內心的尊嚴。“舊女性”向“新女性”的跨越,由一次出走標志性的完成了。
潘玉良一生未育,其原因撲朔迷離,但如普通女性一樣,也是期盼母親角色的。《我的家庭》是這一心跡的真情流露,而從潘玉良的書信以及潘贊化后人的回憶錄中,也可以有力地證實這一點。在此后留法歲月的畫作中,真實的家庭歡聚情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虛構的母子嬉戲、哺乳等情節,彩墨畫《母與子》(年代不詳)、油畫《哺乳》(1961年)是其中最精彩的代表作。在《母與子》中,潘玉良描寫的是母子嬉戲的情節,嬰兒躺在小床上,似乎剛剛從美夢中醒來,歡快地呼喚母親,母親匐下身來將孩子摟入懷中,母子親昵的情境被營造得真實而感人,而母子身形的夸張對比,又有強調安全感的用意;在《哺乳》中,一位身材豐腴的母親躺在沙灘上,嬰兒滿足的吮吸著乳汁,母親深情地注視著自己的孩子,遠處背景是藍色海洋,襯托出母愛之純凈、博大。雖然潘玉良的此類作品有很多未署日期,但從時間可考的作品中可以看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創作的高峰期,此時的潘氏已是暮年,老而無子,無法釋放、無處安放的母愛只能傾注于畫中。與早年不同,暮年潘玉良營構的母愛情節更加富于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樹蔭下,花叢中、碧海藍天,母與子在自在的天地嬉戲,專注于自身處境的“小我”已經悄然讓位于觀照普遍母性的“大我”了。
對親人和故土的眷戀,是離鄉萬里的潘玉良無法拂去的情緒。但潘氏在畫作中宣泄思鄉情緒的方式是委婉的,常常借助歌舞、游戲等母題,進行隱喻性的情節設計,以實現排解離愁、抒發心靈歸宿的目的。《放風箏》(1956年)描寫了一個穿著民族服裝的女孩孤身一人放飛風箏的情節。風箏常被用來象征情思羈絆,一線牽連、漂浮不定,隨時有斷線飛去的危險。而此作中的情節另有所指,風箏似乎暗喻潘氏本人,風箏的主人則象征著故土,無論漂泊多遠多久,那根線永遠牽在故國家園。《玩撲克的女人》(1957年)中的隱喻更值得思考:1956年,潘玉良因思念家人申請回國,但被拒國門之外;而在同年稍后,張仃、吳冠中邀請她回國任教,她卻婉言謝絕了。可見,對于自己在異鄉的去留,潘玉良內心充滿矛盾。“她無法給自己一個答案,于是創作了這幅作品,借用玩撲克的女人這一圖像符號來傳達她對未知的迷惘、對命運的叩問,也反映了面對世事無常,畫家凄惶無助的心情。”[9]此類作品很多,所借助的情節(或符號)也是多樣的,如《雙人舞》(1955年)、《雙人扇舞》(1955年)、《勸酒》(年代不詳)、《采茶女》(1953年)等等。
探詢潘玉良內心的女性世界,其繪畫中的各種休閑情節的描寫是不可忽略的。春游、戲水、沐浴、露營、垂釣、玩牌、聊天等各種休閑活動充斥于潘玉良的作品中,就單個作品看來,這些情節往往沒有特別的意涵,但總體觀之,卻是能清晰地展現潘氏的生活觀和價值觀的。19世紀中后期,印象派的崛起不僅改變了繪畫的審美范式,也極大的改變了繪畫的內容,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戶外休閑生活,成為印象派畫家們熱衷的繪畫情節。這種轉變的緣由,是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變傳統生活形態,進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觀,工作時間以外的多彩的閑暇生活,成了人們的精神居所。與同樣長期寓居海外的其他畫家(如常玉、唐蘊玉、趙無極)相比,潘玉良在作品中對現代性的閑暇生活投入了更多的筆墨,究其原因,除了潘氏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在歐洲度過,受現代生活文化的浸染,從而心向往之以外,其自身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女性意識也是不可忽略的。潘玉良自幼被拐來賣去,兩次改姓,在婚姻中也是低人一等的侍妾身份,早年被命運擺布的生活,使得潘玉良對人身自由和人格獨立有著刻骨銘心的向往和珍視。晚年,思鄉心切的潘玉良始終無法下定決心回國,正是這一心跡使然,就如張仃回憶,“我問潘玉良是不是也想回來,她很爽快,說:‘說實在的,國內生活我恐怕過不慣。’這可能是她沒有回來的主要原因。”[4]輕松浪漫的休閑生活情節被反復吟詠,體現了潘玉良對生活的熱愛,更是其自由和獨立精神的映射。
四、結 語
通過對潘玉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繪畫情節的簡要梳理和剖析,可以發現性別認知、生命體驗、權利覺醒、自我價值的實現等多種維度的女性意識,被有意或無意、或明或暗地嵌入其中。這些女性意識是混沌初開的,并沒有發展為激烈的女性主義,更不類同于當代的女權主義。但是,與蘇珊娜·瓦拉東、赫倫·謝夫貝克、凱綏·珂勒惠支、弗里達·卡羅這些活躍在20世紀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女性畫家一樣,“她們意識到自己是‘女人’,就在于她們意識到有她們自己的視角,有她們自己的經驗領域和判斷標準,有她們自己特別關注和感興趣的事物。而且她們對于這個世界的感知方式、經驗方式與思維方式也與男性不盡相同。”[10]基于獨特的生命體驗,潘玉良以自己的方式,描畫了自己,也描畫了那個時代。
注 釋:
①關于潘玉良的本名及出身,尚無孩童時期的原始證據可考。《上海美術志》記錄其本名為陳世清,生于揚州。桐城潘家樓《木山潘氏宗譜世壁卷》記載潘玉良原姓陳,本名為世秀,字玉良。潘玉良在上海美專學籍檔案中的名字為潘世秀,而在與潘玉良往來的書信中,友人們都稱呼其為“潘張玉良夫人(女士)”。基本可以確定的事實是:潘玉良本姓張,在父亡后隨母改姓陳,嫁與潘贊化后隨夫姓潘,世秀是曾用名。此外,關于潘玉良在蕪湖妓院中的身份問題,王玉立、董松、曹子達等研究者通過考證,均認為,其身份應為婢女或陪唱歌女,而非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