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格南初體驗
潘超群

馬格南圖片社,巴黎,法國,2023。
從2023年9月起,我在馬格南圖片社(MagnumPhoto)參加為期一年的創意紀錄片與新聞攝影課程(CreativeDocumentaryandPhotojournalismwithMagnumPhotosandSpéos)。這個項目是由馬格南圖片社與巴黎攝影學院(Spéos)合作舉辦的,每年一屆,全球范圍內招收10-12名學生。馬格南圖片社負責在視覺敘事傳統下提供有關個人攝影項目的指導,課程中由三位馬格南攝影師擔任長期導師,并每周邀請不同的馬格南攝影師進行講座、研討等,而巴黎攝影學院負責技術部分的授課。
“顧名思義”,我當時選擇申請這個課程的唯一原因就是“馬格南圖片社”。畢竟在攝影史上,馬格南是座繞不過去的“豐碑”,是很多攝影愛好者心目中的“圣殿”。有什么比與那些名字出現在攝影史書上的人面對面交流更讓人激動呢?有什么比面對面向當代最優秀的攝影師學習收獲更大呢?當我在馬格南圖片社見到約瑟夫·寇德卡(JosefKoudelka)、雷蒙·德巴東(RaymondDepardon),在教室里聽帕特里克·扎克曼(PatrickZachmann)和斯圖爾特·富蘭克林(StuartFranklin)聊起他們的創作經歷和攝影哲學時,我就知道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馬格南圖片社,巴黎,法國,2023。
感謝《攝影世界》的邀約,能夠在2024年開設“我在馬格南學攝影”這個欄目,我也期待與大家分享這一年我在馬格南圖片社學習的經歷、體驗與收獲。
馬格南圖片社創立于1947年,由四位堪稱傳奇的攝影師奠基——亨利·卡地亞-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羅伯特·卡帕(RobertCapa)、喬治·羅杰(GeorgeRodger)和大衛·西蒙(DavidSeymour)。他們將各自獨特的風格結合在一起,創立了這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藝術家合作社。其實初創團隊還包括3位圖片編輯,但因為種種原因,如今即使在馬格南內部也很少提起他們的名字了。
“馬格南(Magnum)”這個名字來源于法國的一種大號香檳(每瓶1.5L,是普通香檳的2倍),這是當時攝影師們從戰場上順利返回后最喜歡用于慶祝的酒水,所以幾位有戰爭攝影背景的創始人便將它作為了圖片社的名字。
馬格南圖片社成立的初衷,其實是保護攝影師的版權,并為攝影師爭取獨立報道新聞的權利和地位。自成立起,馬格南記錄了世界上大多數重大事件和人物,涵蓋工業、社會和人物、名勝地點、政治和新聞事件、災難和沖突。當你想到一個標志性的圖像,卻想不起是誰拍的或在哪里可以找到時,它很可能就來自馬格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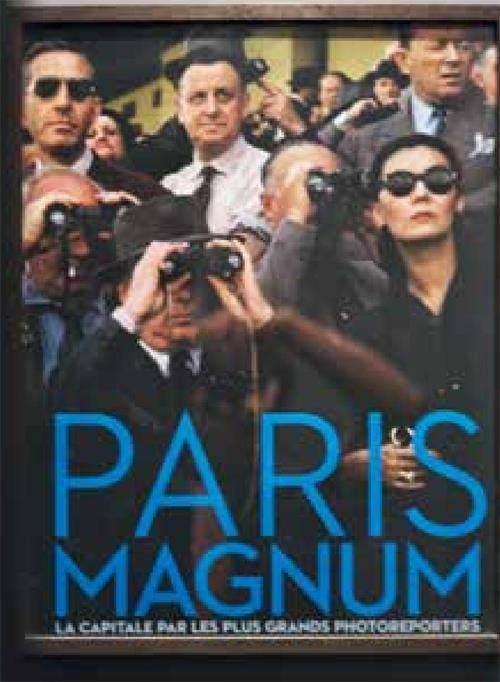
馬格南圖片社內的海報,巴黎,法國,2023。

馬格南圖片社,巴黎,法國,2023。圖書館書架,可以對外出售的部分書籍。
如今的馬格南,依然代表著全世界最優秀的那一批攝影師,并隨著世界的變化,在保持著其創始理念“紀實與新聞”的同時,越來越多地與藝術攝影等其他攝影語言互相融合。正如馬格南攝影師自己所說:“馬格南是一個思想共同體,具有共通的人類品質、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始終充滿尊重與好奇心、并始終保持著以視覺方式記錄它們的愿望。”
雖然一直心心念念,但初見時,卻很難將這個不起眼的地方與大名鼎鼎的馬格南聯系在一起。
馬格南圖片社的巴黎辦公室位于巴黎11區一個很“平常”的街區,這也是2年多前才從18區的舊址搬遷而來。在這里,馬格南甚至沒有臨街的門面或招牌,需要推開路邊一棟仿佛民宅建筑的大門,走過一個小小的院子,才能看到黑色大門上白色的“MAGNUM”字樣。
進門之后,地方也不算大,一樓是畫廊、圖書館和檔案室,二樓是辦公室和我們平時上課的地方,總的來說就是非常非常樸素。
馬格南的畫廊占據著一樓最大的區域,這里會不定期舉辦一些馬格南攝影師的作品展,形式也非常多樣,聯展、個展、攝影書展都有,之后我們項目的畢業展也會在這個畫廊進行。緊挨著畫廊的圖書館,在高高的書架中儲存著馬格南攝影師出版的各種攝影書,既有剛剛上市的新書,也有早已絕版的孤本,其中部分有庫存的圖書也可以銷售。這兩個區域,在非布展時間,都對外開放。
而不對外開放的檔案室,是一樓最有趣的地方。這里收藏著無數馬格南攝影師的“存檔”(包括膠片底片和數碼底片)。在這里能看到卡帕兄弟數以萬計的底片,包括著名的《諾曼底登陸》底稿、布魯諾·巴貝(BrunoBarbey)作品底稿等。在2020年底,巴貝去世后,他的遺孀也將作品底稿挪到了這里,以方便她和馬格南的工作人員一起整理巴貝的遺作并交付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檔案室膠片底片的儲存,至今為止依然采用創立初期設計的模式——全部以獨有的邏輯手寫編號后再分類儲存。雖然是手工編號,但是檔案室的負責人說他可以在5分鐘內找到任何攝影師的任何作品。我們現場測試,確實百發百中。

馬格南圖片社檔案館,巴黎,法國,2023。攝影師的簽名印章,會蓋在出售的印刷品上。
其實馬格南檔案室實際上并不止這一個,而是由多個散落在巴黎各處的檔案室組成。為防止出現被“一鍋端”的情況,無論是膠片底片還是數碼印盤,從成立初期,馬格南就有著分散或多處備份的好習慣。
在二樓的開放空間里,除了常常可以看到拿著印刷作品和攝影書正在討論的馬格南攝影師們,還擠著教育(Education)/檔案(Archives)/合作(Partnership)/授權(Licensing)/文化(Cultural)五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以獨屬于馬格南的方式運營著這個獨特的藝術家合作社。
馬格南全球三個辦公室(巴黎、紐約、倫敦)當前總計注冊有50名正式會員(Member)、3名準會員(Associates)和2位提名會員(Nominees),還有11位“貢獻級”合作攝影師(Contributors),哈利·格魯亞特(HarryGruyeart)和史蒂夫·麥凱瑞(SteveMcCurry)都在此列。
而一直被傳為馬格南會員的中國攝影大師呂楠,實際身份則是“通訊員”(Coorrespondents),但是這個稱號已經在十幾年前就不再授予任何人,所以當前持有這個身份的攝影師只有呂楠和以色列攝影師米查·巴-安(MichaBar-Am)。
而以上所有分類,對外都可以被稱為馬格南攝影師。
成為馬格南攝影師,至今依然是全世界攝影師們心目中最高的榮耀之一。但加入馬格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有著極其嚴苛的篩選過程:每年提交到馬格南各個辦公室的會員申請大約有800-1000份,而獲得“提名”的人數往往只有1-2人(最多一年也僅有7人),遇到“不好的年份”,比如2022年至今,更是無一人獲得提名。攝影師獲得“提名”后,會經歷大約4-5年的考察期,才能逐步“晉升”至準會員,最終成為正式會員,而每個階段的跨越,都必須經過超過三分之二的正式會員投票通過。就連馬格南圖片社前任主席、攝影大師馬丁·帕爾(MartinParr),在正式入會投票時,也僅僅以超過三分之二多數1票的微弱優勢通過。
通過觀察馬格南新會員的提名和入會情況,也能看到攝影在每個時代的發展趨勢,以及馬格南主動或被動做出的變化和調整。如今的馬格南,依然像誕生之初一樣,推動著世界攝影史的發展,也在不斷被新的潮流推動著。
我參與的課程有三位馬格南攝影師作為固定導師,西班牙攝影師盧爾·里貝拉(LúaRibeira)、英國攝影師斯圖爾特·富蘭克林(StuartFranklin)和法國攝影師安托萬·D·阿格塔(AntoineD'Agata)。三位攝影師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盧爾·里貝拉擅長將個人紀實融入社會事件,強調“使用攝影媒介來創造關聯,并質疑人與人之間的結構性分隔”,常常深度參與拍攝主題。斯圖爾特·富蘭克林是攝影記者出身,曾任馬格南主席,具有非常傳統的馬格南敘事風格,同時也非常關注攝影中文字與圖像的關系。安托萬·D·阿格塔師從拉里·克拉克(LarryClark)和南·戈爾丁(NanGoldin),他經常以自己的生活經歷為素材,極為感性,拍攝題材也不乏禁忌話題,可以視作“私攝影”的脈絡延續。除此之外,每周都會有不同的馬格南攝影師來做分享,包括前邊提到的哈利·格魯亞特、帕特里克·扎克曼,等等。
初到馬格南,總是耐不住好奇心要去打聽一些“趣聞”或“秘聞”。
比如羅伯特·卡帕《諾曼底登陸》的照片,是不是真的如傳聞一樣,大部分因為沖洗失敗而損毀,所以只留下了寥寥十幾張?而答案是無人知曉,即使資歷最老的馬格南員工,也只是和我們一樣聽過這個傳說。但真相如何,早已經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是大家都愿意相信這個傳說,因為它本身,已經成為了卡帕那張傳奇照片的一部分。
又比如約瑟夫·寇德卡至今為止也不接受任何商業任務。因為極低的物欲,他也將自己的生活過成了最簡單的樣子。在馬格南還未搬家之前,他常常帶著睡袋就住在馬格南的辦公室里,那時候辦公室還特地裝了淋浴間供他使用。搬家之后,考慮到寇德卡越來越大的年紀,睡在辦公室地上總是不太安全,所以新辦公室就沒有再設計淋浴間了。
再比如大家都會很好奇,在一些商業合作中,馬格南攝影師是怎么與甲方溝通的?會不會遇到甲方對攝影師最終作品完全不認同或者不滿意的情況呢?相關負責人表示,合作(Partnership)部門的任務之一就是居中協調攝影師與甲方客戶的溝通,確保項目順利完成。但是馬格南根本上還是以尊重攝影師創作為基本原則,所以這個任務更多的還是要說服甲方理解和接受攝影師的作品。當然,甲方不滿意,甚至一氣之下按合同結清費用,然后轉身另請高明的案例也不是沒有。看來即使成為了馬格南攝影師,甲乙雙方的矛盾依然是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當然在馬格南的學習也不僅僅是“聽故事”。有關于攝影藝術的辯論、幾乎不間斷的攝影拍攝任務和作業、大量的閱讀、學習圖片的編輯與排版、嘗試用圖片講故事,這些才是馬格南課程的精髓。總之非常開心可以面對面向馬格南攝影師們學習,也期待未來在欄目里繼續與大家分享我的學習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