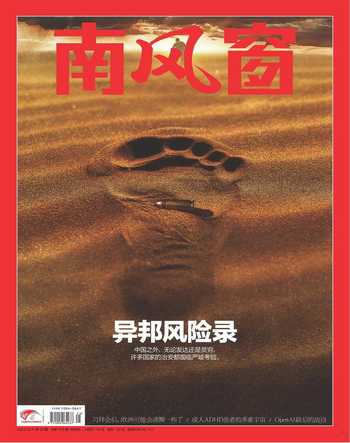我在紐約,恐襲后心境變了
葛文潮

按照美國時間,10月13日是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后的第七天。這場在中東爆發的襲擊的余波,終于傳到了紐約這個世界之都。
周五當天,員工Kenji跟我說他不能去曼哈頓送貨,我才想起前一天看到的一個通告,它建議第二天不要進曼哈頓,因為可能會有恐怖襲擊和暴亂。Kenji的太太在曼哈頓的醫院上班,醫院早早給當班的員工訂了當晚留宿的酒店,以減少路途之憂。Kenji在10月13日凌晨5時開車送太太進了曼哈頓,而平日里,他太太都是搭地鐵上班。
后來我知道,周五這天在時代廣場有大的抗議活動—哈馬斯前領導人哈立德·馬沙爾在社交媒體上呼吁,要人們周五這天聚集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的憤怒。
不再是我熟悉的那個紐約
我記憶里,類似這種關于預防恐怖襲擊的通告,之前只有一次。
“9·11事件”之后,美軍開始攻打阿富汗。有一天,公司總經理把我們召到會議室,非常嚴肅地說,據有關部門的可靠信息,這幾日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沒必要的出行要取消,但公司的運行會正常。我們帶著不安走出會議室,離開公司,打電話告知家人朋友,沒想到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從他們的老板或經理那里得到相同的通告。
部分紐約人惶惶不可終日地過了幾天后,什么都沒發生,仿佛一切如常。
變化的其實是一種心境。2001年9月11日這天,我在上海,剛從紐約回上海探望父母,在電視里看到雙子塔被撞燃燒倒塌,一下子化為烏有。那一天,如果我在紐約,按工作行程,是要到雙子塔附近拜訪客戶的。我沒慶幸當時不在紐約,因為飛機撞樓的那段時間,不是我拜訪客戶的時間。
事后我才知道,一個有生意來往的老板,他大學剛畢業的兒子,那天去雙子塔某公司面試,再也沒有回來;一家粵菜館的大堂經理,是雙子塔頂樓餐館“世界之窗”的唯一幸存者,那天他發燒沒去上班,他的同事全部遇難。
猶記得當時看到雙子塔一下子消失出地平線,我心里還是有些難過的,感覺一下子缺了什么,但也沒太多悲痛,就是覺得可惜,遺憾沒早點去雙子塔頂樓看看。我擔心的是客戶,他們肯定會受影響,生意做不做得下去還真是問題。
兩周后我回到紐約,它已不再是我熟悉的那個紐約了。稍微人多一點的地方,無論是在地鐵站、隧道橋梁,還是大樓門口,都有荷槍實彈的國防軍士兵把守,整個城市的空氣都是緊繃的。
雙子塔燃燒產生的廢氣,長期在曼哈頓區上空盤桓,令人想起在恐襲中枉失生命的冤魂。這些廢氣的味道,傳得非常遠,甚至傳到布魯克林區的家里,即使緊閉門窗,依然可以聞到。“9·11事件”過后的那些年,曼哈頓下城包括唐人街,患上呼吸道疾病、肺癌的人激增。紐約市政府針對這些人提供了免費醫療,甚至在廢氣影響到的地區,只要當事人申請,就給免費安裝空調。
此事過去22年了,雖說時間可以療愈一切,但對紐約人來說,心中的隱痛永遠無法抹平。無論是對紐約人還是其他美國人而言,“9·11事件”都是一個分界嶺,社會、民心、人和人的交往和以前不再相同。容易相信人、比較天真的美國人一夜之間變了,美國人的心態變了。
影響到紐約人生活的事件
我在紐約生活26年了,感覺身在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喧鬧嘈雜、物事紛繁雖然是標配,但大多數日子里還是歲月靜好的。“9·11事件”之后影響到紐約人生活的事件,我記憶里有三次:一次是大停電,一次是颶風桑迪,還有就是剛過去的疫情。
雙子塔燃燒產生的廢氣,長期在曼哈頓區上空盤桓,令人想起在恐襲中枉失生命的冤魂。這些廢氣的味道,傳得非常遠,甚至傳到布魯克林區的家里,即使緊閉門窗,依然可以聞到。
大停電當時,地鐵和交通信號燈都停了,家里沒電更不用說。那天我開車經過十字路口時,都會見到有人自告奮勇地在那里指揮交通。突然的大面積停電,給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見多識廣的紐約人沒有自亂陣腳,該干嗎干嗎,有的餐館點上蠟燭照樣營業。有個西裔員工硬是走了三個小時來上班,知道停電休業后又走了三小時回家。
颶風桑迪是紐約人的又一個共同記憶。曼哈頓下城、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近大西洋的地方,幾乎都被淹了。颶風之后,我經過羊頭灣(水淹重災區),看到馬路上汽車橫陳,都是被海水倒灌沖的,還有滿地的樹枝垃圾。一個住那一帶的朋友,幸虧早早把車子移到別處,躲過一劫。
還有一年深夜暴雪,市政府沒做好鏟雪準備,很多駕車人不得不把愛車拋錨在迅速積雪的馬路上,一高一低踩雪回家。
這些年,紐約人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或是見怪不怪了,或是麻痹了,當新冠疫情來臨時,大家也沒怎么當回事。直到市長宣布全市停工停學,人們自肅在家,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如今新冠疫情結束,生活似乎又回歸正常,但真的如此嗎?表面上是又回到以前節奏了,停業的米其林餐館都重新營業了,包括Eleven Madison Park。這家米其林三星店,在疫情期間賣高檔便當撐了一陣子后,實在撐不下去宣布結業,如今又開門營業了。曼哈頓的那些公司,疫情期間讓員工宅家上班,現在都要求員工回公司了。時代廣場又被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占滿,午夜過后更是人流如織。
偷渡客的問題
紐約又恢復了人滿為患的繁榮,但這次人滿為患比以前多了一點難言的味道。從去年開始,進入紐約的偷渡客已經超過10萬了。
據10月19日的某大報報道,輾轉到紐約的偷渡客已達13.06萬人,紐約市估計今年財政年度要花50億美元,來為這些偷渡客安置住所和提供食物。蜂擁而至的偷渡客,擠爆了紐約213個收容所和17個人權救援中心,紐約市還征用了曼哈頓的酒店來安置這些偷渡客。即使這樣,今年夏天,還是有數十個偷渡客因為收容所滿員,被安排睡在附近的曼哈頓馬路上。

現任紐約市長埃里克·亞當斯,本來信誓旦旦要為全部來紐約的偷渡客提供保障,可最近他改變態度,甚至越來越焦慮。
他一邊要求州政府和聯邦給予紐約更多支持,一邊飛到墨西哥、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告訴那些潛在偷渡客,不要再偷渡去紐約,紐約已經人滿為患,接受不了更多偷渡客。壓力之下,紐約市也開始甩鍋:只要偷渡客愿意離開紐約到其他州,紐約市就提供幫助。紐約還出了新規定:凡單身的偷渡客在庇護所住滿30天后,就必須離開。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工作的紐約七堂空間位于曼哈頓東百老匯街,那里就有一個收容所。收容所隔壁是一家佛寺,另一個隔壁店家是著名的中餐館華園,離七堂所在的大樓也就30米遠。這個收容所,偶爾有流浪漢排在門外等入住,大部分時間門口看不到人,和普通公寓大樓沒什么區別,不知道里面有沒有收留偷渡客,至少我沒見到。可能這個收容所和威爾·史密斯在2006年的電影《當幸福來敲門》里那個收容所一樣,都是傍晚開放入住、早上必須離開那種,所以沒有收容偷渡客。
前陣子是紐約馬拉松日,警察把路口封了后,并沒有更進一步的嚴密防控措施,荷槍實彈的國防軍更是不會見到。一瞬間,我真以為“9·11事件”的陰影已經在紐約上空消失。
對紐約市的老百姓來說,這些偷渡客平時也見不到;老百姓對此唯一關心的是,花在偷渡客身上的龐大開支,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影響。果然,繼明年開始要征收進曼哈頓的車輛費之外,最近當局又宣布,所有的公共圖書館周日閉館。可以預期,未來會有更多的費用被征收,還有其他公共服務會被削減。
偷渡客的問題,對紐約市來說也許是暫時的,頭痛的也更多是市長和疲于應付的市府。而大麻問題,將會成為紐約長期的問題,并影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由于紐約州在2021年立法規定,滿21歲的成年人可以持有和消費至多3盎司大麻或24克大麻萃取物,紐約的大麻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大街小巷。紐約市議會不公布來源的數據稱,紐約的大麻店超過8000家,市長亞當斯則聲稱有1500家。如今走在紐約的大街上,時不時就會聞到嗆鼻的大麻味,比煙味還沖。時隱時現的大麻味,正成為已有的紐約風味里新添加的風味。
仇恨亞裔的犯罪
如果偷渡客和大麻對紐約人來說,是疫情后要面對的新問題,那么對生活在紐約市的亞裔來說,還要面對另一個疫情后遺癥,即仇恨亞裔的犯罪在急劇增長。
根據USAFacts的官網,從今年 6月5日發表的文章看,針對亞裔的犯罪從2020年的330件增加到2021年的820件。最新的數據是CNN在今年10月31日提到的:FBI的數據顯示,2022年仇恨亞裔的罪案數量降低了33%,從2021年的746件降到2022年的499件。按照亞裔隱忍的性格,實際發生的肯定遠不止于此。

在已經發生的仇亞犯罪中,受害者女性居多。人一般都欺軟怕硬,犯罪分子更不例外。記得有陣子,接連發生亞裔在地鐵站被人推下鐵軌的事件。那段時間,周圍的朋友人人自危,我也特別建議家人不要坐地鐵,我本人更是一年里坐不上兩回地鐵。在地鐵這個相對封閉擁擠的空間,被惡意侵犯的概率太高了。
今年8月在地鐵F線上,51歲的華裔女子蘇·楊(Sue Young)遭到了襲擊,當時這個來自內華達州的亞裔家庭正在紐約度假。旁觀者喬安娜·林也遭到了毆打,當時她在拍攝一名黑人女孩騷擾這家人。
事發第二天,打人的16歲黑人少女被紐約警察逮捕。可令人意外、也在情理之中的是,這個華裔女子放了黑人少女一馬,聲稱黑人少女不是因為仇恨亞裔而攻擊她的,她也不會起訴這個少女。待人以恕是我們文化中好的一面,但在美國這個復雜的社會,還真不知道結果會怎么樣。
Sue Young代表了一部分在美國生活的華人,但也有華人不再隱忍。去年春節過后,我接到皇后區圖書館總管移民服務部的總監陳曦的電話,對方要七堂辦一場音樂會—有一個華人自發組織的“停止仇恨亞裔”機構給圖書館捐了一筆錢,讓他們組織一場線上音樂會,讓更多的紐約人了解中國不同地區的音樂文化。于是我找到了我的老師、著名笛子演奏家陳濤,一起策劃了這場線上音樂會。音樂會演奏了從江南到塞北,從國風到少數民族風的各種曲目,也算是為終止仇恨亞裔貢獻了一份力量。
紐約市議會不公布來源的數據稱,紐約的大麻店超過8000家,市長亞當斯則聲稱有1500家。如今走在紐約的大街上,時不時就會聞到嗆鼻的大麻味,比煙味還沖。
變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區
“9·11事件”之后,可能是由于相關部門對恐怖襲擊的高度防控,類似事件不再有,期待今后也不再有。前陣子是紐約馬拉松日,在馬拉松結束前我去了中央公園,只見道路兩旁擠滿了觀眾,以及給選手加油鼓勁的親友團。警察把路口封了后,并沒有更進一步的嚴密防控措施,荷槍實彈的國防軍更是不會見到。一瞬間,我真以為“9·11事件”的陰影已經在紐約上空消失。
我所在的社區海灣嶺(Bay Ridge,位于布魯克林區的西南邊),在“9·11事件”后最大的變化是,大量的阿拉伯移民遷入。離我家兩條街遠的五大道,本來是北歐和意大利移民的社區,現在變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區。整個五大道幾乎布滿阿拉伯人開的各種店,有咖啡店、中東菜館、面包店、家具店、地毯店等等。
前兩日,我在網上訂了一個面包盲盒,取盒子的店就在五大道上,名字叫也門咖啡店,令我想起新聞里提到的從也門發射到以色列的導彈—也門現在可能是恐怖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了。

我找到那家門口貼著“也門咖啡”的店,推門進去。屋頂掛滿了藤蔓植物,店里用綠植隔了幾個空間。這些相對獨立的空間里擺著桌椅,一個白人女子在蘋果電腦上敲打著什么,兩個年輕的阿拉伯男子在喝著咖啡閑聊。我找到柜臺,一個不太年輕、有點壯實的白人男子在收銀機前忙著什么。我給他看我手機里的提貨碼,他一臉困惑。這時,旁邊一個便裝打扮、皮膚黝黑、卷發垂在額上、眼睛閃亮、身形瘦削的年輕人,滿臉笑容,很親切地走過來,看了下我的提貨碼后,就指使白人男子往盒子里裝牛角包、蒜蓉包、菠菜包,裝了滿滿一盒,又很親切地遞給我,還道了聲謝謝。
前兩日,我在網上訂了一個面包盲盒,取盒子的店就在五大道上,名字叫也門咖啡店,令我想起新聞里提到的從也門發射到以色列的導彈。
我拿著盲盒走出門,站在五大道上,滿街燈火,路人悠閑,一片安靜祥和。可就在幾個星期前,就在這條街上,NYPD(紐約警察)驅散了示威游行的阿拉伯人,這些人支持在加沙受難的巴勒斯坦人。那天是10月23日,離哈馬斯攻打以色列那天過去了17天,離Kenji送他太太去曼哈頓上班那天過去了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