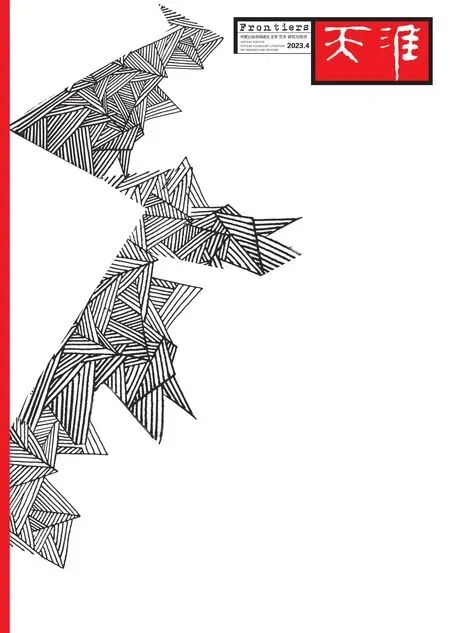流動理發人(外一篇)
陳年喜
一
我們移民小區共有五家理發店,在兩公里長的襟帶相連的門店房散點排開。屬火車橋下生意最好的一家,因為占盡了地利,但奇貴,剪頭每次三十元。我上過一回當,那天下午急著出遠門,又正好經過。那次之后,我再也沒有進過他家的門,不但不進門,每次經過門前時還會給摩托車加一把油,把它甩得遠遠的。小區前門后梢兩家店的生意都不好,但每次剪頭也要二十元,如果只理不洗,十五元,反倒是服務和手藝好許多。
婦女們基本不用理發,勤洗即可,佐以香水,就能往人前面晃悠,當然染發燙發另說,畢竟愛時髦又有實力的是少數。男人很少在小區理發,理一次發的費用能吃兩天飯,買兩包煙,或者打半個月要緊或不要緊的電話。他們一兩個月總會回到鄉下去一趟,侍弄沒荒盡的地,或看看親戚,順帶也把發理了。剃一回光頭,能管三個月。有時實在不得不在理發店理一次,比如兒子一家從外面回來,比如有頭臉的人物要上門來,需要光凈相迎,會因花錢而心疼好長時間。
小區有兩個廣場,大廣場相對排開的兩行是物業和行政機構的辦公室,除了辦事,少有人光顧。群眾文化廣場小一些,但最熱鬧,白天人多晚上人也多,跳廣場舞的和看跳廣場舞的人頭攢動,還有附近來擺攤賣菜的老頭老太。廣場舞是十余年來小縣城一件重要的事,漫漶成河,流淌得到處都是。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經過她們轟轟烈烈的陣仗,朋友化用了兩句古詩:女人不知生活恨,從早到晚廣場舞。她們很多人的丈夫或兒女正在異國他鄉奔突漂蕩。但在這個根本無事可干的縣城,這些人不跳廣場舞又能做什么呢?大約半年前,廣場來了一位流動理發的婦女,一只凳子,一張披布,幾把推剪,生意就開張了起來。因為沒有條件,只理不洗,理完了頭的人,回家想怎么洗都行,剪頭每次只收五元。這種幾乎已經絕跡的有些江湖方式的流動理發正中人們下懷,生意因而不錯。我每次經過正在理發的人,會停下來看一看。除了手藝,我想看看他們身前身后的生活,那些不容易被看見的留痕。
自從春節時“陽”過后,我再也沒有理過發,發長超過了過往任何時候。今天中午從312國道邊的物流點扛了件包裹回來,走到小廣場時正好需要歇一會兒,理發的人也正好在。她看了一眼滿頭大汗的我,欲言又止。那是一雙經歷過風霜的眼晴,已經不再清澈,只有太多的雜蕪。我突然說,師傅,給我理個發。
充足了電的推子在頭頂嗡嗡有聲。對于吃流動飯的沒有半點根基的人來說,需要超常的手藝,更需要超常的認真,任何的失誤與疵都會砸掉飯碗。她的手法很嫻熟,顯然歷經多年,但十分小心,推子走得很慢很細,無微不至。我知道,這一方面是為了出效果,另一方面是想用時長顯示與所收資費匹配。碎發落在披布上,有一半是白的,黑白糾纏在一起,白色的布把白色的頭發放大、彰顯。我怎么也忍不住氣急,不時發出咳嗽聲,我知道身體的抖動會讓她的操作失準失形。我說,我肺不好,總是咳嗽,隨便理一下就行了。她問,感冒了?我說,塵肺,你不懂。她突然停了一下,說,我懂,我家里的也是塵肺。她說的是她的丈夫。我說,怎么搞的,上礦山嗎?她說,不是,打樁,在延安打了兩年樁,給地基打樁,干打,灰土把肺糊住了。我想起在北京時,有一位工人詩人就是打樁工,在南方建筑工地打了多年樁。我一直不清楚打樁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工作,他寫了一首很長的詩《打樁工》讓我看,我因而懂了。我問,身體咋樣?她說,兩年沒下地了。我知道,與地相對的是床,那個男人在床上躺了兩年了。
兩年前的八月,我去秦嶺腹地某縣采訪,見過一位兩年沒下地的人。他家住在三樓,一棟連排的搬遷房。他戴著一條十米長的塑料管子,一頭連著氧氣機,另一頭連著鼻孔,氧氣機放在另一個房間,這樣可以減輕噪音。他的床上被子占了一半空間,他只能靠著它們,日復一日不能躺平。人異常瘦弱,膚色如壁。我離開時,問他,還有什么需要嗎?他說,我想曬一回太陽,我有兩年沒見太陽了。他家的房子窗戶在陰面,離每天的陽光永遠只有一步之遙。
太陽快落山時,我再次經過廣場,理發人已經離開了。她的家也可能很遠,也可能不遠,可能在某條街上,也可能在某座山上。總的來說,那是一個很遙遠的世界,它與所有的人和生活都有一段距離。她把理下的碎發都打包帶走了,每天都這樣。很多年前,它們被用來裝填沙發,賣到本省和外省。現在,把它們拌在土里,是防蟲的好材料。
丹江在對面山腳下閃著的波光日漸盛大,商山上的小桃花正在開放,它們的一部分在丹江口北上。
二
我有一位表叔是個劁豬匠,同時他也是一位走村串戶的理發人。他的理發手藝和劁豬手藝一樣爐火純青。
二十歲前,這位表叔其實一直干著鐵匠的活,那時候鐵匠還可以靠手藝吃飽飯。他給人打造各式農具和日用物品,剪刀、菜刀、剔刀、針鉗等等,有時候也打一把沒什么用場的大刀。再往前回溯,他的爺爺、父親都是打鐵的,這樣說吧,這是一個鐵匠世家。不過,他們的手藝都不怎么好,打造出的家具常被人們詬病。至今,老家百十里方圓的地方還流傳著一段順口溜:
峽河有個劉鐵匠,
打的家具好式樣。
拉葛藤,順皮上,
砍樹子,敲梆梆。
只有割肉血汪汪。
到了這位表叔手里時,技藝不知道怎么就有了突飛猛進。對他來說,要說父輩經驗,那也只能作用在器形上,至于關鍵的淬火,都是靠個人的悟性和靈性。到了表叔正式過日子時,大集體已經解散。他爹在大集體解散前幾年死在了水庫工地,算工傷事故。那時候在大集體里工傷事故不賠錢,只賠了一百個工分,每個工分一斤麥子。沒有了大集體和父親作為依靠,表叔需要自謀生路。有業興旺有業凋零,他不再打鐵,而是跟人學會了劁豬手藝。他看得很明白,哪怕天不下雨河不流水,豬總是要劁的,劁豬是個長遠的飯碗。但人再聰明,也抵不過世事的變幻,在吃過幾年飽飯之后,人們開始進城,全國的農村人都開始進城打工和居住,很多人成了新市民。傳統喂豬的事業成了明日黃花。但天無絕人之路,表叔發現無論走到哪里,老老少少都頂著一頭亂發,鄉村到處缺少理發的人。一般鎮上也有理發店,但要價太高,交通也不方便。
表叔購買了理發的家什,開始流動理發,但他對重要的家伙之一——剃刀很不滿意,從商店買來的家伙總是欠火候,不利落,還常常把人刮出血來。他找來了一根彈簧自打了一把剃刀,裝了槽柄,精致鋒利又華美無比,可以折疊,重要的是,在給人剃須剃頭時,簡直如行云流水。
順著峽河往西走,五十里就到了武關,再往下走,過了商南就到了南陽,峽河的太陽每天也落在南陽方向,仿佛兩個地方天然有著聯系。南陽市有一千萬人口,比有的省會都大。人多了,生意就好做,沒有人,一切都是扯。從前到今,峽河人討生活都往南陽跑。記得有一年,一位鄰居從南陽背回一袋紅薯干,能把人心甜出血來。表叔當然比別人更懂這些。
農村人喜歡看熱鬧,當然也是因為熱鬧變得日益稀少的原因,一個出戲曲的地方,早已沒了劇團。劁個豬,看熱鬧的圍一大堆。劁完了豬,洗凈了手上的血跡,表叔抓住機會擺開理發攤,借主人一把椅子,沒有椅子,站著或蹲著也能理,坐石頭上也能理。剛開始,大伙也不信他的手藝,有人問,能不能理好?表叔說,我理過的頭比劁過的豬蛋蛋都多,你說能不能理好?
表叔給我講過一個故事,那是他一輩子接的最大的單,也是唯一高光時刻。有一位女孩子,人長得漂亮,艷動四方,和對門一位青年談著,三媒六證,收了彩禮,不知怎么又和另外一個村的小伙子好上了,還準備結婚。兩位男青年有一天都發現了情況不妙,也都不放棄,要動手解決。雙方都招了一幫年輕人,摩拳擦掌,要展開搶人大戰。有一方找到了表叔,要全部理出光頭,彰顯決心氣勢。理完了這一方,那一方又找到他,全部理了小平頭。如此一來,整整理了三天,三天后雙方卻偃旗息鼓,不打了,因為女子退了一方的彩禮,問題解決了。雙方都有些懊悔,但木已成舟,剃掉的頭發再也長不回去了。那一回,表叔掙了三百多元。
2010年,表叔上了西寧。
在此之前,表叔從沒到過西寧,連西寧在哪兒也弄不明白,但架不住發小的鼓動。他的那位發小是個角色,十幾歲就去了西寧,干過不少營生,最后倒騰土豆發了財。青海出高淀粉土豆,好吃,供不應求,他一倒騰就是十幾年。發小對他說,西寧人愛吃羊雜,頭發長得快,但人不會打扮,頭不像頭臉不像臉,你去了一定能給他們的形象增光添彩。表叔開始也不信,后來想想,說,也是,你看吃肉的人家發就理得勤些。他打起包裹隨發小上了西寧。
到了西寧,表叔才發現不是那么一回事兒,西寧人愛吃羊雜不假,幾乎天天吃,但不缺理發店。那邊風大,天又冷,北風卷地南風也卷地,在外面擺理發攤根本行不通。表叔從菜市場擺到居民區,從居民區擺到大馬路,從城里擺到城外,從春天擺到夏天,一天根本接不了幾個活。發小感覺對不住他,組織一幫朋友支持了他好幾回,但總不能每天去理一次,頭發長不了這么快。發小的一位朋友在格爾木一座山上開金礦,有一百多名工人,但百里無人煙,沒個理發師,發小又把表叔介紹到了格爾木。
表叔在青海整整待了一年,輾轉了很多地方,嘗試了多種活路,最后發現都比理發費力得多,風險大得多。他最后到了一個牧區,給羊群剪羊毛。那是一個很大的牧區,羊群和大地一樣遼闊,人們騎馬騎摩托車趕牲口,花兒一飄起來就好像再也落不下來,落下來天就黑了。牧人又把他介紹給另一個牧區,這樣,剪完了一家再剪另一家。當然,其間也給人理發。表叔發現,羊的毛質要比人的發質優良得多,羊毛在手里是暖的,人的頭發是冷的,羊毛不變質,人的頭發很快就變色了。他猜想可能是人的飲食太雜,欲望太多,各種營養互相打架,心事互斗,自己把自己克化掉了。
2011年秋天,表叔從青海回來,在家住了一夜,打起行頭又下了南陽。這時候,聽那邊的親戚說,農戶已很少養豬,大型養殖廠興起,也就是說,人們再也不需要游走的劁豬匠,表叔只剩下流動理發一頭。不過,他從此也很少回來,據說,他在那邊參加了樂班,在紅白喜事上給人吹嗩吶。算起來,表叔也六十多了,不知道還吹得動吹不動,能吹出什么花樣來。
關于流動理發人和他們的那些生活的千山萬水,多不勝言,就是把樓前小店里的紙都買來也寫不完。這是一個注定要消失的營生,當然,這也沒什么,就像他們走鄉串戶忙忙碌碌,也沒給這個世界的內容添加什么色彩。沒有了他們,并不影響人們頂著一頭頭發過日子,走過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