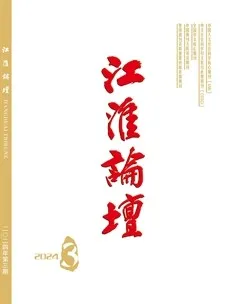分析哲學史兩個教條的批判

摘要:分析哲學史的兩個教條,一是相信在通過給出理由提供對一個哲學主張的論證與通過講述一些因果故事提供對其起源的解釋之間存在根本的分裂;二是相信理性重構主義,即相信基于某些基本假設,任何哲學家的觀點都能被重構成一個理性的體系。類比蒯因“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并結合新康德主義可以論證這兩個教條都是沒有根據的。第一個教條的論證是成問題的,因為既不能通過任何起源性的解釋來論證它,又不能在不乞題情況下論證它,任何這樣的論證都會導致循環,分析哲學史學家只能通過歷史事實作出判斷。第二個教條也是不成立的,因為任何理性的重構都需要準確理解哲學家或文本所說的內容,即任何理性重構不能不考慮歷史理解問題。拋棄兩個教條的結果有二:一是模糊哲學和哲學史之間假定的界限,二是轉向解釋學。通過批判分析哲學史的兩個教條,我們最終可以獲得更加健康的分析哲學史的觀念。
關鍵詞:分析哲學史;兩個教條;羅素;萊布尼茨;康德
中圖分類號:B082"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4)03-0014-012
現代分析哲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兩個教條的影響。一個教條是相信在通過給出理由提供對一個哲學主張的論證(justification)與通過講述一些因果故事提供對其起源(genesis)的解釋之間存在根本的分裂;另一個教條是重構主義(reconstructionism):相信基于某些基本假設,任何哲學家的觀點都能被重構成一個理性的體系。這兩個教條都是沒有根據的,拋棄它們的一個結果是模糊哲學和哲學史之間假定的界限,另一個結果是轉向解釋學。
任何熟悉蒯因作品的人都會看出這是轉換自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之一的《經驗論的兩個教條》。蒯因“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和這里所稱的分析哲學史的兩個教條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似性,并且正如蒯因認為前者需要批判那樣,本文亦將關注對后者的批判。然而,與蒯因的“批判”概念相比,本文的“批判”概念更具康德色彩,并且還考慮了如何通過重視分析哲學史與歷史理解的相互作用來為分析哲學史去除教條。
蒯因的第一個教條是,在基于意義的分析真理與基于事實的綜合真理之間存在根本的分裂。他批判的靶子之一是,認為表達和闡明分析真理是(分析)哲學家的主要任務之一。他的反駁是,我們無法給出分析性的充分的(非循環的)解釋,因此那種分裂并不存在。同樣,本文的靶子之一的觀點是,認為分析哲學史家的主要任務是評價過去的哲學家們對其所提觀點的論證。本文的反駁是:對論證的關注并不能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可以完全不考慮對起源問題的關注,雖然也不能以一種充分的(非循環的)方式論證論證與起源之間的區分本身。
蒯因的第二個教條是還原論,即“相信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都等價于某種以指稱直接經驗的名詞為基礎的邏輯構造”(《經驗論的兩個教條》,第20頁)。他的反駁是,這沒有重視經驗證實的整體特征。這里同樣與分析哲學史的一個基本假設具有相似性,可稱之為重構主義:任何哲學家的觀點都能夠也應該通過展示它們如何從更基本的觀點中得出而被理性地重構。本文的反駁是:我們應該在分析哲學史上更加整體地思考。分析哲學史的這兩個教條顯然是聯系在一起的:論證被看作理性重構的過程。
通過聚焦羅素1900年發表的對萊布尼茨哲學的解釋,本文依次討論和評價每個教條。這不僅是第一個分析哲學史上理性重構的具體例子,而且也為后來的分析哲學史家提供了一個模范。如下表格展示了對兩個教條批判的基本的2×2結構:
移除這兩個教條,將得出一個更健康的哲學史概念。
一、分析哲學史第一個教條及其論證依據檢視
(一)論證與起源之間的分裂與(新)康德主義的解釋
分析哲學史的第一個教條是,相信在通過給出理由而提供對一個哲學主張的論證與通過講述一些因果故事而提供對其起源的解釋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裂。分析哲學史家用這一點來論證他們對論證的關注。但是,對于這個教條及其在分析哲學史上的作用,應該給予什么樣的說明——論證性的還是起源性的呢?
這個教條的根源之一是康德在“法律問題”(quid juris)和“事實問題”(quid facti)之間做出的區分——在正確或合法性問題與事實或起源問題之間的區分。(1)當然,康德想表達什么意思,以及他在工作中有多么重視這一區分,是有爭議的。但是,它的確在新康德主義和后來的傳統,諸如現象學尤其是分析哲學中起到根本作用,甚至今天都很少受到質疑。如果不重視這一點,即通過提供關于起源的一些故事來回答關于論證的問題,那么,人們通常譴責其犯了“起源謬誤”。(2)
這種區分有明顯的吸引力。比如說有人開始相信13×57=741,或者上帝存在,或者謀殺是錯誤的,或者羅素是一位邏輯學家,那是因為被告知如此,但根本沒有提供任何根據,而我們想要的是一個堅持認為它們為真的理由。當然,在過去,其他人(例如神父)或文本(例如《圣經》)的權威被當作擁有一種信念的根據,而拒斥這種觀點通常被看作啟蒙運動的關鍵成就(3)。“Sapere aude”(敢于運用你的理性)作為康德關于啟蒙運動的著名文章的開篇箴言(《何謂啟蒙》),它鼓勵我們思考自身并運用理性去論證我們相信的東西。
然而,這種區分是有問題的。因為在人們為何持有一些信念的問題中并沒有提供根據使得這些信念為真,但是在其他問題中這一點并不那么明顯。也許我的確開始相信某些東西,比如說數學——從第一原則出發開展研究,信念的起源似乎也是持有它的理由。(4)并且,如果可靠的某人告知某些東西,難道這就沒有提供相信它的理由嗎?例如,知道一些關于“好的權威”的東西,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擔心的并不是“權威”,而是權威可靠與否。所以,起源有時候能提供理由嗎?如果的確如此,那么,如何辨認起源、如何從典型的復雜的起源過程中提取理由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如何進入理性空間——假定的純粹推理領域?即使我們在那個空間中推理,也會發現起源過程的侵入。非常清楚,一個人正式提出相信或做某件事的理由往往只是掩蓋動機的一個煙幕彈。在這里,如果我們想談論“真實的”(“心理學的”而非“邏輯學的”)理由,那就會顯示這整個領域有多么棘手:把理由的小麥從起源的谷殼中分離出來實屬不易。
一種更深層次的擔心是維特根斯坦式的。有時給出論證(如果被理解為從某些更基本的東西中推導出來),所有人都傾向于說“這就是我們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或“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但如果我們被鼓勵說得更多,當達到牢固的基座時,我們可能會提供一個起源故事去幫助別人理解。任何論證的方案都有其限制和條件。
分析哲學史的第一個教條最好稱為一個教條而不是一個原則,因為它自己的論證是成問題的。如果這個教條是正確的,那么我們不能通過任何起源性的解釋來論證它(例如,通過追溯到康德那里,展示它如何根深蒂固),因為根據事實本身(ipso facto)就會否證它。但是,我們如何能在不乞題情況下論證它呢?如果這個原則在某種意義上對于論證是構成性的(排除了起源性解釋的意義),那么,如何能夠非循環性地做到這一點呢?這將會是何種類型的論證?如果沒有任何論證的話,它的確就會被當作一種教條。
解答這些問題,可以試著在一些區分的來源中尋找答案,尤其是康德自己的著作,以及對此區分最成熟的討論——新康德主義者文德爾班的文章《批判的還是起源的方法?》(Critical or Genetic Method?)。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純粹知性概念的演繹”這一章的開頭引入了法律問題(quid juris)和事實問題(quid facti)的區分:
法學家在談到授權和主張時,把一樁法律訴訟中的法律問題(quid juris)和涉及事實的問題(quid facti)區別開來,而由于他們對兩方面都要求證明,這樣,他們把前一種證明,即確立授權或合法主張的證明,稱為演繹。(《純粹理性批判》,A84-5/B116-7)
拋開關于本章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個有爭議的問題不談,本文僅關注法律意義上而不是邏輯意義上理解的“演繹”概念。
康德所說的“法律演繹”是什么意思?一個例子足以說明。考慮一下誰是王位合法繼承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法律問題(quid juris)。在一個給定的法律體系下,假設某人是在位君主在世的最年長的孩子,那么他就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這就告訴了我們法律是什么。但是,要回答某個特定的人是不是合法繼承人的問題,就必須確定他是不是在位君主在世的最年長的孩子:這就是在回答事實問題(quid facti)。
在他的倫理學講座中,康德以三段論的形式列舉了這樣的例子。(5)這個問題可以表述如下:
(A1)任何人只要是在位君主在世的最年長的孩子,他就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
(A2)艾瑞斯是在位君主在世的最年長的孩子。
(A3)艾瑞斯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
(A1)是大前提,陳述相關法律;(A2)是小前提,康德稱之為事實陳述(factum);結論(A3)是將法律應用于它所包含的事實而得出的(如康德所說“Applicatio legis ad factum sub lege sumptum”,Vigilantius Ethics Lectures,562)。這就是對聲稱艾瑞斯是王位合法繼承人的法律演繹。
由此,顯然(A2)提供了對這個事實問題的回答:誰是在位君主在世的最年長的孩子。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律問題?而這就是上面的表述方式:誰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但這點在下面兩個問題之間卻是含混不清的:
(1)要成為這個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某人必須擁有什么性質?
(2)哪一個特定的人才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
(A1)回答(1),而(A3)回答(2)。回答(1)是給出一個特定的描述(“在位君主在世的最年長的孩子”),而回答(2)是給出一個專名(“艾瑞斯”)。將它們聯系起來而賦予這個法律演繹效力的是,這個特定的描述和這個專名具有相同的指稱。
這表明我們可以區分兩種法律問題,即僅通過澄清法律就可以回答的問題,和要求回答事實問題即回答法律應用如上“演繹”出答案的問題。康德所談的“法律演繹”是后者。盡管很容易認為法律問題(quid juris)只是第一種問題(它們只是“法律的”問題),如果我們也這么認為,就會在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之間被誘導看出分裂。然而,如果我們認識到了第二種問題,情況就更為復雜了,對法律問題的回答取決于對事實問題的回答。正是后面這種情況與分析哲學史有關。
在這兩種情況中,法律問題都不能僅通過回答事實問題來回答,所以,區分仍然存在。這樣,我們就回答了我們自己的事實問題:論證與起源之間的區別以法律問題/事實問題之間區分的形式出現在康德的著作之中。所以,這里有一個來源。但是,說他作出了這個區分并不意味著說他給出了這樣做的正當理由,盡管我們能理解它在我們所考慮的特定例子中的作用。仍然需要回答這個法律問題:我們論證了論證和起源之間的區分了嗎?
論證和起源的區分在新康德主義有著根本的重要性,文德爾班稱之為康德的基本思想(Grundgedanke)。文德爾班1883年的文章《批判的還是起源的方法?》對此作了充分討論和辯護。他指出,“一種批判的哲學概念的可能性的洞見”正是根植于康德所設定的“根據”(grounding)和“起源”(origin)之間的區分(Methode,272)。因而,康德的批判方法通過與被視為科學獨特的“溯源方法”相對比而得以解釋和激發。
文德爾班的出發點是這樣的主張:一切知識都涉及普遍對特殊的隸屬。他以此說明演繹(從普遍到特殊)和歸納(從特殊到普遍)是僅有的兩種證明,但兩者都依賴自身不能被證明的公理。這就提出了公理的有效性( Geltung)問題,并且他認為回答這個問題是哲學的核心問題(Methode,272-274)。如何實現這一點呢?根據文德爾班,公理不是邏輯上必然的,正是因為它們是不可證的,這就留下了“事實的有效性”或“目的論的必然性”問題(Methode,275)。在這篇文章的其他地方,他批評前者而提倡后者。尋求事實的有效性方式有二,要么是通過經驗心理學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持有哪些原則,要么通過歷史學告訴我們人們在歷史中持有過哪些原則。但是,這兩種尋求事實有效性的方式都不能論證這些原則本身的合理性。大多數人,甚至所有人都可能在某些事上犯錯誤,并且如果人們訴諸歷史的“進步”,那么就預設了判斷進步的標準。概言之,溯源的方法預設了這些公理,而這些公理本身又無法在事實中得到驗證,否則就會出現循環論證。(Methode,275-280)
這就剩下目的論的有效性了,它在于表明“如果要實現某種目的,就必須把公理的有效性認作無條件的”(Methode,275)。在邏輯中,文德爾班認為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真”,那么我們必須接受邏輯法則的有效性。這包括“后承公理”(反映了肯定前件式的規則)、無矛盾原則和充分理由原則。(Methode,282)但是,或許也可以把區分論證和起源的這一原則當作“邏輯的”。我們可以把文德爾班的觀點解釋成它隱含地論證追求真時區分論證和起源的這一原則必須也被“認作無條件的”。理解它起作用的目的,也只能是在目的論上有效。這同樣適用于歷史學:“在對歷史做判斷的意義上,批判的歷史只有伴隨一種目的論意識(zweckbestimmtes Bewusstsein)才有可能。”(Methode,279)
然而,就像康德的情況一樣,文德爾班認識到并且的確強調了規范性事物(the normative)和事實性事物(the factual)之間的聯系。他寫道:“哲學只能在經驗的幫助下解決其尋找規范的任務。”(Methode,282)他又說:
在哲學中,起源的事實從來不是證明的依據,但它們卻是批判的對象:心理學和歷史學必須已經將認知材料從科學之前的模糊性中闡述出來,以至哲學問題可以從中以概念確定和有序的方式發展出來。(Methode,283
這里涉及的是通過認識歷史學的重要性來深化康德的批判方案。(6)在文章的最后兩段,文德爾班談到了這些目的論有效原則如何從“對歷史的批判性闡釋”中產生出來,即要求人們充分認識到“歷史的取向”(Methode,284-285)。
論證與起源之間這種區分的(新)康德式的解釋(康德意義上的批判),可以通過把康德和文德爾班的觀點放在一起來考察。這種區分的確是有效的,但不能理解成暗指論證與起源完全無關。所以,并不存在第一個教條所陳述的那種分裂。例如,在做出法律判斷時,論證與起源都需要;而對公理的論證要求反思起源事實。這是一種論證,盡管這種論證不是“邏輯證明”意義上的,而是“目的論有效性”意義上的,但是對這種論證的認識卻來自歷史反思。所以,哲學和歷史本身并不能像通常設想的那樣可以截然區分。
(二)分析哲學史家既要哲學論證,也要正確理解歷史
康德對法律/事實之間區分的解釋,為思考分析哲學史的第一個教條的作用提供了典型。分析哲學史家強調,他們的主要關注點是評價以往哲學家提出的或在哲學文本中發現的主張。對應上面提出的三段論,可以提供以下三段論,在最簡略的可能的示意圖中表現分析哲學史學家做出的兩種判斷:
(B1)任何認為X的人這么做都是正確的(或錯誤的)。
(B2)P認為X。
————————————————
(B3)P認為X是正確的(或錯誤的)。
(C1)陳述X是真的(或假的)。
(C2)文本T陳述X。
————————————————
(C3)陳述X的文本T表達了一個真理(或謬誤)。
分析哲學家想得出如(B3)和(C3)所示的結論,但考慮到康德對法律判斷的分析,重要的是認識到這里有兩個前提。必須評估這些論點,并作出某些評價性的判斷,就像在相關三段論的第一個前提中所體現的那樣。但也必須確定哲學家或文本事實上確實提出了相關的主張,如第二個前提所述。這就需要回答一個歷史問題,因而,哲學史研究所作的判斷就像法律判斷一樣既要求回答法律問題,也要求回答事實問題。
轉向分析哲學史的一個例子:羅素在1900年出版了《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判性解釋》一書,這是在他反叛的中期——和摩爾一起反對英國觀念論。的確,此書在反叛英國觀念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自身就具有歷史學意義,這是一個事實。通常來說,研究以往的哲學也是建立一種新的哲學方法或觀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本書源自羅素1899年春季學期在劍橋講授萊布尼茨的一門課程,完成于1900年8月在巴黎國際哲學大會上與朱塞佩·皮亞諾(Giseppe Peano)的關鍵會面之前,而正是那場會面導致了他轉向新的數理邏輯。
羅素在序言中明確表達了對第一個教條的認可。他首先區分了兩種哲學史研究方法,一種“主要是歷史的”,另一種“主要是哲學的”。第一種強調“關注時代或其他哲學家的影響,關注哲學家的體系的發展和啟發他提出主要思想的原因”。而第二種涉及“對以前的哲學家持一種純粹的哲學態度……在這種態度中,我們不考慮日期或影響,只尋求發現可能的哲學的偉大類型,并通過研究過去偉大哲學家所倡導的體系來指導自己的探索”。
他認為只存在少數這樣類型的哲學,并且通過“考察任何類型中最偉大的代表”可以了解到支持和反對這種哲學的理由是什么(Philosophy of Leibniz,xv-xvi)。
這里的關鍵不僅是“歷史的”和“哲學的”兩分的問題,更是主張哲學史的哲學部分在于識別哲學的“偉大類型”以及它們的“最偉大的代表”,以此來評價這些哲學。他說:
在這種探究中,哲學家就不再從心理學的角度加以解釋:他被認為是他所堅持的哲學真理體系的倡導者。他是通過怎樣的發展過程得出這一觀點的,盡管這本身是一個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在邏輯上卻與探究這一觀點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無關;在他的觀點中,當這些觀點被確定之后,在對這些觀點本身進行批判性審視之前,最好先刪除那些似乎與他的主要學說不一致的觀點。簡而言之,我們在這一研究中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哲學上的真理和謬誤,而不是歷史事實。(Philosophy of Leibniz,xvi(7))
在這里,我們有一個對心理學的或因果性的解釋與邏輯的或哲學的論證之間的區分(distinction)——確實是分裂(cleavage)的清晰陳述。這個教條位于分析哲學史的核心。
回到如上所示的史學三段論可以發現,分析哲學史學家的目標是對“哲學家P認為X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或“陳述X的文本T表達了一個真理(或謬誤)”這樣的形式做出判斷。但這不僅要求確定X是正確的(或錯誤的),還要確定P或T實際上主張X。在文本中這似乎很容易確定:我們只需找到陳述X的文本。但這沒有聽起來那么簡單,可能會有真實性、翻譯或理解等問題,例如,確定這個主張是確實被陳述的,而非僅僅被假定的或假設的。而當確定了哲學家P主張X時,又有更多的問題,我們需要確切地知道這個主張是何時提出的,以便了解他們觀點中出現的變化。例如,它是否代表了他們深思熟慮的觀點,而不是對帶有敵意的批評意見的沖動反應;在更廣泛的語境下隱含著什么限制或約束,如此等等。為了證實一個哲學家或文本主張X是正確或錯誤的這樣的判斷,我們需要做嚴肅的史學工作。
羅素對此的看法是什么?他關于萊布尼茨的書包含了一個長長的(100頁的)附錄,主要參考的是C.J.格哈特(C. J. Gerhardt)1875—1890年編輯的七卷本萊布尼茨著作合集,這為他的解釋提供了文本依據。所以,就C類型的三段論而言,羅素給出了對事實問題的回答,但依賴他人的工作;就B類型的三段論而言,雖然這也取決于羅素閱讀和選擇的文本,但也取決于他如何解讀它們來表達萊布尼茨的哲學。關鍵點在于,這兩種類型的三段論中兩個前提中的“X”的意謂相同,這對得出結論是至關重要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確定一個人做出正確還是錯誤(真與假)的判斷的東西就是哲學家P實際上所主張的(或文本T實際上陳述的)東西。當然這是顯然的,但它確實需要準確地理解哲學家或文本之所說,這也是需要歷史理解的地方。
分析哲學史學家只能通過預設或依賴歷史事實來作出判斷,正如B型和C型三段論的結論所示的那樣。如果他們的結論所依賴的第二個前提是錯的,那么他們的結論就是錯的。羅素可能會說他只關心“哲學的真理或謬誤……而不是歷史事實”,但是這只有在其他人確定了歷史事實之后才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第一個教條斷言的是論證與起源之間的分裂(cleavage)而不僅僅是區分(distinction),它鼓勵像羅素這樣的人錯誤地輕視歷史考察在哲學史中的重要性。哲學史學家做出的判斷需要同時回答法律的和事實的問題,哲學史不僅要求哲學的論證,而且要求歷史的公正(historical justice)(8)。
二、分析哲學史第二個教條及其論證根據分析
(一)理性重構觀念的起源與羅素對萊布尼茨哲學理性重構的分析
分析哲學史的第二個教條是重構主義(reconstructionism):相信基于某些基本假設,任何哲學家的觀點都能被重構成一個理性的體系。第二個教條顯然依賴第一個教條,因為理性重構的觀念預設了從起源問題中區分出論證問題的能力,還暗示著懸置后者的可能性。因此,關于第一個教條的任何問題都很可能反映在第二個教條中,所以研究后者能深化對前者的批判。
理性重構觀念的來源可以追溯到約翰·雅各布·布魯克(Johann Jacob Brucker)的工作,他首先提出哲學史的任務是基于某些“原則”重構哲學的“體系”。(9)隨后的故事貫穿了康德和一些新康德主義學者。(10)但是,由于這里關注的是分析哲學史上理性重構的這一類型,所以,讓我們(懷著應有的不安)懸置與之聯系的歷史而回到確立這個類型的作品——羅素1900年關于萊布尼茨的書,它確實將萊布尼茨的哲學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如果要評估這樣一種類型的哲學,那么就需要回答另一個事實問題:理性重構的范例是什么?
羅素主張哲學史的“哲學”方法在于識別和評價“偉大類型”的哲學和它們“最偉大的代表”。所以,根據羅素的觀點,萊布尼茨是什么“類型”的哲學中最偉大的代表呢?答案并非簡單明了,因為羅素認為實際上萊布尼茨的哲學是不一致的,因此——據他在前言中所說——在其能夠成為一種“類型”之前,需要刪減掉不一致的部分。然而,羅素聲稱,“萊布尼茨本應寫作的體系”基于5個主要前提,他陳述這些前提如下:
1.每個命題都有一個主項和謂項。
2.一個主項可以具有若干個存在于不同時間的性質的謂項。(這樣的主項可稱作實體)
3.不斷言處于特定時間的存在的真命題是必然的和分析的,而那些斷言處于特定時間的存在的真命題則是偶然的和綜合的。后者依賴終極因。
4.自我是一個實體。
5.知覺產生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即關于我自己以及我的狀態之外的存在物的知識。(Philosophy of Leibniz,4)
第二個前提和第三個前提可以看作對第一個前提的闡釋,而根據羅素,第四個前提和第五個前提是與第一個前提不一致的。因為他將第一個前提看作根本的,所以,這表明萊布尼茨所代表的類型是基于這個前提的哲學。
羅素在第二章的開頭聲稱,所有可靠合理的哲學都應當從對命題的分析開始。他用第一個前提來概述萊布尼茨的出發點:把一個命題分析成主項和謂項。正如羅素所理解的那樣,這蘊含著每個命題都可還原成一種主-謂形式。這也是羅素拒斥的主張,因為在他看來我們不能這樣還原(非對稱的)關系命題,所以,任何依賴這第一個前提的哲學類型都是錯誤的。
基于以上論點,羅素在該書第二章第8節,從認為真命題就是謂項包含在主項之中(除了斷言存在的命題)的觀點,到其單子論的“全部或接近全部”的萊布尼茨哲學,開始了所謂“純粹邏輯的論證”(Philosophy of Leibniz,8-11)。這是一種徹底的重構主義:萊布尼茨觀點被看成從很小一組前提中推導出來的。羅素在書的其余部分給出了論證的細節,在這里只考慮其中部分論證細節。
根據羅素,萊布尼茨的觀點所代表的哲學“類型”究竟是什么?羅素的基本主張是每個命題都可還原成一種主-謂形式。羅素不僅將其歸于萊布尼茨,還歸于許多萊布尼茨之前的學者和后繼學者們,包括笛卡爾、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布拉德雷。羅素認為可還原性問題“是所有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而且,他將其與關系的實在問題聯系起來。實際上他認為拒斥關系的“獨立實在性”的觀點依據在于主張每個命題都有一個主項和謂項。
在第二章第10節,羅素引用了萊布尼茨的一個討論(非對稱的)關系命題的段落,可以將萊布尼茨的論證展示如下。考慮這個命題:
(L) 線段L比線段M更長。
根據萊布尼茨,這可以用三種方式來“考慮”或分析。第一種,可以把“線段L”當作主項,把“比線段M更長”當作謂項;第二種,可以把“線段M”當作主項,把“比線段L更短”當作謂項。在這兩種情況中,我們都將其分析成了主-謂形式。萊布尼茨認為,還可以把它“考慮”成斷言一種存在于兩條線段之間的關系的命題。但是,這里的“主項”是什么?如果把兩條線段都當作主項,那么,萊布尼茨寫道:“我們在兩個主項之間就會有了一個偶性(在這里所歸屬的就是關系),它的一條腿在一個主項之中,另一條腿在另一個主項之中;這同偶性的概念是相矛盾的。”這就把關系本身看作了與被當作主項的東西相對立的主項。萊布尼茨寫道:
我們必須說,在考察它的第三種方式的情況下,這一關系實際上是在這些主項之外的;但是由于它既不是一個實體又不是一個偶性,那就必定是一個純粹觀念性的東西,盡管如此,對它的考察還是有益的。(Leibniz,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Leibnitz,266-267;cited by Russell,Philosophy of Leibniz,13)
羅素反對的正是把關系當作“純粹觀念性的東西”。如果要求萊布尼茨解釋這一點,羅素寫道:“他會宣稱這是心靈的一個偶性。”(Philosophy of Leibniz,13)羅素繼續說,為了堅持主-謂原則,萊布尼茨被迫“接受康德式的理論,即認為關系是真正的心靈的作用”(Philosophy of Leibniz,14)。因此,萊布尼茨被置于與康德相同的哲學類型中——實際上,任何認為關系是“觀念性”的人所持的觀點,都被羅素當作源自堅持這一學說,即每個命題都有一個主項和謂項,他將這一學說看作產生萊布尼茨哲學的第一前提。簡而言之,萊布尼茨的體系所體現的哲學“類型”是一種觀念論。(11)
為什么關系問題對于羅素如此重要呢?答案在于他對數學基礎的關注,自1895年到1910年代早期即當《數學原理》出版的時候,他主要關注數學基礎。羅素的擔憂是,如果關系不是“實在的”,那么關系命題就不可能是真的,因而數學自身也不可能是真的,因為數學充滿了關系命題。更具體地說,所有的系列都涉及非對稱關系,例如自然數的系列,所以,任何理解數學本質的嘗試都必須提供對這些問題的解釋。但正是涉及非對稱關系命題,例如上面的(L),羅素特別反對將其還原成更簡單的主-謂命題。(Beaney,Logic and Metaphysics,270-271)
在英國觀念論的影響下,羅素作為一個新黑格爾主義者開始了他關于數學基礎的工作,而且把內在關系學說看作新黑格爾主義的核心——正如他后來所說,主張“每個關系都是基于關系項的諸本質”(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43)。他在萊布尼茨哲學中也發現了這一學說,最明顯的表達在不可分辨事物的同一性原則中,這也是為什么他關于萊布尼茨哲學的工作變成了發展他自己哲學觀點的試驗場的原因。
羅素(作為一個好的黑格爾主義者)主要關注的是他在數學中看到的各種矛盾。其中之一就是他所說的“點的矛盾”:所有的點是完全相同的,然而每個點又是不同的(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196),這似乎表明不可能有幾何學上的點。現在,對此明顯的回應是,區分質的相同和量的相同:盡管點在質上是相同的,它們在量上卻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僅僅在(外在的)空間關系上。但是,羅素的新黑格爾主義尤其是內在關系學說排除了這種回應。因為,如果點只是在它們的(外在)關系上有區別,那么,它們的固有性質就會存在相應的差異,這意味著它們在質上并非都是相同的。
羅素在算術和其他地方發現了相似的矛盾,并且于1898年出版《相關性的矛盾》單行本。羅素將其描述為“兩個詞項之間差異的矛盾,而沒有應用它們的概念之間差異的矛盾”,認為它遍布于數學之中(An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Reasoning,166)。這樣的描述澄清了它是如何依賴新黑格爾主義內在關系學說的,因為沒有這個學說就不會有矛盾。兩個東西可能在質的方面是相同的(相對于一組概念),然而,在“外在的”(例如,空間的)關系的意義上卻是有差別的。以一種如此普遍的形式表達它,對數學的一致性產生如此嚴重的后果,似乎終于使得羅素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到幾個月,他就放棄了數學中遍布矛盾的想法,這實際上顛倒了這一論點,因為內在關系學說導致了本應被拒絕的矛盾。(12)
隨著放棄內在關系學說,羅素打開了一條更合適的通往數學哲學之路,正是數學哲學這一研究占據了羅素接下來的15年時光。這就要求發展一種體現在量化理論中的關系邏輯,然而,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二)對羅素理性重構萊布尼茨哲學的評價及其歷史學教益
羅素在1899年的前3個月講授關于萊布尼茨的課程。為了做好準備,他在前一個夏天就開始閱讀萊布尼茨的著作,而這本書完成于1900年的夏天。(13)在《我的哲學發展》中,他聲稱“當我在研究萊布尼茨的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關系問題的重要性”(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61)。但這不可能是正確的:正如我們所見,羅素在研究萊布尼茨之前就已經關注內在關系學說了。然而,他對萊布尼茨的研究工作無疑促進了他的思想的發展:它幫助他擺脫了新黑格爾主義,并闡明了內在關系學說的錯誤之處,結果是發展了關于關系的實在論。(14)所以,得出的第一條歷史學的教益是:正是羅素自身的哲學關切促使他提出了萊布尼茨哲學的根本問題,并因此提出了他所做的理性重構。
顯然,也可能存在別的理性重構方式。所以,需要論證羅素的重構公正地對待了萊布尼茨自己“真正”的想法。即使可以找到一些文本支持這一點,也有其他文本可能表明一種不同的重構。(15)羅素聲稱他關注萊布尼茨“本應寫作”的東西,卻由于他自己的哲學關切而犯了乞題的錯誤。如果關于萊布尼茨實際上如何思考的問題被斥為“僅僅是歷史的”而加以拋棄,而去談論“萊布尼茨的哲學”“萊布尼茨的觀點”“萊布尼茨所意謂的東西”等等,羅素真正關注的就只是萊布尼茨哲學可能被描述成的哲學類型,那么貫穿全書他所做的事情就會是不真誠的。所以,第二條歷史學的教益是:評論者在重構代表性哲學家的觀點時需要非常小心謹慎。
這并不是說羅素的重構沒有價值。相反,這本書在闡釋萊布尼茨著作中所發現的各個學說之間的關系是有益的。把這些工作闡釋得越清楚,就越容易考慮其他重構的方式、評估這些學說與給出的理由。但這表明價值更多地在于聯系,而不是基礎主義,這明顯類似蒯因對還原論的教條的批判。尋找一個基礎是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確實涉及一個“體系”,那么,它的力量就在于整體結構,而不是由一小組假定的前提所提供的基礎,蒯因強調指出真值是如何分布在一個整體上的。所以,第三條歷史學的教益是:研究哲學史應該更具整體意識。一個學說的意義必須在一個語境中去追問,而不是孤立地去追問。
羅素主張在第一個前提的基礎上闡明萊布尼茨的“體系”,而且這個前提與第四個和第五個前提之間存在不一致。羅素在后面的章節中詳細地說明了這點,最顯著的就是第九章,他把這種不一致看作對萊布尼茨單子論的根本反駁。但如果碰巧認為單子論就是萊布尼茨哲學的核心特征,那么我們應該嘗試圍繞單子論重構其他一切東西——或盡我們所能去做。那么,我們同樣可以把它當作對羅素重構的一種歸謬(reductio ad absurdum)。所以,第四條歷史學的教益是:如果做出了不一致的指控,我們就需要特別小心謹慎。
羅素區分了萊布尼茨哲學中的兩種不一致。一種是上文提到的萊布尼茨哲學的主要前提之間的不一致,它迫使我們決定拒絕哪一個。另一種不一致,他寫道,“這完全是產生于因為害怕承認與萊布尼茨時代的主流觀點相悖的后果”(Philosophy of Leibniz,3)。他給出的例子是萊布尼茨關于罪和上帝存在的觀點,該書的最后兩章討論了這一點。正是在這里,他批評萊布尼茨最為嚴苛,指責萊布尼茨為了避免斯賓諾莎的無神論和決定論不惜故意自相矛盾,屈從于不誠實和欺騙。然而,如果要避免羅素做出的那種過于草率的判斷,確實需要更詳細地考察歷史,考察萊布尼茨言論的背景、他發表這些言論的時期,以及同時代人的觀點等等。所以,第五條歷史學的教益是:只有對歷史因素的關注遠遠超過羅素所允許的程度,才能公正地對待哲學家的觀點。(16)
當羅素提倡考察哲學“類型”的時候,這是他為自己論證關于評價和拒斥觀念論(他將新黑格爾主義視為其范例的類型)的方式。這種方式本身并不是不合法的,只是考察過去的哲學文本的一種方式——實際上,也是僅有的一種哲學方式。更謙遜地說,我們可能只是對特定的學說以及支持和反對這些學說的論據感興趣,而不想將作者類型化。然而,把我們得出的各種歷史學的教益放在一起來看,在羅素對萊布尼茨的解釋中最成問題的是他對歷史考察方法的輕視而造成的曲解。我們在批評第一個教條時所說的一切,更加不用說也適用于像羅素這樣嘗試理性地重構哲學家的觀點。任何認為哲學家持有某一特定學說為其根本的主張,都需要證實。像羅素所做的那樣,僅僅靠展示其他學說如何從該特定學說中推導出來,那是不夠的。甚至,指控哲學家自相矛盾,卻沒有嚴格地考察被斷言不一致的學說陳述的背景,那就更加不能令人滿意。
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批評羅素癡迷于發現萊布尼茨哲學中的矛盾。表面上似乎作為矛盾出現的東西,特別是把萊布尼茨在不同時間點提出的主張作為其思想中促使其哲學發展的張力,這樣反而可能揭示更加重要的意義。卡西爾的主要例子是萊布尼茨的實體概念,它是在很長時間以來通過賦予其一個動力學特征而重塑了傳統的亞里士多德的實體概念。卡西爾寫道:“做出這種反對的評判,完全是片面的和非歷史的,在其中,整個內在張力所在的地方被當作矛盾。”(Leibniz’ System,539)根據卡西爾的觀點,哲學史學家尤其應該識別和解釋的是某些哲學家思想中的張力,且這要求比羅素愿意尋求的歷史理解力更多。
哲學史學家工作的核心是對某人哲學思想的內在動力保持敏感,不僅僅是挑選和裁定哲學史上做出的論斷。只是竊取觀點和論證的文本以便促進某人自己的哲學計劃,這不是在做哲學史。但是也不是簡單地報告我們發現的觀點,作為哲學家,頭腦中是帶著問題去閱讀哲學文本并且希望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的,這就是伽達默爾(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中闡釋作為“視域融合”的理解觀念時所強調的東西。當我們與文本對話時,尋找答案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其目標“總是超越單純地重構”(Truth and Method,374)。如果不是在不停地尋求和努力回答哲學問題,那么我們就不是在做哲學史;如果不是在尋求理解一個過去的哲學家或文本實際上說了什么,那么我們就不是在做哲學史。(17)這兩者的結合正是解釋學的標志。
三、結論:去教條的分析哲學史
羅素關于萊布尼茨的著作不僅對于萊布尼茨研究,而且對于后來的哲學史尤其是分析哲學史都是開創性的,它也在分析哲學本身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任何哲學傳統的建立都是部分地通過相應的哲學史而實現的、在自我確證中得以闡釋的。(18)所以,任何哲學史本身也必須放在歷史背景中看待。以與蒯因批判經驗論的兩個教條的類比作為出發點,我強調了分析哲學與分析哲學史之間的聯系。關于這個類比,還可以說得更多,尤其是要把我所隱含的東西說清楚。但是,我的確認為分析哲學史可以被有效地描述成被我所識別出的兩個教條所支配。這兩個教條都有自身有教益的歷史(我剛剛提到過的),也都引出了我(作為一個好的分析哲學家)主要關注的論證問題。
教條是未被論證的信念,而在論證分析哲學史的兩個教條方面確實存在問題。如果論證是從某些更基本的東西中推導問題,就像反映在理性重構的觀念中那樣,那么情況確實如此。但最基本的前提和原則本身呢?這里需要一個不同的關于論證的觀點。羅素提倡一種被理解為直接親知的“直覺”(見Russell: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preface),但是,如果其他人沒有我們的“直覺”呢?這里嘗試去展示他們相信的其他事物如何從直覺或這樣的前提和原則中推導出來,這些前提或原則在給定的實踐或思維方式中起到了作用。第一種方法可能是更“哲學的”,第二種方法則是更“歷史的”。任何一種方法都可能有所幫助,但結合這兩種方法或許是最好的,它能促進文德爾班所說的批判性反思。康德認為基本原則要求一種“先驗演繹”;文德爾班談到了“目的論的有效性”,并在闡釋時談到了“目的論聯系的內在必要性”(Methode,283)。把它們放在一起,這樣的基本前提和原則必須是被內在地加以演繹的——不是以某種方式“直覺”到它們的真理性和有效性,而是通過認識到它們在相關思維體系中的(規范的)作用,這些思維的體系既歷史地又哲學地發展著。
分析哲學史的辯護可以從這些方面入手。就第一個教條而言,論證與起源的區分深深根植于當代哲學。令人反感的是這種假設,即它表現了一種分裂,且輕視起源性的和歷史的考察。理解分析考察與歷史考察之間復雜的相互影響,才能給予分析哲學史在哲學史中合適的地位。就第二個教條而言,通過認識到理性重構在重構者自己的哲學中(正如在羅素的情況中說明的那樣)與在擴展理解可能性的解釋學空間中所起的作用,理性重構可以是目的論有效的。我們可以慶賀理性的重構如何豐富了這一詮釋學空間,開辟了新的方式來審視文本,同時又抵制了文本的霸權訴求。
然而,這樣的論證要求放棄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哲學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尋找無條件為真和有效的基本前提和原則——反對一種特定的看或思考問題的方式。換句話說,用它自己的術語——分析哲學史是不可能從它自己的資源中得到“論證”的。它要求一種更廣闊的視角,即認識到它在更寬廣的哲學和歷史理解的實踐中的作用。從語境來看,顯然任何理性重構和論證的計劃都是利用歷史理解而提出的,并且轉而激勵歷史理解:這種洞見位于解釋學的核心。(19)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它允許我們帶著新思維方式的裨益重新思考過去的哲學,這種裨益就是能揭示富有成效的且以前未曾認識到的聯系。從蒯因兩個教條的視角重新審視分析哲學史,并通過思考康德對法律/事實的區分和文德爾班證實它的嘗試,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說明。(20)
注釋:
(1)特別地,參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A84/B116。康 德是受鮑姆嘉通(Alexander Baumgarten)的影響,他在討論倫理學和法律時區分了“事實歸責”(imputatio facti)和“法律歸責”(imputatio legis),例如在他1760年的《第一實踐哲學導論》(Initia Philosophiae Practicae Primae)中。參見普爾普斯(Proops):《康德的立法隱喻》(Kant’s Legal Metaphor)第213頁。鮑姆嘉通并沒有把這種區分擴展到形而上學上,而后者正是康德的獨創性所在。
(2)我找到的最早使用這個術語的是科恩(Cohen)和那格爾(Nagel)的《邏輯與科學方法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第388-390頁。
(3)對這個觀點的否認至少可以追溯到早期現代哲學的開端。例如《笛卡爾的思維引導規則》(Decartes’Rule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第三條規則,以及沙夫(Scharff)《歷史對哲學的重要性》(How History Matters to Philosophy)第1和3章的討論。
(4)關于這類情況具體的討論,請參見克萊門特(Klement):《起源推理何時不會出錯?》(When Is Genetic Reasoning Not Fallacious?)。正如克萊門特所指出的,意義的因果理論以及信念和知識的因果和可靠性理論涉及某種形式的起源推理。
(5)特別地,見始于1793年的《倫理學講義》(Vigilantius Ethics Lectures)(Ak. 27,562)。康德在他1780年左右的倫理學講座(Lectures on Ethics,第58頁)中也討論了這個問題。關于我在此受惠的所有這些有助益的討論,參見普爾普斯(Proops)《康德的立法隱喻》(Kant’s Legal Metaphor),尤其是第2節。
(6)為了回應哲學史提出的理解問題,康德對自身批判方案深化的解釋,參見賴希爾(Reichl):《讓歷史哲學化》(Making History Philosophical)。在我看來,文德爾班比卡西爾更進一步,參見倫茲(Renz):《卡西爾的啟蒙》(Cassirer’s Enlightenment)。
(7)參見羅素為此書所寫的已經丟棄的前言,該前言詳細闡釋了這個主題(Discarded Preface),其中還包含了尼古拉斯·格里芬(Nicholas Griffin)所寫的有助益的介紹。參見摩爾對他1898年學位論文(129-131頁)的介紹。
(8)我們以類比的方式表明,蒯因所反對的那種分析真理與綜合真理之間只是假定的分裂,而非概念上的分裂。蒯因承認“如果每個人通過學習它的單詞來知道它是真的”,那么,這個句子就可以被描述為分析的(Roots of Reference,第79頁)。但是,正如蒯因(Two Dogmas of Empiricism,第20頁)指出的,這不足以保證分析真理的觀念“基于意義而獨立于事實”,這也是他真正批判的靶子。關于蒯因觀點的發展的討論,參見希爾頓(Hylton):《蒯因》(Quine)第3章。
(9)布魯克(Brucker):《哲學批判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相關討論,參見卡塔納(Catana):《歷史學的概念》(The 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哲學史的哲學史》(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哲學史中的哲學問題》(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皮亞亞(Piaia)和桑蒂內洛(Santinello):《哲學史的范型》(Model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0)在畢明安(M. Beaney)的論文《分析哲學與哲學史》(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中,我提供了一些重點的解釋。
(11)更多了解羅素史學中的“類型”,參見亨特(Hunter):《創造歷史的羅素》(Russell Making History)。
(12)關于所有這些更充分的解釋,見格里芬(Griffin):《羅素觀念論的學徒》(Russell’s Idealist Apprenticeship)第4-5章、第8章第6節; 《羅素的哲學背景》(Russell’s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特別是第 98-102頁; 《羅素從萊布尼茨那里學到了什么?》(What did Russell learn from Leibniz?),特別是第 1-3節。 格勞赫爾(Galaugher):《羅素的邏輯分析》(Russell’s Philosophy of Logical Analysis)第2章。
(13)這本書緊隨講座之后完成,正如摩爾在講座的筆記中所述。參見亞索與格里芬(Arthur and Griffin):《摩爾關于羅素萊布尼茨講座的筆記》(Moore’s Note on Russell’s Leibniz Lectures)。
(14)關于詳細討論羅素讀到的萊布尼茨的作品和時間,見格里芬(Griffin):《羅素從萊布尼茨那里學到了什么?》(What did Russell learn from Leibniz?)。格里芬(Griffin)特別指出,羅素在閱讀萊布尼茨作品很早的時候(1898年夏天)就發現了內在關系學說,這支持了他塑造自己的理性重構的觀點。更多關于羅素著作的起源,見:《羅素:伯特蘭羅素研究雜志》(Russell:the Journal of Bertrand Russell Studies)2017年第1期中的多篇文章。
(15)羅素聲稱在萊布尼茨寫給阿爾諾(Arnauld)的信和《談談形而上學》(Discourse on Metaphysics,Philosophy of Leibniz的第8章)中找到了支持他重構的證據,而單子論可能暗示一種不同的重構。有關聚焦于關系理論的對萊布尼茨哲學的不同解讀的例子,見姆格耐(Mugnai):《萊布尼茨的關系理論》(Leibniz’ Theory of Relations)。
(16)對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之間的關系更公正的歷史解釋,參見拉爾克(Laerke):《萊布尼茨關于斯賓諾莎的講座》(Leibniz Lecteur de Spinoza)。
(17)關于哲學史同時作為一種歷史和一種哲學,又參見:安東格納扎(Antognazza)《哲學的益處》(The Benefit to Philosophy)。
(18)參見畢明安(M.Beaney):《分析哲學的歷史學》(The Historiography of Analytic Philosophy)、《分析哲學與哲學史》(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歷史學與歷史哲學》(Historiography,Philosophy of History)、《發展與爭論》(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19)有關最近更好的對解釋學的闡釋,參見馬克雷爾(Makkreel):《詮釋學中的方向與判斷》(Orientation and Judgment in Hermeneutics)。又參見畢明安(M. Beaney):《發展與爭論》(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20)感謝羅薩·安東格納扎(Rosa Antognazza)、阿歷克斯·科恩(Alix Cohen)、摩根斯·拉爾克(Mogens L?覸rke)、麥夏蘭(Sharon Macdonald)、馬克·特克斯特(Mark Textor)、凱瑟琳·威爾遜 (Catherine Wilson)、洪堡大學研究討論會的與會者,以及摩根斯·拉爾克組織的兩位匿名審稿人(在《英國哲學史期刊》[BJHP]同行評審系統之外)對本文提出的精辟批評和有益建議。
參考文獻:
[1]Antognazza, Maria Rosa. The Benefit to Philosophy of the Study of Its History[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15(1): 161-184.
[2]Arthur, Richard T. W., Nicholas Griffin. Moore’s Notes on Russell’s Leibniz Lectures[J]. Russell, 2017(1):143-192.
[3]Beaney, Michael. Logic and Metaphysics i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C]//Edited by Leila Haaparanta and Heikki Koskinen.Categories of Be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257-292.
[4]Beaney, Michael. The Historiography of Analytic Philosophy[C]//Edited by Michael Beaney.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30-60.
[5]Beaney, Michael.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Rational Reconstruction[C]//Edited by Erich Reck.The Historical Turn in Analytic Philosoph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13:231-260.
[6]Beaney, Michael.Historiography,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Turn in Analytic Philosophy[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2016(2):211-234.
[7]Beaney, Michael.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C]//Edited by Kelly Becker and Iain Thoms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45-20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725-758.
[8]Brucker, Johann Jakob. 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M].Leipzig: B. C. Breitkopf 5 vols:1742-1744.
[9]Cassirer, Ernst.Leibniz’ System in S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Grundlagen[M]. Marburg: Elwert, 1902.
[10]Catana, Leo. The 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 “System of Philosophy”. Its Origin, Nature and Legitimacy[M]. Leiden: Brill, 2008.
[11]Catana, Leo.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Lost Biographical Tradition[J].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12(3):619-625.
[12]Catana, Leo.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hat Are They?[C]//Edited by M. Laerke, J. E. H. Smith, and E. Schliesser.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Ai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5-133.
[13]Cohen, Morris R., Ernest Nagel.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4.
[14]Gadamer, Hans-Georg. Wahrheit und Methode[M]. Tübingen: J. C. B. Mohr, 1960. 2nd ed; 1965.Translated by W. Glen-Doepel as Truth and Method[M]. London: Sheed & Ward, 1975.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 Weinsheimer and D. Marshall, 1989.
[15]Galaugher, Jolen. Russell’s Philosophy of Logical Analysis: 1897-1905[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6]Griffin, Nicholas. Russell’s Idealist Apprenticeship[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Griffin, Nicholas. Russell’s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C]//Edited by N. Griff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rtrand Russ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84-107.
[18]Griffin, Nicholas. What Did Russell Learn from Leibniz?[EB/OL].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2013(1). https://jhaponline.org/jhap/article/view/15.
[19]Hunter, Graeme. Russell Making History: The Leibniz Book[C]//Edited by A. D. Irvine and G. A. Wedeking.Russell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397-414.
[20]Hylton, Peter. Quin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21]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 Guyer and A.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84-85.
[22]Kant, Immanuel.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J].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1784(4):481-494.
[23]Kant, Immanuel. Vigilantius Ethics Lectures[M]//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7, Berlin: K?觟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9 vols,Second edition .Berlin: De Gruyter,1968:562.
[24]Kant, Immanuel." Lectures on Ethics[M]. Translated by Louis Infield, and edited by J. London: Methuen, 1979:58.
[25]Klement, Kevin C. When Is Genetic Reasoning Not Fallacious?[J]. Argumentation.,2002(16):383-400.
[26]L?覸rke, Mogens. Leibniz Lecteur de Spinoza[M]. Paris: éditions Honoré Champion, 2008:102.
[27]Leibniz, G. W.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Leibnitz[M]. Edited by G. M. Duncan. New Haven, CT: Tuttle, Morehouse and Taylor, 1890:266-267.
[28]Makkreel, Rudolf A. Orientation and Judgment in Hermeneu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255-267.
[29]Moore, G. E.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Ethics[C]//Edited by Thomas Baldwin and Consuelo Preti.Early Philosophical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115-242.
[30]Mugnai, Massimo. Leibniz’ Theory of Relations[M]. Stuttgart: Steiner, 1992:56.
[31]Piaia, Gregorio, Giovanni Santinello, eds. Model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M]//Vol. II: From the Cartesian Age to Brucker. Translated by H. Siddons and G. Weston. Dordrecht: Springer, 2011:156-166.
[32]Proops, Ian. Kant’s Legal Metaphor and the Nature of a Deduction[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3(2):209-229.
[33]Quine, W. V.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C]//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20-46; original publish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1951: 20-43.
[34]Quine, W. V. Roots of Reference[M].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74:79.
[35]Reichl, Pavel. Making History Philosophical: Kant, Maim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in the Critical Period[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20(3):463-482.
[36]Renz, Ursula. Cassirer’s Enlightenment: On Philosophy and the “Denkform” of Reason[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20(3): 636-652.
[37]Russell, Bertrand.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7: 196.
[38]Russell, Bertrand.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M]." London: Routledge, 1937 2nd ed., first edition 1900:13.
[39]Russell, Bertrand.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Preface.
[40]Russell, Bertrand.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first edition 1959; Reprinted Unwin Paperbacks, 1985:61.
[41]Russell, Bertrand. An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Reasoning [C]//Edited by N. Griffin and A. C. Lewi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2: Philosophical Papers, 1896-1899; London: Routledge, 1989:155-241.
[42]Russell, Bertrand. Discarded Preface to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J]. Russell. 2017(37):245-251.
[43]Scharff, Robert C. How History Matters to Philosophy[M]. London: Routledge, 2014:12-16.
[44]Windelband, Wilhelm. Kritische Oder Genetische Methode?[C]//Prludien. Aufstze und Reden zur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5th ed., Vol. 2. Tübingen: Mohr, 1915:99-135; first published. 1883; translated by Alan Duncan, in The Neo-Kantian Reader, edited by S. Luft, London: Routledge, 2015:271-286.
(責任編輯 吳 勇)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www.jhlt.net.cn
原文Two Dogmas of Analytic Historiography發表于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20年第3期,第594-614頁。
作者簡介:畢明安(Michael Beaney,1959—),英德雙國籍,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分析哲學史”講席教授、英國阿伯丁大學邏輯學欽定講席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賀麟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分析哲學史、中國古代分析哲學、哲學方法論、比較哲學;譯者:徐弢(1983—),安徽潛山人,哲學博士,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暨湖北省道德與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分析哲學史、語言哲學與維特根斯坦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