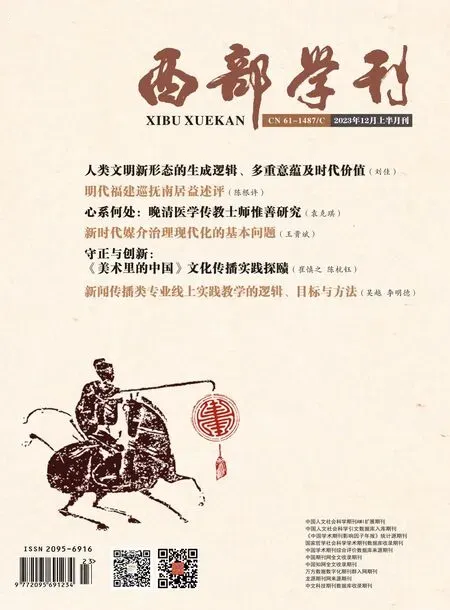論信息圈與新“天人合一”
葛海琪
(黑龍江大學(xué) 哲學(xué)學(xué)院,哈爾濱 150000)
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使得當(dāng)下人們的生存圖景逐漸向“信息圈(infosphere)”靠近,人們已經(jīng)無法完全脫離信息而獨(dú)自生存。這一境況吸引當(dāng)下的哲學(xué)家開始思索人類與信息圈的關(guān)系問題,這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gè)哲學(xué)家就是英國牛津大學(xué)教授盧恰諾·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以下簡稱弗洛里迪),他在出版的幾部著作中建構(gòu)了“信息圈”這一概念。而人與信息圈的這樣一種交融又巧妙地與中國的新“天人合一”思想的精神內(nèi)核相互呼應(yīng)。
一、作為再本體論的“信息圈”
信息圈是弗洛里迪以生物圈(biosphere)為基礎(chǔ),取其“圈”意思的后綴與作為“信息”含義的前綴“info”結(jié)合而成的新詞。其含義正與這個(gè)詞的構(gòu)詞方法類似,指代我們生活于其間的整體生存環(huán)境。當(dāng)代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已經(jīng)滲透到人類思想的方方面面,“比如‘心的本質(zhì)是什么?’‘美和品位的本質(zhì)是什么?’,以及‘邏輯上有效的推理的性質(zhì)是什么?’,已經(jīng)受到了根本性的重新解釋,這導(dǎo)致了心靈哲學(xué)、美學(xué)和邏輯定義的深刻轉(zhuǎn)變”[1]。更為根本的是,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正在將我們生存其中的世界“再本體論化”,以使傳統(tǒng)的生物圈轉(zhuǎn)變?yōu)樾畔⑷碇厮芪覀兊纳羁臻g。
伴隨著生物圈演變?yōu)樾畔⑷?人類的處境也將面臨著類似的變化,人將不僅僅是哲學(xué)中強(qiáng)調(diào)的生命和意志的主體。這么說當(dāng)然并不是否認(rèn)當(dāng)未來人類處在信息圈中時(shí)就沒有生命和意志了,而是在彼時(shí)人類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gè)“信息體(inforgs)”來活動(dòng)。換言之,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不僅在改變著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同時(shí)也在變革著人類自身的存在方式。作為信息體的人不是獨(dú)立于信息圈之外的,我們與信息圈一起共同經(jīng)歷著這一“再本體論化”的進(jìn)程,實(shí)際上信息體就是信息圈的一部分,人與信息化的生存環(huán)境可以說是合一了,“作為有意識(shí)的信息主體,人類主體與其他信息主體共享一個(gè)由信息構(gòu)成的現(xiàn)實(shí)”[2]。弗洛里迪的觀點(diǎn)很明確,構(gòu)成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就是信息,這也是以信息圈為基礎(chǔ)的再本體論化的表現(xiàn)形式,由信息所構(gòu)成的“圈子”將會(huì)與我們現(xiàn)在生活于其間的物理世界逐漸融合,最終,現(xiàn)在所謂虛擬的信息世界反而會(huì)成為真正真實(shí)的世界,這一點(diǎn)現(xiàn)今已開始顯現(xiàn)端倪了,近段時(shí)間大火的虛擬現(xiàn)實(shí)、人工智能以及元宇宙等,無一不是信息圈這一趨勢的領(lǐng)頭羊。
作為當(dāng)下已經(jīng)成年的幾代人可能難以理解未來在信息圈中作為信息體而與其環(huán)境共同存在的場景,“我們作為數(shù)字移民,將被像我們孩子那樣的數(shù)字原住民所取代,他們將會(huì)感激信息圈與物理世界之間并無本體論差異,只有在抽象層次上的差別”[3]。這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然實(shí)則確實(shí)如此。當(dāng)下的我們只是從傳統(tǒng)物理世界“遷徙”到信息圈的“移民”,我們賴以生存的背景是現(xiàn)實(shí)的物理世界,對于信息世界多數(shù)人的認(rèn)知還只是一種對于現(xiàn)實(shí)的模擬、拓展和補(bǔ)充,其根本還在現(xiàn)實(shí)的物理世界。只有當(dāng)信息圈“原住民”以整一代人的趨勢出現(xiàn)時(shí),才是真正到了人類——或者說信息體——與信息圈融合為一的時(shí)候。
二、新“天人合一”辨析
“天人合一”(或曰“萬有相通”)本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中的思想,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可分為以下幾個(gè)類型,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義的‘天’與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道家無道德意義的‘道’與人合一的思想”[4]。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上,雖有各派學(xué)說爭論,但總體上都是秉持著“天人合一”這個(gè)最核心的觀念。
無論是儒家?guī)в械赖乱饬x的“天”,還是道家純粹自然意義下的“天”,兩者作為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其都有一個(gè)無法克服的根本問題,即“天”只是一個(gè)純粹的抽象空洞的實(shí)體,其間沒有對特殊性的任何規(guī)定性,更別說到達(dá)黑格爾所說的個(gè)體性階段。黑格爾在《宗教哲學(xué)講演錄》中對其評價(jià)道:“由于普遍者只是抽象的基礎(chǔ),那么人在其中就仍然沒有真正的內(nèi)在者、充實(shí)者、內(nèi)心深處的東西,他自身中就沒有立足點(diǎn)。”[5]黑格爾的這一評價(jià)抓住了中國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關(guān)鍵。
按照當(dāng)代著名哲學(xué)家、哲學(xué)史家、美學(xué)家、哲學(xué)教育家、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著名教授張世英對中西方哲學(xué)史的研究分類,將天人合一與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中占主流的主客二分相對立,共同作為面對人生在世問題的兩種在世結(jié)構(gòu),這樣兩種的在世結(jié)構(gòu)有三個(gè)發(fā)展階段,分別為原始的天人合一——這一階段相當(dāng)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中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相當(dāng)于西方自柏拉圖以來一路到近代哲學(xué)(尤其是黑格爾哲學(xué))的在世結(jié)構(gòu);吸收并克服了主客二分之后的更高一級(jí)的新天人合一——這一階段就是本文要強(qiáng)調(diào)的新“天人合一”。因此,在張世英的思想中,“天人合一”被定義為“人不僅僅作為有認(rèn)識(shí)、有知的存在物,而且作為有情、有意、有本能、有下意識(shí)等在內(nèi)的存在物而與世界萬物構(gòu)成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這個(gè)整體是具體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6]。他的這一表述實(shí)際上就是指前述作為最后一階段的思想,是內(nèi)含并超越了西方式主客二分于其中的新“天人合一”。這一新“天人合一”最終克服了原始“天人合一”對個(gè)體的忽視,回應(yīng)了上述黑格爾的批判。這才是上述張世英所倡導(dǎo)的當(dāng)下及未來哲學(xué)發(fā)展融合的大趨勢。這一趨勢實(shí)際上也是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人本主義思潮的哲學(xué)家們正在做的,張世英的新“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身也是受到了海德格爾等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家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舊事重提。
三、信息圈中的“天人合一”
以信息圈為基本生存境域的信息體(包括人類),他們的存在論根源大不相同,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的原始“天人合一”的階段,還是包含并超越了主客二分在內(nèi)的更高一級(jí)的新“天人合一”階段,當(dāng)這種新“天人合一”思想境界的發(fā)展匯入生活世界信息化的洪流之中時(shí),注定兩者將會(huì)相互滲透。信息哲學(xué)家們大都喜歡像弗洛里迪一般單純站在科技倫理角度來探討信息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而對其本體論建構(gòu)的篇幅卻少很多;反之,如張世英這般對天人合一一類的本體論演變進(jìn)行研究的哲學(xué)家又很少關(guān)注信息哲學(xué)的領(lǐng)域。事實(shí)上隨著物理世界與信息世界的不斷融合,信息圈與天人合一也在相互融合。
新“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在新時(shí)代的更新再利用,信息圈是弗洛里迪本世紀(jì)新近提出的信息時(shí)代的新本體論,二者乍一看似乎關(guān)聯(lián)不大,然其內(nèi)核卻是殊途同歸。在新“天人合一”境界中,人與其生存其中的世界是骨肉相連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世界就無所謂人,人與不在場的世界是息息相關(guān)的。同樣,通過前述對信息圈的描述,人是以信息體的形式在信息圈中活動(dòng),這一場景甚至更強(qiáng)化了人與世界一體的概念。在當(dāng)下的物理世界的認(rèn)知活動(dòng)中,人們習(xí)慣于通過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將外在世界視為獨(dú)立于自身主體之外的客體來認(rèn)識(shí),那么自然而然人們就會(huì)將作為客體的外部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本身相互對立起來,以此便造成了人與世界的異質(zhì)。雖然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中已經(jīng)有不少哲學(xué)家反思主客二分所帶來的問題,但從大眾整體而言,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主要還是以主客二分的態(tài)度來看待世界。
不同于上述傳統(tǒng)物理世界中的主體,作為信息體的人類將會(huì)從根源上顛覆這種以主客二分為主的日常生活,當(dāng)我們認(rèn)為“人—世界”的本體是由信息方式所構(gòu)成的,那么與之同步的,人的核心定義就會(huì)發(fā)生一次翻天覆地的改變,物質(zhì)的人開始讓位于信息的人。這并不是說以后人就沒有物理的軀體了,主要是指信息世界與物理世界之間幾乎沒有差別,人的任何行動(dòng)都與信息相關(guān)。正如弗洛里迪在其主編的著作《在線生活宣言》里總結(jié)的:“數(shù)字轉(zhuǎn)型至少以四種方式動(dòng)搖了已確立的參考框架:a.實(shí)在與虛在的區(qū)分變得模糊;b.人類、機(jī)器人和自然界的區(qū)分變得模糊;c.當(dāng)它涉及信息時(shí),從匱乏逆轉(zhuǎn)為過剩;d.從以實(shí)體為主導(dǎo)轉(zhuǎn)向以互動(dòng)為主導(dǎo)。”[7]這部書中具體地給出了四種劃分,其核心都是強(qiáng)調(diào)信息與物理的融合,a和b兩點(diǎn)很直白地說明這樣一種融合的兩種表現(xiàn)形式——現(xiàn)實(shí)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融合,人類、人造的能動(dòng)者(即機(jī)器人)與自然的融合。c和d兩點(diǎn)沒有直接說明,c點(diǎn)主要表明信息將會(huì)轉(zhuǎn)變?yōu)橐环N指數(shù)式增長的新資源,而我們現(xiàn)在所認(rèn)知的自然資源是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對生活的全面改造,所有我們的行動(dòng)都將會(huì)產(chǎn)生信息,并且這些信息還可能會(huì)相互疊加組合,因此會(huì)導(dǎo)致信息圈中的資源從匱乏而轉(zhuǎn)變?yōu)檫^剩。d點(diǎn)意在表明由于數(shù)字信息的重塑,主體被解構(gòu)為信息體與其他能動(dòng)者之間的信息交互的互動(dòng),把人的身份認(rèn)同也轉(zhuǎn)變?yōu)樾畔⒔换サ慕Y(jié)果。但這種解構(gòu)并沒有完全拋棄主體,我們在信息圈中仍舊是作為唯一的自我而活動(dòng)著的,由于信息的無限延展性,每一個(gè)信息體實(shí)際上都是獨(dú)一無二的,因此在信息圈中,信息體雖被解構(gòu)于信息之中,但仍不失其主體性。
《在線生活宣言》把信息圈改變生活的幾個(gè)特點(diǎn)列舉了出來,誠然即便是再有前瞻性的哲學(xué)家也很難精確預(yù)測未來,他的預(yù)測不一定百分之百會(huì)實(shí)現(xiàn)。但如今我們正處在這一進(jìn)程當(dāng)中,研讀弗洛里迪等信息哲學(xué)家的著作,其目的本就不是妄圖憑此就對未來有個(gè)精確的打算。哲學(xué)家不是某些具體對策的制定者,哲學(xué)理論描繪得再具體也只是基于大方向的迷途指津,我們通過弗洛里迪的著作要吸收的是他的信息哲學(xué)的精神內(nèi)核,而上述幾個(gè)要點(diǎn)反映出弗洛里迪這一信息哲學(xué)的精神內(nèi)核,其正是與張世英新“天人合一”思想相通的萬物一體的境界。人與生存環(huán)境的充分融合,此處的生存環(huán)境在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學(xué)中便是信息圈,此即在信息圈中的新“天人合一”的要義。
如前所述,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將原本身處物理世界的人進(jìn)行了信息化重塑,使之變?yōu)樾畔⑷Φ囊徊糠?信息的產(chǎn)生、流通和使用與物理世界是不同的。成素梅曾提過信息化社會(huì)中的一個(gè)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用戶在數(shù)字世界里的所作所為已經(jīng)使其成為透明者或全景開放者,從而潛在地喪失了隱私權(quán),無意識(shí)地放棄了會(huì)留下永久性數(shù)據(jù)痕跡的個(gè)人信息的所有權(quán)。”[8]隱私權(quán)的問題是伴隨著信息化過程一直被人們所討論的熱點(diǎn)問題,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信息的逐步透明化象征著在信息圈中信息體將不斷被“解蔽”,作為信息圈內(nèi)的信息體,已經(jīng)脫離了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主客二分的模式,其主要的在世結(jié)構(gòu)反而是東方式的新“天人合一”模式。信息體的本質(zhì)并不是作為在場顯現(xiàn)的主體,而是其背后不在場的他者以及主體和他者的信息互動(dòng),這個(gè)他者并不特指某個(gè)或某些人、物,是層層關(guān)聯(lián)的作為信息體生存背景的其他信息體相互關(guān)聯(lián)而形成的存在之網(wǎng),這無限關(guān)聯(lián)之網(wǎng)也就是信息圈,在場顯現(xiàn)的信息體只是這網(wǎng)上的一個(gè)凸顯的繩結(jié)。繩結(jié)是由相互糾纏的幾股繩交錯(cuò)在一起形成的,同樣的,在場顯現(xiàn)的信息體也是由隱蔽其后的存在之網(wǎng)——即信息圈——所根本構(gòu)成的。這一現(xiàn)象在信息化時(shí)代更加明顯,通過信息和數(shù)據(jù)分析一個(gè)人時(shí)往往其本人的信息是最不重要的,本人的血型、生日、身高體重等數(shù)據(jù)信息意義不大,真正塑造一個(gè)信息體的是他在信息圈中的行為,例如其搜索記錄、出行信息、消費(fèi)賬單等,此種在信息圈中與他者的互動(dòng)才能真正分析出該信息體的各項(xiàng)有用數(shù)據(jù)。正是信息化帶來的數(shù)據(jù)透明化更加促進(jìn)了這種萬物一體,當(dāng)然隱私權(quán)問題是其面臨的一個(gè)巨大挑戰(zhàn),如何確保個(gè)體隱私不被資本利用來牟取不當(dāng)利益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此種倫理問題不應(yīng)成為阻礙信息圈形成的一個(gè)路障,當(dāng)下的法律、倫理道德等應(yīng)該主動(dòng)適應(yīng)即將到來的信息世界,以使轉(zhuǎn)型之后的人類信息體能更好地融入信息圈。
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的進(jìn)步在帶來各種問題的同時(shí),相對應(yīng)的必然也是對個(gè)人有好處的,否則便不會(huì)演變得如此迅速,正如前面提到的個(gè)人互動(dòng)信息的隱私權(quán)問題,這一方面的信息在信息圈中很容易被他人竊取利用,這是未來社會(huì)要解決的一大難題,因?yàn)樾畔⒈旧黼y以具體定位和捕捉,其流動(dòng)性非常強(qiáng)。然而這一點(diǎn)不僅對他人有利,對于使用者自己也是有利的,在信息圈中雖然仍舊是以個(gè)體為活動(dòng)單位,但已經(jīng)沒有一個(gè)絕對固定的主體客體,這意味著我既是“自己”也是“他人”,你我不同而相通。信息流動(dòng)性和透明性不是單向的,別人可以獲得關(guān)于我的信息,我也可以獲得關(guān)于他人的信息,宏觀來看,信息圈就是如此走向“天人合一”的,在信息圈中你我的分別被減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有信息體都是創(chuàng)造、獲取、轉(zhuǎn)換、利用信息的其中一份子,在此種深度的信息交互的過程中,我是他人的不在場的存在,他人也是我的不在場的存在。
四、結(jié)語
張世英的哲學(xué)境界非常之高,其新“天人合一”的理論乃是綜合中西方哲學(xué)而創(chuàng)新出的哲學(xué)理念,但可惜由于生活時(shí)代的限制,雖在其生命的晚年生活世界的信息化已經(jīng)開始全面變革,然其本人的新“天人合一”理論并未直接與信息哲學(xué)對話。即便如此,我們?nèi)阅軓膶π隆疤烊撕弦弧钡脑u價(jià)中窺見其對信息圈發(fā)展的啟示。
張世英將其新“天人合一”觀總結(jié)為:“就是將西方主客二分、物我相分、人我有別的‘主體性精神’納入中國傳統(tǒng)的‘萬物一體’觀之內(nèi),而主張‘萬物不同而相通’。”[9]他之所以要再提出新的“天人合一”,而非只是重復(fù)中國哲學(xué)史上的傳統(tǒng)“天人合一”,關(guān)鍵就在于他的新“天人合一”理論是囊括了西方主客二分的主體性哲學(xué)在內(nèi)的,在萬物一體的同時(shí)能保持住自身的確定性,不使自我消散于他者之中。這一點(diǎn)對于信息圈同樣是適用的,在信息圈中所有信息體的基本構(gòu)造都是一致被信息所構(gòu)建的,生存的本質(zhì)隔閡被消除掉,同時(shí)由于信息化所帶來的萬物互聯(lián)互通,所有信息體與其他信息體都相互依托。同樣地,信息體的互聯(lián)互通并不意味著放棄個(gè)體性,而是如新“天人合一”一般,是內(nèi)含個(gè)體的互通性。
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本體論缺陷就是過于輕視主體性,以至于到了泯滅個(gè)體“人”以實(shí)現(xiàn)“天”的和諧,憑借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的發(fā)展所帶來的信息化的變革重塑,其作為“天”這一面的抽象力量相對于傳統(tǒng)物理社會(huì)而言只增不減,信息圈的發(fā)展雖是科技的狂歡,然而卻也更容易將人異化,因而在接受信息圈的“天人合一”的同時(shí),我們要保持住自身一定的主體性,不致使自我迷失在繁雜的信息圈之中,這一局面將是人類在信息社會(huì)快速發(fā)展的同時(shí)要不斷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