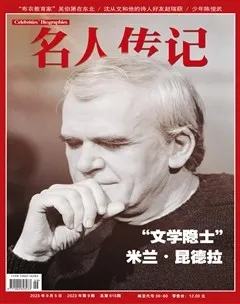周恩來最后600天(七)











明火執(zhí)仗
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又對江青發(fā)出了嚴(yán)厲的警告。就在這一天,外交部就我國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huì)第六屆特別會(huì)議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人選問題專門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做了一個(gè)重大的決定,他主動(dòng)提出由鄧小平擔(dān)任團(tuán)長,喬冠華當(dāng)鄧小平的參謀。
周恩來并沒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他知道江青一伙對由誰來代表中國參加聯(lián)合國特別會(huì)議懷有一己之私,所以他千萬不能掉以輕心。隨后,外交部于3月22日向中央呈送了關(guān)于代表團(tuán)人選的請示報(bào)告。24日,周恩來批示表示同意外交部的意見。周恩來同時(shí)還批示,要把他的意見首先呈報(bào)毛澤東主席,暫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澤東主席批示后再送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核閱,然后退外交部辦。
毛澤東接到外交部的報(bào)告,沒有猶豫,于當(dāng)天就圈閱了周恩來的批示意見。江青在釣魚臺(tái)住所得知毛澤東圈閱了外交部的報(bào)告,大發(fā)雷霆,打電話給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和美大司副司長唐聞生,要求她們撤回外交部的報(bào)告。
盡管王海容和唐聞生經(jīng)常出入毛澤東住所,見到毛澤東要比江青容易得多,而且可以和毛澤東無拘無束地談話聊天,在中南海一些人眼里,她們兩人似乎有著呼風(fēng)喚雨的能量,可這個(gè)時(shí)候,她們不可能將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做了批示的報(bào)告撤回。二人只好一再申明:第三世界國家十分重視這次會(huì)議,許多國家元首都要出席大會(huì),由鄧小平率團(tuán)出席這次會(huì)議的報(bào)告毛主席已經(jīng)圈閱,外交部無權(quán)撤回經(jīng)毛澤東主席批準(zhǔn)的報(bào)告。
4月6日,這一天天氣格外好,沿街盛開著美麗的玉蘭花。鄧小平精神抖擻地率代表團(tuán)乘專機(jī)前往美國參加聯(lián)大特別會(huì)議。周恩來身穿深色的風(fēng)衣,親自為鄧小平送行,他的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在機(jī)場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用周恩來的話說這是“以壯行色”。
4月19日,鄧小平載譽(yù)歸來,周恩來又親往首都機(jī)場迎接。這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送往迎來,它凝聚著周恩來對鄧小平的深情厚誼。為擴(kuò)大鄧小平在國際國內(nèi)的影響,周恩來可謂是煞費(fèi)苦心。因?yàn)檫^度勞累,周恩來的病情在一步步地惡化,他以異常的速度不斷地消瘦,令人心悸。3月11日做的電燒手術(shù),遠(yuǎn)沒有第一次效果好,僅隔一個(gè)月,病情再度抬頭,又開始大量尿血。這次復(fù)發(fā)帶來一個(gè)非常痛苦的并發(fā)癥——尿潴留!
膀胱里出血一多,就會(huì)凝固成血塊,堵住排尿管口,尿被憋在膀胱里出不來,腫脹、疼痛。病人這時(shí)痛苦萬分。每到周恩來會(huì)見外賓或是開完會(huì),他就要開始承受這種難以忍受的痛苦,實(shí)在腫脹難忍時(shí),就倒在會(huì)見廳的沙發(fā)上翻滾,希望能把血塊晃動(dòng)開。每到這個(gè)時(shí)候,周恩來總是一聲不吭,不愿意麻煩任何人,獨(dú)自忍受著痛苦。
束手無策的醫(yī)護(hù)人員只能焦慮萬分地守護(hù)著總理,等待他能解出小便來。大家看著總理如此遭罪,卻不能幫他解除痛苦,心里像刀割一樣,痛楚萬分。后來大家從西花廳搬來一張大木床到大會(huì)堂,讓周恩來翻滾時(shí)有個(gè)稍微寬敞的地方。
周恩來在人民大會(huì)堂參加活動(dòng)多,和大會(huì)堂的工作人員特別熟悉。大家知道總理病了,雖不知道患有如此重病,但能夠感受到周恩來是拖著病體來大會(huì)堂工作的。所以每一個(gè)為總理服務(wù)的工作人員就格外小心,盡可能地減輕總理的疲勞和痛苦。可是周恩來的病情太重了,女服務(wù)員有時(shí)看見周恩來為解一次手要翻滾好久,常常滿頭大汗、筋疲力盡,才能解決問題,她們難過極了,常常躲在大家看不見的地方抹淚。到了給總理添茶或是送手巾的時(shí)候,她們進(jìn)門前總要抹抹臉,然后強(qiáng)作微笑進(jìn)去,一出門,眼淚又會(huì)滑落下來。
眼淚沒有感動(dòng)蒼天,周恩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yán)重。可是,重病中的周恩來卻像一個(gè)上了發(fā)條的陀螺,一直轉(zhuǎn)著,就是停不下來。從他一頁寥寥數(shù)語的日程安排上可以看到日理萬機(jī)的繁忙,時(shí)間是1974年3月26日至27日:
下午3時(shí)起床
下午4時(shí)與尼雷爾會(huì)談(五樓)
晚7時(shí)陪餐
晚10時(shí)政治局會(huì)議
晨2時(shí)半約民航同志開會(huì)
晨7時(shí)在七號辦公
中午12時(shí)去東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2時(shí)休息
…………
“不停轉(zhuǎn)”的結(jié)果是他的身體愈加虛弱。4月28日,周恩來發(fā)生缺氧病狀; 5月19日、23日、25日,又相繼三次發(fā)生缺氧病狀。每個(gè)星期除給總理輸兩次血外,其他什么治療都沒有辦法實(shí)施。可就連輸血,有時(shí)也受干擾。
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來在西花廳輸血,不一會(huì)兒,他靜靜地睡著了。醫(yī)生望見總理消瘦、蒼白的臉龐,希望他能好好睡一覺,就屏聲靜氣地守護(hù)在床前。這時(shí),電話鈴聲不識時(shí)務(wù)地猛烈響了起來。一接,是王洪文的,他通知總理去參加會(huì)議。
“總理正在輸血,剛剛睡著,能不能不去?”那天正好是張醫(yī)生值班,他輕聲同對方秘書商量,心里卻直埋怨:什么會(huì)議,總理病得不輕,不去就不能自己開嗎?
又過了十幾分鐘,電話又一次響起來。這次驚動(dòng)了鄧大姐,她來到總理輸血的房間,為難地看看睡著的總理,又看看輸血瓶,還有好大一半血沒有輸完呢!鄧大姐想了一會(huì)兒,說:“看樣子還是要叫醒總理,他們又叫……參加會(huì)議。”
張醫(yī)生怎么忍心中斷輸血呢,可誰也無奈,王洪文新官上任氣正盛,惹不起他。周恩來歷來注意尊重年輕干部,王洪文剛當(dāng)選黨中央的副主席,他自然也得同王洪文和諧相處。周恩來在屋里似乎察覺門外有動(dòng)靜,睜開眼睛,望著難言的張醫(yī)生:“是不是有事?”
“洪文同志通知你去開會(huì),你正在輸血,是不是……”
“去!”
“那輸血……”
“不輸血了,拔針頭。”周恩來毫不猶豫地坐起來。
周恩來一手壓著胳膊上的針眼,匆匆坐進(jìn)車?yán)铮贿M(jìn)汽車他又疲倦地合上雙眼,臉色越加蒼白。這時(shí)身邊的警衛(wèi)、秘書還有醫(yī)生恨不得要跑到王洪文那里去罵娘,才能解心頭之恨。
5月初,北京醫(yī)院的病理報(bào)告更加不妙,發(fā)現(xiàn)有乳頭狀的癌組織脫落,說明腫瘤已經(jīng)長大,開始脫落,這是癌癥擴(kuò)散的危險(xiǎn)信號。張醫(yī)生按捺不住心中的氣憤,這時(shí)他們醫(yī)務(wù)人員的一腔希望已經(jīng)變成了滿腹悲憤。他們將這個(gè)病理報(bào)告送到大會(huì)堂的會(huì)議上。
張春橋依然一臉陰沉,慢條斯理卻語氣激昂,說道:“總理是黨內(nèi)外、軍內(nèi)外、國內(nèi)外的……主管。從現(xiàn)在到月底有多少外賓需要接見?嗯……現(xiàn)在我們正在貫徹毛主席的外交路線,最后5月30日見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后,才能考慮怎么辦。病理報(bào)告上的結(jié)論可以先改一改嘛,暫時(shí)不要告訴總理,不然會(huì)分散他的精力。”
更改病理報(bào)告,這不是要醫(yī)生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嗎?張醫(yī)生他們氣得腦袋要爆炸了,也不顧在什么場合和什么人說話了,嗓門也大了:“春橋同志,我太不理解,總理執(zhí)行主席的外交路線,要接見許多外賓,只要身體允許,這是他工作范圍的事情,應(yīng)該的。現(xiàn)在總理有病,而且是非常嚴(yán)重的病,不僅嚴(yán)重尿血,而且也尿不出來,疼痛厲害,疼得太厲害,就會(huì)引起心臟病發(fā)作。我還有一個(gè)不理解,總理遲早是要住醫(yī)院治療的,總要有人出來代替他工作的……用總理身體作代價(jià)去會(huì)見外賓,這個(gè)代價(jià)是不是太大了?”
張春橋猛然直起身子,雙眼圓睜,巴掌“啪”地?fù)舸蛟诎缸由希鸬貌璞w叮當(dāng)直響。他用上海普通話嚴(yán)厲地使用了幾個(gè)“你”——“你張醫(yī)生,你不理解?你不懂……你怎么這樣說話?”
張春橋雖然沒有說出“你不懂政治”的話,但是他那蔑視的表情已經(jīng)把“不懂政治”的意思表達(dá)得清清楚楚。“春橋同志,我是醫(yī)生,我每天每時(shí)每刻都看見總理這樣痛苦。我們著急啊,我們是有武器使不上啊!我……只想抓緊時(shí)間早一點(diǎn)治療,康復(fù)的希望就增大一分,總理的痛苦就減少一點(diǎn)。這樣總理還能繼續(xù)為黨為國家工作,對黨和國家都是有利的啊!”
張春橋狠狠瞪了一眼“不懂政治”的醫(yī)生,不吭聲了。最后會(huì)議沒有形成任何文字的東西,不歡而散。
西風(fēng)殘照
1974年5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來中國訪問。他和中國人民是老朋友了,每次來中國都要和毛澤東相見。5月11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里會(huì)見了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他和以往一樣,緩緩站起身,同老朋友緊緊握手……
自從去年8月十大結(jié)束后,王洪文與周恩來一直陪同毛澤東會(huì)見外賓,大概有十次之多,王洪文在電視、新聞電影紀(jì)錄片與《人民日報(bào)》等報(bào)紙刊登的新聞圖片上反復(fù)出現(xiàn),全國人民已經(jīng)習(xí)慣“毛周王”的模式。而這一次會(huì)見,陪同人物發(fā)生了變化。除了“毛周王”外,增加了鄧小平。鄧小平跟在周恩來身后,面帶微笑,沉穩(wěn)老練地走到毛澤東的面前。他還是和以前一樣,平頂頭,灰色中山裝。
見到鄧小平,毛澤東的神情迅速變化,眉宇間露出久違的笑容。除了陪同人物發(fā)生變化外,座次也發(fā)生了變化。以前每次會(huì)見外賓,周恩來都是坐在毛澤東的右側(cè),這基本是“文革”以來的固定座次,而這次鄧小平坐在了周恩來原來的座位上,周恩來則坐在了左側(cè)、巴基斯坦總理布托的旁邊。以前這應(yīng)該是王洪文的位置,而王洪文這次坐在了周恩來的左側(cè),距離毛澤東又遠(yuǎn)了一步。
新聞攝影有時(shí)亦如新聞報(bào)道一樣敏感。很快,外界就知道周恩來身患重病,權(quán)力將由鄧小平接替。
5月25日這天,周恩來和往常一樣,沉著地把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引進(jìn)毛澤東的書房,把陪見的人一個(gè)一個(gè)地介紹給毛澤東相識、握手,而他自己則和以往一樣,默默地站立在攝影鏡頭之外。
毛澤東與希思一見如故,兩個(gè)人無拘無束、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而且一發(fā)不可收,時(shí)間不知不覺地過了一個(gè)多小時(shí)。周恩來怕主席過于疲勞,中間看了三次表,希思意識到是在提醒他,于是起身向毛澤東告辭。而這時(shí)毛澤東談興未盡,跟著站立起來后繼續(xù)與希思交談,希思見狀不好意思忙著走,用眼神請示總理。周恩來也不好掃主席的興,站在后面不再催促,朝希思點(diǎn)點(diǎn)頭。大家站著有說有笑了一會(huì)兒,情緒都顯得特別高,特別是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特有的“仰天大笑”的笑姿,一連來了好幾回,他的笑聲讓會(huì)見場面氣氛更加活躍,毛澤東也在這一情緒感染下,精神顯得特別好。
只有周恩來因?yàn)椴⊥凑勰ィ黠@沒有其他人那么開心。他見主席和希思等人開始握手告別,便先離開毛澤東書房,到外面過廳里等著外賓,然后再一同離開。攝影記者已經(jīng)習(xí)慣周恩來很少留下單獨(dú)和主席握手的舉動(dòng),他一般在最后都將鏡頭集中在毛澤東與外賓握手告別的儀式上。可他并不知道,就在會(huì)見外賓的5月19日、23日、25日,周恩來曾三次發(fā)生缺氧病狀,大夫們急得直跳腳,輪番勸他必須入院動(dòng)手術(shù)。可周恩來淡淡一笑說,要等會(huì)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后才能住院。
幾天后,也就是5月29日,周恩來又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會(huì)見毛主席。杜修賢絕沒有想到這是周恩來在他的鏡頭中最后一次走進(jìn)毛澤東的書房。更沒有想到的是,這也是毛澤東與周恩來最后一次共同會(huì)見外賓。
會(huì)見結(jié)束時(shí),鄧小平、喬冠華和主席告別后就走出書房的門,杜修賢正準(zhǔn)備離開,一扭頭發(fā)現(xiàn)周恩來還站在門旁沒有離開。杜修賢一愣,總理今天的舉動(dòng)一反常態(tài),平時(shí)總理在主席書房并不拘禮,常常會(huì)談一結(jié)束起身就走,害得他們都“捉”不著他的鏡頭,可這次……只見他一動(dòng)不動(dòng)站在那里,似乎期待著什么。既然沒有參加大家最后的告別握手,為什么不走呢?杜修賢猶豫了一下,心里的感覺一時(shí)說不清楚。他決定不急于離開,也站在靠門邊的墻根默默等待著……
毛澤東送客走到門邊,與站在門旁邊的周恩來目光相遇。瞬間,毛澤東一臉的笑容飛逝而去,他憂傷地垂下眼簾。這迅速變化的表情令杜修賢驚詫不已,他第一反應(yīng)就是端起照相機(jī),將鏡頭對準(zhǔn)他們……
鏡頭里,毛澤東憂傷地低垂眼皮,頭稍稍地低著,蒼老的臉上布滿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頭發(fā)整齊地向后披去。他迎著高懸的攝影燈,臉上的肌肉明顯松弛,但很光潔,身穿淺灰色的中山裝,顯得淡泊莊重。
十分消瘦的周恩來用溫馨睿智的雙目凝視著毛澤東。攝影光從他后側(cè)射來,腦后和脊梁猶如披著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濃密,充滿生氣。曾洋溢樂觀笑影的“酒窩”雖已被歲月的刀斧鑿成兩道深深的溝紋,卻依然顯露出執(zhí)著的善意。但是,一絲傷感的凝重神色卻在眉宇之間徘徊。
周恩來看著攜手半個(gè)世紀(jì)的毛澤東,慢慢地伸出了手,毛澤東也把手伸了過去。兩雙掌舵中國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組成了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間。
當(dāng)杜修賢“咔嚓”一聲按下快門時(shí),他沒有想到這是共和國第一位總理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偉大領(lǐng)袖最后一次對著攝影鏡頭握手道別。
后來周恩來從醫(yī)院飛去長沙和毛澤東就四屆人大的問題又會(huì)晤過一次,但沒有帶記者同往,也就再?zèng)]有留下他們握手的照片。
走進(jìn)歷史,毛澤東與周恩來第一次見面是在1925年的廣州。他們從1925年共事,到1976年相繼謝世,并肩戰(zhàn)斗了半個(gè)世紀(jì)之久。
1924年秋,周恩來從歐洲回國,擔(dān)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委員長并在廣州黃埔軍校擔(dān)任政治部主任。而毛澤東也于1925年因?yàn)楸缓宪婇y趙恒惕通緝,躲避到了廣州。于是這兩個(gè)籍貫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甚至連成長經(jīng)歷也不同的人有了第一次握手。
那時(shí)的廣州是國民革命的發(fā)祥地,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紀(jì)20年代中期的中國,革命形勢風(fēng)起云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孫中山先生接受蘇聯(lián)的幫助,改組國民黨,實(shí)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推動(dòng)下,實(shí)現(xiàn)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毛澤東與周恩來正是在共同致力于與國民黨合作的工作中相逢共事、并肩奮斗,開始了艱難的革命歷程。
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前后,他們便發(fā)現(xiàn)兩人的思想認(rèn)識竟然驚人地一致。這次會(huì)議之前,他們都曾向陳獨(dú)秀建議,在大會(huì)上公開提出“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kuò)大左派”的方針,但中共中央沒有采納他們這個(gè)方針,致使蔣介石等右派分子當(dāng)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huì)委員。
因?yàn)閮扇藢r(shí)局認(rèn)識一致,相互對話便覺得默契與投機(jī)。這一時(shí)期,毛澤東和周恩來過從甚密。毛澤東除了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還兼任《政治周報(bào)》主編。在他主編的《政治周報(bào)》第三期上,登了《東征紀(jì)略》,記述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shí)周恩來在追悼攻克惠州犧牲將士大會(huì)上的演說。當(dāng)時(shí),周恩來派人接管的汕頭《平報(bào)》改名為《嶺東民國日報(bào)》,周恩來為該報(bào)副刊《革命》題寫了刊頭,并在這個(gè)副刊上轉(zhuǎn)載了毛澤東撰寫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
1926年3月,蔣介石發(fā)動(dòng)“中山艦事件”。當(dāng)時(shí)蔣介石提出兩個(gè)條件:第一,共產(chǎn)黨員退出第一軍;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單。
毛澤東和周恩來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討論對策。毛澤東分析說:就廣州的一個(gè)地方看,反動(dòng)派的實(shí)力是大的,但就粵桂全局來說,反動(dòng)派的實(shí)力是小的,只要我黨堅(jiān)持原則,堅(jiān)決予以反擊,就一定能夠爭取團(tuán)結(jié)那些動(dòng)搖的中間力量,粉碎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后來,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huì)議上,提出一句醒世恒言:“須知政權(quán)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周恩來非常贊同毛澤東的分析和主張!
1927年蔣介石終于撕掉擁護(hù)革命的面紗,發(fā)動(dòng)了針對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并沒有被殺絕,被嚇倒。他們從血泊中、從槍口下沖殺出來,為尋找中國革命的道路,又各自繼續(xù)投入新的戰(zhàn)斗。
周恩來來到了江西,發(fā)動(dòng)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毛澤東來到了湖南,發(fā)動(dòng)了震驚全國的秋收起義。毛澤東將秋收起義部隊(duì)拉上了井岡山。周恩來在南昌起義之后去廣州領(lǐng)導(dǎo)了工人武裝起義,但是廣州起義再次失敗,周恩來又不幸身染重病,被陳賡與葉挺兩位愛將冒死救到香港,得以生還。南昌起義的另外一支部隊(duì)在朱德和陳毅的率領(lǐng)下也輾轉(zhuǎn)來到井岡山,從此我們黨有了自己的軍隊(duì)。因?yàn)槟喜鹆x是向國民黨反動(dòng)派打響的第一槍,所以我軍的建軍節(jié)定在了南昌起義的8月1日。“文革”中,林彪一伙為討好毛澤東,多次想修改建軍節(jié)為秋收起義的9月9日,都被毛澤東斷然拒絕。
毛澤東自秋收起義之后,開始思考“以農(nóng)村為中心”“實(shí)行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的中國方式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也就是走以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毛澤東這個(gè)理論讓中央的一些人特別是從蘇聯(lián)學(xué)習(xí)回來的一些人不以為然,他們甚至還理直氣壯地認(rèn)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1931年10月,上海派了一個(gè)由三人組成的“六屆四中全會(huì)代表團(tuán)”來蘇區(qū)“糾偏”。這三個(gè)人就是黨史上有名的“三人團(tuán)”。他們作為“欽差大臣”在贛南會(huì)議上對毛澤東開展了一系列“高強(qiáng)度”的批判,給他戴上三頂大帽子:“狹隘經(jīng)驗(yàn)論”“富農(nóng)路線”和“嚴(yán)重的一貫右傾機(jī)會(huì)主義”。
毛澤東武裝暴動(dòng)之后有過三落。秋收起義后就被“開除中央臨時(shí)政治局候補(bǔ)委員”,是他的第一落。第二落是在1929年落選前委書記離開紅四軍那段歲月。那么第三落就是從這次成為中央批判對象開始的。然而,毛澤東不服輸?shù)男愿駴Q定了他頑強(qiáng)的意志力。不管給他戴什么大帽子,他依然我行我素。
毛澤東這一次也不服輸,他戴著三頂“大帽子”領(lǐng)導(dǎo)紅軍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他回到中央蘇區(qū)瑞金,已從上海搬到瑞金的中央機(jī)關(guān)并沒有覺得這位打勝仗的毛澤東有什么特別之處值得大家去宣傳。但毛澤東畢竟是凱旋的將軍,勝利就是他軍事才能的最好證明。由于毛澤東在蘇區(qū)的影響,在蘇區(qū)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shí),通過了在上海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上當(dāng)選為臨時(shí)中央政府主席。
不久,中央做出取消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的決定,所有部隊(duì)集中統(tǒng)一于以朱德為首的蘇區(qū)中央軍事委員會(huì)。到了11月,中央蘇區(qū)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進(jìn)一步撤銷了毛澤東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wù)。
毛澤東是個(gè)個(gè)性很強(qiáng)的人,他覺得自己留在前方難以發(fā)揮作用,憤而同意離開前方,回后方治病休養(yǎng)。
毛澤東在蘇區(qū)黨內(nèi)、軍內(nèi)的職務(wù)都被剝奪了,失去軍權(quán)的毛澤東耳邊沒有了槍炮聲,頑疾瘧疾又卷土重來,久久地盤踞在他的身體里。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馬都停下了腳步,包括手里的那一支筆也停了下來,兩年沒有寫詩。
這時(shí),在上海同樣受著王明排擠的周恩來,轉(zhuǎn)移到瑞金蘇區(qū)中央局擔(dān)任書記。周恩來剛到達(dá)瑞金,就毫無顧忌地首先去看望剛剛受到“高強(qiáng)度”批判的毛澤東。
毛澤東理解周恩來的處境與苦衷,也非常感激周恩來對他的同情與信任。
第一次寧都會(huì)議結(jié)束后,周恩來再次來到毛澤東在小源的住處探視道別。毛澤東向周恩來表示:若前方軍事急需,何時(shí)電召便何時(shí)來。
不久,周恩來帶兵去“啃”贛州城這塊“鐵骨頭”,幾次攻城都不能取勝。周恩來馬上派項(xiàng)英去請稱病“休閑”了五十多天的毛澤東。這雖然不出毛澤東所料,但在他聽到“恩來同志請你下山”時(shí),便不顧自己發(fā)著高燒,甚至不顧賀子珍勸他等雨停了再走,就冒著傾盆大雨下山去助戰(zhàn),并且大獲全勝。從這以后,無論是戰(zhàn)火亂世還是太平盛世,毛澤東與周恩來始終同舟共濟(jì)、相互倚重!
在中央蘇區(qū),任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是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在中央蘇區(qū)的三年中,與眾不同的是,周恩來更加欣賞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他覺得自己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高瞻遠(yuǎn)矚的天才,在這個(gè)天才的身上,他傾注了自己一腔深摯的感情。從此他們又開始了新的合作與交往。這次合作與交往,遠(yuǎn)比以前要坎坷得多,復(fù)雜得多,也艱難得多,但是兩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卻比任何時(shí)候都要深厚與牢固。
如果提及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中的早期地位,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并沒有一下子就選擇毛澤東。他除了在中共三大當(dāng)選中央委員外,未曾擔(dān)任過要職。
毛澤東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預(yù)備會(huì)議第二次全體會(huì)議上回憶往事時(shí),說過一段頗為風(fēng)趣的話:
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中共一大)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huì)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huì)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huì)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gè)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huì)到了,當(dāng)候補(bǔ)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bǔ)中央委員。
盡管毛澤東在中央蘇區(qū)政治命運(yùn)坎坷,但作為黨中央主要領(lǐng)導(dǎo)人之一的周恩來卻始終是他的支持者,有時(shí)甚至是保護(hù)者。周恩來尊重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長處,在他的堅(jiān)持下,紅一方面軍重新恢復(fù)了毛澤東的軍權(quán),任命他為總政委。在寧都會(huì)議前后,周恩來在毛澤東危難之際周詳?shù)鼐S護(hù)了毛澤東的威望,說服更多的人去認(rèn)識毛澤東,直到長征途中周恩來力排眾議,積極推薦毛澤東“出山”。
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fā)展,遵義會(huì)議日益受到國內(nèi)外史學(xué)界的注目。因?yàn)樗敲珴蓶|領(lǐng)袖地位的起點(diǎn),隨著毛澤東聲望的不斷提高,人們才逐漸意識到這一起點(diǎn)的重要,這一歷史選擇的重要。毛澤東在這以前曾幾度被撤職,幾度遭批判,幾番病重,真可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正是在這歷史的角逐中,毛澤東以其正確的思想、策略和路線,以其卓越的才華脫穎而出,一躍成為中共領(lǐng)袖,從此領(lǐng)導(dǎo)中共達(dá)四十一年之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歷史進(jìn)程。
周恩來正是在這個(gè)偉大歷史轉(zhuǎn)折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人物。對此,毛澤東曾說過:“遵義會(huì)議之所以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lǐng)導(dǎo)問題,恩來起了重要作用。”
遵義會(huì)議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關(guān)系史上的一個(gè)重要篇章,也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緊密結(jié)合的開端,這種結(jié)合,終生未變。此后,毛澤東就在周恩來的輔佐下,成功地領(lǐng)導(dǎo)中國革命和建設(shè)的偉大事業(yè)。
綜上所述,這一系列歷史關(guān)頭的真知灼見,使得毛澤東在風(fēng)雨之中感受到患難見真情的巨大精神力量,為他與周恩來后來半個(gè)世紀(jì)的親密合作奠定了基礎(chǔ)。毛澤東與周恩來,惺惺相惜,心心相印,風(fēng)雨同舟,攜手走了半個(gè)世紀(jì),而立于不敗之地。
困頓病榻
1974年5月31日是個(gè)星期日。這一天周恩來將住進(jìn)三〇五醫(yī)院,并直接上手術(shù)臺(tái)做手術(shù)。他下午將自己的大侄女周秉德叫來,他想在離開西花廳之前,與鄧穎超還有侄女再享用一頓難得的天倫之樂的晚餐。
周恩來和鄧穎超曾經(jīng)有過一個(gè)孩子。那是1927年,鄧穎超由于難產(chǎn),男嬰生下來便夭折了,鄧穎超的身體也因此變得非常虛弱。恰逢當(dāng)時(shí)國內(nèi)一片白色恐怖,鄧穎超當(dāng)夜逃難到上海尋找周恩來,一路顛簸下來,身體受到嚴(yán)重傷害,從此再也沒有孕育孩子。但周恩來有兩個(gè)胞弟,他們均有孩子。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蘇淮安。周家在當(dāng)?shù)卦谴蠹彝ィ街芏鱽砀赣H這一輩已經(jīng)破落。周恩來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按照家里的老規(guī)矩,如果一家沒有后代,其他兄弟家應(yīng)該過繼一個(gè)孩子給無子嗣的這一家,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續(xù)香火”。
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家孩子比較多,他向周恩來表達(dá)過,可以過繼一個(gè)孩子給他,男孩女孩都可以,只希望哥哥身邊不要太寂寞,但周恩來還是婉拒了。他怕要了一個(gè)孩子,其他孩子心里會(huì)感到不平衡,覺得自己當(dāng)伯伯當(dāng)?shù)貌还健S谑侵芏鱽頉Q定將弟弟們的孩子都視同己出。他拿自己的工資供他們上學(xué),關(guān)心他們的成長和進(jìn)步。他的侄兒侄女們,一直也將伯伯、伯母當(dāng)作這個(gè)大家庭的最高家長,有什么重要事情是一定要與伯伯、伯母商量的。
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大女兒,在嫡親侄輩中年齡居長,十二歲那年,在周恩來夫婦與家人商議之后,她住進(jìn)中南海西花廳,和周恩來夫婦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才離開中南海。她在親屬中與周恩來夫婦來往最為密切,鄧穎超也曾說過,周秉德是所有親戚中和他們夫婦感情最深的人。
這次周恩來要住院,而且是得了重病,他百忙之中想到了要和大侄女再見一面。對伯父病情一無所知的周秉德接到讓她去伯伯家吃晚餐的電話,很高興,心想伯伯終于有時(shí)間可以在家里吃頓飯了。周秉德一進(jìn)西花廳后院的客廳,就看見伯伯穿了一件襯衣坐在沙發(fā)上看報(bào)紙,神情比平時(shí)放松多了。她記得以前來,伯伯不是在辦公就是說幾句話匆匆離開,很少見他能在沙發(fā)上坐一會(huì)兒的。
這一次,周恩來不僅坐住了,而且還與大侄女拉了好一陣子家常。周恩來在餐桌上,將自己即將去住院的事情告訴了周秉德:“你不是看我很清瘦嗎,我現(xiàn)在也確實(shí)有點(diǎn)病,要去醫(yī)院住些日子。明天我去住院,以后我們見面機(jī)會(huì)少了,你自己要好好工作,教育好孩子,回家問你媽媽、爸爸好。”
也許是周恩來語氣輕松,或者是對病情的輕描淡寫,周秉德聽到這消息不僅不擔(dān)心,反而覺得是個(gè)好事。她覺得伯伯這些年太勞累,人瘦了不少,而且也七十六歲了,這次肯去住院治療,就是一次療養(yǎng)休息的機(jī)會(huì)。她高興地對伯伯說:“這太好了,您工作總是那么忙,身體也吃不消。現(xiàn)在您能想通了去住院,好好休息一段時(shí)間,身體肯定能恢復(fù)起來。”
周恩來愣了一下,說:“我爭取吧!”過了一會(huì)兒,周恩來拿出兩張?jiān)缫褱?zhǔn)備好的七英寸彩色照片遞給侄女。周秉德接過去一看,是伯伯和伯母在大寨虎頭山上拍的照片。
周秉德高高興興地收好照片,她以為伯伯這次住院和以前外出視察、出訪那樣,很快就會(huì)回到西花廳,回到原來的生活軌道上,醫(yī)院只是一個(gè)小小的驛站而已。
可后來不久,周秉德就有了疑問。她要求去醫(yī)院看望伯伯,伯母卻對她說:“不行呀,中央有規(guī)定,為了保證他的治療,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會(huì)把你的關(guān)心和問候帶給他的。”
伯伯到底得的什么病?去看望就會(huì)影響治療?難道……盡管周秉德有不祥之感,但她也沒有敢往“癌癥”二字上想,更不敢想象伯伯會(huì)永遠(yuǎn)離開他們!
她對伯伯如此明顯的告別舉動(dòng)竟然沒有絲毫察覺。她一向覺得伯伯身體沒問題,任何時(shí)候見到他,他都是精神飽滿,笑聲朗朗,走路腳下生風(fēng)似的,非常快。別說侄女周秉德沒有察覺,就連整天跟在周恩來后面攝影的杜修賢也沒有察覺,事先一點(diǎn)兒也不知道周恩來總理要住院的消息。他7月5日接到去三〇五醫(yī)院拍攝周總理會(huì)見外賓的通知,猶如當(dāng)頭一棒。他一下子聯(lián)想到5月29日晚,總理和主席握手道別的場景!他覺得自己真粗心,事先怎么就一點(diǎn)兒也沒有察覺總理生了病呢(到這時(shí)他還不知道總理得的是不治之癥),這簡直是不可原諒的粗心大意!
周恩來這幾年明顯消瘦蒼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大家都以為他是由于工作繁忙,大事小事、國事外事日夜操勞造成的;再加上他樂觀的情緒常常“蒙蔽”了大家,使得總理身邊許多人在感覺上造成了偏差,都不知道他已是身患絕癥兩年多的病人。
杜修賢聽說總理在醫(yī)院里,先是一驚,接著和周秉德的想法一樣,住院對于總理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有了休息的環(huán)境,說不定休息、治療一段時(shí)間,再回到西花廳工作和生活,身體就會(huì)好起來。這樣一想,杜修賢心里反而覺得愉快起來。
事情真是如此嗎?只有當(dāng)事人周恩來與醫(yī)療組的醫(yī)生心里最清楚,重回西花廳幾乎就是天方夜譚。周恩來在這年的4月22日會(huì)見日本朋友,當(dāng)客人再次邀請他訪日時(shí),他沉沉地嘆了一口氣:我欠的賬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說我出不去了。我東邊不能超過日本、朝鮮,西邊不能超過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邊不能超過越南、緬甸,北邊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東走還有很多國家,我都欠賬了……
侄女走后,周恩來到辦公室整理了一會(huì)兒文件,向秘書交代了一些工作,然后穿上中山裝,來到這個(gè)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五年的院落里,懷著訣別的心情,凝視著眼前熟悉的環(huán)境,站立良久,默默地在心里跟這所院落揮手說再見。
周恩來離開西花廳并沒有馬上去醫(yī)院,而是先去了人民大會(huì)堂,他去醫(yī)院前還要處理一件公務(wù)活動(dòng),那就是要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簽署《中馬建交公報(bào)》。這是中馬兩國之間的一件大事,周恩來十分重視這次公報(bào)簽署儀式。在杜修賢的鏡頭里,這一天總理臉色蒼白,顯得神情疲倦,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不像原先那么煥發(fā),眼睛也不如原先那么有神了。杜修賢一陣心酸,只以為總理又因?yàn)榘疽梗瑳]有睡好覺,累成這個(gè)樣子了。
盡管周恩來拖著重病的身軀,在強(qiáng)打精神,勉強(qiáng)支撐著主持外交活動(dòng),但他自始至終都在認(rèn)真地履行總理的職責(zé)。
打開周恩來1974年1月至5月31日的工作日程,我們可以看到,不到半年里,周恩來是怎樣在用自己的病軀承擔(dān)起黨和國家的重?fù)?dān)。除了幾次病重不得不臥床外,工作達(dá)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shí)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時(shí)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過十八小時(shí)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時(shí)的有五次,連續(xù)工作三十小時(shí)的有一次。
在這五個(gè)月中,周恩來接見外賓八十多人次,僅5月份就接見外賓二十多人次。光親自接待、會(huì)談的外賓就有坦桑尼亞總統(tǒng)尼雷爾、柬埔寨副首相兼國防大臣喬森潘、塞內(nèi)加爾總統(tǒng)桑戈?duì)枴突固箍偫聿纪小⑷致匪箍偨y(tǒng)馬卡里奧斯、英國前首相希思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
這哪里是一天一天的記載,也不是一字一字的記錄,分明是一滴血一滴血的流淌,一步一步地走向生命的終點(diǎn)。然而,這就是周恩來,也是性格、使命與無奈并存的周恩來。
他在公報(bào)上落下“周恩來”三個(gè)字,身后賓主一片歡呼,紛紛舉杯慶賀。儀式結(jié)束,賓主離開人民大會(huì)堂,此時(shí)已近午夜。周恩來在鄧穎超以及保健醫(yī)生、護(hù)士等的陪同下,前往解放軍三〇五醫(yī)院。他一到醫(yī)院,日歷就翻到了1974年6月1日……
周恩來住院的準(zhǔn)確記載時(shí)間為1974年6月1日,也是源于此。自此以后,周恩來再也沒有離開三〇五醫(yī)院的病床,這里成為他生命歷程的最后驛站。
為什么會(huì)選定一所戰(zhàn)備醫(yī)院作為周恩來的治療醫(yī)院呢?原因有二:第一,三〇五醫(yī)院位于北海公園西岸,與西花廳只有一墻之隔,距離近;第二,這棟只有四層樓的建筑物,建于中蘇珍寶島事件以后,是專為毛澤東等中央負(fù)責(zé)人修建的戰(zhàn)備醫(yī)院。因?yàn)槭且粋€(gè)新建醫(yī)院,院內(nèi)醫(yī)療設(shè)備在當(dāng)時(shí)還屬先進(jìn)。但是這所醫(yī)院也有不足的地方,這之前是沒有設(shè)泌尿科的,在確定周恩來來三〇五醫(yī)院住院治療后,由衛(wèi)生部牽頭,將上海的熊汝誠、天津的虞頌庭調(diào)往北京,再從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阜外醫(yī)院、解放軍總醫(yī)院、友誼醫(yī)院、北大醫(yī)院、北京醫(yī)院和中醫(yī)院抽調(diào)了吳階平等十多位全國有名的泌尿科、外科、心血管病等方面的專家與麻醉師組成了專門的醫(yī)療小組,與跟在周恩來身邊的保健醫(yī)生以及護(hù)士組成了醫(yī)療護(hù)理班子。就是說三〇五醫(yī)院因?yàn)橹芏鱽碓诖酥委煻鴵碛辛艘粋€(gè)最強(qiáng)大的專家班底的泌尿科。這些專家教授一方面為總理治病,一方面抽出時(shí)間到醫(yī)院門診坐診、查房或者到其他醫(yī)院去為其他病人診療,一邊實(shí)踐一邊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以更好地為周恩來治療。
周恩來有個(gè)奇特的生活習(xí)慣,他睡覺時(shí)必須使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國訪問,他的被褥都要帶著。盡管這套被褥已經(jīng)跟他很久,也非常陳舊,對著陽光看都是絲絲縷縷磨得透亮了,但是周恩來睡覺就是離不開它們的陪伴,好像只有蓋著它們,才會(huì)有睡意似的。就連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那一夜,為了處理這起緊急事件,周恩來第一次住在人民大會(huì)堂的臺(tái)灣廳,衛(wèi)士長也是趕緊叫在家的警衛(wèi)將總理用的被褥抱到了大會(huì)堂。但是周恩來臨陣指揮這場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為危急的意外事件,一連五十多個(gè)小時(shí)沒有合眼,這些被褥自然沒有用上,最后還是抱回西花廳,才蓋在了主人身上,讓周恩來安心地小睡了一會(huì)兒。
這次周恩來住進(jìn)醫(yī)院也是如此,病床上使用的還是自己在西花廳用慣了的被褥,只是進(jìn)行了消毒。
周恩來住院前,還有一個(gè)人格外忙碌,那就是葉劍英元帥。他趕在周恩來住院前,親自到醫(yī)院檢查各項(xiàng)準(zhǔn)備工作,甚至連醫(yī)務(wù)人員的夜餐費(fèi)、補(bǔ)助、伙食標(biāo)準(zhǔn)等都由他親自制定。6月1日凌晨,周恩來上了手術(shù)臺(tái),葉劍英又親自到專家就餐的伙房,向廚師們抱拳叩謝:“拜托大家了,讓專家們吃好,也是照顧好總理。拜托拜托……”
以后,葉劍英每天必定要到醫(yī)院看望周恩來。有時(shí)很晚了,他也要來,如果碰到周恩來睡了,他就在病床旁的屏風(fēng)外默默坐一會(huì)兒。葉劍英無微不至的關(guān)心,令病中的周恩來感到戰(zhàn)友之間深厚的友情與無言的精神慰藉。
經(jīng)過檢查,醫(yī)生發(fā)現(xiàn)周恩來患有腫瘤的位置有了改變,也大了一點(diǎn),但還是可以做手術(shù)切除的。手術(shù)進(jìn)行得非常順利,幾天后,周恩來就能活動(dòng)了,解手也不再痛苦,也沒有血尿了。他的臉上再次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第一次大手術(shù)后,周恩來很認(rèn)真地囑咐醫(yī)護(hù)人員,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shí)如實(shí)地告訴我,因?yàn)檫€有許多工作,要作個(gè)交代。
周恩來住院手術(shù)后一個(gè)月左右,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和夫人來華訪問。
中美兩國由對峙走向?qū)υ挘忻狸P(guān)系的解凍,是毛澤東、周恩來晚年的外交杰作。杰克遜是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對于改善中美關(guān)系至關(guān)重要。周恩來對前來訪問的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自然很重視,加之身體有好轉(zhuǎn),他決定借參議員要求與他會(huì)面的機(jī)會(huì)“復(fù)出”。于是,他將在醫(yī)院會(huì)見美國客人的想法報(bào)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了。
(實(shí)習(xí)編輯/王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