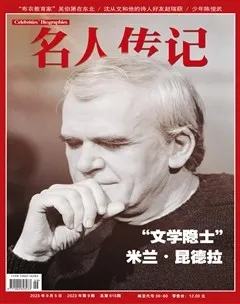“項城張氏”與“壽州相國”的家族交情






河南項城的張氏家族是出了名的耕讀世家,被譽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便出自這個家族。張伯駒繼父張鎮芳是狀元帝師孫家鼐的門生。身為最后一位直隸總督,張鎮芳可謂清末民初政壇上的風云人物。孫家鼐是光緒帝師,安徽壽州(今壽縣)人,因德高望重而被稱為“壽州相國”。從政壇上密不可分的關系網,到文化人之間的君子往來,“項城張氏”家族與“壽州相國”家族間的關系盤根錯節……
關于張伯駒,最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要數他在古書畫鑒賞領域的成就。用張伯駒自己的話說,他“生逢離亂,恨少讀書,三十以后嗜書畫成癖。見名跡巨制雖節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然而,收藏只要有錢有閑有雅興就可以,鑒賞卻需要深厚的底蘊、廣博的學識和獨到的眼光。因此,自古以來,紈绔子弟酷愛收藏字畫者多如牛毛,而能夠成為一代鑒賞大師者卻是鳳毛麟角。
張伯駒能從一個收藏玩家成長為一代文化名家,其天資聰穎,善于鉆研是一個原因;張家家世顯赫,張伯駒具有廣泛的、高層次的社會交往,是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就不得不提張伯駒家族與孫家鼐家族間的三代交情了。
三代世交:官場織起關系網
“項城張”與“壽州孫”是三代世交,在晚清政壇上,兩個家族間織起了綿密的關系網。
孫家鼐是安徽壽州人,四部尚書、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孫家鼐禮賢下士,行事低調,平時雖不顯山露水,卻因德高望重,被稱為“壽州相國”。連清流派首領、軍機大臣張之洞都承認“方今朝廷正論賴公(孫家鼐)主持,天下瞻仰”。
“天子門生,門生天子。”身為光緒帝師,孫家鼐具有十分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1859年(咸豐九年),孫家鼐考進士,殿試試卷要求以清朝歷代皇帝的功績為題撰一副對聯。孫家鼐提筆寫道:“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繼羲皇堯舜;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云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他的這副對聯,將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的年號巧妙地嵌入其中,論述精當,文采斐然。據說咸豐皇帝讀后大喜,遂用朱筆把他點為狀元。一時間,孫家鼐名揚天下。
孫家鼐是近代中國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不僅在政壇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其他領域也卓有成績。他是著名大儒,主編過《欽定書經圖說》(五十卷)、《續西學大成》(十六卷)、《大清法規大全》(一百五十九卷)等叢書。他有較高的中醫造詣,多次給軍機大臣、光緒帝師翁同龢等同僚治病。除此之外,他的書法自成一家,還有高超的古書畫鑒賞水平。1894年即光緒二十年,孫家鼐陪同光緒帝到昭仁殿,檢點“天祿琳瑯”藏書,“皇上留意古籍,常以宋元書畫賜其觀賞”。
張伯駒清楚地記得,父親張鎮芳是“清朝狀元宰相孫家鼐之門生”。張鎮芳拜孫家鼐為師后,得到其悉心指點,在古書畫鑒賞等方面受到熏陶。至于張伯駒是否隨父親拜見過孫家鼐,是否親耳聆聽過他的教誨,現在雖不得而知,但張伯駒自幼受父親影響,接觸書畫等傳統藝術,后來成為收藏大家,未始不是童年埋下的種子。1909年孫家鼐逝世,當時張伯駒十一歲。
張鎮芳生于1863年,為清光緒年間進士,后深得袁世凱倚重,歷任長蘆鹽運使、直隸總督等職。因參與張勛復辟被捕,出獄后棄政從商,擔任鹽業銀行董事長。張鎮芳與孫家鼐家族關系十分密切,尤其體現在官場的聯系上。
首先,張鎮芳與孫家鼐的親侄孫孫多玢、親侄婿龔心銘有同年之誼。
孫多玢是孫家鼐二哥孫家鐸的孫子,龔心銘是孫家鼐四哥孫家丞的二女婿。1892年(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殿試,張鎮芳登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九十一名。同一榜,孫多玢、龔心銘登二甲,分別賜進士出身第九十一名和第九十二名。在科舉時代,同一榜錄取的進士稱作“同榜”,也叫“同年”。同年之間常惺惺相惜,互稱“年兄”,就像現在的同學、戰友一樣。張鎮芳三人“肩膀頭一般高”,是彼此在官場上重要的人脈資源。
其次,張鎮芳與孫家鼐的親侄孫孫履安、堂侄孫孫毓筠共事多年。
孫履安是孫家鼐大哥孫家澤的孫子。1903年8月,張鎮芳受任直隸永平七屬鹽務局總辦,任上勵精圖治,成績突出,自此開始發跡,后升任長蘆鹽運使。張鎮芳任長蘆鹽運使期間,孫履安在其手下做事,任使署監印官,是張鎮芳的親信和得力部下。1930 年,孫履安調任中國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1932年調任天津分行經理,與張鎮芳一樣,都成了大名鼎鼎的銀行家。
孫毓筠是孫家鼐的堂侄孫。1907年1月,孫毓筠奉孫中山之命潛入南京行刺兩江總督端方被捕。由于孫家鼐的庇護,孫毓筠幸免于難,自此名聲在外。中華民國成立后,孫毓筠任安徽省首任都督,張鎮芳任河南省首任都督。安徽、河南互為鄰省,兩人之間亦素有交往。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行,發表接受帝位申令,次日成立“帝制大典籌備處”,張鎮芳與孫毓筠均在“籌備處骨干”之列。
除此之外,張鎮芳與孫家鼐的另一親侄孫孫多鑫是換帖兄弟。孫多鑫是孫家鼐二哥孫家鐸的次子孫傳樾的長子,舉人出身,娶了李鴻章四弟李蘊章的孫女為妻,是李鴻章的侄外孫女婿。孫多鑫投身實業后,生意做得風生水起。1898年,孫多鑫從美國考察歸來,在上海開辦中國第一家機器面粉廠——阜豐面粉廠,產品暢銷大江南北,銷量曾居“遠東之最”。袁世凱對孫多鑫備極賞識,將其攬入自己的幕府,“委任為奏折秘書,凡袁世凱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孫手。自此袁與孫見面無虛日,言聽計從,不久更委為直隸官銀號總辦,天津造幣廠督辦,顯赫一時”。張鎮芳亦是袁世凱的親信,其姐嫁給了袁世凱同父異母的哥哥袁世昌。張鎮芳與孫多鑫一見如故,結拜為異姓兄弟。
君子之交:京劇搭起情誼橋
“項城張”與“壽州孫”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傳到張伯駒這一代時,上一輩的功利之交更是升級為君子之交。這還多虧了京劇這一文化橋梁。
清末民初,京劇風靡全國,一躍成為國粹,無數達官顯貴為之如癡如醉。當時京劇名家輩出,流派紛呈,余叔巖、梅蘭芳、楊小樓并稱京劇“三大賢”。20世紀20年代,余叔巖創立余派,成為京劇生行最受戲迷追捧的流派。張伯駒自幼喜愛京劇,1928年,三十歲的張伯駒正式拜余叔巖為師,跟隨其學習、研究京劇達十度春秋,前后學了近四十出戲。張伯駒還與余叔巖一起合編過一本《近代劇韻》。
“壽州相國”家族的孫履安不僅是一個銀行家,也是一個京劇名票。孫履安曾跟隨羅壽山學丑角戲,能演《老黃請醫》《定計化緣》《打櫻桃》等劇目,善于在臺上臨時抓哏(即興抖包袱,以引觀眾發笑)。孫履安的長子孫養農更是以研究余叔巖出名。孫養農是余叔巖的表親,又是他的摯友,幼年寄居天津時,就曾多次觀看“小小余三勝”(余叔巖少年時代的藝名)的演出,并為之傾倒。孫養農是余府的座上客,在京劇表演上常得到余氏的指點。其一生極度佩服余叔巖,盛贊余是“中國戲劇藝術之最高峰,趨超凡入圣之境界”。
孫養農在其《談余叔巖》一書中提到了張伯駒,說他“為人風雅但生性孤傲,外貌落落寡合,跟他不熟的人,望之生畏而不敢親近”。然而,由于對京劇特別是對余派藝術的情有獨鐘,張伯駒與孫家父子共同語言越來越多,私交也愈加密切。1925年,張伯駒退出軍界,到鹽業銀行擔任常務董事和總稽核,需每年兩次到上海分行、漢口分行等地核查賬目。每次一到上海,張伯駒必去孫府拜訪,且經常應邀參加孫家舉辦的堂會。張伯駒在《紅毹紀夢詩注》中對這段梨園情誼做過多次記述:
壽州孫履安,其祖父清狀元宰相孫家鼐,為先君座師,余與其為三世交。盧溝橋事變次年,余以事去上海,值其六十歲壽日,約余為演戲。
某歲,余去上海,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劉君,及孫履安、孫養農父子款余,共演戲為歡……
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京劇是一門集大成的綜合性藝術,而藝術的規律與審美是相通的。毋庸置疑,與孫氏父子長時間的切磋,不僅提高了張伯駒的京劇藝術修養,而且對提升其書畫鑒賞能力,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兩肋插刀:患難之時見真情
孫履安的小兒子孫曜東曾這樣形容孫家與張家的關系:“我和張伯駒是換帖把兄弟,我的大伯父(孫多鑫)與他的父親張鎮芳,也是換帖把兄弟。”
張伯駒是鹽業銀行董事長的代理人,孫曜東是上海復興銀行的總經理,二人在銀行業務上多有往來。由于家族及公務上的多重關系,張伯駒和孫曜東的個人關系非同一般。而患難見真情,幾件棘手之事的發生讓張伯駒與孫氏父子的交情更上了一層樓。
張伯駒每年兩次到上海分行查賬。在那個時代,作為腰纏萬貫的公子哥兒,張伯駒到十里洋場,交朋會友,逛青樓、聽小曲、吃花酒,都是免不了的。當時上海交際圈有位潘素女士,藝名“潘妃”,彈得一手好琵琶。一天,張伯駒遇見了潘素。孫曜東在其著作《浮世萬象》中記錄了這段往事,稱“兩人英雄識英雄,怪人愛怪人,一發而不可收,雙雙墜入愛河”。
可這件事并沒有那么簡單。彼時潘素已名花有主,跟國民黨一個叫臧卓的中將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誰知半路殺出個張伯駒,潘素反悔,決心離開臧卓,跟隨張伯駒。臧卓豈肯罷休?他在西藏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間房,把潘素軟禁了起來,不許她露面。潘素無奈,每天只能以淚洗面。張伯駒也心慌意亂,他是一個書生,對手則是個國民黨中將,這又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他人生地不熟的,硬來怕會惹出大亂子。無奈之下,張伯駒只好去找好友孫曜東。
在上海灘,孫曜東黑白兩道都吃得開。作為把兄弟,他知道張伯駒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于是兩肋插刀,冒險將潘素解救了出來,并在蘇州請父親孫履安做證婚人,成全了張伯駒和潘素的傳奇愛情。
在上海,張伯駒還有一段更為驚心動魄的經歷。1941年6月,張伯駒遭汪偽政府特工總部“76號”綁架,性命危在旦夕。
剛開始,對方獅子大開口,要張家出二百根大金條(每根重十兩)贖人,否則就要撕票。孫曜東聞訊后,利用自己是周佛海(時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部長)機要秘書的特殊身份,第一時間向周佛海報告,請他打電話給“76號”施壓。同時,孫曜東找到把兄弟、“76號”特務頭子李士群,要他親自過問此事。除此之外,孫曜東還找到上海市警察署署長盧英,要其確保張伯駒的生命安全……
經過長達八個月的艱苦談判,贖金一降再降,最后降到二十根大金條。可即便如此,潘素依然拿不出來。她不能變賣丈夫的古字畫,因為張伯駒有言在先:“無論發生什么事,這些字畫貴賤都不能賣!”無奈之下,她只好向孫履安求助。孫履安不顧年老體衰,親自帶她到各家銀行借貸,終于籌到巨款并按期交了贖金。最終,張伯駒脫離險境,平安歸來。
若干年后,孫曜東回憶道:“張伯駒被解救出來以后,就拿蔡襄的一個卷子(《蔡襄自書詩》卷)送給我。這是他之前花兩萬七千塊錢買來的,價值當然要比二十根條子要大。”孫曜東則婉言謝絕了張伯駒的好意。
生死關頭,孫氏父子的及時救助,不僅挽救了張伯駒,還保住了其視若性命的古字畫,亦間接使這些珍貴的文物不至于損壞或流失海外。1956年7月,張伯駒將其收藏的《蔡襄自書詩》卷,連同陸機《平復帖》等八件書法作品無償捐獻給國家,受到了文化部的褒獎。
(責任編輯/張靜祎" "實習編輯/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