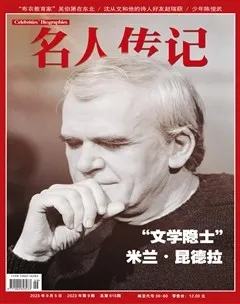“布衣教育家”吳伯簫在東北






吳伯簫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作《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等曾入選中學(xué)語文課本。作為一名作家,吳伯簫以風(fēng)格獨(dú)特的散文贏得了無數(shù)讀者的喜愛。而少有人知的是,吳伯簫還是一位教育家,曾以滿腔心血培育出許多杰出人才。
1946年6月,吳伯簫來到佳木斯,進(jìn)入東北大學(xué)(今東北師范大學(xué))工作,在四年半的時(shí)間里為這所新生的人民大學(xué)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xiàn)。1951年1月,吳伯簫調(diào)任沈陽東北教育學(xué)院(今沈陽師范大學(xué))副院長兼黨支部書記,直到1954年3月被調(diào)往北京。這段在東北工作的歲月成為吳伯簫從事新中國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階段,他也由此躋身當(dāng)代著名教育家之列。
延安著名作家奔赴東北
1906年3月,吳伯簫出生于山東萊蕪的一個(gè)富裕家庭。他先后畢業(yè)于山東省立曲阜第二師范學(xué)校、北京師范大學(xué)。時(shí)值外寇入侵,國家危亡、民族多難,青年吳伯簫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辦教育、寫文章、從軍,以期為抗戰(zhàn)出一份力。然而他看不慣國民黨官僚的腐敗與無能,于1938年4月只身奔赴延安。在國統(tǒng)區(qū)備感孤寂的吳伯簫,“一望見嘉陵山的寶塔,鳳凰山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暢,呼吸自由,到家了”。
到延安后,吳伯簫成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xué)第四期政治班學(xué)員,并任駐瓦窯堡的第一大隊(duì)三支隊(duì)政治班班長。四個(gè)月后結(jié)業(yè)時(shí),毛澤東為他題詞“努力奮斗”予以勉勵(lì)。1938年11月,吳伯簫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抗日文藝工作組”第三組組長,與卞之琳、馬加等人,從延安到晉東南前線,再轉(zhuǎn)河北一帶,挺進(jìn)敵人后方,從事戰(zhàn)地文化宣傳工作。這段時(shí)間他寫出《潞安風(fēng)物》《沁州行》兩組通訊報(bào)道及《響堂鋪》《路羅鎮(zhèn)》等作品,發(fā)表在老舍編輯的《抗戰(zhàn)文藝》上。
解放區(qū)的生活鍛煉了吳伯簫,讓他的思想提升到了一個(gè)新的境界,他不再像在國統(tǒng)區(qū)時(shí)那樣哀怨和惆悵,而是有了改造世界的遠(yuǎn)大志向。1939年5月,從晉東南回到延安的吳伯簫,在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xié)會(huì)工作,一度任該協(xié)會(huì)秘書長,并在中國女子大學(xué)任教。1941年8月,吳伯簫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在延安,吳伯簫主要從事陜甘寧邊區(qū)的教育工作。七年多的時(shí)間里,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歌頌抗戰(zhàn)軍民英雄事跡的作品,如《戰(zhàn)斗的豐饒的南泥灣》《一壇血》《黑紅點(diǎn)》《化裝》等,引起熱烈反響,成為延安的著名作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偽滿洲國隨之覆滅。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戰(zhàn)略決策,一方面派遣部隊(duì)赴東北;另一方面,高瞻遠(yuǎn)矚部署文教事業(yè),旨在將新民主主義的新教育推向新解放區(qū)。9月,毛澤東在延安大學(xué)傳達(dá)黨中央的決定:抽調(diào)一批骨干去東北創(chuàng)辦“新型的東北大學(xué)”。吳伯簫正是其中的一員。
11月中旬,初冬的延安。在緊張而忙碌的準(zhǔn)備后,吳伯簫喝了最后一口延河水,再望一眼寶塔山,帶著戀戀不舍之情,告別戰(zhàn)友,告別久居的窯洞,隨延安大學(xué)遷校隊(duì)伍東渡黃河,直奔東北。途中,吳伯簫內(nèi)心對(duì)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黑土地產(chǎn)生了無限憧憬。
隊(duì)伍翻山越嶺前進(jìn),不時(shí)遭遇土匪騷擾和國民黨軍的破壞,行進(jìn)過程并不順暢。當(dāng)一行人好不容易到達(dá)河北懷來時(shí),因國民黨軍攻占承德,封鎖了山海關(guān)一帶的交通,他們只得停了下來。中央電令,延大隊(duì)伍在剛被我軍解放的張家口待命,暫時(shí)并入華北聯(lián)合大學(xué),吳伯簫任中文系副主任。
在張家口,吳伯簫經(jīng)常為《北方文化》《晉察冀日?qǐng)?bào)》寫稿,作品有《出發(fā)點(diǎn)》《孔家莊紀(jì)事》《把戲》等,以此抒發(fā)自己“留戀延安的熾熱感情”,歌頌解放區(qū)火熱的戰(zhàn)斗生活。
1946年6月,根據(jù)中央指示,吳伯簫等人繼續(xù)向東北進(jìn)發(fā)。一行人白天趕路,晚間露宿。吳伯簫自述:“從多倫、赤峰、白城子一線,時(shí)而卡車,時(shí)而牛車、徒步、火車,勝利地到達(dá)齊齊哈爾、哈爾濱、佳木斯。一路橫跨八省,簡直記不起遇到過什么困難。在內(nèi)蒙古草地遇雨,卡車捂進(jìn)四無人煙的荒野泥沙里,兩天兩夜,拿炒面充饑,接雨水解渴,算是困難吧?但那有什么,我們?cè)缬兴枷霚?zhǔn)備。因此,在那種情況下,連同行的老人、小孩都照常歡歡喜喜,沒有一個(gè)叫個(gè)苦字。”
二十多天后,他們到達(dá)了佳木斯。此時(shí),中共建立和領(lǐng)導(dǎo)的東北大學(xué)幾經(jīng)輾轉(zhuǎn)已落腳于此。吳伯簫等人的到來,為東北大學(xué)增添了新的有生力量,吳伯簫被任命為社會(huì)科學(xué)院副院長兼圖書館館長。
改造和教育東北青年
東北大學(xué)是共產(chǎn)黨在東北地區(qū)創(chuàng)建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xué),1946年2月在遼寧本溪成立。建校伊始,教職員工奔赴東北各地招生。然而隨著東北戰(zhàn)事的發(fā)展,學(xué)校被迫由本溪先后遷往安東(今丹東)、通化、吉林、長春、哈爾濱、佳木斯,一邊遷徙,一邊進(jìn)行招生宣傳。
吳伯簫到東北大學(xué)后,與招生干部們一起走訪了東北解放區(qū)的許多縣、鄉(xiāng)。為了取得家長們的信任,拉近和學(xué)生們的距離,他常常到學(xué)生家里做說服工作,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各項(xiàng)主張,介紹學(xué)校的情況。在這一過程中,被錄取的學(xué)生還沒有到校,吳伯簫就與他們建立了感情,還將他們的家庭成分、經(jīng)濟(jì)情況、文化水平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學(xué)生招到了,該怎樣教育和改造他們呢?彼時(shí)東北已被日本奴役了十四年,偽滿洲國覆滅后,國民黨趁勢而起,這導(dǎo)致許多青年對(duì)共產(chǎn)黨不了解。受學(xué)校辦學(xué)條件和戰(zhàn)爭等因素的影響,許多課程沒法開,學(xué)校只好“辦抗大式的訓(xùn)練班”,主要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一次,吳伯簫帶新生從延吉趕往佳木斯,一行人憑解放區(qū)發(fā)放的通行證坐火車,“開飯的時(shí)候,沿途兵站把飯菜送到車上。冬天,飯菜都是熱的,而時(shí)間不早不晚,碗筷不多不少,準(zhǔn)確得叫人吃驚。從敵偽十四年奴化教育下剛解放出來的男女青年,簡直驚奇得目瞪口呆”。一路上,共產(chǎn)黨人一絲不茍、細(xì)致踏實(shí)的作風(fēng)和全新的工作模式,使青年們深受感動(dòng)。
校方安排有專人迎接新同學(xué),有些不過只來了三五天的學(xué)生也一擁而上歡迎新同學(xué),這讓新生感受到了革命隊(duì)伍的熱情。大家“穿一色的衣服,吃一樣的伙食,師生頓時(shí)形成了融洽的整體”。一開始教室還沒修繕好,大家紛紛聚到院子里,老師站著講課,學(xué)生們沒有小凳子,就席地而坐,但“都肅靜無嘩,唯恐漏聽了‘聞所未聞’的道理”。下了課,師生們平等相處,一起唱革命歌曲、跳秧歌舞,氛圍十分自由活潑。
1948年4月,學(xué)校組織師生體驗(yàn)十天的農(nóng)村生產(chǎn)勞動(dòng)。兼任語文班班主任的吳伯簫,隨學(xué)生下鄉(xiāng),與農(nóng)民同吃、同住、同勞動(dòng)。他根據(jù)這次勞動(dòng)的體驗(yàn)和見聞,在農(nóng)家的土窩棚里寫出了報(bào)告文學(xué)《十日記》。在文中,他這樣記錄學(xué)生們一天的工作安排:“從早起到晌午,下地生產(chǎn);下午干一氣家家戶戶底零活,再讀報(bào),記日記,寫心得;晚上漫談,檢討,交換經(jīng)驗(yàn)。附帶作的組織婦女兒童,辦黑板報(bào),幫辦小學(xué)。唱歌、演劇、敲鑼鼓扭秧歌,搞清潔衛(wèi)生,都是瞅時(shí)間看需要來進(jìn)行的。”在農(nóng)村,學(xué)生們看到了農(nóng)民生活的困苦,感受到了農(nóng)民對(duì)土地的渴望、對(duì)土地改革運(yùn)動(dòng)的期盼。這種親身參與的教育形式,對(duì)學(xué)生們的影響很大。
此外,針對(duì)學(xué)生們喜歡讀書看報(bào),渴望接觸新事物、新思想的特點(diǎn),東北大學(xué)與佳木斯文化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合作創(chuàng)辦了知識(shí)雜志社和東北文化社,分別出版半月刊《知識(shí)》和半月刊《東北文化》,解決學(xué)生們沒書讀的難題。吳伯簫承擔(dān)《東北文化》的編輯工作,《東北文化》于1946年10月10日首次刊行,深受學(xué)生們的歡迎,許多東大學(xué)子多年后回憶在學(xué)校的學(xué)習(xí)生活時(shí),都會(huì)提到它。利用這塊陣地,吳伯簫相繼發(fā)表了《文藝底階級(jí)性》《介紹〈東北文化〉》等文章。
當(dāng)了一次“紙商”“鹽販子”
東北大學(xué)初創(chuàng)時(shí)期,辦學(xué)條件極其艱難。1946年10月初,張如心等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寫信,反映缺衣少食的實(shí)際情況。對(duì)于此時(shí)的學(xué)校和師生來說,一分錢、一點(diǎn)點(diǎn)物資都是好的。
吳伯簫也和學(xué)校其他領(lǐng)導(dǎo)一樣,想辦法籌物資、弄器材、找圖書。一次,他在吉林省榆樹縣(今榆樹市)發(fā)現(xiàn)了一批古籍,立時(shí)眼中放光。這段收書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記憶中,也被他寫進(jìn)了文章里:“我住在縣委一間茅屋的土炕上。屋里除了我的鋪位,滿堆的都是書,從《四書備旨》到《清史稿》,都是線裝古籍。那是土地改革中從地主家里搜集來的。‘這些書你們?cè)趺刺幚恚俊壹婀軋D書館,有責(zé)任籌措精神食糧,就這樣問縣委書記。書記說:‘前線還在打仗,這些書正愁不知運(yùn)到哪里,你們要嗎?全部送給你們。’‘那太好了。’我搶著回答。這樣,靠新生七手八腳裝了二十幾木箱運(yùn)到了佳木斯。當(dāng)時(shí),連一部《辭源》也找不到,這些書可真是及時(shí)雨呵。”
1948年3月,吉林解放。7月初,東北大學(xué)與吉林大學(xué)合校,校名仍為東北大學(xué),吳伯簫任文藝系主任。7月中旬,學(xué)校正式由佳木斯遷往吉林。在此之前,吳伯簫等人已經(jīng)組成先遣隊(duì)奔赴吉林八百垅地區(qū),為后續(xù)大批人員的到來做準(zhǔn)備。師生們迅速投入到校園修復(fù)中去,吳伯簫親自帶頭搬運(yùn)物資,大家備受鼓舞。
還有一次,吳伯簫帶人去遼東省招生。在安東,他訪問了一家由作家朋友雷加當(dāng)廠長的造紙廠,廠里存紙堆積如山,考慮到學(xué)校教學(xué)用紙捉襟見肘,吳伯簫立刻向雷加提出:“學(xué)校能要一點(diǎn)嗎?”雷加答復(fù)道:“財(cái)經(jīng)辦事處批個(gè)條子就行。”于是,吳伯簫急吼吼地拿著介紹信,趕到東北財(cái)經(jīng)辦事處請(qǐng)示,成功地要到了這批紙。這批紙,學(xué)校整整用了兩年,解決了紙張短缺的大問題。
正巧此時(shí)遼東省政府主席約吳伯簫等人吃飯,席間談到“全黨辦大學(xué)”的問題。省主席說:“省里分配給學(xué)校的款子可以順便帶回吉林學(xué)校,免得再派專人押送了。”“不過這次是黃金,帶到吉林可能有差價(jià),到銀行談?wù)務(wù)鄢墒雏}吧,那里正需要食鹽,鹽價(jià)也不會(huì)有太大的波動(dòng)。”吳伯簫興奮不已,馬上把上萬元的款項(xiàng)就地兌換成了食鹽。回學(xué)校的路上,吳伯簫與同事,一個(gè)跟卡車運(yùn)紙,一個(gè)跟火車運(yùn)鹽。到吉林后,他們立刻賣掉了食鹽,還賺了點(diǎn)利潤。吳伯簫對(duì)這次當(dāng)“紙商”和“鹽販子”的經(jīng)歷相當(dāng)滿意,稱其是“半生的驕傲”。
關(guān)愛教師和學(xué)生成長
1948年10月,長春解放。次年,沈陽東北大學(xué)(文、法、商學(xué)院)、長春大學(xué)(文、理、法學(xué)院)、長白師范學(xué)院并入東北大學(xué),新的東北大學(xué)遷往長春。8月初,東北大學(xué)設(shè)立文學(xué)院,吳伯簫任院長。
面對(duì)學(xué)校新的發(fā)展機(jī)遇,吳伯簫繼續(xù)著力提高院系的師資力量和教學(xué)水平。為了留住人才,做好教師們的思想動(dòng)員工作成為他的一項(xiàng)重要工作內(nèi)容。1949年春,滿族作家丁耶從華北聯(lián)大調(diào)入東北大學(xué)工作。當(dāng)時(shí)丁耶已經(jīng)小有名氣,他滿心以為自己是來搞創(chuàng)作的,誰知被安排教書,便想打退堂鼓。吳伯簫來看望他,上來就摸了摸丁耶從華北解放區(qū)穿來的那身薄棉襖,說:“東北比晉察冀冷啊,等一會(huì)兒給你領(lǐng)一件棉大衣來。”從衣著打扮和言談舉止上看,丁耶判斷吳伯簫應(yīng)該是管人事或總務(wù)的同志,他拒絕了吳伯簫的好意。吳伯簫早猜出了丁耶的想法,笑著對(duì)他說:“你在國統(tǒng)區(qū)寫的東西我看過。今后你還可以繼續(xù)寫嘛,我們文學(xué)院正需要懂寫作的教師。你年輕,可以領(lǐng)學(xué)生下廠、下鄉(xiāng)去體驗(yàn)生活。”“蕭軍、舒群都在東大任過教,公木、蔣錫金、楊公驥、田思基都在這里,還要把穆木天教授請(qǐng)回來……”聽了吳伯簫的介紹,丁耶覺得能同這些文學(xué)前輩一起工作也很難得,于是答應(yīng)留下來。離開時(shí),吳伯簫告訴丁耶“不要過急決定,考慮好了再告訴我”,同時(shí)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丁耶此時(shí)才恍然大悟,原來眼前這位老同志就是解放區(qū)的老作家吳伯簫,自己在國統(tǒng)區(qū)時(shí)就讀過他的散文和小說,印象極深。后來丁耶回憶:“這位老延安作家,作風(fēng)樸素:一身藍(lán)棉襖,滿臉笑紋,在我腦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在吳伯簫的努力下,知名學(xué)者如穆木天、唐圭璋、公木、孫曉野、蔣錫金、楊公驥、張畢來、李輝英、彭慧等均來到東北大學(xué)任教,這一時(shí)期的東大文學(xué)院辦得紅紅火火。
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時(shí),吳伯簫還要給學(xué)生上課。他長期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豐富,因而講課深入淺出,很實(shí)用。為鼓勵(lì)學(xué)生寫作,吳伯簫想了很多辦法。吳伯簫的學(xué)生兼同事孫中田教授回憶:“他所重視的是在課堂教學(xué)的基礎(chǔ)上,引領(lǐng)學(xué)生到社會(huì)實(shí)踐和文藝實(shí)踐中去。這時(shí)候,請(qǐng)勞動(dòng)模范到學(xué)校來言傳身教是一個(gè)方面;同時(shí),只要有機(jī)會(huì),就讓同學(xué)們到農(nóng)村去,到工廠去,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寫出來。”
想要做好這些事情,不可避免地要投入大量的時(shí)間和精力。為此,吳伯簫直接住在了辦公室,白天工作,晚上或者節(jié)假日就在辦公室與學(xué)生們暢談,不僅談寫作,聊思想,也談心,話家常。一旦發(fā)現(xiàn)了好的素材和苗頭,吳伯簫就立刻加以點(diǎn)撥,要求學(xué)生動(dòng)手寫出來。作品交到吳伯簫手里后,對(duì)于有新意的文稿,他親自修改,然后推薦到《吉林日?qǐng)?bào)》的《文藝》副刊發(fā)表。后來成為作家的學(xué)生中,很多人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那里發(fā)表的。
布衣風(fēng)范
吳伯簫雖然出身于富裕農(nóng)家,但是自從加入革命隊(duì)伍,他便一直保持簡樸的生活,戰(zhàn)爭年代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后也是這樣,冬天一件藍(lán)棉襖,夏天一身灰布衣,外人一點(diǎn)也看不出他是文學(xué)院的院長、著名作家。1950年4月,東北大學(xué)更名為東北師范大學(xué),吳伯簫任文學(xué)院副院長、副教務(wù)長。
那時(shí),文學(xué)院設(shè)在“滿炭大樓”里。這座大樓原是偽滿洲炭礦株式會(huì)社的辦公大樓,裝修極為講究,橡皮地板需要天天擦洗。可全院只有一個(gè)清掃工,干不過來,清掃工作便由老師和同學(xué)們來承擔(dān)。倒洗痰盂和清掃廁所之類的活,一些新入學(xué)的學(xué)生不肯干。作為學(xué)院領(lǐng)導(dǎo),吳伯簫盡管公事繁忙,仍帶頭打掃衛(wèi)生。他把藍(lán)棉襖袖子一挽,就干起活來,以至一些學(xué)生把他當(dāng)成了老校工。一天,全體學(xué)生聽吳伯簫做《學(xué)習(x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的報(bào)告。新來的學(xué)生只知道吳院長是老作家,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但都不認(rèn)識(shí)他本人。主持人宣布開會(huì)后,“就見那個(gè)老校工一手提著暖水壺,一手拿只茶杯走上講臺(tái),他倒了一杯水就坐下了”,學(xué)生們覺得好笑,竊竊私語,這老校工倒完水怎么還坐下了?主持人接著說:“同學(xué)們靜一靜,聽吳院長講話。”學(xué)生們這時(shí)才明白,原來那個(gè)經(jīng)常倒痰盂、打掃廁所的“老校工”就是吳院長。
吳伯簫不僅用慈母般的愛關(guān)懷著他的學(xué)生,更言傳身教,以正直無私的操守盡顯一位教育家的風(fēng)范。那時(shí)他才四十多歲,卻被學(xué)生們稱為“老媽媽”。
1951年1月,吳伯簫離開工作了四年半的東北大學(xué),調(diào)任沈陽東北教育學(xué)院(今沈陽師范大學(xué))副院長兼黨支部書記。離開北國春城,他在一份手稿中寫道:“長春,有永遠(yuǎn)是春天的意思么?綠柳化翠,紅杏初穎,至少有這愿望。我到長春恰在三山崩搖、黑土翻身的時(shí)候……”
1954年3月,吳伯簫調(diào)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參加編輯中學(xué)《文學(xué)》課本,兼任中央文學(xué)講習(xí)所所長。至此,吳伯簫離開了山環(huán)水繞、沃野千里的大東北。在東北的八年時(shí)間里,他犧牲了個(gè)人的創(chuàng)作時(shí)間,以滿腔熱忱在教育領(lǐng)域深耕,哺育了成百上千的東北學(xué)子。
1956年,吳伯簫參加全國總工會(huì)組織的作家參觀團(tuán),任南下團(tuán)團(tuán)長,走訪中南各省,創(chuàng)作了許多詩文作品,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文革”結(jié)束后,吳伯簫任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副所長,兼山東大學(xué)教授、全國中學(xué)語文教學(xué)研究會(huì)副會(huì)長等職。
1982年8月10日,吳伯簫病逝于北京。臨終時(shí),他對(duì)子女說:“我死后不要給人民添任何麻煩,不通知親友,不舉行任何儀式,希望把骨灰撒在家鄉(xiāng)的泰山。”盡管吳伯簫已經(jīng)離開我們很久了,但正如孫中田所言,“他質(zhì)樸而謙和的形象,他的永不歇止的革命精神,他的‘布衣’風(fēng)范,卻愈見其大,永遠(yuǎn)活在人民的心中”。
(責(zé)任編輯/張靜祎" "實(shí)習(xí)編輯/藕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