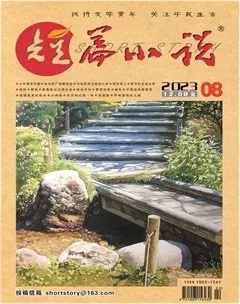電的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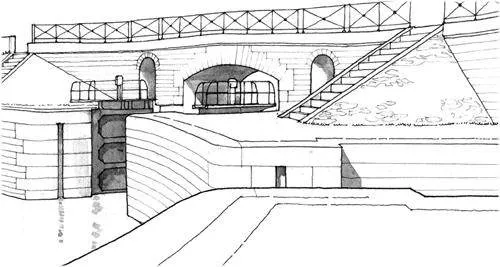
一
1970年,離竹林灣10公里遠的泥塘河開始動工修建發電站了。
瓦漢城聞訊而至。可是剛剛開始修建,不過就是一些石匠、木匠在那兒倒騰,看不出一點電站的蹤影。所以瓦漢城只在工地上徘徊一陣,便非常失望地回家了。
泥塘河電站竣工后,瓦漢城就親自到泥塘河電站去參觀。
瓦漢城有自知之明,僅憑他那點文化知識,說什么也看不透這電站里面的玄機。他只是聽那些站里的人講述著什么叫高壓線,什么叫機組,什么叫水輪機,什么叫電線桿。
雖然他心里懸著,可是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發出白光的電燈。
沒多久,那些主線就拉到龍溪公社街上來了。當然沒有往竹林灣方向延伸,而是向著龍塘區街上延伸。他還聽到消息說,那個電站就是以龍塘區的名義修建的。證明像竹林灣這些山區地帶,也只能望梅止渴。
說是等到哪天區里又在泥塘河增加機組后,才可能把電線往竹林灣延伸。這可是一個已知的消息,未知的答案。
瓦漢城就盼望著,哪一天泥塘河電站能夠增加機組,電線或者電線桿子往竹林灣延伸。
二
1973年,說是我們竹林灣附近的筲基灣生產隊,啟動修建小型水電站。目的當然是因為1972年大天旱嚇怕了。修建一個小型水電站,一可以照明,二可以修建提管站,抽水到筲基灣山頂上灌溉糧田。
瓦漢城非常興奮,仿佛他成了筲基灣的一員。可是我年輕的父親沖瓦漢城說:“細公,你可知道人家筲基灣出了什么人物?”瓦漢城說:“什么人物?”
我父親說:“雖然汪年華在咱們龍塘區當區委書記,可是汪年華是筲基灣人,筲基灣擬屬篩子區的管轄,他可以跟篩子區的區委書記溝通,把相關項目拿到筲基灣來做。當然筲基灣水電站這個項目,肯定不會是篩子區的人要來的項目,而是通過汪年華到縣里或者地區,或者省里直接要的項目。這樣的話,當然篩子區的區委書記不敢把這個項目拿到別地去做啊!可惜我們竹林灣沒有像汪年華這樣的人物啊!”
瓦漢城聽我父親這樣一說,那點兒興奮勁也就煙消云散了。他無奈地說:“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啦?”
我父親說:“沒有辦法了。”
瓦漢城想想,自己小時候沒有認真讀書,如果認真讀書的話,弄個一官半職,問題也就解決了。可惜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后悔藥吃。就這樣,瓦漢城蔫蔫地回家去了。他對手里的馬燈也沒了興趣,好幾個月不去擦它,上面起的煙垢已經把那層玻璃給蓋得嚴嚴的,只透出昏暗的光……
三
就在1974年的夏天,瓦漢城在友誼生產隊做木活,有人專程來告訴瓦漢城:“我們竹林灣生產隊在召集社員開大會,要你回去一趟。”
瓦漢城說:“開什么大會?”
來人說:“研究修建水電站的事情。”
瓦漢城哪根神經波動了一下,說:“修建水電站的事,咋不去呢,一定得去。什么時候?”
來人說:“明天晚上。
瓦漢城說:“好!”
1974年我10歲,開始懂得一些事情。我父親跟水電站站長斯興旺熟悉,斯興旺跟我父親透露說:“竹林灣下面的峽谷可以修水電站。”
我父親問斯站長:“國家會不會給我們撥款?”
斯站長說:“撥款是不會的,但是可以批手續。”
我父親覺著只要能夠批手續,也算國家為竹林灣人盡力了。我父親第一個就想到瓦漢城,因為瓦漢城看見筲基灣修建水電站,就來我父親那兒反映,希望能夠在竹林灣建一個水電站。于是專門找人通知瓦漢城。
那天晚上的會議在集體糧倉舉行。來了二十多個社員。
這些社員都是渴望能夠照上電燈的人,抑或在竹林灣有點威望的人。先以預備會的形式,擬訂出方案,再按照這個方案在集體會議上宣布。
生產隊的資金不多,只有五六百塊錢。
我父親問過斯站長。斯站長說:“五六百塊錢,肯定不夠,至少需要兩千塊錢。”
我父親跟與會者商量,問:“可不可以賣幾頭牛來彌補這個缺口?”
與會者沒有回答。與會者覺著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可能由他們答應。
拖了一會兒時間,我父親又說:“大家表決一下嘛,可以還是不可以總得發一句話噻。”
此時,瓦漢城發言了,說:“只是看國家的意思,如果是我來表決的話,肯定可以賣牛,因為集體的錢,是大家的,那么集體的牛也是大家的。水電站好啊!水電站供電,水電站就是電源,這是我家在部隊上的瓦良普說的。有了電源,就可以照電燈了。況且水輪機我也看了,跟水車沒有多大區別,我們可以只買發電機,水輪機我們修水車來替代。”
瓦漢城大兒子瓦良先說:“你不要出那些餿主意喲,一行服一行,螺螄服米湯,人家那可是配套的東西,你用水車替代?”
瓦漢城罵他大兒子:“你曉得個屁!我在泥塘河觀察了好久,又到筲基灣觀察好久,不稀奇,用水車沒問題的。”
小兒子瓦良賢說:“可就是用水車替代水輪機,然而發電機可沒什么替代呀。你沒想想,發電機是金屬做的,水輪機也該是金屬做的,你用一個木質的去替代金屬,拉得動不?將比說,你用豆腐去跟豬骨頭火拼,你拼得過豬骨頭不?我就認這個死理。”
瓦漢城說:“說一千道一萬,你不試試咋知道呢?”
瓦良賢說:“哎呀,還得那個事兒談,跟你說,木的和鐵的混不在一塊兒。”
瓦漢城揪到一根木棍就要打瓦良賢,被旁的人拽住,說:“哎呀,你說用木車帶行,就用木車帶嘛,瓦良賢也是,硬要從磨眼鉆過嗎,咋的?”
瓦良賢覺得人多嘴雜,就不予理論了。瓦漢城以為他的想法被人肯定了,就狂妄自大地說:“你看人家瓦良佐,才夠聰明,你說木的和鐵的又如何打不到一堆呢?簡直胡扯!”
會場上的人都默不作聲,只有我當隊長的父親說:“這個問題,可不能作兒戲,一旦出了問題,誰都負不起責任。當然漢城細公有這種減少成本的想法,為生產隊、為集體的利益著想,作為我個人,肯定是持贊成態度的,可是這是科學的東西,我個人也做不了主。”
一個在部隊上待過、現在成公社委員的、經常拿著毛主席語錄的瓦中亮說:“毛主席老人家說過,知識的問題是科學的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其的恰恰是其反面。
“瓦中亮這段毛主席語錄背得好,要實事求是,所以我建議找區水電站的站長來跟我們做個評定,看用木車行不,如果行,那我們就用木車,如果不行,那就另想辦法。”我當隊長的父親說。
瓦漢城說:“這樣,水車由我自己出木材,我自己來做,一旦成功,大家拿錢,肯定比水輪機劃算。”瓦良先有些奈何不了瓦漢城,說:“你還不是要人家把發電機買來了再說,你先不先就做水車,做來不恰當咋辦?”瓦漢城說:“噢,你這句話嘛,倒還像句人話。”
我當隊長的父親默不作聲,因為他已經提出找水電站斯興旺來做個評定,行,才用水車,不行,還得買水輪機。
我祖輩是做騾馬生意的,我父親對騾馬不熟,可是我父親對牛太熟悉了,口腔幾牙,那牛脊背的毛出現幾個漩渦,牛蹄生得咋樣,是剪刀蹄還是甲魚蹄——我父親都了如指掌。所以哪些牛可以賣掉,哪些牛作為座根牛,我父親也了如指掌。
我父親平常就在觀察竹林灣所有的耕牛。那頭只有一個人敢犁的大水牯,必須賣掉;那頭只長個不用力的大黃牯必須賣掉。其次就是那頭不拉犁,又不生崽,可肉身還不錯的水母牛必須賣掉。事先賣掉三頭牛,然后再說。這是我父親在隊委會上的決定。
隊委會的人員總共有五個人,大家都一致認為可行。會計痛苦地說:“會不會把責任都攬到我一個人的頭上?”另外的人說:“哪里會呢?是隊長提議的,隊長還要簽字蓋章呢。”
我當隊長的父親眉頭緊鎖,仿佛一下子老了許多,也非常痛苦地說:“還有我呢,你怕啥?”
就這樣確定賣這三頭牛。生產隊的牛,無論誰家喂養,誰也沒有權利掌握它的生殺大權,只有隊里能掌握它的生殺大權,說白了,只有隊長可以掌握它的生殺大權。更進一步說,就是我當隊長的父親,他說了算。
所以盡管你把牛喂養得膘肥肉滿的,隊里說要賣,就得賣;隊里說要留,就留。這個規矩可不是一天兩天了,這可是十多年來訂下的規矩。即使有人心頭不痛快,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后來,我的隊長父親把他定下的這幾頭牛賣給四川的一個牛販子。
牛販子在我家放了兩個多星期的牛,說是發電報過去,那邊還要派人坐火車過來,估計就是送錢過來的人。
送錢來的人來到竹林灣,第二天就把牛給牽走了。
我父親送這兩個牛販子走了很遠。很多年后,出過跟牛販子送牛的人被牛販子暗殺的事,我父親心里也一陣后怕。可是我父親的眼睛毒,他能夠看得出這兩個牛販子是什么品質。當他們把牛送到背彎背坳的地方后,那個先到我家的牛販子把我父親叫到田埂背陰處,把衣服脫下來,我父親才看見他衣服背心的地方縫了一只袋子,他把這袋子的針線撤掉,里面露出的就是那些新嶄嶄的拾元鈔。一匝新嶄嶄的拾元鈔是一百元。總共有多少匝,我父親數得清清楚楚。我父親把鈔票揣進一只紅布口袋里,與兩個牛販子握手告別。
后來,我父親順利地將那只紅布口袋帶到竹林灣來,點數給會計,會計打了收據給我父親,總計是兩千塊錢。
四
那天,斯興旺站長來我家了。大熱天的,站長搖著蒲扇,坐在我家屋門口,把后門打開,讓風從后門通到前門,涼爽得很。旁邊放了一只木凳,木凳上沏好了茶水。站長抽旱煙,準備了一根大頭煙鍋,那煙鍋里裝得滿滿的煙絲,擦一根火柴,點亮后,有過道風拂過,那煙鍋里的煙火像天空的星星閃爍不定。我不理解,人為什么要抽煙,因為煙霧在空中飄散了,煙頭又燃燒盡了,又填不了肚子。我父親就坐在室內的拐角處,嘴角叼著一根旱煙,我父親這人簡單,不用煙鍋。
屋里靜得只聽見房屋背后樹林里知了的叫聲。我父親與站長說話:“站長,你說用水車替代水輪機行不?”
站長說:“這還是一個新鮮玩意,沒看到過,也沒人這樣做過,不知道行不行,咋的,你們準備用水車替代水輪機?”
父親沒有強調說是誰出的主意,父親只說:“我自己在想,你想想,那石碾子那么沉重,都可以用水車帶動,想必那發電機也能用水車替代。”
站長說:“我可沒有用過噢,也沒看見過噢。不過可以試試,反正成本不大。”我父親說:“哦。”
其次就是聊一些自家的一些經歷。嚴格意義上說,父親在水電方面是外行。父親就是想帶領大家好好勞動,不餓飯。
我家熬了一鍋糯米粥,另外還加了幾個酸酸菜,就吃中午飯了。當然父親好的就是喝一口酒。
一般地講,外頭來人了,必須喝酒,這是缺不了的禮儀。站長也喝酒,你一杯我一杯的來,大熱天的,喝過酒后,滿臉通紅不說,那汗水牽了線地流。站長說:“不再來了,不再來了——”
可我父親自己加了一杯,說:“就過過路!”
于是又給站長添了一杯。
站長眼睛都喝鼓了,說:“這酒厲害。”然后不喝了。
站長不喝了,我父親也不喝了。站長與我父親分別扒了一碗糯米粥,就下席了。太陽閃陰閃陰的,但凡這種天氣,都有幾分悶熱。父親與站長克服了悶熱,到實地進行策劃,看看哪里安裝水輪機,哪里安裝發電機。地點策劃在萬佛峽谷的馬達塘。
策劃好后,石匠就要開始動工了。
石匠動工的時候,瓦漢城也動工了,他開始做水車。水車軸上要做帶動發電機皮帶的轉盤。這是一項非常細致的活路,稍計算不準,會出現不松就緊,抑或不緊就松。這項細致的活路,非一般的工匠能完成的。瓦漢城做這個轉盤的時候,是在把發電機抬到峽谷來的時候。瓦漢城在發電機那軸的轉盤上量了又量,一直量到他認為準確無誤的時候,才得出一個數據。也就是這個轉盤的周長是多少,寬度是多少。一分一毫都不能差。在他看來,已經非常準確的時候,石匠們也把該做的活路都做完了,便請斯興旺來我們安裝發電機。
斯興旺對瓦漢城的木匠活,雖然談不上贊不絕口,但還是用認同的口氣說,應該可以帶動。試機的時候,竹林灣有好多人都去觀看。竹林灣人看得真真的,傳送帶像黏在水車軸上一樣,可即使水的沖擊力來得非常激烈,傳送帶還是一動不動。于是瓦漢城考慮到給傳送帶搭一把力。用手去拉傳送帶的時候,那傳送帶嗚一下,轉動起來,瓦漢城那小手指隨著傳送帶的轉動,也飛起來,不知落到何處去了。
被人們送到公社醫院的瓦漢城,通過打針服藥,緩解過疼痛后,便一口一個“撞鬼了”地叫。他再三強調,他的做工是沒有問題的,他的計算也是沒有問題的。可是瓦良先卻強調說:“你的什么都是沒有問題的,是機器跟你過不去。你又沒想想,你想用水車帶動發電機,別人家就沒有想到嗎?那筲基灣的人全都是傻子嗎?不知道造水車嗎?白作聰明——”
瓦漢城準備從病床上彈跳起來打瓦良先。可當他正彈跳的時候,那斷手指的地方鉆心地痛。他只能服輸,又乖乖地躺在床上。但那股怒氣卻久久難以平息。
我隊長父親安慰他,說:“細公,你別生氣,斯站長都說,你那種發明創造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木質與鐵質的確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你沒有成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后來通過斯站長的介紹,從一個叫上塘寨的地方,購買了一臺舊水輪機。加了八抬,有人說十二抬,反正就那么一個意思,才把這臺水輪機抬到馬達塘來。“這臺舊水輪機的功能是帶動十二千瓦的發電機的,而我們安裝的這臺發電機只有六千瓦。所以,不能鉚足勁地讓水輪機轉動。”斯站長再三交代。
五
安裝上水輪機已經是1975年春天了。機房跟碾坊一樣的造型,能夠遮住兩臺機器。瓦漢城的傷勢已經痊愈。瓦漢城木工活都不做了,就陪伴在機房,看發電機轉動,輸電。
瓦漢城跟我當隊長的父親講:“只給我記工分就得了。”我當隊長的父親說:“行,但安全問題,自己處理,隊里活路忙,照顧不了你。”瓦漢城說:“行。”
那一段時間,竹林灣的夜晚真的挺輝煌。除了照明,沒有別的地方用電。所以,白天不用開機。白天瓦漢城就躺在機房的那張簡易床鋪上睡覺,夜晚守到通天亮。
春雷響動的時候,瓦漢城還是有些緊張。因為關于電的知識,他是七竅通了六竅,一竅不通。瓦良先和瓦良賢都叫他退出來,讓懂電的人去守。可是瓦漢城卻毫不服輸,說:“不就守著看它們轉動,一旦不轉動,我就把閘閥關掉,這個我還不行嗎?大驚小怪的。”
后來他征得我隊長父親的同意,大凡打雷下雨,就可以關閘。所以大凡打雷下雨的時候,整個竹林灣又恢復了過去的狀態,照上煤油燈。當然竹林灣的人也不反對,大家都怕死。可是如果沒打雷下雨,夜晚他還把個機子關起睡懶覺,大家就會把他炒掉。所以瓦漢城一直謹小慎微,非常注重這些細枝末節。
那天晚上,又不缺水,電機也沒壞,可在瓦漢城的眼里,那燈光卻非常弱。瓦漢城想當然地覺著是水輪機功率不夠。于是瓦漢城便把閘閥全部打開,增大水流量,讓水輪機完全轉動起來。
瓦漢城忽略了一個問題,斯興旺再三叮囑說:“水輪機功率大,發電機功率小,不能鉚足勁地讓水輪機轉動。”
只見那發電機冒出一道火花,嚇得瓦漢城渾身冒汗。瓦漢城慌張著把堰塘的閘閥關掉,讓水輪機停止轉動。瓦漢城再次打開閘閥,那發電機又冒一道火花,瓦漢城又把閘閥關掉。那個夜晚,沒打雷下雨,卻突然停電,社員們都想不明白。第二天,社員們追問瓦漢城時,瓦漢城做了一個誠實的人,一點沒有推脫責任,說:“是我的錯,是我把閘閥全部打開,讓水流量增大,燒壞發電機了。
至此照了兩個月的好電后,停電了。發電機壞了,三修兩不修的,那水輪機和發電機就當廢鐵扔到峽谷里無人問津了。有人忍不住了,毫無廉恥地,不要臉不要命地去跟筲基灣的人商量,說他們那個發電機功率大,是十二千瓦的,照理照亮我們竹林灣與筲基灣都沒有問題。筲基灣管理電站的人與竹林灣人是親戚,沒有辦法,只能勉強答應了。
最初只有鄰近筲基灣的幾家竹林灣人接上筲基灣電站的電源,后來就發展到整個竹林灣人都接上筲基灣的電源了。有人就到龍塘區黨委書記汪年華那兒打小報告,說筲基灣電站的汪小生答應竹林灣的所有人家用上他們電站的電源。汪年華一想,筲基灣是他的老家,竹林灣與筲基灣是近鄰,又是他當區委書記管轄的范圍,所以他跟筲基灣來打小報告的人做了一通工作,打小報告的人便灰溜溜地回去了。從此竹林灣的人就真是毫無廉恥地順理成章地用上筲基灣的電源了。
六
突然一場大雨,沖毀了筲基灣電站。然而人家筲基灣人并不缺電用,他們用上他們公社的電源了。而我們竹林灣的公社,其電源本身就不足,如果要去接上那個電源,也只能是陰一下陽一下地亮著。有人說,雖然陰一下陽一下地亮著,可是總比沒電燈強。于是大家把電線從那些電線桿子上卸下來,重新栽電線桿子,拉線,從我們黑塔水大隊那兒接電源。從此我們便陰一下陽一下地用起我們公社的電源。
1989年,我家在竹林灣破天荒地買了一臺十七寸黑白電視機。架了天線。可是到處要電,而那電燈都起紅絲絲,咋還能放電視呢?于是我在去泉水縣城開會的時候,順便帶了一部升壓器。起初還行,能夠啟動電視機,可是竹林灣的人最會跟風,看見我買升壓器,可以將電壓升高,每家每戶都跟著買升壓器,大家的電燈又重蹈覆轍,全起紅絲絲。電視也看不成了。好在,隨著打工潮流的興起,年輕人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家里的人在逐漸減少,這樣一日三三日九的,電量基本夠用,電視也抬頭了。瓦漢城這時成了一名電工。雖然沒有資格證,可是他對電真感興趣。他認真負責,除了每月收取電費外,哪家電路有點雞毛蒜皮的小毛病,都是他冒險去解決。后來因為年紀大了,加上瓦良先的竭力反對,他就把他的這套業務交給瓦良賢了。
七
2009年,我父親過世,我們在老家安葬父親。聽竹林灣在龍溪村任副主任的尚華兄講,要搞農網改造了。很久,我都沒有明白農網改造是什么意思。以為是要改造農業農村生產上的一個新名詞,最后得到它的全稱,叫農村電路網絡改造,簡稱農網改造。具體解釋,是電力公司的一個員工在負責,問其究竟,才知道,是要把全國的電力系統合并在一起,也就是把所有的發電站合并在一起輸送電力能源。這一下,我明白了,起碼也就是像以前筲基灣所在的公社電站與當時龍溪公社的電站的電力能源合并在一起。取長補短,平衡電力能源。這樣一來,把那些大型電站合并在一起,也就不會出現電力不足了。瓦漢城也聽說要重新搞電路,要增加電力能源。他戴著一副老花鏡,從牌桌子上下來,不斷地追問尚華兄:“你說什么意思,真要改造電路了?我還是那天上街聽說的。”
尚華兄說:“嗯。”
那是三月的天氣,白天暖和,夜晚有些涼意。可是瓦漢城把面上的衣服一剮,把里面那件襯衫衣袖一撈,卷到胳膊肘子那兒,說:“那就好了,可以像龍溪街上安裝打米機了吧?”
瓦尚華說:“沒問題。
瓦漢城說:“幾百千把塊錢的打米機,可以買得起,而那些電線變壓器買不起,這樣算下來,我們也就不會肩挑背磨地去菜家林打米了。
尚華兄說:“那是肯定的。”
安葬了父親。母親一個人在老家,我們不放心,便把她一起接到縣城生活。
八.
2010年春節,我們拖家帶口地回到竹林灣老家上墳,看見的電線及電線桿子,大不相同了,真可謂鳥槍換炮,煥然一新。
那只電表也換成電子電表,像城里一樣,不用電工去抄表,直接在電腦里顯示出每家的用電量。瓦漢城喜歡熱鬧,他叫他的小兒子買了落地音箱,竹林灣里,一首《常回家看看》響徹云霄。我們去給父親上墳的時候,路過他家,瓦漢城老漢站在院壩里,嘴巴一嗡一合地附和著哼唱著那首曲子——
這樣的日子,瓦漢城老漢過得有滋有味,持續到2017年舊歷三月。尚華兄打來電話,說是老壽星瓦漢城老漢過世了。沒聽說瓦漢城老漢生病,問其死因,尚華兄悻悻地說:“竹林灣的水、電、路全部開通了,高興死的——”
這是說笑,但大家也會感覺到生活如此美好。
在安葬瓦漢城的時候,說是瓦漢城老漢平生對電充滿了激情,為了讓他的靈魂繼續保持這份激情,他的小兒子瓦良賢給他的小棺材里布滿了彩色電燈。說是用一種鉛蓄電池,可以將這些彩色電燈照個十大年。這事準不準,那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