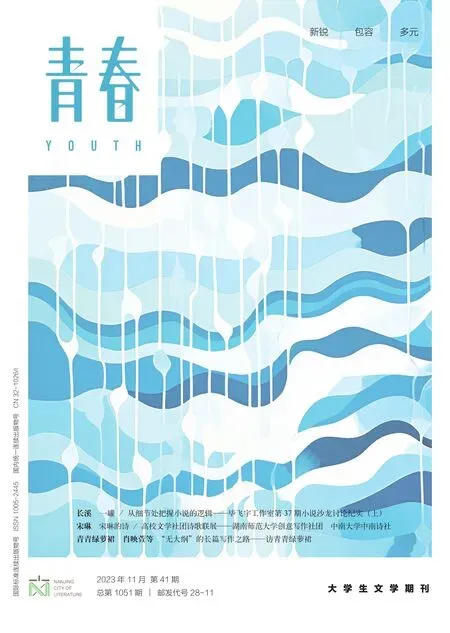抒情·廢墟·懷舊
——理解孫頻近作的三個(gè)關(guān)鍵詞
山東大學(xué) 紀(jì)水苗
無(wú)論是以代際群體被概括,還是以創(chuàng)作關(guān)鍵詞被總結(jié),作家總是無(wú)法避免被標(biāo)簽化的命運(yùn)。孫頻亦是如此,她的創(chuàng)作被冠之以“80 后寫(xiě)作”“底層敘述”“女性寫(xiě)作”“苦難敘事”等標(biāo)簽。眾多的標(biāo)簽說(shuō)明孫頻創(chuàng)作的多重面向,也說(shuō)明孫頻在有意識(shí)地進(jìn)行敘事的實(shí)驗(yàn)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轉(zhuǎn)向。在孫頻2022 年發(fā)表的中篇小說(shuō)中,我們可以看到孫頻有意打破以往“生猛酷烈”的敘述慣性,代之以平和而憂(yōu)傷、素樸而詩(shī)意的敘述筆調(diào)。從《我們騎鯨而去》到“山林三部曲”(《以鳥(niǎo)獸之名》《騎白馬者》《天物墟》),再到《海邊魔術(shù)師》《天空之城》《棣棠之約》,孫頻持續(xù)書(shū)寫(xiě)著對(duì)自然的重返與復(fù)歸,并不斷擴(kuò)展敘述的限域:將寫(xiě)作的視野不再僅僅局限于山林湖海之中,而是讓筆觸伸向了更遙深的歷史和文化之中。
一、詩(shī)性的敘事與抒情的面向
從文學(xué)史的角度來(lái)看,如何以恰當(dāng)?shù)姆绞教幚怼扒楦小迸c“現(xiàn)實(shí)”、“抒情”與“敘事”、“內(nèi)傾”與“外涉”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使個(gè)人的情感世界獲得廣泛而普遍的經(jīng)驗(yàn),以及如何使歷史與時(shí)代的記憶書(shū)寫(xiě)更具審美性,是中國(guó)小說(shuō)在對(duì)傳統(tǒng)敘事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而進(jìn)入“現(xiàn)代”之后無(wú)可避免的問(wèn)題。在20 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視野中,小說(shuō)一直存在著抒情傾向,而這種內(nèi)傾的抒情性在不同作家那里又有不同的風(fēng)格體現(xiàn)。20 世紀(jì)20~40年代,魯迅小說(shuō)既抒“哀而不傷”之情,又有文化批判的反抒情傾向;郁達(dá)夫的感傷浪漫主義小說(shuō)抒發(fā)強(qiáng)烈的主觀情緒;蕭紅以純粹而滄桑的筆調(diào)書(shū)寫(xiě)“小城春秋”的詩(shī)篇;沈從文等京派作家則執(zhí)著于用“溫暖與真摯的情感”塑造審美烏托邦。20 世紀(jì)50~70年代,革命浪漫主義激情高漲,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強(qiáng)烈的抒情性主要表現(xiàn)為郭小川、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shī)和劉白羽、楊朔、秦牧的抒情散文。進(jìn)入新時(shí)期之后,知青文學(xué)帶有強(qiáng)烈的情感抒發(fā)和個(gè)人訴求,或書(shū)寫(xiě)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義,或反思?xì)v史和人性:知青文學(xué)的不同面向無(wú)一不具有強(qiáng)烈的抒情性。20 世紀(jì)80 年代中后期,多位作家創(chuàng)作出諸多抒情意味濃郁的作品,如汪曾祺、王蒙、張潔、張承志、張煒、賈平凹、鐵凝、王安憶等。岳雯在論述抒情話(huà)語(yǔ)在新世紀(jì)的“變聲”時(shí),將其概述為“溫情主義”,并以“對(duì)樸素自然的親近與詩(shī)意體驗(yàn)”“對(duì)人性理想的發(fā)現(xiàn)與珍視”“對(duì)人與人關(guān)系的理解與體恤”和“對(duì)生命的敬畏與悲憫”(岳雯:《溫情主義的文學(xué)世界》,《文藝爭(zhēng)鳴》2011 年第3 期)
來(lái)概括“溫情主義”寫(xiě)作的特點(diǎn)。我想,孫頻的小說(shuō)對(duì)樸素日常的描述,對(duì)重情重義、不卑不亢的理想人格的描繪,對(duì)人間真切情義與和諧關(guān)系的講述,對(duì)人面對(duì)無(wú)常命運(yùn)時(shí)的韌性的表現(xiàn)都可以當(dāng)作是此類(lèi)“對(duì)生命抱有暖意關(guān)愛(ài)的寫(xiě)作”的例子。
《鮫在水中央》在第五屆華語(yǔ)青年作家獎(jiǎng)的提名獎(jiǎng)?lì)C獎(jiǎng)詞為:“孫頻的寫(xiě)作從容大氣,抒情氣息濃郁,人物命運(yùn)的浮沉、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變奏,都在詩(shī)性的敘述里得到豐富呈現(xiàn)。”由此可見(jiàn),“抒情”和“詩(shī)性”是解讀孫頻小說(shuō)的關(guān)鍵詞。孫頻小說(shuō)抒情性的突出之處在于,它立足個(gè)體的感性生命,試圖通過(guò)肆意勃發(fā)的情感、哲理叢生的思想、完滿(mǎn)純熟的技法以及綿密蘊(yùn)藉的語(yǔ)言來(lái)探討人的枷鎖與自由、內(nèi)心的痛苦與平和、存在的艱難與解放的可能。這是生命的荒蕪與靈魂的豐饒、心靈的黯淡與生命的張揚(yáng)交錯(cuò)而迸發(fā)的詩(shī)意;這是形體的孤獨(dú)與思想的蓬勃、肉身的沉淪與精神的突圍交織而迸發(fā)的詩(shī)意;這也是孫頻試圖在生命的廢墟之上通過(guò)自然的召喚恢復(fù)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詩(shī)意瞬間。抒情性在孫頻小說(shuō)中,主要通過(guò)抒情式敘事、詩(shī)性意境、情義世界來(lái)建構(gòu)。
其一,抒情式敘事。陳平原認(rèn)為“詩(shī)騷”是中國(guó)小說(shuō)的敘事傳統(tǒng)之一,而“‘詩(shī)騷’之影響于中國(guó)小說(shuō),則主要體現(xiàn)在突出作家的主觀情緒,于敘事中著重言志抒情”,“引‘詩(shī)騷’入小說(shuō),突出‘情調(diào)’與‘意境’,強(qiáng)調(diào)‘即興’與‘抒情’,必然大大降低情節(jié)在小說(shuō)布局中的作用和地位”(陳平原:《中國(guó)小說(shuō)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年版)。孫頻的小說(shuō)常有很好的故事內(nèi)核,其故事性和傳奇性讓讀者樂(lè)此不疲,但孫頻新近發(fā)表的小說(shuō)不再刻意突出故事的傳奇性和曲折性,而是著意表現(xiàn)人物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訴求。如在《海邊魔術(shù)師》《棣棠之約》《天空之城》中,盡管孫頻仍然設(shè)置了小說(shuō)的懸念——?jiǎng)⑿★w到底去了哪里?戴南行于何處漫游?楊聲約為何失蹤?——但是她不再著意于解密,而是重在展示人物心里的波瀾。因而,孫頻常在敘述中以飽含情感卻不泛濫的筆調(diào)表現(xiàn)情節(jié)發(fā)展和人物的情緒起伏,如戴南行在參悟具象與實(shí)質(zhì)之后,感悟到“春日的雨滴,夏日的蟬鳴,秋日的涼風(fēng),冬日的雪花,把這無(wú)法留住的一切做成標(biāo)本,就是詩(shī)。每一株植物是詩(shī),每一個(gè)星座是詩(shī),跳動(dòng)的燭光、爐子里的火苗、茶杯里的新茶都是詩(shī),蜜蜂采的蜂蜜是金色的詩(shī),夜是黑色的詩(shī),友誼是血紅色的詩(shī),所有的這一切放在一起就是詩(shī)集”(孫頻:《棣棠之約》,《鐘山》2022年第4 期)。像這樣具有哲思、抒情性與審美性的表述在孫頻小說(shuō)中俯拾皆是。
其二,詩(shī)性意境。文學(xué)是情感的抒發(fā)和思想的表達(dá),那么小說(shuō)則往往由情而景而意境。“小說(shuō)中的‘意境’是一種‘場(chǎng)面’化的‘情旨’。把‘情’景化,把‘景’情化”(陳平原:《中國(guó)小說(shuō)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年版)。意境即情景交融。“黑色的夜空倒扣在大地上,大地上沒(méi)有一絲光亮,連河水都是黑色的,從我們腳下流過(guò)的時(shí)侯,帶著一種可怖的幽冥之氣。而古老的星座像神話(huà)一樣懸掛在我們頭頂,就連我們腳下的巨石也散發(fā)出某種精神場(chǎng)域,仿佛天地之間的一切都擁有了自己的靈魂”(孫頻:《棣棠之約》,《鐘山》2022 年第4 期)。趙志平和戴南行闊別重逢,飲酒暢談,天地萬(wàn)物都被賦予了靈性,星空遼闊燦爛,宇宙永恒,而戴南行有志于做月光下的漫游客和大地的守夜人。正如朱光潛所說(shuō):“詩(shī)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從時(shí)間與空間中執(zhí)著一微點(diǎn)而加以永恒化與普遍化。……詩(shī)的境界在剎那中見(jiàn)終古,在微塵中顯大千,在有限中寓無(wú)限”。(朱光潛:《詩(shī)論》,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 年版)這番情境既有“景”之詩(shī)意,又具“情”之詩(shī)性。在無(wú)邊無(wú)際的天地之中,戴南行領(lǐng)悟到個(gè)體之于時(shí)空正如一粟之于滄海,因而將對(duì)逝去時(shí)代的執(zhí)念、自我的失落與痛楚化作于天地間漫游的自在。
其三,孫頻小說(shuō)的抒情性還表現(xiàn)為以情義之柔調(diào)和與現(xiàn)實(shí)的緊張感。在《棣棠之約》中,桑小軍可以為戴南行的房子問(wèn)題只身犯險(xiǎn),戴南行亦可以為桑小軍自愿入獄,桑小軍為戴南行的詩(shī)集夢(mèng)想替他自費(fèi)出版,而戴南行則為桑小軍的文學(xué)理想選擇永行路上。《海邊魔術(shù)師》中海島上形形色色的人,或是拒絕開(kāi)發(fā)的土著居民,或是被迫逃離至此的外地人,但他們相互理解、相互溫暖。《天空之城》中的劉靜默默等待著失蹤的楊聲約,即使在楊聲約殘疾之后,劉靜仍然對(duì)其不離不棄。孫頻在小說(shuō)中沒(méi)有以敘述者的口吻對(duì)人物多加議論,也沒(méi)有用綺麗冗長(zhǎng)的語(yǔ)句反復(fù)渲染,只是以樸素的筆調(diào)講述無(wú)常的歷史中人與人之間永恒的溫情,自然而然使作品流露出抒情意味。
盡管孫頻小說(shuō)有強(qiáng)烈的抒情傾向,但她沒(méi)有刻意通過(guò)打破敘事的完整性和內(nèi)在的邏輯性而使小說(shuō)獲得詩(shī)性品格,而是更為注重保持抒情與敘事、情感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張力,從而使得小說(shuō)在保持情感飽滿(mǎn)、詩(shī)性濃郁的同時(shí),亦對(duì)歷史、時(shí)代、現(xiàn)實(shí)有所指涉。
二、歷史的記憶與時(shí)代的痛感
孫頻小說(shuō)中的人物大多是既定秩序的邊緣者,甚至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潰敗者,他們游離在主流社會(huì)和現(xiàn)代生活之外,在各自凋敝的漫漫人生路上踽踽獨(dú)行。在近期小說(shuō)中,孫頻依然在書(shū)寫(xiě)失意者,書(shū)寫(xiě)著他們失意生活中的詩(shī)意瞬間。《海邊魔術(shù)師》中的劉小飛,因偷竊入獄而被家庭和社會(huì)排斥在外;《棣棠之約》中的戴南行、桑小軍、趙志平失落于20 世紀(jì)80 年代理想主義的潰敗;《我們騎鯨而去》中的“我”、老周、王文蘭無(wú)一不是過(guò)往生活中的失魂落魄者……孫頻在一個(gè)個(gè)灰暗又明亮的故事之中,不僅洞察到人性的晦朔與明媚,還在人性的隱秘幽微處察覺(jué)到歷史的脈動(dòng)。在這些荒蕪又豐饒的生命之中,她不再癡迷于對(duì)“沉重的肉身”的書(shū)寫(xiě),而是向生活的更深更遠(yuǎn)處、向生命的更隱秘處、向歷史的更幽微處,探尋人性的可能以及精神的出路。
孫頻的小說(shuō)幾乎都關(guān)涉時(shí)代記憶、個(gè)人創(chuàng)痛以及對(duì)歷史、人性、生命的反思,與此同時(shí),她常在小說(shuō)中設(shè)置“烏托邦”來(lái)探尋個(gè)人精神困境的出路。孫頻顯然是一位對(duì)生活、對(duì)歷史、對(duì)時(shí)代有所思且有所得的作家,她不滿(mǎn)足于僅僅描寫(xiě)個(gè)人的情感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yàn)世界,而是著意于“通過(guò)介入歷史的方式——這個(gè)歷史也顯然不是她所經(jīng)歷和熟悉的歷史——試圖構(gòu)建出個(gè)人與歷史、與時(shí)代、與世界之間的一種錯(cuò)綜復(fù)雜的生命面相”(韓松剛:《孫頻小說(shuō)論》,《上海文化》2019 年第7 期)。《天空之城》中的劉靜毅然決然地反抗自己“工廠(chǎng)子弟”的命運(yùn),不知疲倦地攻讀學(xué)位并以此來(lái)尋求自我解放。楊聲約由插隊(duì)的北京知青與當(dāng)?shù)嘏咏Y(jié)合而生,但他的父親后來(lái)拋妻棄子,母親精神失常。楊聲約從師大歷史系畢業(yè)之后,返回老縣城,徘徊于仰韶文化的廢墟之上,樂(lè)此不疲地找尋曇鸞墓葬。劉靜和楊聲約顯然都背負(fù)著時(shí)代給予個(gè)人的創(chuàng)傷和痛感,他們無(wú)法擺脫這些創(chuàng)傷,只能不斷向歷史的更深邃處,向文明的更遙深處漫溯,并從中汲取超越創(chuàng)傷的力量。《海邊魔術(shù)師》中的劉小飛行竊成癮,后因行竊失去了學(xué)業(yè),也失去了家庭的庇護(hù)。此后,劉小飛輾轉(zhuǎn)于縣城的各個(gè)角落卻總是無(wú)法找到心靈的歸依,直至他決定以“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行走在大地上”。在行走的過(guò)程中,劉小飛認(rèn)識(shí)了形形色色的朋友,并在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神秘旖旎的自然風(fēng)景中與過(guò)往的自我和解,找尋到精神的依歸。《棣棠之約》中的戴南行、桑小軍、趙志平在20 世紀(jì)80 年代為理想主義所鼓舞,卻在“光輝歲月”流逝之后,惶惑于20 世紀(jì)90 年代的浪潮之中。他們?cè)?0 世紀(jì)80 年代熱情地討論詩(shī)歌,在月下酌酒,在大地漫游,然而,“20 世紀(jì)80 年代那種逢人談?wù)撛?shī)歌和文學(xué)的酒神精神正從山城上空悄然消退,所有人忽然集體轉(zhuǎn)向,拋棄了不久前的價(jià)值觀,轉(zhuǎn)向了一種新的價(jià)值觀,這個(gè)過(guò)程發(fā)生得如此之快之迅速,簡(jiǎn)直讓人措手不及。人們?cè)谝黄鹫務(wù)撟疃嗟脑?huà)題是怎么當(dāng)官和掙錢(qián),怎么炒股和下海”(孫頻:《棣棠之約》,《鐘山》2022 年第4 期)。20 世紀(jì)80 年代的理想主義在20 世紀(jì)90 年代全面潰敗,與理想主義同呼吸共命運(yùn)的知識(shí)分子陷入恐慌與焦慮的精神困境之中。趙志平?jīng)Q心隨波逐流以緩解痛苦,桑小軍以拒絕談?wù)撛?shī)歌的方式來(lái)反抗現(xiàn)實(shí),而戴南行則選擇以拒絕談?wù)撌浪住⒊撩韵笃搴汀兑捉?jīng)》的方式來(lái)衛(wèi)護(hù)理想主義。然而,遺忘并不意味著可以對(duì)現(xiàn)實(shí)視而不見(jiàn),抵抗亦不意味著能與世界相安無(wú)事。他們?cè)诔掷m(xù)的痛苦中抗拒,又在不斷的抗拒中痛苦。戴南行無(wú)疑是三人中痛苦最甚但也是真正從痛苦中解脫之人:他從早期具有表演性質(zhì)的漫游走向于天地間“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真正的漫游,從狹窄、局促的個(gè)人世界走向遼闊、深邃的宇宙空間。
孫頻的小說(shuō)一直試圖通過(guò)個(gè)人的命運(yùn)和時(shí)代的遭際來(lái)使小說(shuō)獲得歷史感和縱深感,試圖通過(guò)多維度的情感面向來(lái)消化時(shí)代記憶、彌合歷史創(chuàng)傷。如果說(shuō)在《河流的十二個(gè)月》中,孫頻嘗試將文學(xué)作為王開(kāi)利、李鳴玉、儲(chǔ)東山、張谷來(lái)精神自救的出路,那么在新近發(fā)表的小說(shuō)中,孫頻則將精神解放和自我救贖的路徑設(shè)置在更深邃的文明、更遼闊的天地之間。無(wú)論是頭頂?shù)脑鹿夂蜐M(mǎn)天星斗對(duì)劉小飛內(nèi)心創(chuàng)痛的撫慰,或是仰韶文化對(duì)楊聲約和劉靜空虛內(nèi)心的盈滿(mǎn),或是漫游于天地對(duì)戴南行心境的平和,孫頻都將精神自救的希望寄托于無(wú)有邊際、無(wú)所制約的自然宇宙和文化文明之中。如果說(shuō)《河流的十二個(gè)月》中王開(kāi)利的死以及其他三人的無(wú)動(dòng)于衷預(yù)告了寄情于文學(xué)的精神自救之路的無(wú)望,《我們騎鯨而去》中老周的失蹤、“我”復(fù)歸現(xiàn)代生活說(shuō)明了一切逃離都是失效的,那么《棣棠之約》《海邊魔術(shù)師》則以戴南行的精神自由、劉小飛的精神解放彰顯著永恒的自然時(shí)空對(duì)人的渡化:“無(wú)論走到哪里,白天都能看到太陽(yáng),晚上,在我的頭頂都有月光和滿(mǎn)天星斗。一萬(wàn)年前的月光和現(xiàn)在的月光是沒(méi)有任何差別的,這是我們內(nèi)心真正的安慰”(孫頻:《海邊魔術(shù)師》,《收獲》2022 年第1 期),“我坐在這河邊,看著河水,看著黑夜,數(shù)著星星,發(fā)現(xiàn)萬(wàn)物靜美,內(nèi)心里溫柔寧?kù)o,沒(méi)有一絲恐懼,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已經(jīng)無(wú)所謂得到和失去,現(xiàn)在任何人任何事都勉強(qiáng)不了我”(孫頻:《棣棠之約》,《鐘山》2022 年第4 期)。劉小飛和戴南行都與世俗社會(huì)格格不入,或是被迫之舉,或是主動(dòng)選擇,但他們都在無(wú)有邊際的自然時(shí)空中感受著有限生命的無(wú)限延展,領(lǐng)悟存在的真實(shí)與生命的真諦。自然對(duì)劉小飛來(lái)說(shuō),是眾生平等無(wú)所差距的存在,是理解所有并寬宥所有的存在。因而,劉小飛在感悟自然的過(guò)程中與自己達(dá)成了和解,劉小飛的父親也在尋找劉小飛的路途中諒解了他和自己。天地對(duì)戴南行來(lái)說(shuō),是詩(shī)的具體形態(tài),是一部完滿(mǎn)的詩(shī)集,是生命的棲息地,是靈魂的徜徉地。因而,戴南行在漫游天地的過(guò)程中領(lǐng)會(huì)了個(gè)體的有限和無(wú)限,參悟了生死的虛無(wú)與實(shí)際。誠(chéng)如孫頻自述,在遼闊的天地之中,“人會(huì)忽然被這來(lái)自宇宙間的巨大力量擊中,仿佛是觸摸到了一只巨獸的鼻息,蒼茫遼闊而溫柔,人會(huì)忽然覺(jué)得自己與腳下的那片落葉其實(shí)沒(méi)有多少區(qū)別。如此一來(lái),那些不甘、那些悲愴、那些屈辱,所有那些難以用言語(yǔ)表達(dá)的情感,竟都煙消云散了,心境里多了幾分澄明與豁達(dá),如月光皎皎,懸于心上”(孫頻:《物對(duì)人的渡化》,《北京文學(xué)(中篇小說(shuō)月報(bào))》2021 年第5 期)。
三、記憶的廢墟與懷舊的未來(lái)
瓦爾特·本雅明在《德國(guó)悲劇的起源》中認(rèn)為,“在廢墟中,歷史物質(zhì)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在這種偽裝之下,歷史呈現(xiàn)的與其說(shuō)是永久生命進(jìn)程的形式,毋寧說(shuō)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的形式”( [德]瓦爾特·本雅明:《德國(guó)悲劇的起源》,陳永國(guó)譯,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1 年版)。也就是說(shuō),廢墟不只是荒廢的場(chǎng)域,而是承載著歷史記憶和時(shí)代印記的載體。廢墟是一種歷史的空間,這些廢墟并非只是象征過(guò)往的一曲挽歌,而是歷史與現(xiàn)時(shí)的“靜止的辯證”的形象;它們顯示了歷史與現(xiàn)時(shí)的共處狀態(tài)以及未來(lái)潛能的多樣性。廢墟的寓言性即在于它所彰顯的歷史內(nèi)容和未來(lái)指向,它蘊(yùn)含著荒涼、頹唐的美感,同時(shí)也蘊(yùn)涵著新生與未來(lái)。
在孫頻的小說(shuō)中,廢墟之義并不只局限在具體事物的崩潰之上,還包含人物精神的荒蕪。一方面,“廢墟”指涉實(shí)體的潰敗。在《天空之城》中,紡織廠(chǎng)是一個(gè)由五湖四海的異鄉(xiāng)人組成的空間,它沒(méi)有歷史更沒(méi)有文化積淀,猶如天外來(lái)物一般降落在千年古城里,其后,紡織廠(chǎng)因?yàn)樯虡I(yè)開(kāi)發(fā)而成為坍塌的廢墟。由熱鬧擁雜的工廠(chǎng)變?yōu)樘艿膹U墟,由人聲鼎沸到人煙稀少,“紡織廠(chǎng)如經(jīng)歷戰(zhàn)爭(zhēng)一般徹底成為一片廢墟”,“燈火寒涼,危樓幢幢,廢墟的效果更加立體逼真,這讓我們感覺(jué)自己已經(jīng)不屬于人類(lèi)社會(huì)了”
(孫頻:《天空之城》,《十月》2022 年第4 期)。與曾經(jīng)繁榮的紡紗工廠(chǎng)相比,坍圮的廢墟百?gòu)U待興,而原屬于紡紗廠(chǎng)的工業(yè)榮譽(yù)則變得黯淡無(wú)光。在這個(gè)意義上,“廢墟”指涉實(shí)體的衰敗與沒(méi)落。另一方面,“廢墟”指認(rèn)的是精神的荒蕪與失落。在《海邊魔術(shù)師》中,偷盜行竊成為劉小飛的精神暗疾,也成為劉小飛生命的枷鎖。《棣棠之約》中隨著20 世紀(jì)80 年代理想主義的消失,曾對(duì)文學(xué)抱有全部熱情的趙志平、桑小軍、戴南行陷入了人文精神失落的精神危機(jī)之中。在這個(gè)層面上,“廢墟”指涉的是精神上的失落或心靈上的空虛。
在本雅明看來(lái),廢墟具有寓言性,這體現(xiàn)在不注重形象與感知整體性的表達(dá),而是從整體的碎片和裂縫中發(fā)現(xiàn)其背后所指涉的意義,從而發(fā)現(xiàn)新生的力量。廢墟“不是通過(guò)可見(jiàn)可觸的建筑殘骸來(lái)引發(fā)觀者心靈或情感的激蕩:在這里,凝結(jié)著歷史記憶的不是荒廢的建筑,而是一個(gè)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現(xiàn)場(chǎng)’”([美]巫鴻:《廢墟的故事:中國(guó)美術(shù)和視覺(jué)文化中的“在場(chǎng)”與“缺席”》,肖鐵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天空之城》中所謂“天空之城”是指紡織工廠(chǎng),它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jìn)程中建立,又在商業(yè)開(kāi)發(fā)浪潮中成為坍圮的廢墟、再起的高樓。從紡織廠(chǎng)的新生——廢墟——新生的過(guò)程中,可以看到城市化、工業(yè)化、商業(yè)化的社會(huì)印記,也能看到企業(yè)改制、下崗潮的時(shí)代記憶。盡管孫頻也對(duì)“天空之城”的消失感到惋惜,但她沒(méi)有因而陷入哀傷與絕望之中,她借劉靜之口表達(dá)自己對(duì)“廢墟”的認(rèn)知:“萬(wàn)事萬(wàn)物都各有使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是一種榮耀,這座紡織廠(chǎng)也不是沒(méi)落了,它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到底還是榮耀的。”(孫頻:《天空之城》,《十月》2022 年第4 期)也就是說(shuō),盡管紡織廠(chǎng)成為衰落的象征,盡管紡織廠(chǎng)的廢墟上已經(jīng)建起樓房和商業(yè)街,但其所承載的集體記憶和個(gè)人記憶并沒(méi)有因此而消失在歷史語(yǔ)境之中,紡織廠(chǎng)也沒(méi)有因?yàn)槌蔀閺U墟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相反,歷史的故事都成了它的“前史”,并孕育了新生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孫頻新近發(fā)表的小說(shuō)流露出對(duì)理想主義、理想時(shí)代的重返意識(shí)以及對(duì)已逝去的文明文化的懷舊意味。如《海邊魔術(shù)師》中劉小飛選擇復(fù)歸游牧民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給劉小飛帶來(lái)了精神的解放;《天空之城》中劉靜被偶然發(fā)現(xiàn)的仰韶文化廢墟所震撼并沉迷于歷史研究之中;《棣棠之約》中戴南行、桑小軍、趙志平三人一直深切緬懷著熱烈而激蕩的20 世紀(jì)80年代,甚至于戴南行一直以自我實(shí)踐著20世紀(jì)80 年代的酒神精神和理想主義。在斯維特蘭娜·博伊姆看來(lái),“初看上去,懷舊是對(duì)某一個(gè)地方的懷想,但是實(shí)際上是對(duì)一個(gè)不同的時(shí)代的懷想……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懷舊是對(duì)于現(xiàn)代的時(shí)間概念、歷史和進(jìn)步的時(shí)間概念的叛逆。懷舊意欲抹掉歷史,把歷史變成私人的或者集體的神話(huà),像訪(fǎng)問(wèn)空間那樣訪(fǎng)問(wèn)時(shí)間,拒絕臣服于折磨著人類(lèi)境遇的時(shí)間之不可逆轉(zhuǎn)性”([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懷舊的未來(lái)》,楊德友譯,譯林出版社2010 年版)。可見(jiàn),懷舊所處理的是個(gè)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guān)系,涉及的是歷史的不可返回、現(xiàn)時(shí)的無(wú)可把握以及個(gè)體的有限性。
孫頻作為一個(gè)對(duì)創(chuàng)作有清醒認(rèn)知和對(duì)歷史有相當(dāng)思考的作家,她并沒(méi)有讓小說(shuō)中的人物沉溺于懷舊的感傷中,沒(méi)有讓他們沉浸在虛幻的個(gè)人神話(huà)之中,沒(méi)有讓他們被情感所羈絆、被想象的浪漫所糾葛,而是讓他們對(duì)“光輝歲月”的懷想成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和未來(lái)的指引。因而,《棣棠之約》中曾痛苦于人文精神失落的戴南行領(lǐng)悟到20 世紀(jì)80 年代的理想主義并沒(méi)有消失,而是存在于心靈的深處:“我原來(lái)以為20 世紀(jì)80 年代的酒神精神和理想主義到了20 世紀(jì)90 年代以后就徹底消失了,為此經(jīng)常懷念那個(gè)時(shí)代,后來(lái)我想明白了,它們其實(shí)并沒(méi)有消失,只是由陽(yáng)而陰了,只要時(shí)光不滅,人類(lèi)一息尚存,它們就還會(huì)由陰而陽(yáng)。”(孫頻:《棣棠之約》,《鐘山》2022 年第4 期)孫頻對(duì)理想主義的“重返”以及對(duì)“重返”局限的思考可以看作是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所認(rèn)為的“反思型懷舊”:“反思型的懷舊更多地涉及歷史的與個(gè)人的時(shí)間、過(guò)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靜態(tài)。在這里,焦點(diǎn)不在于再現(xiàn)所感受到的絕對(duì)真理,而在于對(duì)歷史和時(shí)間逝去的思考。”([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懷舊的未來(lái)》,楊德友譯,譯林出版社2010 年版)對(duì)于修復(fù)型懷舊而言,過(guò)去應(yīng)該是被完整還原的,而不應(yīng)該顯露出衰敗頹唐的跡象。反思型懷舊則更注重對(duì)集體記憶、歷史逝去的思考。在孫頻的小說(shuō)中,反思型懷舊存在于對(duì)往日家園的幻想之中,與此同時(shí),她又在廢墟之上嘗試通過(guò)日常瑣事的歷史來(lái)再現(xiàn)凝固的時(shí)代記憶、把握所處的時(shí)代。孫頻不僅對(duì)歷史記憶和時(shí)代痛感進(jìn)行著反思,也對(duì)小說(shuō)的思想進(jìn)行著或深刻或革新的表達(dá)。
孫頻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的作家,她以“抵抗遺忘”的方式切實(shí)而誠(chéng)摯地書(shū)寫(xiě)著時(shí)代記憶和記憶中的痛感,同時(shí),她又不斷以純熟的寫(xiě)作技法講述著個(gè)體迥異的故事。無(wú)論是《海邊魔術(shù)師》還是《天空之城》或是《棣棠之約》,盡管小說(shuō)中的疼痛感仍然存在,但孫頻都在有意打破以往“生猛酷烈”的敘事慣性,代之以更為從容、更為輕盈的敘事風(fēng)格。孫頻正通過(guò)新的故事和敘事風(fēng)格,探索小說(shuō)的文體結(jié)構(gòu),豐富小說(shuō)的思想內(nèi)涵,但究其根本,孫頻一直在意的仍是人的生命與枷鎖、艱難與自由,這是她對(duì)心靈荒寒但生命炙熱之人的愛(ài)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