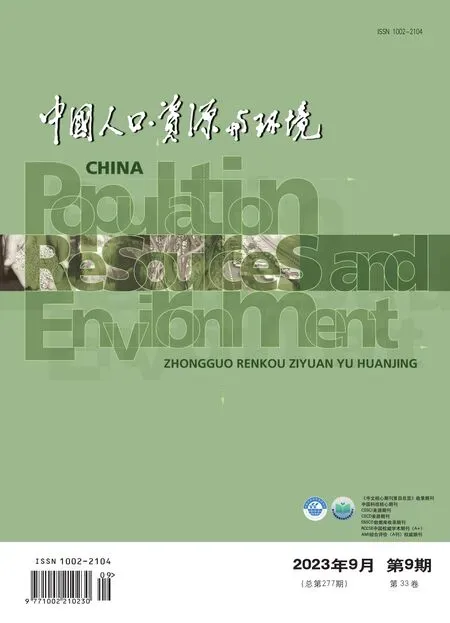城市群多中心發展的碳減排效應及其作用機制
方丹 楊謹 陳紹晴









摘要 城市群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區域,明確影響城市群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推動城市群低碳建設關乎中國“雙碳”目標的實現。作為城市規劃的重要因素——城市群空間結構,其對碳排放的影響尚不明晰。該研究首先利用夜間燈光數據,首次實現對“十四五”規劃中全國19個城市群空間結構的長期評價。在此基礎上,構造2000—2020年城市群面板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實證探究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并識別檢驗其內部作用機制。結果表明:①2000年以來,中國19個城市群的空間結構多中心性增強,沿海城市群尤為明顯。②與單中心空間結構相比,城市群多中心發展更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③多中心空間結構的減排影響部分通過促進產業分工實現,交通基礎設施對空間結構的碳排放影響具有調節作用,市場一體化與多中心發展之間具有替代效應。因此,本研究認為推進構建多中心城市群有助于實現減碳和發展的雙贏。但就目前部分城市群的單中心尚未發育成熟的基本情況,多中心不應成為一刀切的減碳策略,更需重視城市功能定位、優化基礎設施建設并打破市場分割,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由市場引導多中心結構的形成,從而推進城市群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城市群空間結構;多中心發展;夜間燈光數據;碳排放;產業分工
中圖分類號 F061. 5;K902;X32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3)09-0045-14 DOI:10. 12062/cpre20230102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城市群已然成為國家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區、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核心區與碳中和的責任區[1]。有數據表明,全國19個城市群雖僅占國土面積的29. 12%,卻貢獻了全國80. 05%的經濟總量和71. 7%的碳排放[2-3]。日益嚴峻的氣候危機之下,亟須明確影響城市群碳排放的因素、合理規劃并落實措施以建設低碳城市群[4-5]。其中,隨著特大城市數量的增多以及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部分城市群空間結構由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6-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在城鎮化戰略中提出“優化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構筑生態和安全屏障,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空間結構兩類模式反映了資源、要素以及社會經濟活動在城市間的分布與組合狀態[8],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績效表現。在已有研究中,多中心發展被視為提高經濟效率、緩解城市病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策略[9]。然而城市群空間結構是否會對碳排放產生影響?多中心發展是否更具碳減排效應?其影響機制是什么?應如何引導形成合理的空間結構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綠色低碳發展的雙贏?對上述問題的探究,有助于從城市群空間規劃角度為減少碳排放提供政策建議、為應對氣候環境挑戰提供參考。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1. 1 文獻綜述
該研究的多中心發展即是指區域發展所形成的多中心空間結構,反之,單中心發展即為單中心空間結構。空間結構的界定依賴于地域尺度,該研究關注中觀尺度:城市群空間結構,即城市群空間范圍內要素在不同城市之間分布所形成的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態[10]。從人口分布上看,如果一城獨大,城市等級體系明顯,意味著該城市群空間結構越趨向單中心;反之,如果城市群內人口大規模集聚的城市數量越多,核心城市越多,空間結構越趨向多中心。依據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發展初期,區域必須形成要素的空間集聚,作為增長極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因而呈現單中心空間結構;隨著后期主導產業的轉變和集聚成本的提高,要素會在區域內部重新分配,可能形成多中心空間結構。城市群空間結構從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其本質是企業、勞動力等在城市間進行區位選擇,次中心城市變得更有吸引力,從而形成了跨越城市地理邊界的多中心集聚現象。
學界關于區域空間結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測度方法、演變機制和績效評價三個方面。其中,區域空間結構的測度包括形態和功能兩個維度[11]。形態多中心是最直觀的空間結構反映形式,例如黃妍妮等[6]使用市轄區人口指標衡量城市規模,基于帕累托指數、位序規模法和四城市指數測度2007—2014 年中國十大城市群的空間結構,發現東部沿海城市群向多中心演變;而功能多中心則強調城市間不同功能“流”的分布情況,例如姚常成[12]借助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的合作論文數量評價2000—2016年中國八大城市群的空間結構,結果發現城市群功能多中心的轉變趨勢開始顯現。基于區域空間結構的測度,學者們對空間結構的演變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孫斌棟等[7]認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規模的增加導致了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多中心化;姚常成等[13]認為中國城市群向多中心演進是市場驅動的產物,而市場驅動與政府政策引導緊密相關。
隨著城市發展過程中各類矛盾與問題的涌出,城市規劃的重要引領作用得以彰顯,進一步地,學者們開始思考區域空間結構的績效影響。其中經濟績效得到了較多關注,張浩然等[8]基于2000—2009年中國十大城市群數據發現城市群單中心空間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于斌斌等[14]選取20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多中心空間結構更能有效地提升經濟效率;姚常成等[15]證實知識多中心空間結構能夠促進城市群的協調發展。關于區域空間結構的環境影響評價,雖然學者們的討論已廣泛涉及工業煙塵排放[16]、霧霾污染[17-18]、二氧化碳排放[19]和能源效率[20]等,但研究范圍多限于城市或省份尺度。例如,Zhu等[21]基于中國城市數據發現蔓延、多中心的城市碳排放水平更低;Chen等[22]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發現多中心空間結構與碳排放存在著U型關系;而范秋芳等[23]發現省際單中心指數的提升有助于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長。受碳排放數據統計不完全的限制,城市群層面空間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探究相關文獻較少,Liu等[24]對山東半島城市群的研究發現空間結構對二氧化碳排放沒有顯著影響;Wang 等[25]以2005—2019年中國六個城市群為樣本,利用時空地理加權回歸分析城市群空間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細化了區域異質性與時變特征。
綜上:①現有關于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研究較少,尚無定論,該問題主要源于碳排放數據的限制以及城市群研究對象選取的顯著差異。②學界更多探討了空間結構的績效表現,即關系評價,但較少探索其內部影響機制。由于空間結構是市場驅動的產物,亟須探索其內部影響機制,以引導更優空間結構的形成,獲得潛在效益。基于此,文章貢獻主要在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研究對象選取上,以“十三五”“十四五”規劃的全國19個城市群為樣本,借助衛星遙感及各類城市經濟數據,解決城市群層面數據缺失問題,從而探究城市群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二是在空間結構測度上,借助世界上第一套1984—2020年中國的人工夜間燈光數據集(PANDA)[26],對2000—2020年中國19個城市群空間結構進行測度與評價,充分考察城市群空間結構的空間分布差異與動態演變;三是在研究視角上,將空間結構和碳排放納入一個研究框架,借助產業分工、交通基礎設施和市場一體化等概念深入分析城市群多中心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及其內部作用機制。該研究可為城鎮化布局、氣候變化應對提供數據支撐與政策新思路,促進可持續發展。
1. 2 研究假說
單中心和多中心發展的本質差異體現在空間發展策略上所選擇的不同的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態。因此,該研究將從集聚經濟理論出發闡述二者的績效差異。傳統的集聚經濟理論認為,要素的空間集中可以實現成本節約和效率提升,推動經濟增長[27-28];但過度集中也會帶來擁擠、污染等負外部性[29]。早期理論將集聚經濟局限于“單體城市”的地理邊界,并沒有區分單中心集聚和多中心集聚的差異性影響。隨著城市規模擴大以及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間聯系更加緊密,1973年Alonso[30]提出“借用規模”假說,指小城市可以“借用”其鄰近大城市的集聚經濟益處,同時避免集聚的負外部性影響,從而闡述了多中心空間結構相比單中心空間結構可以使區域內部整體的經濟效率得到顯著改善。Capello[31]提出了“城市網絡外部性”概念,突破了傳統的距離限制,指彼此遠離的城市也可以通過發達的交通、信息等功能網絡實現合作與共贏[32]。而城市群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正體現了更加緊密的城市間功能聯系[11],有助于城市間產生跨越地理邊界的網絡外部性[33],提升經濟效率。
與要素集聚的經濟效應類似,眾多研究探討了具有地理邊界的單中心集聚的環境影響,其通常具有雙重效應:產出規模擴張的負外部性和規模經濟、技術進步的正外部性。陸銘等[34]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發現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具有規模經濟效應,有助于降低工業污染強度;楊仁發[35]進行省級面板門檻回歸發現產業集聚在高于門檻值時有利于改善環境污染;邵帥等[36]檢驗了經濟集聚與碳排放強度之間存在倒“N”型曲線關系。綜合來看,單中心集聚達到一定水平后,才符合低碳城市的建設要求。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影響可能與單中心不同,一方面多中心空間結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過度聚集、擁擠效應,減少效率損失;另一方面城市群內部中小城市可以“借用”大城市的集聚效應;與此同時,城市在密切聯系中形成明確的功能分工、共享經濟成果,從而避免同質性功能的冗余建設。因此,在城市群層面,多中心空間結構可能有助于提高區域整體的經濟效率,實現要素的合理配置,從而帶來環境績效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1:作為經濟集聚的不同空間模式,城市群空間結構會對二氧化碳排放產生影響。其中,多中心發展呈現出更少的碳排放,碳排放強度更低。
城市群多中心空間結構減少碳排放的機制是什么?實際上,集聚與分工具有密切的關聯性,分工是促進集聚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集聚的形成又會推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37]。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最初將形成制造業“中心”和農業“外圍”的空間結構[38];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區域開放度加深和貿易成本的進一步下降,將會演變成服務業“中心”和制造業“外圍”的空間結構[39],進而呈現出“中心城市主要承擔管理和研發功能、外圍城市主要承擔制造和加工功能”的功能分工格局[40]。城市產業分工有助于各地區依據自身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從而節約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提高整體的經濟效率與能源效率。王桂新等[41]基于城市面板數據發現產業集聚具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降低碳排放的作用;韓峰等[42]證實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具有城市碳減排效應;王靖[43]發現制造業集聚雖然使本地碳排放量顯著增加,但顯著降低了鄰近空間單元的碳排放水平。因此城市群空間結構可能會通過產業分工渠道對碳排放產生影響。
假說2:產業分工在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過程中具有中介效應。即城市群多中心空間結構促進了城市群內部生產性服務業在中心城市集聚,制造業在外圍城市集聚,各城市分工、專業化生產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城市群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受到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一體化兩方面的重要影響,上述兩個因素可能會調節城市群多中心的碳減排效應。首先,運輸成本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集聚與分散起到關鍵性作用。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會直接對傳統的區域空間距離產生沖擊,大幅降低運輸成本與時間可能引發產業重新布局并促進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從而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的降低。此外,城市群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區域,需要破除城市之間長期存在的市場分割問題。一方面,由于中國財政分權和晉升激勵等制度因素,地方保護行為造成的市場分割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效率,產業同構、重復建設、資源錯配等問題加劇了環境污染[44-45];另一方面,市場一體化是產業分工、地區專業化的前提條件,影響運輸成本,從而成為塑造空間結構的重要因素。而多中心城市群空間結構又會反過來促進城市間的市場整合,形成一體化發展。因此,城市群空間結構可能與市場一體化存在交互效應,對碳排放產生影響。從而提出:
假說3: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對城市群空間結構的碳排放影響具有調節效應;城市群空間結構與市場一體化之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甚至是替代效應,即對于市場分割嚴重的地區,多中心空間結構有助于突破高碳排困境;對于單中心空間結構,促進市場一體化也能實現環境績效的改善。
綜上,該研究將構建中國城市群面板數據,對上述三條假說逐一進行實證檢驗,明確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以及潛在的影響機制。
2 研究設計
2. 1 核心變量說明
2. 1. 1 被解釋變量
城市群碳排放強度。不同城市群在面積、人口上存在巨大差別,且中國自“十二五”開始,將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幅度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因此文章使用標準化指標:碳排放強度EI 作為被解釋變量,即城市群單位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通過比較清華大學中國多尺度排放清單模型MEIC、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化石燃料數據同化系統FFDAS、中國高空間分辨率網格數據CHRED以及全球大氣研究排放數據庫EDGAR等國際碳排放數據庫,僅有EDGAR可提取長時間序列中國各城市碳排放清單,因此該研究從EDGAR(https://edgar.jrc.ec.europa.eu/)獲得了最新的2000—2020年中國城市和城市群二氧化碳排放面板數據,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收集了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以2020年為基期進行價格調整從而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合成碳排放強度指標。
2. 1. 2 核心解釋變量
城市群空間結構。該研究基于城市經濟學中經典的位序規模法,借助夜間燈光數據測度城市經濟活動人口數量,從形態維度構建空間結構指數spatial,評價城市群空間結構。由于功能多中心測度方法受到數據獲取的限制,該研究擬從人口、就業或經濟在中心城市的集中程度,即形態維度,實現城市群空間結構的長期測度與評價。以往研究通常采用人口指標衡量城市規模大小,但是對于跨行政區劃的城市群而言,人口統計指標的缺失和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均會導致空間結構測度的準確性降低;且難以完全揭示產業地理分布、經濟發展水平等信息。夜間燈光數據已被證實是地區經濟活動的良好替代指標[46-49],該研究采用了發表在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http://data.tpdc.ac.cn/home)的世界上第一套中國長時間序列逐年人造夜間燈光數據集(1984—2020年)[26],借助ArcGIS軟件提取2000—2020年中國各城市的夜間燈光柵格數據,對比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數據,結果表明使用城市燈光亮度總值代替常住人口指標表征城市規模具有合理性。城市群空間結構測度公式如下:
其中:Lightijt 是第t 年i 城市群中的城市j 的夜間燈光亮度總值;C 為常數;Rankijt 代表第t 年城市j 的燈光亮度在城市群i 內的排序;分別對每一年各個城市群內的城市燈光亮度進行由大到小的排序之后,進行公式(1)的回歸,可以得到系數qit。qit 越大,城市規模與城市等級間的回歸線越陡峭,核心城市越突出,城市群服從單中心空間結構;qit 越小,回歸線斜率越平坦,人口分布較為分散,呈現多中心空間結構。需要強調的是,由于不同城市群內的城市數量不同,為使空間結構指數在不同城市群間具有可比性,遵循Meijers等[50]的做法,將城市群內排名前二位、前三位以及前四位的城市分別進行式(1)回歸,將三個回歸得到的指數qit 取平均即得到城市群的空間結構指數,將其命名為spatialit,該指數越大越體現單中心結構。
2. 1. 3 中介與調節變量
根據前述影響機制分析,該研究將構建產業分工中介變量、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一體化調節變量分析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機制。
首先,構建了兩類、三個產業分工指標:產業結構相似度、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非中心城市制造業專業化指數。城市群內部城市之間的區域分工深化,即表現為產業結構、行業就業結構的差異化;反之產業結構越相似越意味著產業的重復布局。產業結構相似度能夠從城市群整體層面測度分工情況,其計算如式(2):
其中:i 代表城市群,由m 個城市組成,j 代表城市,k 代表行業,k=1,2,…,n。Rjk 為j 城市k 行業的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Rk 為城市群i 中所有城市k 行業的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比重的均值。產業結構相似度divisioni的取值區間為[0,1],產業結構相似指數越小,表明城市群內城市之間的產業結構越互補,產業分工水平越高。
另外參考齊謳歌等[51]使用城市功能專業化指數來區分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專業化特征。將產業歸類為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兩類,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金融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業和軟件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制造業包括采掘業、制造業、電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在城市群功能分工模式下,中心城市集聚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則表現為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占比上升的過程,計算如式(3);非中心城市集中發展制造業,則表現為制造業占比上升的過程,計算如式(4):
其中:Lcs 代表中心城市c 中從事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人數,Lcm 表示中心城市c 中從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Lns 代表非中心城市n 中從事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人數,Lnm 表示非中心城市n 中從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LTS 和LTM 代表城市群i 的生產性服務業就業人數和制造業就業人數。指標divic 的大小反映了城市群i 中心城市c 中生產性服務業占比的相對值,與產業分工程度呈正相關;指標divin 的大小反映了城市群i 非中心城市n 中制造業占比的相對值,與產業分工程度呈正相關。從而通過三個指標divisioni、divic 和divin 從城市群總體、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視角測度城市群的產業分工水平。其中選取城市群中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為中心城市,其余為非中心城市;細分產業的就業數據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關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一體化兩個調節變量,該研究用單位土地面積的公路與鐵路里程之和(km/km2)表示交通基礎設施水平trans,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EPS數據平臺和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另外參考劉修巖等[52]提出的中國城市群一體化水平評價體系,從經濟一體化方面即經濟發展差距的視角測度一體化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越大,經濟一體化的水平越低。計算城市群內部城市人均GDP 的標準差,標準差是經濟一體化的逆向指標,取標準差的倒數即生成市場一體化指數integ,該指標數值越大說明市場一體化水平越高。人均GDP 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2. 1. 4 其他控制變量
根據相關文獻中對碳排放影響的研究經驗,控制了人口規模、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技術創新變量。該研究選擇常住人口作為人口規模指標pop;產業結構包括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second 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third 兩個指標;外商直接投資fdi,采用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GDP 的比重,實際使用外資額已通過美元年均匯率進行調整;技術創新patent,選取地區人均專利授權量的對數項。城市群層面指標均由內部城市數據加總合成。
2. 2 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城市群空間結構與碳排放之間的因果關系,設定公式(5)所示計量模型,借助中國19個城市群的面板數據驗證假說1:
2. 3 數據來源
該研究選取2000—2020年的城市數據,構建城市群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十三五”及“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指出全國共布局19個國家級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山東半島、粵閩浙沿海、中原、關中平原、北部灣、哈長、遼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蘭州—西寧、寧夏沿黃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因此以這19個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探究城市群多中心發展是否存在碳減排效應。碳排放數據來源于全球大氣研究排放數據庫,夜間燈光數據用于測度城市群空間結構,來自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產值、行業就業人數、外商直接投資、交通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常住人口數據來自于各省市統計局和City‐Population數據庫,各城市專利授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國家統計局提供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數據。部分缺失值數據參考EPS數據平臺、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進行補充,其他進行插值處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3 實證結果
3. 1 城市群空間結構和碳排放強度
表2對比展示了2000和2020年19個城市群的空間結構指數以及中心城市分布情況。其中空間結構指數最小值為0. 08,最大值為1. 21,均值為0. 56,取值越大,說明該城市群空間結構越呈現單中心。從結果可知,在2000年,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指數多數大于平均值,大多呈現單中心空間結構,而沿海城市群的單中心程度比內陸城市群低,山東半島城市群是唯一一個具有明顯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城市群。2000—2020年,全國有13個城市群空間結構的單中心經濟集聚現象有所減弱,其中長三角城市群最為明顯,蘇州、杭州、寧波規模迅速擴張,導致空間結構指數從0. 71降至0. 26,呈現多中心發展態勢。總體來看,全國沿海地區呈現出更多的多中心發展格局,例如珠三角城市群的廣深兩極,泉州、溫州等非省會城市在粵閩浙沿海城市群發揮經濟帶動作用,這可能與港口城市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有兩個典型的雙核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與哈長城市群,始終堅持沈陽—大連、哈爾濱—長春的戰略地位。中西部地區由于發展落后,中心城市較少,主要呈現單中心空間結構。例如天山北坡城市群以烏魯木齊為主,蘭州西寧城市群的中心是蘭州,呼包鄂榆城市群以呼和浩特為中心,滇中城市群的發展主要聚集在昆明。成渝城市群是中西部崛起的重要樞紐,雙核之間的差距有些許拉大,與目前規劃目標存在差異。
從城市群二氧化碳數據可知,各城市群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在2000—2010年間快速增長,2011年后碳排放增速放緩,2020年全國排放總量113. 55億t,19個城市群的碳排放占全國總排放量的80. 29%;而碳排放強度在2000—2007年間呈上升趨勢,隨后逐步平穩下降,至2020年已下降54. 23%,取得初步減排成效。圖1展示了2020年各城市群碳排放總量和強度,2020年19個城市群的碳排放強度均值為1. 12 t/萬元,每萬元產值比非城市群地區少排放二氧化碳0. 38 t,可見城市群發展具有規模經濟特征,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城市群碳排放表現存在空間異質性。雖然沿海地區城市群排放總量大,但除遼中南以外的沿海城市群碳排放強度普遍較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作為經濟最為開放的城市群,碳排放強度最低僅為0. 35 t/萬元。碳排放強度高的主要是遼中南、寧夏沿黃、天山北坡、呼包鄂榆和蘭州西寧等中西部城市群。相關系數表明城市群空間結構與碳排放強度呈現正相關關系,即單中心空間結構導致的碳排放強度越高。
3. 2 基準回歸結果
在進行基準回歸前,面板單位根檢驗拒絕了“偽回歸”的存在,綜合LM檢驗、F檢驗和Hausman檢驗證實了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合理性,VIF檢驗說明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存在。表3展示了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影響的檢驗結果,列(1)為混合回歸,采用聚類穩健標準誤,列(2)—列(7)逐步控制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并加入控制變量。無論哪種模型設定,空間結構指數的回歸系數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即單中心空間結構的碳排放強度更高,城市群多中心發展有助于扭轉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假說1成立。列(7)結果表明空間結構指數的系數為0. 182,即空間結構指數每減少1%,將導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低0. 182%;根據2020年的數據統計,將減少全年0. 21億t二氧化碳排放。
由于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模式差異顯著,城市群多中心發展的碳減排效應也可能存在空間異質性。該研究以秦嶺淮河為界劃分北方和南方城市群,根據是否沿海將樣本劃分為沿海和內陸城市群,表4展示了異質性分析的結果。由結果可知,南北方城市群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印證基準回歸結果,多中心發展模式具有碳減排效應;而這種碳減排效應在北方地區更大,這可能與北方城市群內較弱的城市間聯系相關,除京津冀城市群以外,北方其他城市高鐵網絡布局進程較慢,貿易聯系弱,各自為營的發展模式向多中心轉變有助于大幅提升環境績效。根據沿海、內陸標準劃分城市群,能夠體現差異性影響,沿海地區城市群空間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不顯著,而內陸地區的系數顯著為正(0. 269***),即采取多中心發展模式能夠有效降低中西部碳排放,中西部地區更需將城市群空間規劃提到重要地位。
3. 3 穩健性檢驗
3. 3. 1 工具變量法
該研究使用工具變量法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構建工具變量時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測度人口在城市間的規模分布,二是如何體現人口分布隨時間的變化。針對問題一,Bosker等[54]發現自然地理特征和是否鄰近水源是歐洲城市形成與規模分布的重要影響因素;Wang 等[55]基于中國歷史數據證明人類文明沿河而生,擇水而居的人口分布規律至今尚未顯著改變;Burchfiled[56]等從地表起伏度層面證明了地理環境對人口密度的重要影響,因此將河流密度和地表粗糙度兩種外生的自然地理變量作為空間結構的第一類工具變量。但是由于自然地理變量不隨時間變化,需要尋找一個外生的時變變量與之相結合,解決問題二。劉修巖等[57]對中國的研究證實了對外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會放大大城市的優勢,促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李威等[58]發現區域內城市間的運輸水平會調節國際貿易對城市規模的影響,在運輸成本低的區域,對外貿易開放反而會令城市規模分布趨于分散。因此綜合考慮內外貿易因素,參考劉修巖等[10]選擇匯率作為外貿開放指標,選取區域貨運量占比作為內貿開放指標,測度運輸成本,用兩個貿易開放指標構建第二類工具變量。然后構造自然地理工具變量與貿易開放工具變量的乘積項,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
綜上,區域內的河流密度越大,越有助于多個中心城市的形成;地表粗糙度越大,越起伏,越容易在小規模內集中,形成單中心;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越高,本幣貶值,越促進出口,形成單中心;內貿貨運量大,運輸及倉儲成本低,越易調節外貿影響,促進國內廠商布局,形成多中心。因此可構建四種工具變量,為保持變量影響的一致性,其中兩個工具變量為河流密度與匯率倒數的乘積、河流密度與匯率倒數、城市群貨運量占比的三項乘積,數值越大越促進多中心發展,與空間結構指數呈負相關。另外兩個工具變量為地表粗糙度與匯率的乘積、地表粗糙度與匯率、貨運量占比的倒數的三項乘積,數值越大越促進單中心發展,與空間結構指數呈正相關。其中,河流密度數據根據國家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1∶400萬河流矢量分布圖提取,河流密度=河流長度/區域面積;地表粗糙度數據源自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V003 高程數據,用城市群內城市高程的標準差表示;匯率、貨運量數據分別來自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相關系數檢驗證實了工具變量的相關性,系數符號與預期一致;Hausman 檢驗拒絕“所有解釋變量均為外生”的原假設,即應該使用工具變量法,同時沃爾德檢驗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回歸結果見表5,空間結構指數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證實了空間結構與碳排放的因果關系,多中心空間結構導致碳排放強度的降低。
3. 3. 2 替換空間結構指標
該研究構想三種方式替換空間結構指標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空間結構指數spatial 的滯后項、變換的首位度指數primacy 和四城市指數s4。滯后項可以部分消除潛在的內生性;變換的首位度指數primacy 即1減去規模最大城市占城市群總規模比重,取值范圍為(0,1),指數越大,越表明空間結構趨向多中心,與空間結構指數成反比;四城市指數為第一大規模城市規模與二、三、四大城市規模之和的比重,該指標越大說明第一中心城市規模突出,與空間結構指數成正比。結果見表6:列(1)—列(3):對比展示了使用空間結構指數及其滯后一項和滯后二項的結果,回歸系數數值雖有所下降,但始終為正且具有較高的顯著性;這證實了空間結構多中心對碳排放強度的優化作用,其影響效果隨時間有所衰減。列(4)中變換的首位度指數與空間結構指數負相關,其回歸結果顯著為負,列(5)中四城市指數顯著為正,與預期一致,再次證實了城市群空間結構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城市群多中心發展有助于加強集聚外部性與網絡外部性,帶來環境效益的提升,減少碳排放。
3. 3. 3 區分城市群成員城市
將城市群空間結構指數作為關鍵解釋變量,成員城市的碳排放強度作為被解釋變量,通過區分城市群成員城市,一方面擴大樣本量以實現估計的一致性,驗證結果的穩健性,另一方面深究細化城市群空間結構對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碳排放強度的異質性影響。結果見表7,樣本量擴大至3 734個,涉及206個城市21年的數據,控制變量與上文一致。空間結構指數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與城市群層面一致,即無論是在城市群層面還是子樣本成員城市層面,城市群的多中心空間結構均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根據是否為中心城市進行子樣本分析,結果表明多中心空間結構對非中心城市的減排效果更好,體現了多中心發展戰略對邊緣城市的溢出效應。
3. 4 影響機制分析
3. 4. 1 產業分工的中介效應
為檢驗城市群空間結構是否通過產業分工渠道對碳排放產生影響,即假說2,構建中介效應模型(5)—模型(7),分別代入產業結構相似度divisioni、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divic 和非中心城市制造業專業化divin 三個產業分工指標,進行產業分工中介效應檢驗。上述三個指標互為補充,共同解釋了城市群的產業分工水平,即產業結構相似度越小、非中心城市制造業專業化指數和中心城市服務業專業化指數越高,則產業分工水平越高。列(1)、列(3)和列(5)展示了空間結構對產業分工的影響,系數分別顯著為正、顯著為負和不顯著,這說明空間結構指數越大,空間結構越呈現單中心,城市群內產業結構越相似,越不利于外圍城市的制造業專業化;反之,多中心空間結構有助于實現城市間產業結構差異化,尤其是在外圍城市形成制造業產業集聚,即產業分工,但是對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不顯著;這與預期較為一致,多中心形成、經濟集聚的過程體現了城市間產業分工情況。列(2)、列(4)和列(6)為加入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三個產業分工指標的系數表明產業結構相似會造成更高的碳排放強度;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產業專業化有助于碳減排,但服務業專業化的作用并不顯著。在控制中介變量后,空間結構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但系數有所下降。進一步Sobel檢驗表明產業結構相似度和外圍制造業專業化是城市群空間結構與二氧化碳排放關系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與總效應的比值分別為0. 150和0. 200,即存在城市群多中心→產業分工→碳排放強度降低的傳導機制。結果表明,只有當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在同類型產業上實現集聚與專業化生產,尤其是外圍城市主攻制造業生產,形成城市間相互聯系的分工格局,才能促進減排,這一現象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尤為明顯。而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不大,可能與當前整體上的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水平不高相關。
區分地區子樣本進行產業分工中介效應檢驗的結果與表8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區中心城市服務業專業化的結果,見表9。中心城市服務業專業化的減排效果在沿海地區子樣本中有所凸顯,且空間結構指數的系數顯著為正,與表4的異質性分析和表8的中介效應檢驗有顯著差異。這說明沿海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水平較內陸地區經歷了較大轉變,且確實具有碳減排效應;在當前城市群空間結構轉變過程中,需注重中心城市在研究設計、信息服務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的能力提升與高度專業化,實現分工,引領創新,將有助于通過該渠道實現碳減排。
3. 4. 2 交通基礎設施的調節效應
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會對運輸成本直接產生沖擊,可能會引發產業重新布局,促進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從而調節空間結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因此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加入交通基礎設施變量trans 及其與空間結構指數的交互項spatial × trans,來考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在空間結構影響二氧化碳排放過程中發揮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見表10:列(1)為基準回歸結果,列(2)交通基礎設施變量系數顯著為負,即說明發達的交通基礎設施本身便有助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列(3)加入了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這意味著較高的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有利于緩解單中心空間結構的碳排放增加效應,即存在調節效應,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增強多中心空間結構的碳減排效應。
3. 4. 3 城市群多中心與市場一體化的替代效應
由于行政壁壘所造成的市場分割通過地方保護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動,加劇了資源錯配與環境污染。與之相反,區域市場一體化可為區域協調發展和減排帶來雙重紅利。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政府強調“優化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其最終目的即是“推動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由于市場一體化與城市群空間結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二者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也并非獨立,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效應,甚至是替代效應。為此,逐步引入市場一體化指標integ 及其與空間結構指數的交互項spatial ×integ,分析城市群多中心發展、市場一體化和碳排放強度三者間的關系,結果見表11。列(1)為基準回歸結果,列(2)市場一體化的系數顯著為負,證實了市場一體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列(3)加入交互項后,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市場一體化有助于削弱單中心空間結構的碳排放增加效應,可以作為多中心空間結構的替代策略。因而,對于那些尚不足以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單中心城市群,可以通過降低地方保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倡導市場一體化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該研究發現多中心發展戰略與市場一體化戰略之間存在著替代效應。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在城市群成為新型城鎮化主體形態的背景之下,引導城市群低碳發展以應對氣候變化具有長遠意義。通過梳理相關文獻、構建計量模型,試圖探究城市群多中心發展的碳減排效應及其作用機制,以從城市群空間結構規劃角度為低碳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基于2000—2020年中國19個城市群的數據發現:①中國19個城市群從2000年以來,空間結構多中心性增強。沿海城市群空間結構趨向多中心尤為明顯,由省會城市與港口城市協調帶動區域發展;而中西部城市群由于發展落后仍呈現單中心空間結構。②中國城市群集聚了全國約80%的碳排放,但碳排放強度比非城市群低,具有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除遼中南以外的沿海城市群碳排放強度更低。③通過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運用工具變量法處理內生性問題并替換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發現相比于單中心空間結構,城市群多中心發展有利于實現碳排放強度的降低,且在中西部城市群更具適用性。因此多中心發展模式通過“借用規模”和“網絡外部性”實現比單中心范圍更廣、更強的集聚經濟、環境效應。④結合中介效應模型、引入交互項,發現城市群空間結構向多中心發展一方面加強了內部城市的功能分工,通過外圍城市制造業專業化、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促進產業分工與集聚,提高經濟效率以降低碳排放強度;另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有助于調節空間結構的環境影響;最后,通過與市場一體化的交互作用,多中心發展避免了地方保護主義所導致的要素錯配、效率低下問題,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結合所得結論,鑒于城市群多中心演變有助于協調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二氧化碳減排,多中心空間結構應成為城市群發展、疏散特大城市壓力的未來目標。但就目前部分城市群的單中心尚未發育成熟的基本情況,多中心不應成為一刀切的減碳策略,可以從產業分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一體化角度加以優化。因此,結合新型城鎮化目標,提出如下城市群碳減排政策建議:
(1)重視城市群空間結構規劃,因地制宜,明確城市功能定位。結合當前城市群經濟發展狀況及內部城市人口、產業分布情況,確定合適的空間結構發展目標,對不同城市進行重點產業布局。當前多數沿海城市群已呈現多中心發展態勢,由省會城市、港口城市雙城帶動發展,但功能定位尚存交叉重復,部分中心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程度不足以起到引領作用,制造業企業外遷條件尚不成熟,需加強城市功能定位,引導形成城市間產業分工。對于內陸城市群表現出的中心城市發育及輻射帶動力不足和城市間差距顯著等現象,要避免中心城市盲目蔓延發展態勢,亟須優化明確主導產業,破解行政區劃對要素流動的制約,考慮由核心省會城市促進都市圈的形成,加強城市聯通,調整區域內產業布局,逐步形成多中心空間結構,帶動周邊地區崛起。部分跨省域城市群的雙核存在發展差異,經濟聯系不夠密切,需突破行政界限,形成合作規劃,實現互補與共贏。
(2)推進交通通信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為城市間功能聯系打造基礎。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依賴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來打造城市間的連結性,只有降低人口流動的遷移成本和商品貿易中的運輸成本,才能真正影響企業的成本利潤函數,改變區位決策,構建真正的城市網絡。因此交通基礎設施是多中心發展的基礎。此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推進,信息化成為經濟發展和競爭的集中點,推進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成為影響企業空間布局的另一重要因素。
(3)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促進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城市群多中心空間結構的形成,重在要素基于利潤最大化原則自由進行區位選擇、獲得集聚優勢,因而要素能否自由流動決定了空間結構的演變。日前,國家發布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和《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其中要求打造公平的競爭市場環境、取消縣城落戶限制政策,意在推動要素資源高效配置。因此,無論是在人口落戶、企業借貸、子女教育、政府補貼等方面,均應使外來人口、企業享受同等待遇、共享發展成果。需完善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破除人口流動壁壘,優化市場機制,加強城市間功能聯系,實現一體化發展。
參考文獻
[1] 方創琳, 張國友, 薛德升. 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J]. 地理學報, 2021, 76(12):2898-2908.
[2] 落基山研究所. 中國城市群碳排放達峰之路:機遇與探索[R].2019.
[3] 方創琳. 中國城市群地圖集[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0.
[4] IPCC.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of working group Ⅰ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5] 王軍鋒, 裴子璇. 深刻把握并科學謀劃城市群碳達峰、碳中和行動[J]. 環境保護, 2022, 50(S1):41-43.
[6] 黃妍妮, 高波, 魏守華. 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分布與演變特征[J]. 經濟學家, 2016(9):50-58.
[7] 孫斌棟, 華杰媛, 李琬, 等. 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的演化與影響因素:基于人口分布的形態單中心-多中心視角[J]. 地理科學進展, 2017, 36(10):1294-1303.
[8] 張浩然, 衣保中. 城市群空間結構特征與經濟績效: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J]. 經濟評論, 2012(1):42-47,115.
[9] 卓云霞, 劉濤. 城市和區域多中心研究進展[J]. 地理科學進展, 2020, 39(8):1385-1396.
[10] 劉修巖, 李松林, 陳子揚. 多中心空間發展模式與地區收入差距[J]. 中國工業經濟, 2017(10):____漘(25-43.
[11] BURGER M, MEIJERS E. Form follows function: linking morphological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J]. Urban studies, 2012,49(5):1127-1149.
[12] 姚常成. 多中心空間結構視角下新時代中國城市群的協調發展研究[D]. 長春:吉林大學, 2019:84-89.
[13] 姚常成, 李迎成. 中國城市群多中心空間結構的演進:市場驅動與政策引導[J]. 社會科學戰線, 2021(2):78-88,281.
[14] 于斌斌, 郭東. 城市群空間結構的經濟效率:理論與實證[J].經濟問題探索, 2021(7):148-164.
[15] 姚常成, 吳康. 多中心空間結構促進了城市群協調發展嗎:基于形態與知識多中心視角的再審視[J]. 經濟地理, 2020, 40(3):63-74.
[16] 陳旭, 張碩. 多中心空間結構是否有助于工業減排:來自中國省級數據的經驗證據[J]. 南京財經大學學報, 2021(1):11- 21.
[17] 陳旭, 張亮, 張碩. 多中心空間發展模式與霧霾污染:基于中國城市數據的經驗研究[J].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27(5):30-44.
[18] 劉凱, 吳怡, 王曉瑜, 等. 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對大氣污染的影響[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20, 30(10):28-35.
[19] SHA W, CHEN Y, WU J S, et al. Will polycentric cities causemore CO2 emissions:a case study of 232 Chinese cities[J]. Journal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20, 96:33-43.
[20] CHEN X, QIU B, SUN S O.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and energy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J].Energy policy, 2021, 149:112012.
[21] ZHU K, TU M Y, LI Y C. Did polycentric and compact structure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 spatial panel data analysis of 286 Chinesecities from 2002 to 2019[J]. Land, 2022, 11(2): 185.
[22] CHEN X, ZHANG S, RUAN S M. Polycentric structure and carbondioxide emissions: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provincial data in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8:123411.
[23] 范秋芳, 王勁草, 王杰. 城市空間結構演化的減排效應: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J]. 城市問題, 2021(12):87-96.
[24] LIU K, XUE M Y, PENG M J, et al. Impact of spatial structure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an analysis of theShandong Peninsula, Chin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change, 2020, 161:120313.
[25] WANG Y N, NIU Y J, LI M, et 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carbonemiss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and driving forces[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2, 78:103600.
[26] 張立賢, 任浙豪, 陳斌, 等. 中國長時間序列逐年人造夜間燈光數據集(1984—2020)[Z]. 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2021.
[27]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UK: Macmillan, 1890.
[28] HENDERSON J V, THISSE 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economics[M]. Amsterdam, Netherlands: Elsevier, 2004:2063-2117.
[29] HENDERSON J V.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age and city size[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6, 19(1):47-70.
[30] ALONSO W. Urban zero population growth[J]. Daedalus, 1973,102(4):191-206.
[31] CAPELLO R. The city network paradigm: measuring urban networkexternalities[J]. Urban studies, 2000, 37(11):1925-1945.
[32] 林柄全, 谷人旭, 王俊松, 等. 從集聚外部性走向跨越地理邊界的網絡外部性:集聚經濟理論的回顧與展望[J]. 城市發展研究, 2018, 25(12):82-89.
[33] 姚常成, 宋冬林. 借用規模、網絡外部性與城市群集聚經濟[J]. 產業經濟研究, 2019(2):76-87.
[34] 陸銘, 馮皓. 集聚與減排:城市規模差距影響工業污染強度的經驗研究[J]. 世界經濟, 2014, 37(7):86-114.
[35] 楊仁發. 產業集聚能否改善中國環境污染[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5, 25(2):23-29.
[36] 邵帥, 張可, 豆建民. 經濟集聚的節能減排效應:理論與中國經驗[J]. 管理世界, 2019, 35(1):36-60,226.
[37] 錢學鋒, 梁琦. 分工與集聚的理論淵源[J]. 江蘇社會科學,2007(2):70-76.
[38]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483-499.
[39] ALONSO‐VILLAR O, CHAMORRO‐RIVAS J M. How do producerservices affect the 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accessibil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and space, 2001, 33(9):1621-1642.
[40] DURANTON G, 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7(2):343-370.
[41] 王桂新, 武俊奎. 城市規模與空間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J].城市發展研究, 2012, 19(3):89-95,112.
[42] 韓峰, 謝銳.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嗎:對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17, 34(3):40-58.
[43] 王靖. 新經濟地理視角下制造業集聚對碳排放的影響[D].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 2019:25-32.
[44] 宋馬林, 金培振. 地方保護、資源錯配與環境福利績效[J]. 經濟研究, 2016, 51(12):47-61.
[45] 張可. 市場一體化有利于改善環境質量嗎:來自長三角地區的證據[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9(4):67-77.
[46] 徐康寧, 陳豐龍, 劉修巖. 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性:基于全球夜間燈光數據的檢驗[J]. 經濟研究, 2015, 50(9):17-29,57.
[47] 陳晉, 卓莉, 史培軍, 等. 基于DMSP/OLS數據的中國城市化過程研究:反映區域城市化水平的燈光指數的構建[J]. 遙感學報, 2003,7(3):168-175,241.
[48] 蘇泳嫻, 陳修治, 葉玉瑤, 等. 基于夜間燈光數據的中國能源消費碳排放特征及機理[J]. 地理學報, 2013, 68(11):1513-1526.
[49] CHEN J D, GAO M, CHENG S L, et al. County‐level CO2 emissionsand sequestration in China during 1997-2017[J]. Scientificdata, 2020, 7:391.
[50] MEIJERS E J, BURGER M J. Spat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in US metropolitan area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and space, 2010, 42(6):1383-1402.
[51] 齊謳歌, 趙勇. 城市群功能分工的時序演變與區域差異[J].財經科學, 2014(7):114-121.
[52] 劉修巖, 梁昌一. 中國城市群一體化水平綜合評價與時空演化特征分析:兼論城市群規模的影響[J]. 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49(2):49-61.
[53]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1986,51(6):1173-1182.
[54] BOSKER M, BURINGH E. City seeds: geography and the originsof the European city system[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7, 98:139-157
[55] WANG Y C, BORTHWICK A G L, NI J R. Human affinity forrivers[J]. River, 2022, 1(1):4-14.
[56] BURCHFIELD M, OVERMAN H G, PUGA D, et al. Causes ofsprawl: a portrait from spa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 121(2):587-633.
[57] 劉修巖, 劉茜. 對外貿易開放是否影響了區域的城市集中:來自中國省級層面數據的證據[J]. 財貿研究, 2015, 26(3):69-78.
[58] 李威, 王珺, 陳昊. 國際貿易、運輸成本與城市規模分布:基于中國省區數據的研究[J]. 南方經濟, 2017(11):85-102.
(責任編輯:蔣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