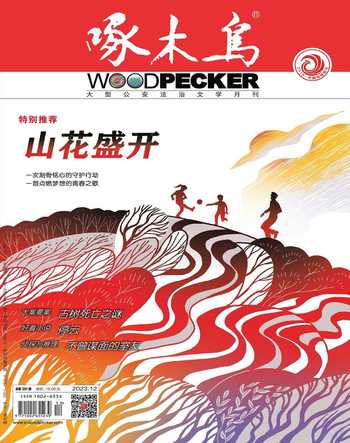一身警服
杜愛鵬

誰會想到堂兄居然遭遇如此境地?要知道,小時候他是我的偶像。一身警服在我們鄉村孩子眼里,那可是天花板般的存在。只是沒想到,幾十年前,擰著眉頭的父親真的一語成讖。
其實,父親一開始挺看好我的這位堂兄,畢竟父親在鄉鎮分管組織人事工作。
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洪林橋街道似乎忽然窄了,連沿街門面房都趴下了身子。一個高大的身影過來,一身警服加上锃亮的皮鞋,那個威嚴啊——到底是警察,人家直接不打彎地到了我家,仿佛身后有雙無形的手,牽扯著一批圍觀的街坊鄰居。
與我父母從未謀面,人家一聲聲那個客套,真是拉風。一袋煙工夫,與半個村子的左鄰右舍自來熟。于是,洪林橋街道都知道了:“老杜家那個親戚,一身警服,公安吶!”
鄰居們眾星捧月,堂兄的話匣子便如江水滔滔,十幾雙聽眾的眼睛隨著堂兄一張一合的嘴唇,噴射出一道道獵奇的目光。堂兄天南海北滿嘴跑火車,可是人們更感興趣的是破案,尤其是城關理發店上個月發生的一起兇殺案。
“大跛子殺小跛子?嗨!女人惹的禍。”繪聲繪色的堂兄,一到某個關口就踩剎車。大家表示理解,內部消息嘛,點到為止。
一身警服,等于我們家出了個大干部。有個愣頭青不服,來我家門前打探,剛瞅見堂兄那健碩的身姿,立馬小腿肚子打顫。也有熱心的找上門來問:“您那大侄子,還沒女朋友吧?”
父親沉默了一下,含笑說:“上門認親的,真不大了解……”
“乖乖,一身警服,眼光高啊!”
難怪人家熱心,堂兄一身筆挺警服,氣宇軒昂,樣板戲《紅燈記》里的李玉和,怕也是相形見絀。
“小老弟,想不想打兩槍?”看出我一臉崇拜,堂兄拍了拍腰間的槍套。
“開什么玩笑?”父親畢竟軍人出身,及時予以制止。
“逗他玩呢!來,教你寫字。”刷的一聲,抽出一支英雄牌鋼筆,“字,人的門面。寫得好,人家才看得起你!”堂兄的教誨,讓我格外留神。
對這位上門認親的“一身警服”,家人原本挺歡迎,那年月,家里來了位供職國家要害部門的親戚,怎能不長臉?后來,陸續從父母的談話中知曉,堂兄在縣公安局工作,當過兵,三十好幾了,還是單身。
隔年,鄰居為堂兄物色了對象——女干部,大學畢業,三十出頭,只是模樣勉強了些。
“天生一對,地設一雙。”鄰居胸脯拍得山響,“舉案齊眉,門當戶對。”
“女干部,一口普通話,縣廣播站播音員!只是長相嘛……”堂兄剛嘀咕了一句,父親重重地“嗯”了一聲,提醒道:“成家立業,主要看人品……你一身警服,到哪兒都要穩重。”
“叔叔,您教導得對。”堂兄連忙找了回來,“她的一手字,也好。”
準備領結婚證時,堂兄卻人間蒸發,兩月不見人影。鄰居急了,我父母更為惱火。好歹也是洪林街道有頭有臉的,丟不起這個人。
多年之后,父親的一位老戰友談心時埋怨道:“你這個侄子有點兒怪,找對象這事,一到關鍵時候就掉鏈子,好多次了。”
又過了幾年,一身警服的堂兄出現在街頭,早已沒有往日的神采。快四十歲的人了,對于婚戀之事只字不提。
有一次,堂兄正津津有味地講起本地剛發生的一起搶劫案,不想遇到途經洪林鎮檢查工作的縣公安局局長。
“他這個小學教師,不就是當了個局長嘛,了不起啊?”堂兄脖子一梗。
“怎么說話的?犯紅眼病了?”父親有些光火。
堂兄垂下頭,佝僂著腰,窸窸窣窣的,掏出一根“大前門”,劃了好幾根火柴,鼻子底下這才冒出兩綹白煙。
當晚,父親長嘆一聲,仍禁不住擔心。
一晃幾年不見堂兄,其間只收到過他一封來信,字體瀟灑依舊,只是筆力有些虛弱。信中談及,前不久崗位調整,他被調去了另一個鄉,當特派員。
特派員這個角色,我那時還不大明白,只是在電影里見過。父親搖搖頭道:“毛病改不了,一身警服,怕是穿不長了!”
果然,當年公安系統大整頓,少數不能勝任的被“禮送”出列。
沒過多久,堂兄公安特派員的身份也沒了。成天與酒為伴的他,難免胡言亂語,頭破血流是常有的事。
某天一大早,有人送信,說是淺水溝處摔了個人,身子都要硬了;那人一身警服……
遠遠地,拉起了警戒線,父親跟了過去。
又過了些天,消息送到鄉里,排除了他殺可能,建議鄉政府安葬——雖說酗酒失足,畢竟穿過一身警服。
責任編輯/謝昕丹
插圖/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