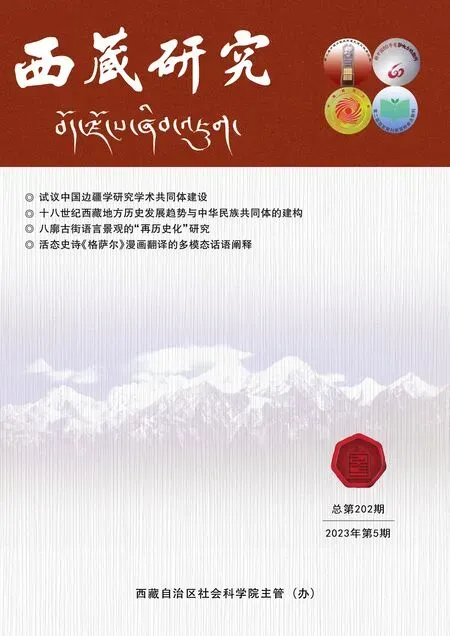活態史詩《格薩爾》漫畫翻譯的多模態話語闡釋*
王治國 張若楠
新媒體時代文學作品的傳播形式發生了新變化,譯作也不再局限于單一的語言文字敘事模式,而變成語言和非語言文本共同作用的多模態混合文本。近年來,傳唱千年的藏族活態史詩《格薩爾》除了說唱藝人口頭傳承、書面印刷文本傳播外,還以連環畫、漫畫、影視等藝術創作演繹形式廣泛傳播,呈現出跨語言、跨藝術的多模態、多維度傳播態勢,為更多類似民間文學、史詩文化的藝術創作和對外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活態史詩多模態翻譯不僅展現出口頭說唱和文本互文傳承交融,多語翻譯與語境重現的媒介融合符際特征,而且書寫了少數民族人民愛好和平、熱愛家園、保家衛國的愛國情懷,同時彰顯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格薩爾》改編為漫畫又進一步翻譯為英語,其中折射出關于漫畫翻譯的藝術改編、翻譯轉換等諸多問題,需要學界給予應有的關注和與之相關的研究。
一、活態史詩的漫畫改編與英譯
海德格爾在《世界圖像時代》中說:“世界被把握為圖像……根本上世界成為圖像,這樣一回事情標志著現代之本質”,(1)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99頁。意指圖像主導的視覺文化開始重新建構人類文化。作為一種特殊視覺文化,漫畫是以視覺圖像為傳達媒介的藝術,是啟迪人們獨立思考、開啟心智的有效視覺圖像之一。傳統的人文內容也需要漫畫視覺文本語言來獲得大眾化、普適化的傳播。在漫畫與傳統人文經典結合方面,中國近代漫畫史上也曾有過類似的探索與成果。民國初期的豐子愷先生曾以漫畫方式呈現古代文學或經典,使大眾意識到漫畫可以承載豐富的人文內涵。文化經典漫畫中圖像與文字兩種不同的敘事媒介對讀者的視、知覺影響雖有不同,卻在同步傳遞信息。讀者的閱讀過程并非圖像加文字的簡單感知,而是對所見圖像、文字進行素材重組,產生出對圖像文字之外形而上的哲學理解,這一過程中產生的閱讀樂趣與情感體驗大于畫面與文字的簡單相加。文字與圖像統一于漫畫的整體敘事中,讀者閱讀便是在這種有機組合中構建自己的認知和獲得審美體驗過程。
活態史詩漫畫藝術改編體現出“圖文闡釋,語圖互文”的特點,旨在對史詩的精準把握與深度詮釋基礎上進行史詩的漫畫藝術改編,讀者從中不僅可以獲得形而下的視覺化滿足,也能獲得形而上的意象化審美體驗。2012年1月大型全彩《格薩爾王》漫畫(全5冊)漢語版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發行,同年9月《格薩爾王》漫畫(全5冊)英文版也由海豚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是漢語版的對照英譯版,裝幀精美。《格薩爾王(1):賽馬稱王》(2)權迎升編繪:《格薩爾王(1):賽馬稱王》,王國振、柯雨譯,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以漫畫形式敘述英雄故事,通過特色鮮明的人物形象勾畫、不失幽默而又活潑輕松的對白、夸張絢麗的色彩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輔以漫畫創作者權迎升行云流水般的畫筆,圖文并茂地將經典英雄史詩精髓展現出來。《格薩爾》漫畫以細膩、變形、多樣的畫面表現,融合鏡頭化的敘事,富于藝術感染力。將史詩以漫畫形式呈現,為活態史詩等文化題材開拓了親近現代大眾的途徑。原創史詩《格薩爾》漫畫改編,以夸張特寫的圖像藝術創造,將大眾真正帶入了《格薩爾》的“讀圖時代”,這是《格薩爾》藝術改編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連環畫和漫畫一起,將《格薩爾》活態史詩的英雄形象以圖像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以動漫形式表現活態史詩是傳統文化現代化詮釋的一種方式,也是漫畫甚至動漫藝術發展取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格薩爾》成為經典長盛不衰,一個原因就在于史詩與不同文化的持續互動與不斷譯介。說唱藝術、文字傳承、視覺圖像等多種敘事模態的綜合運用,構成了《格薩爾》活態史詩傳播的多模態特征。《格薩爾》漫畫改編的最大特點是經歷了兩次敘事模態轉換,將史詩的說唱文本改編為漫畫書籍,在此基礎上又將漢語漫畫譯為英語出版,構成了雙向闡釋的藝術再造。漫畫改變著讀者的認知,而讀者的審美過程亦是對漫畫的再創作。權迎升實際上也是史詩翻譯者之一,首先他要對史詩文本進行解讀與理解,其次通過其藝術創造并結合當下讀者審美心理,將史詩改編為通俗易懂的漫畫,完成了由文字到圖像的迻譯。在理解與闡釋的碰撞中,史詩逐漸被接受并以漫畫審美感知得到持續傳播。漫畫的英文翻譯是王國振,2009年英譯了由降邊嘉措、吳偉編撰的《格薩爾》史詩。2009年版英譯本《格薩爾》雖然是傳統意義上“亦步亦趨”的翻譯,但也是唯一有漢語原本可資對照的《格薩爾》英譯本。由于有了《格薩爾》英譯的經歷,再度英譯《格薩爾》漫畫,譯者顯然更得心應手。
《格薩爾》漫畫的問世,為各國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帶來了愉悅閱讀活態史詩的便捷渠道。通過漫畫、繪本畫等視覺文本藝術,《格薩爾》以連環畫、漫畫漢語版,藏漢對照版,漢英對照版的多語種對照出版發行,對助推《格薩爾》活態史詩在更廣范圍內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以漫畫形式對活態史詩進行藝術改編,既為大眾讀者提供了領略史詩文化的視覺模態文本,也為活態史詩文化大眾化傳承和對外傳播拓展了途徑和媒介。將《格薩爾》改編成漫畫書籍后同步翻譯為英文的藝術創造,給讀者和觀眾以不同尋常的視覺享受。不難想象,藝術改編后再度翻譯為英語,可以吸引更為廣泛的多語讀者,同時也引發了漫畫翻譯的符號轉換與多模態轉譯相關問題的討論。
二、漫畫翻譯的多模態視閾
多模態話語篇章是包括文本、圖像、聲音等語言與非語言符號形成的復合話語和社會現象。不同模態相互作用,共同建構多模態話語意義。側重于翻譯研究的多模態話語分析,或者說是多模態翻譯,至少需要囊括符號學特別是社會符號學、圖像與文字關系以及語用學等不同學科,是跨學科的研究。社會符號學側重于不同模態如何組織,符際關系間的相似性與不同性以及構建意義的潛能。Gonzalez(3)Gonzalez.L.P.,Multimodality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ed.by Bermann,S.&Porter,C,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John Wiley&Sons Ltd,West Sussex,2014,pp.119-131.提出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和翻譯走向主流文化產業,多模態必將成為未來翻譯界的研究焦點。多模態翻譯實則是符際轉換,涉及兩種以上不同媒介間的符際翻譯。正如Liu(4)Liu,F.C.,On Collaboration:Adaptive and Multimodal Translation in Bilingual Inflight Magazines,Meta,No.1,2011,p.208.所言,“視覺元素用于傳遞語言信息,圖文符號同時呈現,圖像以不同的模態‘翻譯’文本”。陳風華、董成見(5)陳風華、董成見:《多模態翻譯的符際特征研究——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為中心》,《學術探索》2017年第10期,第90—95頁。等認為:“符際翻譯涉及兩種不同媒介之間的翻譯,如語言媒介翻譯為圖像媒介,因此‘插圖’的圖像可以視為文本的翻譯形式”。許勉君(6)許勉君:《中國多模態翻譯研究述評》,《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第40—46頁。也認為多模態翻譯包括多模態話語的翻譯、不同模態間的翻譯轉換和多模態理論的翻譯應用。簡而言之,多模態翻譯不僅是傳遞語義表征,更重要的是追求釋義相似。
(一)漫畫翻譯的符號學闡釋
20世紀90年代起國外開始了漫畫翻譯研究,近年來日趨活躍。2008年意大利學者Federico Zanettin出版了《漫畫翻譯》論文集,這是第一本專涉漫畫翻譯研究的論文集。論文集既涉及漫畫翻譯的總體原則探討,又囊括了英語、法語、意大利語、日語、阿拉伯語、東南亞語等語種的個案研究。Federico Zanettin(7)Federico Zanettin,Comics in Translation:An Overview,ed.by Federico Zanettin,Comics in Translation,London,Routledge,2008,pp.1-32.認為:“漫畫使用的所有‘語言’都可以在符號系統內部和/或符號系統之間‘翻譯’”。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指出:“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漫畫翻譯涉及不同層面的闡釋活動,這些闡釋可以是符號間或符號內,也可以是系統間的概念化行為。……漫畫主要是視覺文本,它可能(也可能不)包括語言成分,在漫畫翻譯中語際翻譯發生在視覺翻譯的語境中。語言只是漫畫翻譯中的一個系統(就我們樂于將語言定義為一個系統而言),漫畫的‘原作’和‘譯文’都同時借鑒了許多不同的符號系統。”(8)Federico Zanettin,Comics in Translation:An Overview,ed.by Federico Zanettin,Comics in Translation,p.27.顯然,漫畫中語言和非語言符號對傳達信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漫畫傳播重要一環的漫畫翻譯,僅通過分析語言轉換,而不關注圖像和排版等非語言因素是不夠的。
長期以來,漫畫作為一個獨立的調研對象完全被翻譯界忽視,近來翻譯史研究兩大主要文獻《翻譯研究詞典》和《翻譯研究百科全書》中甚至沒有獨立的漫畫詞條,后者只是在諸如“補償”和“符號學方法”等條目中提及漫畫。反而是凱德爾(Kaindl Klaus)(9)Klaus Kaindl,Multimoda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humor in comics,ed.by Eija Ventola,Charles Cassily and Martin Kaltenbacher,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pp.173-192.提出漫畫翻譯應該從“多模態視角”著手,試圖系統分析不同符號資源,如語言、圖像、聲音和音樂是如何通過它們的相互依存而賦予意義的。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每一個視覺符號都傳達著意義,“因此在提及視覺元素時避免使用‘非語言’(non-verbal)這一常用表達方式,以強調視覺元素作為一個概念的自主身份,而不是通過否定來描述它。”(10)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ed.by Mona Bake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88,Nadine Celotti,The Translator of Comics as a Semiotic Investigator,ed.by Federico Zanettin,Comics in Translation,London,Routledge,2008,p.59.翻譯界終于認識到漫畫的特殊性:漫畫是一個敘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圖片元素也傳達意義,它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文字信息,且通常占據主導地位。
漫畫的特殊性如何影響其翻譯方式,視覺語言如何成為譯者的一種資源而不是制約,是漫畫翻譯始終繞不過去的一個核心環節。從符號學視角研究漫畫翻譯的重要性變得愈發突出。“雅克布森可以說是最早嘗試用多模態定義翻譯的翻譯理論家”,(11)潘韓婷:《翻譯研究的語言學途徑:從比較語言學到多模態話語分析》,《中國翻譯》2022年第1期,第18—28頁。按照雅克布森的翻譯分類,史詩漫畫翻譯過程包括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三種類型,僅將史詩改編成漢語漫畫的過程就包括了語內、語際和符際翻譯,再加上將漫畫文本翻譯成外語則又屬于語際和符際翻譯的范疇。作為語際轉換的漫畫翻譯,主要發生在視覺翻譯的語境中。語言只是漫畫翻譯中的一個符號表意系統,漫畫“原作”和“譯文”都同時借鑒了許多不同的符號系統。將漫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主要是將其翻譯成另一種視覺文化,因此不僅涉及不同的自然語言,如漢語、英語等,還涉及不同的模態轉換以及不同文化傳統下的漫畫慣例。換言之,漫畫翻譯不僅僅意味著語言文字材料的語際、語內替換,用譯入語出版的漫畫譯本也可能經歷一些嬗變,包括對其他符號系統的解釋,而不僅僅是自然語言間傳統意義上的翻譯。一定程度而言,漫畫翻譯的關鍵和難點就在于如何越過因文字和圖像之間由于缺乏同質性或文化差異而造成的閱讀障礙。
(二)漫畫翻譯的多模態轉譯
漫畫是一個圖片和文字都傳達意義并共同創造故事的敘事空間,譯者要解讀圖像元素的意義及其與語言信息的不同關系,類似互補還是對話關系。事實上,漫畫翻譯中閱讀的含義更加寬泛,超過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譯者作為讀者,需要提升閱讀、闡釋視覺符號和語言符號的解釋技能。正如艾斯納(Eisner)(12)Will Eisner,Comics and sequential art,Tamarac,Florida,Poorhouse Press,1985,p.8.所言,“閱讀漫畫是一種審美感知和心智精進的行為”,漫畫翻譯亦是。就一般意義上的漫畫組成要素——圖像符號和文字信息而言,其翻譯策略有所不同。就圖像而言,繪畫占據了相當大的視覺空間,但它們并沒有構成視覺信息的全部。事實上,視覺信息是由多種元素組成的,每一種元素都傳達著意義,并為敘述增添節奏。
多種視覺元素共同構建了視覺一體模態,從而促成漫畫的本質性規定,即連續固定畫面敘事。如此,漫畫翻譯是由一系列模態轉譯而構成的序列轉換。多模態話語分析對多種模態的意義生成與轉換予以高度關注,尤其是多模態的轉譯現象。Kress(13)Kress G,Multimodality,London,Routledge,2010,p.36.認為:“將一種語境中產生的多模態話語意義轉移到另一種語境中去,這就是多模態話語中的轉譯(translation)現象”。轉譯關注的是意義如何從一種模態向另一種或多種模態的轉移,其實質是符號的再設計。例如,將小說改編成電影、把課本上的知識在課堂上傳授,或者將照片畫成圖像等都是轉譯。
譯者應該翻譯所有文字信息,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文字信息都會被翻譯成漫畫。文字信息可以分布在漫畫中不同位置,每個位置都有自己的功能,然而文字部分在具體如何翻譯時,卻存在一定程度的變化。漫畫文字主要出現在人物對白圓圈部分,但也不是唯一的位點,往往是人物第一人稱的口語表達部分,毫無疑問通常需要翻譯。位于畫格頂部或底部的漫畫說明文字,往往是第三人稱敘事文本,標志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但可包括圖片相關評論,一般需要翻譯。漫畫的標題是吸引讀者注意力所在,翻譯時要理解標題和視覺信息間可能存在的聯系,有時需要創譯和文化調適。首先,如同讀者一樣,譯者把一本漫畫書視為一系列視覺符號集合體。呈現在譯者面前的第一個視覺信息就是門檻,即封面、扉頁和故事第一頁之前的所有內容。其次,譯者連續掃視門檻后的頁面,以感知敘述節奏。空間結構的構建依賴于語義敘事,正是由視覺圖像的語義內容繪制出不同的頁面布局。因為“漫畫的核心在于圖像方格之間的空間,在那里讀者的想象力使靜態圖片變得生動起來!”。(14)Scott Mc Cloud,Reinventing Comics,New York,Paradox Press,2000,p.1.譯者要抓住視覺和語言的一致性,必須注意每一個視覺符號,以便發現它對全局意義的貢獻。例如,一個形狀像云的氣球意味著里面的東西是內心獨白的一部分,不會大聲說出來,而重疊的氣球則用來傳達語言交流的速度。再次,譯者還必須決定放在氣球外面的書面信息是否更具視覺效果而非語言效果。譯者需要確定語言信息的位置,以確定翻譯的著力點。漫畫中的文字信息是一種有意義的資源,因為它涉及視覺和語言兩個維度。顯然,每一種模態都在敘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圖像被視為一種普遍的視覺語言,譯者需要注意各種視覺圖像和語言文字間的相互作用,并把漫畫翻譯作為一種符號體驗,“以求譯語受眾能夠以最小的付出認知原文的交際意圖”。(15)鄧顯奕:《多模態圖文譯文生成模式的構建》,《上海翻譯》2019年第3期,第30—37頁。因為漫畫翻譯不只是文字轉換和插圖移植,而是關涉可讀和可見兩種模態之間的一種真正的互補關系。尤其要關注漫畫中出現文字信息的不同位置,關注語言副文本的翻譯,因為這是漫畫翻譯中文字迻譯的焦點所在。
三、《格薩爾》漫畫多模態翻譯舉隅
活態史詩翻譯的多模態符際特征再現了活態史詩對外傳播中的形象構建和語境遷移。《格薩爾》漫畫翻譯突破了單純文字符號模態相互轉化的限制,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傳遞格薩爾文化。譯本以簡單易懂的通俗連環漫畫讀本的形式出現,深入淺出地用漫畫來圖解《格薩爾》精髓。漫畫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表意功能,尤其是其圖像具有更強的自主敘事的能力,對幫助讀者理解譯文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圖像能夠擺脫文字的控制,讀者甚至無須參閱譯文,即可領悟譯者想要傳達的意思。漫畫譯本通過鮮活生動的漫畫形象對《格薩爾》進行了簡明扼要的闡釋,使英語世界的讀者能夠較為輕松地了解藏族活態文化。
《格薩爾》漫畫改編中英文翻譯的特征體現在漫畫文字模態主要采用了替換、意譯和直譯加注等歸化的翻譯策略;圖片模態主要采用了保留的異化策略;字體設計模態主要采用保留的異化策略。為了符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喜好,在文字和字體設計中,譯者把格薩爾文化思想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現出來。由于經濟成本的制約,圖片模態并未多作改動,基本全部得以保留。漫畫翻譯不再是以單純的文字為媒介,各種傳播媒介紛紛登場,既有生動的文字刻畫,又不時配以插圖,圖文并茂呈現,讓讀者的多重感官在閱讀過程中得以激活,觸發讀者的多重體驗,提升讀者對翻譯作品塑造格薩爾史詩文化的認識,實現了對原文敘事的“再敘事”。(16)劉翔、朱源:《伊維德說唱文學英譯副文本的民俗敘事建構》,《外語與外語教學》2019年第6期,第99—108頁。
漫畫翻譯的歷史表明,漫畫翻譯策略從如何調適文本以適應目標文化現有的漫畫市場,轉變為如何保留原漫畫文本,如何對原著進行差異性闡釋和創造性改寫,以突出原漫畫的文化特性。《賽馬稱王》漫畫中文字模態的翻譯獨具匠心,頗見功力。對于史詩中的專有民俗詞語,采用了在分格(gutter)處直譯加注的方式進行注解。如第19頁中對“佛陀空行”的注解就是在分格處增加注釋,即“Buddha is the name of Meto in the realm of the gods”(即梅朵在神界的名字)。蓮花生大師(Great Master Padmasambhava)在第34頁出場時,對梅朵娜澤(格薩爾母親)說“謀事在‘天’,成事在‘人’”。這句漫畫改編得非常絕妙。英文中有一句格言是“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而此處故意將其順序顛倒過來成為“God proposes,Man disposes!”,這就是漫畫中格薩爾投胎轉世的天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而是倒過來“謀事在天,成事在人”,通過文字改編傳遞了史詩人定勝天的人文情懷。第72頁“你休想動覺如(格薩爾幼年時名字)一根汗毛!”,英譯為“I can not allow you to do him even the slightest harm”,增加主語“I”,突出英語中一以貫之的主謂結構,同時,“the slightest”也譯得恰到好處。用“Doggie”而不用“dog”來翻譯“唬兒,回來吧”中的“唬兒”,顯示出兒童用語親切的特點。其他類似的文字翻譯如“過去的事都過去啦”(譯為let us let bygones be bygones),“自相殘殺解決不了問題!”(譯為Dog-eat-dog solves nothing)以及“好厲害”(譯為How smart!)等,均體現出譯者出入自如的翻譯方法,既準確翻譯了原文的意思,又傳達了原文的神韻。
史詩中覺如和母親被驅逐出了嶺部落家園,只好前往北部的瑪曲(黃河上游)謀生。路途遙遠,母親生怕覺如太累,讓他騎在白牦牛背上一起前行。覺如說“我不累。可是這牛走得好慢啊!”白牦牛聽到后頓時“呼呼……”生氣了,“哞哞”直叫,頓足不前。漫畫中對白牦牛的神態刻畫得惟妙惟肖(見圖1)。

圖1:第78頁漢英對照

圖2:第79頁漢英對照
漫畫格中有三處刻畫白牦牛的眼睛,其眼神變化最為精彩,其中一處是當白牦牛聽到覺如嫌它走得慢時,眼睛霎時間變得豆圓豆圓,隨后怒目而視,駐足不前——生氣干脆不走了。通過對眼睛的局部刻畫,傳遞了白牦牛細膩的內心活動。白牦牛的眼神表情尤為夸張,由起初的平靜到生氣,隨之表示反抗,既合乎情理,又詼諧可笑。兩格圖畫細節處理到位,雕琢入木三分,畫面感十足,再加上文字部分的象聲詞“呼呼,哞!(Whirr……Moo!)”,白牦牛的內心獨白和表情高度吻合,反映了白牦牛的心理變化,再配上覺如說“不是吧,老牛這么小氣?”童趣橫生,令人讀后回味無窮。
《格薩爾》漫畫譯文中文字、插圖、顏色等多種模態并用,使相對枯燥的文字閱讀煥發出新的活力,讀者的閱讀興趣隨之提高。除傳統意義上“傳神達意”的語言維度外,漫畫改編者和譯者恰當運用插圖說明、字體變化、色彩改變等非語言符號,來提高譯本內容的視覺化呈現水平,“在傳統的語言文字符號翻譯的基礎上,進行廣義上的翻譯轉換,關注書籍中的圖片、色彩、字體等其他因素的多模態設計”,(17)王海燕、劉欣、劉迎春:《多模態翻譯視角下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國際傳播》,《燕山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第51頁。無疑是文字模態和視覺模態綜合運用的多模態譯本。《格薩爾》漫畫譯本一方面將豐富中國乃至世界的格薩爾漫畫藝術形象,格薩爾以及一系列英雄人物漫畫形象將給讀者帶來愉悅與享受;另一方面多模態的漫畫譯本,在注重格薩爾自身故事性、情節連貫性和磅礴的氣勢外,以夸張、漫畫式的豐富想象力,盡情發揮了漫畫家的精湛手藝和譯文的行文流暢,將表現神話題材最好的傳媒形式——漫畫系列文本表現得淋漓盡致。
《格薩爾》通過多模態翻譯走向世界,既要充分發揮漫畫在當代《格薩爾》英譯中的作用,畢竟對《格薩爾》的藝術改編不可避免,同時還需要各領域專家——作家、畫家、格薩爾學專家、翻譯理論家、翻譯實踐家、出版商等通力合作。如果說漫畫家對人物形象、神態和動作的刻畫直接決定了譯本畫面是否逼真傳神的話,那么作家和格薩爾學專家為改編過程出謀劃策,并保證對原文內涵的準確把握責無旁貸。如果說翻譯理論家從翻譯和跨文化角度提供漫畫翻譯的理論指導,那么翻譯家則扮演了漫畫翻譯實踐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譯作成型后還需出版商組織策劃,負責譯本的宣傳和推介。只要各領域都能撮其機要、收彼精華,盡量避免改編時對原文的曲解或簡化,并能通力合作,跨領域合作才能真正出佳作佳譯,這代表了史詩漫畫英譯走向世界的發展方向。圍繞《格薩爾》漫畫翻譯所展開的活態史詩多模態符號學闡釋,無論是對《格薩爾》翻譯和傳播,還是新時期翻譯研究的視界拓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