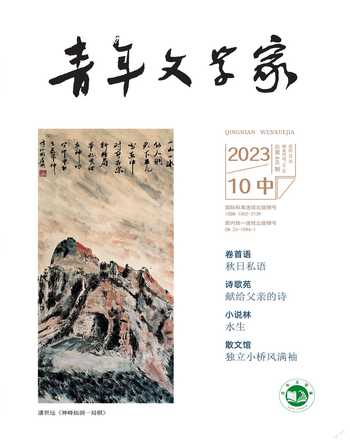任性背后的堅守與執著
龍洋

我們如今談起“竹林七賢”,會稱他們七位為名士,稱贊他們人品高潔,即使身處黑暗的政治環境卻依然堅守著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當時的人并不理解他們的放任曠達,歷代文人也對他們有許多批評,指責他們空有名聲而不帶頭遵循禮制,是一種極其任性行為;但其實“竹林七賢”表面任性的行為舉止與他們矛盾彷徨的內心是統一的,隱藏在任性行為之后的是對禮義真正的堅守。
一、“竹林七賢”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
“竹林七賢”指的是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位名士,《世說新語·任誕》記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生活于社會矛盾尖銳的背景之下,《晉書·阮籍傳》中描述為“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期,政治混亂,環境多變。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漢獻帝讓位,建立魏國。之后的數年間,司馬懿立下許多戰功,成為魏國的權臣。他侍奉過曹魏三代君主,地位日益提高,在遭受曹爽一黨的政治打擊后,開始韜光養晦,最終在曹芳執政期間發動高平陵事變,把持曹魏政權,篡位自立的野心昭然若揭。司馬氏的這次奪位之舉使得天下名士減半,留在朝中之人也都人心動蕩,紛紛遠離仕途以保全性命。
對此,當代學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宗白華認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期,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雖然生活在虛偽、險惡的環境之中,但“竹林七賢”仍然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進行著最大的反抗,他們堅守著自己的人生信仰,執著于自己的道德追求,為后世留下了經久不息的美談。
二、“竹林七賢”的人生信仰
當時,復雜的政治局面使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寧,名士們因前途的不確定性和對性命的擔憂而選擇寄居山林,形成了風行一時的“魏晉風度”。“魏晉風度”又叫“魏晉風流”“魏晉風骨”,指的是魏晉名士們所崇尚的一種人生信念和生活態度,是他們的美學追求,這是一種不同于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的一種言談舉止,“竹林七賢”就是這一風度的集中代表。司馬氏掌權之后開始在朝廷里排除異己,曹魏政權的許多舊臣由于懼怕司馬氏的權力而轉投于司馬氏;但“竹林七賢”選擇隱居山林,發揮道家學說崇尚自然的精神,在政治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拒絕與司馬氏合作,開始了他們那段給后人留下無限向往和憧憬的時光。
其實所謂的“魏晉風流”,也是特殊時代背景之下的無奈之舉,殘酷的社會現實使魏晉士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遭到了重創。在強調入世思想的傳統儒家文化中,知識分子大多渴望有一番作為,“竹林七賢”也不例外,他們大多有濟世的鴻鵠之志。例如,阮籍自幼資質出眾,《晉書·阮籍傳》記載:“容貌瑰杰,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阮籍才華橫溢,但礙于政治壓力被迫仕于司馬氏,他身不由已的痛苦可從他的作品中看出,如《詠懷八十二首》其三十三中寫道:“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竹林七賢”若在政治清明的年代,本可大有一番作為,但現實社會的政治壓力無處不在。因此,名士們表面的放浪形骸是出于對自己內心信仰的堅守和對篡位自立的司馬氏政權的抵抗。
三、對現實的反抗—越名教而任自然
何為“名士”?近現代著名學者牟宗三認為:“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清則不濁,逸則不俗。……風流者,如風之飄,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適性為主。故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才性與玄理》)我們現在雖然談起“竹林七賢”,會以“自由灑脫”“真性情”等詞來形容他們,稱贊他們人品高潔,但是在一千多年前,他們飲酒、服藥、化妝、赤身裸體的生活行為方式并不被世人接受。以《世說新語·任誕》中的一則為例,“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劉伶在室內裸體似乎是不知羞恥的行為,對他人的指責還不以為然。但是,我們不能僅停留在行為的表面,而應從人物的外在行為出發去挖掘其中蘊含的更深層次的精神價值。
人類從遠古走來,生產力不斷發展,思想不斷地進步以適應社會。在“竹林七賢”所處的時代,衣物已不僅僅起到蔽體保暖的作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用外在的衣物來體現個人身份或者內心的重要性。人類告別衣不蔽體的時代,這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從這一角度來看,劉伶的裸袒行為無疑是不合禮制的。但是,由于裸袒行為的初衷不同,對這一行為的評判也應有所不同。雖然歷史上對裸袒行為的評價幾乎都是謾罵,甚至連《晉書》這樣的正史中都記載:“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可見在重視禮儀的中國社會里,脫衣赤身裸體是多么嚴重的行為。“竹林七賢”不拘禮節的生活方式令許多人不解,批評者有之,攻擊者亦有之,如歷史學家郝經,他對阮籍、嵇康等人大加撻伐:“跌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褫裂衣冠,糠粃(亦作糠秕)爵祿,污穢朝廷……至于敗俗傷化,大害名教。”(《續后漢書》)那為什么古人這么重視服飾呢?因為在中國古代,服飾早已不僅僅是人們用來蔽體的工具,更是一個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傳統社會中,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封建帝王用強調上尊下卑這樣具有等級觀念的儒家思想來統治社會,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出等級森嚴、不可僭越的金字塔式結構,而服飾制度就是維持等級制度的標準之一。在周朝的等級制度中對于服飾就有嚴格的規定:“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禮記·禮器》)可見服飾已經成為人的一張名片,所以人們認為“竹林七賢”的裸袒就是公然地破壞禮制和國家的秩序。但是,以今人的眼光重審魏晉名士,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認為裸袒行為就是不合禮制。
赤身裸體的行為既然會引起人們的爭議,那么說明這種行為本身是存在著一定的問題的,至少與社會主流意識認同有出入,但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行為可能有著不同的來源。《史記·殷本紀》中記載“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好酒淫樂的商紂王使宮女們赤裸著身子在酒池里面盡情放縱玩樂,供紂王和妲己欣賞,這種極端變態的裸袒行為純粹是為了感官的刺激和取樂,是在欲望的刺激下對于自身行為的不可控制,這是君王帶頭對國家禮制的破壞,此后的殷商亡國也是對這一行為的嚴重懲罰。
而對于“竹林七賢”的裸袒行為,則需要考慮到當時的整體環境。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極為混亂的年代,呈現出一副“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對于那些在儒家思想指導下成長起來的文人來說,他們的抱負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文人意欲進賢又怯于官場的爾虞我詐,雖然進不能“居廟堂之高”,但可以退而“處江湖之遠”,實現自我超脫,于是玄學之風興盛,視世間的一切為空無,體現在服飾上便有了名士們的袒胸露臂。同樣都是裸袒,《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荒誕行為和“竹林七賢”產生的影響卻是天差地別。如今人們用“酒池肉林”來形容荒淫奢侈、縱欲過度的生活,而“竹林七賢”的裸袒則是為了反抗當時虛偽的禮教,“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實阮籍、嵇康等人作為名士,他們的心里怎么會不重教?只是由于司馬氏靠篡位奪取的天下,又開展了一次次血腥的屠殺,卻仍然宣稱以名教治天下,提倡以孝道為倫理的道德觀,偽人可以稱“賢”,可以在大是大非面前胡言亂語、虛偽做作,那么“竹林七賢”又何必在外在的服飾、言語、行為上面去迎合司馬氏主宰的社會呢?所以,對于商紂王的縱欲式裸袒應給予否定,而對于具有反禮教色彩的“竹林七賢”的裸袒行為則應當給予理解。
四、“竹林七賢”是否真的不合禮義和禮儀?
“竹林七賢”之所以被世人扣上不遵守禮的帽子,從賢人變為“偽人”,是因為魏晉時期的社會是個禮治社會,這里的“禮”指的是社會公認的行為規范,合于禮是說人們的行為合乎社會的標準、符合社會的期待,卻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符合真正的禮教。當時那種崇尚以禮育人的社會并不是我們所憧憬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禮記》)的理想大同社會,而是以禮為枷鎖從而束縛人的思想的假禮治社會。“禮”作為社會通行的行為規范,有倡導相親相愛的真禮教,自然也有封建落后的假禮教,假禮教作為糟粕,使人們的身心發展走向歧途和異端。魏晉時期,司馬氏集團以假禮教為工具打擊異己,表面上推崇禮治,實際行為卻大相徑庭,使得當時的社會充斥著虛假的仁義道德,到處都是拘泥禮教、死守禮法的縉紳之士。
社會在經歷相對動蕩的時期之后就會轉而尋求平靜。例如,在經歷秦末紛亂、異姓諸侯王叛亂、七國之亂,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戰爭后,傷痕累累的漢王朝元氣大傷,統治者開始奉行黃老之學,施行休養生息的國策。同樣,在魏晉時期,由于政治混亂,名士們紛紛歸隱山林,選擇不問世事。嵇康聽到山濤在由選曹郎調任大將軍從事中郎時,想薦舉他代其原職的消息后,給山濤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強調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嵇康強調放任自然,這既是崇尚老莊的無為思想,也是不屑于服務司馬氏集團和對世俗禮法的蔑視。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自己“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其實不管是劉伶裸袒或醉酒的行為,還是嵇康的邋遢形象,“竹林七賢”被世人詬病的原因都只存在于其外在,而不去過問他們的內心。他們的放蕩不羈,蔑視禮法,其實都只是一種表象,而非其本性。恰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才是真心信仰禮教的人!他們所蔑視的“禮教”,恰恰是肆無忌憚地踐踏禮教的“禮教衛道士”們,如篡位弒君的司馬氏之流所極力維護的虛假“禮教”。
身處亂世,“竹林七賢”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痛苦地徘徊,他們不拘禮教的自由已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他們反對統治者以虛偽的“禮儀”為由褻瀆禮教,他們信奉的是“禮”最深層的含義—禮義,因為不拘泥于表面的規矩,所以被扣上了反對禮教的帽子。一些“正人君子”斥責他們的行為傷風敗俗,只不過是因為“竹林七賢”生于亂世,正如“世人笑我忒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唐寅《桃花庵歌》),他們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的背后卻是對禮義真正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