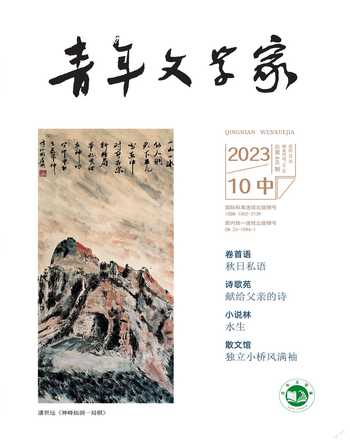艾麗絲·門羅作品中女性群體的創(chuàng)傷書寫 與精神突圍
梁耀方
2013年,加拿大女作家艾麗絲·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這是諾貝爾文學(xué)獎歷史上獲此殊榮的第十三位女性作家,也是加拿大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作家。門羅以短篇小說見長,被稱為“現(xiàn)當(dāng)代短篇小說大師”。門羅總能在不同的人物身上發(fā)掘出內(nèi)容,她的作品大部分講述平凡女性的命運。《逃離》是門羅的代表作,入選《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圖書,也是法國《讀書》雜志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在這部作品中,艾麗絲·門羅用細膩的筆觸講述了女主人公卡拉受到創(chuàng)傷的整個過程,揭露了女性成長之痛、家庭之傷,以及為獲重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犧牲。
本文主要研究《逃離》中女性群體的創(chuàng)傷書寫和精神突圍。主人公卡拉出生在傳統(tǒng)的父權(quán)制社會中,失去了自我的主體地位,同時又生活在沒有溫暖的重組家庭中,成為家庭結(jié)構(gòu)中的弱勢一方。在婚姻中,卡拉的丈夫克拉克獨斷、暴躁,導(dǎo)致卡拉在家庭中并沒有話語權(quán)。門羅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她自身對女性群體的關(guān)懷和同情在《逃離》中得到了極致的體現(xiàn)。《逃離》也啟示女性要不斷在創(chuàng)傷中成長,更好地實現(xiàn)自我價值和精神自由。
一、女性的創(chuàng)傷書寫
創(chuàng)傷是一個現(xiàn)代話題,是一種孤立的情感體驗。在創(chuàng)傷歷史化的過程中,它成為一代人或一群人所共有的記憶的對象,成為文學(xué)、電影等對過去進行再生產(chǎn)和塑造的基礎(chǔ)。
(一)父權(quán)制社會的“他者”
“他者”是與“自我”相對的概念。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談到女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社會將她們建構(gòu)成了女人。長久以來,在男女性別構(gòu)建的話題上,男性天生擁有話語權(quán),而父權(quán)制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喪失了獨立的地位。
克拉克向來瞧不起卡拉。當(dāng)西爾維婭提醒克拉克說,卡拉也是一個人的時候,克拉克驚奇地反問:“我的老婆也是一個人?是嗎?”在他的眼里卡拉只是一件屬于自己的物品,卡拉不應(yīng)該有自己的思維和想法,更沒有權(quán)利自己作決定。“菲勒斯中心主義”將女性視為“他者”,在男性事務(wù)和交際中將女性用作客體,限制和阻礙女性的創(chuàng)造力,避免女性接觸社會知識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領(lǐng)域。西爾維婭的丈夫,著名詩人賈米森先生也從未平等地對待妻子,他貶低西爾維婭的創(chuàng)作思想。西爾維婭認為值得一寫的題材,賈米森先生“總會感到一點點意思也沒有”。因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一直被視為是男性特權(quán),很多優(yōu)秀的女作家不得不以男性化的名字為筆名。在父權(quán)制社會中,身為女性想要創(chuàng)作要承擔(dān)巨大的壓力和排擠。西爾維婭試圖涉足寫作便遭到了丈夫的打壓,在賈米森先生的眼里,盡管他的妻子是受人尊重的植物學(xué)老師,可是永遠不被允許涉足“專屬男性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領(lǐng)域。
不論是簡單淳樸的家庭主婦卡拉,抑或擁有自己事業(yè)的獨立女性西爾維婭,籠罩她們的都是父權(quán)制社會的陰影,永遠當(dāng)著“他者”,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
(二)家庭結(jié)構(gòu)的“弱者”
家庭一直被視為女性重要的職責(zé)地,且父親和丈夫擁有絕對的管理權(quán)。“如同喬多羅在《家庭結(jié)構(gòu)與女性人格》一文中將性別建構(gòu)視為‘每一代人中體現(xiàn)出男女人格以及角色特點的某種一般的,幾乎是普遍差異的再生產(chǎn)過程。”(嵇璐《艾麗絲·門羅小說中的女性生存探索》)也就是說,在家庭結(jié)構(gòu)中,女性長期處于“弱者”地位,她們在家庭中默默付出,辛苦操勞,充當(dāng)著一個犧牲者、奉獻者的角色。家庭結(jié)構(gòu)中的女性時刻都像一個跟隨者,對男性的意愿只能聽之任之,成為家庭中弱勢的一方。
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卡拉的繼父對她毫不關(guān)心,“連她是死是活都不想知道”,“她反正不是他自己的女兒”;卡拉的哥哥對她也沒有什么感情,嫂子更是瞧不起卡拉。卡拉與家人之間橫亙著巨大的鴻溝,原生家庭的冷漠給卡拉留下了深深的創(chuàng)傷,在父母身上得不到溫暖,卡拉天真地將希望放在克拉克的身上。因此,她在遇到克拉克之后很自然地出走,去和克拉克住到一起。父母作為個體幼年時期所接觸到的最親密的人,其精神狀態(tài)、價值取向、情感表達方式皆對個體一生的成長影響深遠。“在卡拉的眼里,她自己的父母當(dāng)年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實際上是為卡拉指明了方向。”然而,卡拉顯然所托非人,這位“吉卜賽流浪漢”早跟家庭完全沒了聯(lián)系,克拉克甚至認為“家庭根本就是一個人血液中的毒素”。有時面對丈夫的怒火,卡拉只能默默忍受甚至卑微討好,盡管心里委屈,但她依然繼續(xù)干活兒,“可是她的淚水不斷涌出來,使得她沒法兒看清手里的活兒”。本就在原生家庭中處于邊緣弱勢的卡拉,又遇到強勢蠻橫的克拉克,她注定成為家庭結(jié)構(gòu)中的“弱者”。
(三)婚姻生活的“失語者”
婚姻對于男女雙方來說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婚姻的締結(jié)從一開始女性就被放在了附屬地位。社會對完美婚姻的期望常常寄托在女性身上,對理想女性有一系列的要求:一個完美的女人應(yīng)該滿足社會的期望,應(yīng)該符合丈夫心目中的標(biāo)準。這樣的婚姻給女性帶來了極大的限制和壓迫,體現(xiàn)在婚姻關(guān)系中女性的“失語”境遇之上。
福柯的“權(quán)利與話語理論”表示,當(dāng)一個人掌握了話語權(quán),他也就擁有了表達自己的權(quán)利,可以帶動或決定其他個體的行為,而與說話者對立的一方則會被壓制。每逢雨天克拉克情緒不好,家里的氣氛也因此很壓抑,卡拉只能去廄棚找點兒雜活兒來干。面對丈夫壓抑的情緒,她選擇默不作聲。作為丈夫,克拉克在聽到卡拉被騷擾后絲毫不關(guān)心卡拉的真實境遇,卻想以此敲詐賈米森先生一筆錢財,在他看來“問題僅僅在于開多少價而已”。卡拉受傷的經(jīng)歷成為克拉克牟利的手段,卡拉全程成為犧牲的“失語者”。除此之外,女性在婚姻關(guān)系中的“失語”還體現(xiàn)在對于現(xiàn)實處境的無力與無助上。面對克拉克的一再逼迫,卡拉表示不想再談?wù)撨@件事,可是“第二天又談到這件事,而且第三天第四天也都談了”。在婚姻里,卡拉沒有權(quán)利主宰自己的生活,來自丈夫的控制讓她無力掙脫,只得生活在無助之中。甚至,卡拉在得知克拉克殺害了自己心愛的弗洛拉之后,她依然選擇一言不發(fā)。“失語者”的狀態(tài)讓卡拉備受傷害,也時刻刺痛著卡拉的心。在卡拉的人生中,她可以成為任何角色,卻永遠無法做她自己。
與卡拉相比,西爾維婭稍顯幸運,但是在夫妻關(guān)系中西爾維婭同樣毫無話語權(quán)。丈夫賈米森先生并不關(guān)注妻子西爾維婭的內(nèi)心世界,她的創(chuàng)作想法在賈米森先生看來不值一提。在他的心里,或許妻子根本沒有創(chuàng)作的本領(lǐng)或才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領(lǐng)域就不該有女性存在。在婚姻關(guān)系中,妻子應(yīng)該保持沉默,順從于丈夫,合格的妻子應(yīng)該是一位“失語者”。
二、女性的精神突圍
在波伏瓦看來,女性長期處于“第二性”的位置,這是社會在性別建構(gòu)中的不平等。可是“沒有一個主體愿意主動成為客體,成為次要者”(《第二性》),如果當(dāng)女性被落后的社會觀念長期束縛,她們壓抑的內(nèi)心世界也會進行反抗,女性被束縛的狀態(tài)也就發(fā)生了改變,實現(xiàn)了精神突圍與成長突破。
(一)逃離家庭囚籠
家庭是性別不平等對待的高發(fā)領(lǐng)域之一。在《逃離》中,卡拉進行了兩次出逃。正是這兩次逃離,代表了女性對自由的向往和對家庭束縛的掙脫,她們想要擺脫被他人安排的不自主的生活,她們渴望把命運攥在自己手里,不再作為“他者”生活。
卡拉第一次逃離的是她的原生家庭。卡拉生活在一個缺少溫暖的重組家庭,從小缺少家庭的歸屬感。當(dāng)父母反對卡拉和克拉克交往的時候,卡拉毅然決然選擇出逃,跟隨自己對愛情的追求離開家庭。這是卡拉第一次實現(xiàn)精神突圍,她不再是生活在父權(quán)下的小女孩兒,不再對家人聽之任之。然而,與克拉克的結(jié)合并沒有卡拉想象中那么美好,克拉克對她進行言語貶低、暴力恐嚇,卡拉與克拉克的生活壓抑又陰暗,這就促使了卡拉的第二次逃離。在西爾維婭的幫助之下,卡拉留下一張簡單的字條便踏上去多倫多的旅途。雖然卡拉最終又決心回歸家庭,但是這次的回歸并不意味著她原諒了克拉克的做法,回歸后的她“覺得跟他配合也并不怎么困難”,這更像是求生的手段而非割舍不下的情感。雖然卡拉的第二次出逃以失敗告終,但這足以證明卡拉并未一味順從,她還在為自己掙扎出路,同時也揭示出在父權(quán)制社會中,女性苦苦尋求解放的道路注定坎坷波折。
(二)尋找情感寄托
情感寄托就是一種移情經(jīng)歷,在無助的狀態(tài)下,人便渴望能得到一位救助者。如果說卡拉的生活一直籠罩著一片陰影,那么小山羊弗洛拉就是她唯一的心靈依靠和情感寄托,在她最無助難過的時候總會想起弗洛拉。卡拉對待馬匹雖然態(tài)度溫和,但是也有點兒母親的威嚴。可是,對于小山羊弗洛拉她沒有任何優(yōu)越感,她們就像是平等的朋友一樣。
在弗洛拉走丟以后,卡拉有兩次夢到它:第一次是弗洛拉嘴里叼著一個紅蘋果走到床前;第二次是弗洛拉引導(dǎo)著卡拉來到鐵絲網(wǎng)柵欄跟前,鉆了出去。“女性的無意識反映在她的夢境中,是壓抑和非社會驅(qū)動的結(jié)果,夢中的無意識女性是被壓抑的心理的一面鏡子。”(籍曉紅、賈青云《艾麗絲·門羅〈逃離〉中的女性創(chuàng)傷敘事》)弗洛拉叼著的“紅蘋果”就像《圣經(jīng)》中伊甸園里的蘋果一樣,象征著一種“誘惑”,引誘著卡拉去追尋自由。小山羊其實就是卡拉的潛意識,它通過夢境的形式把卡拉引到鐵絲網(wǎng)柵欄前,鐵絲網(wǎng)象征著束縛卡拉的世俗藩籬;弗洛拉鉆出柵欄代表著卡拉要掙脫束縛,打破藩籬。對于弗洛拉,卡拉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情感。弗洛拉成為卡拉無助時的慰藉。
(三)建立“姐妹情誼”
“相似的創(chuàng)傷會產(chǎn)生群體認同,弗洛伊德將人群、種族、國家、宗教等定義為群體,將一個相同的對象置于他們自我理想的位置,并在他們的自我中認同彼此。”(籍曉紅、賈青云《艾麗絲·門羅〈逃離〉中的女性創(chuàng)傷敘事》)在《逃離》中,西爾維婭與卡拉兩位女性之間的感情對卡拉的創(chuàng)傷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姐妹情誼”來自英文sisterhood,包含著多樣化的內(nèi)涵,作為一種支撐性力量,協(xié)助女性實現(xiàn)建立在認同感基礎(chǔ)上的理想。
卡拉一直生活在克拉克的陰影之下,她難以獲得自己的權(quán)利和實現(xiàn)理想的機會。與克拉克壓抑的生活讓卡拉的內(nèi)心備受煎熬,因此在西爾維婭家中干活兒時,卡拉忍不住向這個比她年長的女性訴說自己的遭遇。對于卡拉而言,通過講述自己的遭遇能得到心靈的舒緩;而在西爾維婭看來,她在卡拉身上找到一種母性的情感,卡拉的出現(xiàn)也讓她的內(nèi)心得到了極大的慰藉,“她們之間似乎出現(xiàn)了一種難以說清的關(guān)系”。西爾維婭給卡拉的逃離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在聽到卡拉想要逃離這種壓抑的生活時,西爾維婭內(nèi)心的主體性被喚醒,她將未竟的愿望寄托在卡拉身上并給予卡拉精神和物質(zhì)上的幫助。對于西爾維婭而言,卡拉的逃離也象征著自己的自由解放。作為同一個群體,女性在很多方面都能達成共識,“姐妹情誼”蘊含著女性的共同經(jīng)驗和精神追求,在物質(zhì)和精神等領(lǐng)域的獨立訴求。
門羅通過書寫卡拉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揭示了父權(quán)制社會對女性主體地位的剝奪,家庭對女性的束縛,以及婚姻中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門羅又通過卡拉女性意識的覺醒及她的逃離經(jīng)歷,講述了女性面對不平等時的精神突圍。通過對《逃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小說啟示女性要不斷在創(chuàng)傷中成長,更好地實現(xiàn)自我價值和精神自由。
本文系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基金資助項目“艾麗絲·門羅作品中女性群體的創(chuàng)傷書寫與精神突圍—以《逃離》為例”(項目編號:CXJJS2301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