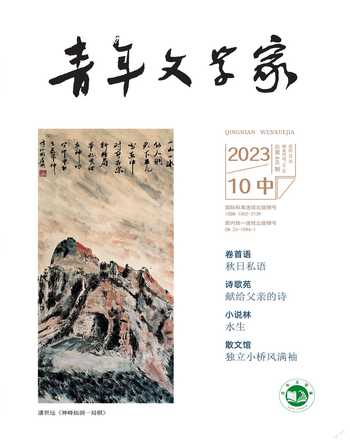糯香
黃志聰
我心中的梯田怎么也請不走,那是因為城里人的慵懶。兒時盼快長大,盼過節吃肉,盼新年放鞭炮、穿新衣。特別是八月金秋糯谷成熟的季節,對我有著特殊的鄉愁之渴。
糯米,在過去的年月,是特殊、不可代替的珍品。糯米的用處可多了。十月十五,農人把它蒸熟后,做出姜黃的、芝麻的糍粑,以圓滿的方式慶祝豐收。接著便是春節包粽子、三月三蒸五色糯等祭祀活動。除此之外,這里的山民還用它來做婦女的產后食品。坐月子期間,為保證充足的母乳,丈夫幾乎天天給媳婦煮糯米,配上姜酒雞湯,便是那個年代最奢侈的享受了。這是我的童年。即使這樣,我們也沒有感覺到什么叫窮,因為父輩常說他們不如我們。我在懵懂中不知窮字怎么寫,但嘗到一段歲月的艱苦是真的。
在農家,糯米是很稀罕的,平時是不舍得煮著吃的。它不僅是農村不可代替的節日用品,還擔負著婚事或吉慶諸事。每年農歷十一月和十二月,是男婚女嫁的高峰期。除了嫁妝,主婚家庭要根據請客吃飯的份額,為每位客人準備一份三色糯米飯,外加一個煮熟的紅色雞蛋,作為回禮。
糯稻每年種一季,生長期長。從三月育秧到八月桂花的芳香溢滿天空時,那一造種在梯田的紅皮、黃皮糯稻便逐日飽滿。嘴饞的人家將熟至八九成的糯谷脫粒,在“灶懷”里翻炒至熟香后,放在石舀里舂著。谷皮脫落后,干煸的米粒松軟,散發誘人的濃香,帶著夢幻一般的神奇,圓了童年的口味,香了一個熟秋。它的香味收購了小小村莊的饑餓,香了茅草屋,香了一叢籬笆矮墻;也香了我童年的口袋,香了姑娘的玉腮……
糯米有種獨特的香氣,它的香像爸爸的旱煙味,像媽媽的蘭花裙,像姑娘的胭脂粉。記得上學第一天,媽媽背著家里人,偷偷在我的口袋里放了幾把生糯米,哄著我好好去上學,告訴我學習好了,就有糯米。知足的我在課間休息時,使勁兒嚼著,米是媽媽四季蒸發的汗水種成的。
秋來,秋又走。彎彎的梯田是媽媽的腰,彎彎的稻穗是媽媽的脊梁。風拐走了媽媽的身影,糯稻仍站在梯田里。風拐走了我的童年,只有四季芬芳還在我的血脈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