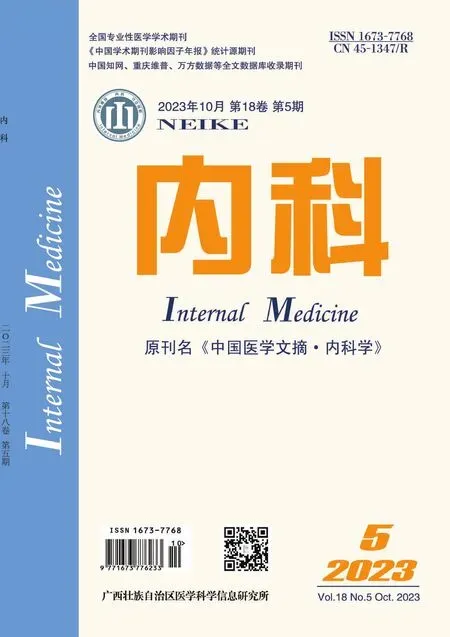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和健康促進行為之間的關系和作用路徑▲
滕蘭軒 廖喜琳 黃子津 呂開月 付晶晶 路漪凡
1 廣西中醫藥大學,南寧市 530001;2 廣西中醫藥大學附設中醫學校,南寧市 530022;3 廣西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南寧市 530021
腦卒中是一種行為相關疾病,不健康的飲食和生活習慣是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對預防老年腦卒中具有重要意義[1]。健康促進行為是指個體為了維持或促進自身健康,提升幸福和生活質量水平,自發采取的一種多方面的健康行為[2],其對激發患者潛在的健康意識、改善其生活質量、延緩疾病進展、防止疾病復發等具有積極意義[3]。復發恐懼是慢性病患者常見的心理問題,會直接或間接地引起患者自我管理紊亂和不健康的行為方式[4]。研究顯示[5],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復發恐懼處于較高水平,不利于老年腦卒中患者建立并保持健康促進行為。家庭彈性是指家庭成員調動家庭資源應對壓力的屬性和能力,其作為一種個人優勢資源,有助于患者克服心理困擾,呈現良好的適應狀態,減輕復發恐懼并保持良好的行為習慣[6-8]。本研究探討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和健康促進行為之間的關系和作用路徑,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法,于2022年6月至10月選取廣西某三甲醫院神經內科和康復醫學科250例老年腦卒中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經臨床診斷為腦卒中[9];(2)年齡≥60歲;(3)具備正常的理解和溝通能力;(4)病情平穩,生命體征正常;(5)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自愿參與。排除標準:(1)有意識障礙或精神病等患者;(2)有惡性疾病或合并其他臟器損傷者。
1.2 方法
1.2.1 患者一般情況調查表 采用自制的患者一般情況調查表收集患者的一般情況,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家庭人均月收入、醫療支付方式、疾病分期、發病次數、病程。
1.2.2 健康促進生活方式量表Ⅱ(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Ⅱ, HPLP-Ⅱ) 采用HPLP Ⅱ評估患者健康促進行為水平。該量表包括人際關系、營養、健康職責、運動鍛煉、壓力處理和自我實現6個維度,共52個條目。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每條目評分1~4分,總分52~208分,得分與健康促進行為水平呈正相關。該量表Cronbach α系數為0.93[10]。
1.2.3 恐懼疾病進展簡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FoP-Q-SF) 采用FoP-Q-SF評估患者復發恐懼水平。該量表包括生理健康和社會家庭2個維度,共12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每條目評分1~5分,總分12~60分,分數和復發恐懼水平呈正相關,≥34分提示心理功能失調。該量表Cronbach α系數為0.883[11]。
1.2.4 中文版家庭彈性量表簡化版(Shorten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 FRAS-C) 采用FRAS-C評估患者家庭彈性水平。該量表包括家庭溝通與問題解決、利用社會資源和持有積極看法3個維度,共32個條目。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每條目評分1~4分,總分32~128分,得分和家庭彈性水平呈正相關。該量表Cronbach α系數為0.96[12]。
1.2.5 資料收集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50份,收回有效問卷232份,有效回收率92.80%。研究開始前對調查人員進行培訓,統一指導語,進入病房對符合研究標準的患者進行問卷調查,研究過程遵循知情同意原則、自愿原則和匿名原則。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6.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兩組間均數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數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檢驗各變量間的關系,運用Process 3.3插件中的Model 4和Bootstrap程序分析復發恐懼在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間的中介效應。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研究對象的一般資料 在老年腦卒中患者中,男性152例(65.52%),女性80例(34.48%);年齡60~93(69.95±7.82)歲;學歷:小學及以下63例(27.13%),初中85例(36.65%),中專及高中66例(28.46%),大專、本科及以上18例(7.76%);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元61例(26.29%),2 000~4 000元103例(44.40%),>4 000元68例(29.31%);醫療支付方式:城鎮職工醫療保險133例(57.33%),城鎮居民醫療保險25例(10.77%),新農合47例(20.26%),離休干部27例(11.64%);疾病分期:急性期73例(31.45%),康復期57例(24.57%),后遺癥期102例(43.98%);發病次數:首次發病186例(80.17%),2次發病30例(12.93%),3次及以上發病16例(6.90%);病程:<6個月100例(43.10%),6~12個月17例(7.33%),>1年115例(49.57%)。
2.2 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和健康促進行為現狀 老年腦卒中患者HPLP-Ⅱ總分為(105.00±14.14)分,FoP-Q-SF總分為(20.69±6.04)分,34分及以上患者7例(3%),FRAS-C總分為(102.57±16.48)分,詳見表1。

表1 老年腦卒中患者HPLP-Ⅱ、FoP-Q-SF、 FRAS-C得分情況 (n=232,x±s,分)
2.3 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的關系 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與健康促進行為、家庭彈性均呈負相關,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呈正相關(均P<0.05),詳見表2。

表2 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的關系 (r)


表3 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間的中介效應
3 討 論
3.1 老年腦卒中患者健康促進行為現狀 本研究中老年腦卒中患者健康促進行為得分為(105±14.14)分,低于相關研究結果[13-14],說明老年腦卒中患者健康促進行為總體水平偏低,需要進一步提高,這與本研究選取對象為老年患者,其獲取健康信息的能力、記憶力、自理能力水平下降有關。
在HPLP-Ⅱ各維度得分中,健康職責維度條目均分較低。一方面,老年腦卒中患者因為疾病導致心理依賴,在疾病的治療與康復過程中缺乏自信,習慣性地依賴家屬,無法獨自履行相應的健康職責。另一方面,本研究的對象是老年患者且大部分學歷水平不高,健康素養水平較低,患者關于疾病的知識儲備比較匱乏、獲取相關知識的渠道十分有限、學習能力較差,因此其健康責任和意識相對薄弱。此外,老年腦卒中患者運動鍛煉維度條目均分也較低。一方面,這與老年腦卒中患者運動能力有關,卒中導致的活動障礙使患者運動鍛煉的次數降低。另一方面,這與老年腦卒中患者運動意愿有關,與中青年患者相比,老年患者沒有贍養家庭的負擔,因此缺乏運動康復的動力,而且老年人的健康素養相對偏低,不能理解運動鍛煉的益處[15]。醫務人員應該動態評估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健康促進行為水平,分析其短板,根據分析結果采取措施改善患者的健康行為。
3.2 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的關系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復發恐懼與健康促進行為呈負相關,提示復發恐懼可以負向預測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健康促進行為。相關研究表明[16-17],復發恐懼和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呈負相關,復發恐懼水平越高,患者的健康促進行為越差。復發恐懼是一種心理負擔,如果長期處于恐懼疾病復發或進展的敏感狀態,患者可能出現抑郁、焦慮等現象[18-20],降低其依從性和自我護理能力,形成不良生活方式,進而降低健康促進行為水平。因此,應密切關注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心理狀態,及時識別復發恐懼狀況和心理功能失調的患者,采用認知行為療法、正念減壓療法、團體干預療法、接納與承諾療法、感恩療法等減輕患者的復發恐懼水平,使老年患者擁有更為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研究結果顯示,老年腦卒中患者家庭彈性與健康促進行為呈正相關,提示家庭彈性可以正向預測健康促進行為的水平。徐瑜的研究顯示[8],家庭彈性與自我管理存在正相關,家庭彈性水平越高,自我管理越好。Zhang等[21]的研究表明,更好的家庭功能與更好的心理狀態呈正相關,可激發患者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家庭是個體生活的直接環境,是獲得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良好的家庭彈性是一種強大的外部保護因素,可以培養患者的自我效能和心理韌性,增強在逆境中對抗挫折的能力,幫助老年腦卒中患者在疾病面前樹立健康生活的信念,并將這種信念投入到行動中,從而養成更為健康的生活習慣[22]。所以,應當注意發揮家庭資源的積極作用,采用整體性、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提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家庭彈性水平,使老年腦卒中患者擁有更強大的家庭支持,促進其健康行為的轉變。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家庭彈性在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與健康促進行為間起部分中介效應,效應占比為27%。由此可見,復發恐懼不僅可以直接影響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健康促進生活方式,還可以通過家庭彈性間接作用于健康促進行為。故而,醫務人員一方面可以采取措施減輕老年腦卒中患者復發恐懼水平,降低其對患者健康促進生活方式的干擾;另一方面還可以積極調動家庭的支持,提高家庭彈性水平,不僅能促使老年腦卒中患者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還可以緩沖復發恐懼的消極作用,讓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健康生活方式得到保障。
綜上所述,老年腦卒中患者健康促進行為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復發恐懼既可直接影響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健康促進行為,亦可通過家庭彈性間接影響老年腦卒中患者的健康促進行為。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處:其一,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對于三者間的因果關系驗證存在局限性,未來應開展隊列研究彌補此項不足;其二,本研究只在一家醫院的住院患者中進行取樣,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未來應在不同社區、不同地區、不同級別醫院開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