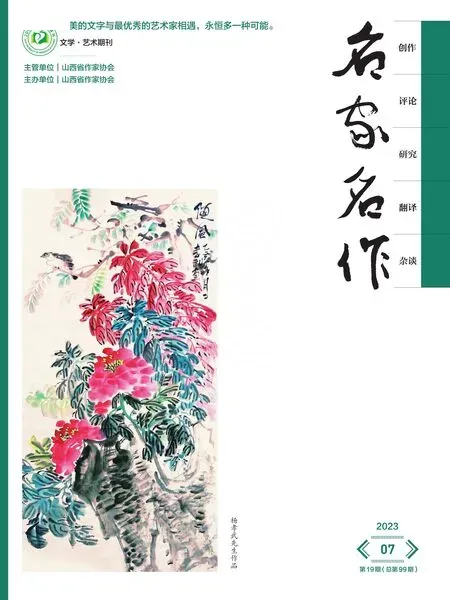喬葉《拆樓記》的曖昧分析、勞動分析與幸福觀念分析
黃張越
一、故事梗概
“我”是一個鄉村的叛逃者,輾轉離開家鄉十五年,在省會工作已十年。“我”姐姐考上鄭州某學校的大女兒,像一根紐帶把“我”和鄉村不可避免地聯系起來。高新區張莊的拆遷事件成為“我”頻繁往返于省會和鄉村的一個重要契機,在姐姐、姐夫的眼里,“我”就是他們的拆遷軍師。
為了姐姐能夠分得拆遷的紅利,改善他們一家的生活條件,與朋友“無敵”通氣后,“我”對姐姐想要在住房前加蓋房子的想法表示同意。后為了順利達成目標,“我”先是動員姐姐的鄰居趙老師一起說服村支書的弟弟王強加入我們,這樣村支書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然后我們擺設“鴻門宴”,在“鴻門宴”上王強同意和我們一起行動。因為農民的普遍心理,想要一起加蓋房屋的四戶人家不愿意借太多錢給王強,最終“我”發話,每戶人家必須拿出兩萬元。看到有利可圖,姐姐這一排上的十六戶鄰居全都或借錢、或合資,用盡各種辦法往外加蓋。
過了幾天,上頭的告示說要拆遷了,“我”召集大家開了個會,但是心中一片茫然,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上頭也從王強這里開刀,護房幫一致對外,安排人員在王強家外邊輪流值夜班。但是為了被扣留的哥哥能夠回家,王強最后還是允許制服幫把加蓋的房子拆了。護房幫里暗流涌動,大家都不想讓對方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利益,寧愿大家什么都沒有。
姐夫、趙老師等一行五人到國家信訪局上訪,收到了回信,但唯一沒拆的姐姐一戶還是被上頭不斷做工作。“我”在此期間動用了大量人脈,與相關負責人談過張莊拆遷這件事,在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不管是高新區政府還是老百姓都不容易。但是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讓姐姐放棄,最后用內置攝像頭作為迎戰上頭的殺手锏,為姐姐爭取到了六萬塊錢的宣傳費,姐姐也把房子拆到了五米界限。區里最終同意了十六戶人家統一把房子建到五米處。經歷了張莊拆遷事件,“我”的心境發生了變化……
二、曖昧分析
《拆樓記》聚焦人、事、物之間的曖昧,在曖昧分析中反思社會現象,探討人心、人性、制度的制約與羈絆。
(一)“我”與農村身份關系的曖昧
這里的農村身份指“我”自身隱含的農村身份和“我”對農村身份的其他人的態度。“我”是鄉村的叛逃者,如果沒有姐姐的女兒以及姐姐家房屋拆遷事情的發生,“我”大概只有清明上墳或是春節走親戚時才會回到農村。但“我”因為農婦的妹妹、鄉村的女兒的身份,在張莊拆遷的這一段時間,常常往返于鄉村與城市。
“我”雖然長期生活在省會,但是農村與農村身份在某些時刻還是羈絆著“我”、捆綁著“我”。“我”對農村身份的曖昧,是內心對農民身份的隱約反感與對骨子里就流淌著農民血液的無可奈何。這使“我”默許了姐姐為了獲得更多賠償款進行的違建活動,并且為姐姐能夠順利加蓋房屋出謀劃策——找到趙老師做同盟,擺設“鴻門宴”邀請村支書的弟弟王強,勸解各家集資拉王強入伙,向城里的朋友打聽有關拆遷的消息……在加蓋房屋的事情上“我”一方面明知故犯,知道這是違法行為,知道這樣做違反理性、違反制度,但對農民身份的曖昧,對姐姐留存的一份親情,使“我”還是選擇幫助農民。
在幫助農民的過程中,“我”卻又對農民“寧可我得不到也不能讓你得”“不愿吃虧”“思維單純可笑”的人性黑洞加以批判,同時也毫不避諱地揭示了自己的冷漠、虛偽、狡詐。姐姐想讓“我”在鄉村住一個晚上,“我”卻萬般推辭,到底還是回去了,只因鄉村的寒夜太冷,“我”怕自己會感冒。由此可見,“我”對農村的生活環境已經感到不適應和陌生,這變相表現出“我”內心對鄉村身份的隱隱抗拒,因為抗拒,所以連一個晚上都不愿意委屈自己,“我”充當城市人已經太久,久到成為習慣。當“我”接近省信訪局的大門,被保安當作上訪者時,“我”感覺到了屈辱。由此可見,“我”不屑于與農民為伍,對農民身份有著一種天然的鄙視,雖然“我”馬上進行了反思,不敢想下去,但“我”的潛意識還是出賣了自己內心尊卑貴賤的標準。
對農民身份的曖昧必然造成偏見和局限,對農民的同情和厭惡,對自身的理解和唾棄,是人性的微妙、身份的割裂,在偏見、局限、微妙、割裂中一次次地重塑自身,體現出人物的豐滿和真實。一次次內心糾結、一次次自我拷問,最后演變成“我最知道的是,張莊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樣”①喬葉:《拆樓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第262 頁。。
(二)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曖昧
在我們的初始印象中,農民與土地之間密不可分,但隨著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變得復雜,土地被道路、商品房等逐漸占據,農民似乎不再扎根土地,而是想著通過土地來謀取更多利益。
因為高新區的建設需要土地,所以高新區政府要對張莊、喬莊、田莊等村莊進行拆遷。然而喬莊“猛”、田莊“橫”,拆遷隊在這兩個村莊都摔了跟頭、鎩羽而歸,那么只能先拿不猛不橫的張莊“開刀”。拆遷的事情已經無可爭議,那么如何在拆遷中得到更多賠償款成了農民思考的頭等大事。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不再純粹,未來路綠化帶的這一長綹土地就要被加蓋的房屋吞噬,農民就要榨盡土地乳房中的最后一滴乳汁了。
為了讓王強加入加蓋房屋的隊伍,“我”提議每戶借給王強兩萬元,不過各戶人家為了不讓自己吃虧,就讓王強打了借條。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談及“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②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3 頁。。這里的借條行為是對鄉土社會的反叛。由此窺見,鄉土社會正在逐步瓦解,鄉村也正在逐漸失落,農民與土地的曖昧關系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變成沒有關系。社會的發展對農村的破壞、對農民的重塑似乎不可避免,就像賈平凹的《極花》一樣,《拆樓記》也同樣反映了農村、農民該何去何從這一問題。
其實,村民的內心深處多多少少還是眷戀著土地的,畢竟就連“我”這個“鄉村的叛逃者”,兒時對土地的記憶也是十分美好的,幼時還寫過一篇贊美土地的作文——《親愛的土地》,更何況仍然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姨媽在市軋鋼廠退休后,因為和小兒媳婦鬧矛盾,便回到了張莊,張莊是她最后的避風港灣。在拆遷政策對村民不利的情況下,趙老師帶領大家解讀各種法規、條例,并且拿出珍藏的合同書增強大家的信心。為了土地拆遷問題,一行五人甚至去往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上訪。雖然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利益的驅使,但是對生活的土地的感情,我相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三、勞動態度、幸福觀念分析
(一)農村老人對新時代的態度和幸福觀念
1.“我”的親姨媽
姨媽在市軋鋼廠退休且姨父去世后,因為和小兒媳婦鬧矛盾便回到了張莊。姨媽雖然因為蓋房子的事情使得高血壓發作,躺在了病床上,但是她活得自由自在,充滿生機和活力,她在農村生活中有一種怡然自得的幸福感。在拆遷隊與護房幫的爭論中,姨媽蒼老、嘶啞、憤怒的聲音總是歷歷可辨。姨媽在村子里的“潑婦樣”體現了她在鄉村生活中的活力與矍鑠,由此可知新時代限制了她的發揮,她不適應新時代。
2.趙老師
文中趙老師對“被上樓”事件的看法反映出農村老人對新時代的不適應。“被上樓”事件指村子集體搬遷到安置房中。趙老師認為農民生活了一輩子,出門就是地,是平展的田野,“被上樓”后農村熟悉的風景就再也見不到了,原先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也不再能夠實現,而且還要交水費、物業管理費、衛生費……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對農民的精神也會產生影響,農民被束縛、被指揮,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趙老師對“被上樓”的看法也反映出他的幸福觀念。他認為勞動是本本分分的農村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勞動人民離不了土地,離不了勞動,勞動就是幸福,生活方式的延續就是幸福。
3.李老太
上訪的李老太是被迫適應這個新時代的。因為上頭的政策,李老太成了釘子戶,上訪三次終于勝利。李老太從小移民的生活經歷,讓她特別熱心腸,誰家有冤屈想要上訪,她就帶著人家去。李老太幼年的移民經歷和年老時的上訪經歷都是時代變遷的結果,并不是自愿為之,所以李老太只是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不受侵害不得不適應新時代,她的幸福是堅持不懈的成果。
4.五嬸
五嬸一看到“我”就開始傾訴她的二女兒去年癌癥去世的痛苦,因為“我”和她的二女兒是小學的前后桌,她認為“我”能懂得她的悲傷,與她產生共情。對失去女兒的五嬸來說,有個訴說的對象進行家長里短的吐露,能為平凡的生活增添傾訴的渠道,得以釋放心中的苦悶就是幸福。小時候每年夏天,五嬸給“我”和她的二女兒用指甲花染指甲,這是一種就地取材、愉悅自己的幸福。
從上述四個例子可以得出,時代的滾滾車輪無情裹挾著農村老人,多數老人一輩子與農村、鄉土為伴,內心并不太愿意有起起伏伏的變化,安于農村生活,但是不斷發展的現實也讓他們明白,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有的希望這個變化來得再慢一點,有的已經被迫卷入變化中。
老人在土地上生活的時間越長久,對土地的感情也就越深厚,同時老一輩往往安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勞動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他們感受幸福與踏實的源泉。
(二)年輕人對于土地勞動的態度與幸福觀念
1.“我”
“我”是鄉村的叛逃者,只要有路,只要有車,只要有盤纏,只要有體力,只想越逃越遠。“我”與農民之間橫亙著體積龐大的生疏,對基本的土地勞動、農業生產知識都不清楚,“我”會問一些在農民看來很是簡單的“黏玉米”“磨房磨面”的問題,“我”已經與土地勞動完全脫節。
“我”并不認同勞動等于獲得幸福的觀念,“我”在心底是不太看得起從事土地勞動的農民的。“我”的姐姐一輩子在農村,但是很多時候都需要“我”接濟她,她的土地勞動所得根本無法保障意外所需的支出,就連加蓋房屋的錢也是“我”給她的,由此可知農村勞動并不能獲得較為富足,起碼是有存款應對突如其來的變故的生活。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感到平常的幸福也是表面的,當遇到生活困境時,幸福就會像泡沫一樣一觸即破。同時,在省信訪局門口,當“我”被保安認為是農民時,“我”很羞愧,從中也可以看出“我”不認為勞動能夠帶來幸福。
姐姐給“我”烙的油餅、蒸的饅頭、收的土雞蛋這些鄉下吃食,讓“我”看不順眼鄭州的食物,但這只是對伴隨自己長大的家鄉味道的懷念。“我”并不可能因為這些食物就愿意放棄城市工作回到農村勞動,“我”連一個晚上都不愿意住在農村,更不會也不愿做一個農民。“我”也承認自己是一條離家之犬,農村總是讓我不由自主地惦著、想著,但是你要讓我說愛這個村莊,我卻怎么也說不出口,我無法真正愛土地、愛土地勞動、愛農村、愛農村生活了。
2.王強
王強以前流轉各地打工,后來帶著媳婦回到村里,在水泥廠勞動。勞動是他們一家的生活來源,他和妻子還有兩個孩子雖然沒有太多錢,但是一家人其樂融融。對王強來說,勞動帶來家的幸福,帶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幸福。
3.小換
“東邊半個院子都被柵欄圍了起來,里面全是雞。院子里還扯著兩根長長的晾衣繩,上面晾著被子、褥子和一些用碎布拼貼起來的五顏六色的小方棉墊。我走近柵欄,看著那些雞。很久沒有看到過雞了,有些稀罕。每只雞,不論大小都羽毛閃亮,元氣充沛,非常漂亮,可見主人養得多么精心。”①喬葉:《拆樓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第161 頁。“雞們聽到她的聲音,頓時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她從墻邊的一個編織袋里抓起一把玉米粒,朝著雞們扔了過去,雞們頓時積極地叼了起來。”②喬葉:《拆樓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第162 頁。這是小換家的場面,足以看出小換的勤勞。小換對土地勞動非常虔誠,一點不馬虎,她精心飼養家里的雞,看著雞們的神情充滿了疼惜和慈愛,因為好品質的雞才能下出高質量的雞蛋,雞蛋是小換零花錢的重要來源,勞動改善了小換的生活條件,給小換帶來了幸福。雞蛋漲價了,但是小換還是原價賣給我和姐姐,這是鄰里之間的友愛。雖然小換家里是低保戶,但她還是那么淳樸,在自己生活不易的情況下,還要送給我們兩個雞蛋。她通過自己的勞動經營著不幸的家庭,活出了自己的尊嚴和幸福。她甚至還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開導我們:“其實,現在咱們的日子也還不錯,折騰太過了也不好……”③喬葉:《拆樓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第166 頁。可見小換對現在的生活還是滿意的。
四、結語
從生活在城市的“我”與生活在農村的王強、小換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城市里有一份穩定工作的“我”并不認為土地勞動能夠得到幸福,而似乎并沒有多少家底的王強、遭遇許多不幸的小換反而認為土地勞動能夠獲得幸福。
我想這是因為敘述者“我”已經被城市思維啟蒙和馴化,“我”懂得更多了,對幸福的要求自然遠遠高于農村年輕人,所以對王強而言家庭的幸福,對小換而言低保的幸福,是遠不及“我”頭腦中的期望的,由此造成“我”的悲觀,不認為勞動是幸福的。而對于靠自己的勞動養活一家人的王強和小換,他們覺得通過自己的努力過日子就是幸福的。
總而言之,因為王強和小換受到的啟蒙較少,所以對于幸福的定義相對簡單明了,看待幸福的問題更加低標準,而“我”獲得的知識和增長的眼界,使自己對自身和外在的本質屬性看得更加透徹,對理想化的生活要求越高,現實往往越達不到這樣的要求,所以使“我”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