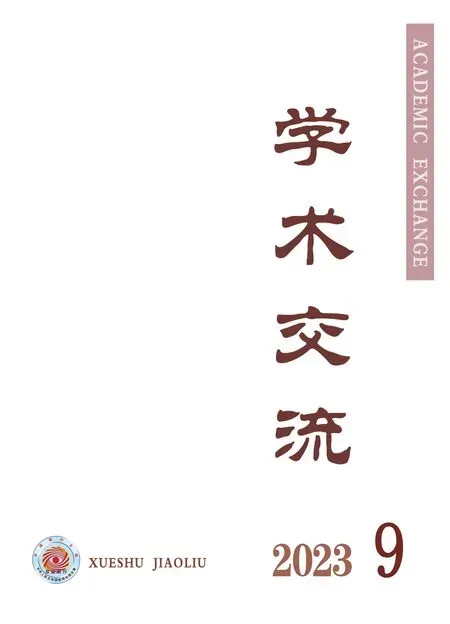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走向:技術(shù)驅(qū)動與范式創(chuàng)新
黃 松,譚 騰
(同濟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上海 200092)
一、研究緣起: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
2023年6月2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強調(diào),要“共同努力創(chuàng)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shè)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1]。構(gòu)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對于提高我國文化建設(shè)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創(chuàng)新力具有重要意義。當(dāng)今,以ChatGPT為代表的強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展開對文化生產(chǎn)與傳播等領(lǐng)域的生態(tài)級變革。在此背景下,建設(sh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既需審思時代之“變”,深化對文化建設(shè)的規(guī)律性認識,又需把握中華文明演進之“新”,更好地擔(dān)負起新的文化使命。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響與沖擊,如何具體展開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范式創(chuàng)新,成為我國主動回應(yīng)時代之“變”、縱深拓展文化之“新”的重要課題。如何解讀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具體意蘊,理解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歷史邏輯,是回應(yīng)這一課題的首要步驟。
(一)時代之“變”:ChatGPT開啟的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
首先,從聯(lián)系性的角度理解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三者的關(guān)系(見圖1)。1956年“人工智能”的概念被首次提出,[2]近年來伴隨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海量數(shù)據(jù)集成、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優(yōu)化以及并行計算廉價化[3]三個方面的迅速發(fā)展,其在社會生產(chǎn)生活的多個領(lǐng)域中發(fā)揮重要的實用價值。按照功能價值可將人工智能技術(shù)劃分為分析式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4],前者主要識別檢測和分析已有數(shù)據(jù)或問題,后者則可以通過創(chuàng)建類似其所訓(xùn)練的數(shù)據(jù)的新穎數(shù)據(jù)來完成模仿與創(chuàng)造。按照全球著名IT研究機構(gòu)Gartner給出的定義,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可以通過各種機器學(xué)習(xí)方法從數(shù)據(jù)中學(xué)習(xí)對象的特征,進而生成全新的、完全原創(chuàng)的、逼真的內(nèi)容(如文字、圖片、視頻)的人工智能。[5]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主要應(yīng)用場景包括圖像生成、自然語言處理、音頻處理、游戲開發(fā)、醫(yī)學(xué)領(lǐng)域、廣告推薦、金融領(lǐng)域和設(shè)計領(lǐng)域等,[6]因強大的技術(shù)能力、多層次的功能維度以及廣闊的應(yīng)用前景,被Gartner列為2022年頂級戰(zhàn)略技術(shù)之一。ChatGPT是人工智能實驗室OpenAI于2022年11月推出的一項基于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預(yù)訓(xùn)練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產(chǎn)品,因顯現(xiàn)出強智能性和功能多樣性的技術(shù)特征[7]開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新篇章。ChatGPT的主要功能包括完成連續(xù)性對話、回答用戶各類提問、進行文本翻譯創(chuàng)作等。從更深層的技術(shù)影響意義看,ChatGPT還掀起了人工智能時代技術(shù)迭代的新一輪熱潮。緊接于ChatGPT的誕生,OpenAI在2023年3月又發(f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GPT-4,不僅新增了識別分析圖像的能力,還在高級推理能力上作了升級,整體應(yīng)用到Bing搜索引擎和Office辦公套裝中。中國公司百度于2023年3月發(fā)布了中國版的ChatGPT——文心一言,標(biāo)志著國內(nèi)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里程碑式突破。
其次,從比較性和超越性的角度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于分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ChatGPT于以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先進。相比于智能翻譯、Siri、微軟小冰等人工智能應(yīng)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在于算法、算力和數(shù)據(jù)三方面的進步,其中算法層面的突破最為關(guān)鍵。[8]算法是驅(qū)動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執(zhí)行處理的背后規(guī)范,起著架構(gòu)訓(xùn)練模型的重要作用;算力源于芯片,構(gòu)成算法和數(shù)據(jù)的基礎(chǔ)設(shè)施,算力的大小決定數(shù)據(jù)處理能力的強弱;數(shù)據(jù)包含各種語音、文本、影像,是算法運行的補給“飼料”。基于以上要素的差異性,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的是“生成式建模”,相較于分析式人工智能采用的“判別式建模”,[9]顯現(xiàn)出更強大的學(xué)習(xí)能力和創(chuàng)造性。比如,向這兩類人工智能同樣提供一首李白的詩的文本,分析式人工智能僅能識別判斷出作者為李白,生成式人工智能則能將文本學(xué)習(xí)內(nèi)化成一套類似于喬姆斯基所說的“生成式語法系統(tǒng)”,即語言交流的對象在接受一套既定的生成原則后可以直接生成屬于自己的語法規(guī)則,[10]另行創(chuàng)作出一首風(fēng)格近似于李白的新詩。ChatGPT之所以被視作一項革命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產(chǎn)物,除了其兼?zhèn)潺嫶蟮臄?shù)據(jù)訓(xùn)練庫、Transformer算法、AI預(yù)訓(xùn)練模型、多模態(tài)數(shù)據(jù)協(xié)同能力及自身建構(gòu)起堅固的算法核心壁壘,更關(guān)鍵的原因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能提供“類人體驗”的高度仿真性,即用戶在與ChatGPT對話時有接近與真人對話的交互體驗感,不容易感知到人工智能的機器屬性。現(xiàn)今的ChatGPT能夠提供情感反應(yīng),越來越多的人甚至把ChatGPT當(dāng)作樹洞,向其尋求關(guān)于愛情、友情、親情等感性話題的答案。從這個角度看,ChatGPT消弭了以往智能對話機器人存在的“對話的形式凌駕于功能之上,答案的不精準(zhǔn)、不穩(wěn)定感逾越于獲得感之上”[11]問題,進一步縮小了擬人度的偏差。二是逐漸走向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hatGPT集合了更多層的功能維度,包括但不限于編程、創(chuàng)作詩詞劇本、設(shè)計廣告文案、撰寫文獻綜述、作醫(yī)療診斷、協(xié)助企業(yè)進行戰(zhàn)略分析,體現(xiàn)出全面通達的能力,從而進一步?jīng)_擊“智人”的自我界定。[12]此外,由于ChatGPT使用的低門檻、開放性和便捷性,幾乎每一個與智能設(shè)備接軌的用戶都能享受其科技成果,在較高程度上推進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化與生活化,呈現(xiàn)出一種動態(tài)嵌入式的社會中介作用。
立足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視角,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指向兩層重要意蘊。其一,ChatGPT等產(chǎn)物正以前所未有的科技能量和覆蓋速度,驅(qū)動多個領(lǐng)域朝向更高階的數(shù)字化和智能化轉(zhuǎn)型升級,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象征的數(shù)字化變革,恰與當(dāng)今運用數(shù)字化手段推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的普遍共識[13]形成適配關(guān)系。據(jù)Gartner估計,2025年將有超過10%的數(shù)據(jù)由人工智能生成,這預(yù)示著一個新時代——人類與機器協(xié)作時代的到來。[14]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即將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新基建的情況下,基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亦需在互聯(lián)網(wǎng)場域中建構(gòu)的現(xiàn)實,推進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中的創(chuàng)新嵌入和深度應(yīng)用,是新環(huán)境下開展民族文化工作的必然挑戰(zhàn),也是調(diào)整共同體建設(shè)戰(zhàn)略中需把握的機遇。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與人類知識和經(jīng)驗進行交互對接的過程中,驅(qū)動我們重新思考“人的本質(zhì)”之問,映射到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時,具體指向共同體內(nèi)每個獨立個體的命運,也對應(yīng)整個共同體的未來境遇。人從無中生成自己本質(zhì)的過程是世界本質(zhì)辯證發(fā)展的宏大歷史的一個環(huán)節(jié)。[15]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并非一個靜止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流動歷史中的變化產(chǎn)物。正如機械化于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電氣化于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信息化于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當(dāng)今智能化的代表產(chǎn)物,對應(yīng)了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并預(yù)示著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新變革。因此,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前景的思考,無法脫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層本質(zhì)審視,其可以重塑我們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認知的新框架,且助力我們觸及更前瞻的視野以探索新時代下的歷史使命。
(二)文化之“新”: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邏輯理路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是必由之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邏輯主要包含了兩層深意:一是基于中國自身國情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形成邏輯,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相結(jié)合的邏輯。
參照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16]。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概念可以分解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三個具體要素,基于要素聯(lián)系組合,層層遞進把握“共同體”到“文化共同體”再到“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內(nèi)涵延伸,可理解為一種依賴人群關(guān)系和多元紐帶(如血緣地緣關(guān)系、共同歷史記憶和傳統(tǒng)習(xí)慣等)且能提供身份歸屬感的綜合體。文化共同體基于共同體的概念,強調(diào)了文化價值同質(zhì)性的紐帶作用,即“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會群體,是一種特定文化觀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組織層面上的有機統(tǒng)一體”[17],其本質(zhì)是一種隸屬人類社會共同體中高級形式的“精神共同體”。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在文化共同體的概念范疇中聚焦“中華”與“民族”,既包含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亦凝聚了56個民族多元化的思想、精神、情感、儀式。綜上所述,我們可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理解為建立于共同的歷史經(jīng)歷與記憶、多元統(tǒng)一的文化思想情感、中華各民族文化認同與整體國家認同,具有文化價值同一性和高度民族凝聚力的“靈魂共同體”。[18]
一方面,時代背景的變化導(dǎo)致民族文化記憶、情感和價值的呈現(xiàn)的流動性,因而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在不同階段對應(yīng)差異化的具體內(nèi)涵。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分裂、民族沖突時期,基于民族禮儀區(qū)分的“華夷之辨”觀念初現(xiàn)一種“族性識別”下的文化認同。至20世紀(jì),中國受西方技術(shù)與思想文化的猛烈沖擊,團結(jié)各民族一致對外成為主流情感,維護整個中華民族的身份獨立性與獨特性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因而展開了“中西之辨”的價值分殊式觀念,顯現(xiàn)出強烈的國族色彩。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中國進入重發(fā)展的和平建設(shè)時期,“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的認同浪潮興起,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與包含和而不同之文化愿景的“十六字箴言”[19],指向各族人民和諧共處、各族文化求同存異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方向。現(xiàn)今,立足全球化縱深發(fā)展階段,ChatGPT代表的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刷新著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時代背景,從技術(shù)到社會再到民族心理逐步蔓延其影響,加速傳統(tǒng)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模式的重塑。基于既要不斷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又要在暗流涌動的國際政治環(huán)境中穩(wěn)固文化傳播話語權(quán)的復(fù)雜國情,基于對更高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情感追求以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價值升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必然邁入新的階段,須主動應(yīng)對技術(shù)變革中的機遇和風(fēng)險,既要在ChatGPT代表的西方技術(shù)文明的新一輪滲透中筑牢自身的文化根基,也要著眼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中國特色化推進,包括核心技術(shù)由中國主導(dǎo)、生成內(nèi)容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拓寬了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創(chuàng)新的實踐道路。其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動“真正共同體”思想嵌入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完善其組織邏輯和空間邏輯。馬克思認為“真正共同體”能夠滿足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和全面發(fā)展,“人不是在某一種規(guī)定性上再生產(chǎn)自己,而是生產(chǎn)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jīng)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20],這與我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fā)展理念相契合。無論處于哪一科技發(fā)展階段,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始終離不開個人與共同體的關(guān)系處理。人與共同體是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激發(fā)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活力需重視對個體的賦能,保障其作為文化參與主體的足夠權(quán)力,刺激其迸發(fā)出全面性的生產(chǎn),為自由人的培育及趨于“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共同體建構(gòu)提供條件。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還印證了馬克思對傳統(tǒng)共同體向現(xiàn)代共同體轉(zhuǎn)化的看法,“從組織形態(tài)上講,就是從無分化的整體到各領(lǐng)域分化再整合的過程”[21]。技術(shù)架構(gòu)起新的共同體成型環(huán)境,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場域從線下拓展至線上,且可以顯現(xiàn)出一種分化又整合的狀態(tài),個體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的身份趨于多重性。比如同一個體,在現(xiàn)實空間可能基于地緣、身份因素與一部分人構(gòu)成緊密的共同體聯(lián)系,在虛擬空間中又可以和另一部分人達成某種一致的價值認同。在空間邏輯上,“真正共同體”思想包含了從地域性共同體走向世界歷史性共同體的趨勢判斷,結(jié)合中國具體實際,指明了從民族性到世界性的共同體影響建構(gòu)思路,即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不僅要作為全體中華民族認同與歸屬的凝結(jié),還要在開放擴大的生產(chǎn)、交往中將其影響力擴展至全球。其二,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打開審視科技發(fā)展影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辯證視野,拓展其再建構(gòu)范式的維度。馬克思主義時代化要求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發(fā)展著的時代背景、時代特征等相結(jié)合,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發(fā)展觀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蘊含的技術(shù)文明辯證批判思想仍可作為應(yīng)對當(dāng)代科技發(fā)展的方法論參考。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科技因素首先在工業(yè)生產(chǎn)中體現(xiàn)出來。[22]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歷經(jīng)了蒸汽機—電氣—信息技術(shù)—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四個創(chuàng)新階段。一方面,馬克思肯定了科學(xué)技術(shù)對人類文明的正面驅(qū)動作用:一是促成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發(fā)展,這也是實現(xiàn)“真正共同體”的前提。二是作為一種潛在生產(chǎn)力且通過知識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驅(qū)動生產(chǎn)效率的提高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社會生產(chǎn)力已經(jīng)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chǎn)出來”[23]785。生產(chǎn)力帶來的改變也影響著人的生活世界,技術(shù)變成人的生活的真正基礎(chǔ),意味著自然文明時代的 “自然人類生活世界”被現(xiàn)代技術(shù)改造為“技術(shù)人類生活世界”。[24]與此同時,馬克思也揭示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異化風(fēng)險,指出技術(shù)文明發(fā)展的歷史性限度:一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科技應(yīng)用導(dǎo)向?qū)θ说膭兿骱蛪赫ァH吮患夹g(shù)使用而不是人支配技術(shù),人在生產(chǎn)活動中的主體價值被異化,其主觀能動性和個性消退,“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個工人階級投入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23]61。二是權(quán)力滲透下技術(shù)對社會的控制。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統(tǒng)治階級逐漸利用技術(shù)實現(xiàn)了對自然的控制、再到對人類社會的控制。科技與資本、權(quán)力結(jié)合而成的控制也會不可避免轉(zhuǎn)化為對人的控制,滑向“單向度的人”和“單面性的社會”的雙重困境。
由此可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要產(chǎn)物,不僅為當(dāng)下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創(chuàng)新建構(gòu)提供了技術(shù)驅(qū)動,也暗藏技術(shù)異化的風(fēng)險。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構(gòu)的范式創(chuàng)新需辯證考慮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正反向影響,保障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穩(wěn)扎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與馬克思主義真理之上。當(dāng)前西方主導(dǎo)的ChatGPT之類產(chǎn)物是否會再現(xiàn)近代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沖擊值得國人關(guān)注與警惕,如何應(yīng)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潛在的風(fēng)險同樣值得研判。盡管當(dāng)前學(xué)界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研究涉及層次和角度已較為豐富,有基于行政管理、民族學(xué)、新聞傳媒、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等多種學(xué)科視角,但是,從緊扣時代脈搏的技術(shù)視角出發(fā)探究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設(shè)路徑仍存在理論上的空白。部分學(xué)者初步打開了將中華民族共同體與算法、元宇宙、智媒等技術(shù)元素相融合的研究思路,但在銜接技術(shù)與文化的基礎(chǔ)上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二者關(guān)系的文獻依然匱乏,由此指向本文研究的創(chuàng)新價值和應(yīng)用價值。
二、技術(shù)驅(qū)動: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作用機制
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即訊息”[25],任何新興媒介技術(shù)的出現(xiàn)都意味著新的作用關(guān)系及影響的產(chǎn)生。透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shù)屬性,剝繭抽絲地厘清技術(shù)對個體、社會生產(chǎn)及生產(chǎn)關(guān)系、群體文化心理的逐層滲透,并歸納組織出完整的作用機制(見圖2),是明晰該技術(shù)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新“訊息”之意義的關(guān)鍵,以及在該技術(shù)背景下推動共同體再建構(gòu)的前提。

圖2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作用機制
(一)賦能個體:文化參與主體的權(quán)力與能力變化
升級個體連接,驅(qū)動參與權(quán)力下沉。傳統(tǒng)線下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主要依賴官方主導(dǎo)的自上而下的單向模式,其影響力受限于核心參與主體的單一性。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雖降低了大眾參與意見表達與內(nèi)容生產(chǎn)的門檻,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去中心化的網(wǎng)絡(luò)社會結(jié)構(gòu)形成,凸顯文化參與主體的多元性,但專業(yè)知識和能力的差異性導(dǎo)致不同個體在話語聲量和實踐效能方面的不均衡,造成了“能力鴻溝”。例如,基于同樣的傳統(tǒng)搜索引擎和不一樣的提問輸入,知識基礎(chǔ)和語言能力處于相對優(yōu)勢的人群更容易實現(xiàn)信息資源的精準(zhǔn)獲得與二次創(chuàng)造,處于能力相對劣勢的人群則較難精準(zhǔn)駕馭一般性的客觀工具,從而滑向信息偏差與價值創(chuàng)造的低谷。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可促進“能力鴻溝”的彌合,任何個體都可以通過該類工具完成各種需求性或訴求性的提問和交流,擁有依照自我意愿、充分調(diào)動海量外部資源的平等機會與權(quán)利,且不受專業(yè)能力的局限。甚至,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個體知覺與連接能力的極大延伸中,前者能為后者提供超出其認知范圍的知識和經(jīng)驗,這意味著用戶媒體權(quán)力的上升[26]。伴隨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的勞動生活、消費生活、精神生活等多領(lǐng)域的影響延展,越來越多的民族個體得以掌握更豐富強大的價值表達及創(chuàng)造能力,從而驅(qū)動社會文化傳播權(quán)力下沉,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趨向生活化與大眾化的過程中,增強共同體內(nèi)部的緊密聯(lián)系與互通。
重塑人機關(guān)系,帶動協(xié)作能力提升。ChatGPT引領(lǐng)的高維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促使機器的角色從智能輔助走向全能代理,[27]一方面通過進一步簡化篩選、決策等環(huán)節(jié)提升人機協(xié)作的效率,另一方面通過賦能個體成長、重新拓展人的技能范圍提供人機共生的契機。馬克思曾提出“物的依賴性”,具體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者都必須借助物的媒介才能滿足生存和生活的需要。[28]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個體在與生成式人工智能交流過程中能快速獲得新的知識經(jīng)驗,趨于一種雙向成長從而淡化“物的依賴性”,機器在向智慧化和人性化深入發(fā)展中被建構(gòu)為共同行動的主體。在人機共生的理想狀態(tài)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存在是一股能不斷進化的,在保障中華各民族主體地位的前提下開拓文化生產(chǎn)生活實踐、提升文化創(chuàng)造力與想象力的后人類文明力量。隨著個體的協(xié)作能力提升,其扮演的文化角色也將受技術(shù)驅(qū)動而發(fā)生轉(zhuǎn)變,影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內(nèi)多元主體的關(guān)系架構(gòu)與作用發(fā)揮。“計算機進入語言過程會影響人們的邏輯思維,進而影響人們的視覺、聽覺、運動、語言等思想意識和知識狀態(tài)”[29],可以預(yù)見,基于對話交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個體的深度耦合,群體的思維模式與能力結(jié)構(gòu)將產(chǎn)生變化。在這種流動性的變化中,個體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一種被安排、被固定的狀態(tài),而轉(zhuǎn)向在數(shù)字空間展開更廣泛實踐的自由狀態(tài),可發(fā)揮出融合信息整合、內(nèi)容生產(chǎn)與傳播、二次生產(chǎn)等多環(huán)節(jié)參與的文化主體作用,其在共同體中的全面發(fā)展能力及個人自由性進一步彰顯,趨向于馬克思所指的“真正共同體”境界。
(二)變革生產(chǎn):文化實踐對應(yīng)的手段與形態(tài)升級
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發(fā)達生產(chǎn)力是構(gòu)建未來共同體的基礎(chǔ),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如果沒有這種發(fā)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30]。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文化生產(chǎn)鏈條,將推動生產(chǎn)工具的改進、生產(chǎn)資源的高效整合、產(chǎn)業(yè)文明的轉(zhuǎn)型升級,積極作用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過程建設(shè)與成果轉(zhuǎn)化。
一是作為直接生產(chǎn)工具與間接生產(chǎn)工具,對文化生產(chǎn)實踐的改進。一方面,ChatGPT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直接介入中華民族文化相關(guān)的內(nèi)容生產(chǎn),提升虛擬世界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chǎn)能力,[31]豐富民族文化的網(wǎng)絡(luò)信息庫并起到擴充話語體系的作用。ChatGPT類生成式人工智能還可與其他生產(chǎn)工具或傳統(tǒng)文化生產(chǎn)方式相結(jié)合,帶動原有硬設(shè)施和軟設(shè)施的升級并發(fā)揮疊加生產(chǎn)效益。比如將ChatGPT與線下民族文化活動建立映射關(guān)系,結(jié)合數(shù)字孿生和數(shù)字線程技術(shù),創(chuàng)造模擬文化活動全生命周期的全息數(shù)字空間,[2]借助ChatGPT的智能化分析展開對活動影響的預(yù)測與方案的改進,使其向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精準(zhǔn)提升文化效益的目標(biāo)不斷優(yōu)化。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shù)能夠被文化生產(chǎn)中的勞動者所掌握進而被運用于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32]間接發(fā)揮提升生產(chǎn)力的效能。比如在民族文藝創(chuàng)作的管理領(lǐng)域中,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shù)載體向其輸入有關(guān)民族價值觀的共識機制,以保障其生成內(nèi)容符合意識形態(tài)需要,在此基礎(chǔ)上整合區(qū)域群眾的精神文明需求、文藝創(chuàng)作者的個性化訴求、作品類型特征、文藝發(fā)展目標(biāo)等多維度信息,智能生成針對民族文藝創(chuàng)作管理者的、全面具細化的智能培訓(xùn)系統(tǒng),提升其信息掌握能力及管理實踐技能,使其更精準(zhǔn)地把握民族文藝創(chuàng)作的整體前進方向與階段調(diào)整目標(biāo),有效促成勞動資料的優(yōu)化配置及利用、勞動者主觀能動性與勞動對象的接合,通過拔高整體管理與治理水準(zhǔn),深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認同,增強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向心力。
二是作為整合生產(chǎn)資源的智慧容器,對文化記憶和經(jīng)驗的保存與激活。一方面是針對真理性或經(jīng)典性的知識經(jīng)驗。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人類在口述時代和印刷時代的經(jīng)驗代際傳承難題,不僅可以完整保存?zhèn)€體和群體的龐雜記憶并使之永久存在于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據(jù)庫中,而且能滿足后代人對前代人知識經(jīng)驗的穩(wěn)定延續(xù)、反復(fù)抓取和循環(huán)利用,完成知識的遞延式創(chuàng)新發(fā)展,即避開了歷史文脈的斷層問題,下一代人不需花費太多時間對前人文化成果梳理和消化,而是直接立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構(gòu)建出的強歸納性、高時效性、完整系統(tǒng)化的信息基礎(chǔ)之上。文化領(lǐng)域中的重大突破性經(jīng)驗、經(jīng)典成果和權(quán)威知識若能經(jīng)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處理被固化下來,或轉(zhuǎn)化為新的文明形態(tài),將大大提升中華民族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的速度。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文化記憶不會被塵封在故紙堆中,其建設(shè)經(jīng)驗也不會隨專家的離去而消失。基于對文化資源的保存,除了文化生產(chǎn)中的直接還原,生成式人工智能對經(jīng)典的模仿與再現(xiàn),也體現(xiàn)出對文化記憶和經(jīng)驗的盤活,能夠鞏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靈魂,促成文化資源的靈活轉(zhuǎn)化與再生產(chǎn)。例如,有用戶曾設(shè)定某一主題,讓ChatGPT圍繞該主題模仿李白的風(fēng)格進行詩創(chuàng)作。ChatGPT基于對李白詩風(fēng)的模仿所完成的創(chuàng)作,本質(zhì)即一種融合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雙重語境的銜接式內(nèi)容生產(chǎn)。另一方面是針對多樣性包括邊緣性的民族文化產(chǎn)物。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豐富意蘊包括了民族文化的多元統(tǒng)一和求同存異,“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33]。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偏向于普適性的信息喂養(yǎng)模式,即生成結(jié)果往往遵循一種普遍經(jīng)驗或主流價值,其提供的解決方案的細膩程度或者說個性化程度比較依賴用戶自身對理想最優(yōu)答案的主動追求,用戶在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連接互動中,需經(jīng)過信息接收、價值感知、需求匹配、輸入表達優(yōu)化、得到二次反饋的反復(fù)循環(huán)和摸索,才能實現(xiàn)自身細微需求與最終生成方案的精準(zhǔn)匹配。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于大數(shù)據(jù)、大算力和“中央廚房”式的云計算,能夠高效實現(xiàn)對個性化長尾需求的識別、聚合與匹配價值生成。基于以上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下的多民族文化發(fā)展需求能夠得到更寬廣的連接覆蓋和更精細的連接回應(yīng),許多在傳統(tǒng)場景中易被忽視被排拒的小眾民族話語、遺產(chǎn)、創(chuàng)造等文化存在,可以受到更多的關(guān)注和倚重,演進成充盈中華民族共同精神文明家園的活化資源。
三是作為升級文化產(chǎn)業(yè)的驅(qū)動引擎,對中華民族數(shù)字文明形態(tài)的營建。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根本在于對民族文化內(nèi)涵的深入發(fā)掘,包括差異化與共享性的文化符號及民族形象的含義挖掘,能夠打牢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社會基礎(chǔ)和思想基礎(chǔ)。將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入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布局,有利于拓展產(chǎn)業(yè)鏈、激活新興產(chǎn)業(yè)、豐富產(chǎn)業(yè)生態(tài)。以ChatGPT為例,其關(guān)聯(lián)產(chǎn)業(yè)鏈已可拆分為上中下游三層:上游產(chǎn)業(yè)對應(yīng)芯片等硬件技術(shù)研發(fā)生產(chǎn)、內(nèi)容創(chuàng)作者、底層技術(shù)輔助工具等,中游產(chǎn)業(yè)主要對應(yīng)與ChatGPT產(chǎn)品直接相關(guān)的數(shù)字類產(chǎn)品,下游產(chǎn)業(yè)包括各類內(nèi)容創(chuàng)造及傳播平臺、第三方內(nèi)容服務(wù)機構(gòu)等。一方面是ChatGPT與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有機結(jié)合推動原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升級,比如好未來(學(xué)而思)和科大訊飛將ChatGPT用于學(xué)習(xí)機產(chǎn)品的研發(fā)迭代。另一方面是由ChatGPT衍生出的新文化產(chǎn)品與功能,助力文化產(chǎn)業(yè)的優(yōu)質(zhì)供給,比如將ChatGPT融入文旅數(shù)字人功能的構(gòu)想,由數(shù)字人擔(dān)任民族文化旅游景區(qū)的向?qū)Ы巧?為游客提供文化講解、即興答疑、路線規(guī)劃、互動討論等智能服務(wù),提升游客對當(dāng)?shù)孛褡逦幕牧私庹J同。綜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為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提供更靈活的內(nèi)容呈現(xiàn)手段,兼具理性與感性吸引力,優(yōu)化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價值表達方式。如尼葛洛龐帝所說,“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 使用的人越多其價值越低;比特可以由無限的人去使用, 使用的人越多其價值越高”[34]。在必經(jīng)的數(shù)字化時代潮流中,以數(shù)字文明形態(tài)保存與顯現(xiàn)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之生產(chǎn)成果,同樣遵循以數(shù)據(jù)為首要資源的規(guī)律,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將進一步驅(qū)動信息數(shù)據(jù)的共享范圍擴大,從而推進共同體在空間向度的包容開放與時序向度的繼往開來。
(三)重構(gòu)關(guān)系:智能連接中樞下虛擬共同體成型
虛擬共同體的本質(zhì),是現(xiàn)實個人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在個體價值取向和利益關(guān)系的導(dǎo)引下形成的新的組織形式和社會關(guān)系格局。[3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網(wǎng)絡(luò)場域中聚合了巨量的用戶數(shù)據(jù)和信息鏈條,可以成為承載并輸出虛擬群體情感與價值觀的中介樞紐,并推動散布網(wǎng)絡(luò)各節(jié)點的虛擬個體不斷匯合成穩(wěn)固的虛擬共同體,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得以突破時空限制,以更具流動性和互動性的形態(tài)從線下投射進線上,實現(xiàn)對共同體存在范圍的拓展。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縮短交流關(guān)系層級,“智能互聯(lián)”是虛擬共同體成型的架構(gòu)基礎(chǔ)。文化認同建立在社會共享的文化經(jīng)驗或體驗上,離不開個體在對外部感知與交流中方能完成的對自我身份意識的確認。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傳播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文化認同的重要條件。在以往關(guān)系層級過于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文化信息經(jīng)由不同人群不同傳播環(huán)節(jié)會受到較大的折損,不利于構(gòu)建趨向同一的價值觀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創(chuàng)造無限量的巨大信息網(wǎng)絡(luò),將從前無法納入其中的更加多維的關(guān)系連接納入人的實踐體系的可操控范圍,[36]不僅實現(xiàn)個體內(nèi)部要素與外部要素的更細顆粒度的連接,重構(gòu)個體在全連接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的狀態(tài)與結(jié)構(gòu)作用,還帶動了信息傳播模式從以往的層層遞進式傳播,轉(zhuǎn)向所有節(jié)點直接與生成式人工智能這一核心樞紐相連。從個體連接成群體,再聯(lián)結(jié)為更大規(guī)模的互聯(lián)互通的集合體,最終指向內(nèi)部關(guān)系更加緊密的虛擬共同體。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彌合網(wǎng)絡(luò)情感溝壑,“情感認同”是虛擬共同體成型的靈魂填充。情感認同是主體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作出的喜愛、認可、贊同、自豪等價值判斷與積極情緒體驗。[37]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能夠識別用戶情緒并提供相匹配的情感反應(yīng),從而在自然對話中與用戶建立親近的情感連接,進一步推動信息交互中的價值共識達成。基于智能互聯(lián)的信息結(jié)構(gòu),結(jié)合用戶共情與情緒輸出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滿足本族人對他族人的文化理解與情感想象,經(jīng)過和諧友好為導(dǎo)向的智能處理,降低以往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因信息傳播不可控造成的族際偏見與誤解,繞開現(xiàn)實中族際接觸的矛盾沖突,在虛擬環(huán)境中拉近各民族間的心理距離,提升各民族間的情感緊密度。
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構(gòu)文化共通路徑,“流動交往”是虛擬共同體成型的黏性成因。我國56個民族的文化演進與交融,本質(zhì)是辨證揚棄的“文化重構(gòu)”過程,包括共同利益、發(fā)展目的、文化符號的不斷重構(gòu)。在網(wǎng)絡(luò)空間組建起的共同體,面臨著比在現(xiàn)實空間更豐富多樣的文化接觸面,除了傳統(tǒng)的地緣、身份、宗教等相對固定的文化認同元素,趣緣、業(yè)緣、觀點立場等具有變化性的元素,也成為在流轉(zhuǎn)的網(wǎng)絡(luò)世界中牽系個體交往、增強群體黏性的重要因素。以上要素組成了促使不同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體間團結(jié)在一起的動力,而受網(wǎng)絡(luò)流動交往的影響,吸合虛擬共同體成型的核心點可能是興趣文化,可能是政治文化,可能是信仰文化,還可能是多重文化的疊加,等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這種流動交往后,可創(chuàng)造更多的文化內(nèi)容吸引點,比如發(fā)掘潛在共同話題、生成討論熱點、開拓意見分支,加速中華民族文化在網(wǎng)絡(luò)中的交流互動與重構(gòu)新生。
需要強調(diào)的是,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整體建設(shè)而言,對應(yīng)網(wǎng)絡(luò)主陣地的虛擬共同體和對應(yīng)線下主陣地的現(xiàn)實共同體,并非相互獨立的剝離式存在,而是顯現(xiàn)于不同場域的意識集合或精神文明集合。二者緊密聯(lián)系,相輔相成,且能夠相互映射,互作補充,一齊構(gòu)成完整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形態(tài)。當(dāng)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shù)驅(qū)動,助力中華各民族達到更高層次的互相接納與包容,走向更深厚的價值共識與情感凝聚時,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牢固性已然超越了其載體本身的意義。
三、困境觀照: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風(fēng)險生成
正如馬克思意指的科技發(fā)展正反效應(yīng),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作用機制肇始于激發(fā)個體活力、改善文化生產(chǎn)、緊密民族聯(lián)系的目標(biāo),但在現(xiàn)實中易引發(fā)技術(shù)控制、信息異化、認同解構(gòu)的負面效應(yīng),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梗阻。
(一)技術(shù)控制:工具依賴掣肘文化活力可持續(xù)
在馬克思主義視閾下,技術(shù)是包含肯定性“解放”力量與否定性“控制”力量的矛盾統(tǒng)一體。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變革文化生產(chǎn)方式的同時也可能破壞原有的文化生產(chǎn)秩序,在賦能個體的同時也可能誘發(fā)個體主體性被侵蝕的風(fēng)險。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控制”的概念,認為我們對技術(shù)的擁抱決定了我們必然與其相關(guān),從而成為它們的伺服機制。當(dāng)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構(gòu)的重要工具時,意味著它對中華民族文化生產(chǎn)與生活的多方位滲透,而不對其加以限制的滲透將會造成新的控制,包括對人的主體性的單向度控制與對共同體靈魂的單面性控制。
其一,對人的主體性的單向度控制,扼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多元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伴隨生成式人工智能運用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人無法置身事外而不得不深度介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營造的新媒介環(huán)境中,潛移默化改變著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造、傳播、交流路徑。這種媒介技術(shù)對人的延伸同樣意味著對人腦思維的閹割,即人越來越習(xí)慣于不依靠活躍的思維過程,而是依靠外延的思維結(jié)構(gòu)產(chǎn)品去獲得所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推動文化參與主體權(quán)力與能力的上升,但無法保證文化參與效益的提升。具體而言,如若文化參與主體依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甚至產(chǎn)生對技術(shù)智能的崇拜,可能走向思維淺表化,使人成為技術(shù)的附庸,其在文化參與中的實質(zhì)主導(dǎo)地位被取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扮演起虛擬的意見領(lǐng)袖。一方面,人的參與缺位將造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文化記憶、情感和價值的空白;另一方面,人對生成式人工智能體現(xiàn)出的參與權(quán)力讓渡,也會引發(fā)個體對“我是否處于自己理性、自主的主體性的中心”[38]的質(zhì)疑,個體的意志搖擺達到規(guī)模效應(yīng)時將撕裂整個共同體的凝聚力。由此可見,技術(shù)解放依賴于人的解放,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有效建構(gòu)應(yīng)在技術(shù)賦能個體的基礎(chǔ)上,保障個體在文化生產(chǎn)中的實質(zhì)參與以防出現(xiàn)技術(shù)凌駕于人之上的被動局面,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創(chuàng)新主體互動的方式而非僅停留在人機關(guān)系的應(yīng)對,重視發(fā)揮人之主體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其二,對共同體靈魂的單面性控制,削弱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精神內(nèi)核的豐富性。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靈魂正在于特殊的文化經(jīng)歷和記憶、流動的文化情感和價值。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夠?qū)⑷说闹黧w性話語轉(zhuǎn)化為客體結(jié)果,卻無法完全模仿人類心智的內(nèi)在機制過程。“算法必然是局部的,完全復(fù)制人的生物算法是不可能的。對于設(shè)計性算法來說,生物算法相當(dāng)于無限,這是永遠達不到的,同時,也不需要達到,這并不是人工智能努力的方向”[39]。由此可見,生成式人工智能雖能促進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內(nèi)部情感認同建構(gòu),但其在情感識別與精神模擬的具體環(huán)節(jié)上,始終與人類本身存在一定差距。無論是活化民族文化資源,還是講好中國故事,生成式人工智能象征的技術(shù)元素都不應(yīng)占據(jù)決定性的主導(dǎo)地位,而是作為內(nèi)容元素和創(chuàng)意元素的輔助,共同助力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內(nèi)核塑造。
(二)信息異化:技術(shù)失范破壞意識形態(tài)穩(wěn)定性
智能算法技術(shù)正在以特定的技術(shù)框架和運行規(guī)則開展一場輻射人類生活各個領(lǐng)域的全景式革命,迅速成為影響社會運行結(jié)構(gòu)和權(quán)力分配模式的底層框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應(yīng)用結(jié)果受數(shù)據(jù)、算法、算力等多樣復(fù)雜因素的影響,在使用過程中也會融入用戶價值觀等主觀因素影響。如果缺乏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規(guī)范化治理,可能導(dǎo)致其在應(yīng)用中出現(xiàn)信息異化,催生意識形態(tài)風(fēng)險。
其一,雜糅的虛假信息擾亂輿論生態(tài)。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ChatGPT創(chuàng)建的摘要被提交給學(xué)術(shù)評審人員,他們只發(fā)現(xiàn)了63%的造假。[40]在未受監(jiān)管和約束的情況下,ChatGPT為代表的強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可能作出高欺騙性的信息造假且通過強大的論證能力“自圓其說”,還可能在技術(shù)和政治互嵌的媒介景觀中使虛假信息傳播的隱蔽化和復(fù)雜化變得更容易,為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等不良價值觀的傳播制造可能,埋下煽動公眾非理性情緒、分化群體價值、撕裂民族整體認同的隱患。其二,潛藏的價值偏見激化關(guān)系矛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數(shù)據(jù)挖掘和算法運行并非完全自我形成,而是人工編譯的結(jié)果及其延伸,因此一定程度上滲透著特定人群的價值傾向。缺少發(fā)揮核心牽引的主流意識和統(tǒng)一規(guī)范的話語體系,內(nèi)容生成與傳播更容易走向支離破碎的局面,在群體極化后形成不相協(xié)調(diào)的多個“偏見共同體”。然而,考慮到我國民族領(lǐng)域議題——比如邊疆治理、民族教育公平等——的復(fù)雜性與敏感性,消解在這些議題上的分歧、促成共識是鑄牢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必要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介入諸如此類的民族議題時必須被注入合乎我國統(tǒng)一政治立場的信息編碼,且作為維護意識形態(tài)穩(wěn)定性的“數(shù)字看門人”,否則可能使得網(wǎng)絡(luò)偏見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偏執(zhí)。其三,外部的算法霸權(quán)增加風(fēng)險滲透。ChatGPT起源于美國的研究機構(gòu),受西方數(shù)據(jù)語料庫和價值觀的浸染,其生成內(nèi)容難免沿襲西方的語言習(xí)慣、思維模式與意見立場。現(xiàn)階段,以ChatGPT為代表的強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實現(xiàn)中國本土化的發(fā)展,仍具備較強的西方文化底色,導(dǎo)致其難以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國家偏見”,即生成內(nèi)容的立場偏向以西方價值觀為核心的相對狹隘的局部視野。若缺乏規(guī)范監(jiān)督,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旦被政治化利用,將存在被部分國家進行輿情攻擊、干擾他國內(nèi)政的可能,甚至造成技術(shù)權(quán)力下的“意識形態(tài)戰(zhàn)場”,加劇全球輿情矛盾和國家民族間的文化沖突。
綜上所述,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我國意識形態(tài)的解構(gòu)風(fēng)險是捍衛(wèi)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穩(wěn)定性的重要前提。為抵御上述風(fēng)險,需充分考慮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在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建構(gòu)上的獨立性和特色性,既要形成一套屬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統(tǒng)一價值解釋規(guī)則,也要激發(fā)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反技術(shù)控制”的生命力。同時,強化主流意識的牽引與價值理性的鞏固,促成技術(shù)與政治、文化生活的有效互動,彌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shù)缺陷,使之更好地作用于對異質(zhì)性意識形態(tài)的精準(zhǔn)辨析及外部風(fēng)險應(yīng)對,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構(gòu)營造有利條件。
(三)認同解構(gòu):技術(shù)泛用埋藏主體泛在的隱患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嵌入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走向普及化應(yīng)用時,會逐漸形成主體泛在的傳播結(jié)構(gòu),即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接入生成式人工智能這一媒介。ChatGPT的生活化和普及化印證了這點,無門檻使用導(dǎo)致任何用戶都可以與ChatGPT發(fā)生對話互動。然而,ChatGPT和用戶共同構(gòu)成的傳播結(jié)構(gòu)不再適配傳統(tǒng)單向輸出的傳播方式,而是多個傳播節(jié)點間相互影響、聯(lián)通共生的新模式。個體行為產(chǎn)生的“蝴蝶效應(yīng)”可能導(dǎo)致整個傳播生態(tài)的變化,增加虛擬共同體成型的不穩(wěn)定性。
主體泛在的結(jié)構(gòu)中,脫離了工具輔助和價值引導(dǎo)的個體很容易迷失在紛繁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信息里,或陷入信息繭房,或走向意見極端,或滑向“烏合之眾”的困境而丟失對真正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體認。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應(yīng)用空間整體指向一種去中心化的傳播場域,可能削弱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權(quán)威性。去中心化在滿足用戶擴張性信息需求的同時,也可能因信息量級和傳播頻次的大幅提升而增加信息傳播不可控的風(fēng)險。用戶對信息內(nèi)容的選擇與再生產(chǎn)都趨于多元,但也昭示著主流意識形態(tài)將面臨更復(fù)雜的多元思潮夾擊環(huán)境。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被惡意植入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崇洋媚外思想等錯誤價值觀,主體泛在的結(jié)構(gòu)反而易加劇信息失真與價值扭曲的程度,在影響范圍、影響速度、影響深度等方面都超過大部分傳統(tǒng)傳播方式。另一方面,主體泛在也為去中心化后的再中心化聚合現(xiàn)象的形成制造了條件,可能解構(gòu)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圈層間認同。主體泛在意味著處于全連接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各個節(jié)點的個體及其附帶信息具有長期活躍重組的可能,即會反復(fù)出現(xiàn)再中心化現(xiàn)象,體現(xiàn)為局部網(wǎng)絡(luò)資源的集中化、新的群體共識達成及其傳播能力的擴大化。然而,再中心化帶來的不僅有圈層內(nèi)的聚合,也有圈層間的區(qū)隔,即“不同群體之間排斥對話和交流的情況經(jīng)常出現(xiàn),對‘他者’的定義和想象往往陷入‘非友即敵’的思維”[41]。這種割裂化的圈際圖景可能導(dǎo)致圈層內(nèi)的信息輻射窄化、圈層間的話語鴻溝加劇,阻礙超越局部共同體的更高階認同建構(gòu)。
基于對主體泛在隱患的考慮,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下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構(gòu)應(yīng)進一步審視虛擬共同體成型后更細微層面的主體聯(lián)系,在技術(shù)驅(qū)動關(guān)系重構(gòu)的作用機制基礎(chǔ)上,創(chuàng)建引導(dǎo)主體良性互動的范式,促成多元共存、價值共通、相處協(xié)調(diào)、參與有序的主體關(guān)系。將中華各民族文化認同與整體國家認同轉(zhuǎn)化為動態(tài)性的、日常化的流通符號,作為深度黏合多元主體的吸引焦點,鞏固“智能互聯(lián)”“情感認同”“流動交往”的虛擬共同體特征,把握好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之認同建構(gòu)的整體方向不偏移。對于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潛在趨向則要趨利避害,利用好去中心化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推動文化參與權(quán)力的下沉,在維護意識形態(tài)穩(wěn)定性的前提下讓更多主體親身深度參與到中華民族文化的共享與交融中,合理引導(dǎo)再中心化的走向,催化不同民族文化圈層求同存異、和諧共生的局面產(chǎn)生。
四、范式創(chuàng)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作用機制為賦能基礎(chǔ),兼顧風(fēng)險防范意識,基于信息配置、內(nèi)容生產(chǎn)、主體互動、對外傳播四大環(huán)節(jié),展開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再建構(gòu)范式(見圖3)。再建構(gòu)意味著對傳統(tǒng)文化共同體建構(gòu)經(jīng)驗的部分保留,比如強調(diào)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dǎo)性、文化的交融與認同等,但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語境中延展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實踐方法與影響范圍,實現(xiàn)更高階的意識整合、更有特色的文化敘事、更和諧的主體關(guān)系、更強大的文化影響。

圖3 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下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再建構(gòu)范式
(一)共同體的意識整合范式:基于海量數(shù)據(jù)語料的中華民族文化信息配置
意識整合范式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范式體系中的基礎(chǔ)部分,其決定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意識形態(tài)導(dǎo)向與頂端資源發(fā)展。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形成,需要基于共同的價值理念和文化認知,流通在不同群體間的文化信息能夠作為這種共同理念或認知的具體寄托,并使有關(guān)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因素疊加融合,從而串聯(lián)起更廣泛的文化族群。伴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所納入群體的規(guī)模擴大,其又能反作用于文化信息的生態(tài)優(yōu)化,推動信息渠道及文化資源的拓展。
一是發(fā)揮生成式人工智能聚合信息的優(yōu)勢,全面搭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話語體系。共同體的話語體系不僅包括語言符號,還指向集文化、思想、價值理念于一體的精神凝練。[42]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聚合能力和深度學(xué)習(xí)能力,高效捕捉全網(wǎng)范圍內(nèi)的信息包括各類邊緣化信息,將碎片化信息集合轉(zhuǎn)化成一種連貫性的全景文本。比如用戶在與ChatGPT對話的過程中,ChatGPT能夠基于海量數(shù)據(jù)語料庫和用戶的實時反饋,不斷完善內(nèi)容輸出,能夠針對用戶的提問迅速從背后信息庫中篩選并配置生成有效回答,并且其生成內(nèi)容的全面性和成熟度,在一定程度上與用戶的使用時長和深度成正比關(guān)系,因此有不少用戶震驚于ChatGPT所給出答案的全面性。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可保存激活文化記憶的“智慧容器”,能夠滿足共同體話語體系中精神性與情感性部分的需求。將生成式人工智能強大的信息配置能力融入中華各民族文化背景與價值理念的共享性建設(shè),從個體角度可以幫助用戶在短時間內(nèi)全面便捷地獲取豐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并實現(xiàn)個體記憶的留存與延續(xù),從整體角度可以提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話語體系構(gòu)建的效率,充盈話語體系的具體內(nèi)涵與民族情懷,導(dǎo)向“價值共通”“命運共同”的認同目標(biāo)。
二是牽引生成式人工智能價值系統(tǒng)的設(shè)計,打造以主流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的信息廣場。中華民族生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生活框架之中,其文化認同必然浸染國家認同的成分,而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為保持民族團結(jié)和國家統(tǒng)一,必須將國家認同放在首位。[43]建立國家認同離不開自上而下的意識牽引,具體可通過對共同語言、文化符號、核心價值觀等的強化,彰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中心地位及核心牽引力。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具體內(nèi)涵灌輸?shù)缴墒饺斯ぶ悄艿挠?xùn)練數(shù)據(jù)、模型搭建、運行標(biāo)準(zhǔn)中,設(shè)置貼合國家認同之涵義的結(jié)果導(dǎo)向框架,促使其生成內(nèi)容符合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價值系統(tǒng)。首先,強化政黨意識形態(tài)的植入。政黨意識形態(tài)指“政黨在長期活動中形成的一套價值觀念、理論體系和是非標(biāo)準(zhǔn)”[44],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黨意識形態(tài)具體包含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等。其次,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相關(guān)主流價值體系也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層框架與算法模型,加強技術(shù)端與主流意識端的合作,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業(yè)運用能夠在規(guī)范框架中平穩(wěn)進行。百度公司的文心大模型便體現(xiàn)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shù)與官方主流力量的聯(lián)合效益,該模型基于文心NLP大模型ERNIE3.0,引入了人民網(wǎng)輿情數(shù)據(jù)中心在傳媒行業(yè)積淀的行業(yè)知識與任務(wù)樣本數(shù)據(jù),目前已在新聞報告生成等應(yīng)用場景取得了明顯的提升效果。此外,將多元化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亦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數(shù)據(jù)語料庫的重要補充,整合塑造出具有中國特色意蘊的信息資源儲備系統(tǒng),進而影響人機交互或協(xié)作生產(chǎn)的流程,為涵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構(gòu)建民族文化特色敘事范式奠定基礎(chǔ)。
(二)共同體的特色敘事范式:基于人機協(xié)同能力的中華民族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
特色敘事范式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范式體系中的重點部分,其是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之抽象概念轉(zhuǎn)化為具體表達的關(guān)鍵。構(gòu)建文化共同體所需的身份認同離不開敘事維度。如夸梅·安東尼·阿皮亞所言,“通過我的認同,我使自己的人生故事符合某種模式……對全世界的人們來說,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講述一種融入更大敘事的人生故事。這可能包括進入成年禮;或者是一種將個人生活融入更大故事的民族認同感”[45]。中華民族的個體或族群所經(jīng)歷的“人生故事”,一部分表現(xiàn)為由傳統(tǒng)文化積淀的原型經(jīng)驗、敘事母題和情節(jié)框架,這些成為中華文化宏大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連接中華民族文化信息庫后,能夠生成具有可讀性和個性化的內(nèi)容,通過影響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的邏輯形式,進而促成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文化敘事方式,并在人機協(xié)同的生產(chǎn)格局中加速打造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敘事特色。
一是推進精細化的內(nèi)容生產(chǎn),鋪墊現(xiàn)代文化敘事的民族性底色。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發(fā)揮的賦能個體、變革生產(chǎn)及重構(gòu)關(guān)系作用,每個用戶都可以參與到新的內(nèi)容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中,一方面可以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獲取靈感素材,并與其共同完成跨模態(tài)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或續(xù)寫;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也在交互關(guān)系的深入中不斷學(xué)習(xí)和獨立生成新內(nèi)容。整體而言,人機協(xié)同格局中的中華民族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有著主體更廣泛、工具更高效、環(huán)節(jié)更細化、效果更明晰的特點。基于精細化的生產(chǎn)優(yōu)勢,從主體性、豐富性、靈活性、親和力四個方面強化中華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為鑄牢共同體意識集聚能量。主體性方面,明確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中華民族文化創(chuàng)造的輔助性而非替代性地位,強調(diào)人機協(xié)作需努力超越技術(shù)邏輯而回歸人本身,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情懷滋補機器程序情感欠缺的部分,達成一種“柔性情感的調(diào)適”,鑄牢由中華民族自身主導(dǎo)的共同體精神世界。豐富性方面,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shù)加速規(guī)模化與縱深化的內(nèi)容生產(chǎn)。規(guī)模化指向內(nèi)容體量和覆蓋層次的增加。符合各民族地區(qū)、各民族類別需求或特征的文化內(nèi)容都能夠被創(chuàng)造出來,且相比以往人工獨立創(chuàng)作有著更快的速度、更發(fā)散的思維面、更與時俱進的迭代,形成百花齊放、融匯古今的繁榮內(nèi)容生態(tài)。縱深化指向文化資源及價值底蘊的挖掘。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耕能力,在智能分析與生成中完成對文化資源的解構(gòu)與重組,使得原本容易被忽視或停留于淺顯化開發(fā)的文化寶藏能夠在人機協(xié)作的合力下重?zé)ㄐ律?以更創(chuàng)新通透的方式被闡釋講述出來,即以技術(shù)生產(chǎn)力重新演繹和活化中華民族文化,剖解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內(nèi)部意蘊并使之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創(chuàng)意支點。靈活性方面,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shù)嵌入文化生產(chǎn)的各行各業(yè),激發(fā)民族創(chuàng)新的活力,打造多民族特色的原創(chuàng)內(nèi)容集聚高地,并拓展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話語體系的生動表達。由格蘭莫頤文化藝術(shù)集團創(chuàng)作的“瑰麗·猶在境”沉浸式數(shù)字意境展體現(xiàn)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展覽領(lǐng)域的成功運用。圍繞《千里江山圖》《洛神賦圖》《百花圖卷》三幅經(jīng)典古畫的意象元素,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元素的拼貼重組、融合復(fù)刻與二創(chuàng),最終進行自主視覺繪制,在展覽空間中為觀眾營造出如在畫中美景穿梭的視覺意境。借鑒該成功案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助力多元化的中華民族文化超越文本或?qū)嵨锏男螒B(tài),以智慧化、數(shù)字化、情景化等創(chuàng)新形式表達出來。親和力方面,基于前文所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成情感認同方面的能力,可推動主流話語向大眾化、生活化的敘事方式轉(zhuǎn)變,實現(xiàn)以“小敘事載大道”,使得具體生產(chǎn)出來的文化內(nèi)容能夠適應(yīng)多民族的心理需求,兼顧多民族的審美偏好。
二是接軌國際化的敘事體系,提升自主文化敘事的世界性高度。國際體系敘事主要指政治行為體如何解釋與構(gòu)想國際秩序。[46]在西方推行的敘事體系中,人機協(xié)同生產(chǎn)發(fā)展的重點在于提升本土信息科技產(chǎn)業(yè)在全球生產(chǎn)鏈中的地位,或增加意識形態(tài)輸出的砝碼,甚至開展核心技術(shù)領(lǐng)域的冷戰(zhàn)以獲得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中的話語優(yōu)勢。依托于擁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中華民族文化價值基因,由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主導(dǎo)的人機協(xié)同生產(chǎn)將更好地服務(wù)于中華民族數(shù)字文明的全球共享,并兼顧跨國文化的關(guān)系處理,導(dǎo)向包容普惠性的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與國際接軌背景下的共同體特色敘事范式包含了兩層獨特意義:一方面,中華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使其主導(dǎo)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為中華民族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形象代言工具,因此文化敘事帶有獨特的民族身份辨識;另一方面,強調(diào)“科技向善”“文化包容”的敘事理念,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推行的國際敘事區(qū)別于西方模式,因此整體敘事具備獨特的世界高度。
(三)共同體內(nèi)和諧共生范式:基于智能互聯(lián)形態(tài)的中華民族文化主體互動
和諧共生范式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范式體系的動力,其維系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內(nèi)部穩(wěn)定與可持續(xù)活力。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意識整合與特色敘事范式為共同體內(nèi)各主體間的互動提供不間斷的援引素材與話題點,也作為關(guān)系粘合劑鞏固共同體的成型。此外,對內(nèi)的和諧共生范式是對外影響構(gòu)建范式的重要基石。
一是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接日常生活,擴大文化共享與交融,實現(xiàn)沉浸式的文化參與。“智能互聯(lián)”與“流動交往”構(gòu)成中華民族文化主體互動的重要條件,在此基礎(chǔ)上需進一步推進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深度激活共同體的發(fā)展要素。不同于移動互聯(lián)時代的文化主體參與,生成式人工智能開辟的新互聯(lián)時代中,文化主體的參與途徑、范圍、手段以及其參與的深度都將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尤其是指向一種沉浸式的文化把握,即將中華民族文化置于技術(shù)滲透的全過程中,將其生成的有關(guān)中華民族文化的內(nèi)容信息潛移默化地融合進各民族的日常生產(chǎn)生活中,使之“日用而不覺”。西方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常化方面作出探索,比如馬克·扎克伯格在Meta第一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將在WhatsApp等社交應(yīng)用中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提升聊天內(nèi)容、創(chuàng)作工具、廣告營銷等方面的體驗。基于中華民族文化發(fā)展的特殊國情,可借鑒西方的先進經(jīng)驗,探求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各族人民日常生活耦合之路徑,具體如網(wǎng)絡(luò)社交、文化宣傳、民族創(chuàng)作、校園教育等領(lǐng)域。在達到完善的技術(shù)布局后,便有望營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意識環(huán)繞式的文化環(huán)境,促使每個民族成員都能在耳濡目染中深刻把握中華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信息與精神真諦,以親歷者而非旁觀者的身份參與到與之相關(guān)的各類活動及交流互動中。如此一來,各文化主體間的互動是源于親身感知與感悟的自然行為,而非任務(wù)性的、強制性的、被迫性的生硬互動,且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充當(dāng)優(yōu)化互動、美化互動的工具,改善提高互動效果,從而促進文化互動中的彼此認同加深。
二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創(chuàng)設(shè)共同焦點,開拓民族議題和符號,豐富共同體的互動儀式。柯林斯曾指出:“互動儀式的核心是一個過程,在該過程中參與者發(fā)展出共同的關(guān)注焦點,并彼此相應(yīng)感受到對方身體里的微觀節(jié)奏和情感。”[47]在長期的、流動的互動過程中,創(chuàng)新地制造有吸引力和凝聚意義的共同關(guān)注焦點,是推動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中各參與者和諧共生的關(guān)鍵所在。發(fā)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強大創(chuàng)造性,生產(chǎn)或改進互動儀式所需的共同關(guān)注焦點,主要包括社會議題和象征符號兩方面。社會議題既涵蓋常規(guī)的嚴(yán)肅性議題,如中華民族的崛起復(fù)興、現(xiàn)代民族關(guān)系發(fā)展、民族文化相關(guān)時事新聞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參與此類議題的傳播互動時需置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范框架內(nèi),再進行識別放大議題核心點、豐富議題視聽表達形式;又包括生動的大眾化議題,比如洛陽的一系列出圈節(jié)目——《唐宮夜宴》《洛神水賦》《龍門金剛》曾掀起國內(nèi)民族文化節(jié)目的觀賞熱潮,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協(xié)助該系列節(jié)目進行熱點制造、IP營建,或可達到更顯著的“出圈”效果,激發(fā)更廣范圍的互動討論。象征符號指沉淀中華民族情感記憶的文化載體,現(xiàn)有符號包括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圖騰的“龍”、寓意美滿團圓的民族情懷的“中國結(jié)”等。伴隨智能互聯(lián)結(jié)構(gòu)中的主體互動深入,互動儀式所衍生的民族情感和群體記憶將更豐裕也更復(fù)雜,精準(zhǔn)提煉象征符號的難度加大,需兼顧多類身份參與者的情感體驗與實際利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從海量的互動信息中判別個體和群體的情感利益等因素,挖掘潛藏在其中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符號,并通過與用戶的互動反饋,幫助其在互動儀式活動中實現(xiàn)對自己本質(zhì)力量的強烈確證,并衡量互動儀式的成效。[48]
(四)共同體的影響構(gòu)建范式:基于開放交互場景的中華民族文化對外傳播
影響構(gòu)建范式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范式體系中的升華部分,其體現(xiàn)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思路升維,是契合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銜接人類命運共同體境界的長遠布局。正如習(xí)近平主席向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大會烏鎮(zhèn)峰會致賀信指出的,“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擔(dān)起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zé)任……讓數(shù)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文化的國際傳播是助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破除西方散播的“泛蒙古主義”等分裂思想、重塑出海影響力的核心環(huán)節(jié)。
一是推動全球范圍開放共享,打通線上與線下的壁壘,促成全方位多領(lǐng)域的國際傳播。首先,發(fā)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信息數(shù)據(jù)共享方面的優(yōu)勢,實現(xiàn)對中華各民族文化生活與文化發(fā)展產(chǎn)物的集中映射與傳播,使全球任何人都可全面快速地了解到在原本現(xiàn)實空間中與自己并無牽連的其他民族群體的信息。其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引擎,編織中華民族數(shù)字文明新形態(tài),與線下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工程相結(jié)合,助推民族文化事業(yè)與文化產(chǎn)業(yè)對外發(fā)展。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基于中國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地區(qū)的現(xiàn)實互信與合作機制,整合各國文化資源、文化發(fā)展需求與成果、文化合作軌跡信息等,同步至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融入的網(wǎng)絡(luò)合作空間,便于為我國提供清晰的文化對比情況與互補發(fā)展建議,為加強我國文化軟實力、政治觀念和政策吸引力獻策獻計,還可進一步結(jié)合全球海量信息庫,智能規(guī)劃21世紀(jì)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參考路向。此外,將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框架中,再喚醒其在文旅產(chǎn)業(yè)、品牌營銷、遺產(chǎn)開發(fā)等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能力,催生產(chǎn)業(yè)思維與模式的迭代升級,以新文化產(chǎn)業(yè)形態(tài)承載并傳播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之影響力。
二是把握點對點的精準(zhǔn)傳輸,規(guī)避“大水漫灌”模式,實現(xiàn)針對性滴灌式的傳播影響。根據(jù)施拉姆的傳播思想,傳播至少包括信源、信道和信宿三個要素。中華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可被闡述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信源)將中華民族文化通過一定媒介(信道)傳遞到海外受眾(信宿)。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范式體系中的前三大范式基本滿足了傳播信源和信道的要素要求,而信宿的完善,即共同體的內(nèi)部受眾與外部受眾的全部在場,才意味著共同體影響構(gòu)建的完整,否則可能陷入閉門造車、故步自封的危險。生成式人工智能極大縮短信息傳播的層級,為滿足中華民族文化的精準(zhǔn)化出海布好前提。首先是基于個性化識別的精準(zhǔn)推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動態(tài)跟進用戶的言行變化后可對用戶畫像進行靶向瞄準(zhǔn),從而為其針對性地推薦符合其需求或偏好的內(nèi)容,整體上呈現(xiàn)“千人千面”的文化傳播效果。比如有海外用戶對中國的漢服文化感興趣,內(nèi)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交平臺便可為其精準(zhǔn)生成漢服相關(guān)的社交話題及圖文素材,滿足其參與討論和分享的欲望。其次是基于明面問題和潛在危機掃描的精準(zhǔn)處理。良莠不齊的網(wǎng)絡(luò)信息環(huán)境中不可避免存在丑化中華民族形象、歪曲中華文化價值的內(nèi)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作為24小時輿論糾偏的強大工具,圍繞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影響力維護的任務(wù)核心進行反駁式、糾正式的內(nèi)容回擊。最后,鑒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我更新迭代能力,其對每個用戶節(jié)點傳輸?shù)男畔⒁嗍歉叨韧礁碌?一定程度上消除傳統(tǒng)信息傳播的時間差問題,保障點對點傳輸機制的實時精準(zhǔn)性。將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其他同樣具備開放交互特性的技術(shù)結(jié)合起來,如區(qū)塊鏈、物聯(lián)網(wǎng),可進一步拓展中華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分眾化模式、互動化模式、社交化模式等。
五、結(jié)語
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喻示著新一輪的技術(shù)變革,再度呼應(yīng)了技術(shù)與文化之關(guān)系審視的經(jīng)典命題。生成式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本質(zhì)是媒介技術(shù)與社會生產(chǎn)力的進步,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的根基在于流動的民族共同文化記憶和價值,前者為后者提供了新的技術(shù)驅(qū)動力與建設(shè)條件,后者亦顯現(xiàn)出與前者指向的數(shù)字化、智能化等特征所適配的發(fā)展需求。尋求二者之間的契合點與銜接通道,構(gòu)建可持續(xù)的良性互動關(guān)系,能夠?qū)⑸墒饺斯ぶ悄茏鳛榧夹g(shù)增量補充進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工程從而達到效益提升與創(chuàng)新轉(zhuǎn)型的目的。通過帶動文化參與主體的權(quán)力與能力提升、文化實踐對應(yīng)的手段與形態(tài)升級、智能連接中樞下虛擬共同體成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從個體、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維度多層次地形塑出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作用機制。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現(xiàn)實應(yīng)用也面臨著三大層面的挑戰(zhàn),包括技術(shù)依賴對應(yīng)的文化活力限制、信息異化催生的意識形態(tài)風(fēng)險、主體泛在潛藏的認同解構(gòu)危機。立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作用機制與風(fēng)險生成,重塑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構(gòu)范式,強勢布局信息配置、內(nèi)容生產(chǎn)、主體互動、對外傳播四大環(huán)節(jié),分別鑄造意識整合范式、特色敘事范式、和諧共生范式、影響構(gòu)建范式,全方位且立體地提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整體實力,鑄牢共同體的文化靈魂與民族認同。
用辯證的眼光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響,重審其與中國社會雙向適應(yīng)的過程,在技術(shù)把握與范式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上還需進一步思考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再建構(gòu)范式的治理問題,以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融入性應(yīng)用是合規(guī)的、可控的、向善的。一方面,需重視內(nèi)部規(guī)范建設(shè),包括使用技術(shù)的主體行為規(guī)范、技術(shù)倫理規(guī)范、生成內(nèi)容規(guī)范等,破除人工智能的異化困境,超越如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技術(shù)文明形態(tài),構(gòu)造中華民族主導(dǎo)的“自由共同體”。另一方面,積極防范外部風(fēng)險,尤其是意識形態(tài)滲透風(fēng)險和價值偏見風(fēng)險,通過實行技術(shù)監(jiān)管、算法審查、產(chǎn)權(quán)保護、追責(zé)制度等構(gòu)筑起安全屏障,保障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趨向統(tǒng)一的“穩(wěn)定共同體”。最后,秉持中國特色的技術(shù)文化自信與包容互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斷推動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建設(shè)迸發(fā)內(nèi)外合力,不僅促成本民族內(nèi)部各族群的共生繁榮,更要在“走出去”中躍升至全球化的高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彰顯大國文明的風(fēng)范,以“創(chuàng)新共同體”的姿態(tài)解構(gòu)西方中心論,引領(lǐng)開辟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