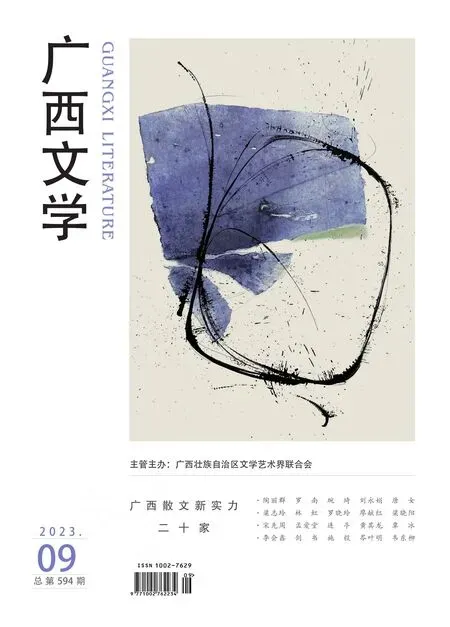現實主義標尺下的散文突圍之路
——《廣西散文新實力二十家》專號閱讀札記
周 聰
《廣西文學》編輯部策劃的《廣西散文新實力二十家》專號是廣西散文界的重要事件,將70后、80后、90后的散文家以專號的形式集結,一次性推至讀者的面前,呈現廣西散文創作的大體風貌和整體水平,對于入選的散文家而言,也是一次精彩的亮相。在文學邊緣化、閱讀方式視頻化、內容碎片化的自媒體時代,該欄目的策劃者可謂獨樹一幟,散文這種文體在文學式微的當下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愿以散文為志業的創作者寥若晨星。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散文沒有小說家與影視結合后的榮光,也缺乏詩歌的喧鬧聲響,它儼然成了文學門類中的“多余人”。在此種背景下,這期散文專號的推出,意義重大,它事關散文寫作者的尊嚴與價值,也體現出策劃者的散文觀和審美趣味。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說:“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譯的對象。”疾病與死亡休戚相關,也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主題:對于個體而言,因患病而引發的心理變化能折射出人們對待生命、死亡的態度;對于家庭而言,疾病和死亡是透視家庭倫理的重要窗口;對于社會而言,疾病與死亡則是人口老齡化逐漸加劇后必然面臨的社會難題。在這期散文專號中,疾病成為作家們不約而同的切入口,由疾病見人物內心世界,見社會現實,見生命感悟。例如,陶麗群的《疾病》從一場疾病起筆,在尋醫問藥的過程中一步步敞開自己的內心,對精神世界的審視是其最大的亮點,這段患病經歷與祖父的疾病史引發了作者對生命、死亡的探討,從肉體的“病魔”到心靈的“心魔”,疾病的抽象化、心靈化意味著思考的深度和廣度的加深,疾病影響了個體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在常態與病態之間的轉換,個體審視內心與觀照世界的視角都會出現差異化,疾病提供了一種非常態的角度。
羅曉玲的《密林,或另一種索引》呈現了疾病帶給身體的疼痛感,圖書館的工作環境影響了“我”感知外界的方式,疾病賦予了“我”對聲音異于常人的感知力:不論是開篇幽靜的圖書館發出的尖厲的叫囂聲,還是結尾時陽光灑在桌面上發出的伐木聲,疾病改變了“我”身體器官的部分機能,讓“我”能從日常生活中發現一些異常的動靜。身體疾病的困擾與敏感抑郁的情緒相互纏繞成一座密不透風的“密林”,“我”與同事在這樣的密林中艱難穿越。散文彌漫著一種神秘的氣息,在相對封閉的空間里,壓抑和躁動的情緒、尖銳的聲音、噩夢與臆想……都指向了一種異于常態的超驗世界,“那片幽閉陰暗的森林”宛如一片巨大的磁場,人性深處的幽暗與光亮都被悉數吸附而去,演化成極具個性的文學表達。唐女的《萬物安生》是一篇讀來頗為沉重的散文,它記錄了一個患有抑郁癥的女兒與母親之間的情感碰撞——沖突、疏遠、冷漠、理解、寬宥、信任……情感狀態的變化袒露出母女關系的復雜和多變,也反映出母女在應對社會現實時所采取的心理防御機制。在散文中,寵物狗拽拽的走丟,撕開了女兒在校被霸凌并逐漸患上重度抑郁的心路歷程,寵物狗和藥物都無法將女兒從疾病的困擾中拯救出來。在陪伴女兒的日子里,母親的擔憂和焦慮是不言而喻的,令人欣慰的是,女兒最終選擇了信任和依靠母親,母親由此感受到了大地上萬物安生之境。《萬物安生》寫出了一種復雜的代際關系,對于這對母女而言,萬物安生是歷經磨難和痛苦才能抵達的心理狀態,它透露出母親內心深處的淡然與釋懷。李會鑫的《修羅場的黃昏》寫的是“我”帶爺爺去南寧看病的經歷,爺爺的患病改變了一家人按部就班的生活,在老家與南寧之間的來回奔走,爺爺的心態也在悄悄發生變化,結尾以一個上籃動作,推演了他單薄的肉身對疾病和命運的防守和搏擊。《消失的岸》則將敘述的重心集中在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奶奶身上,記憶力的衰減、生活自理能力的逐漸喪失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共同面臨的現實難題。李會鑫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文字直指社會現實:在老齡化日益加劇的今天,老年人如何面對疾病和死亡的命題?他從一個親歷者的角度發出了自己的疑問,并嘗試著給出答案。
除去非常態的疾病書寫,對日常生活的捕捉、剪裁、提煉、呈現也是該期散文專號中很多作品的藝術追求,在審美旨趣上,這類作品多關注普通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波瀾,山川景色、自然萬物、親友的故事皆可成為素材,日常化與生活流是其重要的文學品格。羅南的《下一個路口》聚焦作者從山城遷居南寧的心理嬗變,南方雨季中的白玉蘭勾連起山城的往事、童年獨坐門檻望向遠方的記憶、新城市的忙碌生活,構成了“我”的生活軌跡,下一個路口意味著新的開端,也是“我”在新的環境下重新檢視過去的挑戰,這篇散文在敘述中流露出一種淡然、積極的生活姿態,下一個路口預示著在路上的行走狀態。在面對充滿未知的生活時,“我”的內心泛起層層的波瀾,在旅途中也平添了豐富多彩的人生經驗。
劉永娟的《憐憫》以“我”的視角來講述我的師傅李美嬌的人生經歷,五十年的歲月中,婚姻、疾病、職場煩惱……女性的生存困境在“我”的敘述中娓娓道來,倒推著李美嬌命運的一步步成因。語言和場景極富桂林地方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標題“憐憫”二字,它包含了“我”對師傅的理解,也暗含女性對自身、對男性的洞察與共情。在《憐憫》的結尾,“和另一個自己緊緊擁抱在一起,同時擁抱那些我們還無緣相遇的陌生人”,與自己的內心世界達成共識,將憐憫之心向所有人敞開,悲憫萬物、心系眾生,以擁抱的姿態給陌生人送去善意和理解,盡顯作者的胸懷和格局之開闊。施毅的《越過取景框》以鏡頭記錄生活和世界,在“我”的取景框內,變幻莫測的自然景象、養蜂的黃哥、講述苦難生活的李姐、坐在水泥凳上的三位奶奶……那些凝固在歲月里的景觀和人物,都成為“我”眼中的“風景”,不同的風景線寄寓了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人生姿態。作為一個攝影者,他的鏡頭從最初的平面記錄上升到從浩瀚星空俯視地球的闊大和豁達。這篇散文存在的問題是在敘述的過程中,議論的話語和略帶人生感悟式的語言過多,有些許說教意味。廖獻紅的《大田面的鳥兒們》看似寫的是鳥兒,實際寫的是生活在大田面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從地理位置到鄉村風俗,從歷史沿革到城鎮化進程,大田面這個地名承載了中國式農民的命運,它成為中國鄉鎮的一個縮影。
林虹的《像雪花覆蓋著》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再現了城市裝修工人的生存狀態,“我”為了寫一部小說,對工地上的外墻裝修工人進行了采訪,卻被誤認為是暗訪的領導,繁華的街道上,無數民工在為這個城市無私奉獻著。農民工是一個沉默的群體,他們建造了一座座城市,城市卻不屬于他們,他們是城市的外來者。《看見溫暖的光》則將筆墨聚焦鄉村的直播帶貨,這是一個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帶領村民致富的故事。黃其龍的《人潮漫卷》關注的是網約車司機,這是一個隨著互聯網技術變革而產生的新群體,他們寄生在城市中。沉醉于城市聲色犬馬的女孩、充滿隔閡與冷漠的一家人、孤身前往墓地祭奠母親的女孩……陌生的顧客構成了“我”觀察與書寫的對象,“我”在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的接觸和交流中,看到了人生百態,也體驗到了來自他人的悲喜。《像雪花覆蓋著》和《人潮漫卷》的相同點在于,二者都是以旁觀者的視角來觀察他者的生活,對人和社會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由技術變革引發的新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群體,觸碰了創作者們的神經,他們的書寫提供了一種文學化的路徑,具有記錄社會現實的意義。
生態散文或自然主義文學是近年來不容忽視的散文類別,一些作家紛紛將筆墨轉向對動物、植物的觀察和書寫。在這一期的散文專號中,有一些篇什可以歸為生態散文的范疇。琬琦的《金蟬變》和《人形青蛙》是一組典型的動物散文,細部的處理(真實、荒誕、夸張、變形等)是該作品最大的特色,依托強大的想象力,多樣化的細節使得該文本獨具一種陌生化的魅力。《金蟬變》從一只蟬殼寫到蟬與夏天、村莊的關系,作為藥方的蟬蛻與作為食材的蟬具有經濟、食用的雙重功能,終究難逃被村民捕捉的宿命。這篇散文的結尾想象奇崛,“無數蟬的叫聲合并成一個,無數棵樹木的搖擺合并成一棵”“我后退幾步,呼嘯的風掃過樹林,像驅趕著千軍萬馬的大軍自山頂上撲下來”,將蟬鳴聲比擬成復仇的大軍,順著風的方向呼嘯而至,聲音與空間的深度融合,充滿想象力的表達制造了一種橫掃千軍的效果,在視覺上極具沖擊力。《人形青蛙》聚焦青蛙在鄉村被捕殺的命運,“開膛破肚”的血腥、暴力行為在多年后的生物課上依舊讓人心里一顫,“我”終究走上了懺悔之路。琬琦的散文寫作客觀冷靜,于細節中直擊靈魂,她的作品中有反思精神,有悲憫意識,體現出一個寫作者難得的藝術追求。
梁志玲的《目之所及》同樣可以看作是動物散文,它與《金蟬變》的區分在于,《目之所及》更注重人與寵物之間的情感溝通,寵物狗“瓜皮”與“我”之間有了情感的紐帶,它的每一次生病都牽動著“我”的心緒,也影響著“我”的生活。“我”對瓜皮的喜愛與重視,在散文的最后被推廣到了所有生命之間的盤結與關聯、萬物之間彼此的尊重與愛憐,提升了這篇散文的精神高度。宋先周的《追逐,向暗處》刻畫了一個鮮活的父親形象,父親與老鼠之間的斗爭史是作者敘述的重點,在窮追不舍的捕鼠生涯中,父親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捕鼠成為父親一生的事業,一場終生不懈的糧食保衛戰,他把對老鼠的捕捉上升到了一種“儀式感”的高度,平時連雞都不輕易宰殺的他表現出殘暴的一面,人物性格的反差和復雜性躍然紙上。與大多的生態散文不同,《追逐,向暗處》雖然寫的是動物,但它的落腳點并非號召大家保護生態環境,父親與老鼠的“敵對”關系構成了這篇散文的主體部分,由動物來寫人的性格,呈現人的精神世界的向度,才是作者的興趣所在。
孟愛堂的《等風來》重述了家族的歷史,滿爺的“魔法”充滿了傳奇性,他以每天做一件善事來化解花姑娘的劫難,風是這篇散文的核心意象,它飄忽不定、輕盈的特性隱喻了家族中女性的命運。《空房子》講述了農村孩子的房子夢,住房是城市化進程中每個人不可逃避的難題,對于“我”而言,房子綁架了“我”的生活與情感,我們大多數人都活在了房子的“奴役”之下。梁曉陽的《布爹布奶》則以小說的講述方式,再現了布爹、布奶一生的命運沉浮,同樣可以看作是重構祖輩歷史的作品。在敘事形態上,《布爹布奶》有一條明顯的時間線索,也就是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來重構歷史,書寫民間小人物的微觀史,在敘述中略顯平鋪直敘,缺少一定的起伏。
從敘事策略上看,連亭的《我的農民工父親》、韋東柳的《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覃冰的《鞋》大多采取了“以物賦形”的方式,具體來說,選取日常生活中的某種常見之物,將其與所寫人物的性格進行比擬或隱喻,以物喻人,人與物在散文中呈現出一種交融、互文的形態。例如,連亭的《我的農民工父親》,深入挖掘了牛的勤勞、忠誠等品格,重現了父親的打工生涯,從精神層面上來說,牛與父親都是無私奉獻的勞動者,他們都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他人,獻給了社會。《我的農民工父親》聚焦當下備受社會關注的農民工題材:中國50后、60后農民工是中國社會的建設大軍,他們是生活的負重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記錄他們,是記錄歷史的片段,也是記錄生活的本相。重新發現他們、看見他們,體現了文學對生存的關注和悲憫情懷。《我的農民工父親》敘寫農民工父親在時代變遷中的打工故事,由鮮活的有溫度的個體去呈現農民工這個群體的生存境況和堅韌不拔,生活本相與內心幽微。對于多數85后、90后農村孩子來說,農民工是他們的父母、親人,打工的辛酸與甘甜對他們而言也是血肉相連的真實發生的一切,所以當作者敘述起父親的打工點滴時,我們能感知到文字中的熱度,大量的細節仿佛一個個有態度的長鏡頭,將農民工的時代生活刻畫得入木三分。韋東柳的《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的處理方式與《我的農民工父親》異曲同工,只不過將比擬的對象從牛替換成樹,父親的木匠身份與村莊里的樹木形成了某種呼應,樹木的品格塑造著父親的品行,二者共同構成了父親的性格特點。與《我的農民工父親》建構父親的打工史相對,覃冰的《鞋》則充滿了隱喻的色彩:一方面,“鞋”隱喻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遭際,從出生到結婚生子,歷經了生活的磨煉與波折,母親的一生與時代密切相關,她終究在婚姻的破裂中走向了“牛角尖里赤足搏殺”。鞋是母親一生的宿命,大腳的她無法逃離出那段愛過、被傷害過的婚姻;另一方面,“鞋”也寄托了女性在面對失敗和挫折時心中尚存的希望,“鞋”與遠方相關,“鞋”承載了一代代女性對遠方和夢想的渴望,在愛情、婚姻中失落的她們,通過自己的雙腳,依舊能抵達一片未知和充滿可能性的天地。不論是“以物賦形”,還是隱喻式的表達,這些作品的落腳點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人物的性格、命運、情感、心理等,始終是作家們無法繞開的話題,唯有寫活了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作品才能立得住。
余華曾說過:“童年的經歷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方向。”兒時的記憶,會深刻地影響著一個作家后來的創作,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大多是根植于童年經驗的基礎之上的,童年是作家們一生都無法回避和逃離的烏托邦,它賦予了作品的精神底色。終其一生,作家們都在想象和重返童年,童年經驗也是作家們創作的重要“方法論”。劍書的《水聲喧嘩》依托的主要是童年經驗,野馬河、紅水河、金城江,三條河流構成了“我”的精神成長史,“我”的記憶與生活經驗的積累,都與這三條河密不可分。饒有意味的是,“我”畢業后最終又重返野馬河,人經歷生活的磨煉后又回到了出發地,“我”才意識到唯有一路向前才能闖出一條路,在生活的靜水之下可能暗藏著洶涌的波濤。岑葉明的《一個人熱鬧》重在記敘兒時經歷對自己性格的影響,對村子和家庭的厭倦,青春期對愛情的憧憬,著魔般陷入對寫作的癡迷中……童年的遭遇對后期“我”的成長和性格的養成至關重要,一個人的時候,并不覺得孤獨,意味著成長和蛻變。這是一種私人化的寫作,童年經歷與個人內心世界的完全敞開,在追憶過去和書寫現實的交替中剖析自己與世界的關系,自審中帶有反省的意味。對于作者而言,寫作意味著一種心靈救贖,它被賦予了多種崇高的意義:在寫作的過程中,作者實現了內心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和解;寫作也促使作者自身的精神成長,它儼然成為一種信仰。
縱觀這期散文專號,從寫作姿態上來看,散文家們的創作無疑是可圈可點的,一些作家把自己身體的疾病、心理的焦慮和困惑、家族的歷史等,全都毫無保留真誠地交付出來:對待寫作,作者們心懷虔誠與敬畏,不少的作者都愿意把寫作對自己的影響寫入文章就是明證,寫作被認為是一種莊重和崇高的事業;對待讀者,散文家們不故弄玄虛,不故作姿態,于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娓娓道來,關注老百姓的日常,形成了言之有物、樸實、沉穩的藝術風格。從作品呈現的具體內容來看,南方背景下的自然景觀、當下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家庭倫理關系中的碰撞與消弭等,都是作家們的題中之義。在這期專號中,散文與現實生活的血脈關系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作家們感興趣的大多是真實可感的現實生活,鮮活的生活經驗為作家們提供了大量原生態的素材,也就是說,現實成為作家們觀照世界、展現內心、追溯歷史的有效策略,日常生活化的現實主義品格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延續和發展。
本期專號略顯不足的地方在于,寫作者們聚焦的大多是童年記憶、家族歷史、自然界中的動植物等,對日常生活的書寫依舊是主流,現實主義的價值標尺深刻地影響了創作者們的敘事和布局,這期的散文大多可以看作是專注于個體經驗的“小散文”,我們幾乎看不到對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時間節點的敘述,歷史在這些創作者筆下往往演變成了具體的個人史、家族史,他們著力表現的是那些來自民間的野生人物、底層人物。究其根源,一方面,相同的生活經驗、知識背景,使得創作者們在選材時往往從自身熟悉的題材、人物著手,“小散文”的輕盈、相對穩定的敘事模式,成為創作者們的首選;另一方面,“小散文”處理的往往是相對單一、簡單的日常生活經驗,它沒有“大散文”的復雜和斑駁,從技法的角度來看,個體的私人化表達往往比群體的抽象化、哲學層面的挖掘更為簡便。在此,我們并非有意貶損“小散文”,相反,“小散文”也是可以出現經典、有格局、有深度的大作品的。
從寫作風格上來看,本期專號的創作者們不約而同地遵循經典的現實主義的筆法,對散文文體的探索與創新相對較少——無論是從中國古典的筆記、小品中吸取有益的養分,還是從西方的對話體、哲思體的片段式散文中進行形式上的探索——這是在讀完所有作品后的明顯的缺憾。中規中矩的創作方式,趨同的生活經驗和表達方式,讓這些散文整體散發出相似的氣味,它們天然地攜帶有農耕時代的氣息,著力于再現城市化進程中的日常生活。那么,散文這種文體的突圍之路在哪里?這或許是每個散文作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期待著,在現代性的書寫、哲學層面的掘進、形式上的創新等層面,更多的散文家們能帶給讀者新的驚喜與閱讀體驗。這也許是一條充滿艱辛的探索之路,更是每一個以散文為志業的寫作者義無反顧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