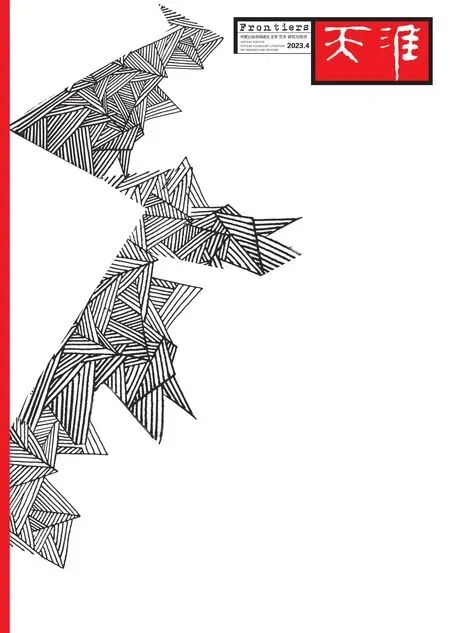疾病、藝術與互助
——李博、唐浩多對談
李博 唐浩多 蔣浩
源起
李博從十九歲患尿毒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與這種絕癥伴隨、忍受和抗爭一生。他在患病之初,碰見了當代藝術,特別是受他偏愛的裝置,并以此作為他人生的一部分。即使他一直處于中國藝術圈的最邊緣,作品也不曾被更多的人看見和認可,但是他仍然在堅持對藝術的實踐和思考。李博在去年11月份被診斷為肝癌晚期,但是他并沒有打算進行治療,反而是覺得心里踏實。“萬物皆有病”是李博確定的展覽主題,他說萬物并不是完美的,我們要接納這種不完美。李博的本次個展,不僅是他個人藝術之路的回顧,同時也是一場人生的告別。這場展覽并沒有藝術機構的支持,而是由他的藝術伙伴和朋友們合力相助籌辦起來的。這完全是一場自發性的展覽,它由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串聯起來,所以這也是一場“互助行動”。本次展覽將展出李博自2006 年以來的手稿、繪畫、方案效果圖、行為和裝置等近60件(組)作品(其中有5件裝置作品是第一次呈現)。觀眾可以通過這些作品,了解李博的經歷、生活、情感、病痛、婚姻、藝術和思想。此外,李博還有一個正讀初中的還未成年的孩子,因此我們也希望本次展覽既是為了完成李博的心愿,也是對他兒子的關注和支持行動的開始。
(唐浩多)
前言
疾病無異于受難。很難想象,李博從十九歲到現在,二十年始終飽受病痛折磨的同時,還在孤寂地從事自己喜愛的當代藝術實踐。在他自己看來,藝術不是治療,不是自戀,不是審美,不是雅趣,不是拯救,而是“批判”(李博訪談)。這意味著他至少在同時進行著兩種孤絕的戰斗:與自己身體所居的病魔,與自己身體所處的時代。也許,我們不能說這是一個病人對他認為的“萬物皆有病”的時代的發自本能的身體性理解、診斷和對話,但這孤絕的“一個人的運動”(德·庫寧語)無異于雙重的受難。真可謂:博者,搏也。因此,對于李博來說,每況愈下的“沉船上的生活”(杜尚語)就像《生,活》(2008)中那倒扣在大地上的青花瓷碗,簡直就是在心里隆起的一座巨墳。而在高速物化、動蕩不安的當代同質—擬真生活造就的《旋轉的人》(2012)中,具體有別的個性細節被抽象成柱體上凹凸起伏的曲線構成的共性輪廓,展現的正是一個失去個性或“沒有個性的人”(穆齊爾語)的“臉之悼亡”(里爾克語)的同時代悲劇。如果把這個作品理解為是對德勒茲意義上的“無器官身體”的某種重構和致敬,那么李博顯然不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光明柱》(2012)中蠟燭燃燒熔化形成的人形蠟燭和煙熏形成的人形黑影之間畢竟是有一道光,照耀和指引著他的“堅持”、“方向”和“正直”品格,像那枚經過他藝術分解的《螺絲釘》(2012)深深地楔入到他的整個藝術思考中,因此,他手稿中那只理想主義的《氣球》(2019)利用掙脫地心引力的艱難飛升來拉滿弓弦。《凝視》(2017)顯然是對深淵哲學(尼采)的又一次積極改寫:你凝視的不僅僅是你自己的眼睛。與其說這種自我凝視是對自我的“精神空間”的追問式概括,不如說是我們對待生命的他者態度,不管是因為疾病,還是因為藝術,或如李博這樣,不管是二者兼而有之,還是兼而因之,正如尼采所說:“不妨大膽一點,因為我們終究要失去它。”善哉!
(蔣浩)
唐浩多(以下簡稱唐):李博,你好!我第一個想了解的是,你的童年是怎么度過的?請你概括一下。
李博(以下簡稱李):童年就是在農村度過的,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十幾歲初中畢業。小學的時候比較聽話,那時候讀書成績還是算比較好的,初中就開始跟著(別人)玩,學著抽煙。那時,我家里的生活條件在農村還算可以的。
唐:你當時讀小學的時候是在農村上的學嗎?
李:一直都是在農村,從我出生起,讀小學和初中基本上都在農村,很少去別的地方。初中的話就在鎮上,一個很小的鎮,哪也沒去過。
唐:那當時在農村上學的時候是跟誰在一起生活?
李:在農村的時候,父親在外面做生意,基本上每半年回來一兩個月。我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跟我母親和我姐姐在一起生活,沒有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
唐:當時你也算是一個農村的留守兒童,因為父親常年在外面做生意,這一段經歷,對你有沒有影響?爸爸不在身邊的話,你當時心里面會怎么樣?
李:當時農村的小孩子基本上都這樣,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一段時期,每個家庭都是三四個小孩,父母基本都在種地。我家里面也沒怎么種地,畢竟父親在外面做生意。母親沒上過學,也沒有文化,所以說小時候在學習方面也沒人管,我過的是比較普通的農村小孩的生活,對比現在來說也不算是留守兒童。因為最起碼母親一直在家里面照顧我們,父親有一些文化,但是常年不在家,在學習方面也沒有管我們什么。那個年代基本上每家小孩都多,大多數農村人都沒什么文化,基本上也沒怎么去管小孩,兒童的心理和學習方面,他們也不懂。感覺也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基本上都是那樣的,每家每戶基本上都是那樣。
唐:就是說其實沒有跟別人有家境上的不同,其實可能也不是說沒有影響,但是因為大家都一樣,沒有差別,是這樣嗎?

油畫《十月懷胎》 60×80cm 2007年 李博
李:對,基本上就是這樣。自己跟其他小孩子沒有什么不一樣,只是說有些父母是一天到晚在種地,而我父親在外面做小生意,我母親有時候也種地,但是種得比較少,然后就打打麻將什么的。
唐:那你是什么時候才跟父親長期生活在一起?
李:大概是從2015 年開始長期生活在一起,之前他基本上都是每年回來兩次,每次回來待半個月或一個月。
唐:當時你已經結婚了,是嗎?
李:2015 年那時候,我差不多三十一歲了,我兒子都八歲了。
唐:那就是說,你從童年到青年的大部分時間是沒有跟父親生活在一起,那么當時對父親有過一些不解或者不滿嗎?
李:小的時候是有的,一直到十幾歲都有這種想法,感覺父親經常不在身邊,好像沒什么依靠和安全感,后來逐漸習慣了。習慣以后,后來經常跟他生活在一起,反而感覺還不如以前那么的舒服了。
唐:因為經常不在一塊,所以人的情感的聯接是減少的,就有點變得陌生。二十多年以后,又生活在一起,就變得有點像是跟一個陌生人生活,情感上還是有點疏離的。以前,我也不算是留守兒童,我是流動的,我跟我家人也是有一種疏離感。
李:對的,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就是總感覺觀念或者是什么話題都聊不到一塊去,或者說各有各的想法,經常產生一些爭執。
唐:那你年少的時候有過叛逆嗎?
李:我很小的時候特別聽話,到初中時,十五六歲開始產生叛逆心理。
唐:你能描述一下當時的這種叛逆的狀態嗎?比如說對某物某人某事有一些怎樣的一種質疑,或者是一種抵抗?
李:那是上初中以后,因為離家遠了一點,學校在小鎮上,騎自行車十來分鐘。那時,開始偷偷地曠課,或者是在外面打游戲,學著抽煙,跟著一些外面的人玩。這樣子就基本上不愛學習了,就變成了班里面最差的那一批中的一員,經常坐在最后面睡覺。
唐:但是它有個過渡,你當時作為一個比較好學的,班里面學科成績不錯的一個學生,轉變成為一個翹課、不學習、愛睡覺(的學生),這樣的一個變化。我特別好奇的是那種轉變是怎么來的,或者是當時你的心理是怎樣變化的,當時是怎么想的,有沒有過一個難忘的一瞬間?是什么能夠讓你放棄過去小學生的那種狀態,轉變成為初中生這樣的一種狀態?
李:那個時候主要的問題可能是因為父親生意的失敗,剛好我是在讀初中,那段時間,我父親有兩年沒回過家,過年也沒回。然后,初中二年級開始,家里沒錢,上學經常被老師趕回家,因為我交不起學雜費。平常這費那費,一交就是一兩百,那時算很多了。這樣,我漸漸地不愛學習了,也趁著被老師趕回家的這個“機會”跑去玩。主要是父親生意的失敗,家庭條件的急轉直下,再加上離家里比較遠,那時候也沒有電話,老師也沒辦法馬上去找家長,所以說那時候就轉變挺大的。
唐:家境的變化,父親的創業的失敗,帶來了生活的變化,包括你的學習和身份的轉變。那你覺得這樣一段兒時的經歷,包括后面叛逆期的一個轉變,對于你后面的生活,比如說現在選擇當一名藝術家,有什么直接的關聯嗎?
李:應該說多少會有一點,如果那時候學習成績一直很好的話,可能來到海南之后,學習應該也挺好的,再怎么說也應該不太會去學習繪畫,即使生病以后也不太可能去選擇繪畫。學習繪畫畢竟比較輕松一點,對我個人來說,對我的身體來說。生病以后,學習成績也不好,即使重新讀高三,再重新考試,也考不上大學,所以那時候干脆就讀了成教班,想去學點書法,畫點什么行畫,給人家畫畫裝飾畫之類的。剛開始就是這種想法,就是為了養家糊口。后來,才慢慢喜歡上藝術,開始接下來的學習生涯。
唐:如果不是因為這樣,如果不是后面的轉變,有可能你就不會接觸到藝術,像你說的學習好的話就不會學畫畫了。那現在來看,成為一個藝術創作者,你覺得當時的那種轉變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油畫《我和兒子》 60×80cm 2012年 李博
李:這個東西你沒有辦法說是好還是不好,畢竟你走到哪一步,是無法預測的。也許當初我一直好好學習下去,考個好學校,或者是上個名校什么的,過得也挺知足挺好的,但是這個東西沒辦法說。只能說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最好的結果就是我畢竟還是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愛好,我還能夠一直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就覺得挺好了。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按照你想象的那樣發展,只是說走到哪里再看,再一步步往前走,只要是你能夠做你喜歡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沒有什么好壞,或者說規定你一定得做什么,畢竟做什么還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唐:就是說人的生活,人的生活的轉變,選擇做什么樣的人,或者做什么樣的事,過什么樣的生活,它并不是由人的一個意志來預定好的,就像你說的那樣:我們還是隨著各種人生的轉變,選擇自己的生活,這也是對命運的一種接納。
李:是的,接受生活,再去發現生活,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堅持做下去,這就是后來的我!
唐:那么你是什么時候接觸到當代藝術的?
李:最早接觸是在2006 年。2006 年的時候去大學里學習繪畫,因為身體的原因就想學一下繪畫。在學繪畫的時候接觸到一些同學,他們比較了解當代藝術嘛,我當時是一點都不了解。所以,經常跟著他們了解到一些當代藝術的信息。那時候當代藝術也比較火嘛,我慢慢地從他們那里了解到當代藝術,包括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等等。了解到以后,我就特別喜歡裝置,特別鐘情于裝置,就從2006年開始,去查一些資料,買一些書,開始去了解它。

裝置效果圖《螺絲釘》 2012 年 李博
唐:剛才你說到比較鐘情、偏愛于裝置藝術,那你覺得做裝置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李:最吸引我的是做裝置藝術時對材料和空間的利用,這兩種東西比較吸引我。像行為藝術,以我的性格,我不太適合做。所以我就把自己縮小在裝置藝術這一塊。當代藝術有很多類別、很多形式,我就特別喜歡利用一些材料,采用一些不同的手法,結合一些空間,去表達自己的一種感想或者是一種體驗,所以就一直在堅持做裝置。
唐:我看到你有很多作品方案的手稿,其中很多做成了效果圖。因為我也是做當代藝術創作的,也會面臨經費的問題。當時你是否也遇到同樣的問題?為什么會想著用效果圖來呈現,它能夠起到一個替代的作用嗎?還是出于什么考慮?
李:有時候想知道作品的具體效果是怎樣的。當自己有個大概的想法時也會畫一些草圖,但是真正想知道最后呈現的效果,你就必須要做出效果圖來,看看是否能夠達到你想要的那種效果。我以前也想去做一些簡單的裝置,也想去把它做出來,所以就做這個效果圖。另外也想去報名參加一些評選,別人要看效果圖,我沒有實物圖,也不敢輕易去把一件裝置做出來,因為經濟條件太差了。做成效果圖的話,就便宜一點。如果有展覽,需要我去展覽某件作品的話,我就可以先把作品效果圖發給他,再去做出來,這樣的話也不會浪費經費。我自己這么多作品,如果只是給別人看草稿的話,別人有時候也不知道你具體想表達什么。因為裝置本身就很注重空間感的那種效果。有些裝置作品,如果我不在旁邊寫上一些闡釋性的文字,有些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做了很多的效果圖。
唐:你覺得藝術和你的關系是什么?
李:反正我自己覺得從我生病以后,也干不了其他很累的活,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接觸了裝置藝術。從感興趣到創作,那時候就覺得我這輩子即使一事無成,我也離不開裝置藝術這種表達形式。我本身就不是很擅長用語言表達的人,但是裝置它會讓我感覺像是一個人寫日記一樣,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呀,一些經歷呀,融入到裝置里面去,用裝置來訴說一些自己的經歷、經驗,自己想說的話、想表達的東西。它就像是我的一種語言、一種私人的日記本一樣,最能表達我內心真實的東西。它在我生命中,就像一個人和他的語言一樣,合為一體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現在,可能在我死之前,我都會一直做下去,即使一件作品也賣不出去,哪怕自己的作品從來得不到那種所謂的高端成功藝術家的認可,但我覺得總會有人去理解它,所以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唐:我覺得無論做藝術也好,還是做其他形式的事情也好,對一個人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它成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一種精神方面的組成部分。其實你剛才說到了一點,不管在這個系統里面、在這個圈子里面,能否獲得知名度或者所謂的成功,我們仍然會繼續做。我們也看到很多人,包括以前有一些藝術家,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好像是帶著某一種目的性或者某一種功利性去進行藝術創作,做了一段時間以后,可能有一些人最后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就停止或者轉向了。但是你仍然還在堅持著,特別是你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之下,還是堅持在做,不管是做方案還是對這方面的思考,我覺得都是挺可貴的。你是一個真正熱愛藝術和做藝術的人,這一點很打動人。接下來,我想請你來聊一下,你是如何看待當代藝術在中國的現狀的?
李:現狀的話,我覺得大部分做當代藝術的藝術家,比較傾向于市場。他們可能也是受市場的影響,受生活各方面因素的影響。為了讓作品好賣一點,有些做得很花里胡哨,或者是景觀式的那種,能吸引大眾眼球。但真正純粹的,去關注當下一些事件,關注當下社會的某種現象,去做出一些真實的、批判性的東西,我就比較喜歡。只有思考當下,這個社會才會更加進步、更加美好。
唐:你剛說到一點就是當代藝術需要批判性,在我看來也是如此。當代藝術之所以成為這時代所謂的一個先鋒(過去我們也會把它稱為先鋒藝術),是因為它具有這種批判性。我覺得這是當代藝術的本質之一吧,我也是非常認可你的看法。
李:不僅是對社會的批判,還有對當代藝術自身的一種批判。
唐:對!也就是說它并不是一個所謂的組織或者是固定的某個流派。當代藝術不是一個流派,當代藝術講的是思想價值的問題,它永遠都站在一個批判者的角度上。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李:當代藝術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唐:對!多元化是當代藝術的一個重要思想理論。剛才你說到自己的病痛的問題,那么能不能談一下這一場病?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以及對你來說它意味著什么?
李:發病的時候是2004 年,我在高三上學期,之后做了移植手術,五年之后又發病,然后就一直到現在。這個社會,生病的人很多,比我更慘的也有很多,所以說生病對于我來說,是我必須接受的一種現實吧,就像做裝置作品一樣,你必須去感受那種真實,去接受它,接受之后順其自然地去生活吧。
唐:當初在高三的時候,你年齡應該也是十八九歲。
李:那時候是十九歲。
唐:十九歲,當時你對這種病有了解嗎?
李:一點都不了解!我當時身體很不舒服,去醫院,有經驗的醫生一看全身浮腫啊、心率快啊、血壓很高啊,就直接讓我去抽血化驗。因為是急診,結果很快就出來,半天時間吧,各種指標出來以后就診斷為尿毒癥晚期。
唐:當時,你知道尿毒癥晚期這個診斷結果之后是什么心情?
李:高中的時候還不是特別成熟,我也不知道會一直透析,那時候不懂,我以為半個月、一個月這樣子出院以后就會好了,從來沒有想過透析這么多年。那時候父母也一直陪在身邊,都是安慰說,沒事的。

李博手稿
唐:沒告訴你實話。
李:對。我也沒意識到這個病的嚴重性,也不懂。
唐:什么時候才知道這個病的嚴重性?
李:大概做了半年透析以后,就知道這個病沒辦法醫治,只能做腎臟移植。透析一年以后就做了腎臟移植手術,后來才了解到即使做了腎臟移植,也是有年限的,后面基本上就比較了解了。做完腎臟移植以后,就看靠自己保養的情況了。
唐:可以談婚姻的問題嗎?
李:可以。
唐:你結婚是在什么時間?
李:我在2007 年結婚,大學沒有畢業,上一年大學,出來就結婚了。2006年,上了一年的成教班。
唐:是在省內還是省外讀?
李:海南大學的成教班,混了一年,2007年結婚。
唐:當時跟你老婆,現在算是前妻了,當時你和她在一起是怎樣的一個機緣?
李:是家里人介紹的嘛,她和我是同一個地方的人。結婚之前我也把我的這個病告訴她了,她也能接受。以為(腎臟移植)可以用很長時間嘛,起碼用個十年八年,沒想到五年就壞了,我又發病了。從我又發病以后,家里面經濟條件又開始下滑了。
唐:我記得以前你做過一個行為作品叫《求生之路》。你當時在寫關于征集器官捐獻的一封公開的求助信。如果有人遇到意外后,當他意識還清醒的時候——我不一定記得清楚,你可以糾正一下——就是說希望有這樣的一些人可以把腎臟捐贈給你,是這樣嗎?
李:對。但是這個行為藝術作品的初衷并不是說真正為了去尋找一顆腎源。我當時做的背景是,那個時候在中國愿意去捐獻身體器官的人很少,包括什么肝移植、心臟移植,這些都非常非常稀缺。很多人都等著這個救命,需要別人捐獻。但是在國外很多,包括國外很多健康的人,他們都會有個生前遺囑,有遺體和器官捐贈的協議書。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想從身邊的朋友開始,一點點去影響大家對這種器官捐獻的理解。這樣的話,以后捐獻的人肯定會越來越多,就像現在很多人都開始捐獻了。一個人腦死亡以后,他的身體器官可以救活好幾個人、好幾條性命。現在的人的思想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了,也是因為社會的進步。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非常好的現象。
唐:當時,我記得是你的前妻愿意跟你簽了這個協議。
李:對。她愿意簽。
唐:當時已經離婚了?
李:嗯,離婚了。她愿意捐獻,但并不一定是捐獻給我,因為這個是要配型和排隊。我如果跟她是夫妻關系的話,她是直接可以捐獻給我的,但是我們已經離婚了,即使她要捐獻也不一定輪到我。她跟我簽這個協議,是我想讓她參與進來,因為她也是一個比較善良的人。假如出了事故啊什么的,如果她愿意捐獻器官的話,也能救活很多人,但不一定是我,我只不過是想要通過這個行為藝術,讓身邊的人去了解器官捐獻。
唐:對。我當時在康學儒策劃的“海的距離”那個群展的時候看到你這個作品,印象很深刻,尤其深刻的是你的前妻愿意簽了這樣的一個協議。雖然說她不一定把這個器官捐給你,因為你們已經結束婚姻關系了,但她是在你身邊的人中第一個去響應你的人。在我看來這是挺能打動人的一個行為。其實她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是普通人,不過她是一個非藝術家的身份,而且她也不是很喜歡寫作或者做其他藝術創作的人,我們只是比她多了一個(做藝術的)嗜好而已,但是她卻能夠支持或者理解你的這個行為和作品,并且作為第一個參與的人。
李:因為她跟我畢竟生活了這么多年嘛,對這個病情也比較了解,所以她可能比一般人要更加地知道器官捐獻的重要性。只是我們的婚姻走到了盡頭,但是她對我這個行為藝術還是很支持,而且很理解。因為她畢竟接觸我的這個病情有很長時間,她比一般人要理解,所以她就第一個簽了。
唐:對。而且我感知到你也挺接受這段婚姻的離舍的,也能夠理解她。
李:我能夠理解。
唐:嗯。是你提出來離婚,還是她提出來?
李:她提出來的,那時候小孩還小。她之前就有提過,我當時沒答應,是因為小孩子才幾歲。我就跟她說,你可以去外面打工,但是先不要正式離婚,先不要影響到小孩。但是后來小孩長大幾歲,她覺得小孩可以接受了,然后我說,你既然覺得小孩可以接受,那么我也沒有辦法去阻礙你的。畢竟兩個人可能三觀方面不太一樣,雖然她也是一個比較善良的人,而且我的身體狀況、經濟情況也不好,自己沒有經濟來源,對于她來說都是一種束縛。所以說與其這樣子,還不如讓她自由。我覺得要互相理解,就像她愿意第一個跟我簽那個協議一樣,互相理解嘛!
唐:當時結婚的時候,是父母有這種欲望,還是你有這種欲望?
李:我們結婚,是比較草率的那種,她那時候年齡也不小,她比我大半歲。我家里也是急著讓我結婚,就是讓我傳宗接代,帶著一個目的性。她家里也是帶著目的性的。那個時候,她也是為了快點結婚,再加上我家里那時候條件還可以,我們就很草率地結婚了。在我們農村,很多人都是這樣,都是經人介紹之后,半個月一個月就結婚了,然后又出去打工。所以說,為什么現在八后離婚率很高,是有原因的。
唐:就是說她開始結婚的時候,是在一個比較草率、懵懂,或者不是在自己全然的意志之下結了婚的。所以到最后她還是會覺得自己隔了一層,當大家都可以坦率地去面對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婚姻的變化,其實都可以理解。
李:互相都可以理解,沒有什么怨恨之類的。
唐:其實都是一代人,不管是男方還是女方,好像都是父母左右了很多。
李:特別是八后這一代。
唐:很多人的婚姻都會有父母的一個想法在里面。當他們在度過婚姻的時候,就知道婚姻的這種尷尬存在著某種不可調和。然后各自都想再追求一下自己的生活,這個時候就會提出離婚的想法。這個是可以理解的。接下來我想請問你,你是如何去面對這種病痛呢?你方便說你現在還有其他的什么病嗎?
李:我現在是尿毒癥晚期已經十九年,最近又查出肝癌晚期。反正經歷了這么多吧,我覺得受的苦我也熬過來了,對于生死這個問題或者說得了兩種重病,我已經可以非常平靜地接受了。我確診肝癌的那一天,我心里就挺踏實的。真的!因為我感覺不管是尿毒癥十多年也好,還是得了肝癌晚期也好,就是說我的生命已經快到盡頭了。而且這么多年面對生死,都不知道什么時候突然會死掉,這是很焦慮的。就像一個殺人犯在外面逃,每天都是提心吊膽的,但是突然被抓到以后,反而踏實了。
唐:這種踏實是來自于什么?
李:來自于有了一個確切的結果,就是知道我的時間還有多長。然后,心里的那種焦慮感就減少了很多,就不會再擔心我什么時候死呀,我還要活多長時間呀!因為這個病一般都是,快的話兩三個月,慢的話半年。而且,現在我家里也沒有錢去治療呀,吃什么藥呀,就是已經完全放棄治療,只是在做透析而已。
唐:就是還在做針對尿毒癥的這個透析。
李:肝癌的話,就是放棄治療了,就這樣了。所以說自己過一天少一天嘛,好好地開心地去過吧。
唐:對于我來說,可能不會存在這種焦慮,因為我沒有病痛。我其實有點害怕和恐懼發生那種不知所措的意外。你面臨長期的十九年的病痛,當時診斷就已經是尿毒癥晚期了,這十九年來,你覺得比較痛苦的是什么?
李:十九年來最痛苦的就是沒有自由。因為離不開醫院,不管去到哪里,首先要找醫院,而且隔一天去一次,完全沒有自由。得尿毒癥的話,不能亂喝水,吃東西也要小心,睡覺也睡不好,身上也癢,還要面臨一些并發癥,面臨透析中的高血壓、低血壓等等各種問題。很麻煩。這十幾年,真的是有生不如死的感覺。再加上事業上,可以說是一事無成吧,三十多歲還是啃老。十幾年來,這些東西都是一直在困擾著我的。所以,當我得知又得了肝癌晚期以后,我覺得以后不用再面對這些了。我覺得這就是命運的一種安排吧!如果不是肝癌晚期,是我自己跳樓或者什么樣的話,可能別人會覺得我多少有點不負責任,對家庭呀,對小孩呀,是吧?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對于我來說,我可以接受。而且我能夠非常平靜地去接受,非常坦然。我確診以后誰都沒告訴,父母都沒告訴。
唐:到現在也沒說嗎?
李:現在他們知道了,因為還有一些后事需要我去交代嘛!我交代給我姐了,后來我姐告訴我父母。父母也理解,他們知道家里條件也就這樣,不可能再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他們也慢慢地接受現實,畢竟我也生病十九年了嘛。他們也知道早晚會有這么一天。
唐:說到父母的話,作為父母的角色,面對自己的孩子十九年的病痛,這樣的一種折磨(是十分巨大的)。對于你父母來說,我想他們也不輕松。
李:對!父母也過得比較辛苦,這些年。
唐:父母也是過得比較辛苦的,因為自己的孩子。但我們也沒法知道他們當時的想法,但是這么多年來,他們應該跟你差不多,(現在)也是有一種解脫感。現在反而好了,像你說的,都很坦然了。對于自己的生命,面對這十九年來的病痛,在掙扎和抗爭中度過。當然,這個也是需要意志的,我覺得如果意志薄弱的人,可能會像你說的那樣,會用其他的方式來結束生命。另外,談談我們最近要籌辦你的這個個展吧。你覺得這個個展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李:這是我第一次個展,也應該是最后一次個展了吧!對于我來說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做藝術,一邊學習,一邊創作。從2007 年開始吧,一直到現在2022年,有差不多十五年了吧。這是對我自己的生命的一次總結吧。回過頭來,從開始接觸藝術,畫畫,創作裝置,一路走到今天。這個展覽可能包含了我這十幾年的一些創作的過程,還有一些對于這個社會的體驗和思考,等等。這也算是對自己的一種回顧吧。
唐:就是個人的藝術史的一個回顧。可以這么理解嗎?
李:可以。
唐: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繪畫,接觸美術,后面還讀了成教班?
李:就是2005 年做完手術以后嘛。2006 年,過完年,我本來是打算學書法的,因為書法比較輕松,以后可能寫寫對聯呀,去靠這個養家糊口,想得很簡單的。
唐:當時還是很功利化的,就希望學個小技術,學個手藝。
李:2006年就去了海大的成教班,跟著同學畫畫,老師也不管,也不教,靠同學教我。2006年學了一整年,2007年結婚,就再沒有去過學校。
唐:高中之前你是沒有接觸過藝術,也沒有想過要學這個?
李:根本就沒有想過,我連看都沒看過。我那時候從農村過來的,根本就沒見過那種繪畫呀、石膏像呀,沒見過!完全是一無所知的狀態,包括我2006 年去學習,我都是很驚訝的。進去一看,唉,怎么能夠用鉛筆畫出大衛這種這么立體的石膏像?這直接把我給震撼到了,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

李博個展現場的自畫像 小曹 攝
唐:剛才我們說到一點,你是2006 年接觸到當代藝術嘛,當時你是從什么渠道接觸到的?
李:對,2006年,當時就是通過同學了解到的。
唐:同學也是在討論當代藝術和藝術家的作品。
李:那時候很火嘛!當代藝術。所以說經常聽他們講一些當代藝術的事情,包括看一些繪畫。
唐:跟老師有關系嗎?
李:跟老師一點關系都沒有。
唐:純粹就是這種信息在社會上傳播以后,學生自己獲得了這樣的一種信息。
李:可以說是同學讓我了解到了有當代藝術。然后,學習全是靠自己自學,自己創作。
唐:其實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解,還真的沒有所謂當代藝術課程,可能你學得更多的是當代藝術史、美術史這樣的東西,甚至沒有固定的所謂課程。下面這個問題也許我不該問,但是我也想更敞開一點說,剛才說到你會在家里面有交代一些后事,我不知道你對我們有沒有這種交代。我們認識有八九年了,是好朋友的關系了。你對我們這些朋友有沒有一些想要說的?
李:2014 年,是我最焦慮的一年,也是我鼓起勇氣走出來的一年。之前一直都是不跟任何人聯系,不跟外界聯系,然后我就走出來找到以前海大的一些同學,就知道了江萍,還有他們當時做的海口當代藝術館(王小飛創辦的)。我就去找江萍了,她就把你們介紹給我,我就在這個圈子里面認識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多一直在幫助我的人,讓我從焦慮里面慢慢走出來。一直到今天,即使很長時間不聯系,你們這些老朋友、藝術圈朋友,一直都是很關心我的,一直在盡全力幫助我。真的,我是很感謝你們的,很多人。
唐:不用客氣。那還有一個問題,你覺得做藝術創作的話,最要緊的是什么?一個人要做藝術創作的話,他應該持怎樣的一個態度?
李:要真實地表達自己,要非常理性地去看待這個現實的社會。也許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我只能用自己那種可能跟別人不一樣的表達方式,去盡量真實地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感觸,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真實、客觀、理性。要一直保持這種初心,然后要堅持下去。這就是我做當代藝術的理念。
唐:今天我們剛好是用了一個小時,談了一些話題,當然有可能我問的也不一定很全面啊,不過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訪談或者是一個記錄。我覺得是挺重要的、挺珍貴的。
李:你們以后可能還會想起我這個朋友吧。
唐:那肯定的。在每個人的生命當中都會有這種記憶,這種經歷,這種生活,都會有。謝謝,那我希望盡快在一月十號左右,我們張羅起來,一起來把你這個展覽做起來。
李:非常感謝你們!你們替我完成這次展覽,完成我這輩子最重要的心愿。非常感謝!
唐:不客氣,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這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我們在海南真誠地做當代藝術的,是特別少的,而且很多人做著做著也沒辦法持續,但是你即使在很困難的時候,也還在持續地去思考和關注,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真誠地去做藝術的人,我認為做藝術很需要這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