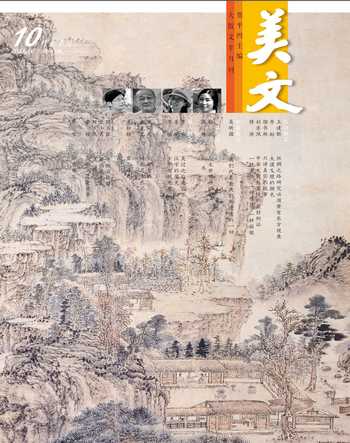瓦松·桄榔
瓦上有“松”
七年前的深秋,我在深圳的田寮社區有著一枝之棲。有一天路過龍灣路,池塘邊一棟老房子引起我的注意。與別處不同,它的屋頂上擎著一個紅五星。初步了解,這兒是原龍灣生產隊隊部之所在。只見正門的老墻縫冒出一株瓦松,它彎腰下探,非但不因杌隉而不安,反倒有著處之泰然的意味,大有一種置身危崖的松樹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勇毅。以后每次行經那兒,我都要朝它注目致意,表達由衷敬佩之情。
瓦松,是道道地地的中國多肉植物,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是其產地,我的故鄉——華中地區亦是它最重要的產地之一。奇怪的是,此前它在我的田野知識里竟是一片空白。我對它的關注還是南來后,在一個原本“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的地方——田寮,才與它邂逅。難不成我與瓦松都像鳥一樣飛到南方,認準這兒就是宿命所歸之地?我們的相似之處還在于,在貧瘠之地見縫插針,讓生機從針尖迸發出來,這也是它令我怦然心動的所在。
在以夢為馬的游子心目中,深圳是繁華的現代化都市,年輕、亮麗、魅力四射,令人得以傾心歸附的除了傳說中遍地取如拾遺的機遇,還有它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的包容性,使得它成為四十余年來熱度不減、魅力不怯的筑夢的熱土。這兒有一個貌似可以填平此間一切溝壑的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前提當然是你首先得把自己當成深圳人,渾然地融入這片熱土。“世界如其所是。”奈保爾說,“那些無足輕重的人,那些聽任自己無足輕重的人,注定了在世界上沒有位置。”推而及之,所謂樂土就是為有備而來的人們準備的。這是色彩斑斕和高度城市化的繁華之地,城市的天際線大抵由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繪上浪漫的一筆,天際線下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將晝之白與夜之黑攪合得渾然一體。
其實,這個青春朝氣的都市還有多元呈現的點、線與面,它的襞褶里尚有諸多農耕社會的遺存,最常見的是輝煌的祠堂、低矮的民居、窈然的古井、斂碧的池塘、蔥郁的風水林。這兒的許多地名也打上了農耕時代的烙印。廿年來,我在不少地名土得掉渣的地方淹留過:鹽田、沙井、松崗、塘下涌、李松蓢、薯田埔、田寮、坑尾、水田……每個地名都在矜持地講述自己難以湮滅的歷史。五光十色、人潮洶涌是它的后發之勢,歷史的幽邃才是它的前塵。就在一片推陳出新和摧枯拉朽的砉然巨響中,其貌不揚的瓦松在鋼筋混凝土的城市夾縫里隱韌地存活下來。
應該說,與瓦松的邂逅是一種難得的緣分。因為這一路走來,我的暫棲之地大多已被參差不齊的“接吻樓”給占據著,它們勾肩搭背卻牢牢地掌握著話語權,經常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愛倫·坡那個關于人造建筑是大地傷疤和方塊狀贅疣的比喻。目下,比屋連甍卻低矮湫隘的民居早就踅入了歷史隧道的深處,驀然回首,那凄迷的眸光還不時閃過一抹抹柔媚的光華,讓人平添些許難舍的情愫——基于這一抹珍貴的情感,許多原本頗具規模的老民居又破繭重生,被修葺或重建,甚至還搖搖晃晃地挺直了腰桿,變成旅游景點,供人探古尋幽,抒發懷古之幽情。更多垂垂老矣的民居則藏身于鋼鐵叢林的深處茍延殘喘,恍惚還在用蒼老乏力的聲音叨念農耕文明的田園之樂。瓦松僥幸逃出生天,得以賡續自身攜帶的基因傳奇,在風中、在鳥喙里飛起又落下,命懸一線又重獲新生。而它的存在,亦是城市多元化一個有些漫漶的印記。
瓦松絕非現代城市文明的天然擁躉,它對鋼筋、水泥、瓷磚、柏油、玻璃等諸如此類的現代建材總是唯恐避之不及。它賴以生存的條件極其簡約,一堵老墻、一片黛瓦、一點稀薄的塵土便可以讓它有如東山高臥的隱士,悠然地低吟屬于自己的《擊壤歌》,歌曰“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的,對它來說,帝力是無所謂的,真正帶給它致命打擊的是,隨著時移世易,屋檐上的那份逸豫早就置換為鋼鐵叢林的恓惶,讓它審容膝之易安的饜足也難以為繼。這個植物界的圣徒比美國康科德特立獨行的思想者梭羅走得更遠,一直行走于簡約的極致,用一把奧卡姆剃刀毅然決然地割舍生命的贅余。瓦松是簞食瓢飲的顏回,身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相較于肥沃的卑濕之地,它寧可選擇干旱的坡地或毫無回旋余地的石縫瓦溝。它沒有翅膀,但向往像鳥雀一樣在悠悠高旻自由地翱翔。這也讓人對它產生了誤解,把它看成趨炎附勢的澆漓之徒。但總的來說,毀譽的天平還是朝著稱譽的一邊傾斜,畢竟,安貧樂道才是它一貫的安身立命之本。唐人崔融在《瓦松賦》中贊曰:“進不必媚,居不求利,芳不為人,生不因地。”說它簡直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存在。
在有些地方,瓦松被視為老宅的靈魂,不但賦予它“墻不倒”的諢號,還被奉為“房神”。似乎只要有它坐鎮,這個大宅門就安如磐石,住家便吉祥止止。瓦松,誠如其名,迨及層層疊疊地長成一片,遠觀之下的確頗似松林的縮影,有一種悠然的意味。王夫之詩贊“檐影分仙桂,珠光浥瓦松”。瓦松雖然生性簡樸,足跡卻撒得很遠很遠,一直登上廟堂之高,那就是唐人李華所說的“華省秘仙蹤,高堂露瓦松”。
瓦松別名“瓦花”,曾在九五之尊的天語綸音中閃出一道異彩。魏明帝曹叡大修東宮洛陽的宮城時便特意下旨,說自己當年御駕親征,攻打長安,望見那兒的城郭瓦花爛漫,現在打算將它們移植過來。盡管洛陽也有瓦花,但長安的瓦花似乎別有一種韻味。他還饒有興味地回味著那次大捷,打得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著稱的諸葛亮落荒而逃,只得把吃了敗仗的過錯一股腦都記在丟失街亭的馬謖身上,最后揮淚斬馬謖。曹叡邊說邊暗中觀察司馬懿的神色。他知道這個喜怒不形于色的股肱之臣城府極深,但又抓不著狐貍尾巴,只能不時對他敲敲打打,以警醒他,讓他徹底明白今日魏國究竟是誰家之天下。曹叡有關瓦花的潛臺詞是,哪天你要是惹得我不高興,我也可以讓你從此徹底消失。只是到頭來他還是沒能抓住置司馬氏于萬劫不復的機會,沒過幾年就龍馭上賓。
瓦松有過它的黃金時代。遠在唐代,據崔融描述,彼時崇文館的屋檐上瓦松千株萬莖,吐葉開花。在詩人眼里,瓦松有著清寂和蕭條的意味,“屋老瓦松長”這樣的詩句在陸放翁的詩中反復出現,大有要流于口頭禪的趨勢,須知,惜墨如金總是被金牌詩人奉為圭臬。后來,瓦松的版圖日漸衰落,到了有清一代,詩人黃景仁是這樣寫瓦松的:“寂寞誰家院,憑來客夢家。吟聲振高閣,落得瓦松花。”
在《本草綱目》里,瓦松被賦予一個令人有些不解的別稱,“昨葉何草”。原來,人們一直以來都對這種其貌不揚的兩年生草本植物有些琢磨不透,只見它頭一年還只是安靜地長成蓮座的樣子,第二年卻搖身一變,長得像松塔一般,開花結果,好似兩種不同的植物。清代書法家伊秉綬給陳嵩慶題寫過一個橫額,是用顏楷筆意寫的隸書“昨葉書堂”四個大字。現代人不明就里,揣想“昨葉”在這里是不是瓦松的別稱。據說這幅匾額現在起拍價已高達上千萬。
現實中,有著“房神”美譽的瓦松早就從神位上跌下來,復歸于自帶衰敗氣息的野草,人們修繕房屋時總是隨手將它拔掉。
在深圳,瓦松除了承受業已完成的城市化進程對農耕文明的滌蕩,使它處于岌岌可危的生境之中,還面臨著千奇百怪的現代建材給它帶來的犁庭掃穴般的打擊。因此,當我在深圳某個村墟的小巷與幾株瓦松邂逅,我會深情地凝望著它們,因為我深知它們的不易和矜貴。就在它們帶給我片刻出神中讓我領受到一種睽違已久的田園氣息。恍過神來,我望見不遠處有一株綽約多姿的桄榔。
桄? 榔
我對棕櫚科植物的喜愛由來已久。兒時,透過一抹椰樹的剪影,讓我對南方的熱帶風情神往不已。愛屋及烏,那種神往在現實生活中有了具體的投射物——蒲葵。楚地多蒲葵。楚人將它的功用發揮到極致,葉子除了可以制成蒲扇,細葉還是唾手可得的細繩,殺豬佬往往用它系肉,棕毛可以制成棕繩、棕席和簑衣。簑衣一度是我家最重要的雨具之一,是我家的傳家寶。對于尋常農家來說,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雨天亦勞作不輟,每逢其時,爺爺就穿上簑衣,與風雨頡之頏之,再大的雨水總是來不及滲透就滴落在地。
炎炎夏日,似乎讓我觸及了邃古之初后羿尚未射日時的酷熱,熱浪搖撼之下,草木為之震顫。這當兒,手搖蒲扇自然是無上清涼的美事。所謂羲皇上人,應該是扇不離手吧。我們當地有一舊俗,端午節走親訪友順便送幾把蒲扇。我也有一把蒲扇,扇面上寫著我的名字,還題了一首打油詩,其中兩句是“你熱我也熱,扇子借不得”。雖然借不得,我的蒲扇還是屢屢被人順走。就算在某個時刻我與別人的儻來之物似曾相識,但因為扇面已經換作別的名字我也奈何不得。我在小園栽植了幾棵蒲葵,憧憬它們易長易大,蔥翠怒發,可以在我的頭頂呼風喚雨。但它們委實長得太慢了,一陣驟雨飆風,我的腳印便散落在大地山河的襞褶里。山川冉冉,歲月骎骎,當我多年以后重返故園,驚喜地發現那幾棵蒲葵竟然已經高過人頭,棕毛飄飄,似乎還有待我為它們打理呢。
南來后,椰子由抽象的剪影變成了具象。這才發現,嶺南的棕櫚科植物甚蕃,據我所知就有棕櫚、蒲葵、棕竹、椰子、油棕、魚尾葵、假檳榔、大王椰……自然也少不了出類拔萃的桄榔。
桄榔早就出現在嵇康的侄孫嵇含的傳奇大作《南方草木狀》里,這一書寫開創了中國地方植物志的先河。它之所以堪稱傳奇,是因為其時嵇含雖然已經被授予廣州刺史一職,但此君未及上任就在戰亂中不幸罹難,因此作為秘境的嶺南自始至終都只在他夢里。這部光彩粲然的著作的誕生一如從未到過岳陽樓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一樣,都是神來之作,同樣流傳千古。
關于桄榔,嵇含如是記述:
“桄榔,樹似栟櫚實,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為舟。皮中有屑如面,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面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理,工人解之,以制弈枰。出九真、交趾。”
“胡人”二字透露了些許內華夏外夷狄的草蛇灰線,是當時內向天下觀的心理投射。這段文字讓我看到了桄榔的細部,說明采用桄榔須連木為舟已經為時已久,起碼要早于嵇含所處的西晉。根據唐末劉恂《嶺表錄異》記載,其時打造商船不用鐵釘,只用桄榔須縛緊,用橄欖糖做填充物,糖漿干燥再入水的效果等同于現代常用的桐油石灰。桄榔須的妙用在于,經過海水的浸漬就會膨脹,其強韌和耐腐性便充分激發出來,南越之民用桄榔須縛船、織巾,當然也用它編織生活的綺夢。橄欖糖是橄欖樹的精華,用橄欖樹脂、樹皮和枝葉熬制成的泥狀物。當桄榔須與橄欖糖相遇,一艘乘風破浪的船便呼之欲出,人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便有了更多從容和保障。唐德宗年間,瓊州郡守韋公干貪黷成性,私蓄四百奴隸開設手工作坊,生產各種各樣的手工器用。為了將產品源源不斷地運至廣州牟利,他派人在海南大肆砍伐堅韌的良木用來造船,自然也就少不了桄榔須與橄欖糖的大力襄助。值得一提的是,桄榔木本身也是造船的優質木材。想不到吧,暴戾與貪婪的副產品竟然推助了當時造船業的發展。
桄榔除了器用之外,還是嶺南重要的輔助性糧食作物,其幼嫩種子的胚乳經過糖的醞釀可制成蜜餞。木心富含淀粉,桄榔粉自古以來就被視為一味良藥,對疴吐溫熱或熱性癥疾具有一定的療效。《海藥本草》指出它的藥效,作餅炙食,補益虛羸乏損,腰腳無力。桄榔粉最常見的吃法是制成桄榔面,或與牛奶共食,或做餅而食。早在漢代,桄榔面就是海南人的天賜食糧。據《后漢書·夜郎傳》記載:“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面,百姓資之。”其實,桄榔面早就聲名遠播,魏晉左思《蜀都賦》曰:“異物崛詭,奇于八方。布有橦華,面有桄榔。”可見當時成都的物質生活十分豐富,商人已經把桄榔面帶到蜀都。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沒有忽略這種地方特色的糧食。他說海南盛產桄榔樹,高產,有的大樹出面百斛,和著牛奶一起吃,讓人的味蕾有著全新的體驗。
桄榔可以制糖釀酒。《野生植物圖說》指出,桄榔的花序用來制砂糖,每株每年可產糖10公斤,有的更是高達50公斤。糖和酒,意味著奢侈的甜蜜和讓身體適度的陶醉,人們從桄榔樹上就可獲得。
到了清代,桄榔面仍然是海南最重要的糧食之一。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海南某地的人在饑饉之年全靠桄榔過活,耕者甚少。還說海南人習俗是“檳榔為酒,桄榔為飯”。這讓我想到,在我兒時,位于華中腹地的故鄉還有“半年南瓜半年糧”一說,更有超支和衣食之虞。有一年苧麻價格一下子跌到谷底,麻賤傷農,幾乎讓苧麻產業瀕臨滅頂之災,苧麻被傷透了心的農人挖去大半。奇形怪狀又有些腫壯的麻蔸堆在一起,做柴禾尚嫌火力不足,但麻蔸富含淀粉,人們荒年的記憶被瞬間激活,有人碾碎麻蔸,像加工苕粉一樣讓麻蔸獻出淀粉,再做成黑乎乎的麻蔸粉耙,雖說不上好吃,但味道獨特。那是苧麻大難臨頭時為人們所做的最后的奉獻。時至今日,猶記得那種摻雜著粗糙質感和絲絲甘甜的滋味。
不要以為生在太平年代,含哺鼓腹便是必然,其實在過往的眾多年月,人們為了捱過饑荒總是絞盡腦汁。雖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但有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最悲慘的就莫過于春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了。總之,在過往歷史的許多年月,填飽肚子往往是第一要務,為此人們著力于拓寬食物的來源。出于有備無患的目的,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曾經親自參與編撰《救荒草本》,它是一部專講中原地區的植物并結合救荒方面的植物志。
人們愛桄榔,也贊譽它,桄榔樹——一條心,應該是一副慈悲心腸!
一〇九七年七月,年逾花甲的蘇東坡已經在惠州熬鷹般地捱過了一年多,接下來,他的命運將和儋州的桄榔緊緊相連。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到了他這里就變成了以天地為棟宇,以桄榔為裈衣,不僅僅如此,他和光同塵,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
客套的文章還是要偶一為之的,但希望之光實則比一粒螢火還要微弱。在上書給皇帝的《至昌化軍謝表》中,他低到了塵埃:“而臣孤老無托,瘴疬交攻。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于海上,寧許生還。”
哀憐的心已經哀憐過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一個異常有趣的靈魂斷不至于還要像蝸牛一樣一直背負鈣質的軀殼。
垂老投荒,生還無望,遺囑已擬: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
死得干脆,死得徹底,也就是生寄死歸了。
七月初二,對海南人來說,是一個值得銘記和紀念的吉日。世人皆說,東坡不幸,海南幸,然則,海南之幸又豈能以東坡不幸作為鋪墊。
那一年,蘇東坡已經年逾花甲。在此前的二百多年前,新繼位的唐宣宗因為忌憚趙國公李德裕功高蓋主,對他啟動了連番的貶黜模式,先是將李德裕貶為潮州司馬,未幾又貶為崖州司戶。在顛連頓踣的途中,李德裕寫道:“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巧合的是,那一年李德裕也是六十一歲,沒過兩年他便病故崖州。厄運的軌跡驚人相似,難道也預示著蘇東坡會有相似的結局?!
在那個年代,有著“蘇海”別稱的蘇東坡絕對是傳奇中的傳奇、奇跡中的奇跡。那時沒有報紙、手機和互聯網,但他早就名滿天下,到處都不乏粉絲。有的鐵桿粉絲本身也是腹笥宏富的知識分子,他們癡心不改地追隨著蘇東坡,無論九垓八埏,不論順境逆境。
昌化軍軍使張中也是“蘇粉”,他自作主張將蘇東坡安置在當地官方招待所——倫江驛官舍。說是官舍,其實里面不過是環堵蕭然,空無一席,但即使如此,蘇東坡還是很快被人趕出來,招致一通嚴辭譴責,就連張中也因此丟官。
就這樣,海南的桄榔翼護著一代文豪,“文章憎命達”在此有了明證。
荒誕滑稽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曾幾何時,對戴圓履方的萬物靈長來說,幕天席地不再是超脫之語,而是生境的真實寫照。好在,結成人間的內在凝聚力一直都在,那就是真誠與熱情。由當地熱心人士黎子云牽頭,連同十幾個慕名前來向蘇東坡求教的學生,以最快速度在桄榔林里為先生蓋起了五間茅屋,是為“桄榔庵”。它將與杜甫草堂一道并列為中國讀書人的精神圣地。
感激之余是無盡欣慰。對大文豪來說,最好的方式莫過于援之以筆,可楮先生竟然暫付闕如,只有桄榔的芳香分子在激活他的腦細胞。先生腦洞大開,曩昔不是有所謂的貝葉經嗎,那么就寫在葉子上。他一揮而就寫下《桄榔庵銘并敘》,銘曰:
“百柱赑屃,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斤鈇。”
作《新居》一詩,詩曰:“……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
他頻頻寫信。致程秀才:“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和陶和劉柴桑:“……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疏……”
給鄭靖老:“近買地起屋五間一灶頭,在南污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
贈南華寺禪師桄榔杖:“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杖,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桄榔也是友情的見證。
蘇東坡一生,從不乏人間煙火的溫情。屋旁有一荒池,但這個生活藝術家沒有聽任荒廢,而是將它改造成一方美池,植上荷花。又將鄰近一處黎宅改建成講學會友之所,名為“載酒堂”。沒過多久,就書聲瑯瑯,弦歌四起將從這兒傳開,輻射到整個儋州,使得天涯海角成為整個海南的文化中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儼然是喧囂塵世一道最美的風景線。受教于蘇東坡的姜唐佐成了海南歷史上第一位舉人,在蘇東坡走后不久,昌化軍人符確也考中進士。
雖然只有瓊州別駕的虛銜,蘇東坡仍初心不改,想干的事情一件都不曾落下,充實了桄榔林下的流年。宦海沉浮,有人受不了;寵辱得失,有人放不下。于是,世間便有了由極度精神潔癖而走極端的人生悲劇。蘇東坡早就超越了只有通過職務升遷才能體現不斷做加法的人生價值的狹隘心理,要知道,古往今來有多少人都深深沉陷于這個怪圈。
他自認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兒。
這內心無比豐贍的生活藝術家,似乎有著讓晦暗的生活變得流光溢彩的魔力。從此,世間便有了東坡肉、東坡魚、東坡酒、東坡墨、東坡苙、東坡路、東坡井……
桄榔還有鮮為人知的別名“須木”,正所謂:“勿言天涯,可以為家。食有須木,飲有酒花。”
我還想附上一句:野有蔓草。
(責任編輯:孫婷)
金克巴 原名金學舜,現居深圳。魯迅文學院廣東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學員。作品散見于《天涯》《散文》《中國鐵路文藝》《中國校園文學》《福建文學》《湖南文學》《天津文學》《四川文學》等刊。部分被《新華文摘》《散文·海外版》選載。曾獲首屆汨羅江文學獎散文九歌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