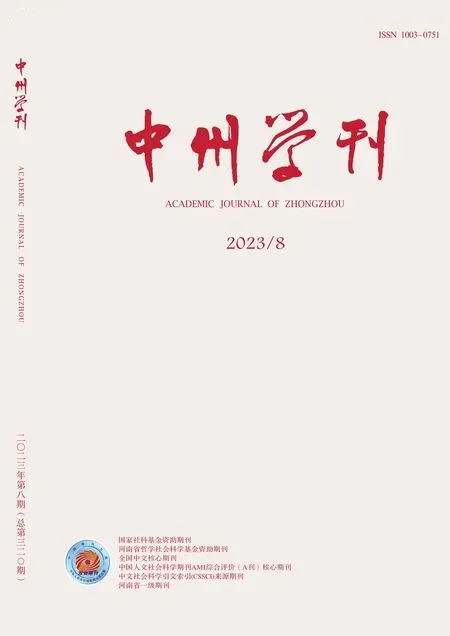大眾文化視域下的海派話劇圖景
尹 詩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海派話劇①即使以今天眼光來看,其繁榮景象也是異常耀眼的。它以市民性的彰顯與解放區、大后方話劇區別開來,在百年話劇發展史上留下了市民圖景的印痕。以海派話劇和大眾文化的關系作為文學史研究的線索,通過對20世紀上海市民文化的回眸,重新思考一些文學史問題,不僅可以加深人們對海派話劇的了解,而且可以強化話劇史中一些被人忽視的因素。如海派話劇隱含著怎樣的文學經驗,傳遞著怎樣的大眾文化生產信息,我們究竟該如何認識這一文化奇觀,所有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一、海派話劇生產的大眾文化語境
海派話劇和海派小說、海派散文一道組成了海派文學的大致圖景,呈現出媒介、市場合力下的大眾文化景觀。長期以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學被認為是“小市民”文藝。如茅盾曾言:“一種是完全按照個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鏡頭,編成故事,既無主題的積極意義,亦無明確的內容。這種純粹以趣味為中心的作品,顯然是對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眾的基本立場。”[1]此言論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左翼對這一時期上海市民文學的態度,凸現了對市民文學的排斥,影響可謂深遠。而實際上,海派文學的多重面相被遮蔽了,從大眾文化、都市文學等生產環境加以觀照,可以逐漸看清海派話劇的真實面貌。
大眾文化是和現代都市相生相伴的現象,在本質上也屬于都市文化。話劇在上海這個國際化大都市里移植成功,絕非偶然。從開埠直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現代化都市發展成型,“成為了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工商業中心,積累了成為現代型商業消費城市的物質基礎”[2]。以商業消費取向為特征的大眾文化興起,為娛樂業的繁盛提供了土壤。20世紀30年代中期,上海的商業消費日漸興盛,大新公司和中國銀行大樓于同年落成,百老匯大廈與號稱“遠東第一樓”的24層四行儲蓄會大樓開始屹立在外灘和南京路上。1933年革新后的“大光明”開張,配備美國RCA實音式有聲放映機和空調設施,有1900個沙發軟座,其豪華魅力首屈一指。“跳舞場以1932年開辦的百樂門為代表,地處靜安寺,有遠東第一樂府的美稱。”[3]此外,還有跑狗場、回力球場、現代劇院等現代娛樂場所的興建,以及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館、公園、動物園、植物園等文化配套設施的逐步完善。話劇作為現代社會的文化娛樂形式,正是在上海都市的土壤中滋生和成長起來的。
“市場經濟、技術文明、全球時代造就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界口味,即公共的審美追求、文化趣味。”[4]市場經濟是大眾文化興起的前提,話劇的發展自然離不開成熟的話劇市場。滬上的話劇為何遲遲走不進一般市民階層呢?主要因為話劇市場薄弱,成熟比較晚。1936年,《雷雨》在卡爾登劇院上演成功,標志著中上層市民觀眾對話劇的接受(愿意買票進劇場觀看)。話劇最初作為文明思想的代名詞由外國引進過來,但其只說不唱不舞的表演方式不符合中國大眾觀戲的習慣,以至于在“文明戲”階段需要以加唱加舞的方式來吸引市民。為了吸引更多市民走進劇場,話劇歷經了多次改良,進行了一系列市場化的嘗試。文明戲、新劇、白話新劇、改良新劇、男女新劇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名字變化,實則折射出話劇的榮辱興衰。此外,編演劇人才的缺乏,也制約著話劇藝術的發展,使得文明戲不得不頻頻向傳統戲劇求援,但一味追求通俗甚至低俗無法滿足觀眾日益增長的審美需求。而像春柳社那樣追求話劇的純粹的做法,終不免在風雨飄搖中宣告失敗。但這些做法都不失為話劇市場化進程中的有益探索。
歷經起伏變遷的海派話劇在商業大潮中逐漸完善自身的生產體制,到1941年前后,在人才、資金、場地、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基本保障。“大約從1941年起,‘演劇職業化’運動在上海和大后方同時開花結果,四五年間先后有20多個職業劇團問世。劇本創作、舞臺藝術、演劇活動持續高漲,達到空前的活躍與協調。”[5]這一時期,除了姚克、顧仲彝等一批劇作家留滬之外,眾多話劇專門人才積聚于上海,為海派話劇的長足發展提供了人才保障,話劇演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一批有著較高學識水平的導演,如黃佐臨、吳仭之、胡導等,為觀眾奉獻了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市民作品。上海話劇演員基本上都接受過中高等教育,相當一部分是經過招考成為職業話劇演員的。劇壇繁榮背后還有大資本的投入,這是淪陷時期特殊形勢下的經濟行為。評論稱一批“有投資眼光的‘后臺老板’們,認定這事業在現階段有抬頭發展的機會,而且說不定會和電影事業爭一日之短長,所以紛紛投資,向話劇新市場發展”②。此外,版權意識的增強、演出稅等制度的形成,亦保證了話劇的良好從業環境。從報刊新聞史料可以看到,20世紀40年代,上海經常演出話劇的劇場已有“卡爾登、金都、巴黎、金城、蘭心、美華、綠寶、麗華等八家”③。
報紙、雜志和書籍見證了海派話劇的繁盛景象,形成一道獨特的媒介景觀。雖然沒有今天這樣發達多樣的新媒介,但筆者能查閱到的涉及話劇的大眾報刊不下百種。其中既有專業刊物《戲劇雜志》《劇藝》《話劇界》《舞臺藝術》,也有具有影響力的報刊如《申報》《萬象》《半月影劇》《大眾影訊》《良友》《雜志》《天下》,還包括眾多的都市小報如《社會日報》《力報》《海報》《大上海報》《平報》《中國藝壇日報》《娛樂》《鐵報》等。市民階層的興起為話劇接受傳播群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評劇者往往是話劇愛好者、報刊編輯,或是話劇活動的實踐者,多重身份使得他們的藝術主張和創作實踐融入媒介傳播活動中,產生消息、報道、演出手記、廣告、座談會紀要等各種形式的劇評。一般認為,大眾文化“是工業化的——其商品的生產與銷售,通過受利潤驅動的產業進行,而該產業只遵從自身的經濟利益”[6]28。海派話劇利用大眾傳媒牢牢地把握住觀眾的審美趣味,商業化的功利性的文學觀念要求它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消費者趣味為目標。正是現代大眾傳媒的參與,使海派話劇實現文化、藝術與商業消費的合流,發展成為批量化、商品化和標準化的娛樂消費品。
為了吸引觀眾,每個劇團也都格外注重宣傳效應。他們經常會在話劇首演前夕組織招待會,邀請新聞界人士參加,充分運用媒介的力量來宣傳劇目。海派話劇的宣傳花招多種多樣、層出不窮,當時常見的話劇宣傳刊物即“演出特刊”。各劇場頻頻推出“演出特刊”,刊印內容除了應有的本事與演員表外,還可載入編劇人的意見、導演的自白、演員演技的研究,以及一切有關劇目的各項問題。這如同今日大片上映之前的宣傳花絮,將作品的亮點優勢集中展現。另外,還有“劇透”預告類報道、話劇內幕和演出花絮、演出廣告、明星選舉的新聞等娛樂化的宣傳方式,像有些劇團的“道歉聲明”被評論界認為是廣告手段。費穆導演《梅花夢》時,報上刊登了原作者譚正璧保留著者權利的抗議廣告,這被人看穿了把戲:其實這是上藝的宣傳手法④。話劇在報刊的推動下,表現為一種社會化、媒介化的文化生產形態。如果忽略話劇的傳播途徑和方式,忽略報刊印刷媒介在此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就無法真正認識市民文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無法觸摸到話劇發展的生動脈絡。
二、海派話劇的大眾文化特征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通常被認為“徹底擺脫了傳統貴族社會的文化認同,自尋目標地發展起獨自的近乎當時世界標準的大眾文化”[7]。這和今天學者對于大眾文化的定義不謀而合: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傳播媒介(機械媒介和電子媒介)為手段,按商品市場規律去運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形態”[8]。海派話劇以明星制、打對臺、流行風、娛樂化等表征書寫了大眾文化的眾聲喧嘩。
高額的演劇報酬使得一批話劇明星應運而生,成為大眾文化的象征。中國旅行劇團的唐若青實行“包銷前十排”⑤的做法,李綺年在綠寶上演《潘金蓮》,實行每座抽一元的辦法,花樣不一而足。主角與明星制相連,這是商業化演劇的必由之路。每個劇團都會注重用明星的公眾影響力提高產品的號召力,分級別的演劇報酬制度也在客觀上具有“造星”的效用。報刊是現代上海明星文化滋生的溫床,通過媒體的大肆宣傳,孫景路、上官云珠、沈敏、石揮、陸露明等明星成為公眾追捧的對象。明星的演藝活動、興趣愛好甚至飲食起居都成了大眾關注的熱點。如《拉角風潮》一文曾言:“喬奇的退出‘上藝’加入‘光明’,也是拉角家乘他和石揮鬧意見的當兒,從中拉攏所得。石揮似乎已成了‘紅伶’,更多的拉角家企圖重金禮聘。”⑥關于明星的各種消息和流言成為都市里最有聲有色的風景。通俗期刊里各種夸張性的批評與褒獎共存,它所帶來的休閑趣味是單純閱讀純文學評論很難體會到的。媒體在諸如此類的報道中扮演了“捧角”“造星”的角色,將演員、明星以更加立體生動的形象展露出來,滿足了社會大眾以明星為談資的窺視欲。為了擴大影戲、吸引觀眾,各劇團還會在劇本的分量或名演員、名導演的號召力等方面與競爭對手形成“對壘”之勢,評論界將此類現象稱為“打對臺”。1942年12月24日卡爾登推出《秋海棠》之時,藝光劇團公演《甜姐兒》(魏于潛編劇,胡導導演),中中劇團上演叫座戲《欲魔》,由話劇賣座明星孫景路主演。三部作品制作陣容強大,各有所長,由此可見當時劇壇競爭的激烈態勢。海派話劇努力將觀眾視為上帝,在追逐時代潮流的同時,亦能變換不同的風格適應觀眾多變的口味。
海派話劇具有釋放都市生活快節奏的功能,將娛樂的消遣休憩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符合大眾文化的本質屬性:“偏重感性愉悅,它不以提供對世界的理性反思為目的,而主要傾向于創造娛樂大眾的文化形式,達到‘捕獲’大量受眾、獲取商業利潤的目的。”[9]因此,感性層面上的快樂成為大眾文化的運作核心。海派話劇中,夸張性的鬧劇如《八仙過海》旨在給人們帶來放松和愉悅,《梁上君子》在演出時,觀眾始終不停地開懷大笑。外國改編作品則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異域風情,適應了上海觀眾追新逐異的欣賞需求。才子佳人之類的民間題材劇目,則賺足了舊式觀眾的眼淚。歷史劇如《楊貴妃》布景壯觀華麗,配以古典優雅的音樂,使得觀眾沉浸在纏綿悱惻的帝妃戀里。《傾城之戀》《清宮怨》等表現愛恨情感的劇作,滿足了觀眾追求熱鬧好看的心理需求。懸疑破案劇如《天羅地網》也是百姓愛看的一類劇作,破案的趣味性很能吸引民眾的好奇心。20世紀40年代,在國破家碎的淪陷區上海,話劇工作者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愁米愁煤愁得太苦”的上海人帶來了笑聲,使他們在對娛樂的追求中使生命緊張之后的倦怠與失落得到暫時的放松和彌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海派話劇為觀眾打造出一個特殊的文化領域,發揮了建立民族認同、慰藉精神的巨大能量。
由市民觀眾和都市媒介共同參與形成的潮流風是海派話劇的另一表征。“潮流風”即某個劇目的賣座會引發此類作品的流行。1942年上半年戀愛劇《香箋淚》《茶花女》《水仙花》《紅樓夢》《花花世界》走紅滬上,隨著年底《秋海棠》的轟動演出,現代通俗派劇作爭相出爐;1943年古裝戲流行一時,7月《武則天》開啟風氣,8月《楊貴妃》《清宮怨》緊隨其后,《香妃》《釵頭鳳》《浮生六記》《李香君》等持續上演到歲尾;《潘金蓮》的上演引起一波民間劇的熱潮,《梁山伯與祝英臺》緊隨其后;到了1944年,鬧劇又成了上海劇壇一條主要的線路⑦。潮流風的形成標志著話劇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這是之前的話劇所不具有的。
海派話劇、左翼話劇以及電影、戲劇、通俗小說在媒介營造的公共空間互相影響。在世俗大眾中占主流的市民劇評,以大眾趣味的培養和滿足為基本導向,以鮮明的商業娛樂性凸顯市民觀眾的審美趣味。市民劇評之外的左翼劇評、自由派劇評,以堅守政治立場和藝術性為主要特征。但無一例外,它們也都處于大眾文化的浸染之中,并且相互影響、彼此促進。市場化在推動左翼話劇擴張觀眾市場、促進演劇職業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商業競爭在促進劇團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精英思想的引領能有效避免話劇誤入過度商業化的泥淖。左翼劇評提出話劇為國家民族生存而服務的目標,阿英的《碧血花》、于伶的《大明英烈傳》等將抗戰與民主的現實要求寓含其中,對劇壇商業化起到了一定的糾偏、制衡作用。此外,“反映現實的程度和是否有利于改進人生理應成為評價作品藝術的標準”⑧之類的言論,對于防止話劇低俗化也有著積極的意義。各種流派的文學觀念在話劇里交匯融合,帶來話劇現代意義的演變和審美藝術的革新。
三、大眾文化對于話劇審美經驗的特殊開發
海派話劇以民間性的堅守開辟了廣闊的演劇市場,逐步贏得了市民大眾的喜愛。傳統文化不會創建大眾文化,但卻是大眾文化發展的土壤。“通俗性到了現代,常常要由民間文學與舊文學這樣兩方面來輸送營養。”[10]作為都市文化日常生活的參與者,世俗大眾為自己發聲,從某個程度而言,這確實翻轉了傳統主流社會“由上而下”的規訓文化。而民眾發聲最常用的工具就是民間文化,經過改良創新的民間戲劇或者小說與話劇實現了有機結合,在戲劇形象的塑造、戲劇沖突的營造等方面發揮著獨特的功效。直到1944年的話劇舞臺上,還有傳統戲曲改編劇《春阿氏》。至于20世紀30年代的舞臺上,《趙五娘》《珍珠塔》《玉堂春》等劇目就更為常見了。名劇《秋海棠》更是離不開京戲的功勞。話劇導演費穆跟周信芳、梅蘭芳都是很好的朋友,石揮為演好名伶“秋海棠”,專門拜訪黃桂秋、梅蘭芳、程硯秋等演員[11]12。
大眾文化對于民間傳統文化加以改良創造,使其更為現代化、更富于美感。如《秋海棠》開頭和結尾以“戲中戲”的手法將京戲《蘇三起解》穿插到話劇舞臺上,這成為該劇的最大看點。深受海派京戲影響的導演、演員亦將戲曲的唱念做打手法運用到話劇中。胡導在《陳圓圓》中出演算命先生時,運用“老鼠胡須、彎腰駝背”[11]8等京劇丑角的表現手法,強化了人物的喜劇效果。
傳統戲曲、通俗小說在與話劇的交融中,創造出了獨特的藝術美感。話劇中的“伶人戲”可以看作青樓文學的延續,但表現范圍已從妓女擴展到了歌舞明星、舞女、京戲名角兒,由此聯結起娛樂業、商界、家庭之間的情感利益糾葛。這不僅投合了市民喜好明星的獨特心理,而且使劇作的主旨指向對藝術從業者的同情,以人物最終難逃滅亡的悲劇命運控訴社會。由此可見,海派話劇內容社會涉及面之廣、批判性之深刻,顯然不是以往的通俗小說所能達到的。
上海孤島和淪陷時期出現了歷史劇演出熱潮,《文天祥》《明末遺恨》《岳飛》《葛嫩娘》《楊娥傳》等劇傳達了上海市民的愛國情緒和民族氣節,隱晦曲折地表達了抗議外族侵略的心聲。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大眾文化理解為“通過對霸權力量進行符號學意義上的抵抗,而在社會的意義上運作”[6]68。一方面,歷史改編劇的盛行適應了大眾喜愛談古論今的心態;另一方面,在當時的環境下,尤其是孤島時期,直接談論抗戰是不行的,歷史劇搬出古代衣冠較易避開當局檢查。因此,這種歷史改編劇是對時代主題回應的愛國劇,劇場成為觀眾曲折表達愛國情懷的特殊空間,亡國之痛和愛國情懷在觀劇過程中得以釋放和表露。面對日本侵略者入侵、國土分裂的現實,民眾對統一國家的期盼與想象不只包含在對歷史傳奇的向往中,更是通過歷史劇對“中國文化”的強調,表達對侵略者反抗的心聲。這樣,歷史被賦予了舒緩焦慮、抒發民族大義的拯救性意義。無論是英雄傳奇人物劇目《文天祥》《李香君》,還是傳唱至今的愛情劇目《楊貴妃》《梁山伯與祝英臺》,都被涂抹上了“精神性家園”的虛化色彩。李香君、葛嫩娘更是成為抗戰歷史劇中經常出現的主角,她們都具有聰明果敢、率真純情、蔑視權貴的性格特征,以及為了維護民族尊嚴不惜獻身的崇高精神。
家國情懷歷來是民間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動力。在這一點上,海派話劇和當時進步的左翼話劇是相通的。“大眾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這意味著大眾文化在微觀政治的層面,而非宏觀政治的層面,進行運作,而且它是循序漸進式的,而非激進式的”[6]68,但卻是“日復一日與不平等權力關系所進行的協商”[6]68。海派話劇在寫實和想象交織中構建的家國形象,不斷激蕩、影響著市民的愛國情懷,在異族統治的孤島這一特殊的環境下,這不啻一劑殖民地子民心靈療傷的良藥。民間愛國熱情裹挾著反抗侵略的快感,使得歷史劇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力量。
海派話劇對民間文學的創新式傳承體現了改良的功用。改良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生產方式,貫穿海派話劇的發展歷程。話劇能夠克服傳入初期的“水土不服”而在中國大地上生存下來,歸功于不斷的改良。改良使其在不同的文化之間不斷調適,兼容并蓄,有了不斷更新、持續精進的機會。無論是話劇初期與通俗小說和傳統戲曲的聯姻,還是電影興起后大量電影改編劇的出現,都體現了話劇向傳統和創新雙面出擊的能力——改良。在改編外來劇時,海派話劇十分注意題材的擇取。黃宗英主演的《甜姐兒》等“流線型喜劇”成為首選,因為與悲劇相比,喜劇能夠減少審美距離帶給觀眾的陌生感。顧仲彝改編《簡愛》時,特意將劇名改為《水仙花》,故事中的地名和人名也都進行中國化處理,這些本土化的改編方式使得外國劇作逐漸收獲了更多的中國觀眾。
改良還包括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互動交流。話劇和電影、京戲、越劇等藝術形式之間的改編比比皆是,著名京劇演員周信芳曾演過朱端鈞導演的《雷雨》里的一場戲[11]87。在海派話劇中,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開放交流異常活躍,這固然離不開商業利益的驅使,但較為成熟的、市場化的演出環境更是基本保證。話劇在20世紀40年代興盛時期,夏佩珍、宣景琳、王雪朋、白虹、顧夢鶴等人都曾登上話劇舞臺。1941年,天風劇團在推出姚克編劇的《清宮怨》時,邀電影明星舒適參演,增加不少票房。費穆創造性地把電影手法引入話劇舞臺藝術,使話劇的場面調度更具視覺沖擊力。如《浮生六記》最后一場,蕓娘說完臨終前的最后一句話“春天不遠了”之后,病榻后面的綠幔掀起,露出窗外暮春三月的景象⑨,這種畫面切入的手法顯然來自電影。
海派話劇在不斷的改良中汲取各種藝術的精華,在上海話劇舞臺上始終占據重要一席。在與左翼話劇共存的時代,左翼注重社會意義與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等藝術特性在海派話劇里都有體現。海派話劇曾演出左翼劇作《龍鳳花燭》(改編自《一年間》)。海派話劇的經營者深諳人們的觀劇心理,通過改良使不同流派風格的劇目適應觀眾多樣的欣賞口味。在成熟的話劇市場上,呈現的是雅俗結合、新舊交融、中西結合的圖景。各流派的互動共生不僅促使精英文化、意識形態文化成為市民大眾文化的構成要素,而且使大眾文化的品位獲得空前的提高。話劇藝術在與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交流中不斷提升,呈現出市場與審美、政治與商業、抗戰與娛樂之間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海派話劇注重變換風格保持演劇的“新鮮感”,悲劇和喜劇、古裝戲和現代劇、鬧劇和抒情劇、改編劇和國產劇等各種名目的劇目次第上演。這種做法適應了觀眾不同欣賞心理的需求,是趨新求變的市民品性使然。
海派話劇參與建構了城市生活的公眾休閑與流行風尚,這是大眾文化在都市日常生活層面的顯現。演劇及觀劇成為現代都市生活的一種方式,話劇中現代生活理念傳輸滲透也變得無處不在。在海派話劇中,推崇物質文明、多元生活方式的現代思想理念和價值立場,多以旅游、出國留學、蜜月旅行等現代生活方式加以展現。而其中諸如女性意識的覺醒、新型家庭關系等也成為引領現代都市生活的重要面向。各種刊登在戲劇專業期刊、休閑雜志、都市小報上的劇評不拘一格、蔚為大觀。觀眾體驗都市的歡樂喧嘩和悲歡離合,借助現代媒體發聲評戲,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一種流行風尚,話劇由此成為大眾文化蔓延至整個都市生活中的重要藝術形式。
“受眾同文化工業一起,成為大眾文化的共同創造者。”[12]有劇作者和演員以及觀眾的參與,才能成就作為觀演藝術的話劇。觀眾推動著話劇前行,話劇影響大眾生活,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建構。受市民關注的影星也會被寫進劇本,以拉近劇作與觀眾的距離。《春閨風月》里,編劇王兆墀加進了許多現代生活的例子,“例如二加二等于五,楊梅冰淇淋,桃拉塞拉摩之類”⑩,桃拉塞拉摩即為當時的國際影星。話劇劇場作為傳輸新型價值的空間,折射了人們對于都市、現代生活的理解與想象。
結 語
對于海派話劇的大眾文化生產,我們不僅要看到其商業化、娛樂化的特征,更要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學的大環境來看待。“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調是鄉村,城市文學不能算作主流,都市文學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如果我們將觀察話劇的目光從傳統的立場轉向“市民觀眾”的角度,也許會有新的發現。以大眾文化、市民文化的視角考察海派話劇,揭示商業、都市對文學的滲透以及都市文學呈現的特色,可以為話劇史發展經驗提供有益的補充。這樣的研究不僅可以透視多元、立體的都市文學景觀,而且能夠發現市民通俗文學、現代文學史的多重脈絡。對于文學和商業的關系,我們不能像以往那樣,簡單地劃分陣營,下個對錯結論,而是要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從文學自身的生存環境,來理解文化市場、大眾媒介作為一種現代的文學生產場域對作家創作產生的影響。除了海派話劇,海派小說、海派散文、都市期刊也都是大眾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它們與此前、此后文學史上的作品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海派話劇對于當今劇壇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也正在于此。
注釋
①這里所說的“海派話劇”是指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產生的帶有商業性的、以市民觀念為主的通俗大眾劇。“海派話劇”的說法由來已久,最常見的理解是泛指在上海演出的所有海味話劇,包括當今正在上海演出的海味話劇。這成了一個包括現、當代文學在內的現象。而實際上,先厘清現代文學中的“海派話劇”,然后再用歷史的眼光來打量今日上海話劇的情況,才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態度。詳情可參看尹詩的文章《文明戲改良和海派話劇的產生》與《1940年代海派話劇的璀璨綻放》,分別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1期、第12期。②⑥參見雷諾:《劇壇秘話》,《太平洋周報》1943年第55期。③參見慧星、王林:《劇壇崩潰的秘密:蓬勃也,衰落也》,《劇藝》1944年9月4日第4期。④參見重逢:《費穆的梅花夢》,《太平洋周報》1942年第1卷第23期。⑤參見洛西:《上海各劇團經營內幕》,《太平洋周報》1942年第1卷第44期。⑦參見《申報》1942—1944年的部分話劇廣告。⑧參見萬里浪:《劇評及其他》,《劇藝》1944年第1卷第2期。⑨參見王希堯:《浮生六記觀感》,《太平》1943年第2卷第12期。⑩參見春理:《觀“春閨風月”》,《中華周報》1943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