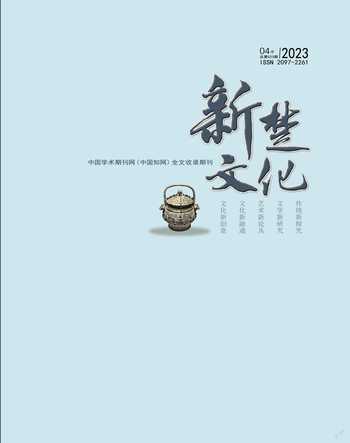作為方法的身體
【摘要】哲學家約翰遜認為,文學實際是“身體性過程”,鮮活的身體便是文學的根本起源。沈從文、莫言的創作具有共通的文學表達與審美理想:皆以身體為基點和依托,傳達關于個體生命、道德及民族國家的想象,表達不拘囿于社會文化制約的個體生命內在秩序和自由意志,重構以身體感受為核心的道德倫理及民族精神。以身體為方法探究兩人的創作,對于深化兩人作品的理解及探究“身體”的文學史意義及人類存在的可能皆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沈從文;莫言;身體;民族精神;道德倫理
【中圖分類號】I206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11-0024-04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沈從文身體倫理敘事研究”(項目編號:XSP22YBC418);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一般項目“莫言的身體倫理敘事研究”(項目編號:21C0769)。
20世紀初哲學領域的“身體轉向”,將一直被身心二元對立格局壓制下的身體推到了人類歷史的前臺。在尼采、巴塔耶、德勒茲、福柯、詹姆斯、舒斯特曼等人的努力下,身體概念得以重新詮釋,其重要性也被逐漸認識。20世紀80年代,身體話語被中國當代作家納入文學視域,因其內涵豐富含混而迅速成為女性主義、倫理道德、政治文化、消費主義等意識形態的愛寵,它們各取所需,或者將其視為顛覆假道學、釋放欲望的武器,或者將其作為權力爭斗的中心,或者將其作為對抗男性中心的武器,或者視為“最美商品”的載體。
盡管關于身體話語的大規模引入與討論發生在八九十年代,但之于“身體”的關注,則從魯迅開啟白話小說史,便一直延續至今。從更宏觀的角度而言,現當代文學凡是關注身體欲望、身體力量、身體感受的作品都可歸屬于關于身體的寫作,僅僅將其限定于八九十年代興起的文學現象,有失公允。如評論家朱國華所言:“身體寫作首先從命名開始就是錯誤的。”[1]77筆者以為,與其糾結于莫衷一是的“身體寫作”的界定,不如回歸“身體”本體,將其作為審視與考察現當代文學作家之于個體生命、道德、民族的一種方式與手段,以此真正還原身體寫作的意義與價值。本文所提及的身體,立足于當代哲學美學之于身心二元對立觀念的超越基礎上,意指“身心”統一、靈肉并存的主體。在此思路下,本文將沈從文與莫言關于身體的寫作作為重點考察對象,審視作為方法的身體。原因在于:兩人皆是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重鎮作家,其創作皆以身體為基點和依托,借助文學審美方式傳達關于個體生命、道德及民族國家的想象,具有相似的文學表達與審美理想,具有典型代表性,可以借由二者打通現當代文學,審視“身體”在百年文學史中呈現的意義,探尋人類存在的多樣性。
一、立人:本真性存在的還原
盡管身體之于人類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但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倫理史卻竭力漠視、否認這一事實。直至19世紀,身體一直處于被忽略、被壓抑的狀態中,被視為高貴靈魂的牢籠而被哲學家抨擊與批判。而之于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為強化對個體的控制,從儒家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到宋代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古訓漸趨僵化與絕對,揚靈抑身的文化傳統使理性被推崇為至高無上的存在,身體則被視為肉欲與罪惡的策源地而被壓抑、貶斥與放逐,個體的生命活力和自由意志因此而被鉗制。
自五四啟蒙運動以來,“改造國民性”的“立人”思想便成為現代知識分子肩負的一個世紀性命題。與魯迅之于“健全”“茁壯”然而“愚弱”國民的否定、強調“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立人”路徑不同的是,沈從文和其后的莫言等作家,則立足于人“是一種利用原欲沖動又能超越這種沖動、不斷獲得新的誕生的動物”[2]71,將視野投向身體,試圖通過還原身體的原欲與本能強力,以此實現“立人”理想。
“力”與“美”的推崇。無論是沈從文湘西世界的柏子、虎雛、七個“野人”、龍朱等,抑或莫言東北高密鄉的余占鰲、羅漢大爺、沙月亮、司馬庫、孫丙等男子,無一不是自然之子,擁有最強健的體魄、蓬勃旺盛的情欲、肆意張揚的個性,他們熱情彪悍、率直坦蕩、敢愛敢恨、能喝能打、擁有著最強盛的生命力;而這片土地的女人們,癡情的湘西女子,蔑視道德的戴鳳蓮、孫眉娘,寬厚堅強的上官魯氏等,都有著美麗妖嬈的身姿,卻皆不是傳統束縛下痛苦呻吟的舊式女子,她們溫柔炙熱、健康活潑,自由地伸展著不羈的靈魂,隨“身”所欲,隨心而行,綻放著自己美麗的靈魂。他們的創作,如評論家所言:“對于原始強力的呼喚,在以魯迅和‘五四式的思維繼續描寫和鞭撻著種種‘國民劣根性的同時,也刻意挖掘和刻意放大著民族的原始性的獷悍生命強力和性格,以生命和性格的強力照亮著灰暗卑污的人生,鑄造著國民和民族的靈魂,表達著他們對‘立人的主觀化的、理想化的、浪漫化的理解與追求。”[3]83
生命原欲的肯定。作為人類繁衍發展的唯一途徑,性顯然是生命力最明晰的證明。沈從文的筆下,雨后的女人聽著些情話,便由著情人四狗擺布,得著些“一些氣力,一些強硬,一些溫柔”(《雨后》);回娘家的新婚夫婦“看看天氣太好”,“于是記起一些年青人可做的事”(《夫婦》);因著感覺需要“一種力,一種圓滿健全的,而帶有頑固的攻擊”的年輕的旅店女主人黑貓,便欣然與中意的宿客野合(《旅店》)。這些鄉村的小兒女們皆不拘于外在的拘囿,純乎遵循身體本然的吸引,享受著生之樂趣;而莫言筆下的人物則更為狂熱:“我爺爺”和“我奶奶”被彼此健康強勁的身體所吸引,無懼世俗桎梏,轟轟烈烈地在高粱地里“野合”;上官家的女人們原始而狂暴的情欲幾乎掃蕩了高密鄉“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草莽英雄們,他們激情而熾烈的愛欲種子肆意播撒在故鄉的熱土。
這些民間文化熏陶的自由精靈們,他們擁有最強壯的身體、最旺盛的情欲以及無羈的靈魂,有力便使,有愛便愛,有仇便報,從不糾結于身體之外的諸多束縛。“中國人的本能力量的衰竭使得現代啟蒙主義在‘立人途徑的尋求中最終又將原動力折回到人的本能欲望——原欲。”[4]59身體在沈從文與莫言的筆下,被還原至生命的本體地位,“與其說是借身體本身反抗任何精神層面對其的壓抑,不如說是希冀從根本上恢復生命未被現代文明浸染時的本然性和純潔性”[5]50。
二、立德:道德倫理的重塑
通常情況下,“道德”與“倫理”被視為同義詞,李澤厚卻認為兩者存在較大差異:“倫理是外在的制度、風習、秩序、規范、準則,道德是遵循、履行這些制度、習俗、秩序、規范、準則的心理特征和行為。”[6]74在此意義上,康德強調作為一種先驗理性的“倫理道德”思想更近于“道德”,而黑格爾則偏于“倫理”,更注重人與人、人與家庭、社會、國家的規范、秩序等。然而,作為身體來到世界的人類個體,無論是著眼于內在秩序屬己的自律的“道德”,抑或偏重人倫關系的他律的“倫理”,身體皆是通往自我、他人與世界唯一的通道。個體通過屬己的身體感受與他人、世界相互聯系與交互,身體是我們體驗與理解他人與世界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倫理道德秩序的建構顯然必須立足于身體,以身體立法。
五四以來,伴隨著個性解放的潮流,以周氏兄弟為首的理論倡導及郁達夫、丁玲、施蟄存等作家的創作實踐中,身體的正當性獲得了一定的認可。相較于多數作家將身體書寫僅僅作為反抗傳統道德、個性解放的武器而言,沈從文和莫言顯然是頗為特殊的:兩人都強調身體的獨立性,拒絕身體被任何意識形態收編,試圖借由自由本然形態的身體為現代人重新建構理解世界的道德價值標準。
“湘西世界”是沈從文在現實基礎上提煉的寄寓自己審美理想的道德烏托邦。生活于此的鄉下人,遵循著身體自然而然的生命法則,既無道德的捆綁束縛,又無需服膺于倫理的種種規范。沈從文坦言,“我看一切,卻并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固定我的愛憎”,“我不太能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7]13卷323。因此,在他的文學世界里,婚姻是可有可無的,水手與吊腳樓的妓女相互惦念,盡管幾日便揮灑了柏子數月的積蓄與氣力,但兩人皆心滿意足(《柏子》);快樂卻是必需的。勇猛如獅子般的七個脫離社會秩序的隱者,用悅耳嘹亮的歌聲,吸引著年輕的女子,將她們“引到洞中來,興趣好則不妨過夜”,“就抱得很緊舒舒服服睡到天明”(《七個野人和最后一個迎春節》)。而長輩們則見慣不怪,“人既在一塊長大,懂了事,互相歡喜中意,非變成一個不行,作父親的似乎也無反對理由”(《阿黑小史》)。沒有頑固而空虛的教育,無所謂戒律,無所謂得失權衡,身體循著大地與四季的規律,歸于自然,自由地舒展。
如果說沈從文之于倫理道德的重審是以身體的自由自然呈現生命的自然法則,莫言之于倫理道德的重構則在于以身體本然力量撕裂現代文明附加于其的種種捆綁與束縛。余占鰲與戴鳳蓮的愛情便是高粱地里誕生的叛逆之火。為了她,他不惜手刃單家父子;為了他,她無懼流言蜚語。沒有利益權衡、沒有精打細算、沒有悱惻纏綿,有的只是兩具自由自在放蕩不羈肉體的碰撞與交匯;而眉娘與縣令錢丁的愛情原始而純粹:“有情愛而無淫色,有原欲而無社會功利氣息。”[8]137之于他們,愛欲是渴望合一的身體自然渴求,是自然本真生命散發的醇香,熾熱奔放的眉娘坦言:“為了你俺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哪里還在乎人家飛短流長?”這些野性十足、無拘無束的靈魂,對于生命的態度,恰如戴鳳蓮生命垂危前的自由宣言:“天,什么叫貞節,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是按著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作主。”[9]69
“倫理既是對內在生命的看護與整飭,也是對外在秩序的訴求和表達,是對生命感覺的梳理和現實生存的規范,而這種梳理和規范又是以身體的在世生存為起點的。”[10]141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與莫言的創作恰是通過還原身體的純粹與本體地位,以此顛覆傳統道德倫理之于身體的壓制,借助身體自身的力量重構合乎健康人性、充滿血性與生氣的新的人倫關系。
三、立國:民族精神的重構
盡管相隔半個世紀,但沈從文與莫言的創作契機卻如出一轍。之于沈從文,創作源于對伴隨著文明發展出現的“閹寺人格”的憂郁與憎惡。“至如閹寺性的人,實無所愛,對國家,貌似熱誠,對事,馬馬虎虎,對人,毫無情感,對理想,異常嚇怕。也娶妻生子,治學問教書,做官開會,然而精神狀態上始終是個閹人。”[7]12卷43“大多數人都十分懶惰,拘謹,小氣,又全都是營養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7]8卷195而這份關于國人委頓靈魂的焦慮一直延續到莫言,在莫言的創作中,“種的退化”是激發其創作的核心元素。在《紅高粱家族》中,他悲哀地寫道:“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9]4鑒于國人人種的弱化與衰退,沈從文與莫言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注于身體,以期借助強健的體魄、“野蠻的靈魂”、彪悍的原始生命力拯救羸弱衰頹的國民,構建“優美、健康、自然”理想人生形式,實現民族振興。
之于“閹寺人格”的憎惡,沈從文將因文明的偽飾而使身體處于扭曲與壓抑的都市世界作為批判的對象。《八駿圖》便是作為“閹寺人格”集中營的典型之作。在這部小說中,本應是社會中流砥柱的八位學者,他們或偷窺,或意淫,或虛偽,或有虐待傾向,但無不處于性的壓抑與扭曲中,精神萎靡,活得矯揉造作;知識不能拯救羸弱的身體,財富亦不能拯救頹墜的身體,過著衣食無憂日子的紳士和紳士的太太們,身體卻百無聊賴,在肉欲與亂倫中攪滾(《紳士的太太》);而有學問的人則滿足于相互調情試探,彼此卻不愿承擔任何的責任與義務(《有學問的人》)。莫言的系列小說則演繹著關于“種的退化”的民族歷史寓言。如果說《紅高粱家族》尚且還以“我”父親豆官一顆睪丸的喪失作為生命力喪失來隱喻后輩生命力的衰退,《食草家族》則以顯性的方式明確地表現后輩們已然徹底喪失了食草家族祖先們曾經的輝煌與神奇;而《生死疲勞》更是通過動物們“蓬蓬勃勃的野精神”對比投胎為人的孱弱與生命力的萎縮。
在對“閹寺人格”的批判與“種的退化”的焦慮中,沈從文和莫言的創作都傳遞了一個相似的文學心愿:對生命強力與原始野性的呼喚,對民族精神振興的渴求與期盼。嚴肅的作家,其創作必然穿越一己之體,將目光投注于民族、國家。純粹本然的身體便是沈從文、莫言試圖拯救羸弱衰退國民的救贖。他們的創作,實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11]456,由此激發民族生命之強力,讓中華民族以昂揚振奮之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結語
身體既是個體存在的肉身之軀,亦是被社會文化所建構精神靈魂之所在。它是自然的,有自己的欲念、渴求、沖動,但它更是社會的、文化的、民族的,為特定的歷史文化所建構。自現代文學的郁達夫、沈從文、丁玲等,到當代文學的張賢亮、王安憶、賈平凹、莫言等,在某種意義上,百余年的中國文學史,實質是身體追尋自身合法性的精神歷程。以沈從文、莫言為代表的作家們,立足于身體作為感覺與體驗的存在,還原身體自然健康的欲望本能,肯定個體生命強悍的原始生命力;同時以身體為軸心,用文學審美方式表達不拘囿于現實道德倫理及社會文化制約的個體生命邏輯和內在秩序,重構以身體感受為核心的生命內在秩序和個體自由意志的伸展,探究人類之于生命存在的可能和多樣性要求;尤為重要的是,借助身體本體地位的還原,重構國民體魄、健全國民人格、探尋重建民族品德、振興民族靈魂的可能。以身體為契機,還原個體的本真存在,恢復人的生命活力與自由意志,鑄造“新人”,重構“新道德”,因此,身體書寫不僅僅是現代中國人之于健康人性的強烈渴求,更是實現個體自由與解放之途的必然訴求,是現代中國審美現代性之于啟蒙現代性的補充與矯正。
參考文獻:
[1]朱國華.關于身體寫作的詰問[J].文藝爭鳴,2004(05):77-79.
[2]吳炫.中國當代文學批判[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3]逄增玉.五四時期的“立人”思考及其文學表現和嬗變[J].世紀論評,1998(03):79-83.
[4]李俏梅.中國當代文學的身體敘寫(1949-2006)[D].廣州:中山大學,2007.
[5]張森.論沈從文創作中的身體敘事[J].中國文學研究,2009(04):47-50.
[6]李澤厚.倫理學綱要續篇[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7]沈從文.沈從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8]楊友玉.莫言對原始生命力的全新詮釋[J].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0(03):136-138.
[9]莫言.紅高粱家族[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
[10]唐健君.身體作為倫理秩序的始基:以身體立法[J].學術研究,2011(10):141-146+160.
[11]蘇雪林.蘇雪林選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9.
作者簡介:
胡艷,女,湖南婁底人,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在讀,湖南人文科技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