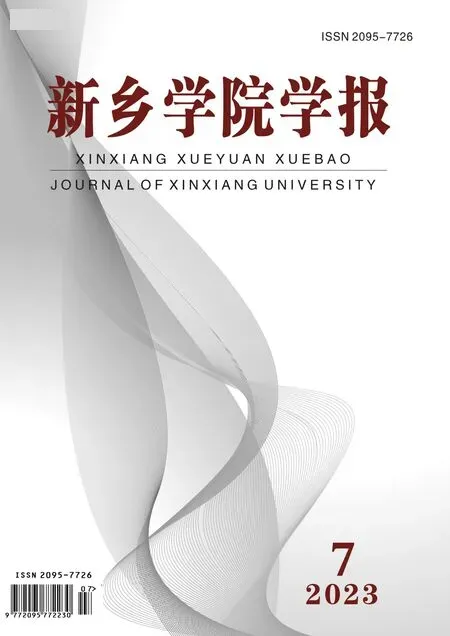文獻學方法與文學史辨的融通之作
——評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
楊 棟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一、文學史與研究史兼具
從事學術研究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熟悉原始文獻,能夠熟練運用相關的文獻史料;二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知道某一問題前人有哪些觀點,有無深入發掘的空間。 熟悉文獻史料才能進而發現問題、分析材料、解決問題;了解前人的研究情況才能進一步完善和深化相關問題, 提出自己的見解。 有了這兩個前提條件,我們才有可能推進學術研究,作出自己的學術貢獻。 曹道衡先生在《中古文學文獻學》初版序言中強調了這一點,他說:“一個研究者在他所從事的科研工作中要有所發現、有所推進,都必須充分總結前人的成果, 在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深化和發展。 否則要想取得較好的成績無疑是很困難的。 劉躍進同志的這本《中古文學文獻學》的撰作宗旨,正是為著這樣一個目的。 ”[1]1《中古文學文獻學》從初版到增訂版都秉承著這一撰作宗旨,出色地完成了撰寫目標: 一是將中古文學的原始資料交待清楚,二是評述歷代研究狀況。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既對中古文學的作家作品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考證, 又詳細地介紹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與不同的學術觀點。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可以說既是一部中古文學史,也是一部中古文學研究史,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就以《文選》為例,作者在充分利用原始文獻史料的基礎上,詳細論述了《文選》的編者、成書年代、文體分類、選錄標準、注釋和版本等,使讀者可以很輕松地掌握《文選》的基本文獻情況。同時,在論述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又適時地引入前人的學術成果或不同觀點,還專列“《文選》學”一節,梳理了《文選》研究的歷史發展脈絡,不僅總結了《文選》的研究成就和學術觀點,而且展示了當下《文選》研究的視角及新課題,為推進《文選》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再如《玉臺新詠》,與《文選》一樣,作者也專設一章,分別從《玉臺新詠》的編者名稱及成書年代、《玉臺新詠》 的版本、《玉臺新詠》的性質與價值、《玉臺新詠》的影響等四個大的方面一一講述,內容翔實,資料豐富,論述深入淺出。類似《文選》《玉臺新詠》這樣的例子全書比比皆是,為中古文學的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的原始資料和研究文獻。
更為可貴的是, 作者不僅羅列原始資料和綜述前人的成果,而且常常有自己的考證和見解,并指出已有成果的缺失和不足,給予客觀的合理的評價。關于這一點, 曹道衡先生在初版序言里已經舉了不少例子。 增訂版新增了作者的不少卓見,比如關于《文選》和《玉臺新詠》這兩章,相較于初版,增添了很多新內容,這些新內容多是作者常年研究所得,展示了作者的新觀點和新成果。
二、重視文獻學方法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固然應堅持文學本位, 但文獻學研究是基礎, 完全脫離文獻的文學史研究無異于緣木求魚、升山采珠。劉躍進先生在讀書治學中一直非常強調文獻學的方法,認為:“文獻學不是學問,是一種讀書的方法,是進入歷史的一種重要途徑。 ”“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有一個基本的途徑, 就是文獻學。 ” 他甚至說過比較極端的話:“誰如果繞開文獻學,學術界一定繞開他。 ”[2]傳統的文獻學研究涉及文獻的成書與流傳、作者與編者、版本與目錄、校勘與辨偽、輯佚與編纂、接受與研究等眾多內容,將這些內容與文學史研究結合起來是大有可為的。
王鳴盛曾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 ”[3]劉躍進先生就特別重視目錄學在學術研究中的功用, 他說:“文獻與目錄是學術研究的基礎, 傳統目錄學經典文獻和當代出版的高質量古籍目錄為當代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和參考依據。”又指出:“傳統目錄學思想和方法是歷代賢達學士治學智慧的結晶,譬如小序、題解對考證歷史人物、 事件、 物品、 作品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4]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在介紹或考證某一文獻時, 非常注重爬梳該文獻在相關書目中的著錄情況,以此論述其作者、真偽、篇卷、流傳、版本、文獻性質等,進而探討其文獻價值和學術源流。這樣的論述方式,可以說是對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真正實踐。
版本對于文學研究同樣重要。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 一書對于重要的文學文獻都盡可能地介紹其版本流傳情況。 如《文選》,作者分別介紹了《文選》 的抄本和刻本, 其中刻本又詳細論述了五臣注本、 李善注本、 六臣注本等不同版本系統的具體情況,使讀者對《文選》的版本異同、優劣、遞嬗一目了然。如此詳細的版本論述同樣見于《玉臺新詠》《陶淵明集》《文心雕龍》等重要文獻。這樣的撰述實際上是建立在作者多年的研究和積累之上的, 并不是泛泛而談。像《文選》《玉臺新詠》這樣的經典文獻,劉躍進先生都已經研讀經年,著有《文選舊注輯存》《〈文選〉學叢稿》《玉臺新詠研究》《〈玉臺新詠〉史話》等專書。詳細地論述經典文獻的版本情況, 既為初學者閱讀《文選》等書的文本提供了便利,也為該書的版本研究提供了路徑。更有價值的是,作者除了介紹原始文獻的古代版本以外, 幾乎于每一種古書還特別推介了今人的點校、校注、箋釋、輯錄、匯編等古籍整理成果,極便于讀者進一步研讀。
另外,作者還關注文獻的真偽與寫作年代、詩文集的輯錄、作家的生平家世、文獻的流傳與接受等諸多內容。如關于蘇李詩的真偽問題,作者詳細梳理了前人的辨偽言論, 總結了今人關于蘇李詩寫作年代的不同說法,認為“蘇李詩出于后人擬作無疑,但確實難以考證出現的時代”[1]548。對于《柏梁臺詩》,作者認為其時代大抵不能早于魏晉之世[1]559。漢魏六朝小說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也眾說紛紜,《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也都給予了關照。如《燕丹子傳》的撰著年代有成于先秦、秦代、兩漢、宋齊等不同的說法,《西京雜記》的作者有無名氏、劉歆、葛洪、吳均、蕭賁等諸說,作者都一一評說。這樣的爬梳無疑為初涉中古小說的讀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文學總集對于文學史研究的價值不言而喻, 劉躍進先生在上編第三章專門論述了唐宋以來所編的中古文學總集, 分類梳理各個時代所編輯的詩歌總集和文章總集。 對像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這樣的名著則詳細介紹其優缺點及價值。 《中古文學文獻學 (增訂版)》還比較關注作家的生平家世以及作品的流傳和接受, 從文獻學的視角極大地豐富了中古文學的諸多細節,讓文學史研究更厚重扎實,也更立體化。
傳統文獻學非常注重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與辨偽等,但作為專題形式的文學文獻學,應有適合文學自身的撰寫內容和寫作方法。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一書就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作者試圖擺脫傳統文獻學的羈絆, 將文獻學置于文學史與文學研究史的視野之中,使整部書既有文學史特色,又不乏文獻學的厚重,為之后的“文學文獻學”著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宏通的學術視野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文獻數量非常多。 如何將這些文獻合理地分類論述, 以彰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脈絡,是作者撰寫《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文獻分類不合理,文學史的線索就會雜亂無章,顯得支離破碎。
作者立足于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實際情況,將《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分為三編:上編為總集編撰與綜合研究,首先重點介紹《文選》和《玉臺新詠》兩部總集的基本文獻情況,又依次梳理從唐宋以訖近現代所編中古文學總集,涉及詩歌總集、文章總集、詩文總集等,還述及有關中古文學研究的其他資料,諸如正史、其他史籍、類書、文獻類編、書目文獻等。另外還專設“中古文學的綜合研究”一章,系統介紹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論著, 如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學史》等。中編為中古詩文研究文獻,以時間為線索,以作家為中心,歷敘魏晉、南北朝至隋代的詩文研究,并對樂府詩、《古詩十九首》、蘇李詩等詩歌進行了相關考證。 下編為中古小說文論研究文獻, 從作者歸屬、成書年代、文學價值、論著成果等多方面對這一時期的小說和文論文獻作了詳盡的論介, 其中第三章為“《文心雕龍》研究文獻”,重點突出了《文心雕龍》的文學史地位。全書章節布局合理,詳略得當,全方位地再現了中古文學史的作家和作品。 上中下三編合在一起,自成體系。 正如沈玉成先生所言,看似孤立的原始材料和研究文獻,“在中古文學的研究體系中為這些材料和成果各個安排了恰當的位置,如登高望遠,村落田園,歷歷在目”。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這樣的整體規劃,體現了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和總攬全局的宏通意識。 這樣的視野和意識則是來源于作者對整個中古時期歷史文化的總體把握, 將文學史的發展置于當時的時代文化背景中敘述和書寫,具有清晰的歷史意識。
同時作者又時刻關注今天的學術研究, 有很強的當代意識。 在書中常見到作者對于當今學界的研究動態、研究熱點的觀照,以及高屋建瓴地對未來的研究新課題的展望。 如在“當代《文選》研究的新課題”這一部分中,劉躍進先生從《文選》的文獻學研究、《文選》的集成式研究、《文選》的文藝學研究、《文選》的文章學研究、《文選》的普及工作等五個方面給予了非常全面的研究規劃[1]48-54,對于未來的《文選》學研究無疑具有指導意義。 陶淵明的詩作和詩風對后世影響較大,他是學界比較關注的詩人。劉躍進先生總結出了學術界關于陶淵明的研究熱點問題:關于名字、關于年齡、關于里居、關于折腰五斗、關于《詩品》“陶詩源于應璩”說、關于《五孝傳》《四八目》、關于陶淵明的思想。 這樣的著述風格真的是溝通古今,啟迪后進,讓人耳目一新。
劉躍進先生開闊的學術視野還體現在他對域外文獻流傳與研究的廣泛關注上。 《文選》至遲在唐代就已流傳到日本,日本現在還保存有《文選》的一些重要版本,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也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被加以研究。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特別關注到這一點,專門介紹了《文選》在域外的流傳以及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玉臺新詠》這一章也涉及了該書的域外流傳情況。
需要指出的是, 劉躍進先生宏通的學術視野是建立在其扎實的文獻學基礎上的, 沒有對基本文獻的反復研讀,沒有對相關史料的爬梳整理,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這樣的文獻基礎又源于作者所倡導的“回歸經典,細讀文本”。 文本細讀需要有文獻的強大支撐,更需要文獻的考訂。 而細讀文本的目的,不僅僅是材料的整理和闡釋, 還要關注文本背后的深邃思想、歷史規律,從而讓文本細讀、文獻考訂和理論思索三者找到最佳的結合點[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