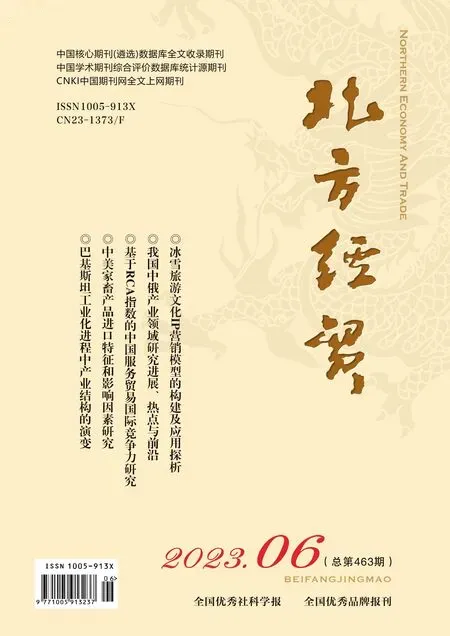論我國短視頻平臺版權侵權責任的認定
楊 豪
(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西安 710063)
一、短視頻法律規制勢在必行
我國當下對短視頻并無法律定義,而結合2014年中國科協對科普短視頻的定義與實踐分析,短視頻之所以廣受網絡用戶推崇并得以衍生發展,鑒于其時長短、易制作、內容豐富、傳播廣而迅速以及收益可變現等特點,換言之,短視頻是指由自由主體進行創作的以網絡為媒介的內容豐富的短時音像作品。當下,我國互聯網技術比較成熟,信息碎片化背景下,“快餐式”網絡文化產業迅速發展,自媒體時代下的“短視頻行業”迎來發展熱潮。據中國互聯網中心第4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披露,截至2021 年12 月,在網民中,短視頻用戶使用率為90.5%,用戶規模達9.34 億,較2020 年增長7%。短視頻業已成為一種規模大、影響廣的文化傳播方式與經營模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與短視頻業發展現狀相比,當下我國與短視頻相關法律規范仍較落后。近年來,短視頻行業搶注網紅商標、短視頻背景音樂侵權等糾紛案件不在少數,又由于短視頻行業門檻低、網絡用戶規模大,以網絡為媒介傳播迅速,侵權證據難以搜集,維權成本高、“法不責眾”等原因,短視頻版權侵權問題頻發,相關保護機制仍待完善。在短視頻行業發展過程中,行業建立在網絡媒介基礎上的特性是規制關鍵,這要求提供網絡介質服務的短視頻平臺相關準入審核、視頻發布監管及侵權視頻及時處理等責任的明確落實。但也同時需要保障網絡平臺經濟發展的基本需要,允許平臺適當運用“避風港原則”和“紅旗標準”規則,以避免對平臺的過度歸責,從而真正實現衡平平臺發展與著作權利人權利的保護。以下試從短視頻行業運營模式、平臺侵權責任基礎、責任認定和抗辯事由適用等角度加以論述,以期探求如何完善平臺侵權責任認定的相關制度規范。
二、短視頻行業運營模式及平臺侵權責任承擔基礎
在探究短視頻作品侵權糾紛中的責任承擔時,首先需明確短視頻制作發布后,經網絡點擊觀看,產生流量、廣告、打賞等利益,作為發布者的網絡用戶可提現獲利,若短視頻構成侵權,網絡用戶侵權責任毋庸置疑。而一旦發生侵權,平臺作為侵權行為發生載體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其版權保護義務基礎為何。實踐中相關侵權糾紛發生后,由于網絡虛擬性和跨時間、跨空間的特性,往往難以溯及追究網絡用戶責任,大多被侵權人會優先選擇追究侵權視頻發布平臺責任,而平臺多會以“避風港原則”“紅旗標準”進行抗辯。協調短視頻行業健康發展,既不能苛加義務于平臺,又不能忽視平臺的經營管理義務,應當依據平臺在多種短視頻行業運營模式中充當角色來合理分配其義務。
實踐中可見的短視頻運營模式大致可分為兩類,包括:工具型(逗拍、快剪輯等)和內容型(抖音、快手、微視等)。工具型模式中,平臺僅僅提供視頻剪輯制作服務,并不涉及視頻在線發布分享。而內容型模式下,平臺則同時具備錄制、剪輯及在線發布分享功能。[1]由于工具型平臺運營模式中,并未產生與網絡其他用戶的交互,故而不具有版權侵權基礎,換言之,網絡用戶可以“合理使用”為由進行抗辯,而平臺也就談不上版權保護之義務負擔。但與之相對應的內容型短視頻運營模式則不同,內容型短視頻平臺在整個短視頻營運過程中涉及較深,不可簡單以“居間人”身份處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424 條:“居間合同是居間人向委托人報告訂立合同的機會或者提供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同樣的“互聯網+”運營模式下,相較網約車、短租民宿的平臺地位界定,內容型短視頻平臺則相較絕對地處于“非居間地位”。
相較網約車、在線短租民宿的“P2P”共享經濟模式下平臺僅在交易過程中產生的聯結作用不同:首先,平臺維系整個網絡服務經營,處于核心地位,沒有第三方平臺介入就不可能完成整個行業運營過程。平臺是行業運營的組織者、主導者、調度者,且行業收費變現標準、服務內容、服務標準等網絡服務合同的核心條款完全由平臺制定和執行。本質上是平臺提供服務并與網絡用戶之間形成的網絡服務合同,網絡用戶只能被動選擇是否接受,視頻一經發布,更無法對其盈利模式進行控制。其次,網絡用戶之間交互以平臺服務為基礎,乃至某一用戶選擇哪一平臺均可能受到該平臺運營規則、變現商譽和其影響力的影響,更何況平臺通過短視頻運營收取中間利潤。最后,短視頻平臺為吸收流量,多會定期進行熱點視頻推廣、分類推送,甚至直接搜集搬運其他平臺視頻,作為視頻直接發布者。所以如果僅將平臺界定為居間者,那么發生侵權糾紛時,實踐中平臺簡單以居間者、“避風港原則”為由推脫其有能力承擔也應當承擔作為共同的網絡服務合同義務人的相關責任,最終致使權利人受損而維權難,顯失公平,將對我國文化產業健康發展產生消極影響。[2]
三、平臺侵權類型及歸責原則
前述針對內容型短視頻運營模式下平臺責任基礎進行討論,而當下就網絡用戶侵權情況下,平臺侵權責任承擔地位認定主要在于“直接侵權的共同侵權”和“間接侵權”之間的爭論。[3]間接侵權意味著平臺就侵權事實處于后置支配地位,而實踐中的侵權事實無非兩種,一種是平臺未經許可而直接進行短視頻搬運、發布,另一種則是平臺發布分享事實上侵權的短視頻。由此,主要需討論第二種情況即平臺分享發布網絡用戶制作、搬運的申請發布的侵權短視頻,平臺在何種情況下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承擔何種侵權責任。侵權行為的事實發生在于平臺不能知道侵權事實,或應知而不知,更或者知之而放任。根據《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 條(“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確定其是否承擔教唆、幫助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包括對于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明知或者應知”)平臺責任承擔在于其過錯(知或應知),也即上述后兩種情形。但須強調的是:首先,平臺“能不能知”與其本身技術水平密切相關,相關舉證責任難以歸于權利人,歸于權利人也難以落實,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其次,結合以上三種侵權事實發生狀態,在前述后兩種情況下,平臺本身負有過失或故意的主觀過錯,屬于一般歸責原則之適用,而在第一種控辯雙方掌握信息能力不對稱的情形下應當為平臺方負加舉證責任以衡平權利人的權利保護弱勢地位,建立健全實行過錯推定歸責原則,以免除權利人舉證責任負擔便于其維權。
綜上,平臺就侵權事實并非間接支配,應當屬于直接侵權,基于侵權事實及推定平臺主觀狀態,一般情況下可將平臺侵權行為認定為與網絡用戶間的共同侵權,而由于權利人信息弱勢地位、維權難等現狀及平臺侵權狀態,應當健全實行過錯推定歸責原則。
四、平臺侵權一般抗辯事由適用及其責任認定
以“北京銀河公司訴抖音著作權侵權”案為例,銀河公司主張抖音發布分享第三人泰安公司上傳侵權作品《賣油翁》構成侵權,而抖音則以平臺僅就該案中充當信息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開通有相關侵權投訴通道已經盡到法定注意義務與責任、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理由應當知道涉案內容侵權并不存在過錯三點理由進行辯駁,法院最終主要以銀河公司不能舉證相應主張為由支持抖音抗辯理由,判定抖音并不構成侵權。從上述抖音的三個抗辯理由來看,主要可歸納為:1.平臺在一起著作權侵權糾紛中所處地位、發揮作用決定其侵權行為構成;2.短視頻平臺主要以“避風港原則”即“通知- 刪除”,以通知為刪除前提并以之為免責事由;3.“紅旗標準”下平臺知或應知侵權事實的欠缺。那么是否誠如該案判決中的認定,將絕對大部分的舉證責任歸于權利人,而憑借平臺相關舉報設置即可一概適用“避風港原則”,“紅旗標準”下的“知或應知”又應當如何界定,以下將就平臺著作權侵權一般抗辯事由進行適用性具體分析。
(一)舉證責任分配合理性論證
就討論案例中,法院在該判決中以“銀河公司不能證明抖音對涉案視頻的上傳者進行了教唆或者幫助以及兩者之間存在分工合作,亦無證據證明抖音對涉案作品進行了選擇、編輯、修改、推薦等行為”論證抖音平臺主張適用“避風港及紅旗原則”抗辯事由成立。本案中,可直觀看到案件爭議過程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將很大程度影響判決結果以及論證事由的成立。抖音抗辯事由的成立建立在權利人就平臺涉及侵權事實程度的舉證不力基礎之上。但前述已經論述在雙方信息地位不平等的事實狀態下,苛責權利人進行大量侵權事實舉證是不現實的,且如此歸責,一來不利于著作權保護,助長平臺消極審核的不良態勢;二來著作權人在遭受現實直接財產利益損害的同時,可能由于網絡傳播迅速而產生大量附加利益難以保護,打擊作品創作熱情,不利于國內文化產業原生創作的健康有序發展。因此,應當基于平臺在短視頻行業運營模式下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地位,相對提高其法定義務,推動平臺積極審核,有效打擊侵權行為,轉變侵權糾紛歸責原則。
(二)“避風港原則”的區分情形合理使用
出于衡平網絡服務提供者與權利人之間的利益,應當避免“避風港原則”的濫用,厘清該原則的適用情形。本案中,抖音平臺僅以“開通有相關侵權投訴通道”為由主張“已經盡到法定注意義務與責任”,法院僅基于權利人舉證不利及平臺舉報通道設置為支持理由過于單一、失之偏頗,要合理適用“避風港原則”須得首先厘清其與“紅旗標準”規則適用之間的關系。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以“設置舉報通道”為由,要求通知前置,并以“已刪除或采取措施”為由主張免責,將極大刺激平臺的消極審核,若不加區別適用“避風港規則”,將使得該原則從鼓勵“網絡服務”轉變為“著作權侵權”的“保護傘”,在外在保護被打破之前,平臺完全可以“肆意而為”。[4]因此,在判斷平臺侵權責任時,應當優先適用“紅旗標準”規則,判斷平臺是否“知或應知”,若符合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9 條乃至一般可判斷情形的,應當要求短視頻平臺承擔主動審核、監測及刪除義務,否定“避風港原則”的當然適用。
(三)“紅旗標準”規則的補充完善
該案中,法院單純以權利人無法舉證《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9 條第(三)項“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主動對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進行了選擇、編輯、修改、推薦等”為由進行抖音平臺不符合“知或應知”的認定。但實踐案例中,應當注重該條第(七)項“其他相關因素”的補充認定與靈活適用,以一般判斷標準來說,針對短視頻是否熱播(流量)、是否被列于網站首頁、視頻內容長度及是否完整、視頻標題是否屬于防范侵權關鍵詞等因素均應當被適當考慮。首先,平臺以視頻流量進行獲利,因此,某一視頻點擊量、瀏覽量的極高是平臺作為短視頻運營者所合理關注的范圍;其次,某一平臺首頁作為吸引用戶關注的“第一版面”必然是平臺比較重視的;再次,某些平臺內短視頻將某一作品分割成若干小段,但播放時卻可連續甚至順暢,從某種角度上實現了作品的“完全復現”,其中短視頻平臺的“無意排序”實際上是構成侵權事實的重要因素;復次,從現有技術來說,面對大規模的上傳視頻苛求平臺全面盡到審核義務是不現實的,但對于視頻內容的人工審核外的標題文字審核是可以通過軟件技術高效實現的,對于某些侵權視頻其本身通過侵權作品名稱吸引網絡用戶關注,這正是規制它的重要著眼點。綜上所述,在實踐中對于“紅旗標準”規則適用認定標準上應當結合一般判斷標準,對平臺附加合理范圍內的注意義務。[5]
(四)平臺責任兜底性規定
首先,在短視頻侵權糾紛中除平臺直接搬運作品侵權外,最為常見的是網絡用戶制作或發布侵權視頻,平臺提供分享服務,二者共同侵犯著作權人的權利。而由于網絡的虛擬性特點,網絡用戶實際主體難以確定,甚至確定主體由于實際空間距離,維權成本高而難以維權,相較之平臺作為營利法人,往往具有相對雄厚的資本并固定可循,其作為侵權行為事實上的技術提供者,在網絡用戶侵權人難以追究的情況下應當承擔相應的補充連帶責任。其次,本案中法院僅從平臺滿足“避風港原則”及“紅旗標準”規則適用的侵權責任免責事由而直接將平臺從權利人損失責任承擔中摘除有所不妥。即使平臺對于侵權事由具有正當抗辯事由,但在短視頻傳播迅速、流量或廣告獲益的特點下,平臺不可否認地從中獲取利益,基于侵權視頻而缺乏正當事由獲利,應當承擔不當得利之責任。這是當下實踐中所應廣泛注意的,即平臺基于其不當得利事實,不能從某一短視頻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完全摘除,否則亦是對權利人的一大損害。綜上所述,應注重平臺的責任承擔,并歸結于平臺對侵權事實“應知”的認定。這在我國《民法典》第1197 條對《侵權責任法》第36 條的規定加以明確中也得以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97 條:“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即明確“平臺‘應知’侵權事實而未采取相應措施的承擔侵權責任”。
五、結語
就現有司法實踐中,應在適當加重平臺責任承擔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要避免絕對的苛責平臺,片面追求對作品著作權的保護,注意衡平兩者之間的關系,以推動實現短視頻乃至整個網絡經濟平臺行業的健康積極發展。如《民法典》中第1195條、1196 條規定,權利人主張權利須初步證明侵權事實并應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以避免惡意或錯誤的權利主張對穩定網絡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同時,借鑒《電子商務法》第43 條“反通知規則”的規定,保障平臺作為以分享視頻為目的之中介的技術中立性,并享有在接到否認侵權事實的網絡用戶的通知后轉通知及在合理期限不能得到回應情況下終止措施的權利。[6]以“優酷訴北京奇果不正當競爭”案、“浙江電視集團訴千衫公司侵犯網絡信息傳播權”案為例,被訴侵權公司僅以“遵循技術中立原則實行行為”為由主張免責,即使在兩審裁判中也難以得到支持。但是類似案件當然得認定是否合理,經過比較可以發現,優酷案中奇果公司設置鏈接后不僅屏蔽原網站盈利廣告并改變了跳轉后呈現界面,較原界面有根本性變化,而千衫公司案中,平臺僅僅設置視頻鏈接,二審法院卻直接將侵害網絡傳播權中“提供”行為解釋為“不應只局限于將作品上傳于向公眾開放的網絡服務器的行為,還應包括通過設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軟件等方式將作品置于信息網絡中的提供行為”,僅以平臺文件分享行為即界定侵權近于苛責。網絡信息平臺本身以提供網絡信息為業務,在不涉及直接的視頻搬運播放、編排情況下,應當充分尊重平臺技術中立性,這與我國保護知識產權的立法精神并不沖突,也正體現當下我國尚需衡平平臺責任承擔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