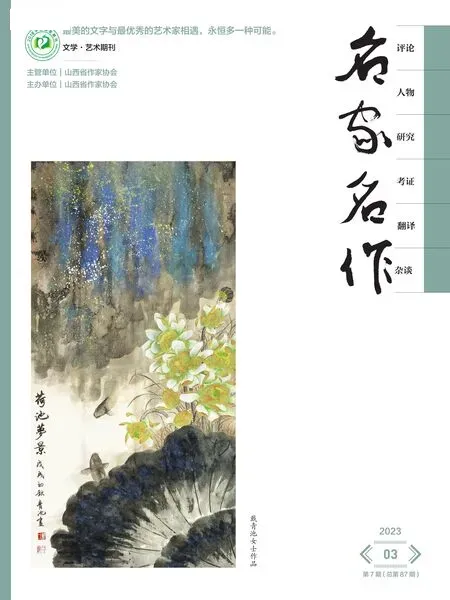論《史記》的“悲夫”之嘆
張 云
《史記》被譽為“無韻之離騷”,其在客觀敘述背后蘊含著太史公的熾熱情感與理想追求。后人對《史記》抒情性的分析,或基于記述的內容,或基于描述的手法,或基于表達的句式……本文從抒情的詞匯入手,以《史記》中的十三處“悲夫”為切入點,分類敘述太史公的時勢變化之嘆、榮辱成敗之嘆、名實相左之嘆、世態(tài)炎涼之嘆。
一、《史記》中的十三處“悲夫”之嘆
劉德煊在《〈史記〉的抒情特征》中言:“司馬遷喜用‘悲夫’一詞來表現(xiàn)某種豐富而深沉的感情。這樣的喟嘆,沉郁、寂寞的心情宛然如現(xiàn),表現(xiàn)出司馬遷遭受李陵之禍后對世態(tài)人情的深刻認識。”[1]詳究其實,全書共有十三處“悲夫”之詞,分別是《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伍子胥列傳》《李斯列傳》《韓信盧綰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楚元王世家》《絳侯周勃世家》《六國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從正文位置分布來看,“悲夫”一詞主要分布于論贊部分的“太史公曰”,共計九處,其余四處,兩處出自他人之言,一是“褚先生曰”,一是“光祿徐自為曰”;兩處出自列傳本人之言,一是李斯之言,一是司馬相如之文。
全書十三處“悲夫”之詞,不僅分布的篇目、位置不同,其所表達的情感內蘊也不同。《〈史記〉導讀十講》中提到,《史記》“通古今之變”的內容主要包括時勢之變、興亡之變、成敗之變和窮達之變[2]四大方面。通過十三處“悲夫”之詞,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太史公對時勢變化、榮辱成敗、名實向左、人情冷暖的悲嘆之情。其中,尤以榮辱成敗之嘆為甚。
二、太史公“悲夫”之嘆的情感表達
《史記》中的“悲夫”之嘆寄托了司馬遷真實而濃烈的情感。在這些表述中,司馬遷針對朝代更迭時勢變化,王侯將相榮辱成敗、名實相左、人情冷暖等做了深入細致的描摹,或贊嘆,或惋惜,或悲傷,或崇敬之情感表達躍然紙上。正如李巍在《論〈史記〉抒情性及其得失》中論述道:“司馬遷把自己的真實感情,隱藏在對事件即人物悲慘遭遇的真實描寫中,又借傳中人物在此悲慘遭遇中流露出來的思想感情,來抒發(fā)自己的思想感情。”[3]
(一)時勢變化之嘆
秦國集六世之功而一統(tǒng)天下,但是后人僅以秦國二世而亡、《秦記》文辭疏略而看輕秦國、譏笑秦國,這種避重就輕、舍本逐末的認知,讓太史公不由生出對時勢變遷的“感嘆”之情。
《六國年表》記載了秦國“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4],一展天下時勢之變。縱觀《六國年表》,秦國于“襄公始封為諸侯”,歷經(jīng)文公“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閑”,穆公修政“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此后,秦孝公變法強秦,成效宏大。至秦一統(tǒng)天下,統(tǒng)一文字與度量衡,實行郡縣制等,功業(yè)非凡。
《六國年表》內容多參照《秦記》而作。但因《秦記》文詞疏略,秦國二世而亡,漢初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可見漢初對秦國的譏笑看輕態(tài)度。當世對于前世之功業(yè)視而不見,反因文辭看輕譏笑,太史公故有此嘆。
(二)榮辱成敗之嘆
《史記》中,對于個人榮辱成敗之嘆尤為突出。王侯將相均有涉及,他們或篡位得權,或忍辱負重,或起于微末,終能成就非凡之功業(yè)、名揚于天下,但或因自身失德,或因同僚進讒,主上猜忌,終以悲劇收場,故太史公有此“悲夫”之嘆。
1.《楚元王世家》中的“悲夫”之嘆,嘆楚靈王操行不得而眾叛親離、客死在外
楚靈王殺其侄以自立,會盟諸侯而驕縱無禮。對外窮兵黷武,征戰(zhàn)陳、蔡、徐等國,在內窮奢極欲,建章華臺以供己享樂。太史公論其“操行之不得”,由此而來。
楚靈王榮耀之時,“會諸侯于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5]。及其一朝行樂在外,宮中變亂,天下離心,獨傍偟山野,無人收容、饑餓難起。觀此榮辱之變,故有悲嘆。為進一步凸顯楚靈王的榮辱之變,強調操行對于榮辱的重要性,太史公通過觀起之子與申無宇之子一正一反的描述,強化了“悲夫”之嘆。從反面來看,因楚靈王“殺蔡大夫觀起”,觀起之子勸吳伐楚,會合各方力量,讓楚靈王眾叛親離、客死在外;從正面來看,楚靈王傍徨山野之時,申無宇之子申亥為報答其父“再犯王命”而靈王“弗誅”之恩,往山中尋求靈王,奉之歸家。
2.《絳侯周勃世家》中的“悲夫”之嘆,明嘆周勃父子性格使然,實悲所遇非人
周勃與周亞夫出身皆因赫赫軍功獲殊榮。周勃起于布衣,隨高祖起兵,在楚漢之爭中屢立戰(zhàn)功,此后兵討韓王信、陳豨、盧綰,誅殺呂氏,擁立文帝,位及丞相。周亞夫起于文帝時細柳營治軍之嚴,景帝之初,封為車騎將軍,此后平定七國之亂、位遷丞相。太史公贊其“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穰苴曷有加焉”,足見認可。從二人性格來看,周勃質樸剛強,周亞夫耿直剛毅。周勃與儒生相交不能尊重,身在絳縣適逢守尉巡視,畏懼被誅而“令家人持兵以見”,因此被人誣告謀反而下獄;周亞夫因直言諫廢太子,阻匈奴王封侯等事漸被景帝疏離,此后因其子盜買官器而被誣謀反入獄。所不同的是,周勃用千金賄吏,以公主為證,薄太后開脫得以生還;周亞夫在獄中“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李景星言:“絳侯兩世有大功于漢,俱以下吏收場,此太史公最傷心處,故用全力寫之。”[6]太史公在描述二人悲劇結局中,無限同情二人的悲慘遭遇,同時也表達了對君上、同僚和讒吏的憤怒與抗議。
司馬遷在《絳侯周勃世家》中,用“足己而不學,守節(jié)不遜,終以窮困”來悲嘆二人的命運其實是“似貶而實褒”。表面看來二人性格確實會導致先榮后辱的悲劇命運,但細究起來,無論是周勃被人“上書告勃欲反”,還是周亞夫下獄“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7],足見同僚佞言、君上猜忌、下吏侵迫讓兩位軍功卓著、耿直剛強之人不得善終。所謂“削平吳楚大功成,一旦生疑觸怒霆”,這才是太史公真正的悲嘆所在。
3.《伍子胥列傳》中的“悲夫”之嘆,贊伍子胥隱忍成事,嘆其所遇非人
伍子胥“棄小義”逃亡吳國,最終攻入楚國“雪大恥”,因其隱忍終能成事。在《伍子胥列傳》中,楚平王以伍奢為人質,“詐召二子”欲一并除之。伍尚赴死,伍子胥逃往吳國,后伍子胥父兄皆被楚平王殺害。伍子胥逃往吳國之后,成為吳王闔閭重臣。公元前506 年,伍子胥協(xié)同孫武帶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終報父兄之仇。此后,伍子胥助吳北敗徐、魯、齊,成為諸侯一霸。
西漢韓詩學的創(chuàng)始人韓嬰說:“伍子胥前功多,后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后遇夫差也。”[8]夫差繼闔閭成為吳王之后,伍子胥多次勸諫不被采納。此后,太宰伯嚭多次進讒,稱伍子胥陰謀倚托齊國反吳。最終夫差派人送一把寶劍給了伍子胥,令其自殺。伍子胥自殺前讓門客將其雙目掛于城門之上以觀越國滅吳,反因此觸怒夫差,被浮尸江中。伍子胥死后九年,吳國被越國所滅。在《伍子胥列傳》中,太史公論贊四句話中三句反問,一句感嘆,從語氣里即可見其感情的激動。從周勃、周亞夫父子,到伍奢、伍子胥父子,其悲慘結局皆因“所遇非人”。讒臣的進言、君主的猜忌,導致他們凄涼的收場,太史公在論贊中對此寄予了豐富的情感和無限的慨嘆。
(三)名實相左之嘆
《后漢書·左周黃列傳》中有言:“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9]太史公對孫臏、吳起、伯夷、叔齊、陳豨之嘆,或因其名實不一、言行不一,或因高義未揚,或因名過其實。由此,他人之名、他人之言,未必真如其實,更應客觀、辯證地看待。
1.《孫子吳起列傳》中的“悲夫”之嘆,嘆孫臏與吳起名實不一、言行不一
孫臏能料敵于先擊殺龐涓,卻未料龐涓之計而被刑,所謂名實不一之處。孫臏在齊,兩次因勢利而圍魏救趙、救韓,通過桂陵之戰(zhàn)、馬陵之戰(zhàn),計殺龐涓,可謂“籌策龐涓明矣”;但反觀孫臏初入魏國,未能預料龐涓刑而隱之之心,而致腿斷面黥,太史公稱之“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兩者對比,即為名實不一之處。
吳起殺妻貪將、母死不歸,也能與卒同苦、盡得士心,在魏言德,在楚刻暴,所謂言行不一。曹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說,“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10]吳起雖然于家少德,但卻能盡得士卒之心,成就功業(yè),此為一處不一;吳起在魏之時,魏武侯言山河之固是“魏國之寶”,吳起諫言“在德不在險”;反觀其在楚之時,則“刻暴少恩”,此為另一處不一。
綜上所述,人之名實未必一致,人之言行也未必一致,所以太史公在《孫子吳起列傳》中對孫臏、吳起才有此一悲。
2.《伯夷列傳》中的“悲夫”之嘆,嘆君子高義未必能名揚于世
《伯夷列傳》中,太史公言:“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11]伯夷、叔齊讓一國之位被世人稱贊,因“得夫子而名益彰”;但是許由讓天下之位而少有記載,故太史公有“名堙滅而不稱”之悲。由此可見,君子高義未必能名揚于后世,能名揚于世者是因有人彰名或者能夠“附青云之士”而上。所以,揚名于天下者未必最為有名,高義之士也未必能夠揚名天下,故有一悲。
3.《韓信盧綰列傳》中的“悲夫”之嘆,嘆陳豨名過其實招致禍患
太史公悲嘆陳豨“名過其實”而致禍患。陳豨仰慕信陵君之名,有招攬賓客、禮賢下士之心,回鄉(xiāng)過趙“賓客隨之者千余乘”且能夠“待賓客布衣交”。因此遭周昌疑心,陳豨“懼禍及身”,最終走上反叛道路。劉邦觀陳豨排兵布陣評價其“無能”,察常山守尉不隨其反評價其“力不足”,陳豨最終被樊噲軍卒所殺,可謂名過其實之禍。
(四)人情冷暖之嘆
主父偃、汲鄭均是先得其勢,后失其勢。在得勢之時“諸公皆譽”“賓客十倍”,而一旦失勢則“爭言其惡”“門可羅雀”。前后之別,太史公引翟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深刻而形象地描繪了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之悲。
1.主父偃“悲夫”之嘆,嘆其得勢“諸公皆譽”失勢“爭言其惡”
《平津侯主父列傳》中,主父偃未得志時嘗盡人間冷暖,當其得漢武帝信任拔擢之時“諸公皆譽之”。后因舉發(fā)齊王“淫佚行僻”導致齊王自殺,漢武帝下令殺之,則“士爭言其惡”。眾人前后態(tài)度之變,凸顯世態(tài)之炎涼,太史公故有此悲。
2.《汲鄭列傳》中的“悲夫”之嘆,嘆汲、鄭二人得勢“賓客十倍”,失勢“門可羅雀”
《汲鄭列傳》中引用下邽翟公做廷尉時賓客盈門,中道被廢以致門可羅雀,后復職為廷尉,賓客又要登門,于是翟公在門前寫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tài)。一貴一賤,交情乃見。”[12]太史公以此來比汲、鄭二人“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的境遇,對封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勢利關系,對世態(tài)炎涼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諷。
三、余者“悲夫”之嘆的情感異同
《史記》中還有四處“悲夫”之嘆,并非出自太史公之口,而是由他人所言或所記人物自身之言。其中,褚先生對“功臣侯者”成敗的補述、李斯一生榮辱及其下獄后的悲嘆,此二處與太史公榮辱成敗之嘆甚為吻合。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中的“悲夫”嘆眾人目光不夠長遠,只言害而不見利;光祿徐自為之嘆,則表達了對酷吏的痛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褚先生對《史記》所載“功臣侯者”的“成敗長短”加以補述,對其“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爭”終至失身滅國的榮辱之變備加感慨,也與太史公著書宗旨和主旨觀念一脈相承,相得益彰。
《李斯列傳》中,李斯被囚于囹圄之中,仰天長嘆,“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13]回顧其一生,起于上蔡閭巷布衣,至盛之時位居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shù)”。[14]后因畏禍與趙高合流,導致“沙丘之變”,為自保而上書曲意逢迎,在與趙高爭勢中落敗下獄。后被趙高誣為謀反,腰斬于咸陽市,夷三族。觀其一生榮辱成敗與太史公所嘆甚為契合。
《司馬相如列傳》中,司馬相如所撰《難蜀父老》圍繞大臣和蜀中對通西南夷的非議和畏難之情,通過“鷦明已翔乎寥廓”但“羅者猶視乎藪澤”之喻,暗示眾人沒有意識到開拓疆域,交好夷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是盯著西南邊疆開發(fā)的勞民傷財,故有“悲夫”之嘆。
《酷吏列傳》對十名酷吏作了描述,其中對王溫舒捕郡中豪門奸詐“連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之事,言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復言其為人諂諛,對待有權勢者“有奸如山”也不過問,對待無權勢者,雖是貴戚也必然侵辱。天子凡認為王溫舒有治事的才能,予以升遷。待王溫舒因罪而被滅族,光祿徐自為有“悲夫”之嘆,感慨“古有三族”,而對王溫舒的罪行誅其五族也不為過,表達了對酷吏的痛恨。
在司馬遷《史記》中,擁有著豐富的語氣詞,除“悲夫”之外,尚有“嗟乎”“嗚呼”“宜乎”“惜哉”等諸多詞語,明確表達出了太史公寫史之中的各種情感。這些詞語為《史記》的抒情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太史公的著述宗旨和主旨觀念提供了有力的印證與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