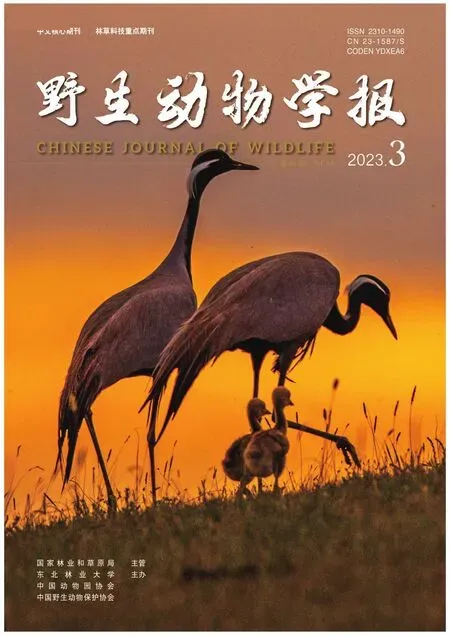四種菊頭蝠在不同狀態(tài)下回聲定位聲波的可塑性
張現(xiàn)政,黃曉賓 ,王玉娟,楊金颋,鄭小燕
(1.大理大學病原與媒介生物研究所,云南省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控技術重點實驗室,大理,671000;2.東北師范大學環(huán)境學院,吉林省動物資源保護與利用重點實驗室,長春,130000)
蝙蝠(翼手目,Chiroptera)是僅次于嚙齒類(Rodentia)的第二大哺乳動物類群。全世界已知蝙蝠共21 科230 屬超過1 400 種,約占哺乳動物總數(shù)的20%[1]。作為唯一真正擁有飛行能力的哺乳動物,蝙蝠分布于全球除兩極和某些太平洋島嶼外的其他地方,是分布最廣泛的哺乳動物[2]。同時,除狐蝠科(Pteropodidae)部分物種外,絕大多數(shù)蝙蝠物種都能夠發(fā)出回聲定位聲波,并通過提取回聲中的時空信息來感知周圍世界,從而實現(xiàn)空間導航、獵物追蹤和目標識別等目的。大量研究指出,蝙蝠正是憑借復雜而強大的回聲定位能力,才成功占據(jù)許多動物難以利用的夜空生態(tài)位,也成為進化最為成功的動物類群之一[3-4]。
自20世紀40年代Dijkgraaf[5]首次證實蝙蝠能夠發(fā)出回聲定位聲波用于躲避障礙物后,針對蝙蝠回聲定位聲波的研究從未停止,其中,對蝙蝠回聲定位聲波可塑性的研究是近30 年來的一個熱點領域。這些研究認為,蝙蝠在不同捕食階段或不同生境中,為適應活動任務和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能主動調(diào)節(jié)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結構。例如,當蝙蝠通過回聲定位聲波搜索周圍獵物時(搜索階段,search phase),可發(fā)出持續(xù)時間較長且頻帶較窄的聲波以探測獵物;當蝙蝠發(fā)現(xiàn)并逐漸接近獵物時(接近階段,approach phase),所發(fā)聲波持續(xù)時間變短且頻帶變寬;在抓獲獵物之前的最后階段(結束階段,terminal phase),聲波持續(xù)時間急劇縮短,重復率顯著增大,在獲取最大化信息量的同時避免聲波與回聲的重疊[6-9]。此外,當蝙蝠在開闊生境飛行或捕食時,因沒有障礙物及回聲干擾,蝙蝠能發(fā)出持續(xù)時間較長和主頻較低的回聲定位聲波,進而實現(xiàn)遠距離探測;當蝙蝠進入復雜生境(如森林)后,則發(fā)出持續(xù)時間短、間隔時間短且高頻的聲波,不但可避免聲波和回聲重疊,也可近距離精確分辨獵物和周圍環(huán)境[10-11]。
蝙蝠在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同樣存在可塑性變化,如孫克萍等[12]證實馬鐵菊頭蝠(Rhinolophus ferrumequinum)在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持續(xù)時間、間隔時間和主頻均較懸掛狀態(tài)低。同樣的結果也在彭樂等[6]對大蹄蝠(Hipposideros armiger)和中蹄蝠(H.larvatus)的研究中被發(fā)現(xiàn)。但令人疑惑的是,李艷麗[13]通過對中華菊頭蝠(Rhinolophus sinicus)4 種行為狀態(tài)(飛行、懸掛、布袋和手持)下回聲定位聲波的研究,發(fā)現(xiàn)飛行狀態(tài)下的主頻顯著低于其他3 種狀態(tài),但持續(xù)時間卻明顯高于其他 3 種狀態(tài)。劉穎等[14]也發(fā)現(xiàn)普通長翼蝠福建亞種(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parvipes)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主頻顯著高于懸掛和手持狀態(tài)下的聲波,持續(xù)時間則是懸掛狀態(tài)最長。不同的結果可能源自:(1)不同的研究存在實驗環(huán)境及研究者處理方式等方面的差異;(2)蝙蝠回聲定位聲波在不同行為背景下的可塑性變化存在種間差異。因此,為更加全面地揭示蝙蝠在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可塑性變化,需要在相同實驗條件下對多個蝙蝠物種進行聲信號采集和分析。鑒于此,本研究選擇回聲定位能力較發(fā)達的菊頭蝠科(Rhinolophidae)4種蝙蝠(大耳菊頭蝠Rhinolophus macrotis、貴州菊頭蝠Rh.rex、馬鐵菊頭蝠和中菊頭蝠Rh.affinis)為研究對象,對在飛行、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下發(fā)出的回聲定位聲波進行錄制,通過分析聲波脈沖的持續(xù)時間、間隔時間和主頻參數(shù)的變化,系統(tǒng)地探究蝙蝠在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回聲定位聲波的可塑性。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點
法古甸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qū)雙河彝族鄉(xiāng),平均海拔1 937 m,屬于低緯度高原北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2 ℃,年平均降水量890 mm,四季如春,干濕季分明,植被覆蓋度較高,多為常綠闊葉林,為蝙蝠提供了理想的棲息環(huán)境。
2022 年7 月,以法古甸村仙人洞為研究地點開展工作。仙人洞位于法古甸村農(nóng)田邊,洞口向下延伸,深約100 m,洞口寬約6 m,高約2 m。洞穴內(nèi)棲息大耳菊頭蝠、短翼菊頭蝠(Rh.lepidus)、小菊頭蝠(Rh.pusillus)、貴州菊頭蝠、馬鐵菊頭蝠、中菊頭蝠、三葉小蹄蝠(Aselliscus stoliczkanus)、大衛(wèi)鼠耳蝠(Myotis davidii)和華南水鼠耳蝠(M.laniger)等多種蝙蝠,集群數(shù)量達上千只。
1.2 蝙蝠捕捉
試驗前,在洞外搭建臨時錄音實驗棚(9 m×4 m×4 m),實驗棚頂部覆蓋黑色遮光布,棚內(nèi)無障礙物,以防對蝙蝠在棚內(nèi)的活動造成干擾。實驗棚距村莊和蝙蝠洞穴均超過100 m,能夠有效避免人類活動和蝙蝠洞穴內(nèi)雜音對聲波錄制產(chǎn)生的潛在影響。在傍晚蝙蝠飛出前,于洞口處懸掛霧網(wǎng),捕捉外出覓食和歸洞的蝙蝠。通過蝙蝠翼的掌骨和指骨連接處的愈合程度判斷年齡,如抓捕到亞成體以及懷孕和哺乳個體則立即釋放。將捕獲的蝙蝠放置在干凈透氣的布袋內(nèi),每布袋放置1 只,帶回實驗棚內(nèi)錄制聲波。試驗全程采用正確姿勢持握蝙蝠,輕拿輕放,避免對蝙蝠造成傷害。最終捕獲18 只成年菊頭蝠科蝙蝠,分別是大耳菊頭蝠7 只、貴州菊頭蝠4 只、馬鐵菊頭蝠4只和中菊頭蝠3只。
1.3 回聲定位聲波錄制與分析
逐一將蝙蝠放于錄音棚中,自由飛行一段時間后,使用超聲波錄制儀(Avisoft-UltraSoundGate 116H,Avisoft Bioacoustics,Germany)獲取每只蝙蝠飛行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錄制儀與筆記本電腦(聯(lián)想ThinkBook,中國)連接,采樣頻率為375 kHz,精度為16 bit(后續(xù)聲波錄制參數(shù)與此一致)。之后,捕獲蝙蝠并用手將其控制住,使用超聲波錄制儀錄制每只蝙蝠在手持狀態(tài)下發(fā)出的回聲定位聲波。最后,在棚內(nèi)釋放蝙蝠,任由其自由懸掛在大棚頂部,待蝙蝠安靜數(shù)分鐘后,錄制懸掛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每種行為狀態(tài)下每只蝙蝠至少錄制5 min的聲音文件。待錄音完畢后,將蝙蝠帶回捕捉地放飛。
選擇每只蝙蝠每種行為狀態(tài)下具有較高信噪比(>30 dB)的10 個回聲定位聲波脈沖進行分析。聲學分析僅分析每一脈沖的最大能量諧波,分析測量的參數(shù)包括脈沖持續(xù)時間(pulse duration)、脈沖間隔時 間(inter-pulse interval)和主頻(dominant frequency,能量最高處的頻率),軟件為Avisoft SASLab Pro(Avisoft Bioacoustics,Germany),聲學分析參數(shù)統(tǒng)一設定:Hamming window,512 FFT,75% overlap,100% frame size,頻率分辨率為732 Hz,時間分辨率為0.341 3 ms。
1.4 統(tǒng)計分析
為比較每種蝙蝠在不同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差異,對每種蝙蝠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脈沖間隔時間和主頻參數(shù)進行K-S 檢驗(Kolmogorov-Smirnov test),以明確聲學數(shù)據(jù)是否為正態(tài)分布。若數(shù)據(jù)為正態(tài)分布,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較同一物種在3 種行為狀態(tài)下發(fā)出的聲波是否存在差異,如存在差異則通過最小顯著差法(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進行兩兩比較,明確任意2 種狀態(tài)下的聲波差異。若數(shù)據(jù)為非正態(tài)分布,使用克魯斯卡爾-沃利斯秩和檢驗(Kruskal-Wallis test)判定同一種蝙蝠在3 種狀態(tài)下的聲波差異,如存在明顯差異使用鄧恩檢驗(Dunn’s test)確定任意2種狀態(tài)下的聲波差異。以上統(tǒng)計使用SPSS 26.0和R 4.1.2進行,顯著性水平設為0.05。
2 結果
2.1 4種菊頭蝠回聲定位聲波特征
4 種菊頭蝠在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均為調(diào)頻-恒頻-調(diào)頻(FM-CF-FM)型,能量也均主要集中在第二諧波的CF 部分,其中中菊頭蝠主頻最高,其后依次為馬鐵菊頭蝠、大耳菊頭蝠和貴州菊頭蝠(圖1)。

圖1 4種菊頭蝠在3種行為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時域波形和聲譜Fig.1 Sound envelopes and spectrogram of echolocation calls emitted by four species of horseshoe bat in three behavioral statuses
2.2 4種菊頭蝠不同狀態(tài)下回聲定位聲波差異
大耳菊頭蝠在飛行、懸掛和手持3 種狀態(tài)下所發(fā)出的回聲定位聲波存在顯著差異(脈沖持續(xù)時間:F=36.339,p<0.001;脈沖間隔時間:χ2=81.483,p<0.001;主頻:χ2=12.526,p=0.002)。其中,飛行狀 態(tài)下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顯著長 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p<0.01),而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 間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差異并不顯著(圖2A、B)。飛行狀態(tài)下聲波主頻顯著低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而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間聲波主頻無明顯差異(圖2C)。
貴州菊頭蝠在3 種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存在明顯差異,脈沖持續(xù)時間(F=11.075,p<0.001)和脈沖間隔時間(F=8.409,p<0.001)差異顯著,但主頻并無顯著差異(χ2=0.461,p=0.794))(圖2A-C)。飛行狀態(tài)下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顯著長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而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間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差異不顯著(圖2A、B)。
馬鐵菊頭蝠在3 種狀態(tài)下發(fā)出的回聲定位聲波存在顯著差異(脈沖持續(xù)時間:F=6.901,p=0.001;脈沖間隔時間:F=8.238,p<0.001;主頻:χ2=11.694,p=0.003)。懸掛狀態(tài)下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顯著長于飛行和手持狀態(tài),而飛行和手持狀態(tài)間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差異不顯著(圖2A、B)。飛行狀態(tài)下聲波主頻顯著低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而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間聲波主頻差異不顯著(圖2C)。
中菊頭蝠在3 種狀態(tài)下發(fā)出的回聲定位聲波存在明顯差異(脈沖持續(xù)時間:F=13.317,p<0.001;脈沖間隔時間:F=9.600,p<0.001;主頻:χ2=42.074,p<0.001)。懸掛狀態(tài)下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顯著長于飛行和手持狀態(tài),飛行狀態(tài)下脈沖持續(xù)時間顯著長于手持狀態(tài),而飛行和手持狀態(tài)間脈沖間隔時間差異并不顯著(圖2A、B)。飛行狀態(tài)下聲波主頻顯著低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而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間聲波主頻差異不顯著(圖2C)。
3 討論
本研究在相同試驗條件下獲取了大耳菊頭蝠、貴州菊頭蝠、馬鐵菊頭蝠和中菊頭蝠在飛行、手持和懸掛3 種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在進行比較分析后發(fā)現(xiàn):(1)大耳菊頭蝠和貴州菊頭蝠在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脈沖間隔時間均最長,與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相比差異顯著;而馬鐵菊頭蝠和中菊頭蝠在懸掛狀態(tài)下所發(fā)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間隔時間最長,與飛行和手持狀態(tài)相比差異顯著,且中菊頭蝠在手持狀態(tài)下的脈沖持續(xù)時間明顯短于飛行狀態(tài);(2)除貴州菊頭蝠外,其他3 種蝙蝠在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聲波的主頻顯著低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以上結果證實,蝙蝠在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表現(xiàn)出明顯的可塑性,且這種可塑性存在種間差異。
有研究發(fā)現(xiàn),馬鐵菊頭蝠、大蹄蝠和中蹄蝠在懸掛(靜息)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間隔時間均比飛行狀態(tài)下長[6,13]。本研究對馬鐵菊頭蝠和中菊頭蝠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回聲定位聲波的分析結果與這一結論一致。一種推測認為,在快速飛行過程中,蝙蝠若發(fā)出較短持續(xù)時間和間隔時間的聲波不僅能夠有效緩解所發(fā)聲波脈沖與回聲的重疊,同時也有利于提高脈沖的重復速率,最終保證蝙蝠快速獲取多變的時空信息[15];另一種推測則認為,發(fā)出更多的回聲定位聲波脈沖需要蝙蝠消耗更多的能量,而當蝙蝠處于懸掛(靜息)狀態(tài)時,對獲取外界環(huán)境信息的需求變少,為了節(jié)約能量,便會減少單位時間內(nèi)發(fā)出的脈沖數(shù)量[16]。本研究也發(fā)現(xiàn),馬鐵菊頭蝠和中菊頭蝠在手持狀態(tài)下所發(fā)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間隔時間顯著小于懸掛狀態(tài),甚至中菊頭蝠在手持狀態(tài)下的聲波持續(xù)時間還顯著小于飛行狀態(tài),這與劉穎等[14]對普通長翼蝠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是手持狀態(tài)下蝙蝠受到捕食威脅和驚嚇,發(fā)出更為急促的聲波以獲取更多關于周圍環(huán)境和捕食者(實驗人員)的信息。本研究對大耳菊頭蝠和貴州菊頭蝠在不同行為背景下的聲學可塑性分析得到了不同結果,即在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聲波的脈沖持續(xù)時間和間隔時間均顯著長于懸掛和手持狀態(tài),可能原因是:相比馬鐵菊頭蝠(翼載:9.45 N/m2)和中菊頭蝠(翼載:7.70 N/m2),大耳菊頭蝠(翼載:5.77 N/m2)和貴州菊頭蝠(翼載:6.02 N/m2)具有較小的翼載,表現(xiàn)出速度較慢但更加靈活的飛行能力,因此飛行狀態(tài)下不用擔心所發(fā)聲波脈沖和回聲產(chǎn)生重疊,為了最大化獲取信息,蝙蝠也相應增大所發(fā)聲波的時間參數(shù)[17-19]。
本研究中大耳菊頭蝠、馬鐵菊頭蝠和中菊頭蝠在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主頻顯著低于手持和懸掛狀態(tài)。馮江等[9]、孫克萍等[12]、李艷麗[13]和郭偉健等[16]在對馬鐵菊頭蝠、普氏蹄蝠(Hipposideros pratti)、華南菊頭蝠(Rhinolophus huananus)和大蹄蝠在不同行為狀態(tài)下回聲定位聲波的比較分析中也發(fā)現(xiàn)類似結果,并認為不同狀態(tài)下的主頻差異可能是由恒頻蝙蝠的多普勒補償效應引起,即恒頻蝙蝠在飛行過程中,由于逐漸地接近前方目標,不斷發(fā)出回聲定位聲波的主頻會隨著距離縮短而相應升高,故許多種類蝙蝠為使所聽到回聲的頻率維持在其聽覺最為敏感的頻率范圍內(nèi),往往會主動將發(fā)出的聲音頻率降低[9,12-13,16],這一現(xiàn)象在劉穎等[14]和朱旭等[20]對調(diào)頻蝙蝠(普通長翼蝠和大棕蝠江南亞種Eptesicus serotinus andersoni)的研究中未被發(fā)現(xiàn)。但本研究結果證實,貴州菊頭蝠在飛行狀態(tài)下所發(fā)回聲定位聲波的主頻與其他2 種狀態(tài)相比并無顯著差異,可能是貴州菊頭蝠自身聲波主頻較低(24.1~24.9 kHz),雖然仍為超聲波,但已接近許多動物類群的可聽聲學頻率范圍,如果過多降低飛行狀態(tài)下的主頻可能導致回聲定位聲波被潛在獵物和捕食者竊聽,從而影響捕食和反捕食行為。
本研究證實菊頭蝠在不同狀態(tài)下的回聲定位聲波具有明顯的可塑性,可通過改變回聲定位聲波結構來更好地適應行為狀態(tài)的變化。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試驗中捕捉的蝙蝠數(shù)量較少,未來的試驗應加大蝙蝠樣本量;二是受制于環(huán)境條件,臨時實驗棚搭建較為簡陋,內(nèi)部空間較小不利于蝙蝠飛行;此外,雖然在試驗過程中盡力避免人為活動對蝙蝠的影響,但在蝙蝠的聲波采集過程中,錄音人員的活動難免會對蝙蝠狀態(tài)造成影響。以后的試驗應盡量避免或減少上述不利因素的影響,增加樣本量和優(yōu)化試驗條件,深入開展蝙蝠聲波的研究,也可探索不同的環(huán)境因子對蝙蝠回聲定位聲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