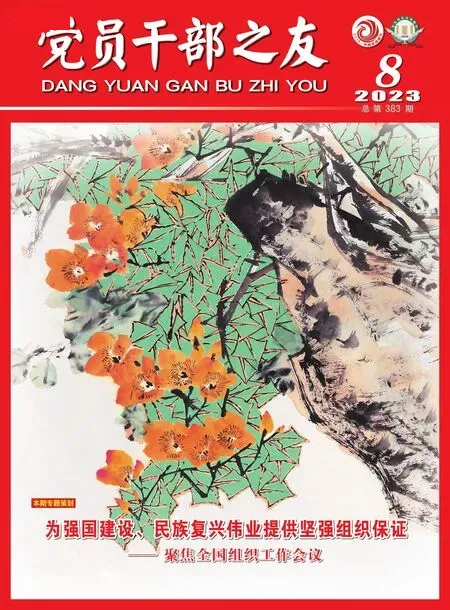拒絕遺忘靠什么
□ 逄春階

黎 青/圖
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法國(guó)作家安妮·埃爾諾說(shuō):“一切事情都以一種聞所未聞的速度被遺忘。”遺忘如雨珠落海,無(wú)影無(wú)蹤。拒絕遺忘,靠什么?
我在淄博市淄川區(qū)太河鎮(zhèn)峨莊下端士村看了《守望峨莊四十年——錢捍鄉(xiāng)土攝影回顧展》,被著名攝影家錢捍守望峨莊的情懷所感動(dòng)。一幅幅照片告訴我,拒絕遺忘的秘訣,是信念、天分與堅(jiān)守。
我與錢捍是老同事,他是《大眾日?qǐng)?bào)》攝影部原主任,曾連續(xù)兩屆獲得全國(guó)十佳新聞攝影記者稱號(hào),是全國(guó)勞模,享受國(guó)務(wù)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如今70 歲的他,依然沖鋒在第一線,端著他的相機(jī)在拍攝,在記錄。我打心眼兒里佩服他,常常問自己,他哪里來(lái)的這么大的能量。
錢捍40 多年的攝影生涯,我覺得他是小跑著的,一路向前,他的專注力非一般人所能達(dá)到。他跟蹤拍攝四胞胎兄弟長(zhǎng)達(dá)31 年,至今還在跟蹤;全年無(wú)休撰寫攝影日記;冒著零下30 多度嚴(yán)寒,拍攝新疆哈薩克牧民轉(zhuǎn)場(chǎng),一拍又是8 年……小到一個(gè)家庭,中到一個(gè)部門、一級(jí)組織,大到一個(gè)國(guó)家,你看歷史的變遷,要對(duì)比,就得有足夠的時(shí)間,時(shí)間越長(zhǎng),越有歷史的滄桑感。錢捍做到了。我想起了知名畫家余任天先生的一首詩(shī):“一藝功成豈偶然,人工天分兩相連。還應(yīng)滋養(yǎng)源頭水,寂寞樓居四十年。”錢捍不是寂寞樓居,而是寂寞地奔跑與蹲守。
峨莊曾經(jīng)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大山深處的窮山村,從某種程度上講,因?yàn)橛辛隋X捍等人的關(guān)注,峨莊才引起了世人的關(guān)注。錢捍與峨莊互相見證、互相發(fā)現(xiàn)、互相成就。我在他的攝影展上,給他寫了這么幾句話:“他遵從內(nèi)心選擇,挽回了峨莊40 年消失和即將消失的景象。40 年的牽掛與守望,40 年的心血凝聚與清晰表達(dá),40 年的溫暖故事與精彩傳奇,皆濃縮于此,呈現(xiàn)于此。”
要了解峨莊,必須從發(fā)展中去了解,必須從聯(lián)系中去了解。沒有背景的峨莊,是平面的,有了背景,則有了立體感。這個(gè)“背景”就是把現(xiàn)在跟過(guò)去和未來(lái)比較,這是縱向的比較,把當(dāng)下的你和當(dāng)下的我和他比較,這是橫向的比較。峨莊的小腳女人蹣跚在山路上感受改革開放初期的新鮮與激動(dòng),春耕時(shí)節(jié)扛著自秦漢時(shí)就使用的耩耬的漢子,麥地里揮舞著鐮刀的壯漢和打麥場(chǎng)上的老人緩緩舉起的木棍,指向的都是溫飽。要合影了,盡管衣衫不整潔,但在腳下一定要擺一盆鮮花。扛著一袋袋山貨往外走,雖然看不到他們的面容,但從他們邁步的姿勢(shì),你能看出他們走出大山、告別貧窮的決絕。熙熙攘攘的集市、責(zé)任田頭丈量土地的場(chǎng)景、修繕房屋的從容女人、谷子地里的稻草人,皆成歷史遺跡。父親母親溝壑般的滿臉皺紋,如歷史的兩扇大門,如兩本厚厚的人生之書,延展到更遠(yuǎn)的歲月,昭示著未來(lái)的氣息。
錢捍攝影展的峨莊“背景”止步于小汽車進(jìn)村。象征著時(shí)間的車輪從每個(gè)人面前碾過(guò),一輪、二輪、三輪、四輪,不舍晝夜地滾滾向前。不知不覺,車輪飛馳的意象變成了大樹的年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如電唱機(jī)的唱盤一樣,訴說(shuō)著峨莊與時(shí)代大大小小的故事。
“驚醒了,五千余年的沉夢(mèng)。”鄉(xiāng)村振興的宏偉構(gòu)想,意味著農(nóng)耕文明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最近十年來(lái),錢捍的腳步也加快了。山還是那座山,但已經(jīng)不是原來(lái)的山;人還是那些人,但歲月又把人的棱角塑造得更加分明。他們依然在趕集,但臉上掛著的笑容跟30 年前大大不同。2020 年疫情期間,他拍到了75 歲的王炳蘭和78 歲的老伴李玉樹老兩口趕大集的鏡頭;他拍到了72 歲的李一利和67 歲的李承學(xué)老哥倆在集市相遇,有拉不完的悄悄話的鏡頭;他在峨莊在集市上遇到了為老百姓剃頭已有42 年的66歲的孫啟海,他還碰到了年輕時(shí)一天能喝4 瓶白酒的65 歲的趙增效,現(xiàn)在身體不很好;他跟91 歲的肖洪忠攀談,老人獨(dú)自趕峨莊大集,來(lái)回要走幾公里路,等等。
山鄉(xiāng)的每一點(diǎn)變化,都逃不出錢捍的眼睛。修舊如舊的“農(nóng)家旅館”“農(nóng)家餐館”,分紅的場(chǎng)景,果園采摘紅杏的場(chǎng)景,萬(wàn)壽菊花海的盛況,親子歡樂園、觀光游覽車等游玩項(xiàng)目……錢捍的身心已經(jīng)融入了峨莊。他像峨莊的一塊山石,一棵老樹,鑲嵌在那里,迎風(fēng)送月。他在捍衛(wèi)峨莊的尊嚴(yán),捍衛(wèi)峨莊的生態(tài)美,人情美。
如果說(shuō),前30 年峨莊人的笑臉還沒有徹底綻放的話,那么最近10 年,他們的笑臉是從內(nèi)到外的最開心的狀態(tài)。別的不說(shuō),以大山為背景,參與到鄉(xiāng)村振興火熱場(chǎng)面的企業(yè)家李翠霞和下端士村村支書肖玉愛互相點(diǎn)贊的瞬間,那笑容是最燦爛也最意味深長(zhǎng)的,兩位美女正在策劃峨莊的一場(chǎng)大戲呢。
錢捍特別鐘情于孩子。他遇到孩子,每見必拍,其代表作就是《山里的孩子》,山里的孩子,豐富的情感凝聚在那些透明坦然、純真頑皮的笑容中,成為上世紀(jì)八十年代錢捍的代表作,入選第32 屆“荷賽”,并收入世界新聞攝影年鑒。
雖然在這之后的30 多年里,錢捍幾乎每年都到峨莊,來(lái)到下端士村拍片,也曾多次打聽過(guò)6 個(gè)“山里的孩子”的下落,但再未見過(guò)他們,不能不說(shuō)是遺憾。2021 年10 月14 日,錢捍在下端士村老人集體歡度重陽(yáng)節(jié)的人群里,意外地見到了當(dāng)年照片中10 歲的男孩肖滋宏和14 歲的男孩肖子田。他們?cè)缫央x開了山村,在淄博市淄川區(qū)城里工作并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6 個(gè)“山里的孩子”都姓肖,都住在下端士村。眼眶發(fā)濕的錢捍與這倆“大孩子”相擁,好像失散多年的孩子突然找到了。歲月的時(shí)光,帶走了青春,卻帶不走真誠(chéng)的笑容。滋宏和子田又坐在村子里的老井臺(tái)上,回憶起童年他們?cè)谝黄鹜嫠r(shí)的情景,感慨萬(wàn)千。錢捍再次按下快門,記錄了這個(gè)珍貴時(shí)刻。
100 歲老人和7 歲孩子同框的照片,放在攝影展的最后,也最溫馨。百歲老人一路走來(lái),滿目滄桑,而7 歲孩子的人生之路才剛剛開啟,90 多年后,這7 歲娃也100 歲了。峨莊那時(shí)會(huì)是什么樣子呢?引人生出無(wú)限遐想。
意大利當(dāng)代量子物理學(xué)家卡洛·羅韋利說(shuō):“我們發(fā)現(xiàn),物質(zhì)實(shí)相的核心不是粒子,而是關(guān)系。每個(gè)物體的定義都來(lái)自與其他物體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當(dāng)它沒有互動(dòng)時(shí),它就不存在。一個(gè)物體就是它影響周圍其他物體的方式的集合——一個(gè)物體的存在是由其他物體映射出來(lái)的。”
誠(chéng)如新華社記者李錦所言:“從深層次看,錢捍峨莊攝影是對(duì)四種關(guān)系的揭示。在這些照片里看到是人與自然環(huán)境,人與社會(huì),人與生活,人與人。錢捍選擇峨莊,是因?yàn)檫@里是封閉的深山,在這種環(huán)境里,他找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huì)、人與生活的聯(lián)系,最終在人與人關(guān)系中定位。我覺得錢捍的功能,重在工業(yè)化中期中國(guó)鄉(xiāng)村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認(rèn)識(shí),這種文化的認(rèn)識(shí)功能是強(qiáng)大的,有沖擊力的。”
錢捍與峨莊在互動(dòng)。峨,“我”之“山”也,有“我”有“山”才存在。進(jìn)一步說(shuō),互動(dòng)起來(lái)才存在,影響周圍才存在,綻放出光芒才存在。
40 年,錢捍記錄的姿勢(shì)不變,初心不改;40 年,錢捍發(fā)力的狀態(tài)不變,枕戈待旦;40 年,錢捍奔跑的激情不變,使命在肩。目的無(wú)他,拒絕遺忘!
我反思自己,我也是記者,我怎么就沒持續(xù)關(guān)注一個(gè)小村,不用30 年,3 年也行啊!我總是在掘淺井,淺嘗輒止,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到頭來(lái)兩手空空。而錢捍呢,一直在揮汗如雨地打深井,不打出水來(lái)不罷休。他有自己的根據(jù)地,他在根據(jù)地里縱橫捭闔,呼風(fēng)喚雨。跟錢捍比,我就是新聞界的“流寇”,后悔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