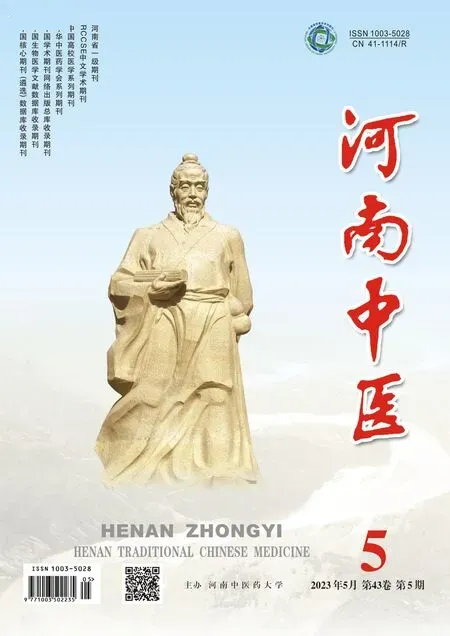《傷寒論》“傳經”概念的演變與探討*
陳媛,黃作陣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
《傷寒論》中與“傳經”相關的條文主要集中在原文第4條、第5條與第8條。原文第4條言:“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原文第5條言:“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其中的“不傳”又有“傳經”意味,第8條則提出“傳經”的周期:“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從以上條文可知,在《傷寒論》時代,“傳經”這一概念始終圍繞單一維度,將“六經”的傳變以時間聯系,這種說法最初源于《素問·熱論》。隨著后世醫家對“傳經”“六經”概念的不斷解讀與創新,“傳經”一詞的釋義早已從“日傳一經”“七日復傳”的舊窠中脫離,從以文本為主的傳統路徑逐漸趨向以客觀實際為主的個人闡釋,而個人闡釋又依托于《傷寒論》的臨床研究與合乎病情發展的現實邏輯。
至近代,有關“傳經”的概念演變進程明顯加快,并逐漸呈現多元化釋義思路。其演變進程主要包括:對“日傳一經”的質疑與否定、“六經”傳變方式的延伸、“傳經”一詞的拆解與詮釋。筆者通過梳理近現代有關“傳經”的概念,將這些概念總結成相關議題,以期探討“傳經”一詞的演變趨勢與研究方向。
1 “日傳一經”的演變與發展
1.1 理論發源“日傳一經”的理論依據源于《素問·熱論》:“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素問·熱論》言:“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其兩感于寒而病者”,《素問·刺熱》言:“肺熱病也,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可知《黃帝內經》“傳經”之“經”未超出“經絡”“經脈”范疇,對于“傳經”日期以及是否傳經的認識都有著明確的時間劃分。晉代王叔和在其編次的《傷寒論·傷寒例》中沿用《黃帝內經》中“兩感于寒”的“傳經”說法,對后世影響頗深,近代學者章太炎認為:“昔人謂少陰病必由太陽傳入者,則由叔和序例日傳一經之說誤之”[1]。
1.2 概念形成成無己在《注解傷寒論》中繼承《黃帝內經》“傳經”的概念,首次提出“日傳一經,七日復傳”的說法。成無己認為,傷寒自一日至六日便已傳遍三陰三陽,至七日當愈,“若七日不愈,則太陽之邪再傳陽明,針足陽明為迎而奪之,使經不傳則愈。”[2]成無己的說法主要依據《素問·熱論》中“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這一句。自成無己首次全面注解《傷寒論》,提出“傳經”理論以來,因其學術地位高,“日傳一經,七日復傳”的外感病按六經病順序發展的理論模式,被后世諸多醫家推崇備至,甚或成為《傷寒論》研究的主要思想[3],至近代,仍有部分醫家深受清代五運六氣學說以及《黃帝內經》經絡學說的影響,對“日傳一經”這一概念進行闡發。
1.3 時間質疑至明清時期,傳統“日傳一經”的說法遭到了愈來愈多醫家的質疑。針對《傷寒論》“傳經”中的“一日”“二日”“三日”,方有執提出“日為次序”的說法,認為這些時間代表病程次序:“猶言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之次序也,大要譬如計程,如此立個前程的期式約摸耳,非計日以限病之謂。”[4]方有執此說已現后世六經傳變“病程說”之雛形;柯韻伯則指出以上時間“是言見癥之期,非傳經之日也。”[5]并認為仲景未有此說:“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5]吳坤安在《傷寒指掌》中亦云:“傷寒斷無日傳一經之理,仲景既無明文,其說始于誤解經義。”認為以上時間“有淺深先后之次序,非謂傳經之日期也。”[6]。自此,醫家們漸漸從臨床經驗中脫離盲目追求文本與故訓,不再機械地將《黃帝內經》家言與仲景之說附會在一起,而是以個人體悟的方式對“日傳一經”作出新的解讀,而解讀方式大抵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否定“日傳一經”的說法,另立新說;另一類則在未全然否定《黃帝內經》說法的同時,針對“日傳一經”的日期與方式做出多元化的闡釋,這些闡釋在近代尤為突出。
1.4 個人闡釋近現代,“日傳一經”的原有概念已被多數醫家摒棄,甚至不再以傳經的具體時間作為研究的重點,而是趨于從科學的角度探討“傳經”相關概念的合理性。當然,其中不乏仍受之前舊注影響者,總而言之,這一時期對此概念的探討呈現出多元性。
1.4.1 章太炎“經為期候”說章太炎先生以“經為期候”的說法否定了“日傳一經”。太炎先生認為,太陽病的“傳變”“過經”“是傷寒非皆傳遍六經,三陰病不必自三陽傳致,更無一日傳一經之說也[1]。又曰:“然人之病也,客邪自有淺深,形體亦各有強弱,或不待一經而愈,或過經仍不愈,或不待一經而傳,或始終未嘗傳。其以七日為一經者,特略說大候,以示別與舊義焉爾”[1]。
太炎先生認為“日傳一經”的說法與實際不符,且《傷寒論》之“傳經”別有他義。其將“傳經”之“經”釋為“期候”,而非其“形質”:“《傷寒論》所以分六部者,各有所系,名目次第,雖襲《黃帝內經》,固非以經脈區分也……柯琴《論翼》謂:‘經謂徑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經字,不煩改義。若其云過經不解,使經不傳,欲作再經者,此以六日、七日為一經,猶女子月事以一月為經,乃自其期候言,非自其形質言矣。”太炎先生這種理論與近代“六經即六病”的普遍認知關聯,完全脫離了“日傳一經”的概念束縛,將“傳經”的概念向疾病病程的演變這一方向引導,又對“傳經”之“經”的概念進行了新的闡釋,擴大了“傳經”這一概念的含義。
1.4.2 曹穎甫“一日為一候”說曹穎甫受《黃帝內經》以及清代張志聰運氣學說影響,堅持《傷寒論》之“日傳一經”的說法與《素問》一致:“此本《黃帝內經》文宇,仲師祖述《黃帝內經》,豈有推翻前人之理。”“自來注家不知一日為一候,遂致相沿偽謬……夫六經營衛晝夜流通,豈有即病傷寒一日專主一經之理?”[7]又言:“傷寒七日為一候,在《黃帝內經》即名一候為一日,本論中間亦有沿襲之者,如一日、二日、三日之日,皆以一候言之;六日愈,七日愈之日,即以一日言之,是不可以不辨也。”[7]按曹穎甫所言,《傷寒論》“一日一經”與《黃帝內經》相合,但《黃帝內經》之“一日”則為“一候”,由此可以推知,“一日一經”為“一候一經”。
曹穎甫所言“日候說”的理論依據在《素問·六節臟象論》對“氣”的論述中已有提及:“岐伯曰:五日為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據郭靄春先生注釋,這里的“候”指氣候[8]。《逸周書·時訓解》言:“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此處“一候”即代表五日。可見,曹穎甫對“日傳一經”的說法并未遵循上文所述的“五日為一候”,而是進行了新的闡釋。首先,曹穎甫根據《傷寒論》第8條的“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推算出本條的“日傳一經”之“一日”,乃是第8條的“七日”:“傷寒發于太陽以七日為一候,猶黃疸病發于太陰以六日為一候也”。
就曹穎甫而言,“一日為一候”是核心觀點,但“一候”究竟代表幾日,卻可靈活看待,曹穎甫結合《黃帝內經》,據《傷寒論》“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反推出“一候”為“七日”,筆者認為此說法未免牽強,尚且存疑,但曹穎甫在《黃帝內經》時代的語境下針對“日傳一經”這一概念進行創造性闡發,在當時可謂獨樹一幟。曹穎甫的“日候說”理論盡管無從得知是否源自《黃帝內經》,但其深受“五運六氣”觀念影響,在釋義方法中很難擺脫《黃帝內經》“運氣”思想的桎梏。
1.4.3 時逸人“傳經之謬”說時逸人注解《傷寒論》時,不但否定了“日傳一經”的說法,還否定了“傳經”這一概念:“《黃帝內經》有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病受之等語。《中藏經》有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之說,后世死于句下之醫者,疑傷寒之病,由太陽,至厥陰,一日遞傳一經,又創有氣傳經傳等說,揆之病證實際,固成夢囈。”[9]時逸人的主張,與太炎先生的“經為期候”相類,卻又結合了“惟病是視,見證治證”的臨床思想。其將“六經病”的基本特點與西醫的病理表現結合,認為臨床表現中的“六經病”傳變與日期并無具體聯系:“以太陽證為起點,或傳少陽或傳陽明,既傳之后,次無再傳之理。故傷寒原文中,于少陽、陽明二經,有十三日、十五日等字者,可知少陽病及陽明病,均為固定之名詞。”[9]時逸人這種將“傳經”概念整體否定的觀念,代表著相當一部分醫家,這些觀念對現代“傳經”的研究,有一定影響。
至于“日傳一經”之“日”的意義,時逸人雖無針對性研究,但其結合西醫病理生理知識,將“六經”等同六種疾病表現,并且認為“三五日”“十三日”“十五日”等字目是疾病發展以及出現兼證的病程記錄,與“傳經”無關,更否認了“傳經”這一說法:“太陰病,為吐瀉腹痛之腸胃病。因吐瀉太過,波及心臟衰弱者,是謂病證中之續發病,不得謂之傳入少陰。因心臟衰弱,續發膈膜炎證,亦為病證中之續發病,不得謂之傳入厥陰。明乎此,則傳經之謬,不攻自破。”[9]嶺南醫家陳伯壇認為:“《傷寒》無所謂傳經……要皆因一‘傳’字自難自解,謂邪氣傳固臆說,安有六日六病其經?謂正氣傳尤臆說,安有六日六主其氣?”[10]但時逸人過于追求中醫與西醫的統一,以西醫的視角全然否定“傳經”概念,又失于偏頗。
1.5 現代學者的邏輯思辨毫無疑問,現代學者對于“日傳一經,七日復傳”這種說法基本持否定態度,探討時多從這一概念流傳背后的緣由進行思辨。宋尚晉、阮亦認為“日傳一經”并不符合臨床疾病發展規律,成無己是誤將仲景之“傳”“行”“經”“作”“再經”“過經”“到后經”“復過一經”等言六經病間相互轉化規律的詞語,誤解成了“六經經絡”之“經”,錯誤地提出了“日傳一經,七日復傳”的“傳經”理論[3]。
李心機否定了“日傳一經”的說法,認為太陽病是一個自然過程,并進一步解釋《傷寒論》中以“六日、七日為一經”的說法:“自成無己注云‘六日傳遍,三陰三陽之氣皆和’以來,日傳一經之說盛行,以致謬誤流傳。關于‘經’字,王樸莊《傷寒論注》有云:‘經者,常也。’若過一經未愈,則為作再經,又當以六七日為期也。”[11]李心機引用太炎先生對“傳經”之“經”的注解,對其“經為期候”說法頗為認同。至于“日傳一經”的流傳與影響,李心機認為,經過成無己的誤讀,后世注家形成了思維定式,將“傳經”之“經”誤解為“經絡”,而“三陰三陽”則自然而然是六種經絡病:“于是就有了‘六經’這個原典中并不存在的所謂‘術語’,并把《傷寒論》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經’字誤解為‘經絡’”[12]。
趙洪鈞受《素問·熱病論》影響,言:“該篇按六經循環推演,傷寒必日傳一經。若非兩感于寒,又一定要前三日在陽,三日后入陰。”“既然日傳一經不妥,又不能撇開六經循環論,便有二日、六日、七日傳經說……這種推理,受后人解釋《周易》的影響。晉人王弻解復卦卦中‘七日來復’四字說,孔穎達就此說,以為‘天之陽氣絕滅之后,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于是七日傳經竟有了自然公理依據”[13]。
“日傳一經”這一概念演變至今,早已跳出原有概念的框架,現代學者更傾向于在尊重原有文本的基礎上進行新的闡釋。王大海將“日傳一經”之“一日”解釋為“虛數詞,是不久、剛開始的意思。”與此相對,“傷寒二三日,同樣也是虛數詞,就是時間相對長一點。”[14]關于“傳經”日期,王大海又針對《傷寒論》“發于陽,七日愈。發于陰,六日愈”這一句展開探討,首先,認為陸淵雷“傷寒傳變,大多數過六七日一經”這一觀點值得采納,其后,將傷寒“傳經”之日期比作人體的“周期律”:“我們先不糾結七日、六日這一具體數字,對于人體的周期律是必須承認的。人體的生理和病理的晝夜節律、周節律、月節律、四季節律、年節律等,都是存在的。最常見就是女性的月經周期。因為有了這一認識前提,我們就不應該輕易否定這一說法”[14]。
2 “傳經” 之“傳”與“經”的相關闡釋
2.1 “傳經”之“經”
2.1.1 “經”為“經脈”“經”字本義為“織物上縱的方向上的紗或線”,與“緯”字相對,又可引申為“南北縱貫的道路”,《離騷·王逸注》言:“經,徑也”,中醫指人體內氣血運行通路的主干,常代表“經絡”“經脈”。前文中已經提及,《黃帝內經》中“傳經”之“經”為“經絡”“經脈”之義,這一解釋對后世影響最早,亦最受質疑。但有部分學者仍秉持此觀點,如針灸學家承淡安,認為“傳經”是合乎道理的:“依淡安經驗,當取頭維、足三里、內庭諸穴,可確實收效于爾傾……信乎傳經之理為不誤,即筆而出之耳。”[15]趙洪鈞在《傷寒論新解》中指出,仲景只講六經,不講十二經,六經之經,即三陰三陽非經脈之經,但在《傷寒論》的文本中仍未完全消除“經脈說”,例如第160條有“經脈動惕”之說,再如有涉及針刺之法與灸法的條文,其“經”字都應釋為“經脈”。據趙洪鈞統計,《傷寒論》中共有19個“經”字,除卻與婦人“經水”相關的“經”,其余皆代表“經脈”之“經”[13]。趙洪鈞盡管通過邏輯方法證明了“傳經”之“經”仍為“經脈”之義,但其認為,經絡學說僅為理論需要,不能應用于傷寒體系,針刺療法可以而且應該從《傷寒論》中清除。
2.1.2 “經”為“經氣”“經”為“經氣”的說法自清代起在“傳經”的概念中占據一席之地,此處“傳經”的完整意義為“六經之氣相傳”。張隱庵創“六經氣化說”,將“六氣紀日,自有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以次相紀,日數甚多[16]”視為生理常態。陳修園將“傳經”概括為“一論陰陽表里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17]。唐容川《傷寒淺注補正》言:“今醫者止守日傳一經之說,必以太陽傳入陽明,陽明傳入少陽,少陽傳入太陰等經矣。豈知經氣之傳有定至,于病氣或隨經氣而傳,或不隨經氣而傳,變動不居有如是哉。此從少陽而推廣傳經之義也”[18]。
嶺南派醫家也在“經氣相傳”的基礎上多有創新,例如陳伯壇的“陰陽經脈合化說”:“一面懸忖邪氣之必傳,一面僥幸邪氣不盡傳,《傷寒論》直作傳經說……經氣本行而非動,脈氣動之則且行且動;脈氣本動而未行,經氣行之則且動且行。”陳伯壇認為,脈象不僅能判斷疾病的傳變,還可以判斷臟腑陰陽,“與其謂之病在經,不如謂之病在脈”,并提出“陰陽合脈”的觀點:“脈氣是陰陽之太素,經血合脈兩而化,陰陽合脈一而神”[10]。
2.1.3 “經”為“經界”清代柯琴在《傷寒論翼》中提出“經為經界”的說法。“經界”有“土地、疆域分界之義”,《孟子·滕文公上》言:“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柯琴認為,“傳經”是由一經地面的邪氣轉移到另一地面的結果,并以大量比喻手法解釋“經界”之義:“請以地理喻六經猶列國也,腰以上為三陽地面,三陽主外而本乎里,心者三陽夾界之地也……更以兵法喻,兵法之要,在明地形,必先明六經之路才知賊寇所從來……太陽是大路,少陽是僻路,陽明是直路,太陰近路也,少陰后路也,厥陰邪路也。”[19]從柯琴的論說來看,其筆下之“經界”有兩重含義,一是“地面”,一是“路徑”,二者構成了“傳經”的整個過程,有確定方位的屬性。“經為經界”的說法在近現代并不算主流,但由于柯琴對《傷寒論》見解獨到,其注常被近代醫家引用,章太炎更是在對“經”的解釋中引柯琴“經為經界(章太炎引用時作‘徑界’)”的說法,并將之意義從空間變化轉變到時間的衡度上。
2.1.4 “經”為“期限”“過程”黃西平認為,“傳”與“經”二字,前者為“變化”,后者為“期限”,并非“傳經”之意[20]。以“經”概“期”的釋義,反映著《傷寒論》傳統概念逐漸脫離以文本為主體,為求臨床實證探尋新解趨勢。李克紹《傷寒論語釋》中便有“經為過程”的說法:“傷寒從發病之日起,邪正不斷斗爭,陰陽氣血在不斷變化。觀察其變化的結果,是以六日為一過程,也叫經。[21]”基于章太炎“經為期候”的說法,李心機對“傳經”概念進一步解釋:“所謂‘傳經’不是言邪氣在經絡間相傳,而是言病勢的自然發展變化,是指從發病早期過程,經過癥狀期,而至轉歸期的過程……原文第8條‘以行其經盡故’此“經”字指有規律的時間或過程。在本論中,這個‘經’字是指六天為一過程,病過七日不愈,為‘欲作再經’,病過十三日不愈為‘復過一經’。[11]”就現代釋義趨勢來看,“經”作疾病發展的“過程”“期候”,有一定規律可循,這種趨勢也反映了一種詮釋學現象,即“文本的理解和解釋與文本的應用不再是先后相繼的兩個階段,而是互不可分的統一過程”[22],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傳經”一詞進行批判性關聯。
2.2 “傳經”之“傳”的方式與規律
2.2.1 繼承《黃帝內經》的“以傳達變”“傳經”作為復合詞,屬于中醫術語,《漢語大詞典》定義為:中醫上指傷寒病證沒能及時發散出來,循六經的次序而感傳。北宋醫家龐安時根據《素問》“六日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的說法提出,“六經”傳變應為“表里傳”:“是表里次第傳,不必兩感,亦有至六日傳變五臟六腑者也。”[23]龐安時的這種觀點,朱肱《類證活人書》中仍有沿用。金元醫家李東垣則根據太陽分傳其他五經的情況將“傳經”方式分別定義為“循經傳”“越經傳”“表里傳”“誤下傳”以及“循經得度傳”。明代陶節庵則將“傳經”方式細分為“不罷再傳”“間經而傳”“傳二三經而止”“始終只在一經”以及“越經而傳”等,陶節庵的這種將各種“傳經”方式考慮在內的分類方法,被明清不少醫家引用,如孫一奎,李中梓等。以上醫家對于“傳經”順序的解讀,仍然受《黃帝內經》“傳經”說法的影響,即便有所發揮,卻始終停留在“次第傳經”“單一線性”或“多一線性”的思維邏輯中。
“傳經”方式的闡釋往往伴隨著對“傳”之性質的探討。張隱庵認為,《傷寒論》中的“傳經”不同于“六氣行經”,“傳”是帶有病理性質的說法:“須知本論中紀日者,言正氣也,傳經者,言病氣也。正氣之行,每日相移,邪病之傳,一傳便止”[16]。清代柯琴則據《黃帝內經》“人傷于寒,而傳為熱”的說法將“傳經”之“傳”,定義為“太陽之氣”:“太陽之氣,生熱而傳于表。即發于陽者傳七日之謂,非太陽與陽明、少陽經絡相傳之謂也。”[5]他認為“按本論傳字之義,各各不同,必牽強為傳經則謬”,將“傳經”方式以“傳”與“不傳”為基準歸納為“寒傳本經”與“熱傳本經”:“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是指熱傳本經,不是傳陽明之經絡。陽明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是指寒傳本經,不是傳少陽之經絡[19]”。
近現代,受科學觀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影響,對于“傳經”方式的探討已經不再以《黃帝內經》的文本為主,而是更加注重臨床實際。以中西匯通的臨床家張錫純認為,《傷寒論》六經之次序,皆以《黃帝內經》為法:“而未明言其日傳一經,至愚生平臨證之實驗,見有傷寒至旬日,病猶在太陽之府者,至他經相傳之日期,亦無一定,蓋《黃帝內經》言其常,而病情之變化恒有出于常例之外者,至傳至某經,即現某經之病狀,此又不盡然,推原其所以然之故,且加以生平臨證之實驗,知傳至某經即現某經之病狀者,多系因其經先有內傷也。若無內傷則傳至某經恒有不即現某經之病時,此在臨證者細心體察耳”[24]。張錫純結合臨床,將“傳經”病理現象的發生歸結于是否有“內傷”存在。
2.2.2 “傳經”順序的質疑惲鐵樵基于“六經”即“六病”的理論基礎,認為探討“傳經”的順序沒有意義。惲鐵樵認為,《傷寒論》中“六經”的次序,源于《素問·熱論》,但《傷寒論》中“三陰三陽”,卻并非臟腑經絡相配之“六經”,且此處的“三陰三陽”已成為“病”的修飾詞,若論疾病,則既往“傳變”次序無意義:“本文三陰三陽次序,原于《黃帝內經》‘熱論’,非敢有錯,蓋義不得不然,惟至論病之傳變,則固不得拘編次之先后也。”[25]持此類似觀點者,還有余無言,余無言認為,“傳經”在詞性上沿襲《黃帝內經》,但詞義上針對的是臟腑病變:“病邪之中于人體,傳于內臟,漫無常軌,六經之說,實可有可無。”[26]由此可知,當“六經”為“六病”這一說法廣泛為人接受時,“傳經”順序的探討亦出現了多種走向。
陸淵雷則以“六種證候群”的觀點對“傳經”順序提出質疑:“仲景之論六經,沿熱論之名,而不襲其實故也。熱論三陽之次,太陽、陽明、少陽,謂太陽傳陽明,陽明傳少陽也……然仲景之少陽,來自太陽,傳諸陽明,故柴胡證不可次于陽明之后,即不可列于少陽篇矣。熱論之三陽,皆仲景之太陽,故皆可發汗。仲景之少陽,則為柴胡證,不可發汗。”[27]陸淵雷認為“少陽”不應在“陽明”之后,并以“不可發汗”將《素問·熱論》之“三陽”與《傷寒論》“三陽”作出區分。
陸淵雷、惲鐵樵二人將“六經”視為各自獨立的疾病系統,并不具有線性聯系,因此“傳經”次序便有了多種可能。現代學者鄭述銘[28]認為,六經各子系統之間的聯系是非線性的,它們有著復雜的立體網絡式結構,并從“有違臨床”“附會《黃帝內經》”“背離開闔樞”三個方面糾正了“三陽”的傳變順序,認為《傷寒論》中“三陽”傳變應當為“太陽-少陽-陽明”這一順序,此觀點與陸淵雷相同。蘭鵬飛等[29]則就鄭述銘的論述專作一文,從“祝氏經脈正反雙向運行理論”(此祝氏為祝華英),從三維立體的空間認識出發,認為《傷寒論》在六經病發病次序上與《黃帝內經》如出一轍,并不是對《黃帝內經》的附會,只是人們以線性的思維定式來機械考慮疾病轉化趨勢所形成的誤解。
2.2.3 “經病合化,既傳則變”的趨勢認同近現代醫家將“六經”釋為“六病”,又逐漸合化為“六經病”,認同人體臟腑經絡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將“傳經”概念與“傳變”規律放在同一命題中進行探討,已成為切合實際又能回溯經典的必要趨勢。《傷寒學》七版教材對“傳變”一詞的定義為:“傳,是指病情循著一定的趨向發展;變,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不循一般規律而發生性質的改變,但傳與變常并稱。”[30]據教材說法,“六經”屬于生理性概念,但“傳經”所涉及的“六經病”以及“傳變”,則為病理性概念。
現代學者劉素平將“傳經”之“傳”釋為“病情循著一定的趨向發展”,將《傷寒論》六經傳變概括為表里傳和循經傳,其中循經傳之“六經”則默認為“六病”[31]。孫源梓等[32]以感冒為例,認為“傳經”是客觀存在的,原因在于《傷寒論》中有大量的條文直接或間接反映傳經規律,“傳經”表示疾病有向某一方向轉變的趨勢,反映了急性外感疾病由淺入深、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杜青雄[33]認為,六經證的傳變不是空間距離的變化,而是表述人體功能狀態在時間上質的變化,“傳變”是“傳經”的前提,且“傳經”之“經”仍代表時間及變化過程。
2.2.4 “傳經”與“轉屬”的同異表述基于“既傳則變”的思路,從另一角度來看,“傳經”一詞概念已經脫離原本的詞義范疇,趨向經驗主義化的表達。現代學者李克紹在《傷寒解惑論》“傷寒傳經的實質和傷寒日數的臨床意義”一節中,弱化了“傳經”一詞的概念性,而是綜合《傷寒論》原文外感病的癥狀變化,將“傳經”及相關概念“轉屬”“轉入”納入外感病發展變化的結果:“這些變化的結果,除了自愈者外,其余的在《傷寒論》中,有的叫作‘傳’。有的叫作‘轉屬’或‘傳入’。后世注家所謂‘傳經’,就是以此為根據,又加以主觀想象和神秘化而造出來的。”[34]李克紹認為,“傳”與“轉屬”雖然皆可代表“傳經”的演變過程,但二者有本質區別——“傳”為某一經病之病程變化:“由前驅期進入出現各經的癥狀期,這就叫‘傳’。”“轉屬”則為一經至另一經之病位變化:“或因誤治,或是自然演變,由這一經病變成另一經病,是常有的。但是這不叫‘傳’,而叫‘轉屬’或‘傳入’。”[34]值得注意的是,李克紹先生在解讀“傳經”一詞時,以“臆說”為由,將臨床詮釋置于文本探討之上,重點分析“傳”這一字的意義,打破了原有文本釋義的詮釋思路。
為了進一步說明“傳經”與“轉屬”的關系,梁華龍將“傳經”方式以概念的形式區分,以《傷寒論》原文為標準,將“傳經”方式分為“傳”與“轉屬”“轉系”兩類:其中原文第4條、第5條、第8條為“傳”的描述;第181條、第185條、第188條、第244條等為“轉屬”的描述。梁華龍[35]認為,《傷寒論》對于傳經的表述,有“傳”和“轉”兩種不同方式:“所謂‘傳’即是未經治療或叫‘失治’而引起的傳經;所謂‘轉’,包括轉屬、轉系,是由于誤治而引起的傳經。”由上述可知,“傳”字之于“傳經”的表達,在“傳經”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中,具有一定的針對性,無論是“傳經”抑或是“轉屬”,其所對應的“經”都不再是近代以前的傳統釋義。
3 結論
近代醫家對“日傳一經”的認識,建立在對“六經”概念的重組以及對“傳經”一詞的質疑基礎上,現代學者又能從不同方向進行更為深層的邏輯思辨。從“日傳一經”與“傳經”一詞的概念流變來看,現代對于舊有概念的闡釋,不同于近代醫家“激流勇進”般的質疑與否定,而是在嘗試解構文本的同時,賦予這些舊有概念新生的意義,換言之,“傳經”一詞演變至今,已在不斷更新的闡釋中形成了多元概念系統,使之合乎時代價值觀與臨床需求。當“傳經”的概念跳出“時間”“空間”“順序”以及“規律”的限制,在文獻與臨床的較量中被辨證看待時,便有了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