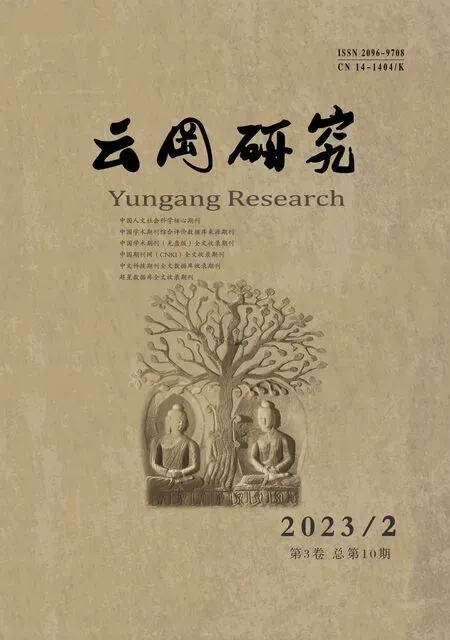山西北朝佛教造像題記書法風格特征探析
吳利國,楊 州
(山西大同大學美術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一、北魏平城時期造像題記書風特征
從天興元年(398年)道武帝建都平城開始,到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期間為北魏平城時期,這個時期造像題記數量不多,以大同云岡石窟造像題記為代表,著名的有《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圖1)和《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圖2)等。平城時期為魏碑的發源時期,此時期造像題記無不顯示出平城魏碑的風貌特征,成為平城魏碑書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1 五十四人造像題記
(一)楷中參有隸書筆意
楷隸相參的書寫特征是平城魏碑的主要特征之一,諸多專家學者對此已有論述,從對《嘎仙洞祝文刻石》書寫特征的評語中可見一斑:“從書法上說,這是魏碑;從字體上說,這叫隸字。”[1](P161)“字體古拙,介乎隸楷之間,似由隸到楷的過渡。”[2]“書體遒勁,猶存隸風。”[3]“隸意猶重,古樸蒼然,清晰可辨。”[4]“隸意濃重,但卻很少波磔”,[5](P22)殷憲先生則提出了“‘手寫體草隸+銘刻體隸楷’,是代魏早期書法的基本構成”[6](P28)的觀點。諸家之言無不強調了平城魏碑的隸書筆意。而云岡石窟《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和《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正體現出平城魏碑所具有隸書筆意的書寫特征。
對于《五十四人造像題記》中的隸書筆意,書家學者亦多有闡述。董其高先生指出《五十四人造像題記》“與《爨寶子碑》有點相似卻又隸少魏多”。[7]殷憲先生則指出:“此刻書法高古質樸,墨酣筆凝,溫文敦厚。基本面目是楷書而存隸意,結字方而略長,寬綽而外拓,略呈左高右低之勢。”[5](P161)“結字和用筆都明顯帶著其母體隸書的波磔痕跡,集中體現了早期魏碑的鮮明特點。”[6](P400)姜壽田先生則指出《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尚存隸意,作為平城魏碑已“達到相對成熟的境地。”[8]《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同樣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殷憲先生評價為:“隸意猶存,長橫收筆的方挑、折筆處的圓轉……而無挑,是隸則,也是平城期書刻風格……因隸筆時現而更見稚拙……亦隸亦楷,非隸非楷,都為這件書刻平添了幾分奇逸之致。”[9]
平城魏碑的風格形成源于西晉、西涼及南朝書寫樣式等因素的匯集和相互間的交融。由于去西晉未遠,平城碑刻中多有隸書筆意實為書法發展之自然規律,正因如此,平城魏碑均呈現出古拙質樸、圓厚勁健的風格特征。此風貌在《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和《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中表現尤為突出。另外,兩題記為民間書法范疇,與之官方碑刻書風相比具有明顯的滯后性。①當下學者往往對平城魏碑中官方與民間書法進行趨同對待,混淆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如比《五十四人造像題記》早23年的皇家書跡《皇帝南巡之頌》,已具備高超的筆畫表現能力和字體結構處理能力,筆畫精湛,整篇行列分明,具有井然有序的秩序美。這些因素在《五十四人造像題記》中卻并不明顯。書于太和十二年(488年)的《暉福寺碑》,在整體風格的新妍方面、筆畫表現的精湛方面都優于《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官方書手往往能接觸到最新、最流行的書寫方法,更有條件接觸不同地域和政權的書寫風格,正因為此,官方書寫風格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而民間書手多繼承固定的寫法,書寫方式很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干擾,因此能保持一貫的書寫風貌,導致民間書寫比之官方更古樸、更傳統,從而更多的保留了隸書書寫的筆意特征。
(二)“平畫寬結”的結體特征
關于“平畫寬結”,沙孟海先生對此有精辟的論證:“北碑結體大致可分‘斜劃緊結’與‘平畫寬結’兩個類型,過去也少人注意。《張猛龍》《根法師》、龍門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剛經》《唐邕寫經頌》是后者的代表。后者是繼承隸法,保留隸意。”[10](P114)沙先生提出了北魏書法結體的兩個陣營,可謂極有見地。對于“平畫寬結”形成原因,他認為是存有隸書筆意,此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他將《吊比干文》《泰山金剛經》《唐邕寫經頌》視為“平畫寬結”的代表,忽略了北魏建都平城時期這將近一百年時間所出現的碑刻,可見他對平城時期碑刻尚沒有足夠的了解和認識。
其實,真正代表著北魏時期“平畫寬結”結體特征的書法,非平城魏碑莫屬。
《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和《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即為典型的“平畫寬結”結體特征。二題記橫畫多平直,以取隸書橫“平”之勢,無明顯粗細變化。二者結體寬博,雖結構有長短高矮之變化、局部有筆畫疏密處理之變化,但主體結構均受隸書結構的影響,筆畫空間相對勻稱,筆畫不做過多的疏密收放處理,而強調筆畫整體之美,從而更加充分地體現出寬博開張、雄強凝重之藝術風貌。
(三)古拙質樸、圓厚勁健的書風
由于《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和《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具有濃厚隸書筆意特征,因此二題記更具古意,呈現出古拙質樸的氣息風貌。趙孟頫自畫卷跋語說:“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孰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11](P396)趙之“古意”雖指作畫,然與書法并無二致,對于中國書畫藝術來說,習“古”當視為取法乎上。饒宗頤先生對此說到:“學書歷程,須由上而下。不從先秦、漢、魏植基,則莫由渾厚。所謂‘水之積也不厚,則扶大舟也無力’。二王、二爨,可相資為用,入手最宜。若從唐人起步,則始終如矮人觀場矣。”[12](P55)饒先生所言極是,學習書法當以篆隸為根基,方得正脈,而篆隸即為書法的“古意”。《五十四人造像題記》和《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乃平城魏碑,加之為民間書手所為,因此更具古拙質樸之美,此點當是北魏龍門造像題記及后期隋唐造題記所無法企及的。
由于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因此二題記呈現出圓厚勁健的書風。殷憲先生論述《五十四人題記》到:“此刻書法高古質樸,墨酣筆凝,溫文敦厚……用筆以圓筆為主,偶然雜以方筆。”[5](P161)此題書寫繁密厚重,具有泰山壓頂的視覺效果。筆畫不做過多收放處理,強調筆畫之間的遒勁緊密,加之筆畫厚重古樸,呈現出大巧若拙的藝術效果。筆畫雖有隸書筆意,但已是典型的楷書特征。其厚重古拙、勁健雄強的風格與北魏統治者鮮卑拓跋的力量與彪悍相一致。《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晚于《五十四人題記》6年,較《五十四人題記》雖多了些許“奇逸”的姿態,但由于隸意猶存,加之“更具有民間書跡的特征,其面貌似《五十四人題記》而粗率過之,因隸筆時現而更見稚拙。”[9]因此,《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依舊具備圓厚勁健之風貌特征。
《比丘尼惠定題記》中有多個字的撇為末端出鉤的寫法,此為隸書的筆意特征,說明在晚于《五十四人題記》6年后,隸書筆意依然在民間書寫中流傳,也再次說明了民間書寫的滯后性。殷憲先生評價《比丘尼惠定題記》“隸意猶存。長橫收筆的方挑、折筆處的圓轉和‘歲’‘戒’‘咸’等‘戈’法的斜出而無挑,是隸則,也是平城時期書刻風格。”[5](P165)其實,云岡石窟造像題記普遍具有平城魏碑風格,是平城魏碑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比丘尼惠定題記》的筆畫起筆處多有筆鋒頓筆的現象,有別于《五十四人題記》的裹鋒起筆,說明此時民間書手對于筆畫的表現已經開始趨于豐富性和多樣性。此題記在結字及筆畫表現生動活潑的同時,又能做到筆畫勁健硬朗,活潑而又不失沉重,是非常難得的。
可見,平城時期云岡石窟造像題記具有古拙、勁健、質樸及渾厚的書法風格。題記有濃厚的隸書筆意。與同時期的官方書跡相比,題記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及古樸性。明顯的隸書筆意也說明,民間書寫雖然活潑生動,各具特征,但依然沒有擺脫隸書筆意,古拙氣息依然濃重。平城時期云岡石窟造像題記等民間書法與官方書法一起,構成了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體系。
二、北魏洛陽時期造像題記書風特征
進入北魏洛陽時期,山西北朝佛教造像題記不再是云岡石窟一枝獨秀,而是多點開花,爭奇斗艷。在山西多個地區都發現洛陽時期佛教造像題記,其類別有石窟造像題記、獨立造像碑題記及青銅造像題記等,可謂蔚為大觀,異彩紛呈。其中,石窟造像題記有大同云岡石窟造像題記、陽泉市盂縣石佛山摩崖造像題記、陽泉市盂縣千佛寺摩崖造像題記、晉中市壽陽縣陽摩山摩崖題記、長治市長治縣羊頭山造像題記、晉城市沁水柳木巖摩崖造像題記、杜村紅泥溝摩崖造像題記、安澤摩崖造像題記等。造像碑題記有晉城高平市建寧鄉千佛造像碑題記、臨汾市襄汾縣北魏群體造像碑、臨汾堯都區開明主梁道造像碑、晉中市左權縣北魏造像碑、長治市黎城縣造像碑等。金銅造像有太和十九年金銅造像等。
(一)延續平城初期書風特征
此類造像題記并未受到遷都后洛陽魏碑書風的影響,也未出現新時代趨于精致的書寫樣式,而是依舊延續著北魏平城初期古拙質樸的民間書風。這類題記書寫依然殘留有明顯的隸書筆意,且結字寬博、氣象恢弘,筆畫平直勁挺,其風格似乎與新時代的書風格格不入。
刻于景明元年的云岡石窟《玄事凝寂造像題記》(圖3)即為此類風格。題記字體結構開張,筆畫平直勁健,有濃厚的隸書筆意。如“父”字,撇捺開張,撇的末端彎曲出鋒,具有明顯的八分書筆意。“三”字最后一長橫的末端翻筆出鋒,隸書筆意明顯。此題記中的個別筆畫表現雖趨于精致,但整體氣象依然是平城初期書法風格。

圖3 玄事凝寂造像題記
山西博物館藏的《王黃羅等人造像碑》(圖4),其題記書法風格同樣顯示出濃濃的平城初期書風樣式。此題記八分筆意明顯,撇捺多做左右開張處理,字的結構多寬扁取勢,與隸書頗為相似。筆畫普遍以橫平豎直處理,加之筆畫遒勁緊密,空間勻稱而又中宮疏朗,造成了強烈的塊面感,從而增強了字體的重量和整體性。

圖4 王黃羅等人造像碑題記(局部)
晉城高平市建寧鄉千佛造像碑(圖5),題記為典型的平城書寫風格,有明顯的隸書筆意,結體寬博厚重,橫畫伸展,筆畫空間勻稱,一派古拙質樸氣息撲面而來。進入洛陽時期后,造像題記的風格較之平城時期已有明顯的變化,具有隸書筆意且筆畫平直開張的平城初期書風雖然偶有出現,但已非主流。然而,這類風格并沒有因為遷都后新書風的迅速崛起而消亡,它始終伴隨著新書風的發展而延續。現存龍門石窟造像題記中,此類風格依然存在。對于民間書手來說,新的書寫樣式并非得到所有書寫者的肯定和仿效,與此相反,傳統的書寫風格樣式所具有的親切感使得一部分民間書手依然熱衷以往熟悉固有的書寫傳統,由此平城初期的書寫樣式得以延續。

圖5 千佛造像碑題記(局部)
(二)“斜畫緊結”結體特征的新書風
此類書風代表著山西洛陽時期佛教造像題記的風格樣式,山西洛陽時期的造像題記數量以此類書寫風格為最,這類造像題記分布范圍廣,具有普遍性的特點。
此類造像題記書法風格與平城時期具有明顯差別,平城時期具有明顯隸書筆意的書寫特征在此類造像題記中已很難找到,平城時期體勢寬博、橫畫平直的結字方式在此類風格中幾乎蕩然無存。最為主要的變化莫過于“平畫寬結”向“斜畫緊結”的轉變。沙孟海先生將《張猛龍》《根法師》、龍門各造像視為“斜劃緊結”的代表。[10](P114)并將“斜畫緊結”形成的原因視為“用右手執筆,自然形成。”[10](P114)沙孟海先生將“斜劃緊結”原因的視為用右手執筆,自然形成,未免有些牽強。隸書的書寫也是由右手執筆,為何沒有形成“斜劃緊結”的樣式,而偏偏魏碑出現?這顯然不合乎道理。“斜劃緊結”是“平畫寬結”后的必然趨勢,是書法發展的自然規律,與左手右手執筆毫無關系。書法的發展規律即為由古趨妍,以魏碑為例,魏碑的發展同樣存在由隸書筆意的平城“古質魏碑”,發展成為洛陽時期乃至后來的“妍美魏碑”的過程。只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古拙和妍美偶有迂回反復的現象。
刊刻于太和十九年(495 年)的云岡石窟《吳氏造像記》(圖6),是為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云岡石窟最早的造像題記,此題記書寫風格與平城時期云岡題記風格明顯不同。整幅作品書寫井然有序,行列清晰,一改平城時期有列無行或是無行無列的章法布局。《吳氏造像記》橫畫非平直伸展而是傾斜有姿態,筆畫空間不再寬博均勻而是緊密有收放,這些特征都表現此題記的結體為典型的“斜劃緊結”。孝文帝遷都后,新的書寫方式在故都平城出現,遷都后的最早作品《吳氏造像記》無疑是這種新書風影響下的最早范例。對于這種現象,還不能肯定是外來因素影響了平城書寫,還是平城書寫在孝文帝遷都后即發生了改變,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新的書寫風格在孝文帝遷都之前便已經在平城出現。

圖6 吳氏造像題記(局部)
另外,題記的主人吳天恩官為冠軍將軍,爵封散侯,秩為從三品。是現有云岡石窟題記主人中官職最高的。從題記主人來看,《吳氏造像記》與《五十四人造像記》及《惠定造像記》不同,后兩者為典型的普通民眾,而前者卻與皇家有些許關聯,也就是說《吳氏造像記》不能看作是典型的民間所為。我們現在審視三題記的書風,《吳氏造像記》與后兩者差別明顯,風格完全不同,這其中除了時間因素的原因,是否有階層的原因呢?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在僅次于皇族爵高位重的階層中,為家族所寫的碑刻及為家族某人造像所寫的題記,其書寫者為具有高超書寫技能,且具有大致相同書風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以書寫技藝高超而受到高官望門的賞識,從而專門為其服務?答案是極有可能的。殷憲先生評價《吳氏造像記》書法寬博肅穆,藝術水準在《五十四人題記》和《惠定題記》之上,是比較中肯的。
刻于景明四年(503 年)的《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圖7),1956 年發現于20 窟前的積土中,為云岡石窟難得保持完整的一塊造像題記。關于此題記的書法特征,殷憲先生給與了極高的評價:“《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書法極佳。縱觀其以圓筆為主。寬博雄渾的書風,應與魏碑名品《鄭文公碑》相類。特點之一是圓潤沖和。此記用筆幾乎是筆筆中鋒,不似一般魏碑書體大起大落的方頭重腦。除少數點畫偶見方起外,起落之處大多破方為圓了。橫畫一改露起為藏入,鮮見刀斧棱角,迭橫多見連帶和筆斷意連的行書筆致。折筆除‘照’‘寂’等個別例子外,都取篆法,用圓轉作方折。捺畫寫得飽滿開張,起筆出鋒全是圓筆,既存隸意,又具楷則。斜提和戈挑。全無‘丑魏’方重面目,頗多鐘王沖和內擫之態。此石書法的另一個特點是寬博從容。結字方整,筆勢開張,寬厚穩健,古樸閑逸。總而言之,其書結體為方形,分而觀之,則寓方整于變化之中。”[13](P53)殷先生的評價將《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書法捧到了一個極高的層面,其中有恰當的地方,如評價此題記以圓筆為主,頗為恰當。在北魏書法體系中,方筆和圓筆是兩個路線,最初為圓筆,實為接近或采用隸書表現特征及筆意而為,這種有隸意的圓筆書風,基本涵蓋了整個平城時期的書寫。但是在遷都后,平城時期富有隸意的書風很快被打破,出現了字體欹側多姿、“斜畫緊結”的妍美書風,這時候圓筆已非處于筆畫表現的主導地位,而是出現了方圓共出,或以方筆為主的表現特征。觀此題記,即為以圓筆為主,方筆為次的筆畫表現特征,其結體亦為“斜畫緊結”的特征。

圖7 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
殷先生評此題記“筆筆中鋒”,此觀點似乎不妥。這與他評價此題記“圓筆為主”明顯自相矛盾。圓筆為主,另一層意思是方筆為輔,這也是此題記的用筆特征之一。眾所周知,圓筆以中鋒寫出,方筆需要側鋒表現,那么,此題記用筆就應該是中鋒為主,側鋒為輔,而不是先生說的“筆筆中鋒”。另外,評語中說此題記的書風“寬博雄渾”,也未免言不符實。此題記已經改變了平城時期的“平畫寬結”而轉變為“斜畫緊結”,由此失去了平城時期書法寬博厚重的風格特征。加之此造像點畫極盡扭曲擺動之能事,導致作品充滿扭捏的氣息。又點畫多尖刻寫法,特別是豎畫和捺筆的末尾以尖筆為之,又增添了尖刻輕薄之氣。因此,從結體樣式、筆畫表現、細節描刻等多方面來看,此題記與“寬博雄渾”實相差甚遠,正如其名中有“媚”字一樣,此題記實為妍媚有余,雄渾不足。至于殷先生說此題記與《鄭文公碑》相類,就更顯得過于牽強了。《鄭文公碑》無論在結體樣式還是筆畫表現亦或是細節描刻等方面,與此題記都有著極大的差異,二者完全不是一個風格的作品。如果以“寬博雄渾”來衡量,《鄭文公碑》實為當之無愧。
長治市長治縣的羊頭山造像題記(圖8),書刻于北魏洛陽時期,此題記與云岡石窟《吳氏造像題記》、《曇媚造像題記》風格頗為相似,結體為“平畫寬結”向“斜畫緊結”過度樣式,字勢動蕩,姿態各異,具有民間活潑生動書寫風格,同時亦有官方碑刻點畫嚴謹的特征。由此可見,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山西地區的書風漸趨于相似,形成了此期間山西佛教造像題記的主流書風樣式。

圖8 羊頭山造像題記(局部)
(三)巧拙相生、細勁靈動的書風
此類書風多出現于洛陽時期的中晚期,這類題記婀娜多姿,變化多端,筆畫之間多松散靈動、活潑,甚至有的題記過分強調筆畫的靈動感,從整體風格來看,已經缺少了平城時期寬博雄渾的氣象。雖然如此,此類題記終究為北魏時期書風,勁健與力量之美依舊,筆畫多細勁富有彈力,散發出有別于雄強的勁健之美感。
長治市沁源縣的《邑主王郭仁合邑者邑子六十人等敬造觀音石像題記》(圖9)、長治市沁源縣的《五號造像碑題記》即為此種風格的作品。兩題記書寫姿態萬千,筆畫細勁挺拔,雖無雄強厚重之風,亦有勁挺瘦硬之氣,同為洛陽時期造像題記中的上乘之作。

圖9 六十人等敬造觀音石像題記(局部)
綜上所述,山西北魏洛陽時期的佛教造像題記呈現出風格多樣的特征。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專為皇家服務的具有典范性、秩序性的書寫樣式隨之轉移到洛陽。由于孝文帝的漢化思想在平城時期已經形成,諸多領域受到孝文帝漢化思想的影響而發生改變,書寫便是其中一項。我們發現在平城時期晚期和洛陽時期早期,山西境內的造像題記和其他載體的書跡多呈現出風格相似的特征,這不能說與孝文帝的漢化思想無關。其結果是,平城晚期的造像題記風格已經與平城初中期大相徑庭,基本失去了平城書法寬博雄渾、古拙質樸的氣象以及“平畫寬結”的結體特征,轉變成遒媚勁健、靈動細挺為主的風格特征,以及“斜畫寬結”為主的結體特征。同時,山西北魏洛陽時期的造像題記又并非具有統一的風格特征,古拙的、質樸的平城初期書風依然存在于這個時期,與其他風格一起,共同組成了山西北魏洛陽時期佛教造像題記風格樣式大系統。
三、東西魏時期造像題記書風特征
東、西魏時期,山西佛教造像題記的書法風格與這個時期其他地區的書跡相似,多為民間書手所為。東、西魏時期,山西佛教造像題記的結體由洛陽時期的“斜畫緊結”轉變為“平畫寬結”,出現了書風的“反古”現象。劉濤先生對此有專門的論述:“東魏時期的楷書造像題記遺存頗多……東魏造像記上的楷書,書寫者多是一般書手,甚至是工匠以刀代筆,無論筆畫的方圓,或是風格的雅俗,還是刻工的精粗。結體大多也是‘寬結’。”[14](P453)“東魏時期的楷書,擯棄了北魏洛陽體長槍大戟式的雄強之勢,轉向寬綽平正的優雅,我們可以用‘平劃寬結’來概括東魏楷書的變化。東魏‘平劃寬結’的楷書是繼承北魏洛陽體楷法而來,他們把曾經是‘直流’的發揚為‘主流’,這就是他們的成績。”[14](P454)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北魏王朝覆滅后,南朝的楷書風格樣式受到擯棄,而中原古拙的隸書筆意書寫特征又開始受到青睞。“北朝后期,東魏是隸書由‘隱’而‘顯’的轉折期,也是隸書的復興時期。”[14](P456)“西魏造像記楷書,雖然有著種種的不同,可是無論書刻者承襲何家何派,字形是修長還是橫方,點畫是呈圓還是顯方,其共同的特點也比較明確,那就是橫向筆畫都已經平沓下來,結字呈橫平之勢。這一特征也存在于東魏的楷書中,想必當時北方東、西地區楷書演變的進程大體相當。”[14](P457)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雖然在遷都洛陽后執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身為游牧民族的鮮卑人,從心底里排斥漢化,因此北魏政權崩潰后,漢化政策也隨之煙消云散,文化政策思潮重新回到了原點,在書寫方面,回到了平城時期最初的風格特征上來,但時過境遷,此時已非昔日強大的北魏王朝,其書寫僅在外形方面相似于平城時期,在精神力量上早已相去甚遠。
山西已發現的東魏造像題記中,《贈代郡太守程哲造像碑題記》《比丘尼法徹造像碑題記》《比丘僧纂造釋迦多寶佛碑題記》等,都呈現出了上述東魏書法的特征。特別是《比丘僧纂造釋迦多寶佛碑題記》,書體明顯具有隸書風格特征,撇捺開張,結字扁平。而筆畫的起筆頓挫明顯,具有楷書的顯著特征,從而也驗證了,在東、西魏時期,隸書的復興對碑刻的影響,出現了以隸書書體入碑石、或以明顯有隸書筆意的楷書來書寫的現象。
四、北齊北周時期造像題記書風特征
山西境內北齊、北周時期的佛教造像題記數量頗為可觀,數量遠多于北朝其他時期,代表的作品有臨汾市安澤縣《上寨摩崖造像題記》、長治市沁源縣《大齊天保摩崖石刻題記》、晉城城區《北齊造像石題記》、陽泉市盂縣《元吉村佛坐題記》、長子縣《北齊釋迦佛立像碑題記》、臨汾市堯都區《神武皇帝寺主造像記》等等。
對于北齊時期的書風,劉濤先生有專門評論:“北齊書法的復古傾向,顯著的表征是隸書的興盛,不獨刻經好作隸書,當時許多墓志、碑刻也采用隸書書刻,尤以首都鄴城一帶的上流社會最為流行……可以說,隸書在北齊時期又恢復了銘石書的主體地位,起碼在政治中心鄴都及周邊地區已經蔚為風尚。”[14](P475)
北齊時期隸書開始興盛,其表現多為刻經大字方面,在全國各地已發現的北齊書法中,刻經是一大宗。在其他載體的北齊書跡中,有隸書,亦有隸書筆意的楷書。而山西北齊時期的造像題記多為有隸書筆意的楷書,純粹的隸書作品鳳毛麟角,此時期與平城早期的平城體書法似乎有相似之處,即都存有隸書筆意。北齊時期的書跡有隸書筆意,同樣早已經沒有了平城時期書法的博大恢弘氣象,而表現為纖弱的風貌特征。劉濤先生對此評價到:“北齊碑志隸書大多為流麗、輕柔一路,既無漢隸雄強渾厚的氣勢又無曹魏隸書的峻整之態。”[14](P475)已發現的山西北齊時期的佛教造像題記,其書法風格基本與其他地區北齊時期的書風一致。除了筆畫的孱弱和用筆的纖巧之外,亦有書寫草率、筆畫凌亂的現象。不管怎樣,山西北齊佛教造像題記所呈現的書法氣息即為流麗和孱弱,無論是書寫工穩一路還是書寫潦草一路,都沒有了雄渾博大的氣象,與平城時期和洛陽時期題記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顯。
北周時期造像題記書風大體與北齊時期相仿,不再贅述。
結語
山西北朝佛教造像題記涵蓋了北朝的北魏平城時期、北魏洛陽時期、東西魏時期以及北齊北周時期,可謂琳瑯滿目。山西北朝佛教造像題記以北魏平城時期及洛陽時期為翹楚,魏碑中的兩個結體特征“平畫寬結”和“斜畫緊結”都出現而又完備于這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的造像題記除了具有魏碑的普遍特征以外,更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彰顯了山西地區北朝佛教造像題記高超的書法藝術風貌。雖然這兩個時期的造像題記數量不多,但足以在魏碑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時期造像題記數量眾多,異彩紛呈,其書法藝術價值同樣不容小覷。由此可見,山西北朝佛教造像題記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是中國書法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