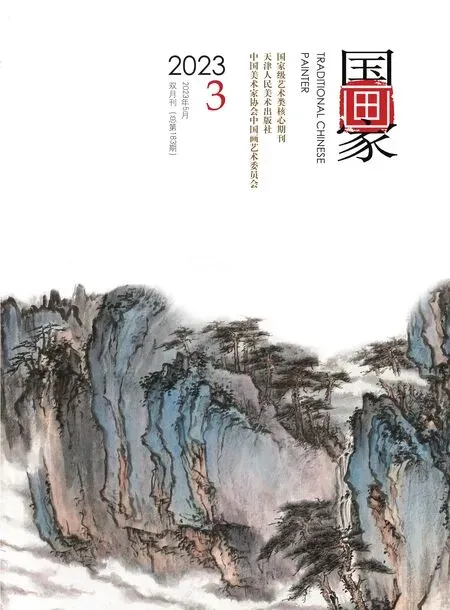心像應焉
——廣勝寺元代《藥師經變圖》壁畫藝術語言與表現技法芻議
首都師范大學/孫頻捷
壁畫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被賦予“成教化,助人倫”[1]的使命。隨著宗教的發展,人們用繪制壁畫的方式,表達超脫物質生活層面的精神追求。時至元代,中國寺觀壁畫形制已達于極盛,進入了法度森嚴、程式完備的成熟時期。此時的寺觀壁畫形制成熟,造型完整。以陸探微的“秀骨清像”[2]風格、張僧繇的“張家樣”[3]風格、曹仲達的“曹家樣”[4]風格為代表的佛教畫人物造型樣式是中原地區的藝術家進行宗教藝術創作時所遵循的主要程式。山西地區屬元朝統治中心,時至今日仍保存著元代木構建筑三百五十余座,建筑之中不乏精美的寺觀壁畫。縱觀整個中國壁畫史,不論是作品數量還是藝術水準,山西省寺觀壁畫皆位列全國首位。
山西省洪洞縣廣勝寺始建于東漢末年,是佛教東傳中國最早的寺廟之一,共分有上寺、下寺、水神廟三處。其中下寺以華麗宏富的壁畫獨樹一幟,蔚為壯觀。位于大雄寶殿前后兩殿的壁面分別繪有以“熾盛光佛佛會”和“藥師佛佛會”為題材的四面主要壁畫。民國十六年(1927),這四鋪壁畫被盜販國外。[5]其中的元代《藥師經變圖》壁畫幾經輾轉,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被美國精神病學家、收藏家賽克勒(Arthur M.Sackler)以其母親名義捐贈至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并作為該館中國館鎮館之寶陳列至今。
元代《藥師經變圖》壁畫現存面積約為70平方米,[6]畫面表現了“藥師三尊”“八大接引菩薩”及獻花供養童子等神將天尊護持東方凈土、[7]救度眾生的場景(圖1)。主體人物造型體態莊嚴,形象舉止生動自然,面部神態靜穆慈悲。作品氣勢雄渾的布局構圖與獨具匠心的用線設色相輔相成,雖經七百多年滄桑風雨卻瑰麗依然。其中,畫師對于線條的處理、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對于色彩的運用依然值得后代藝術創作者學習。
一、線條形式
廣勝寺壁畫《藥師經變圖》人物形象的描繪以線條為主要架構,畫家將線性造型發揮到了極高的水準,同時準確地凸顯出人物的氣質特點。其中“柳葉描”與“鐵線描”是最為主要且最具特色的線描形式。[8]整鋪壁畫以有別于敦煌壁畫的寫實與精致塑造出氣韻生動的佛像尊容,成為元代乃至整個古代寺觀壁畫的范本標桿。
(一)“柳葉描”
“柳葉描”是指線條形狀似柳葉,兩端較窄而中部較寬,此種描法又被稱為“蘭葉描”或“莼菜條描”,最初由唐代吳道子所創。此種描法善于展現出人物的衣袖飄帶迎風招展的動勢,富有灑脫的輕盈感、井然的秩序感和強烈的節奏感,畫面有著“天衣飛揚,滿壁風動”[9]的意境。因此吳道子所繪的道釋人物被冠以“吳帶當風”[10]的美譽,他的繪畫風格也被稱為“吳裝”[11],其獨特的宗教圖像樣式——“吳家樣”[12]為后人所推崇效仿。“柳葉描”講究用筆時通過執筆手腕、肩部、肘部轉動以及毛筆運行時筆鋒的提按變化表現出線條輕重緩急、抑揚頓挫、圓轉流暢的效果,呈現出飄逸靈動、張弛有度的韻律。
廣勝寺《藥師經變圖》中的線條運用宗法吳道子,整體畫面渾圓磊落。采取“柳葉描”造型不僅使得人物衣袂飄舞,更有利于營造出空靈圣潔的東方凈土世界,彰顯佛教仙境的安逸與美好,達到感化人心、宣揚佛教的功用,是藝術作品表現手法與內容內涵的完美結合。這種描法形式與宗教題材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另一個絕佳例子便是傳為吳道子所繪的道教題材白描長卷《八十七神仙卷》。作品描繪了以東華帝君、南極帝君為主的八十七位行進中的神仙,畫面以“柳葉描”表現出眾神仙列隊出行的恢宏景象,形神兼備的同時也符合道教清虛脫俗的價值觀。而《藥師經變圖》中不論是主尊藥師佛、兩側的脅侍菩薩還是十二神將,甚至于畫幅下方的供養人與供養童子,無不服裝繁縟、飾帶華麗,而畫師卻別樹一幟,僅以寥寥數根柳葉狀線條便將眾神祇輕盈曼妙的姿態、飄逸悠然的神韻恰如其分地描繪出來,整體造型洗練生動,神情畢肖,大氣磅礴,令人嘆為觀止。另外,佛祖菩薩等天尊神將面部五官、手掌足部的質感相較于衣物更富彈性,結構間的穿插關系更加復雜,起伏變化更加微妙,因此對其刻畫同樣運用了舒展挺拔的“柳葉描”,畫師用線時刻意使人物臉部及裸露于服飾外部的肢體線條稍細于衣紋,以此來展現人物皮膚細膩柔和的質感,運筆一氣呵成,線條流暢貫通,氣韻高古飛動,人物的風度神采無不閃耀著神性的光輝與偉大(圖2)。

圖2 《藥師經變圖》人物面部的“柳葉描”
(二)“鐵線描”
“鐵線描”與“柳葉描”的表現手法不同,需以中鋒行筆,筆力內含且施力均勻,所繪出的線條形狀好似鐵絲,勻稱協調而無明顯粗細變化,往往挺拔有力,給人以剛勁之感。以“鐵線描”為主要線型作畫可以塑造出中正堅韌、沉穩大氣的人物形象,較之“柳葉描”更能夠支撐起佛陀菩薩端莊持重的氣質和整體畫面莊嚴肅穆的氛圍。
“鐵線描”最初產生于魏晉時期,經過八百余年的發展,這種描法在元代已十分成熟。據明代馬愈《馬氏日抄·憨皮袋》記載:“河內縣民家墻內得一石碑,乃貫休所畫彌勒佛像,橫一拄杖,挑皮袋于背,腰間曳一蕉扇,筆法乃鐵線描也。”[13]可見,“鐵線描”早在五代時期已被人物畫家廣泛使用。
與《藥師經變圖》同為元代宗教壁畫的山西永樂宮《朝元圖》人物眾多,結構復雜,場景宏大。畫家為使畫面更具秩序感,便運用了“鐵線描”作為主要線條形式進行勾勒,匠心獨運的同時也將藝術語言與意境意蘊高度融合,成為藝術史上的典范(圖3)。《藥師經變圖》中,畫家在稠密的衣紋以及佛衣外邊緣處都采用了“鐵線描”勾畫,目的在于凸顯衣紋層疊下墜的質感,厚重而暢快,遒勁而豐滿(圖4)。另外,“鐵線描”造型規整,適合表現邊緣整齊、質地堅硬的客體對象,畫家根據這一特點,將它用于寶座、佛光、冠冕、笏板等物象的塑造,常采取雙鉤的形式,賦予對象方正硬朗、沉著穩重的視覺效果。通過線條的精心編排與組織,整幅畫面被描繪得生動飽滿,不僅使經變畫合乎宣揚佛法教義的目的,同時映現出宗教藝術獨有的神圣與威嚴。

圖3 永樂宮元代壁畫《朝元圖》局部

圖4 主尊藥師佛衣紋處的“鐵線描”
(三)“高古游絲描”
除“柳葉描”與“鐵線描”外,畫家還在人物的須眉處運用了“高古游絲描”。這種描法為東晉畫家顧愷之所創,要求落筆、收筆時虛入虛出,形成露鋒,其間以中鋒平穩運筆,利用筆尖時須圓勻、細致,線條有秀勁古逸、舒緩平靜之感,猶如“春蠶吐絲”,[14]連綿婉曲又含蓄飄忽,雖靜猶動,因此也被稱作“春蠶吐絲描”。“高古游絲描”因其纖細的形態,柔軟又不失勁健的獨特優勢,通常被用于須發的表現。例如,壁畫中日光遍照菩薩的鬢角、眉毛、胡須部分就是以這種描法進行繪制的。
二、人物造型
畫面正中央描繪的是主尊藥師琉璃光佛,他正端坐于藏傳經變畫中典型的蓮花瓣須彌座之上,雙耳垂肩,面如滿月,容貌慈悲,儀態莊嚴,頭頂螺發肉髻,身搭佛衣帔帛,袒胸露懷,左手撫膝,右手端舉,雙足結跏趺坐。主尊佛兩側跏趺而坐的大菩薩是觀音菩薩與文殊菩薩,同藥師佛組成“佛三尊”,而原本脅侍藥師佛的兩大菩薩——日光遍照菩薩與月光遍照菩薩則被降至次要位置,位列主尊藥師佛后側,手中分別持日輪與月輪。藥上菩薩與藥王菩薩立于主尊前側,手中分別持藥師佛的藥缽與錫杖。對于菩薩尊格的認定,主要根據文獻記載中對于菩薩外觀的描述與壁畫中的圖像特征相互對照。中國寺觀壁畫研究領域專家學者孟嗣徽認為,如此別出心裁地安排人物主次關系,可能是由于觀音菩薩和文殊菩薩屬佛教信仰中的精神標識,信徒對于他們的熟悉程度遠大于日光遍照菩薩和月光遍照菩薩。[15]
《藥師經變圖》人物形象上承接唐代梵像體態豐腴的造型樣式。中唐時期的人物畫家周昉是這種樣式的代表,他擅畫仕女、佛像、肖像,早年宗法張萱,后期加以變化,自成一體。由周昉所創的“水月觀音”之像以秾麗豐腴著稱。[16]在唐代以前,中國道釋人物畫受南朝劉宋陸探微影響,多作“秀骨清像”。唐代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物質生活逐漸豐富,百姓安居樂業,人們的審美取向也隨之發生變化,唐人開始青睞豐肥的體態。周昉所作的人物線描細勁暢快,富有韻律感,將秾麗豐肥的身形和細膩柔嫩的肌膚特點表露無遺,十分接近現實生活中深宮貴婦的人物外觀,不僅張揚了唐王朝繁榮昌盛的生活狀態,具有強烈的時代感,還迎合了唐代中晚期官僚貴族們的審美意趣。其作品有歌頌世俗生活中升平向上的一面,同時體態豐盈、容貌端莊的造型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宗教藝術的審美理想,故而為歷代宗教畫家所推崇,成為日后佛教畫的主流,影響深遠。如今,我們仍可以從敦煌唐代乃至后代壁畫中領略其曠世遺風。
(一)人物的頭部和面部造型
藥師佛頭部渾圓,肉髻微隆,面形圓潤,臉頰飽滿,而元代藏傳佛教興盛也使晉南地區佛像繪畫融入了一些唐卡的風格特色,畫面更富形式感,具有一定的理想美。眾菩薩同樣豐頰秀眉,神采飛揚,而其發髻與華蔓冠形制也格外精美,裝飾繁復講究,具有明顯的元代菩薩像特點。五官勾勒相當簡潔概括,只提煉出最具代表性的形狀特征,不多作藻飾,可以復見張僧繇“筆才一二,象已應焉”[17]的余韻。盡管眾人五官概括,卻不是籠統機械的重復,畫家對于不同人物的神態捕捉極為細膩,尤其體現在對眼睛的刻畫上,例如位于文殊菩薩寶座下方的供養童子,他的雙手向前托舉,頭呈微微下低的動勢,但一雙調皮的眼睛望向斜上方,仿佛在羞澀地偷瞄頭頂上方的文殊菩薩。童子目光灼灼,人物形象瞬時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圖5)。正如顧愷之所言:“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18]畫家只有重視對眼神的表現,著意描摹對象的精神面貌,才能烘托出人物的個性,使整鋪壁畫生動傳神,達到以形寫神的目的。

圖5 位于文殊菩薩寶座下方的供養童子
(二)人物的軀體造型
藥師佛身軀渾厚,胸膛寬闊,雙肩圓滿,儀態端莊,身穿袒右臂袈裟,外搭透明薄紗帔帛,腰間束寶帶,褒衣博帶的服飾體現了中國傳統服裝寬大遮體的特點;菩薩體形豐臃,姿態優美,上身著天衣,下身著百褶籠褲或貼體長裙,系項鏈,戴臂釧、腕釧,身佩花瓣形瓔珞,飾帶繪有祥云等紋樣,衣裳華麗,雍容華貴。這樣的軀體造型與衣著裝飾在宋元壁畫中較為常見,例如位于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的宋代壁畫中的佛陀與菩薩像,從中可以看到與《藥師經變圖》壁畫相同的風格樣式。
三、賦彩設色
(一)媒材
與紙絹作品可以使用天然礦物質顏料或水性動、植物顏料不同,壁畫繪制只選用天然礦物質顏料,這種顏料的化學成分相對固定,所以發色穩定。礦物質之間存在著晶體結構的差異,往往難以調和,不易分染,因此壁畫賦色多以平涂為主,通常使用“勾填法”,即以墨線為骨干,避開線條,填充色彩。繪制壁畫使用到的天然礦物顏料有朱砂、石青、石綠、胡粉、雄黃、雌黃、赭石、云母等。由于礦物質經研磨后的顆粒大小不同,同一種原料又可以呈現出不同的色相、明度或純度,畫師則可根據畫面需要制出適宜的顏料。
(二)色彩搭配
《藥師經變圖》滿壁以赤、綠、白為主色,并輔以青、赭、黃等顏色,畫面具有獨特的單純感與優雅感。整鋪壁畫尤以主尊藥師佛的形象最令人矚目,其中除去構圖因素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畫師以亮麗醒目的朱砂為藥師佛所著佛衣的主要顏色,除此之外的菩薩、天將、供養人的服飾設色則以綠色、白色為主。這樣的布置增強了畫面的對比關系,主體人物因此被襯托得更加醒目。人物的膚色以胡粉做底,再以土黃渲染,從而達到接近于亞洲人種皮膚的發色。人物的配飾以石綠為主,又以石青、朱砂、朱磦、雄黃點綴,其中寶石、珍珠等球狀物還以蛤粉提點高光,使裝飾物極具立體感,彰顯璀璨奪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經歷了幾百年的氧化和后期剝離切割的過程后,其中部分顏料已經從壁面脫落而露出了墻體本身粗糙的地仗層,這種斑駁陸離的效果反而使這鋪元代壁畫具有了時間所賦予的獨特質感,沉穩凝重,歷久彌新。
結語
《藥師經變圖》中的線條精準入微。創作者以理想化的藝術手法寄托并傳達著信眾的精神訴求。壁畫師們用線簡練流暢且富有力度,在局部尋求變化,充分發揮線描豐富的表現力,從而達到氣韻生動的至高境界,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物畫的造型語言。線條是中國傳統工筆畫藝術語言的靈魂與核心,是中國人在二維空間中表現客觀對象本質的特殊方式。一根線條猶如一系準繩,衡量眾生百態,方圓曲直間勾勒出物象豐富而無窮的變化。如果沒有線條的存在,工筆畫的美學特色就無從談起。
《藥師經變圖》中的人物形象鮮活達意。畫家在塑造人物時并不滿足于容貌逼真或動態自然,而是在探索表現人物性格與內在深度,簡言之就是“傳神”。“形神兼備”作為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評判人物畫的最高準則,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畫家極力追求的目標。這種“境”的營造,反映了古代藝術創作者胸羅宇宙、俯察品類的狀態,體現了他們由表及里、去偽存真的態度。
《藥師經變圖》中的色彩協調統一。筆者認為,創作者在著色方面的拔群之處在于對細節的苛求與對整體的把控相結合。對于寺觀壁畫而言,如何才能做到既讓畫面色彩在局部中對比強烈,絢麗非常,又能在整體觀感中使典雅而和諧的畫面色彩與莊嚴肅穆的宗教氛圍相得益彰,從而輔助畫面實現陽剛的力量感與陰柔的靜謐感的調和平衡,是畫家在賦彩設色時必須考慮的問題。《藥師經變圖》在色彩運用上之所以能夠不落窠臼,其精髓在于始終保持用色不花哨,細節不喧賓奪主,堅持取精用宏、刪繁就簡的用色原則,追求大道至簡、返璞歸真的藝術境界。
廣勝寺元代《藥師經變圖》壁畫的藝術語言與表現技法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成果,優秀的晉南職業壁畫師們根據宗教信仰的特點,繼承、提煉唐宋畫風,吸納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相關題材的樣式與元素,繪制出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鴻篇巨制。至此,中國寺觀壁畫開啟了瑰麗恢宏而又兼具世俗氣息的新篇章。而傳統寺觀壁畫藝術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我們以如今的審美眼光挖掘出它所蘊藏的藝術魅力,讓現代繪畫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敢于突破,開拓創新,取得更為輝煌的成就,使傳統壁畫藝術煥發出嶄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1][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1頁。
[2]同注[1],第126頁。
[3][4][12]同注[1],第31頁。
[5]梁思成、林徽因,《晉汾古建筑預查記略》,《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3期,1935年,第46頁。
[6]1965年,時任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遠東藝術部研究員利珀(Aschwin Lippe)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刊物發表的專文,通過《藥師經變圖》壁畫的尺寸對該壁畫所屬的佛殿位置進行考訂。參見Aschwin Lippe,“Buddha and the Holy Multitude,”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Bulletin,vol.13,1965,pp.325-336.
[7]美國學者景安寧(Anning Jing)于1991年發表文章,對《藥師經變圖》壁畫中主尊佛尊格進行了考訂。參見Anning Jing,“The Yuan Buddhist Mural of Paradise of Bhaisajyaguru,”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vol.26,1991,pp.147-165.
[8]為便于下文論述,各類線描所對應的名稱引自鄒德中《繪事指蒙》中“描法古今一十八等”的記載,該提法雖始于明代,但其對于歷代繪畫作品中不同線性的概括與總結頗為恰當,已為當下繪畫創作者所共識。
[9][清]孫岳頒,《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六,《欽定四庫全書》,第22頁。
[10][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20頁。
[11]“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謂之吳裝。”參見[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21頁。
[13][明]馬愈,《馬氏日抄》,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6頁。
[14]“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筆法如春蠶吐絲。”參見夏文彥,《圖繪寶鑒》卷二,《國學基本叢書》,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8頁。
[15]孟嗣徽,《元代晉南寺觀壁畫群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95-103頁。
[16]“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長史。初效張萱畫,后則小異,頗極風姿。全法衣冠,不近閭里,衣裳勁簡,彩色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參見注[1],第204頁。
[17]同注[1],第36頁。
[18]同注[1],第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