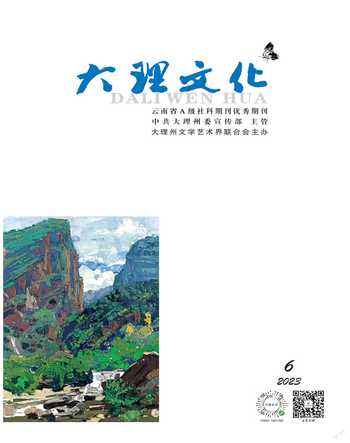于絢爛處探幽深,于細微處尋奇偉
農為平
說及概念的復雜性,“文化”一詞必然位居前列。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人類學家克魯伯、克拉克洪搜集的1871—1951年八十年間各種關于“文化”的解釋就多達164種,其豐富和復雜可見一斑。對文化的多樣性認知在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英國古典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那里便可尋及源頭,泰勒認為文化是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它作為社會一分子所習得的任何才能與習慣,是人類為使自己適應其環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這一解釋,時至今日依然是眾多關于文化的釋義中的經典,也是后世識別文化范疇的重要來源依據。文化的這一包容開闊特性,在由大理白族作家、學者又凡歷時五年完成的《大理非遺守藝人》(以下簡稱《守藝人》)一書中,可謂是得到了最具體形象又淋漓盡致的呈現。該書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內遍及十大類目、共72位非遺傳承人為對象,通過他們對地域民族傳統文化的持守和傳續,以兼具寫實和詩性的手法呈現滇西大理地區多元駁雜、精彩絕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景觀,讓人領略并驚嘆于祖國西南邊陲蒼洱大地上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
大理古稱葉榆,是云南歷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享有“文獻名邦”之稱,文化底蘊深厚,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2011年,大理州被原文化部公布為“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至2022年,全州共有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719項,其中國家級項目18項;四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2344人,其中國家級12人,全州建有非遺傳習展示中心、傳習所、傳習點共200余個,確保了非遺文化在蒼洱大地上薪火相傳。各種如星辰般散布于大理各地的非遺文化項目,可謂是大理地域文化的豐厚“家底”,它們影響、決定著大理的文化底蘊與氣質。
《守藝人》作者又凡與大理非遺文化的正式結緣,源于一場目的明確的“誤打誤撞”。作為小說家,她“最初是被扎染、大理石、木雕、銀器等打動,想采寫這些精美傳統手作的制造者,書寫他們的同時豐富自己的閱歷,為日后寫小說收集素材”。慶幸的是,她的計劃得到《大理時訊》的認可和支持,并為此特別開設“大理非遺”專欄。從2016年8月22日開始,到2021年五年時間里,又凡共發稿72篇。在專欄名目的規定下,在一次次與非遺傳承人的接觸、訪談中,又凡的目的意圖不知不覺從原初的興趣滿足、積累小說素材,逐步向深度探尋、打撈民族文化的密碼和底蘊過渡,她本人也在這種與故土文化的近距離觸碰過程中,不知不覺完成了一場意義非凡的華麗轉身與精神蛻變:由作家到文化學者;由文化的旁觀者到如數家珍的文化講述者、守護者。可以說,《守藝人》既是一部第一次系統對大理非遺傳承人進行采寫、呈現大理非遺文化精華的煌煌之作,也是作者個人一場意味深長的精神朝圣的心路手記。
一
蒼洱大地,山奇水秀,物華豐富,曾與盛世大唐、趙宋鼎足而立的南詔與大理國地方政權,書寫了中國邊疆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成就了這片大地歷史文化的厚重與輝煌。這里曾是串聯起中原文化與印度文明的茶馬古道、南方絲綢之路上的要塞和樞紐,千百年來,北上經四川深入中原腹地或轉入西藏而至印度、中亞地區,南下或經普洱或經騰越出境東南亞的馬幫,風塵仆仆的這里經過、歇息、出發,他們的行囊裹挾著中原的泱泱氣象、印度洋暖濕的風、青藏高原的清冽寒氣,拂過蒼山的雪、洱海的水,最終留下了不同文化曾在這里交集、碰撞的深深印跡。大理又是多民族雜居之地,漢、白、彝、回、傈僳、納西等13種民族,在歲月的更迭中無聲交匯融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有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斑駁雜糅、豐富多姿的多元文化共存景觀。如此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在歲月的不斷打磨、塑形中,最終造就出大理地區獨一無二的文化資源與形態。遍布蒼洱大地上令人驚嘆的種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正是這一文化寶庫中最耀眼的一粒明珠。然而,歲月流轉,往事漸漸斑駁模糊,還有多少人知道這些依然鮮活的民間技藝背后曾發生的前塵往事?又有多少人對其中所積淀的前人生存智慧與情感密碼心領神會?而這些,正是文化的魂魄和根基所在,離開這一根本,所謂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僅剩干癟空洞的形式、表象、技能,無法承載起一方水土的精神血脈。
《守藝人》的特別與成功,就在于自覺承負起探尋文化之根的重任。全書從文化傳承這一特別視角入手,在呈現一個個傳承人風貌,書寫一項項傳統技藝、習俗、器物等的現代傳承狀況的同時,有意識地去追尋隱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內涵,力圖還原作為一種象征符號的非遺文化所承載的精神密碼。因而在寫作取向上,該書選擇了與時間逆行的姿態,通過非遺傳承人,搭建起通向歷史的幽深隧道。
以銀器制作為例,這項文化遺產稱得上是大理各類非遺項目中最具現代特質的典型代表,以鶴慶新華村為集中地的白族手工銀器制作、售賣,已成為大理旅游中的一大特色與亮點,是當地旅游創收的優勢項目。書中采寫到了寸發標、母炳林兩位國家級傳承人及汪開榮、李福明等省州級傳承人,在深入采寫他們對傳統技藝的繼承、發揚歷程,巧奪天工的制作技藝,以及辛勞執著、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之外,還揭示了銀器制作何以在白族民間流傳不絕的內在原因。大理地區的銀器制作始于南詔時期,迄今已有1200多年歷史,時至今日,白族民間對銀器的喜愛依然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剛出生的小孩子要帶純銀的長命鎖,虎頭帽上栓系銀子以辟邪;新娘子訂婚,婆家的聘禮中最不能少的是一對銀鐲子;建蓋新房時,中柱底下通常要放置銀器,以示富貴根基;老人過世了,家人要在其口中放一塊碎銀子,叫“合口銀”,以示吉祥……這種現象意味著白族民間對銀器的認知已從單純的物質需求提升到了器物崇拜的內在精神層次。在中國民俗文化中,器物崇拜是普遍現象,它“是民眾創造的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結合體,成為民眾無價可估的生活支撐”(呂洪年《民間器物崇拜述略》)。也就是說,對當地民眾來說,銀器并不只是簡單的商品和裝飾物件,而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含義,成為一種象征辟邪求瑞的文化符號,寄寓著民間最素樸的生活愿景,因而才不會被歲月輕易湮沒,而得以代代傳承,綿亙不絕。
正是循著這樣的寫作理念,《守藝人》在娓娓講述傳承人故事與文化遺產狀貌的間隙,引領著讀者穿越回到古老的歷史現場,去找尋這些歷經滄桑流傳下來的文化之根:每年農歷四月在大理幾乎傾城參加的民俗活動“繞三靈”,是大理農耕文化與宗教文化的產物,在民間傳說中起源于南詔第一代國王細奴邏和三公主的故事;外地游客到大理都會品嘗的特色茶飲“三道茶”,將當地特色飲食與茶飲巧妙結合,充分體現了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同時還與南詔國王閣羅鳳女兒阿蘭公主的婚事傳說相關;在各種節慶儀式上必不可少的霸王鞭表演,據說是南詔大理時期的宮廷劍術,也與元初忽必烈征服大理時人們的反抗歷史有關聯;巍山“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打歌”的彝族中流傳的“打歌”傳統形成于古代部落之間的爭斗;白族傳統民居屋頂上常見的“瓦貓”,由白族古老的圖騰崇拜物老虎演化而來;每年農歷七月舉行的劍川石寶山歌會起源于十姐妹智斗惡龍的民間傳說,反映了白族人民能歌善舞的特性,以及青年男女以歌交友的自由婚戀傳統……有的非遺項目并沒有特別的起源傳說,卻也是在民間長期的生產生活中逐漸累積經驗而形成,如扎染、乳扇、刺繡、黑陶、土堿等等,反映出極富特色的地域生產與生活傳統。
特別的是,有的遺產項目形成的時間并不算長,卻有著特殊意義,典型者如朱苦拉咖啡。這一明顯的舶來品,是法國傳教士田德能于1894年從越南帶來的,由于他幫助朱苦拉村民打贏了一場官司而贏得人們信任,后來他回國后,這些咖啡樹繼續在村民看護下生長、結果,他傳授的煮制咖啡的方法也在當地流行,成為人們閑暇時和勞作之余鐘愛的飲品。這一文化項目,顯示了大理文化“海納百川”的開放、包容特性,其根源正在于大理所處的多元文化交匯地帶。早在南詔鼎盛時期,統治階層在擴張領土的同時,已經有意識地主動向多種文化學習,公元829年南詔軍隊攻占四川成都,擄掠了一批當地能工巧匠,將他們帶回大理傳授技藝,還有走南闖北的馬幫捎帶回來的各種信息、技能,早已花開無聲,在時間的黏合之下完全融入到當地的生產生活之中。
時至今日,事實上已經很難識別清楚哪些是純粹的本土技藝,哪些是外來的。不過,這已無關緊要,一種成熟的文化應該是充分吸納各種養分之后的自在、飽滿狀態,是多種因素在生活中不斷打磨、淬煉而融合的結果。在大理文化中,一個尤其突出的特殊現象是,在大理白族供奉的本主神祇中,甚至有天寶戰爭時率唐軍攻打大理、最后兵敗身死的大將李宓,老百姓感其忠義,奉為利濟將軍,立廟祭祀,此外還有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十八位將領,也享此殊榮。這種舉世罕見的奉敵為“神”的現象,充分顯示了大理文化自古就有的開放、包容、自信氣度,因而當地各類非遺文化中多種文化元素并存景象,較為普遍。《守藝人》正是通過挖掘傳承人所守護的文化遺產背后的文化根祇,從宏觀視角展示了大理傳統文化的多元與豐贍。
二
《守藝人》是迄今為止云南省唯一一部以非遺傳承人為對象的專著,作為一部僅憑作者一己之力完成的作品,其容量之大、涉及面之廣無疑是驚人的。全書50萬字,一共采寫了大理地區72名非遺傳承人,包括了國家、省、州、縣四個級別,在類目上涵蓋了國家所界定的傳統技藝、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美術等非遺文化十大類目。書中所采寫的非遺傳承人及代表項目,不論是在類型上還是在影響上,在當地都極具代表性,比如大理州的12位國家級傳承人,全部囊括于書中;白族扎染、乳扇、白曲、繞三靈、下關沱茶、劍川木雕、諾鄧火腿、耳子歌、霸王鞭、三道茶、跳菜……這些知名度、辨識度極高的非遺文化項目,在書中一一呈現。可以說,《守藝人》薈萃了大理非物質文化的精髓,是一部生動、深入展示大理深厚絢爛歷史文化底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本幫助讀者深度了解大理文化的絕佳讀本。
《守藝人》有別于常規文化類讀物之處,在于這并非是一部各種客觀材料的堆砌和再加工集成,而是全部建立在作者深入現場、走訪非遺傳承人所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基礎之上,帶有鮮明的個性印記。又凡放棄已有的現成資料,拒絕任何形式的先入為主,采取人類學學科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形式——田野調查,到現場去,到采訪對象生活之中,通過面對面訪談和實地觀察、體驗,獲取真實而鮮活生動的材料。這種嚴謹、慎重的寫作態度,既是對傳承人、對文化的敬重,也使作者獲得一種沉浸式的文化體驗,從而加深對訪談對象的了解和把握,能夠從極富現場感和生活感的獨特視角呈現出人物和文化的本色。尤其是在人物的塑造上,又凡顯示了作為一個小說家對生活的敏感和對人物特點的快速準確把握優勢,擅長并有意識地從毛茸茸的世俗煙火生活中入手,在尋常的生活細微處去捕捉人物的特質和動人之處,從而避免了寫這類文化人物容易陷入扁平化、模式化窠臼的弊端。
大理民歌“田埂調”傳承人張樹先,是一個三歲就失明的盲人歌者,書中既寫他出眾的音樂天賦和在民歌道路上的發展、聲名,寫歌星汪峰、大理古城中的音樂人與張樹先的交往,更蕩開一筆,用溫馨的筆觸特別寫到這位在歌聲中燦爛的盲歌者,年輕時用彈三弦對歌的方式收獲了愛情,“雖然他從未見過她長什么樣子,但她總是牽著他,成為他的眼睛,不僅陪著他出遠門參加各類音樂活動,更陪同在附近村村寨寨十冬臘月的喜事演奏中”。在作者自己最推薦的《解苦散郁所以吹小悶笛》一篇中,有幾個細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傳承人葉春龍回憶1980年到北京演出48天的難忘經歷時,作者追問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稍有遲疑后坦誠地說,“不怕你笑話”“最大的感受就是沒有錢”,為了支持他去北京,當時家里把三百多斤的年豬賣了;另一處是寫晚飯時分的情形,葉春龍的兩個上小學的小孫子在一邊嬉戲玩耍,間或吹一下小悶笛,“院子一角時不時傳來老人口齒模糊的呼喚聲,是葉春龍80多歲的母親,已癱瘓20多年。聊天間隙,他忙小跑下臺階,將老人抱回房間,而他的妻子正在廚房煮晚飯。那天的晚餐,有老臘肉,有酸腌菜燴三線肉、小瓜洋芋以及色澤鮮艷的腌豆腐,簡單而少油,即使是燴肉,也顯得寡淡”。
這種瑣碎而真實的生活細節的加入,看似與光鮮亮麗的文化不搭邊,實際上卻于不動聲色中還原了文化的真相。所謂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其實質正是民間生產生活經驗的結晶,本身是世俗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們是鮮活的、立體的,浸染著煙熏火燎的生活氣息;而作為文化守護者的傳承人,他(她)們也是擁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悲欣歌哭,只是人生本色。又凡以直觀真實的體驗,用樸實生動的文學筆法,消解了文化常常被賦予的莊嚴肅穆感,將視角直接拉回到最真實的生活現場,呈現民間文化和傳承人充滿人生況味的本真面目。
對于中心點——傳承人所秉持文化項目的核心技藝或內容,自然是《守藝人》濃墨重彩書寫的重點。以田野調查為根本,聆聽、觀察、體驗,再將核心工序或過程原汁原味搬到文字中,是又凡呈現一項項傳統技藝的“笨拙”方法(少部分具有保密性質的除外),這種寫法避免了刻板的材料復制,保證了對核心技藝的真實再現,帶著似乎觸手可感的現場氣息,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示出這些傳統文化的精髓;同時,跟隨著書中栩栩如生的描述,閱讀者猶如置身現場,大大加深了對這些古老文化傳統的認知和感受。
譬如在大理享有盛名的三道茶,即便是當地人,很多也只知其名其形式,而不清楚其中的奧妙所在,更遑論走馬觀花的游客了。根據《蠻書》《南詔野史》等志書所載,白族三道茶已有一千多年歷史,是白族獨特的民俗茶藝,又凡根據此項目傳承人董麗的講述,將最正宗的白族三道茶的繁瑣細節娓娓道出:首先是器皿選擇,其次是原料選用,接下來才正式進入制茶環節。每一環節均有諸多講究,比如器皿以劍川黑陶為上,建水紫陶為中,較一般的是普通土陶。在“一苦二甜三回味”三道程序中,所用杯具也有不同,苦茶杯最小,其次是回味茶,甜茶杯子最大,講究的是“甜打底,苦出頭,回味在心頭”;原料中的茶是關鍵,宜用綠茶,蒼山雪綠,感通雪芽、蒼山碧綠等是上品,下關沱茶宜佳,普通綠茶次之;甜茶中的乳扇以鄧川乳扇為佳,核桃最好用云南山核桃,以小推刨推成薄片,回味茶中用上好的花椒、桂皮、生姜作為原料……前期準備即如此繁復、考究,正式的三道茶制作環節已可推而想之。這獨特的將茶與飲食相融并講求“一苦二甜三回味”滋味的茶俗文化,作為白族最高的待客禮儀之一,既反映了白族地區飲食文化的特性,也將“苦、甜、回味”這樣的人生感悟巧妙寄寓其中,可謂韻味無窮。
大理地區的非遺傳承人中,既有傳承大眾廣泛周知的諸如銀器、扎染、乳扇等一類傳統技藝的,也有人默默守護一些少為人知的小眾技藝。比如《解苦散郁所以吹小悶笛》中的小悶笛。這種知名度不高、流傳不廣,且與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喜樂”相悖的樂器,為何能進入非遺保護名錄呢?一是因其制作技藝的奇、巧,核心工藝是哨片的制作,選用深山里的野蠶制成:“當野蠶還是蠶蛹的時候,將其從樹上取下,輕輕按捏直至死亡,陰干后,蠶蛹的肚子就會自然中空,去頭去尾即是上好的哨片。更有意思的是,雄蠶和雌蠶的哨片也有區別,一般要選雄的,因為雄蠶制作的哨片吹奏出來的聲音更細軟、勻凈、綿長,雌蠶則粗獷且呆板,不好聽。雄蠶和雌蠶一般都是一對一對掛在樹上,同一對蠶中,稍微細一點的即為雄蠶。死蠶不能用,因為沒有韌性,聲音亦呆板難聽。”如此簡單又如此奇絕玄妙的工藝,實在令人忍不住拍手稱絕,那是多少經驗的摸索、累積,才最終成就了這小小的樂器!它凝聚著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們從大自然中獲得的獨特美學啟迪;其二是小悶笛的功能直接定位為“解苦散郁”,這在樂器界并不多見,在現實層面反映了山間生活的艱辛不易,其深層意義在于直面人類情感世界的復雜性,真實表達為傳統所忌諱和遮蔽的孤獨、愁苦等情緒,并自行找尋這一藝術性的傾訴與宣泄途徑。從現代心理學來看,這正是一種科學而有效的對抗消極情緒的方法。
從點到面,從形到神,從現實到歷史,《守藝人》開啟了解讀非遺文化的一條獨特路徑。作者置身于民間生活現場,在五味雜糅的世俗生活中,以近景視角、細膩情感,引領讀者走近維系文化血脈的傳承人,走進匯聚民間智慧的文化遺產,近距離感受大理非遺文化的煙火氣息與幽深厚重。
三
與眾多面目謹嚴而文字規整的文化類讀物形成區別的是,《守藝人》是一部充溢著作者個性氣質和情感溫度之書,這從書名便可直觀感受得到。作者以“守藝人”指稱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承者,較之正式的名稱“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在氣度上稍顯遜色,卻更接地氣,更形象熨帖,顯出一種柔和動人的人文關懷溫度。又凡在“前言”中如此解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傳播和弘揚,核心只有兩個字:守、藝。‘手藝更需‘守藝,守是堅守,藝是技藝。只有用心守,才能讓技藝留存;只有精湛的技藝,才能代代相守。”此語可謂精當而形象,點出了文化傳承人在人類歷史文化長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書中篇目在標題命名上也極富特色,大多直接取自傳承人的生活語言,不事雕飾,樸實無華,同時又極具概括力,諸如“劉麗湖:手閑不住就扎布”“董月暢:每件黑陶都是獨一無二的”“楊玉藩:魚鷹是比狗都聽話的動物”……這種命名方式,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匠心獨運,作者需從傳承人的無數話語中捕捉、打撈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通過它來傳遞傳承人個性或所傳承文化的特質,從而達成給讀者留下先入為主深刻印象的效果。
《守藝人》拂面而來的感情氣息源自作者的感性寫作。又凡是一個具有詩意氣質、情感豐沛的作家,她常常很自然地在行文中流淌出詩意,放任情感的自由奔涌,這種感性的顯現,必然對文章整體的嚴謹性有所影響,卻形成了情感上的動人與行文上的靈動效果,而這恰恰是作品的獨特魅力所在。
石寶山歌會的姑娘小伙是不睡覺的,加長版電筒一閃一閃,燈泡燒掉再換一個新的,心跳比電筒光的閃爍還急,直到找著自己心儀的姑娘。小伙子會這樣唱:對面的小妹妹幫阿哥找一個相好,就找像你這樣漂亮的一個,像你一樣找不著,就你也可以。(《姜宗德:歌王一路放歌的精彩》)
劍川石寶山歌會是大理有名的民間盛會,集宗教信仰、民間藝術、婚戀習俗、商貿活動等多種性質于一體,青年男女在歌會上以歌交友,自由地找尋意中人。以上充滿濃烈感情色彩的描述,頓時生動再現歌會上歡快熱烈、激情四溢的場面,青年男女以歌為媒介,自由、大膽追尋幸福的傳統習俗躍然紙上,并且為歌王傳承人姜宗德的文化傳承故事做了濃墨重彩的氛圍鋪染。試想一下,這里如果置換成客觀嚴謹的介紹性文字,其效果和感染力必然大打折扣。
你有沒有想過在一房子樂器陪伴下安度晚年是什么感覺?如果那些樂器還是自己親手制作的呢?它們像一群孩子,和你相依相伴,讓每一天的日子都浸透著過往歲月的美好回憶,如同那些歲月一天都不曾流失,因為它們就在每一件樂器身上,觸手可及。(《段文信:和親手制作的樂器相伴一生》)
這段融詩意、溫情于一體的開篇文字,奠定了全文的情感基調,作者所欲達成的敘事意圖呼之欲出:對于段文信這樣的民間手藝人而言,樂器制作不僅僅是一種能力、技術,也傾注著畢生的心血和情感,每一件親手制作的樂器都飽蘸著溫暖的時光記憶。事實上,在所有傳承人與文化之間,都存在著這樣隱秘的情感紐帶,這就是民間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內在精神密碼。
另外,作者還會把自己在采訪過程中所捕捉到的動人瞬間和剎那間的震撼,用充滿詩性的語言與讀者分享:
田埂調蒼涼,在大理所有民歌中,最為悲愴,沒有之一。……三弦彈奏間隙,當張樹先那一聲帶血的歌喉如紅杜鵑向蒼穹綻開,說不清是調子的蒼涼還是歌聲的蒼涼,只覺一腔飽蘸生活的悲愴裂石穿空,讓天地山川黯然失色。”(《張樹先:在黑暗中譜寫田埂調的燦爛》)
書中諸如此類溢滿情感與個性體驗的文字,顯示著作者是用心去感受、再現傳承人與文化血脈相連的生命歷程,用真誠甚至是虔誠去記錄非遺文化的風采,具有扣動人心的感染力。可以說,《守藝人》搖曳多姿的生動和獨特正在于作者并未過多為理性思維所拘囿,她以一種充滿個性化的真率表達,建構起嚴謹與活潑、科學與詩意相雜糅的講述空間,讓背負文化使命的傳承人以樸實本真的自然狀態浮現,讓傳統文化綻放出古樸而迷人的光輝。她的文字讓人感受到民間文化是美的,那是民間生活經驗與時光之河共同澆灌而盛開的智慧之花,散發著醇厚獨特的氣息,而不僅僅是脫離生活的刻板的文字表述;同時也讓人感受到非遺文化是活著的,它們穿越歷史滄桑而來,在一代代守藝人的守護、傳續下,依然鮮活地在世俗生活中發揮作用,帶著熱氣騰騰的煙火滋味,一伸手,仿佛就可觸碰到那種令人迷醉的溫度和氣息。
最后需說的是,《守藝人》的最終完成,就在于作者的執著與堅持。她用5年的時光,一心一意深入大理的文化寶山之中尋寶訪奇,把一個個隱在市井、深山的守藝人推至前臺,讓那些帶著歲月滄桑印記的文化瑰寶顯露真容,從而讓更多的人識認、了解大理地域文化的風姿與魅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又凡賦予了傳承人及文化一種新的時代風范,喚醒了閱讀者沉睡的文化記憶和情感,這在國家大力呼吁保護和弘揚民族文化的當下,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而這份執著和堅持背后,是作者自覺而強烈的故土情結與文化使命感。作為一名生茲在茲的白族文化人,自小就浸潤在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之中,天然地擁有深沉的文化情感。在多年游弋于小說的虛構世界之后,她將目光轉回到地域民族文化,看似偶然,實質上卻是一種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自覺回歸。5年的時光,主要以自駕的方式幾乎走遍全州山水,完成對72位傳承人的采訪,在如今這樣一個普遍追求快捷便利的浮躁時代,稀缺而難能可貴,令人肅然起敬!多少個時日,一次次的出發、歸來、再出發,路途上的勞累、寂寞,難與外人道來的酸澀,都被她輕而易舉地消解于文字之外,讀者從中讀出的只是一份甘之若飴的堅持與樂趣,原因何在?答案其實已在書中呈現:“他們守藝,我用文字守護他們,作為守藝人的守藝人,倍感榮幸”;“來路串串腳印,歪歪斜斜,橫橫縱縱,淺淺深深,正是你一直以來想要取的,閃閃發光的貝葉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