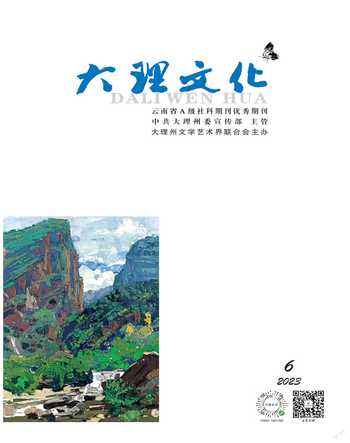小冊頁
張羊羊, 1979年5月生于江蘇武進,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見于《鐘山》《天涯》《十月》《散文》《大家》《中國作家》《山花》等刊物。有詩集《馬蘭謠》《綠手帕》,散文集《庭院》《舊雨》《草木來信》《大地公民》等出版。
七星瓢蟲
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忽左忽右地蹦跳在麥地間的小路上,他的黃帆布書包斜搭在腰下。他有著發現萬物的天賦,突然停住了手中甩動的樹枝,悄聲蹲下來,用手指去數麥葉上的小蟲子,數呀數呀怎么也數不完。這些小蟲子很多被他氣壞過,后來慢慢地住進了他的詩集里:“那過去了的……/還有牧歌、泥巴/還有小甲蟲背著的七顆星星/一切在漢字中倒流/我的淚水倒映著古老的南方。”他長大后總是在一頁紙上想起許多過去的事,眼眶就溫熱了。
孩提時代,我時常去捉弄一種蟲子,因為它憨態可掬,個頭又是不會造成任何威脅的小不點。我會把它翻過身來,肚皮朝天,六足亂蹬,然后伸展一只翅膀抵地,慢慢轉圈,終于翻了過來。在它暗自高興、累得剛透過氣來,我隨手又將它掀了個身。就這樣樂此不疲地看它翻來翻去,猜想它也是滿肚子的火。
它叫七星瓢蟲,會受困于我捉弄螞蟻時差不多慣用的伎倆。一只螞蟻好好地在趕路,它一早就有了美好的打算。被我遇上了,蹲下身來一大口唾液堵住了它的去路。它想了想,繞開這該死的障礙繼續趕路。我又是一口唾沫堵住它。它是知道今天不下雨的,只是奇怪這玩意哪來的。于是繞來繞去,惱火得很,所幸我的口水吐干了。
對七星瓢蟲的外觀描述,泉麻人的一句頗為出彩:“在帶有光澤的橘紅色上,均勻地配上七個黑點,頭上有兩個白點,仿佛設計師用亮漆畫上的一般。”而且,在他的筆下,日本的鄉間也不乏我這樣的孩子以及我這樣的孩子參與的某類場景,“被當作卡通或玩具角色的,幾乎都是七星瓢蟲。”
時隔多年,當我看見那只熟識的小可愛在草尖上休憩,或者說在一個美夢中也淌著口水,它的腦袋里會是怎樣遼闊的一片天地?它背的可是北斗啊。我開始將自己慢慢縮小,小得在一粒土上躺著看天,一株稻穗已是我眼里的滿天星斗。我對它的情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我的詩歌里慢慢閃現它們更為動人的樣子,而不是那種被戲耍得翻來翻去的笨重和無奈——“今日不取花香/不付碎銀/今日我邀七星瓢蟲/不醉不歸”(《美妙》)、“我們憨厚的鄰居/住在青椒里/鞘翅目籍貫的/七星瓢蟲夫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看星光下的棉花和果園”(《小王國》)。
一個北方的文友說,他們那里說到“花大姐”都知道是瓢蟲,說瓢蟲未必知道是“花大姐”。這個“花大姐”與七星瓢蟲不一樣,紅褐色,背上有二十八個黑點,每一個鞘翅上有十四個黑斑。其實遠古以來,瓢蟲們過著各自想要的生活,直到人類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在這個世界,連這些無辜的蟲子也被咬牙切齒地類分為害蟲和益蟲。比如泉麻人的經驗是,在二十八星瓢蟲出沒的土地上種植出來的橘子,色彩也顯得黯淡。對此,我還真是不清楚二十八星瓢蟲的能耐。可當我寫下七星瓢蟲照看星光下的棉花和果園時,我又何嘗不是存在一種偏見?夏天,在棉花、槐樹、豆類等植株上,七星瓢蟲們聚集在一起享用蚜蟲。天寒時,它們在小麥和油菜的根莖間、向陽的土縫中越冬。而二十八星瓢蟲因為口味不同,喜歡以茄科、豆科、十字花科等植物為食。說白了都只是為了飽暖的生存本性,才能繁衍后代,這個星球上于是有了千姿百態的生命。
有一天,我捉弄過的兩個小家伙在同一棵植株上相遇了。那時,七星瓢蟲先生正在美滋滋地吞咽著蚜蟲。而優雅的螞蟻小姐看到這一幕,瞪大了眼睛,這些蚜蟲可是它飼養的啊,蚜蟲以植物的汁液為食,經過消化產生帶有甜味的糞便叫蜜露。螞蟻小姐最喜歡這種甜品,它想喝時,就用觸角輕輕敲打蚜蟲的腹部,蚜蟲就可以分泌出蜜露來。眼見七星瓢蟲一大口一大口吃掉它心愛的蚜蟲朋友,螞蟻小姐再也不顧體面,沖上去就和七星瓢蟲大戰了起來……斗轉星移,故事卻這樣年復一年地發生著。
七星瓢蟲與螞蟻,都是我童年的“玩具”,它們有時又會同時在另一種“玩具”上散步,那個“玩具”叫野豌豆。
豌豆·野豌豆
從宋人舒邦佐的“豌豆斬新綠,櫻桃爛熟紅”到方回的“櫻桃豌豆分兒女,草草春風又一年”,可看出豌豆和櫻桃差不多在同一時節。方回是徽州歙縣人,那地理也屬江南。方回估計是個喜歡豌豆的人,我大致翻了翻,寫過好幾首關于豌豆的詩,經常把含桃與豌豆并列。我在猜含桃是什么樣子的桃子、有沒有吃過,一查含桃原來就是櫻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有些名字來得挺有意思。
豌豆這東西,直覺上是從西方引進來的。西漢時的張騫就帶回了苜蓿、芝麻、大蒜、蠶豆以及我非常愛吃的一種水果葡萄。《太平御覽》載:“張騫使外國,得胡豆種歸。”在漢時,最早胡豆就是指豌豆,不過張騫帶回來的胡豆其實是蠶豆,后來經李時珍之類“其苗柔弱宛宛”的描述,豌豆就不叫胡豆了。不過,豌豆和蠶豆都是張騫帶回來的,至于哪個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哪個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帶回就不得而知了。
同是引進物種,豌豆入了那么多的詩句,我有點替花生米不值當。兩者炒熟皆可下酒,但我更鐘意后者。
初夏的時候,又看見了那一大簇花,多為粉紅色,有的近紫色,卻喊不出名字來。湊近瞧一下,還結有許多略扁的青色莢果。
它們根莖匍匐,細柔的莖略斜升有攀援狀,花冠蝶形,最大的一片花瓣像把提琴。我拍了照片,問身邊的朋友。有的說是野豌豆,有的說是苕子,有的說就是《詩經》里的薇,還有一個朋友說它的豆殼可以做哨子。
說到哨子,我大概有點印象了,忘了自己是否以此莢果做過,可以肯定的是見伙伴們這么玩過。事實上,五天以后我就看到了有個孩子用這種莢果做成了哨子,在吹,吹著吹著滑出了嘴巴,她哈哈一笑,門牙掉了兩顆。
豌豆我認識,它的果實也叫青豆,被制作成一種“蒜香青豆”的零食,我還挺愛吃的,脆脆的,又可以佐酒。嫩的豌豆莢(也叫荷蘭豆)清炒一下有點像扁豆,炒扁豆我從小就吃,談不上多愛,也沒覺得討厭,豌豆莢我似乎不愿意接受。還有豌豆苗,已是餐桌上一道時令蔬菜,我聽大多數人都說好吃,我夾過一筷子后,再沒嘗過。那味道說起來別扭,所以口味的事真是麻煩事。我問我媽,我們那以前種豌豆吃豌豆苗嗎?我媽說,很多人家種了吃豌豆苗。可我好像沒見過哪家蔬菜地里種過這東西。我又問,我們家為什么不種?她說,奶奶也沒種過,都不喜歡吃。
所以,豌豆真正的文化之根還扎在西邊。在丹麥,一個叫安徒生的人把豌豆種成了童話。比如《豌豆公主》:一個王子要娶一位真正的公主,但他總是無法判斷哪個是真正的公主。一天晚上,有一個美麗的女子出現了,她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取出二十張床墊子壓在豌豆上,又在這些墊子上放了二十床鴨絨被。第二天,公主告訴大家整夜都沒有合上眼,有一粒很硬的東西把她硌得痛苦不堪。于是大家認定她的確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為,她居然還能感覺得出來壓在這二十層床墊子和二十床鴨絨被下面的一粒豌豆,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任何人都不會有這么稚嫩的皮膚的。又比如《五粒豌豆》:一個豆莢里有五粒綠色的豌豆,它們以為整個世界都是綠的,后來它們成熟了,感覺整個世界都在變黃,它們想出去看看,比比誰走得最遠。它們被一個男孩當作子彈通過豆槍飛射出去。五粒豌豆中有三粒躺進了鴿子的嗉囊里,有一粒落在水溝里,在臟水里躺了幾個星期。只有最后一粒飛到了頂樓一個生病女孩的窗口長滿了青苔的裂縫里,溫和的陽光呵護它發芽了,長出長長的藤蔓,小女孩用一根小木棍支起它、用一根線牽引它,它還開出一朵美麗的花。小豌豆天使般給小女孩帶來了生命的希望與力量,她欣慰地笑了,想著“自己也會好的”。她看著它,自己一天天好起來了。
在中國,豌豆的妙處是給我多添了一種好酒。白酒的原材料無一例外全部都使用谷物高粱、小麥、玉米、大米、糯米等為原料,汾酒的釀造原料除了糧食外多了豌豆。豌豆并不直接用于釀酒,用來制酒曲。酒曲可謂酒的風骨,因為豌豆的融入,汾酒的口感就有了獨特的清香氣味。
我所遇見的那簇花是野豌豆,它被種進了《本草綱目》與《詩經》,它們或充饑,或為中藥。野豌豆有個學名叫救荒野豌豆,一個救荒作前綴,令我肅然起敬,遙遠的苦難似乎還寫在耄耋之年的老人臉上,有刀削斧鑿的凝重,與《本草綱目》里野豌豆又名翹搖完全不是一個樣子:“翹搖,言其莖葉柔婉,有翹然飄搖之狀,故名。”好多人說野豌豆尖可以吃的,我沒吃過,它當然是可以吃的,要不它怎么能救荒呢?至于如何吃法,我也無需多想象了。身邊的人大魚大肉地吃成了“三高”,開始熱捧起野菜來,難得享用野性的清新自然是很好的感受。有一種吃法,說是等到莢果完全成熟后采摘,剝開里面的豆子煮粥或磨面吃。我想饑荒年代誰也不覺得野豌豆有多好吃,起碼沒有一籠蟹黃湯包可口、過癮。
至于叫苕子,好像與野豌豆在微風里輕搖的姿勢沒什么關系,但無論誰愿不愿意,它完全可以擁有這樣的名字。
還有說野豌豆就是《詩經》里的薇,我挺喜歡這個名字。微笑本來就好看,微笑的草就更令人動容。我小的時候見過爸爸同事家的女兒,比我小兩歲,她微笑起來就是好看;我孩子讀小學的第一個班主任,比我大兩歲,她微笑起來也很好看。她倆的名字都叫“小薇”,她們和野豌豆的花一樣陽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剛止”……采薇菜啊,采薇菜呀,薇菜開始發芽了,薇菜已長得柔嫩了,薇菜長得又粗又硬了。一個普通士兵思鄉的哀傷,帶著淚般飄灑在他很熟悉的平時底層人民用來充饑的薇菜上。“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一刻,薇又有了苦難的色彩。
但我聽說,野豌豆是一種很好的牧草,想起成群的牛羊經過,嚼得那么香甜,我會快樂一點。
又過了一陣子,野豌豆的莢果成熟了。我看見朋友家的孩子可可正鼓著腮幫吹哨子,聲音并非特別悅耳,卻獨屬童年。這真是一個乖巧伶俐的女孩,她是怎么用豆莢做了一個哨子的呢?我小時候究竟有沒有做過、有沒有吹過,真不記得了。
種? 子
大概許多孩子都有一個會種香瓜的奶奶吧,而這個孩子也一定特別喜歡吃奶奶種的香瓜,我這開頭一句,或許在我孩子眼里已是一個“病”句,因為我的媽媽沒有地給他種香瓜吃了,他也沒機會見到奶奶的手可以變出許多他喜歡的食物。從前奶奶那塊小小的香瓜地,有我好多個坐在門檻上守望的夏日。小黃花開了,結小果了,繁密的瓜葉間一個個白白的肚皮鼓起來了……摘吧,甘甜的童年。只是,到最后的幾個香瓜,奶奶是決不允許我吃了。
等瓜熟透了,自個兒從蒂上脫落,奶奶會剖開香瓜,取出瓜瓤,將瓜籽洗凈、曬干。最后,用灶膛里的草木灰和些泥土加水拌勻,裹好香瓜種子,一個灰漆漆的泥團黏貼在面對灶口的墻壁上。我一直記得兒時灶披間里那個黑餅狀的糊團,安安靜靜地待在墻上到來年春天又被奶奶取下來,播撒在她那塊小小的香瓜地,然后我的夏天很快就來了。
好多年后我才問起奶奶,為什么要那樣存放瓜種呢?奶奶說了兩個字:保暖。這種古老的留種方式,欣許是她的奶奶教給她的,至于為什么她也許問過,她的奶奶可能同樣告訴了她兩個字:保暖。我依稀感受到了那寒冷冬日柴禾的殘余灰燼從灶口彌散出來的余溫。
從奶奶那里,除了那些直接可以吃的種子(比如花生、玉米、黃豆、赤豆等)外,我還認識了許多鄉間常見蔬菜種子的樣子。我知道那些種子里面最小的種子是芥菜籽,你可能吃過雪里蕻,但你未必認識芥菜籽。
有了對種子的認識,我足夠假設一種生活,那么給我一片荒地我就可以去謀生了。從閑置的茅屋里,我首先要磨亮那些生銹的農具。你看我是如何飛舞鐮刀除去那些雜草的,我自己也不相信一會工夫就把鋤頭使用得得心應手。我的這片荒地初具了畦、壟、埂的輪廓,板結的泥土被敲得松軟,它們的呼吸開始勻暢。我擦了擦額頭的汗水,從腰間解下那個小小的布袋,嗯,該是你們睡醒的時候了。
水稻的種子是一定要帶上的,它會是我黏稠的米粥生存的底線,喝了米粥我才有力氣繼續勞作。糯稻的種子也要帶些,收好谷子囤上一年,岳母曾說陳年的糯米最適合釀酒,有上那么幾缸好酒,我心里會踏實些。麥子呢?起初沒想帶上,我對面食并無太多的依賴,最終抓了一把是因為突然想起秋天月圓的日子要吃幾塊月亮餅,然后想想奶奶活著時給我做餅吃的情景。月亮餅需要菜餡,所以,做餅用的青菜種子會帶上。平日里,青菜可是南方媽媽做得最多的一道蔬菜哦。吃不完的青菜可以腌制咸菜,咸菜下粥對我而言可是美味。黑芝麻種子也要帶些,星星般灑在餅的兩面,嘴巴里會盛下一整個星空的香。烙餅不能少了豆油,所以帶上大豆的種子自然不必說了。
我已經播下了多少種種子?一、二、三、四、五、六。好了,我最喜歡的蔬菜是莧菜,紅紅的湯汁攪拌一下米飯,那是年少時多么誘人的食欲啊,我怎么長大、變老,都深深迷戀著那一抹微紅。“菹有秋菰白,羹惟野莧紅”,陸放翁隨口一句就畫了一個味美的秋天。那就把茭白的種子也取出來吧,我扛了把鐵鍬去荒地西南角挖了個小池塘,雨就下了起來填滿了我的池塘。有了挺拔的茭白,池塘也好看點。魚的種子可沒帶啊,不急,幾只白鷺看見我這里已是一片蔥郁,它們原本去遠處那個湖里捕食,返回喂鳥寶寶時在我這稍息了片刻,它們為這里突然的變化感到驚訝,一不留神,叼著的小魚滑落了下來。有那么兩條垂死的一下子喘過氣來,甩了甩尾巴隱入池塘深處。我笑了,我知道水底藏下了美好的秘密。
人是不能貪心的,我來這塊荒地時準備了十種種子,還剩下兩種了。我先安心地住上一段日子,順便修葺一下茅屋,把堆在屋邊的蘆葦整理整理,編上幾條像樣的籬笆。還有一棵枯了的楝樹就砍了吧,以做過木匠的爺爺的眼光來判斷,它的料子我估摸著可以先打上一張小方桌、兩把小椅子。
我就不需要花種了,有泥土的地方春天總會冒出野花。你看,婆婆納草就快開了,有只鳥飛過拉下的糞便里居然有牽牛花種子,于是它們也醒了,慢慢纏繞上籬笆。戀愛中的昆蟲在周圍飛來飛去。鳥的糞便里總是有奇跡,我希望再來棵樹的種子,因為我還缺一把椅子。
屋子后還有一小塊空地,種點什么呢?我瞅了下屋子里那架老紡車,雖然舊了點,結構還是完整的。那我種下第九種種子棉花吧。等摘棉花的季節快到的時候,會有一個遠方的姑娘愛上我這勤勞的小伙的。
多好啊,夕陽下,我擺上一張小方桌、一張小椅子,斟滿一碗陳年的老酒。菜不多,一碟炒黃豆,幸虧我沒忘帶大豆種子,豆油可以烙餅,還可以炒豆子佐酒,豆子真是好東西,就像自己和自己玩也能玩出好花樣。還有一盤可是當年爺爺最喜歡的下酒菜:油炸鰟鮍。你看,我的池塘里魚兒多得不斷地躍出水面,那幾只白鷺也早已安居了下來。
一口老酒喝下,想起棉花白了,我搬出另一張椅子。有個身影慢慢近了,布衣布鞋,樸素得像我種的棉花的氣息。她愿意坐下來倒上一杯,陪我說說話,陪我聊聊明天……關于第十種種子也許你已猜到了。等我打好第三把椅子,我就要把媽媽接過來一起住了。我來這里時把奶奶留下的那個灰漆漆的泥團從墻壁上剝了下來,等媽媽親手種下它們,會有另一個孩子坐在門檻上等奶奶的香瓜地里那一個個白肚皮鼓起來。因為我也是一顆種子……
每當我嘴角微揚時,我總從孩子的舉動里尋找到當年的影子,就像每當我看見爸爸嘴角微揚時,我似乎看得出他也尋找到了當年的影子。“嘴角微揚”,多美好的短句啊,有著如此迷人的對世間的暫時放松。就像當年奶奶喊我“小接種”時,她干癟的面容上居然也能嘴角微揚。你看——
王老師說,預備,起。張羊羊和一粒粒小種子們昂頭挺胸,雙手背握,開始了最初的《語文》:冰雪融化,種子發芽,果樹開花……光陰“蹭”地一下晃了過去,張簡之和另一些小種子們各自長著當年那些種子們的臉龐,又一個王老師開始說,預備,起……想想這樣一幕的循環,我們大概都在嘴角微揚了。
菜花鱸
里下河離我出生的地方并不遠,一江之隔。我見有人列過那邊的一份四時魚鮮的食單:一月的“糊涂呆子”(塘鱧)、二月的季花魚、三月的甲魚、四月的螺螄、五月的白魚、六月的鳊魚、七月的昂嗤魚、八月的雜魚、九月的鯽魚、十月的螃蟹、冬月的鰱魚和臘月的青魚。
這個單子有點“糊涂”,螺螄與螃蟹不是魚,八月的雜魚則包括了許多魚。
菜花鱸與鱸魚沒有關系,和里下河的“糊涂呆子”是同一種魚,指塘鱧魚。魚不大,胖嘟嘟的,看起來卻有點兇,體形粗壯,前部渾圓,頭大稍扁平,有些地方喊“虎頭鯊”,像袖珍版的黑魚。我們這喊它“刺鯱”或“癡咕頭”。這種魚屬于底層魚,常伏于水底,所以往往耥螺螄時也能耥到。
刺鯱與鳑鲏兒時常見,奇怪的是,小鳑鲏魚常常將其掐去頭、捏去內臟,油炸一下撒些鹽,成了一盤很美的下酒菜。刺鯱似乎從來不吃。袁子才在《隨園食單》中曾載:“杭州以土步魚為上品。而金陵人賤之,目為虎頭蛇,可發一笑。”說的也是這種刺鯱,可見杭州人以為的上品魚,在南京人眼里就不起眼了。
這兩種小魚對水質的要求很高,于是慢慢少見了,刺鯱也漸漸珍貴起來。雖說不是很貴重,數量遠遠不比以前。袁子才說這種魚“肉最松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腌芥作湯,作羹,尤鮮。”有年我給小鎮嘉澤寫本書,常去一個叫“慶蘭樓”的小酒館吃飯,那個店里能吃到油炸的椒鹽鳑鲏,刺鯱則是清蒸或紅燒,但最常見的是燉蛋時放幾條下去,蛋更鮮,魚肉更嫩。
國宴中有過一道“薺菜塘鱧魚”:以塘鱧魚片、薺菜茸為原料,采用春末夏初上海特有的野生塘鱧魚與地方野菜做成。每條塘鱧魚都不超過二兩,將小魚去骨去皮,只取其中的兩片(據說用去750條塘鱧魚),切成魚片上漿滑熟,然后放入剁碎的野生薺菜茸,勾的芡剛好讓魚片漂浮在碧綠的菜茸上面。
這道菜我只能遙想一下,咽幾下口水了。可與此相媲美的是一道“葷豆瓣”,即塘鱧魚雙頰上半月牙形的腮幫肉兩粒。需將魚頭蒸至半熟,用竹簽將腮幫子撥開,挑出完完整整的一粒半月芽形“豆瓣”肉。一小碗“葷豆瓣”其用量,據宋代《玉食批》記載的“土步辣羹”:耗魚一百零八尾,得“豆”二百一十六粒。
太湖快禁捕了,一禁捕就是十年。這十年怕是刺鯱更為少見。不過,經過十年的孕育,太湖的肚子會越來越滾圓。
刀? 魚
鳥有一種飛翔叫遷徙,魚有一種游泳叫洄游。這些都是生存繁衍里艱難又美好的旅程。淮揚菜有“醉蟹不看燈,風雞不過燈,刀不過清明,鱘不過端午”之說,指吃醉蟹和風雞最好是在農歷十二月,吃刀魚最好在清明前,清明后刀魚刺硬味差;吃鱘魚最好在端午節前,端午節以后,鱘魚就會洄游大海。
小時候清明前的刀魚很貴,常常是清明過后買刀魚吃。魚肉雖還算鮮嫩,魚刺硬了,吃起來很麻煩。所以鄉黨趙甌北一直有個美好的心愿,他寫《鱽鲀》:“河鲀有毒鱽魚刺,至美中偏不美存。夜夢忽然來報喜,鱽魚骨變作河鲀。”
我最后一次吃到野生刀魚,大概是十年前了。我的散文集《庭院》要搞個首發式,責任編輯鮑伯霞阿姨從天津過來,我一個老同學在長江邊請我們吃刀魚。四個人四條刀魚,都是二兩不到的,魚肉與魚骨分開來兩吃,魚肉清蒸,魚骨油炸。一個入口一抿即化,一個細嚼松脆,那個魚吃起來真是享受。
這就是真正的江刀。
在東營,我吃過所謂的“河刀”,即黃河刀魚。做法似是煎過后糟鹵,切塊作涼菜,口感像酥帶魚。黃河刀魚也叫梅鱭。
太湖刀魚我常喊“湖刀”,實際上當地漁民都喊梅鱭魚。黃河刀魚與太湖刀魚品質差不多,一個做成酥魚,一個是清蒸。
黃河刀魚、長江刀魚、太湖刀魚,都叫刀鱭。但江刀是清明前最好吃的。所謂的刀魚餛飩,我想是不會舍得用清明前的刀魚作料,應是河刀、湖刀之類,去刺洗凈,做魚丸子或餛飩餡。
秋刀魚與刀魚沒什么關系。秋刀魚適合油煎或燒烤,口感雖粗糙,卻也深得人們喜愛,讓我想起小時候的青占魚的味道。我搞不清楚那時水鄉的魚類極其豐富,但老是迷戀紅燒青占魚的粗糙,吃起來還十分下飯。
刀魚要春天吃,春天有燕筍,沒有幾片嫩綠又透點兒黃的燕筍,怕是要失色幾分。
鱖? 魚
里下河二月食單上的季花魚,我們是排到了三月吃。季花魚就是鱖魚,“鱖”我們常寫成“桂”。鄉下一直喊“鯚婆子”,一般的河塘并不多見,偶爾也會釣到。背鰭一豎,一排棘在抖動,再看那尖銳的牙齒一張一合,紅著眼充滿敵意,我是怕它的。
海中梭、江中鰣、河中鱖,鱖魚當然是很好吃的。那種“松鼠桂魚”我嘗過兩口后,再也不碰一筷子。魚一糖醋就不好吃了,再說把桂魚做成松鼠狀,番茄汁一淋,看了就不習慣。
也有將桂魚去骨切薄片,放打邊爐燙了吃,或者與羊肉片煮一鍋魚羊鮮,新鮮的桂魚當火鍋一樣吃總覺著不是那么回事。
我喜歡吃金花菜蒸鱖魚,清清爽爽的顏色,整條魚睡得那么香,湯汁篤到奶白色,味道極其鮮美,且刺少肉多。
徽菜有道“臭鱖魚”,多年前吃到后,倒是令我念念不忘。聞起來臭,吃起來覺得其很香很嫩。幸好,我們這個地方也有很多徽菜館,時常可以去吃到。“味廬”餐館做的臭鱖魚,形態完整,散發出純正、醇實的腌鮮香味,肉質細膩,微辣又富有彈性。
張志和的詩不多,那句“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卻是寫得非常唯美的。我不曉得這位本家是看風景呢,還是想吃鱖魚,可能白鷺也想吃吃。一盤清蒸鱖魚,一盤紅燒白鷺,只是唐代的醬油品質估計還不是很好。
鰣? 魚
張愛玲有三恨:“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夢未完”,她將鰣魚多刺列為人生第一恨。至于她對鰣魚有多愛,各自去體會吧。鰣魚出水就死,有段相聲中說到一天色變、二天香變、三天味變,其實一天就色香味都變了。當年鰣魚是貢品,沒有飛機與高鐵,兩千里路三日內送到,怎么辦?張能鱗《代請停供鰣魚疏》中描寫了運送鰣魚的情況:“鰣產于江南之揚子江,達于京師,二千五百余里。進貢之員,每三十里立一塘,豎立旗桿,日則懸旌,夜則懸燈,通計備馬三千余匹,夫數千人……故一聞進貢鰣魚,凡此二三千里地當孔道之官民,實有晝夜恐懼不寧者。”那年月,帝王們干了好多“紅塵一騎妃子笑”的大事。
至于鰣魚的吃法。先讀到清人顧仲的《養小錄》,有“蒸鰣魚”:鰣魚去腸不去鱗,用布抹血水凈。花椒、砂仁、醬擂碎(加白糖、豬油同擂,妙),加水、酒、蔥和味,裝錫罐內蒸熟。
后來讀到清人朱彝尊的《食憲鴻秘》,也有“蒸鰣魚”,幾乎一字不差:鰣魚去腸不去鱗,用布抹血水凈。花椒、砂仁、醬擂碎(加白糖、豬油同擂,妙),水酒、蔥,錫鏇蒸熟。
顧仲是醫生,飲食注重養生,從兩人年齡來看,若是抄食單,顯然是顧仲抄了朱彝尊的。朱彝尊除了蒸鰣魚,還有糟鰣魚(內外洗凈,切大塊。每魚一斤,用鹽半斤,以大石壓極實。以白酒洗淡,以老酒糟略糟四五日,不可見水。去酒糟,用上好酒糟,拌勻入罈。每罈面加麻油二鍾、火酒一鍾,泥封固。候二三月用)、淡煎鰣魚(切段,用些許鹽花、豬油煎。將熟,入酒漿,煮干為度。不必去鱗。糟油蘸,佳)。
再說袁子才,他吃鰣魚是用蜜酒蒸食,如同烹制刀魚之法就很好;有的直接用油煎,加清醬、酒釀也不錯。千萬不能把魚切成碎塊,加雞湯煮;有的人剔掉魚背骨,只取魚腹,那么鰣魚之真味就全沒了。
明人陸容在《菽園雜記》中稱:“鰣魚為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為瘟魚,不食。”夏曾傳在《隨園食單補證》中搜集了很多資料,其中有《升庵外集》:“江而西謂之瘟魚,棄而不食。”這個有點像杭州人眼里那么好的刺鯱遇到了南京人。夏曾傳還提到,鰣魚清腴之品,用甜味殊為掃興,油煎之法尤難,聞吳中有能為燒烤者,先大夫曾遇之。
我倒覺得烤鰣魚味道應該不錯。無論何種做法,似乎鰣魚不去鱗是常識了,鰣魚之味美在于皮鱗之交。
許多年前,蘇東坡大飽了江南水中珍品鰣魚的口福后感嘆:“芽姜紫醋炙鰣魚,雪碗擎來二尺余。南有桃花春氣在,此中風味勝莼鱸。”讀這詩就挺饞的;許多年后,若想品嘗野生刀魚、鰣魚、河豚此長江三鮮已經近乎奢望,諸如鱗白如銀的外形和骨軟如綿的內質皆變成了一代人的美好記憶。
鰣魚每年四五月份進入長江產卵,到九十月份再回到海中,年年準時無誤,故稱鰣魚。雖說二十年來,我每年都能吃上鰣魚,卻不是蘇東坡吃過的鰣魚了,也不是袁子才、朱彝尊吃過的鰣魚了。
至于原因,無非是泛濫捕捉以裝胃這只無底的口袋所致,即便瀕危禁捕,仍有漁民經不住高額利潤的誘惑甘作食客的幫兇。加上一些樞紐工程的興建,阻斷了鰣魚的產卵洄游路線。于是成了如今現狀:我國從2002年起,從美國引進了鰣魚,當時引進的是魚卵,一粒魚卵賣到一萬元人民幣,再加上其他成本,“到岸價”高達兩萬元人民幣。
拆? 肉
肉這個字自成形到現在的簡體結構,在大多數人眼里有著異彩的視覺效果。我認識好些人,幾乎一天都離不開肉,一盤肥而不膩的紅燒肉端上桌,他們吃肉的歡愉簡直可以用個“吞”字。切成大塊的肉叫胾,切成小塊的肉叫臠,北方人喜歡大口吃肉,南方人可能多偏愛膾、炙那種細條的肉。“人曰肌,鳥獸曰肉”,從前猛獸也大口享用著人類的肌。至于果肉,那是北方人和南方人都喜歡的肉。
拆肉,確切地說叫拆骨肉,兒時的一道尋常美味。從煮熟的骨頭上拆下來的肉,蘸點兒醬油或爆炒一下,近乎原味,不過也只有到快過年時才能吃上。近來我聊起為什么有拆肉這樣的吃法時,我媽一句“那時不太懂得去熬骨頭湯”的說法有點讓我匪夷所思。
豬蹄切塊文火燉好,加入肉圓和條狀的肉皮,可以做成一大碗常州人喜愛吃的“老三鮮”。這道菜的做法談不上復雜,但一塊豬皮曬干后用溫油炸成金黃酥脆的肉皮的過程,也遠沒有熬碗骨頭湯喝簡單。然而仔細一回想,那時的餐桌上真沒有見過煲骨頭湯時再放幾塊白蘿卜的做法。奶奶沒做過,媽媽也沒做過。好好的骨頭不曉得去熬湯,這可能只是蘇南平原上一個小小角落里才有的事。就像在另一角落的居民未必曉得肉皮會有這樣的吃法。飲食這個事,有傳承也要有會搗騰的智慧。
我糾結的是,那么多的骨頭熬了一鍋湯,湯就倒掉了嗎?我媽的回答沒我想的那么奢侈。骨頭多,熬到最后的兩缽湯已經非常濃厚,加上天寒地凍,一缽湯的三分之一已經凝結成厚厚的類似豬板油一樣的白色油脂。那時可以供給于日常的豆油、菜油實在太少,媽媽們怎么可能舍得丟棄呢?平時炒青菜、炒白蘿卜都撇上一勺這些的油脂,于是那些青菜、蘿卜又變得口感豐腴了起來。剩下的三分之二,媽媽又用來或煮粉絲湯或煮面條或篤咸泡飯,反正不會浪費一絲絲好東西的。
再說白蘿卜成熟的季節,吃來吃去就是光蘿卜自個兒在鍋里翻身,偶爾也會見上和肉煨在一起,那大概是節日了。那么多的白蘿卜去哪了?除了腌制蘿卜干,就是喂給豬吃了。
以前的豬,伙食可好了,除了白蘿卜,還有胡蘿卜、山芋藤、水花生、紅花郎……各種各樣的時令食物。即便這樣,養上三四個月,也就一百七八十斤,不像現在的豬,困在一個鐵格里不知吃的是什么東西,動輒就長到三百多斤。所以,兩種豬肉的味道,可以吃出哪頭豬是快樂的,哪頭豬是不快樂的。
我們那大多數人家的豬圈只養兩頭豬,一頭豬賣了換錢,一頭豬宰了過年。每年臘月廿四、廿五時,蒸饅頭、做豆腐、殺年豬共同釀起了過年的氣氛。隨著殺豬佬手起刀落,“呱呱”亂嚎的豬冒完最后一口熱氣,大人們忙活起來,小孩們的口水也慢慢豐盈起來。
像豬肝、豬肚、豬肺、豬腸、豬心之類的下水是不能腌制的,基本上在年前吃完,于是那幾日餐桌上尤其豐富,鹽水豬肝、爆炒豬肝、肚肺湯、大腸篤豆腐等等,我們的嘴唇總是油亮油亮的。像豬頭、豬尾、豬蹄以及大部分豬排、豬肉就腌好,慢慢吃,最后一塊咸豬肉吃完時,已是來年的蒔秧季節。
而我念念不忘的,則是那些剜下來的豬扇骨、豬筒骨、豬脊骨,一股腦放進土灶的里鍋(三口鍋中最大的一口,平時用來煮豬食的)慢慢燉起來。兩三個小時后,柴火的余燼逐漸黯去,系了圍裙的爸爸揭開鍋蓋,我依然記得那些騰騰熱氣涌出來霧一般籠住四十瓦的燈泡時的美妙場景。爸爸撈出一塊骨頭,利索地拆下幾乎離骨的肉,每拆兩下就甩甩手蘸下涼水,那滾燙的幸福的溫度。等把骨頭全部拆完,一大臉盆的拆肉就擺在了灶頭。我試著拆了下,燙得我連忙用嘴巴吹都不濟于事,拇指、食指和中指都紅腫了,于是再沒拆過。那時候仰望爸爸,一塊小小的拆肉塞進嘴時才覺著拆一鍋肉也是件大事。
骨頭們丟進院子里,草狗“小嘿”的節日也來了,它搖頭晃腦,眼里充滿了喜悅,趴在那“咯嘣咯嘣”響上好幾天。它的牙齒真好啊,在我牙齒非常好的時候,就感嘆它的牙齒實在是太好了。我懷疑,那些骨頭擺在現在,住在八樓或十樓那些穿裙子、系圍脖的狗們還啃不啃得動。
剛拆好的肉裝上一盤,爛乎乎的,蘸點鹽或醬油已十分入味,吃起來就特別滿足。爸爸佐酒,我和妹妹下粥。因天寒的緣故,第二天的拆肉就得炒著吃了。最好時節的青蒜葉,二三十厘米,洗凈切段,一把撒下去,屋子里都溢滿了香味。
后來也去過一些地方吃的拆肉,是將豬頭蒸熟后拆下來的肉,用辣椒爆炒后吃。我并不多鐘意這樣的吃法,于我,豬頭腌制后蒸了吃,很是愜意。
三十來年沒吃過那種拆肉了,離開村子離開土灶離開大鍋,也沒有養過豬。平時買了豬棒骨、豬脊骨、豬筒骨回來,只習慣用以熬湯,要么放點白蘿卜,要么放點黑木耳,似乎與小時候的做法完全切斷了關系。現在過年差不多和平常一樣,所謂的年味也輕飄飄的。年味,年味,得有點味道,那味道好像還在那個四十瓦的燈光下、爸爸揭開煮大骨頭那只鍋鍋蓋的一瞬間,我和妹妹齊刷刷地盯著他忽上忽下地拆著一塊塊肉。那味道飄了幾十年,飄得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爸爸已忘記了。寫著寫著突然發覺,我不是挺傻嗎?那些買回來的骨頭們為什么一定要熬湯呢?
比如,又快過年了,我也可以在廚房間用一只大點的鍋把它們煮起來,煮上幾個小時,系上圍裙,每拆兩下就甩甩手蘸下涼水。孩子像當年我看爸爸那樣看著我。裝上一盤新出鍋的拆肉,蘸點鹽花或醬油,爸爸的眼神又亮了起來。可不可以說,三分之二的年味回來了呢?一直喝慣了骨頭湯的兒子,第一次吃上了拆肉。
霜
霜快起時,青菜最初就知道了。青菜怕冷,它為了取暖越冬,將身體內的淀粉類物質轉化成糖分,它的細胞液就不容易被霜凍壞了。被霜打過后的青菜,味道就變得甜甜的,尤其受人喜愛,這個也叫“霜打菜”。
我小時候住的屋子前,有一畦畦這樣的霜打菜,夠吃上一個冬天。
霜與瓦,像人與狗,是一種古老的溫情結構。瓦不是指現在的斑斕的琉璃瓦,而是那時黛青色的瓦,它有著迷人的舊。秋末冬初之際,一層薄霜鋪在瓦上,毛茸茸的,常年被風吹日曬的瓦終于可以有了休憩的片刻,仿佛蓋了床被子,終于可以睡會了。溝瓦凹,瓦頭向上瓦尾朝下;蓋瓦凸,瓦尾向上瓦頭朝下。凹凸相扣,鱗次櫛比,這情景被詩人看見了,會用上四個字“霜瓦鱗鱗”。于是,“瓦上霜”似乎成了一個固定的詞。
我可能像陸游,尤其喜歡瓦上霜這一道風景。陸游在《初冬》里的表述極為直接,“絕愛初冬瓦上霜”。他也是吃過不少苦的人,在《咸齏十韻》就袒露過自己的儲備憂患意識:“九月十月屋瓦霜,家人共畏畦蔬黃;小甖大甕盛滌濯,青菘綠韭謹蓄藏。”陸游對霜的喜愛也不是隨便說說的,在《聞笛》里有“雪飛數片又成晴,透瓦清霜伴月明”句,他甚至還有句子只改一字,《落葉》里便是“萬瓦清霜伴月明,臥聽殘漏若為情。”可能對瓦與霜的結構愛得過了,轉身在《梅花絕句》里再有“萬瓦清霜夜漏殘,小舟斜月過蘭干”,到最后在《讀》詩中感嘆人生易逝也用了句“人生忽如瓦上霜”。
雖然學過多年物理,卻一直存有霜與雨雪一樣的錯覺,從天空洋洋灑灑而下,落在柳枝、蘆葦以及矮草之上。就像多年來把霜降等同于降霜一樣,實則這個時節的天氣還不夠寒冷到水汽凝結成這種白色晶體。古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為務農歲序,秋曰霜降,萬物收縮,而農事已然收成。段玉裁在《說文》以霜為喻,既是萬物喪失,也是成就萬物之征。
自古以來,很多人喜歡雨、喜歡雪,即便哆嗦著也能看到幾分暖意來,五字一句、七字一句,冒也冒不完。唯獨霜,總帶了幾分冷色調。好好的美女偶有不開心的時候,得說她冷若冰霜;好好的小伙子恰好連續遇到兩件糟心的事,得說他是雪上加霜。這霜似乎變成了一種陰影。
霜這個字唯一給我帶來暖意之事,是小時候因為天冷干燥,長了一副“蘿卜絲臉”,媽媽會用熱水為我捂會面孔,用食指從扁圓形鐵盒中一層薄薄的錫紙下面掠出一種叫“百雀羚”的霜,細細地涂抹在我臉上,還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盒子上是四只鳥的圖案,什么鳥我記不起來了,其中有一只應當是燕子吧。這種霜產自上海,那時連城里都沒去過,別說是上海了。這可能是我兒時僅有的護膚品,甚至有家里買不起“百雀羚”的同學會羨慕地聞著這香味。多年以后,我好像少有被凜冽寒風吹割的日子,久居溫室,長不出“蘿卜絲臉”了,雖然皮膚易干燥,天一冷臉上會起白屑,卻不用任何潤膚之物。只是常想,那些如“百雀羚”之類的物品為什么要叫霜呢?面霜、眼霜、防曬霜……玻尿酸、甘油、氨基酸、膠原蛋白、維他命原B5、AHA,原本物理的霜落于萬物,現在變為化學的霜涂滿肌膚。“百雀羚”已少見,我的愛人也不用這個牌子了,它曾在民國時期十里洋場陪伴過阮玲玉、周璇、胡蝶等佳人的芳華。以致幾年前看到一張“百雀羚”的宣傳海報,一個老上海名媛托著一只經典的“小藍罐”,下面的兩排字讓我有點百感交集:愿你走出半生,歸來仍是少女。我也想著買回一罐來,找個機會再吹出一張“蘿卜絲臉”,用這霜涂抹涂抹我這差不多也飽經了點風霜的臉。
有一種菊科植物叫五月霜,有一種茜草科小灌木叫六月雪。五月霜只是在北方見過幾次,并不起眼。六月雪我養過兩回,沒伺弄好,后來就枯了。
五月降霜、六月落雪,看起來都緣于大冤之事。實則極端天氣越來越多,沒什么可奇怪的。張岱的《夜航船》有詞條“五月降雪”——《白帖》:“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系入獄。衍仰天而哭,五月為之降霜。”這個事《論衡》《后漢書》《淮南子》《昭明文選》等均有記載。許多詩句也用了這個典故,包括李白《古風三十七首》里的“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李白有時挺沒意思的,在另一首《上崔相百憂章》又提“鄒衍慟哭,燕霜颯來,微誠不感”。賜金放還出長安時,你不是寫了“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嗎?好好喝酒便是,想那么多干嘛。
漸漸地,燕霜一詞成了蒙冤之典。
天還未亮,河岸邊的蘆葦一片蒼黑,深秋的白露,已經凝結成寒霜了;天已微亮,河岸邊的蘆葦一片凄清,未干的白露,還在葦葉之上;天已大亮,河岸邊的蘆葦泛出白光,深秋的白露,所剩無幾了。《詩經·蒹葭》說的是北方一個清晨,露水在葦葉上變化的故事。這幅景象,我在南方一個村莊旁的小河邊也能常見,只不過是氣候的緣故,季節略微比北方要推遲些。
二十四節氣的表意是很美的,但有些較為約莫,比方說霜降時,霜未必就已來臨,小雪時,雪未必就落了下來。
關于霜,我最愛的還是庾子山那句“霜隨柳白,月逐墳圓”里古老中國的清寂氣息,這氣息在一千多年后,我依然能夠嗅到。雖然霜附在光禿禿的柳枝上,而不是外婆采摘用來裹粽子的蘆葦葉上,我還是寫下來“外婆的粥碗空了/墳頭一篩霜降”,而且篩得那么均勻,仿佛外婆從泥土里跑出來親自篩的那般。北宋晏幾道有詩“天邊金掌露成霜,云隨雁字長”,這一句有了庾子山之句的妙。霜與云都有可托付之物,那是柳與雁。
可無論如從李白“疑是地上霜”“我無燕霜感”,還是蘇軾“鬢微霜”到“鬢如霜”,無論從張繼看到“月落烏啼霜滿天”還是杜牧看到“霜葉紅于二月花”,霜已是漢語長河里涌動不歇的流水,我們該擁有“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活法。
霜降過后一周,因有事去鄉間幾日,見那些蔥郁的紅蘿卜纓子、白蘿卜纓子、山芋藤時,心里很是盈實。尤其看到壟間一茬茬的青蒜葉和憨厚的大頭青,我只想著三個字“等霜來”,等霜抹過你們的身體,那滋味就更是妙極了。
代課老師
你還好嗎?六歲那年的某個雨天,爸爸突然對你說,你該去上學了,說完就把你舉起來,騎在他脖子上,你哭嚷著不愿去,十來分鐘后你已坐在了鄉村小學簡陋的教室里。你周圍是一張張陌生的臉,媽媽在教室外面打了半個月的毛衣陪你,你終于乖了,也喜歡上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梅村小學,大概是十幾個小村莊的中心地,你的同學們從家到學校差不多都只要走上一里多地。你們是好孩子,大風大雨將傘刮翻成了碗狀還可以小草般搖晃著來回在鄉間的小路上。
你永遠記得第一個老師姓李,扎兩條辮子的女的,不是很好看,皮膚也黑,卻有清脆的嗓音,從“a、o、e”開始教你發音,并讓你學會了第一首兒歌“小兔子乖乖,把門開開”,從此你也知道了世間還有一種動物叫“大灰狼”。
系上紅領巾,在國旗下行注目禮,背誦“五講四美三熱愛”,你慢慢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你的左胳膊上別上了“二道杠”的標志。那個白色的牌牌令多少孩子和家長羨慕啊。
你想起那個“二道杠”卻是在三十年后。那天,你和那些長大了的小臉蛋去相聚,巧遇一位正好做了服務員的女同學,她站在你們旁邊,其他人都讓她來倒酒、敬酒,你卻一聲不吭,給她斟上一杯酒并給了她一個真誠的擁抱,讓她坐到同學中來。這個多年未遇的女同學對你說了一聲:“還是老班長好。”四十歲了,你百感交集,轉身偷偷抹掉兩滴淚。
你的小學老師加起來好像也就七八個,一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鄉村還流行“供先生”,所有老師在全校學生中挨家挨戶吃午飯。基本上每個學生一個學期輪到一次,自家地里的蔬菜為主,但作為對老師的尊重,那天總歸還是會割塊肉、買條魚的。你的爸爸是唯一一家鄉辦廠的廠長,你還有個妹妹,所以“供先生”會連續兩天,你的爸爸會比別人家多添兩道菜。雖說那時候沒什么好菜,看起來好像更豐富、更熱情了點。你的爸爸做得一手好菜,每次還會雕只紅蘿卜,像花一樣,擺在桌子中間,日子清貧,仿佛也精致了點。
老師們似乎特別關心你。他們分別教你語文、數學、自然以及沒有課本的音樂、體育、寫字。有的教了你一年級、二年級,有的一直教到你六年級。你現在熱愛寫作,應該還是因為四年級的語文老師戎老師,在他布置的一篇八百字的作文里,你居然用了二十一個成語。雖然你已經不愛使用成語了,當年一個用了二十一個成語寫作文的孩子,從此每篇作文都成為范文在教室里讀,你愈加珍愛書桌上那本表哥送的別人沒有的《成語詞典》,褐黃色的封皮,綠顏色的書名。
你的小學老師不多,記得最深的卻是兩個代課老師,他們沒有其他幾個民辦老師的待遇好。
一個是數學老師,姓管,你所有小學老師中唯一一個有高中學歷的人,你可能是他最鐘愛的學生,每次期中、期末考試,時間剛過半,你就會放下筆,手托了下巴看著他,等他發現你的這個動作,他就會朝你走來,拿起你的試卷掃幾眼后對你說:“你可以回家了。”你看似從容地把文具盒整理點響聲出來,收拾好書包,在同學們的集體羨慕中走出教室,然后興奮得撒腿奔跑,你的假期起碼比別人快來了半個小時。也有一次,管老師在拿起你的卷子后,例外地重新擺回你面前,輕聲說了句:“再檢查檢查。”你縮回收拾書包的手,糾正了一道答錯的題,那個題的答案像個紅著臉的男孩。
還有一個是語文老師,姓劉。你見他忙農活的時候比你見他上課的時候還多,扛了把鋤頭,挑了擔大糞。他個子高,扁擔上的谷物捆得比一般人都結實。他很得意一手粉筆字,在黑板上將筆畫劃得“吱吱”響,再用左手一捋頭發頭一甩,他的頭發其實禿掉了很多。他總是叫你回答問題,然后再好好表揚一番,看得出他對你這個班長很滿意。而你也是個傻瓜,他把成語寫錯一個字,你舉手,他讓你站起來。你說哪個字應該怎么寫,他很尷尬,臉繃得紅紅的,支支吾吾著說:“好,你坐下吧。”等他把成語的意思講完,你又舉手了,他故意不讓你站出來,擁有一本《成語詞典》的你愈加有勁,胳膊舉得高高的,他沒辦法,只能讓你再起身,你把成語的正確含義說了一遍。他頓了頓,對同學們說:“還有半堂課,大家自習。”課后,他把你叫過去,臉色很不對,你還據理力爭,他只吼了聲:“以后再這樣,把你的班長撤了。”四十歲了,你知道你當年錯了嗎?
小學快畢業時,你聽說管老師病了,肝炎,問家里要了五塊錢,約了其他五個成績好的同學,湊到了三十塊錢,在小學門口一個戲樓下的小副食品商店買了五樣東西一起去看他。買的東西你記不全了,只記得有一包紅糖,一條“紅河”牌香煙好像倒花了二十多塊。看望一個病人,給他送香煙也不知道怎么想出來的。管老師后來把你喊過去,批評了你一番,但很溫和,大致是你們還是學生,不能亂花家里的錢。完了,卻從一只老式的破黑皮包了取出六本精美的日記本,讓你轉送給其他同學。那本日記本后來累積了你第一本詩集的手稿,可惜,找不到了。
很多年以后,你回那個出生的地方,總能碰到劉老師。他還是那么壯實,除了頭發幾乎禿掉,對你的微笑也變得光溜溜的,卻很真誠,他興許已忘記了當年和你關于一個詞語引發的小沖突。你也遇見過幾次管老師,每次他都和后來娶的師母在散步,臉色看起來很是不好。再過幾年,聽說他死了,得了肝癌,你聽說了也沒見得有多難過,只是回想起一件對不起他的事。你小學的時候,有次和同學一起放學,那個同學對你說,常看見管老師和于老師一起去她家,不會做那個事吧,你說他們是軋姘頭。第二天,管老師找那個同學去訓斥了一番,管老師怎么會知道呢?哎,生生不息的告密文化,那天你和同學瞎聊時,同班另一個女同學從身邊經過。管老師怎么沒找你呢?那個同學是差生。
你的小學老師過世得差不多了,活著的剩一個還是兩個?你終于有時間想起他們,一張張臉地找,你不怎么看得清楚了。最清晰的,是你坐在課堂里,一邊聽老師上課,一邊看著窗外的泡桐花,那花朵,多像下課鈴快敲響的鈴鐺。
放蜂人
玩昆蟲是小時候的樂趣,但胡蜂例外。數月前,我漫不經心地晃蕩在小道上,感覺有個細小的影子俯沖過來,下意識地甩出右手胡亂拍打了幾下,糟糕的是,一只胡蜂揚長而去時我的右耳垂火辣辣地疼起來,再摸摸,腫脹得圓鼓鼓的了。按理說,我根本沒招惹它,頂多從一棵樹下經過而已,而這棵樹上沒有蜂巢,也就談不上是它的家,難道它認出了我就是那個三十幾年前淘氣地用竹竿捅掉它老屋的孩子?哎,事隔這么些年了,與被它追著跑的地方也相隔近百里了,第二次被胡蜂蟄到,童年的陰影仿佛伸出手來,與這次的陰影好好握了下手。我想,有生之年,定要躲你們遠遠的。
而有一種蜜蜂其實很乖,它在我的詩里細聲飛舞著:“1985年的平房/小雨梳著它/黛色的頭發/青磚墻上有個洞小了點/那只肥蜜蜂/嗡嗡叫喚/總也擠不進去/我坐在門檻上/小手托著下巴。”這種蜜蜂不蜇人,我時常用一根細竹枝塞進墻眼里,輕輕地探,輕輕地撓,它就惱火地扭著肥身體慢慢爬出來,悶著頭鉆進了我早就準備好的小瓶子口中。那個辰光,平原上的油菜花正金黃透亮,從未聽說過一個人還要趕很遠的路去看一片油菜花。相反的是,總有一個人或一對夫婦拖著長長的木板車來我們這住上一陣。那些天,只要發現周圍的蜜蜂突然多了許多時,放蜂人就來了。
木板車上裝滿了蜂箱和簡易的鍋灶用具,待油菜花地旁空地上簡陋的棚子搭好后,他們臨時的家就安好了。蜜蜂就像聽話的孩子,圍著它們轉。那時我就在想,院子里的、籬笆內的東西都是有名有姓的,即便是一塊塊莊稼地,雖然沒有標好主人,也知道哪塊是哪家的。只有這無數的花粉,無論在院內還是院外,都無名無姓,誰也管不著,只有風與蜂在用最好的方式成全它們。
我喜歡看放蜂人,喜歡看他們臉上蕩漾得快要淌下蜜的笑容,喜歡他們在我旁觀時伸出的那根并不很干凈卻掠過蜜后香甜的樸素的手指,多年后,似乎還在擦拭著我的嘴角。而我,叫不出他們的名字,甚至沒有一張臉是清晰的了。我讀瑞典作家拉斯·古斯塔夫松的小說《養蜂人之死》,還記住了從小學教師轉行而來的養蜂人叫維斯汀,他在黃色筆記本上記下:“一個蜜蜂社群死去時,感覺差不多是一頭動物死了。那是人會思念的有個性的存在,幾乎像思念一只狗,或至少是一只貓。人對一只死去的蜜蜂完全無動于衷,人不過將它掃開。”我看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養蜂人》時,也記住了在一個失戀少女的身上重新有了對生命存在的確定的養蜂人叫斯皮羅,當短暫相聚后少女再度上路,他很傷感,覺得沒有什么可以依戀的了,于是在陽光下打開了所有的蜂箱。
我卻沒有記住一個見過的放蜂人的名字。
而在我四十四歲這年,有次與媽媽聊天時,她提到了一個人,一個名字。至于那天我們說起了什么話題,我一時記不起了。有些東西就是來得那么偶然,若沒有她無意間說到,那么我就不知道這個人曾經存在過,其實這個人存沒存在過,與我也并沒有太多的關系。但正因為一些無意,就像一星油燈的火舌,輕柔地反復舔著我的腦子,讓我覺著有沒有可能試著用文字找找那些模糊的歲月、模糊的影子。
媽媽提到的這個人,不知道哪年出生的,也不知道哪年過世的了。我總是心疼那些生卒年不詳的女子,她大概擁有過許多才情,在那樣一個過去的年代里曾好好地燦爛過。至少,我想在我一篇短短的含糊的文章里,給她豎上一個墓碑,讓我這樣一個多少有點血緣的晚輩,通過方塊字組成的石頭,給她刻下一個名字,那么這個世上她曾來過。
這個人的名字叫孔鳳英。
我的外婆叫孔美英。是的,媽媽說的這個人就是外婆的妹妹,我的姨婆。
張家村與孔家村現已合并為同一個村子——梅林村。那年,張家村緊挨著孔家村,之間相隔一條窄窄的水渠,小學路上,我一只腳還踩在自己出生的村莊,另一只腳已踩到了外婆出生的村莊。外婆娘家斜對面不遠處有一座破敗的孔廟(梅林孔氏于明泰年間(1450—1457年)遷居于此,這座孔廟是孔氏第六十一代孫孔宏鏜遷移到此時建造的),里面堆滿了附近鄉鄰用的柴禾、稻草和麥秸。外婆的童年時代還在民國,那時這座孔廟應該還是好好的,至于什么樣子我是無法想象了。外婆入不了家譜,她的兄弟是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孫。
外婆活著的話,一百零二歲。她屬雞,媽媽也屬雞,她比媽媽大三圈。我出生的時候,外婆的晚年開始了。我從來不知道外婆年輕時長什么樣,所以,媽媽回憶她這個阿姨時說,姨婆長得白皙又好看,我無法從外婆的照片上找到一絲絲年輕時代姨婆的模樣。媽媽說,不曉得姨婆是哪一年生的了,只曉得也屬雞。因為再也找不到記得她生日的人,按以前農日算屬相的習慣,我想來想去,她應該出生在1933年2月4日14時16分至1934年2月4日20時5分間的一個時刻。比如外婆屬雞,原本可以出生在1921年2月4日16時21分至1922年2月4日22時7分之間,因為我媽和我姨記得她的生日是農歷十一月廿六,那么我就能確定她出生于1921年12月24日,而不是其他任何一個日子。那么姨婆為什么不會是出生在1945年2月4日12時12分至1946年2月4日18時1分之間呢?我媽說,姨婆死的時候三十幾歲了。
關于姨婆的少數記憶,是十歲左右的媽媽與她三十多歲的阿姨之間的一次短暫旅行,那個旅行有多短暫,我實在難以描述。在媽媽那次旅行之后不久,姨婆就意外死了,死因不明,那年差不多1966年了。
媽媽說,姨婆是一個放蜂人。她這是做著多么有趣的事啊。民國二十二年或民國二十三年出生的她,五六歲時,扎了小辮子,在孔家村那個矮小的土房邊采摘油菜花,看著蜜蜂在土墻洞眼里鉆出來鉆進去,估計她也會拍著手歡快地跳著。她或許像我一樣,想不明白蜜蜂為什么采蜜呢?我們一起疑惑著晚唐羅隱“采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的疑惑。甚至我倆可以隔空對話——姨婆說,為了人吧?我說不會,蜜蜂釀蜜的時候,人還沒有出現。姨婆可愛地說,為了熊吧?我說,熊也許還在海洋里生活。是的,蜜蜂為了避免饑餓,所以提前釀蜜,當外界沒有食物或不宜采集時,蜜蜂便能以蜂蜜為食。蜜蜂釀蜜這種為了自己過冬儲備食物的本能,羅隱當年也不知道,姨婆也不知道,而我現在即便知道了,還寧愿相信蜜蜂采蜜是為了給熊和人嘗嘗甘甜的滋味的。
誰知道呢?因為偶然的緣故,一個浙江的放蜂人帶著蜂群跟著花開來到了姨婆出生的村莊,遇見了油菜花地情竇初開的女子,他們就相愛了。小伙子的采蜜路線應該是走的東線:上年十二月至本年的二三月份,蜂群在廣東、廣西、福建采集油菜、紫云英花蜜,二月至四月去江西采油菜、紫云英花蜜,四五月份回到上海、江蘇采油菜、紫云英花蜜。這個女子打算陪著小伙子去隨季節尋找花朵。在時間流逝中,她也變成了一個熟諳蜜蜂性格的高手:“五月的蜂群,價值等于大量甘草。六月的蜂群,價值等于銀匙。而七月的蜂群,價值則不如蒼蠅。”
所以,媽媽有了那樣一次短暫的遠行。估計姨婆很疼她,拗不過她反復撒嬌,就帶著媽媽去蘇北的泰興采油菜花蜜。因為媽媽膽小,剛到目的地就吵著回家,姨婆又從泰興把她送了回來,再回泰興,采完蜜后隨姨公回浙江。從那次后,媽媽再沒有見過這個阿姨,據說姨婆在去江西采蜜時死了,被殺。至于案發地點、案發經過,沒有人知道了,兇手也沒有找到。
我聽了在想,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么走了也沒去討個說法,姨婆的家人又做了點什么?那1966年發生了什么事呢?在媽媽眼里那個長得比外婆漂亮、扎了條大辮子的阿姨會不會遇上了一個垂涎她美色的歹徒?我不敢去想了。安哲羅普洛斯說,養蜂人這個職業很奇怪,他們身上有詩人的靈魂,他們和自然的關系特別親密,采起蜜來就像藝術家一樣。哎,想想姨婆最后無助的眼神,怎樣的人才會對一個漂亮的女放蜂人下得了手啊。
再往后,因為姨婆的去世,外婆這邊也慢慢與姨公那家失去了聯系。而令我沮喪的是,我可以用文字追蹤消失的大灰熊或者小鹿,我卻沒有虛構的能力來給一個相關的人設計出一種合理的死亡緣由。在東部中國的平原上,我仿佛看見那個瑞典人拉斯·古斯塔夫松借小說主人公維斯汀之手在寫下“而那單獨的一只蜜蜂如同發條上的一只螺母或螺絲一樣沒有個性”。
孔鳳英,從媽媽那搶救到的一個名字與一段記憶。她活著的話,也不算太老,九十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