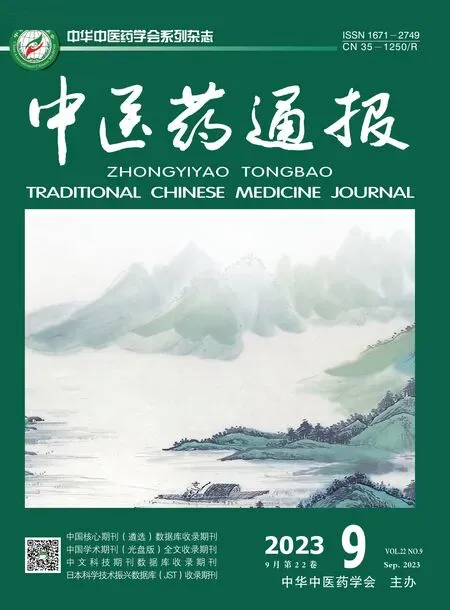從中藥與西藥之差異論中藥的發展
李致重
中醫學是在運用“綜合到演繹”的哲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在對人類生命現象觀察與實踐的臨床過程中,逐步演繹而來的以五臟六腑、氣血陰陽為中心的人類生命醫學體系。中藥學里的藥物、方劑以及針灸、推拿方法等,是這一生命醫學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中的“生命”一詞,尤其重要。而西醫學是在運用“分析到歸納”的近代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在對解剖刀之下的人體組織、器官、功能觀察與實驗的臨床過程中,逐步歸納而來的以局部結構、功能為中心的現代醫學體系。西藥學里的藥品、手術療法等,是這一局部結構、功能醫學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中的“結構與功能”一詞,也尤為重要。這是討論中藥與西藥之比較時,需要明確的前提。
1 中藥的起源
1.1 中藥歷史的簡要回顧從《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拾遺》,到清代以來的《本草備要》《本草從新》《本草求真》等,中藥臨床使用的理論標準,是貫徹始終的。應當說,中藥的價值,是由《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以及《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共同的理論與臨床原則決定的。
鑒于近代流行的把中藥從中醫理論體系中獨立出來的傾向,這里有必要強調兩個原則性觀點:其一,《神農本草經》與《傷寒雜病論》,是中藥與中醫在臨床中融合為一的歷史性樣板;其二,從《本草綱目》到《本草備要》《本草從新》《本草求真》,中醫臨床在對中藥的選擇中不斷得到提高。張仲景在《傷寒論》只用了84種中藥,卻為后世留下了中醫治療外感病經典的理論規范與精準的用藥原則。清代《本草備要》《本草從新》《本草求真》雖然只有三四百種中藥,卻是明代《本草綱目》在臨床實踐中檢驗篩選的結晶。從歷史的角度看,從東漢張仲景用藥的84種到清代的四百余種,臨床用藥從少到多,這是用藥精準的發展與進步;從明代的1892 種到清代的四百余種,這一變化是臨床用藥由多到少、由博返約的發展與進步。
從少到多、用藥精準向從多到少、由博返約轉變,是兩千多年來我國中藥發展與進步必然的歷史過程。對于中醫臨床而言,欲用藥精準,務必由博返約;只有由博返約,才能不斷地提高用藥精準的水平。不論是討論中藥學的發展與進步,還是檢驗中醫臨床的用藥水平,這兩條都是值得高度重視及認真思考的。
1.2 脫離了方劑則無中藥可言中醫臨床方劑的組成中,有君藥、臣藥、佐藥、使藥的不同。而君、臣、佐、使的設定,是由患者臟腑之間生、克、乘、侮的整體關系以及各臟腑氣、血、陰、陽的不同特點而決定的,也是醫生統攬全局的大將智慧,以治愈為目的的戰術性安排。中藥學中的每一味中藥,固然各自有獨到的酸、苦、甘、辛之味,寒、熱、溫、涼之性,補虛、瀉實之功,但從方劑君、臣、佐、使的組合中,更能體現每一味中藥性味、功效的真正意義。
張仲景在《傷寒論》中,使用桂枝的方劑共19首。桂枝甘草湯用桂枝四兩,并且要求一次全部服盡(相當于現在一次服下桂枝60 g),取急救心陽、以通為補之功;麻黃升麻湯中桂枝用量是桂枝甘草湯的1/16,并且分3次服下(每次用量相當于桂枝甘草湯中桂枝一次用量的1/48),取其溫通經脈之效;桂枝湯用桂枝、芍藥各三兩,意在調和營衛;麻黃湯用麻黃、桂枝各三兩,意在發汗解表;桂枝加桂湯加桂枝至五兩,治太陽中風兼心陽虛衰、沖氣上逆……當今《中藥學》教材提及桂枝具有調和營衛、發汗解表、溫通經脈、平沖降逆、峻補心陽等功效,其實是《傷寒論》中桂枝在不同方劑中所具有的療效之羅列,若脫離了方劑而言桂枝的功效,則沒有真實的臨床意義。
這里有兩點要強調。其一,人們常說,“醫為藥之理,藥為醫之用”“中醫中藥,同源同流”“道歸于一,理無二殊”。若是把不懂中醫理論與臨床原則,把超越方劑而亂用中藥的錯誤歸咎于中醫中藥,顯然是不對的。因為輕醫重藥而把中藥從中醫理論體系割裂開來的做法,是廢醫存藥或者中藥西藥化的原則性錯誤。其二,“用藥如用兵”,本質意義應當是“用方如用兵”。這里的“兵”,是兵法意義上的兵,而不是游兵散勇、單槍匹馬的兵。如果說中醫臨床治療原則是以病機為根據的戰略性決定,那么方劑則是戰略指導下的戰術運用。所以說,脫離了方劑則無中藥。
1.3 性味是中藥功效的根本標準中藥的功效就是以自然界物性的寒熱溫涼之偏,來矯正人體的氣血陰陽之偏。《新唐書·裴潾傳》曰:“人無故不應藥餌,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之不平。”清代名醫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一書也說:“用藥治病者,用偏以矯其偏。以藥性之偏勝太過,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黃帝內經》里追求“以平為期”,《傷寒論》里追求“陰陽自和”,顯得既精準,又簡潔。這里的“偏”字,正面的意思是中藥的藥性、功能、作用,倘若人們將方和藥用偏了,方和藥也便是致害之“毒”了。
需要說明的是,中醫學里藥性的寒、熱、溫、涼四氣,酸、苦、甘、辛、咸五味,升、降、浮、沉四性,以及藥物的歸經、功效等,均非形容詞,而是名詞。這些名詞從修辭學的意義上講,均為抽象名詞,并非具體名詞。而西藥體系中的藥物名稱、成分、性狀、適應癥、規格、用法用量、不良反應等,都用的是具體名詞而非抽象名詞。如果因為西藥體系使用具體名詞而認為中藥體系里抽象名詞不準確、太模糊,那就令人見笑了。
2 西方藥學的簡要回顧
丹皮爾的《科學史》一書,記載了西方科學發展的歷史。早期,西方的第奧斯科理德雖然寫過一部植物學和藥學方面的書,而后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西方醫學史至今沒有與《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相類似的以植物藥學為主的專著。17世紀之前,西方尚無系統的醫學、藥學可言,直到西方文藝復興以后,西醫學才形成并逐漸成熟。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里,對西方醫學與中國醫學進行了比較。李約瑟認為,從醫療效果看,西方醫學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后,外科的發展是驚人的,遠遠超出了中國《黃帝內經》以來的任何一個階段。李約瑟推斷,西方醫學在臨床治療效果上的快速進步,大體在1900 年前后,最早不會早于1850 年前后。而西醫臨床療效超過中醫的,主要是外科領域,尤其是戰地外科手術。
17世紀時,西班牙總督夫人在南美的途中染上瘧疾,在當地人的建議下使用一種稱之為“魔葉”的藥煮水服用,燒很快便退了,故在病愈后從南美帶回許多“魔葉”作為禮品送人。“魔葉”其實就是金雞納樹的樹葉。可見,西方當時在瘧疾的治療上還是相當落后的,與張仲景《金匱要略·瘧病脈證并治第四》理法方藥俱備的辨證論治相比,大體上相當于《黃帝內經》之前隨機治療的經驗性水平。李約瑟還提及,數千年來西方在藥物治療上,一直處在遠遠落后于中國的狀況。不必說中醫宋、元、明、清以來內、外、婦、兒等臨床各科的發展,僅從《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而言,就已經注定了西方在傳統醫學上不可能超過中醫的宿命。
3 兩種醫學體系下中藥、西藥的比較
2002年,筆者在美國德克薩斯州遇到一位長期從事藥物研究,學術造詣頗深的華人學者孫立。在討論到從中藥材里提取西藥的問題時,孫立坦率地說到“不太可能”四個字,并笑著打了一個左手高舉朝上,右手直指下方的手勢說:“西醫是朝著形而下走的,中醫是朝著形而上走的。”這令筆者頓生萬里遇知己之感慨。孫立說:“美國在藥物研究上舍得花錢,大學研究部門也有的是錢。我們不少人曾被派到南美,把南美各個國家早年土著人用的藥材幾乎全都拿到美國來反復分析研究。最后的結果是一無所獲。”其接著解釋說:“前提是理論上、思路上中藥與西藥的背道而馳。按照西藥研究的理論、思路,人們寧可在結構化學上慢慢前進,為什么要用化學手段去解釋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什么元素構成的呢?又如何能夠用那里發現的思維元素,制成西醫用的化學藥品呢?”孫立說的道理,其實是人類文化科學分類的一般性原則,豈能被忘記和違背呢?
電視臺演播廳里坐滿了觀眾。杰克坐在一邊,蘇穆武坐在另一邊。主持人上來,拿著話筒: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我們請來的是美國的瑞恩杰克先生,和他的中國岳父蘇穆武先生。杰克先生今年4月從華盛頓來到中國,與蘇老先生的女兒蘇婷婷結了婚。最近杰克先生與蘇老先生在生活方面產生了一些分歧。今天我們把兩位當事人請到節目現場,讓兩位面對電視觀眾談談自己的想法。大家鼓掌歡迎!
與筆者同期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的胡世林教授,曾是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副所長,也是國內在地道中藥材研究領域建樹頗多的知名專家。胡世林教授多次說過,20世紀60年代啟動的青蒿素研究,國家非常重視,一次又一次地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經費,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 世紀90 年代,《中國藥典》已將雙氫青蒿素列入西藥的目錄,這表明我國并沒有因為青蒿素是從中藥材青蒿里提取出來的,而將其列入中藥的目錄。當代用化學方法研究中藥的課題鋪天蓋地,而中藥材地道化種植的問題卻少有人關心。中藥材是生產中藥飲片、中成藥的原料,是確保中醫臨床療效最重要的問題,忽視這些主流性問題,無疑是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失誤。從中藥材里提取出西醫所認為的有效成分而生產新的西藥,是絕對不會受到反對的。但是,中醫藥行業應當抓好中藥材的地道化生產,西醫藥行業應當抓好從中藥材里提取有效成分的新西藥研究。這些見解,筆者每次在講授中西醫比較時,都會強調。
4 中藥與西藥學科定位的比較
對一個學科的科學定位,是學科傳播、發展的首要學術問題。在中西醫并存的時代,對中藥與西藥兩個學科的科學定位進行比較研究,是必須解決的基礎課題。在教科書尚未對中藥與西藥的比較研究作出明確定義之前,大家不妨將其理解為對中藥與西藥的解釋。
4.1 關于中藥學的科學定位筆者在《中醫復興論》一書中,對中藥是這樣定位的:以中醫經絡藏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理論為基礎,按照藥物四氣五味、升降浮沉、功效歸經的原則和指標,在中藥材的基礎上生產的,供中醫辨證論治使用的飲片、成藥,稱之為中藥[1]。
中藥是中醫理論體系的一個部分,“以中醫經絡藏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理論為基礎”,意在說明中藥與中醫理論的從屬關系。
“四氣五味、升降浮沉、功效歸經的原則和指標”,是中藥從屬于中醫基礎理論的理論原則。這是中藥定義的核心部分,也是中藥與西藥相區別的關鍵所在,不可或缺。
“在中藥材的基礎上生產的”,意在強調中藥材與臨床中藥的關系和區別。臨床中藥來源于中藥材,但是中藥材未經過必要的加工、炮制,是不能直接用于中醫臨床的。固然,西醫可以從中藥材中提取西醫認可的有效成分,成為用于西醫臨床的新西藥。但是,從中藥材中提取有效成分制成的藥品則已經是西藥,便不能再劃歸于中藥了。
“供中醫辨證論治使用的飲片、成藥,稱之為中藥”一句,包含兩個重點。其一是“供中醫辨證論治使用”。這里的“辨證”,一方面指的是以經絡藏象的基本理論為根據,另一方面是指以臨床四診所見到的證候為根據,然后在基本理論與證候兩者之間的反復理性思維中,作出對疾病的病機診斷。其二是“使用的飲片、成藥”。這里的“使用”,包括三個方面:一要根據病機診斷確定治療原則;二要根據治療原則確定方劑組成原則;三要根據治療原則或方劑組成原則,選擇合理的飲片或中成藥。
總而言之,在中醫與中藥兩個基本原則和理論標準的基礎上,以中藥材為原料生產出來的飲片和中成藥,才是可以供給中醫辨證論治使用的中藥。從中藥材里生產出來的飲片配制為湯劑,是中醫臨床治療的主要劑型;在湯劑理論的基礎上制作出丸、散、膏、丹、湯、露等中成藥,是中醫臨床治療的補充。飲片和中成藥的臨床運用,必須遵循中醫基本理論,即藏象經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方劑的理論原則。中藥材四氣五味、升降浮沉、功效歸經的理論原則,應被視為中藥所遵循的不同于西藥的客觀標準。只有遵循中藥獨有的理論基礎與客觀標準,中醫的臨床辨證論治才能發揮出應有的特色和優勢。
4.2 關于西藥學的科學定位關于西藥學的科學定位,主要是為了便于理解西藥與中藥的區別。筆者對西藥學的科學定位表述如下:用西醫的藥物物理和藥物化學的方法,按照西醫生理和病理的原則,從中藥材中提取西醫所認可的有效成分,根據西醫臨床藥理的指標,用于西醫臨床的藥物,屬于西藥。
這一表述包含了6個“西”字。如此冗長的文字,意在與中藥學的科學定位上下呼應,相互對照,以說明中藥與西藥的區別。這是關系到兩個理論與臨床體系之間多項的復雜的區別,文字上的確冗長了些,但并無重復。
“西醫的藥物物理和藥物化學的方法,從天然原料或中藥材之中提取西醫所認為的有效成分”,這是西藥研究、開發的基本方法之一。除此之外,就是化學合成了。不論是物理方法萃取、化學方法提取,還是化學方法合成,這都屬于西藥研究、開發的基本方法。具體研究、開發的方法、技術盡管有所提高,但基礎原理至今還是以上幾種。從中藥材里萃取或提取西醫臨床所用的西藥,當然也是如此。
在實施上述西藥研究、開發的方法、技術時,西醫生理、病理的原則始終是西藥研究、開發實踐中必須遵循的理論原則。毫無疑問,西藥的用途是解決西醫認為的病理問題,所以西藥與病理和生理必然是直接聯系的。按照西醫生理和病理的原則,從中藥材里提取西醫所認為的有效成分,也必然以西醫的生理和病理為理論根據。否則,中醫認為再好的飲片或中成藥,西醫臨床上都是不會接受或使用的。根據西醫的臨床指標,從中藥材中提取西醫所認為的有效成分的藥物,當然應該劃歸為西藥[2]。
從天然藥材里提取有效成分,是西醫形成過程中固有的做法之一。中國閉關自守時期,西方國家沒有把中國的醫學體系放在眼里;中國大門打開之后,突然發現中國有這么多可治療疾病的藥材,故而給予了極大關注。但是,如何選擇真實可靠的中藥知識面對世界,是值得深思熟慮的。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歷經十余年編輯出版了一部中藥巨著,名為《中華本草》。全書2400余萬字,分為34卷,共收錄藥物10112種,是明代《本草綱目》收錄藥物的5.3 倍。其中中藥30卷,收錄藥物8980種,藏、蒙、維、傣四種民族醫藥4卷,收錄藥物1641種。該書于“文革”之后不久編輯,許多藥是“中草藥群眾運動”未經證實的產物,故而大家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容盲目樂觀。因此,在討論中藥、西藥的比較時,選用中藥文獻的時代應確定在清末之前。
5 從以上比較引發的思考
筆者從中藥發展的主體上,提出“一條原則,兩條出路,四個重心”。
5.1 一條原則一條原則即醫藥一家。藥物生產中要停止在中醫劑型改進中以技術領先為重的做法,應當把中醫藥的經絡藏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以及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性味歸經理論,真正使用在臨床上,務必在保證療效的前提下穩健地推進劑型改革。日本的津村順天堂,在劑型改革上利用先進的技術,獲取巨大的經濟效益。20世紀60年代,日本人借著先進的包裝技術,將中藥劑型改成很小的中藥顆粒劑。患者每次服1~3 g,開袋即服,一口水就能沖下,很方便。但是,日本在使用經方時,已經比張仲景時代中藥用量小許多,一般是仲景用藥量的1/5 到1/3,現在再把劑型做成1~3 g的粉末,粉末里還有許多賦形劑,如此算來,這1~3 g 的粉末里有效成分到底有多少,著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筆者在《日本漢方醫學衰落軌跡》里將其稱為安慰劑,這種安慰劑,治不好病也吃不壞人。20世紀90年代,日本曾經引發了“小柴胡事件”,要求把日本漢方從醫療保險藥里剔除出去。這種現象,值得深思。
5.2 兩條出路兩條出路是指西醫走西醫的路,中醫走中醫的路。西醫按照西藥的標準,從中藥材里提取西醫所認為的有效成分生產西藥,這是西藥的路。中醫中藥,應該按照中醫中藥的理論原則走自身的路[3]。
5.3 四個重心其一,以中藥材的質量控制為重心。其二,以中醫理論為依據重心,開展中藥飲片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其三,中成藥的調整、整頓、開發、生產過程中,取締以經濟利益為目標且沒有治療效果的中成藥。其四,加強中醫、中藥知識產權和藥物資源的保護[3]。
6 嚴守“四至”開創中藥質量的未來
人是天地萬物之靈,藥物是救人于危難之圣品。中藥是中醫治病的利器,中藥的質量事關中醫的存廢。對于中藥質量的把控,中藥生產企業首先要有“四至”意識,并要遵循具體的行業質量標準。這里所說的“四至”是:至圣、至一、至優、至嚴。
所謂“至圣”,指的是中藥是用來治病救人的,當為最圣潔的商品,而不是用于衣、食、住、行的普通商品。乘人生命之危,制造銷售假藥,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為。所以中藥的圣潔性,是生產、采集、加工、炮制、運儲、經營、銷售、管理各個環節必須高度堅持的唯一、至上的原則。
所謂“至一”,指的是提供臨床使用的中藥,不論是飲片還是成藥,其生產企業都要最大限度地堅持至一的經營管理觀念。不論是東西南北中還是國內與國外,中醫講的都是同一個理。提供臨床使用的飲片或成藥,都要像西藥的原料生產與臨床制劑一樣,在經營管理觀念上要力求統一。
所謂“至優”,指的是中藥生產、采集、加工、炮制、運儲、經營、銷售、管理各個環節,都必須堅持一個質量標準。中藥材的生產環節有等級差異,但臨床飲片的質量標準只能是一個,這就是至優。
所謂“至嚴”,指的是中藥生產、采集、加工、炮制、運儲、經營、銷售、管理各個環節,在管理制度上務必遵照至圣、至一、至優的要求,嚴肅立法,從嚴管理。
近一百年來,中醫藥出現了部分盲目自殘的現象。這其中有經濟利益的驅使,有中醫西化的干擾,有中醫學術的困惑,有中醫藥管理的落后,也有部分人道德良心的沉淪。這里的“四至”,也是針對這一現象而言的。中藥方面“四至”觀念的確立和落實,一定會有力地促進中醫藥學術的復興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