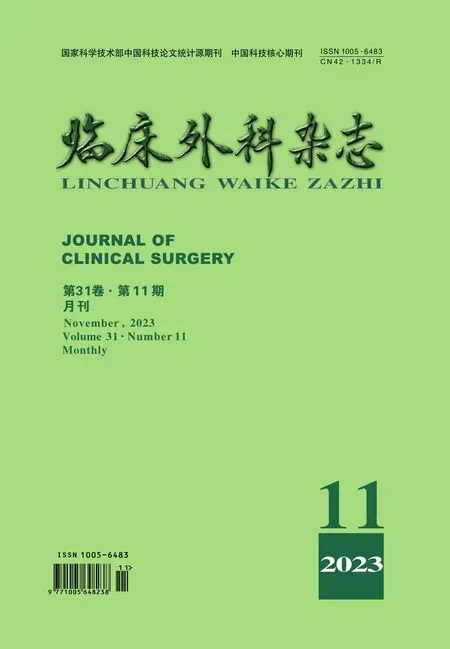煙霧病科研與臨床的未來之路
倪偉 顧宇翔
煙霧病(moyamoya disease,MMD)是一種較為罕見的慢性閉塞性的腦血管疾病,目前病因尚不明確。該病最早由Takeuchi和Shimizu于1957年發現,由于這種顱底異常血管網在腦血管造影上形似“煙霧”,故稱為“煙霧病”[1]。MMD在東亞國家高發,且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遺傳因素可能參與發病。該疾病在女性多發,存在兒童和青壯年2個高峰發病年齡,主要癥狀是腦缺血和顱內出血。近年來,MMD在我國的發病率和患病率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其病因學、診斷和治療上仍存在諸多爭議。我們認為,未來臨床與研究工作應關注以下方面:(1)深入研究MMD的發病機制,尋找新的治療靶點和策略;(2)MMD認知功能障礙;(3)MMD的高級別循證醫學研究。
一、MMD發病機制研究
1.遺傳學因素:迄今為止,MMD的確切病理生理機制尚未得到闡明。基于疾病流行病學進行評估,2.1%的MMD病人有家族史[2]。同卵雙胞胎有更高的煙霧病共同患病率,而且MMD病人的后代發生MMD 的可能性升高[3]。結合發病年齡特征、家族性病例以及不同種族之間發病率和患病率的顯著差異,早期研究便將注意力集中在遺傳因素上。疾病的特征包括血管壁和平滑肌細胞受累、血管生成活性增加以及血管可塑性等改變。鑒于這些病理特征,可能有多種基因參與了MMD的發展。
在過去幾十年的基因研究中,研究者對MMD群體進行了從遺傳連鎖研究、關聯研究到包括全基因組測序在內的DNA測序[4]。這些技術為我們揭示了關于MMD遺傳基礎的新結果,這些結果部分地反映了病變特征。既往研究還探討了MMD病人的HLA系統,并發現了一些關聯性。連鎖分析驗證了與17q25染色體的連鎖,并對該區域編碼的基因進行了測序,發現了一個新的候選基因,即RNF213。在一項全基因組連鎖和外顯子組分析研究中,在日本人群中95%的家族性MMD病人、80%的散發性MMD病人和1.8%的對照個體中發現了氨基酸替代p.R4859K[5]。有研究將RNF213基因的臨床相關性從MMD擴展到數種全身性血管疾病,稱為RNF213相關性血管病。考慮到其低外顯率,RNF213p.R4810K變體的攜帶者在伴有其他遺傳或環境驅動因素時(二次打擊)有可能發展為MMD或 RNF213 相關血管病變,如自身抗體和微生物感染。因此,進一步明確這些起始因素將有助于制定針對MMD和RNF213 相關血管病變的診斷標準。
2.非遺傳因素:除了遺傳因素外,MMD還與眾多非遺傳因素相關。有研究報道MMD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細胞因子、內皮祖細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等因素相關。這為未來探索疾病發展機制開辟了新的途徑。
免疫系統和炎癥參與MMD病理生理過程。Masuda等[6]發現,在MMD病人動脈內膜中有巨噬細胞和T細胞浸潤。此外,細胞因子異常分泌所形成的促炎環境還可能刺激內皮細胞和巨噬細胞的激活、平滑肌細胞的增殖和血管新生[7-11]。MMD可與1型糖尿病、Graves病、血小板減少癥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時存在[12-14],也促使人們對MMD發展過程中免疫調節紊亂和免疫蛋白表達異常的機制進行研究。蛋白質陣列數據分析和生物信息學分析已經鑒別出165個在MMD病人血清中顯著過表達的自身抗體,這些抗體與翻譯后修飾、炎癥反應和DNA損傷修復和維持有關[15]。煙霧病病人頸內動脈彈性層和大腦前、中動脈中有IgG和IgM沉積[16]。 免疫復合物的沉積可引起腦血管主血管及其分支的內彈性層變性、迂曲、破裂,可引起中膜平滑肌細胞大量遷移至內膜下,導致內膜增厚,血管管腔狹窄。此外,有研究報道RNF213具有抗微生物蛋白的功能,并在免疫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17]。總之,來自臨床和研究實驗室的新證據加強了感染或免疫相關觸發因素作為MMD發作的第二種打擊的論點。綜上。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闡明感染、先天免疫和進行性動脈狹窄之間的聯系。
EPCs具有分化為成熟血管內皮細胞的潛能。MMD病人的外周血中EPCs水平高于動脈粥樣硬化性腦血管疾病病人和健康對照組[18],并且這一現象在有煙霧狀血管形成的大腦大動脈閉塞(或嚴重狹窄)病人中被觀察到,但在沒有煙霧狀血管形成的大腦大動脈閉塞(或嚴重狹窄)病人中未被發現[19]。一項前瞻性臨床試驗也發現,在116例MMD病人中EPC計數與術后良好的側支循環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20]。
MMD病人血漿中細胞因子濃度顯著改變,包括VEGF、基質金屬蛋白酶-9 (MMP-9)和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BB (PDGF-BB)[21]。在MMD進展過程中,局部腦缺氧會引起VEGF表達的改變,這可能有助于煙霧血管的形成。然而,細胞因子在MMD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是啟動作用還是僅僅是中間產物尚不清楚。
二、MMD認知功能
MMD的臨床癥狀主要包括缺血/出血性腦卒中、短暫性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癲癇、頭痛等。近年來血管性認知障礙(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逐步受到重視,成為研究熱點。然而血管性認知障礙常起病隱匿,近年來MMD認知障礙研究集中于影像學探索。
擴散張量成像(DTI)后處理圖像處理技術和彌散參數的量化,使得研究者能夠量化評估白質損傷的特征。降低的各項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被認為反映髓鞘纖維數量減少和髓鞘破壞。Kazumata等[22]分析了23例無癥狀的MMD病人和健康對照者的DTI數據發現,外側前額葉、扣帶回和頂下小葉葉區的白質束的FA與處理速度、執行功能(注意力)和工作記憶顯著相關。因此,對于受長期低灌注影響的MMD的白質損傷,尤其是髓鞘的損傷或發育不良,更可能是認知功能障礙的重要原因之一。血運重建后灌注的時間依賴性改善可能是通過恢復白質功能改善認知功能的可能原因。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神經、區域和網絡水平腦區之間功能連接的方法。研究發現,執行功能網絡的右側后扣帶回、左側頂上回和左側枕上回激活降低[23-24],這表明高級認知功能與基礎腦網絡的有序性可能存在關聯。靜息態網絡分析進一步明確MMD網絡變化的靜態和動態特征,為MMD的認知功能提供潛在的生物標志物,這為我們理解MMD認知功能障礙提供了新的視角[25]。
18F-FDG PET通過測量細胞葡萄糖攝取水平來直接反映細胞的活性,已被廣泛應用于腦成像。18F-FDG PET在缺血性腦血管病評估方面的應用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線中[26-27]。18F-FDG PET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探討慢性缺血性腦血管疾病與腦葡萄糖代謝的關系。Weng等[28]發現,MMD相關血管性認知障礙在18F-FDG PET影像上存在一定的特征性,且優勢側腦區的低代謝更易導致血管性認知障礙。
隨著研究不斷深入,血管性認知障礙已成為MMD研究領域重要組成部分,如何進一步闡明MMD相關血管性認知障礙的發生機制,并將這些科學發現應用于臨床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三、MMD手術干預的臨床研究
盡管目前主流觀點認為,血流重建手術是治療MMD的唯一有效方案,然而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始終缺位。MMD血流重建廣義上分為以下幾類血管重建手術:(1)直接重建:通常是在顳淺動脈和中腦動脈之間建立直接的顱外-顱內吻合;(2)間接重建:通過將顳淺動脈、顱外組織(如顱淺動脈、頭皮、顳肌和翻轉的硬腦膜)與腦表面接觸進而形成動脈新生;(3)上述方案的結合即聯合手術。直接重建手術具有即時血流再灌注的優勢,而間接重建則依靠血管新生,需要幾天或幾周的時間。直接重建手術的技術要求較高,潛在的圍手術期并發癥較多。盡管血流重建手術是目前降低MMD病人中風風險最成功的治療方法,然而其圍術期并發癥的發生率仍然非常高[29],如何降低圍術期并發癥是MMD手術治療面臨的重要障礙。目前尚無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探討MMD血管重建手術在缺血性中風預防方面的療效。目前唯一隨機對照試驗比較了手術與藥物治療在出血性MMD病人中的療效,顯示直接搭橋手術能夠降低再出血率[30]。薈萃分析表明,直接搭橋或聯合方法在腦卒中預防和影像學預后方面優于間接搭橋[31-34],但這些薈萃分析和其源研究存在缺陷,包括非隨機治療分配、隊列中年齡和臨床表現的異質性、不設盲的結果評估、不一致隨訪時間等[33]。美國心臟協會/美國中風協會2021年指南認為,手術重建(無論是直接重建還是間接重建)對于預防缺血性中風或TIA發作可能是有益的,但證據級別較低[35]。近期發表的CMOSS研究雖然沒有取得明確的陽性結果,但為血流重建手術的多中心隨機研究提供了實踐基礎。缺血性MMD血流重建手術的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值得大家共同努力推進。綜上,雖然血流重建手術已經廣泛應用于臨床,但從循證醫學的角度出發,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尤其是高級別證據支持我們的外科臨床實踐。
綜上所述,發病機制的研究是從根本上明確MMD病因與治療方案的基礎。血管性認知障礙是MMD的重要臨床表型,是MMD臨床評估與科學研究中值得重視的環節。治療策略上,雖然血流重建手術治療MMD已經成為行業共識,但目前缺乏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支持。因此,MMD的發病機制、認知功能障礙和血流重建手術效果的驗證值得進行深入研究,在尋找新的干預靶點的同時完善現有的治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