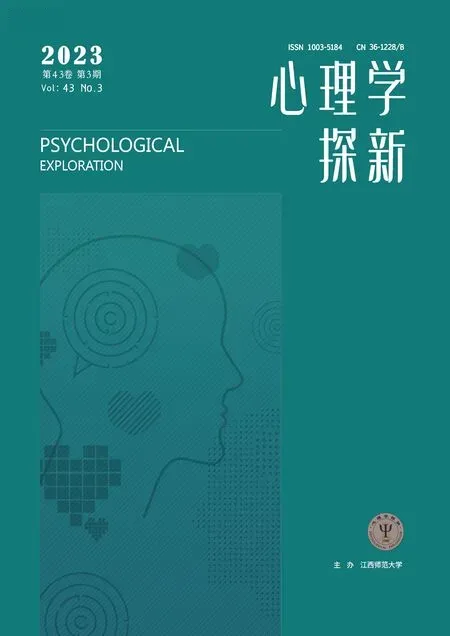感恩干預效果的個體差異
鄧衍鶴,李奕辰,田思思,高似彤,劉翔平
(1.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北京市“學習與認知”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73;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 100875)
1 引言
所謂感恩,既可以被視為在獲得他人的善舉時所產生的感激和喜悅的情緒體驗(Emmons &McCullough,2004),即狀態感恩;亦可以被看作通過感恩體驗來覺察或回應他人的善舉,由此衍生出對日常生活心懷感恩的積極人格傾向(何安明 等,2013;Wood et al.,2010),即特質感恩。感恩源于對他人善意的認知與覺察,也涉及到欣賞生活中美好一面的積極認知風格(Jans-Beken et al.,2020;Emmons &McCullough,2004)。諸多研究業已揭示出,感恩與人的適應性功能具有密切的關聯,包括與幸福感、積極情緒、樂觀和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而與抑郁、焦慮、消極情緒和壓力等功能紊亂呈負相關(Emmons &McCullough,2003;Kong et al.,2021)。
研究者發現,通過采取一些策略來主動練習和提升感恩,能夠豐富個體內在積極資源,進而對其生理、心理與社會功能發揮積極效用(Emmons &McCullough,2003)。自千禧年以來,聚焦于感恩練習的干預得以蓬勃發展,被廣泛認為是最成功的積極心理干預策略以及一種與臨床治療相關的實用技術(Seligman et al.,2005)。常見的感恩練習策略,包括細數感恩、感恩沉思以及諸如書寫感謝信和感恩拜訪的感恩行為表達(Wood et al.,2010)。練習者在指導下對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件和體驗予以回憶、沉思或記錄,抑或是通過具體的行為表達感恩,加以重復練習,逐漸形成自動化的積極認知風格,從細微中覺察到他人給予的恩惠,促進其親社會性(Emmons &McCullough,2003;鄧衍鶴 等,2016)。簡而言之,諸類感恩干預均意圖通過不同種類的練習策略來培養個體的感恩水平,繼而促進其適應性功能的發展。
感恩干預不僅能夠有效改善個體的積極心理功能,如心理幸福感、基本心理需求滿足(Lee Tong &Sim,2015;Geier &Morris,2022)、樂觀(Kerr O’Donovan &Pepping,2015)、心理韌性(Salces-Cubero et al.,2018)、自尊(Rash et al.,2011)、主觀幸福感和親社會行為(Watkins et al.,2015;Southwell &Gould,2017),同樣有助于降低消極情緒(O’Connell et al.,2017;Salces-Cubero et al.,2018)、抑郁(Disabato et al.,2017;Sirois &Wood,2017)、焦慮(Southwell &Gould,2017)和攻擊性(Deng et al.,2019)。此外,臨床研究表明在治療體像障礙和過度擔憂方面,感恩干預同常用的臨床技術一樣有效(Geraghty et al.,2010)。基于諸多實證依據,感恩干預愈發成為一種高效、低成本并易于實施的心理治療技術(Seligman et al.,2006)。
縱觀既往研究,感恩對個人身心健康助益良多,因此一直以來有關感恩干預的積極成效似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感恩特質或表達感恩的行為未必總是有益。在某些情況下,誘發感恩會引發負債感、歉疚等消極情緒,甚至導致幸福感下降(Watkins,2004;Walsh et al.,2022)。與此同時,向他人表達感恩意味著自己的幸福體驗有賴于他人,由此產生的脆弱感會令某些個體感到不舒服(Kashdan et al.,2009)。Wood等(2010)也對感恩干預的療效提出了質疑,認為將感恩干預視為積極心理學運動的重大成功還為時尚早。Davis等(2016)在一項關于感恩干預的元分析中發現,盡管干預效果顯著,但效應量微弱。無獨有偶,Dickens(2017)在另一項元分析中發現,只有與如細數煩惱和后悔事件的消極對照組比較(Emmons &McCullough,2003;Froh et al.,2009),干預才顯示出顯著的效果;而當對照組是中性或積極的條件,干預只能帶來微小的改善。Cregg和Cheavens(2020)在關于感恩干預對焦慮和抑郁癥狀療效的元分析中發現,與無干預的等待組相比,干預具有中等效應,但與有主動控制的安慰劑組相比,干預效果微弱;這表明感恩干預在減輕焦慮和抑郁癥狀方面的效果有限。甚至,當人際聯結需要與道德規范發生沖突時,對施惠者的感恩會促使受惠者的思維變得更加狹隘,激發漠視社會規則的道德違反行為,如撒謊和降低應有的懲罰(Zhu et al.,2020)。以上研究表明,感恩干預并非總會引發理想的效果。
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感恩干預在不同個體之間所發揮的效應并非一致,有些人獲益更多,而有些人卻會由此產生損耗。因此,有必要厘清感恩干預效果的個體差異,進一步明確干預對具有何種特征的個體能夠發揮更為積極的效用。鑒于此,本文首次系統梳理了調節感恩干預效果的個體因素及潛在的解釋,以期拓展個人特征與感恩干預活動適配性的認識,明晰影響感恩干預效果的目標特征,為制定個性化的精準干預方案明確思路。
2 調節感恩干預效果的個體特征
2.1 基線心理特征
作為一種對日常生活心懷感激的特質(何安明等,2013),在干預前的特質感恩基線水平影響人們從感恩干預中的獲益程度。例如,Rash等(2011)實施了4周感恩沉思練習,發現相比于高特質感恩者,僅低特質感恩者的生活滿意度有所提高。同樣,Harbaugh和Vasey(2014)對大學生進行了兩周的細數感恩練習,發現干預只在低特質感恩群體中效果顯著,表現為抑郁水平下降和主觀幸福感提升。盡管低特質感恩通常預測個體較低的幸福感和積極情緒,以及較高的抑郁水平(Wood et al.,2010),但感恩練習卻能夠打破這種模式,幫助低特質感恩者獲取與高特質感恩者對等的幸福感和積極情緒,并保護其免受抑郁癥狀的持續影響。盡管多項研究支持了特質感恩水平是調節干預效果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研究的發現與此不一致,如Toepfer等(2012)未發現特質感恩調節書寫感謝信對幸福感、抑郁癥狀和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再者,積極情緒的基線狀態對感恩干預效果同樣有所影響。例如,在一項關于感恩行為表達的研究中,Froh等(2009)指導青少年書寫并郵遞一封感恩信,結果發現,相比于中性控制組,僅基線積極情緒較低者在干預后報告了更高水平的感恩和積極情緒。然而,Rash等(2011)在持續4周、每周1次的感恩沉思練習中,沒有發現基線情緒狀態顯著調節感恩干預對幸福感的影響。但該研究的對照組與干預組樣本不同質,在控制參與者的日常情緒方面可能存在混淆因素,且存在干預時間短、次數少和樣本量小等問題。
此外,以往研究認為抑郁癥患者從積極心理干預中獲益較少,因為認知、情感和行為功能的紊亂會阻礙其充分體驗積極活動。然而,Sin和Lyubomirsky(2009)發現,積極心理干預對于那些符合抑郁癥診斷標準的群體顯示出更加顯著的療效。Harbaugh和Vasey(2014)進一步揭示出,細數感恩練習僅對那些高抑郁水平者有益,包括提升了幸福感和積極情緒,改善了抑郁癥狀。再者,Sergeant和Mongrain(2015)通過聚類分析區分出兩類群體,包括病態群體(更多的抑郁癥狀和消極情緒、更低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指數)和非病態群體(較少的抑郁癥狀和消極情緒、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指數),并對其采用線上誘發感恩的練習,發現病態群體在接受干預后表現出更少的抑郁癥狀和更高的生活滿意度。換而言之,干預為處在消極心理狀態下的人們提供了更為有效的幫助,通過接觸新的認知、情緒和行為體驗進而改善了幸福感。然而,Cregg和Cheavens(2020)的元分析表明,感恩干預的效果并沒有隨著抑郁癥狀的加重而增加。甚至有研究發現,書寫感恩信組與聽古典音樂的控制組相比,重度抑郁和焦慮的個體在感恩練習后幸福感顯著下降(Sin et al.,2011)。
針對上述研究發現,究其潛在原因。一方面,依據阻力假說(Resistance Hypothesis;McCullough et al.,2004),具有如高感恩和積極情緒的基線心理特征的個體,能夠一直以積極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已經獲得了應有的積極體驗,因此由感恩練習額外帶來的積極體驗難以引發更多的效果;反之則具有更多的提升空間,更容易從感恩練習中獲得助力。同樣,Watkins(2004)認為,在基線階段具有高積極心理特征的人在感恩和幸福感之間已經存在了穩定的協同效應,短期練習難以促進其進一步躍升;反觀不具備這種特征的人,干預則為其開啟了協同效應。與“天花板效應”類似,基線階段心理特征的積極水平愈高者,其主觀幸福感已經很高,因此感恩干預引發的正向變化程度有限。
另一方面,感恩練習對于本就缺乏積極體驗的個體更為有效。類似于“地板效應”,具有更多消極心理特征的病態群體相比于非病態人群,擁有更多提升與進步的空間,因此更能夠從感恩練習中獲益(Sin &Lyubomirsky,2009)。然而,對于重度抑郁和焦慮者而言,動機、情感和認知功能的紊亂可能使其在開啟感恩練習時存在一定的困難,激發出更多負面情緒,從而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不一致的研究發現,提示了感恩練習對患有不同嚴重程度的抑郁或焦慮的人仍存在效果差異。未來應繼續探索如何干預能滿足不同水平焦慮或抑郁患者的需求和偏好,為其定制精準化干預策略。
2.2 人格類型
研究者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探索了人格對感恩干預效果的調節效應。基于人格的兩極發展理論(Two-polarities Model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Blatt,1976,2004),Sergeant和Mongrain(2011)發現,細數感恩練習僅對高自我批評者起效,包括增加了主觀幸福感和自尊水平,且顯著緩解了軀體癥狀,但對高依賴者不起作用,甚至損害了他們的自尊。究其潛在原因,不同人格特征與干預策略的適配程度可能影響了干預效果。具體而言,不同個體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需求、價值、興趣和偏好等特征,當人們實施與自身特征相匹配的練習活動時,更容易從干預中獲益。一方面,高自我批評個體傾向于關注和感知自身的錯誤和缺陷,以至于很難理解并欣賞生活中的積極一面(Zeeck et al.,2020)。在感恩干預條件下,高自我批評者被鼓勵去思考生活中忽略掉和錯過的積極體驗,彌補了以往消極的自我關注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對外部世界的欣賞,從而發揮出積極效果。另一方面,高依賴個體極度依賴與他人的真實聯結來滿足情感需求(Sekowski &Prigerson,2021),但細數感恩不涉及人際互動,屬于自助式練習,因而難以提升其幸福感,甚至會被獨立的練習形式誘發出消極情緒,因此他們可能更需要涉及人際互動的練習策略。
再者,基于大五人格類型(Big Five Personality Model;Goldberg,1993),Senf和Liau(2013)發現外傾性和開放性顯著調節了感恩練習對幸福感和抑郁癥狀的效果。具體而言,高外傾性個體在感恩練習后幸福感提升更多,抑郁水平下降更多;相似地,高開放性個體在感恩練習后幸福感提升更多。同樣,另一項研究在為期一周的感恩拜訪練習后發現,高外傾性個體的幸福感有更大程度的增加,抑郁癥狀有更大程度的減少(Schueller,2012)。此外,Winslow 等(2017)在對公司職員進行為期四周的感恩干預后發現,高宜人性者的感恩與積極情緒得到了更多的提升,但高盡責性者在接受了干預后卻出現了更強烈的消極情緒。而且值得注意的是,Ng(2016)探索了神經質對細數感恩干預效應的影響,發現只有低神經質個體從活動中提升了幸福感并持續獲益,而高神經質個體并未顯著獲益。同理,大五人格的特點與干預內容的契合度也許是潛在的作用機制。一方面,高外傾性、開放性和宜人性個體更為擅長和偏好增加人際紐帶的練習活動,因此表達感恩行為更能發揮出積極效果。另一方面,高盡責性的個體更傾向于將感恩練習當作一種外在要求的任務來完成,由此破壞了自主練習本應產生的積極作用;而高神經質個體則存在消極認知偏差,尤為不擅長使用適應性策略調節情緒,因而很難從常規感恩練習中獲益。
2.3 內在動機與投入
個體參與練習的內在動機以及對效果的預期也可能影響感恩干預的成效。Sin和Lyubomirsky(2009)的元分析表明,明晰活動目的并積極報名參加、渴望通過練習提高自身幸福的參與者,相比于并未主動報名但同樣完成了干預練習的參與者而言,從感恩練習中獲益更多。原因在于,這種受內在動機驅使的人更加認同干預活動的價值,練習時更加努力主動,由此幸福感提升更多。Sheldon和Lyubomirsky(2006)在為期4周的細數感恩干預中發現,只有在練習中付出更多努力、受內在動機驅使的參與者,在干預后顯著提升了積極情緒。同樣,Lyubomirsky等(2011)讓參與者每周書寫1封感謝信,持續8周,發現這種干預方式并不能對所有人產生效果,幸福感的提升僅發生在那些內心渴望變得更幸福的群體中,而內在動機在控制組內沒有起任何作用。此外,在干預結束后仍然主動練習的參與者,其幸福感提升更多(Lyubomirsky et al.,2011;Sheldon &Lyubomirsky,2006)。由此可見,受內在動機驅動的參與意圖是有力的影響因素,想要通過感恩練習獲得持續的幸福感,需要自我意志的努力。
2.4 人口學特征
首先,人們所屬的文化背景會影響干預的成效(Dickens,2019)。例如,Boehm等(2011)招募了英裔和亞裔的美國人進行持續6周的感恩信練習后發現,相比于亞裔,英裔美國人在干預后的生活滿意度提升更多。進一步地,Layous等(2013)直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參與者之間比較了練習效果,發現美國人比韓國人的幸福感提升更多。由此可見,相比于集體主義文化,受個體主義文化影響的參與者從感恩干預中獲益更多。究其潛在原因,強調自我意識提升的個體主義文化價值觀,與感恩練習的目標更適配,而在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中較少關注個人目標和自我完善,他們的幸福感不僅取決于自身,還存在他人取向(Ho et al.,2014)。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使用感恩策略,可能容易引發參與者的自責和對施惠者的愧疚,甚至誘發焦慮和抑郁情緒。因此,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開展的感恩干預不能只是簡單復制先前適用于個體主義文化的干預方案,以避免干預效果適得其反。
此外,研究發現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練習感恩時更為虔誠,所以感恩干預在信徒中開展更為有效(Van Cappellen et al.,2021;Portocarrero et al.,2020)。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已經足夠感恩(Lambert et al.,2009),干預效果或許不如無宗教信仰的人。因此,干預研究有必要納入個人的宗教信仰作為考察干預效果的控制變量。
再者,年紀大的人更可能從感恩干預中獲益(Carr et al.,2021;Sin &Lyubomirsky,2009)。年紀大的人往往擁有更高的智慧,更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和完善的自我目標(Linley et al.,2007),接受感恩干預時更認真并愿意付出更多努力。因此,練習感恩在處理與年齡相關的逆境時,是一種積極的應對機制,有助于建構心理韌性,降低消極情緒狀態的影響(Killen &Macaskill,2015)。
最后,女性相比于男性似乎更有可能體驗并表達感恩,但這并不意味著女性始終會從感恩干預中獲益更多。研究表明,處于青春期早期的男性要比同一年齡段的女性從感恩干預中受益更多(Froh et al.,2009)。這或許是因為女性有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并表達著感激,而男性更看重自我獨立,因此難以承認自己對他人的依賴,也甚少表達對他人的感激。但也正因如此,男性通過感恩干預而獲得的提升空間要比女性更大(Watkins,2013)。
3 未來研究與展望
一枚硬幣尚且有兩面,面向具有不同特征的個體,感恩干預的效果自然也會有所差異。一味關注感恩干預的積極效應的普適性,對于該領域的長期發展來說弊大于利。感恩干預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但干預適用于所有人似乎過于理想。本文聚焦于感恩干預效果的個體差異,系統地梳理了調節干預效果的不同的個人特征,加深了對參與者特征的理解以及對感恩干預效應的重新評估,為發展個性化感恩干預提供了證據基礎。
然而,目前仍存在兩大問題亟需引起學界的重視。首先,個體特征對干預效果的影響,有些結論尚不一致,亟待更多的實證研究予以澄清,得出更為穩定的結論。再者,解釋個體差異調節作用機制的相關理論尚不完備,有待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在科學理論的框架下予以系統整合,明晰對干預效果產生影響的本質原因。基于現存問題,未來在開展感恩干預的研究和應用中,可從以下方向進一步深入。
3.1 規范研究程序,提升干預流程的標準化
關于個體差異對干預效果的調節作用,研究證據仍處于初期階段,有些結論還不一致。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既往干預研究采取的練習流程不一致,以及設置對照組的類型不同。比如,同樣是以個人的特質感恩為調節變量,Harbaugh和Vasey(2014)使用的細數感恩屬于自助式練習策略,而Toepfer等(2012)采用的感恩拜訪則涉及人際互動過程。此外,同一種干預的流程也尚未標準化。如Toepfer等(2012)要求參與者在三周內完成三封感恩信,借由主試郵寄給施惠者;而Kaczmarek等(2015)則要求參與者在每周完成三封感恩信,并自行遞交給施惠者以表達感謝。對此,未來研究有必要對同類型干預的流程進一步標準化,控制額外因素以更準確地探究個體特征對干預效果的作用,如采用數字化形式呈現統一的干預內容。另一方面,在研究程序上應統一設置惰性對照組和安慰劑對照組,更加嚴謹地評估干預效果中潛在的個體差異。
3.2 納入客觀生理指標,擴展個體特征作用的范圍
以往研究主要通過自陳式調查來衡量干預效果,由于測量指標的全距有限,加劇了天花板或地板效應的產生,由此阻礙了對個體特征作用的探究。采用客觀的生理指標評估則更加自然真實,對個體狀態的反映更為精確敏銳,有助于更為廣泛地探測個體特征作用的領域。伴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研究者可以通過如可穿戴傳感器和智能手環等新興技術手段,采集穿戴者的腦內神經機制、語音、體征、行為和環境等數據,即時獲取如內側前額葉皮層、眼動、心率和血壓等動態化的客觀指標,并結合主觀報告信息以全面評估干預的效果(劉冠民,彭凱平,2019;Kong et al.,2020)。
3.3 擴展個體差異特征在遺傳和生理層面的探索
現有個體差異特征的研究集中于心理特征、人格和動機等方面,缺少對遺傳類和生理類特征的探討。考慮到遺傳類基因和生理類指標有其客觀和穩定的優勢,有必要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在感恩干預中檢驗各種基因型和基因組合以及其他生理類特征是否具有調節作用。已有研究發現,兒童的副交感神經反應性和呼吸性竇性心律不齊水平能顯著調節其從促進備擇思維干預中的獲益程度,即對恐懼低反應的兒童受益更多(Gatzke-Kopp et al.,2013)。感恩干預作為一種特殊的積極環境,具備某些遺傳或生理特征的特定群體是否對其反應程度存在差異,未來研究應著手回答這一重要問題。
3.4 優化個體特征與干預內容的適配性,實現生態瞬時干預與評估
在應用層面,圍繞個體差異特征,為不同類型的參與者設計精準個性化干預方案,實現干預效應的最大化。比如,相比于低抑郁水平者,抑郁程度較高的人雖然可能從干預中獲益更多(Job &Williams,2020),但由于存在消極的認知偏差,自我啟動干預的能力更弱,使其初期練習感恩時存在一定困難。因此,針對該群體需為其在干預初期準備門檻較低的感恩暖身活動,降低他們參與的難度,幫助其逐漸沉浸到感恩練習中。此外,針對內在動機不足的參與者,可采取生態瞬時干預(Ecological Momentary Intervention;Smith &Juarascio,2019),將干預場景拓展到日常情境下,為參與者提供在自然情境下更具個性化的干預內容,提高練習的趣味性和生態性。同時結合數字化技術,利用智能手機APP、小程序或移動互聯設備,實時動態觀測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