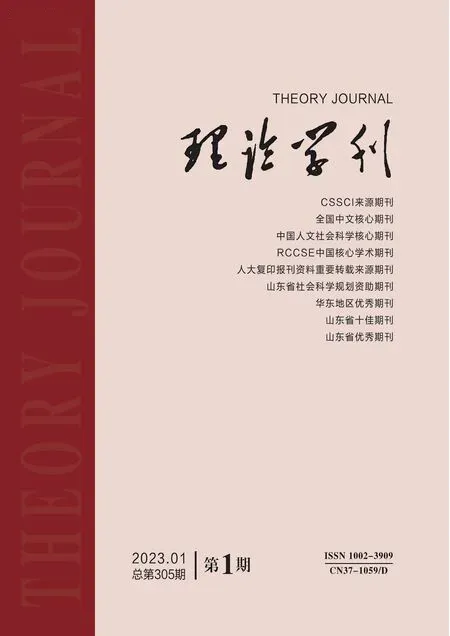黃老思想及其在宋初的實踐
王英娜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 大連116081)
黃老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資源,為現當代歷史學、政治學、文化及文學等領域的諸多學者所共同關注。從黃老思想本身來看,作為道家的一個重要分支,它更加注重對治世之道的思考,漢代的“文景之治”即是在黃老思想主導下創造形成的盛世景觀。漢武帝獨尊儒術后,黃老思想漸呈衰落之勢。然而考察相關文獻記載可以發現,黃老思想在宋初也發揮過重要的政治作用。對此,學界曾進行過專門的討論。有的學者認為宋初政治崇尚黃老,黃老思想對“宋初的統一和安定局面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1)張其凡:《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頁。;有的學者則肯認北宋是“繼西漢以后黃老思想流行的另一高峰”(2)李固盛:《論北宋的黃老思想》,《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那么,黃老思想是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了宋初的政治生活,其參與的方式與黃老思想內容之間有怎樣的關聯,黃老思想的參與對宋初國家治理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于這些問題,本文擬基于對宋前黃老思想生成與流變的考察,探討其在宋代政治中的基本參與方式及成效。黃老思想與其他思想流派一樣,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3)《元史》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517頁。,因而本文亦試圖通過爬梳史料,從不同方面探討宋代統治者對黃老思想的推重及其在政治文化中的融入。可以說,黃老思想參與了宋初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對于宋初的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黃老思想的產生與流變
在傳世文獻中,“黃老”一詞首先見載于《史記》。司馬遷不僅記錄了漢人對黃老思想的尊崇,而且追溯了它與先秦諸子的關聯,如謂申不害“本于黃老而主刑名”(4)《史記》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611、2612頁。,韓非之學“歸本于黃老”(5)《史記》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611、2612頁。,慎到、田駢、環淵等人亦“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并發明其“指意”(6)《史記》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852頁。,等等。先秦諸子對黃老思想的借鑒與融通,表征了后者作為諸子思想之濫觴的地位。那么何為黃老思想?《史記》中有多種表述,如黃、老二字并用的“黃老之言”“黃老之術”“黃老道德之術”“黃老術”等,也有黃帝、老子兩個人名連用的“黃帝老子之言”“黃帝老子之術”等,可見,“黃老”即是“黃帝老子”的省稱。《史記·樂毅列傳》亦記錄了從樂臣公到曹相國的一脈師承,并明確指出“樂臣公學黃帝老子”。他們無疑是漢代黃老學派的代表人物。
黃老思想以“黃老”命名,從字面看當包含黃帝思想與老子思想。不過在當下學界,學者們對于其中的黃帝思想有著不同的看法。張維華認為,黃帝并非歷史真實,黃帝之言不過是假托(7)張維華:《釋“黃老”之稱》,《文史哲》1981年第4期。;丁原明亦指出:“黃老學的基本內容應當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而不是老學與黃帝學的結合”(8)丁原明:《黃老學論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頁。。與之相反,李零則認為黃老之黃具有實在性的思想內涵(9)李零:《說“黃老”》,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157頁。;曹峰亦斷定:“黃老道家中,‘黃帝’與‘老子’兩種元素各占半壁,互為補充、缺一不可”(10)曹峰:《黃老道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四川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基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的黃帝史料,筆者比較傾向于后面一說。對于黃老思想中的黃帝的思想,我們也應認真考察和給予足夠重視。
首先,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我們可以看到,黃帝打敗炎帝,擒殺蚩尤,征戰南北,會盟諸侯。他“習用干戈”,是討伐殘暴之人的古部族首領。戰亂之時他正義護民,和平時期則有較多祭祀活動,即所謂“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對于治理國事,他則主張“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節用水火材物”(11)《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7、245頁。。對于人們的勞動生活,黃帝亦強調歷法,重視節令,可見其遵循天地規律、順應萬物死生的自然轉化,并以之指導民眾的生活與生產實踐。對于黃帝的治世之道與貢獻,司馬遷用“法天則地”四個字加以概括,并說“四圣遵序,各成法度”(12)《史記》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007頁。。可見,黃帝“法天則地”的治道不僅在當世惠澤了百姓,亦為其后的圣君“各成法度”提供了必要前提。此外,通過“法天則地”理念在社會生活中的記述,也刻畫出了一個敬天、愛民、教民、理政的崇高人君形象。在《史記》其他篇章中,與黃帝相關事件的記載時有所見,如“自上圣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13)《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7、245頁。、“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14)《史記》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41頁。、“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15)《史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500、1637—1638頁。、“黃帝封泰山”(16)《史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500、1637—1638頁。等,這些內容富含著黃帝治世的珍貴信息。
其次,《漢書·藝文志》記載,道家、陰陽家、小說家、兵家、天文家等諸家書目中,均有直接以黃帝命名的作品,數量大約有26種(17)《史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500、1637—1638頁。。此外,在先秦典籍中,亦可見與黃帝相關的具體記載,如《管子·任法》曾載黃帝的無為而治,謂“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又言黃帝通過“鉆鐩生火”而化天下。有學者認為,“鉆鐩生火”者并非黃帝,而應是燧人。對此,另有學者指出,“熟食為普遍用火,在發明為食之后,‘黃帝’二字不誤”(18)黎翔鳳:《管子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10頁。。其實,此句的關鍵并不在于說明“鉆鐩生火”的發明者究竟是誰,而在于傳遞出了黃帝重視和關心百姓生活的信息。對于黃帝的治世之功,亦有說他通過“五聲”“五行”“五官”等方法實現“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的描述和贊嘆(19)黎翔鳳:《管子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66頁。。關于黃帝的治世活動及思想,其他如《列子》《莊子》《韓非子》《山海經》《左傳》《國語》《逸周書》等先秦典籍中也有不少記述。值得注意的是,與《史記》相較,其他先秦典籍對黃帝的記載存在不少神話色彩,如《列子·黃帝》記載,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體驗到了“無利害”“無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等神境,并由此悟得“養身治物之道”,二十八年過后,“天下大治”“而帝登假”。何為“登假”?楊伯峻言:“《禮記·曲禮下》:‘告喪曰天王登假’,假亦作遐。登假乃帝王死亡之詞,猶言升天。”(20)楊伯俊:《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2—43頁。由此可知,“登假”乃是對黃帝去世的諱稱。
再次,關于黃帝其人的歷史真實性,一些新出土文獻也給予了印證。如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即記有不見于現存史籍的“黃帝伐赤帝”之事,稱黃帝在取得勝利后,實施了“休民,□谷,赦罪”等措施(21)《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頁。。孫子評議時,歷數黃帝南伐赤帝、東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從而“已勝四帝,大有天下”之功績,并將其“大有天下”之因歸為“得天之道、□之□、民之請(情)”(22)《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102頁。按:關于黃帝勝四帝,《太平御覽》卷79引《蔣子萬機論》:“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于是遂即營壘, 以滅四帝。”。對于《孫子兵法》的成書時間,學界一般認為在戰國時期或更晚,而銀雀山漢墓竹簡的出土則為其成書時間的前移提供了新證據,有學者據此判斷其成書于春秋后期(23)黃樸民:《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佚文〈吳問〉考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由此可以推知,在戰國之前,休民、順天、得民之情等黃帝治世之道已在社會文化中得到傳播。
從上述與黃帝相關的文獻記載看,黃帝思想多與治世有關,主要表現為法天則地、敬天愛民、無為而治等,其中,依循天地運行規律的治世原則應是黃帝治世思想的根本與主導,正如曹峰所言:“司馬遷用‘法天則地’四字形容黃帝,不是偶然的。《老子》之前,事實上存在著一個以天地之道為最高法則來指導人事活動的、更為原始的思想傳統,這個傳統后來以‘黃帝’的名義加以統稱。”(24)曹峰:《黃老道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四川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可以說,老子的“道法自然”與黃帝的“法天則地”一脈相承,老子的最高范疇“道”正是吸納了黃帝思想后的產物。
黃帝和老子思想的融合,也與后世統治者對黃帝的推崇有關。在傳說中,黃帝就已確立了戰勝四方的“始帝”地位,因此后世統治者均追溯于此,如司馬遷記夏朝始祖禹是“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25)《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3、119頁。,商朝始祖契的母親是黃帝曾孫的次妃(26)《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3、119頁。;《國語·晉語四》則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由此可知,姬姓周族的始祖亦追溯至黃帝。可以說,最高統治者向上溯源至黃帝的思維一直被后世效法,而齊威王以黃帝為高祖的做法,更成為黃帝和老子思想融合的重要推動。田氏代齊后,齊威王欲將其祖先溯源至黃帝,以證明其統治的合理性,戰國時的青銅器銘文記錄了當時的情況:“唯正六月癸未,……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朝向諸侯,合揚厥德。……以蒸以嘗,保有齊邦。”(27)引自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頁。齊威王不僅自言其遠承黃帝,而且在治國上也體現了對黃帝的推崇,稷下學宮的創辦便是明證。《管子·桓公問》記載:“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風俗通義·窮通篇》則稱:“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尊寵之。”可見,齊國稷下學宮的創辦當是對黃帝“明臺之議”的繼承與發展,它促進了諸家思想的交流與融合,而黃老思想亦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得以發展和走向成熟。
司馬遷將融通諸家的黃老思想概括為“道德之術”。司馬談在評析“六家要指”時言:“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8)《史記》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993—3994頁。從諸家名稱與評析內容的對應關系看,文中所言“道家”即是“道德”一派,其特點既指向個體內在的精神世界,也包括側重事功的治世之道。對于后者,司馬談以“術”稱之。通過以上評述,我們可以看到,“道德之術”兼采陰陽、儒、墨、名、法等諸家優長,并具有適時應變、無所不宜、易操而多功的成效。正因為有此優勢,黃老思想得到了漢代統治者的重視,并將其應用于國家治理之中。
漢初,黃老思想即盛行于世。高祖、呂后、惠帝、文帝、景帝統治時期,黃老治世理念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并最終創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觀。武帝獨尊儒術后,黃老思想日漸式微,即便仍有一些官吏習慣于以黃老之學治理政事,如汲黯、鄧章等,但已非主流大勢。劉秀建立東漢,亦愛好經術,推崇以儒治世的政治實踐。雖然面對戰亂后的民生凋敝之局,他奉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但黃老之學已然處于政治的邊緣地位。黃老思想原本包括內在精神與外在政治兩個方面,當它的政治功能被淡化后,其個體精神方面的潛能便相應地凸顯出來,如帝王們祈求長生,往往要從黃老思想中求取妙道。東漢桓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29)《后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82頁。,黃老思想與神仙家結合的宗教化,說明其已走向了精神世界的終極。綜觀漢代,黃老思想經歷了從政治到養生、再到宗教化的流變過程。
漢代以后,黃老思想之余脈與內在精神仍不斷流傳。兩晉時,玄佛合流;南北朝時,儒、釋、道三家在沖突中融會發展;隋唐時,統治者推行三教并行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思想上,唐代統治者相對而言更推崇道教,如高祖詔令“先老,次孔,末后釋宗”(30)劉林魁:《集古今佛道論衡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77、229頁。;太宗言“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31)劉林魁:《集古今佛道論衡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77、229頁。;玄宗亦崇奉道教,并“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32)《舊唐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409頁。。但是在政治上,儒家仍是社會統一、政權鞏固所仰賴的主導思想,如唐太宗曾言:“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33)《資治通鑒》第13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054頁。可以說,此一時期,黃老思想已化為一股暗流融入到道家、道教與治國安民之中。至北宋,這股暗流再次顯明起來,參與到國家治理之中,促進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新發展。
二、宋初統治者與黃老思想
唐末的戰亂使得百姓死傷相枕,經濟衰敗凋敝。面對社會的滿目瘡痍,如何使新興政權得以穩定和鞏固,如何盡快恢復戰亂后的生產與生活秩序,是宋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宋太祖基于晚唐以來的諸多弊端,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立法,在文化上則尤其重視儒、道、釋文獻的整理,其中,黃老思想以及由此演化而來的道教,因了統治者的重視和推崇而得以融入北宋朝廷的治國安邦實踐之中,并對北宋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
其一,對黃老治道的接受運用。作為開國之君,宋太祖非常重視治國之道。史載,他曾詢問左右侍臣:“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34)《宋史》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頁。在他看來,“通治道”是讀書的目的,因此,當聽聞到黃老治世之道時,他便由衷地表現出喜愛和接受的態度。開寶二年(969),太祖召見道士蘇澄欲求養生之法,蘇澄言:“臣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則異于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3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26頁。蘇澄的回答包含了黃老思想中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養生之道,一個是治世之道。帝王大都有學養生、求長生之愿,因此,道士是其召訪的重要對象,太祖召見蘇澄即有此意。不過,從蘇澄回應的內容看,他并未局限于養生,而是從養生延展到了治世,即君主“無為”“無欲”從而使民“自化”“自正”。這顯然是黃老思想中“無為而治”的社會理想。對于蘇澄的回答,太祖大悅而厚予賞賜。此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記載,太祖也曾向處士王昭素詢問治世養身之術,王昭素答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深以為然,書之于屏。太祖對黃老思想的喜愛與接受,使其在施政中呈現出黃老治世的特征,同時也激發了他之后的統治者對黃老治道的推崇。
黃老的“無為而治”融合了儒、道、名、法等諸家主張,其中,法家學說的融入是黃老治道的特色之一。《黃帝四經·經法·道法》即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可以說,黃老思想對法的重視,為“君無為”“民自正”提供了保障。宋太祖建國后,即開始了革除時弊及助力于政權鞏固的各種立法工作。同時,他也注重“恩威兩得”(3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頁。,可謂深得“刑德相養”的黃老之旨。太宗即位后便宣布沿承太祖遺制:“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守,不敢逾越。”(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頁。并告誡臣子須“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3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62、758、797頁。。在為政上,太宗亦多次直言“黃老之道”,體現出對黃老思想的積極推崇。與太祖相較,太宗更側重于對黃老清靜政治的推行,如淳化四年(993),在與大臣們討論治道時,太宗即明言自己要力行“黃老之道”,他說:“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對此,參知政事呂端表示了贊嘆,而宰臣呂蒙正則以實政之事相與探討,并以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為據,鑒于“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建議“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對此,太宗回答說:“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3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62、758、797頁。從太宗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黃老之道的理解,即清靜無為并不是停止一切有為的活動,而是應在臣子的有為中實現無為。從“不欲塞人言”這句話中可以見出其為政的開明與寬和。太宗的回答亦詮釋了自有為而至于無為的力行之徑,可謂深得黃老之旨。太宗不僅自己推行黃老之治,而且以此教導真宗(當時為開封尹):“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4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62、758、797頁。之后,真宗、仁宗等均承繼先帝遺志,沿襲了黃老的清靜之治,如真宗自稱:“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靜以臨民。”(41)《宋史》第3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515頁。仁宗在冊文中亦言:“宗黃老之言,尊高清凈。”(42)《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5頁。宋初歷任統治者的重視,使黃老思想得以在朝野流行開來并發揮作用。
其二,對老子之言的政治省思。在宋代,隨著黃老思想的流行,老子思想亦成為帝王治世思維中的重要鏡鑒。宋太宗在治理國家過程中常會想到老子之言。當“有司請備冬狩之禮”時,太宗想到的是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之語。老子認為,若以狩獵作為娛樂放縱的游戲,那么將會導致人的心性放蕩,難以收止。對于“冬狩之禮”,太宗即以老子之語為訓誡,告訴左右:“朕今順時蒐狩,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4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頁。這種對畋獵之樂的節制分明體現了黃老思想中的王者之術,正如《黃帝四經·經法·六分》所言:“知王術者,驅騁馳獵而不禽荒,飲食喜樂而不湎康。”太宗將可能導致“心發狂”的冬狩,轉化為“為民除害”的活動,體現了帝王智慧。雖然從外在行為上看并沒有變化,但這種內在動機的不同,使其具有了道德境界與政治意義上的根本差別。
宋初統治者對于文、武的態度,也不乏老子的影響。太宗曾對近臣言:“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4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頁。老子明確指出戰爭會給人帶來災難,在為了正義“不得已而用之”時也要“恬淡為上”(45)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9頁。。老子的反戰思想對于太宗而言無疑頗有觸動,但是完成太祖未竟的統一大業是他必須承擔的歷史重任,故而他“三復以為規戒”,盡可能把戰爭的規模和造成的破壞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內。或因如此,宋遼之間的戰爭時斷時續,直至真宗時代,以“澶淵之盟”的簽訂為標志,彼此間的百年和平終告開啟。當然,宋初統治者所實行的偃武修文、重文輕武的政策,也為后來軍事上的積弱埋下隱患,這說明老子治道的精髓并未得到準確的領會和把握。
其三,對黃帝其人的尊崇效法。黃帝很早就被尊奉為華夏始祖。宋朝建立后,黃帝受到格外的推崇,太宗、真宗等均曾下詔安排對黃帝的祭祀活動,如太宗頒詔曰:“祀土德于黃帝壇,圭、幣、牢具如太祠,俾祠官領之”(4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55頁。;真宗亦“詔諸州有黃帝祠廟,并加崇飾”(4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831、1637頁。。從詔文內容看,宋初統治者很重視祭祀的儀式和規模,相關規定使得祭祀黃帝的活動更為莊嚴和普遍。與此同時,黃帝的治世之道也更加深入人心,如真宗在鼓勵群臣進諫時即以黃帝為典范,詔曰:“在昔黃帝有下風之問,伯禹有昌言之拜,勤納規諫,以致雍和,……今順考舊規,延進讜議。”(48)[宋]王稱:《東都事略》第1冊,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24頁。群臣在進諫時也往往列舉黃帝的事例,如仁宗時參知政事宋庠在對帝王出行時的車駕禮儀提出建議時,便首先言及了黃帝,指出“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為營衛,蓋所以防微御變也”(4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038頁。。這里對黃帝的強調值得玩味,因為就黃帝出行時的陣仗而言,后人其實是難知究竟的,而漢魏唐五代的行儀卻是史有明載,然而即便如此,宋庠仍要將黃帝的行儀拿來說事,這無疑反映了當時黃帝在君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在宋初,黃帝不僅是一個被祭祀的祖先神的形象,而且是一個值得效法的圣君明王,其盛德遺范足以為天下表率。
其四,對道教文化輔治作用的重視發揮。道教與黃老思想雖然存在差別,但是兩者的關系卻不失密切。黃老思想含有治國與養生兩個方面,而道教的形成主要是“沿著它的養生思想,以及這種養生思想的神仙化而表現出來的”(50)丁原明:《黃老學論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頁。。在宋代,統治者對道教的推崇與對黃老思想的重視可謂相得益彰。從宋太祖開始,就有推崇道教的一系列舉措,如修復宮觀、選拔道官、規范道士等,并曾多次問道求教。雖然道教的終極目的是體道合真、羽化長生,但其修養理論亦可指導現實生活,如太宗曾言:“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臥,至于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覺得力。……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調適。……無自輕于攝養也。”(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88頁。太宗的養生實踐與黃老思想中的養生之理頗為一致,《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即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太宗所謂“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老子之言,并不見于傳世本《道德經》,而見于《抱樸子·黃白》所引之《龜甲文》,其云:“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從內容來看,它顯然具有道教丹道的特點,且強調了人在生命過程中的能動作用。太宗以之為老子之言,反映了老子天命自然思想的黃老化與道教化。至真宗時,則開始以“神道設教”,“天下始遍有道像矣”(5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831、1637頁。,進一步推進了道教的發展。此外,宋初統治者亦重視對道教典籍的募求與整理,如太宗時啟動了《道藏》的修訂,真宗時完成了《云笈七簽》等藏外道書的編撰。從文獻記載看,宋初統治者還注重發揮其輔助治國的效用,如《混元圣紀》稱,太宗淳化二年(991)重修太清宮,“自是凡水旱必遣使祈禱,屢有感應”(53)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6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頁。。此外,宋初統治者也重視道教中的因果教育,引導民眾行善止惡,這與黃老思想中“德積者昌,殃積者亡”(54)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77頁。的觀念亦具有一致性。宋初統治者很少關心道教中的羽化成仙之事,而是將敬神與愛民及性德涵養相結合,重在實現道教的政治作用。
南懷瑾先生在所著《老子他說》中嘗言:“細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會發現一個秘密。每一個朝代,在其鼎盛的時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秘訣,簡言之,就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自漢、唐開始,接下來宋、元、明、清的創建時期,都是如此。”(55)《南懷瑾選集》第2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這番闡述雖然看上去似乎有些絕對,但是也并非沒有道理,至少與宋初的情況是相契合的。宋初統治者較少探討道家和道教中幽遠、玄妙的問題,而是高度重視黃老治道,從而較好地完成了整飭綱紀、休養生息、養民阜物的治政實踐。
三、黃老思想與宋初治理成效
宋太祖懲于唐末五代之弊政,改弦易轍,實行了揚文抑武、偃武修文的基本方略。他推重黃老思想,踐行黃老治道,其系列舉措為身后的統治者提供了依循的章法。太宗、真宗、仁宗沿襲成制,進一步推行清靜無為之治道,促進了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
宋朝建立之初,太祖實施休養生息的政策,這為社會經濟整體的發展營造了寬松的環境,并使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以及商業經營迅速恢復了正常的秩序。雖然當時面臨著南北統一的戰爭任務,但是太祖仍強調“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民”(5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2、404、554頁。。他體恤民情,重視減輕農民的負擔,曾為繼位君主立下戒語,對此,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在所著《宋論》中記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其中的第三條“不加農田之賦”即生動體現了對農民和農業生產的體恤,同時也表達了對保持休養生息政策連續性的高度重視。在減輕農民的徭役和賦稅負擔的同時,太祖還十分重視水患的治理和水利工程的興修,使得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大為減輕,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水陸交通和商貿活動迅速走向活躍,不僅醫治了綿延上百年的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而且在較短時間內就把國家的經濟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因此,史家把太祖建隆年間的這種治理盛況稱作“建隆之治”。太宗即位后,繼承太祖遺志,實行清靜無為之治,而減輕刑罰與減免租賦是其重要體現。史載,太宗登基之初,即“降詔恤刑”(5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2、404、554頁。;在治國理政實踐中,他亦時常提出節用愛民的思想主張,曾明確告誡“官吏不能為朕經度”(5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2、404、554頁。,告誡群臣不要“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而應“共務均節,無致厚斂于下”(5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18、921頁。。因了對于太祖治國之道的這種因循和傳承,太宗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繼續得到較快發展,商貿流通更加興盛和繁榮,社會治安良好,百姓生活富足,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進一步增強。真宗登基之后,同樣遵循祖宗成法,直言“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6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18、921頁。。咸平元年(998)四月,當得到朝臣關于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稅數額巨大、百姓無力繳納、地方官經常催收且借機勒索的奏報之后,真宗當即下令:凡屬積年拖欠的田賦,一律免除。此后,他還多次下詔減免各地賦稅、開倉賑濟災民。真宗重視開荒,鼓勵擴大耕種面積,同時積極推動改良作物品種,他在位期間,北宋的耕地面積增加到了5.25億畝,比盛唐時期的5億畝還要多,畝產量也從唐代的每畝約2石提高到了3石,增幅達50%。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真宗實行戶籍改革,從而促進了市民這一新興社會階層的興起,推動了手工業和商業經濟的發展。生活在真宗時期的魏野“早衙連廟鼓,夜市雜船燈”(61)[宋]魏野:《三門與臧奎推官聯句題東樓》,張文欣主編:《河洛水韻·洛陽歷代詠水詩輯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頁。的詩句,無疑是當時城市發展、物阜民豐、商貿繁華景象的生動寫照。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就是真宗年間出現的,由此亦可證知當時商業貿易的蓬勃發展與空前繁榮。根據有關學者的統計和測算,真宗時朝廷的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每年的各項收入總額相當于地域遼闊的大唐帝國歲入的7倍,即便是災荒年份,各項收入仍然相當于唐太宗貞觀年間歲入的3倍,可謂是富甲天下;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相適應,真宗時北宋的人口也顯著增加,短短的20多年間,全國的戶數就增加了416萬戶,人口突破了一億,相較宋太宗時期增長了46%(62)參見張志偉:《古代中國王朝盛世》,合肥:安徽少兒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頁;薛存心:《宋真宗的“咸平之治”與啟示》,《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對于真宗在位期間特別是咸平年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盛況,史家名之曰“咸平之治”。南宋史家王稱在所著《東都事略》一書中對咸平之治作了如下描述:“宋興,承五季之余,天下得離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來,君明臣良,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請和,示以休息,德明納款,撫以恩信。……絕代曠典莫不具舉,禮樂明備,頌聲洋溢。崇本報功,以告神明,千載一時,豈不休哉! 噫,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成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63)[宋]王稱:《東都事略》第1冊,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31頁。其中雖然不乏溢美,但是基本的事實應當是真實可信的。在這個意義上,王稱把咸平之治同歷史上著名的周初成康之治及漢初文景之治相提并論,并不為過。
同時,尊重知識與人才的尚文政策,推動了宋代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宋初統治者不但禮遇、重用知識分子,而且使科舉選士成為常制,其擴大錄取名額之舉則為更多士人打開了入仕門徑。朝廷以此網羅了大批治世人才,同時也促進了宋初教育的發展,社會文化風貌整體上也由唐末的消頹轉向醇厚,而那些具有黃老思想傾向的文人也積極對當世的社會治理提出意見和建議,如王昭素、呂端、馮元等。對于圖書文獻,宋初統治者亦非常重視,并對儒、道、釋等各類典籍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求和整理。如太宗時編纂了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真宗時曾將《道德經》《南華真經》《沖虛至德真經》等道家典籍校畢刊印;仁宗時則命集賢館校定《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等,而雕版印刷的發展更是促進了書籍的流通,由此激發了開卷有益的讀書之風。太祖提倡武將、大臣讀書,太宗、真宗、仁宗除自好讀書外,亦重視臣下、士人通過讀書增智、廣見以利于治世。可以說,宋初的崇文政策及相對寬容的文化環境,促進了三教思想的交匯與融合,成就了宋初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總之,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幾代統治者對黃老思想的推重和應用,為宋初社會提供了相對寬和的環境與氛圍,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同時亦為社會整體的安定和有序運轉提供了積極的助力。當然,宋初統治者的治國理政也并非無可指摘,歐陽修就曾在奏議中指出:“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偷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6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556頁。南宋朱熹更是直率批評太宗、真宗兩朝“可以有為而不為”(65)《朱子語類》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044頁。。對此,有識之士大聲疾呼革弊除害、完善政治,仁宗朝的“慶歷新政”便是這種救治時弊的積極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