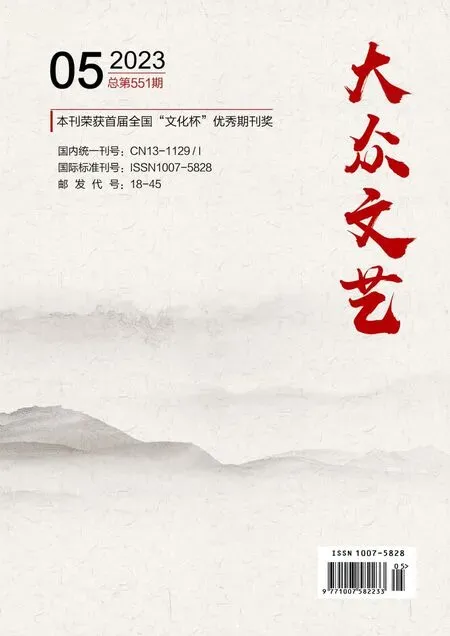探究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興起的原因和發(fā)展歷程*
徐 婧
(南京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江蘇南京 210024)
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在上海掀起的一場由群眾自發(fā)組織參與的救亡圖存運動,日寇發(fā)動的侵華戰(zhàn)爭讓中華大地的半壁版圖淪喪敵手,在此國破家亡的環(huán)境下,上海的熱血群眾在音樂家們的引領下,將抗戰(zhàn)歌詠作為武器開始了揭露敵軍丑惡行徑、喚醒大眾奮起抵抗的艱難路程,對后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
一、抗戰(zhàn)歌詠運動在上海興起的原因
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創(chuàng)救亡歌詠運動之先河,九一八事變是在東北爆發(fā)的,戰(zhàn)火半年后蔓延至上海,那么,為何是上海率先刮起了抗戰(zhàn)歌詠的狂風,除了受戰(zhàn)爭形勢的影響,還得將原因歸結于上海的特殊地位。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上海一直是外來侵略者青睞的寶地,他們一方面帶來了殺戮與掠奪,另一方面也給上海帶來了畸形的繁榮和多元的文化,這些無疑都造就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特殊性,為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興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上海是學堂樂歌的試驗場
歌詠是群眾集體歌唱的形式,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學堂樂歌,上海和學堂樂歌淵源頗深。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一批愛國人士意識到落后的教育是中國百年積弱的主要原因,想要改變這個局面必須進行教育變革,同時他們還發(fā)覺了音樂在思想啟蒙中的重要作用,康有為最早在《請開學校摺》中指出:“令鄉(xiāng)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shù)、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yè)。”[1]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寫道:“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2]由此引發(fā)了學堂樂歌運動,學堂樂歌中的“學堂”指的是廢除科舉制度后建立的新型學校,“樂歌”指的是學校中開設的音樂課,是集體唱歌的形式。
學堂樂歌早期的推廣者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三人,其中沈心工和曾志忞都是上海人。沈心工1900年時與南洋公學師范班的同學一起籌辦了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這所學校正是第一所將“樂歌課”列入課程設置的學校,在這所學校任教期間,沈心工編寫了《學校唱歌集》和《重編學校唱歌集》,教授學生們集體詠唱《男兒第一志氣高》等歌曲。曾志忞同樣在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教授音樂,在學堂樂歌運動中,他編寫了《教育唱歌集》是我國音樂教育的第一批教材,還編譯了《樂典教科書》,這是中國最早的系統(tǒng)完備的關于西方音樂體系的樂理教科書,除此之外,曾志忞還在上海地區(qū)推行社會音樂活動,極大地提高了上海的師資力量,當時上海樂歌課的水平和普及范圍之廣是遠遠領先于其他城市的。
雖然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變法最后迎來了悲劇結尾,新學制未能全面落實,但值得慶幸的是,學堂樂歌運動獲得了成功,不僅真正達成了將音樂教育作為社會化的國民素質教育的目標,還成功地推廣了群眾集體歌唱的形式,為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興起作了準備,上海經(jīng)此成為醞釀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溫床。
(二)專業(yè)音樂人才集聚上海
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歸根結底是一場音樂運動,音樂人才的助力是必不可少的,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的上海已經(jīng)聚集了一大批專業(yè)音樂人才,這些音樂家的出現(xiàn)是抗戰(zhàn)歌詠運動在上海興起的重要前提。
抗戰(zhàn)前夕聚集在上海的音樂人才可分成兩個群體,一是蕭友梅、黃自、江定仙、陳田鶴、劉雪庵等為主要代表的上海國立音專師生,還有一部分是深受左翼革命文化影響的音樂人才,最具代表性的有聶耳、任光、張曙、呂驥、田漢、安娥、賀綠汀、沙梅、冼星海等,這些音樂家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逐漸形成了一支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音樂隊伍。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上海是國際音樂大師薈萃的城市,還有號稱“遠東第一”的管弦樂隊,鑒于這兩點優(yōu)勢,蕭友梅決定在上海籌建創(chuàng)辦音樂院校,1927年11月時上海國立音專誕生了,這是中國第一所高等音樂教育機構,雖然上海當時得風氣之先,但受各封建理念的桎梏,當時的招生非常困難,在此窘境下,上海國立音專依然堅持嚴苛的教學標準,給中國樂壇輸送了眾多精英學子,學校所教授的西方先進音樂技術豐富了歌曲創(chuàng)作的體裁,大大助益了抗戰(zhàn)歌詠運動。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誕生,左聯(lián)最初專注于文學領域,后擴大到美術、戲劇、音樂等領域。1930年7月聶耳到達上海,受左翼文化運動影響,政治思想和音樂技能提高,九一八事變后,他日夜思索怎樣服務于民族解放和革命事業(yè),實行了撰寫音樂短論、創(chuàng)作抗戰(zhàn)歌曲、創(chuàng)辦音樂小組等舉措,推動了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發(fā)展,與他同陣營的還有任光、張曙、呂驥、沙梅、冼星海等人,他們作為左翼音樂文化立場上的音樂家群體,為掀起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立下了汗馬功勞。
推動抗戰(zhàn)歌詠運動在上海興起的兩個音樂家群體雖政治立場不盡相同,音樂觀念和創(chuàng)作作風有所區(qū)別,暗藏對立,但同時存在相當?shù)穆?lián)系和共同點。總言之,抗戰(zhàn)初期上海的兩大音樂家群體圍繞愛國和救亡的主題唱響了相同的主旋律,推動了抗戰(zhàn)歌詠運動在上海的興起。
(三)發(fā)達的報刊業(yè)和都市新媒體提供傳播路徑
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是一場群眾性的愛國歌唱運動,需要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才有可能達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預期效果,而運動的宣傳動員工作顯得重要非常,上海發(fā)達的報刊業(yè)和都市新媒體正是承擔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
20世紀初,由于時局的變動,人民群眾渴求得到動蕩社會時期的時事訊息,報刊涌現(xiàn)再掀高潮。“1927年后,滬寧一帶成為全國報刊的中心,上海一地的報紙超過五十家,全國日發(fā)行量五萬份以上的報紙全部集中在上海。”[3]由此可見,上海在抗戰(zhàn)初期已經(jīng)具備了全國其他地區(qū)的宣傳陣地,報刊是抗日救亡運動宣傳的主要載體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fā)行的《樂藝》《音樂雜志》等期刊上每期都設有專門的欄目刊登音專師生創(chuàng)作的抗日救亡歌曲,除了專門的音樂期刊外,在《申報》《立報》《讀書生活》《上海青年》等各書刊上刊載的抗日救亡音樂的內容同樣豐富多彩,如音樂曲譜的問世、歌詠活動的報道、歌詠團體招收會員的通知、歌詠工作推行的大綱等,后期還有專門的歌曲集的出版,這些內容有助于激發(fā)民眾參與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熱情,從而積極主動地自發(fā)參與抗戰(zhàn)歌詠活動。
報刊業(yè)是書面?zhèn)鞑サ耐緩剑酥猓€有一些都市新媒體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如電影業(yè)和唱片行業(yè)。上海的電影業(yè)自鴉片戰(zhàn)爭后萌芽,逐漸發(fā)展壯大,1928年有“遠東第一電影院”之稱的大光明影院的落地后達到巔峰,占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但“九一八”事變和上海“一二八”事變的爆發(fā),令上海輝煌的電影業(yè)深受打擊,電影工作者開始拍攝反映現(xiàn)實抗爭和表達民眾心愿的戰(zhàn)爭故事,隨著電影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有聲電影的誕生給抗日救亡歌曲的傳播提供了新的路徑,如《旗正飄飄》是電影《還我河山》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是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曲等,這些歌詠作品和電影作品相互滲透和融合,帶給民眾無盡的震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上海的唱片行業(yè)主要依靠三家公司發(fā)展,分別是東方百代唱片公司、大中華唱片廠和上海勝利唱片公司,其中百代唱片公司所占市場份額最重,1928年時由任光擔任百代首位音樂部主任,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徐家匯百代小樓中,常常可見聶耳、冼星海、賀綠汀等人的身影,他們將創(chuàng)作的歌詠作品錄進唱片中,廣泛地傳播在群眾中,影響深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集中國報刊業(yè)、電影業(yè)、唱片業(yè)三大行業(yè)的中心于一身,特殊的地位營造出特殊的環(huán)境和氛圍,賦予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傳播的新路徑,給予抗戰(zhàn)歌詠運動強有力的宣傳支持。
二、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發(fā)展歷程
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掀開了全國性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序幕。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自“九一八事變”后已出現(xiàn)雛形,1934年后逐漸遍布到人民群眾中,1936年至1937年間,群眾歌詠是整個上海最受歡迎的活動,可惜的是,“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后不久,這場運動的高潮戛然而止,隨著上海遭受重創(chuàng)開始孤島時期,抗戰(zhàn)歌詠運動由盛而衰,上海慢慢失去了歌詠中心的地位,歌詠中心由此轉向了武漢。
(一)萌芽形成階段——抗日救亡歌曲開始傳唱
1931年9月18日,駐中國東北的日軍借“柳條湖事件”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日軍掠奪中國版圖,殺戮中華民族同胞的殘忍行徑令人發(fā)指。上海國立音專的師生們率先作出反應,黃自、蕭友梅領導音專師生創(chuàng)立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抗日救國會”,創(chuàng)作愛國歌曲,激勵軍民勇氣,喚醒國人。他們創(chuàng)作了早期的抗戰(zhàn)救亡歌曲,積極傳唱,借此達到為東北義勇軍募捐的目的。黃自創(chuàng)作的作品《抗敵歌》是我國最早的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歌曲,作品強烈表達了中華民族要求團結抗日的強烈愿望,除此之外,還有蕭友梅創(chuàng)作的《義勇軍》《從軍歌》,黎錦暉創(chuàng)作的《向前進攻》,劉雪庵創(chuàng)作的《前線去》等愛國歌曲廣為流傳。
日本的荒蠻野心在“九一八事變”后尚未得到滿足,在侵占東北三省以后,他們很快又在上海發(fā)動“一二八事變”。事變爆發(fā)后,韋瀚章和黃自合作創(chuàng)作了四部合唱《旗正飄飄》,表現(xiàn)了“國亡家破,禍在眉梢”的悲憤情緒,塑造了中華民族英勇抗爭的偉大形象,這首號召性強且富有藝術性的作品是抗戰(zhàn)音樂會歌詠的保留曲目。
1933年春天,在上海地區(qū)左翼文化影響下的左翼音樂組織粉墨登場,以聶耳、任光、呂驥為代表的青年音樂家們,相繼組織了一系列著名的音樂團體,他們在左聯(lián)的機關刊物上發(fā)表音樂相關文章,除此之外,他們還集中研習群眾歌詠的創(chuàng)作,給進步電影、戲劇配樂,譜寫歌曲,創(chuàng)作了《抗敵行軍曲》《前進歌》《大路歌》《漁光曲》《畢業(yè)歌》等廣泛傳唱的抗戰(zhàn)歌曲,為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繁榮作了必要準備。
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在左翼音樂工作者的積極支持下,1935年2月,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學生干事劉良模主持成立了最早的、影響最廣泛的抗日救亡歌詠組織——民眾歌詠會,這標志著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正式形成,從民眾自發(fā)進行的歌詠零散活動變成有策劃、有組織、有宣傳的歌詠活動集合。
(二)邁向高潮階段——歌詠團體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
民眾歌詠會的創(chuàng)立是標志也是開端,自創(chuàng)立后,隊伍日愈龐大,但僅憑這一歌詠團體是無法滿足群眾投身抗日救亡歌詠的激情的,業(yè)余合唱團應運而生,這是一支1935年5月由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音樂小組組織領導由呂驥發(fā)起的重要抗日救亡歌詠組織。
1935年至1937年兩年間,在民眾歌詠會和業(yè)余合唱團的啟發(fā)下,上海的歌詠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大概有六十余支隊伍,這一盛況可在《立報》“花果山”欄目中窺見,在“花果山”欄目中推廣的歌詠團體包括但不限于:洪鐘歌詠團、蜜蜂歌詠團、大同歌詠隊、農民歌詠隊等。
歌詠組織的涌現(xiàn)意味著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發(fā)展有了領導者和組織者,這些歌詠組織“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既專注于走向學校、農村、工廠、女校等地宣傳教唱歌詠作品,也不忘合集體的力量舉辦盛大的歌詠集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聶耳逝世追悼會”“淞滬抗戰(zhàn)四周年紀念大會”“魯迅葬禮挽歌游行”“援綏音樂會”等,這些集會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占據(jù)了輿論高地,有效地鞏固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除了歌詠的教唱與演出,音樂家們敏銳地覺察到大眾需要歌曲集,因此順運動發(fā)展的需求,出版了《中國呼聲集》《大眾歌聲》《青年歌集》等歌曲集。總而言之,救亡歌詠團體已然成為這時抗日民主愛國的中堅力量,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點燃了抗日的烽火,同時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愈加洶涌澎湃,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迎來了最后的高潮。城市、農村、工廠、學校,各行各業(yè)爭相成立了歌詠隊,“國民救亡歌詠協(xié)會”正是此時組織起來的,集六十六支歌詠隊伍的力量傳唱新的抗戰(zhàn)歌曲,宣傳抗日救亡。“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前后,上海的歌詠團體已多達一百有余,聯(lián)抗將此局面比作“矯捷的海燕”,活躍在市民眼前,歌詠著暴風雨的來臨。這個高潮是輝煌且短暫的,僅三個月后,迫于各方壓力,歌詠中心進行了轉移,從上海撤出,逐漸轉向武漢,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由盛而衰。
(三)崎嶇發(fā)展階段——歌詠活動隱蔽進行
1937年8月13日,中日雙方在上海進行鏖戰(zhàn),三個月后,11月13日,國民政府發(fā)表告全體上海同胞書聲明,淞滬會戰(zhàn)落下帷幕。這場大戰(zhàn)雖打破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但中方還是傷亡慘重,失敗而告終,隨之而來的是上海的淪陷,此時上海開始孤島時期,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由公開活動轉為隱蔽進行。
淞滬會戰(zhàn)戰(zhàn)敗后,中央江蘇省委發(fā)出《關于新環(huán)境下上海組織工作決定》,遵循決定的精神,上海出現(xiàn)了聯(lián)誼會、俱樂部性質的組織,成為當時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活動的主要陣地。這一時期活躍的組織主要有“上海銀聯(lián)”“益友社”“華聯(lián)同樂會”“職業(yè)婦女俱樂部”等,還有一部分學校歌詠組織。各組織發(fā)揮自己的力量運用歌詠來團結、教育群眾,他們積極排演作品,分別到學校、農場、工廠、難民收容所去教歌,利用義演所得救濟在滬難民,募集寒衣鼎力支持英勇抗戰(zhàn)的新四軍。
1939年5月發(fā)表的《上海歌詠的新生》中描述了大批歌詠運動干部和工作者向武漢轉移后,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幾近沉寂的境況,但因群眾亟須歌唱,公開的合唱團體開始建立起來,積極的歌曲傳唱起來,1938年12月底開始籌備統(tǒng)一領導組織,直到劉良模回滬的歡迎大會上正式建立起來,這一組織主要負責團結歌詠,培養(yǎng)干部和供給歌曲三項事宜。此時上海的抗戰(zhàn)歌詠運動沿著不同的路徑艱難地推進著,一面推動著歌詠在人民群眾中的傳播,一面為抗戰(zhàn)歌詠輸送著歌詠骨干。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共發(fā)出了“隱蔽精干,積蓄力量”的指示,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進入“冬眠”狀態(tài),至1943年才蘇醒過來,開始出現(xiàn)零星的歌詠活動,直至抗戰(zhàn)勝利后民主歌詠運動興起后歌詠又火熱起來。
結語
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是抗戰(zhàn)音樂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浩浩蕩蕩的歌詠運動培育出一大批愛國音樂人才,促進了時代之音的探索,豐富了戰(zhàn)時及戰(zhàn)后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弘揚傳承了抗戰(zhàn)精神,增強了中華民族的生命力量。回顧上海抗戰(zhàn)歌詠運動,探究其興起的原因和發(fā)展歷程有助于積極推廣催人奮進的抗戰(zhàn)音樂文化,助力創(chuàng)新新時代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音樂發(fā)展,凝聚起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