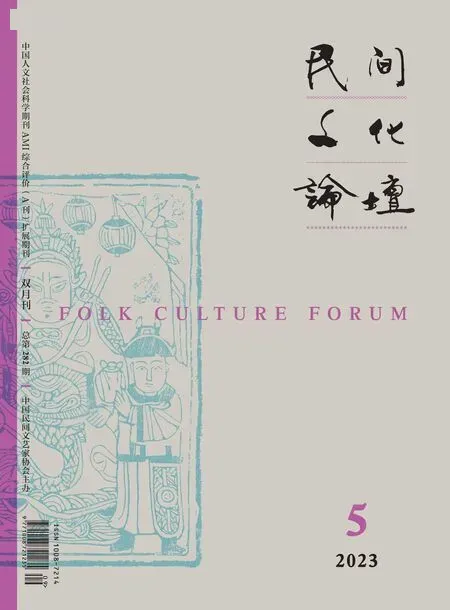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禮從宜”與“不求變俗”的“誤讀”史及其民俗學意義
李 濤
一、“禮從宜”與“不求變俗”的現代解讀
在民俗學剛興起時,周作人、江紹原就圍繞“禮俗”進行過比較研究,然而江紹原之后,民俗學研究主要關注“俗”,對于“禮”關注不多,少有民俗學者關注“禮俗”這一范疇。“近年來,漸有民俗學者重新思考禮儀對于理論話語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①蕭放、何斯琴:《禮俗互動中的人生禮儀傳統研究》,《民俗研究》,2019 年第6 期。,禮俗研究再次引起重視,也引發了很多學者的討論。
在論及禮俗關系時,《禮記·曲禮》的“禮從宜,使從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被反復引用,并被視為禮俗互動、禮源于俗的重要依據。不少學者據此認為從先秦、兩漢起,中國思想就有肯定、尊重民俗的傳統。劉志琴在《禮俗互動是中國思想史的本土特色》中提出:
這兩者的關系是:“禮失而求諸野”,“禮從宜,使從俗”。有生活才有規范的禮,所以俗先于禮,禮本于俗。俗一旦形成禮,上升為典章制度和道德準則,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和強制性的力量,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②劉志琴:《禮俗互動是中國思想史的本土特色》,《東方論壇》,2008 年第3 期。
張士閃策劃的“禮與俗”系列,總序《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開頭就引用了這兩句話,用以論證民俗與國家政治運作的關系:
在三禮之學中,“禮俗”問題已是中國古典思想的一大命題……“禮從宜,使從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禮記·曲禮》等)等。至漢代,猶有傳言“子曰:禮失而求諸野”(《漢書》)。由此可見,在“禮”愈來愈制度化的大趨勢下,“俗”逐漸轉為潛在地卻又是堅韌地繼續參與國家政治運作,這其實是世界文明進程中的一般規律。③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 年第6 期。
張勃對移風易俗的關注選取禮俗研究的另一路徑,《風俗與善治:中國古代的移風易俗思想》主要討論中國古代的移風易俗思想。這一思想,顯示的是以禮化俗的主流傳統,是要改造“俗”,但她同時引用了“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用以補充歷來也有主張尊重民間選擇的傳統:
《禮記·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可見亦有人主張不一定要對風俗進行移易,而是充分尊重民間的選擇,順其自然即可。①張勃:《風俗與善治:中國古代的移風易俗思想》,《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年第5 期。
總之,在現在的學術語境中,“禮從宜”與“不求變俗”都普遍被用來描述禮俗關系,禮是規范化、制度化的國家典章制度、政治運作,俗是民俗,并且這兩句話被認為是早期文獻中,少有的肯定、尊重民俗的表述。
二、《禮記》本文、漢唐注疏的原意
然而,在《禮記·曲禮》的原文語境中,在漢唐的經典注經傳統中,“俗”并非指民間習俗,這兩句話也并不是在論述典章制度與民俗的關系,更不是禮不變俗、禮隨民俗的理論支撐。
“禮從宜,使從俗”,鄭玄用晉士匄帥師侵齊不待君命而還的典故來注解:
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使從俗,謂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亦不可常也。②《禮記正義·卷一·曲禮上第一》,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2662 頁。
這一典故出自《春秋》,《左傳》《公羊》《谷梁》三家均有闡釋。《春秋》的原文是: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③《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四·襄公十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272 頁。
杜預為這句話做的注是:
禮之常,不必待君命。④同上,第4274 頁。
孔穎達詳細解釋說:
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為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使從俗者,使謂臣為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為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⑤同上,第2663 頁。
顯然,東漢鄭玄、西晉杜預、南朝皇侃、唐代孔穎達的注疏,都認為“禮從宜,使從俗”是用來描述臣子出使、出征之法的。“禮從宜”是在表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將軍在外出征,進退可以不待君命;“使從俗”是指外交官出使他國時,朝聘牲幣從本土出,不可去境外尋求本土沒有的物資。這與今天“禮俗互動”語境下的“禮從俗”完全不一樣。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一條,《禮記·曲禮》原文是: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后;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⑥同上,第2721 頁。
在原文語境中,很明顯是用來指君子去國遠行居于他國時,也要踐履本國故禮,不能變用當地的禮法,在去國三世之后,如果在故國無列于朝、無詔于國,才能變為施行新國禮法。所以孔穎達正義明確指出,“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①《禮記正義·卷四·曲禮下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721 頁。這里的“俗”也并非指民間因而襲之的民俗,而是指故國的禮法。因此,在《禮記·曲禮》原文中“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也并不是在說“充分尊重民間的選擇”。
鄭玄的注是:
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②同上,第2721 頁。
鄭玄明確指出,這句話是用來表示居他國時,不變先祖之法。比如夏殷后代,在他國居住時,也要行夏殷之制度。孔穎達的正義說:
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于齊魯,齊魯之臣,入于杞宋,各宜行己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③同上,第2722 頁。
孔穎達也認為,“君子行禮”的“行禮”,指的是大夫去先祖之國居他國,比如杞國、宋國的臣子去齊國、魯國,或者齊國、魯國的臣子到杞國、宋國,都要遵行本國禮法,也就是說,“不求變俗”的“俗”,其實也是“禮”,只是不同國家、不同族群的禮法,而不是民間習俗。總之,在《禮記·曲禮》原文里,在鄭玄、孔穎達的注疏里,這句話是說,離開故國,依然施行故國禮法,不改變為他國禮法,與今天的理解有很大區別。
在《儀禮注疏》中,鄭玄引用“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表達了另外一重意思,《儀禮》“若不醴,則醮用酒”下,鄭玄注:
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圣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④《儀禮注疏·卷三·士冠禮》,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063 頁。
在這里,鄭玄用“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來解釋“國有舊俗可行,圣人用焉不改者也”。孔穎達指出:
鄭云:“若不醴,國有舊俗可行,圣人用焉不改者也。”云圣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引《曲禮》據人君施化之法,不改彼國舊俗,證此醮用舊俗之法也。故《康誥》周公戒康叔,居殷墟當用殷法,是以云茲殷罰有倫,使用殷法,故所引《曲禮》皆據不變彼之俗。但“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有二途,若據《曲禮》之文……謂臣去己國居他國,不變己國之俗。⑤同上,第2063 頁。
也就是說,鄭玄“圣人用焉不改”是指,西周初年,周天子分封到地方的諸侯,在統治夏殷遺民的時候,要用夏殷的禮法,這里的舊俗,指的是夏殷等其他國家或民族的禮法,而不是今天所理解的民間習俗。實際上“禮”“俗”仍然是用于描述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禮法制度,而不是上層的禮制與下層的民俗。注《周禮·誦訓》“以知地俗”時,鄭玄再次以與此相同的意義引用,來表達人君統治新國,不求變更新國的舊禮。因此,北朝熊安生、唐朝孔穎達也都認為“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有兩重意思。認為這句話可以用來描述人臣,也可以描述人君,在形容兩種不同的主體時,表達著不同的意思。熊安生對《禮記·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的解讀是:
與此不同者(與鄭玄注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于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于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①《禮記正義·卷四·曲禮下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722 頁。
如果說鄭玄在他處引用“不求變俗”時使用了其他意思,在《曲禮》原注下還是忠于原文,那么在熊安生這里,在對《曲禮》原文注解時,就直接加入了人君治理新國,不須改變舊俗,并主要是從古代明君治理新國案例中尋找事實依據。
鄭玄的注、孔穎達的正義,分別是漢代經學和唐代經學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漢唐經學的最高成就,塑造著一代代學者的讀經傳統,西晉杜預、南朝皇侃、北朝熊安生,也分別代表著一代學人的觀點。可見,在漢唐經學傳統中,對《禮記·曲禮》中這兩句話的主流看法,還是忠實于原文,即“禮從宜,使從俗”,是在說為君出使出征之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在說人臣去他國不改故國禮法,或者人君不改新國之禮法。
而現在的學術界,是在政治文化分層、雅俗禮野的意義上理解這兩句話,把禮理解為國家制度、上層禮制,把“俗”依照現在對“民俗”的定義,理解為民間承襲的下層民俗,用這兩句話來描述國家典章制度對民間風俗習慣的尊重與吸納。
這明顯是對《禮記·曲禮》原文和漢唐注疏的“誤讀”。
三、宋代經學與明清經學的誤讀
然而,這樣的“誤讀”,并不是從現在開始的。
宋人衛湜《禮記集說》采摭群言,鄭玄注以下,所取注《禮記》者一百四十四家。②衛湜:《禮記集說》提要,四庫全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1 頁。其中,有關于“禮從宜,使從俗”的注解,除了鄭注孔疏,還有以下六種宋人注:
藍田呂氏曰: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體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周還而無窮也……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之類。使于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永嘉戴氏曰:儒行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雖圣人亦不敢為異以駭俗也……宜者義也,禮與義俱禮,不合宜是為非禮之禮。俗非流俗之謂,風俗各有所尚,故曰入國而問俗,茍非俗之所安,君子不以為禮。
王氏又曰:夫禮者天下萬世所通行非止為一槩設也,使知時中之義,務當其可而已,則委巷之人皆可以為禮,故曰禮從宜。禮不從宜,夏裘而冬也;使不從俗,山魚鱉而澤鹿豕也,而可乎?
長樂陳氏曰: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夫以誦詩之多不足以議禮與為使,則禮之與使,其可不知變哉!
廬陵胡氏曰:禮從宜,從時之宜,使從俗,役使人必從俗所便。
新安朱氏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吊齊,齊裴昭明以兇服吊魏,蓋得此義。③衛湜:《禮記集說》卷一,第33—36 頁。
可以看到,呂大臨強調禮要因時而變,戴溪強調禮要合義,王子墨強調禮要符合時中之義、務當其可,陳祥道強調禮以義起、知變,胡銓的解讀是禮從時宜(他還把“使”誤解為“役使”),朱熹的解讀是事之所宜。
可見,在宋代的注經中,對“禮從宜”的注解,已經較為普遍的從解讀為出征出使之法,變為禮要因時而變、合乎義理,將軍在外出征、進退自決的意義已經少有學者再提。這一解讀與鄭注孔疏,就發生了很大的偏離。對“使從俗”的解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朝聘物資用土俗所出,不可境外求物,轉為側重出使他國時入國問俗、“入境隨俗”。
然而,在宋人的這幾種注解中,對“禮從宜,使從俗”的解讀,普遍地還是認為禮要因時因義而變,不必泥古,比較少將這句話用來描述俗先于禮、禮對俗的整合。也就是說,是描述歷時性的禮制允許因時變遷,而不是描述共時性的上層禮制接受、吸納下層民俗。關于“禮從俗”,《困學紀聞》還有這樣一條: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①王應麟、翁元圻:《困學紀聞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第1409 頁。
在這里,王應麟還特意論證《慎子》“禮從俗”的表述是錯的。
到了明清,對這句話的注解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黃以周《禮書通故》,對于“禮從宜,使從俗”的語序,形成了和王應麟截然相反的解讀:
以周案:《初學記·政治部·奉使類》大書“從宜”二字,注引《禮記》“使從宜,禮從俗”。史徵《周易口訣義·觀卦》引先鄭注“從俗所為,順民之教”,并引“太公封齊,五月報政,禮從俗”。玩注引士匄事,亦證使之從宜,非證禮,下云“牲幣之類”,乃言禮之從俗也。孔疏本“使”“禮”二字已誤倒,當依徐、史引為是。使從宜者,《聘禮記》所謂“辭無常”。《公羊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禮從俗者,《曲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②黃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1217 頁。
與王應麟據《曲禮》認為《慎子》“禮從俗則非”不同,黃以周反而從文義出發,認為歷來流傳的《曲禮》版本中,“使”和“禮”位置是錯的,正確的應該是“使從宜,禮從俗”。并引“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證本句話的意思是施行禮制要順從民俗,這就與現在學術界的主流理解一樣了。
目前看到的《禮記》各種版本及注疏中,只有黃以周提出了“禮”“使”二字錯位的推測,少有其他學者回應,一般還是讀為“禮從宜,使從俗”。但將這句話的意思闡釋成“禮從俗”的做法,在明清注經中大量出現,甚至逐漸成為主流。明代郝敬《禮記通解》:
君子用禮義以為質,茍生今反古,矯世絕俗,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蓋禮強世則難行,宜民則可久,此處世群俗,毋不敬也。③郝敬:《禮記通解》卷一,浙江汪啟淑家藏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3 頁。
將這句話解讀為推行禮制不能強制推行,要方便民眾,不可矯世絕俗。
方苞《禮記析疑》:
圣人制禮,乃從義之所起,而使民行禮,則必因其俗而利導之。居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所必革,則因其俗而變通之也。④方苞:《禮記析疑》卷一,四庫全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2 頁。
方苞認為禮從宜的意思是制定禮儀時,要因俗利導、因俗變通、因俗制禮。
蓋禮固有一定之節,而時異勢殊,有不盡合者,亦當從權以行之,不可執也。如使固有一定之禮,而俗有不同,亦當從之。
汪紱的《禮記章句》:
先王之世,家不殊俗,然或有風土所囿,小若不同之間者,可從則從之,不為駭俗耳。若禮之大經,不可變者,而亦曰從宜,末俗之反道敗德,必不可從者,而亦曰從俗,則同流合污,其為害大矣。讀者無失記者之意焉,可也。①汪紱:《禮記章句》卷一,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2 頁。
汪紱是從消極的意義上來闡釋“禮從俗”的限度,認為如果面對反道敗德的末俗,也要從俗,那就是同流合污。雖然是消極角度,但也可見,他認為這句話是在描述禮制與民俗的關系,并且很可能是在反駁當時行禮從俗的思潮。
劉沅《禮記恒解》:
適乎中而不膠于一,是從宜也。使人不必遽矯其俗,而裁之以義,如孔子獵較是也。蓋圣人因時立法,通變宜民,皆如此。②劉沅:《禮記恒解》卷一,道光八年(1828)豫誠堂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2 頁。
劉沅將這句話理解為不必改變民俗,只需裁之以義,通變宜民。
也就是說,到了明清,不少經儒對“禮從宜,使從俗”的解釋,已經與現在民俗學界所理解的意思基本一致了。
看起來巧合的是,“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的注解,有著非常相似的變化過程。或許是因為“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的上下文更加明確,“誤讀”的空間比較小,衛湜《禮記集說》中所收宋及以前注經,大多與鄭注孔疏同,較少有發揮:
橫渠張氏曰:行禮不求變俗于新國。
藍田呂氏曰: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
馬氏曰:喪祭從先祖是也。
廣安游氏曰:所謂國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而不茍然也。
廬陵胡氏曰:俗謂本國之俗,君子居本國不當變易風俗,求合于禮而已。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逾久可以忘故俗。
孔氏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
臨川王氏曰:故國各有法也。
藍田呂氏曰:可以變舊國之俗從新國之法矣。
嚴陵方氏曰:夫于朝猶有列于國,猶有詔于家,猶有宗與族,則彼所以待我者,恩好猶未絕也,如之何其遽絕之哉,則反告之禮固所冝矣。
馬氏曰:去國三世而恩義不靳,理固然也。
廬陵胡氏曰:孔子去宋既久,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不從新國之法者,與此異也。
廣安游氏曰:于其興起為卿大夫之日,然后從新國之法焉,皆所以重其本之道也。③衛湜:《禮記集說》卷十,第22—25 頁。
衛湜所收宋代十余種解讀中,只有廬陵胡氏把俗解讀為“本國之俗”,把這句話誤讀為君子居于本國,不應當變易風俗,只求合于禮,與今天的理解有些相同。《欽定禮記義疏》所收馬晞孟的注解:
從俗,禮也;變俗,亦禮也。求變俗,非禮也,君子之于俗也,可則從,否則變。《周禮》本俗六,以安萬民,《易》在革則去故,在鼎則取新,豈故拂民以求變俗哉?①允祿等:《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四庫全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15 頁。
不拂民變俗,是說不改變民俗,也是在與今天類似的層面上使用,其余宋人傳注,均解讀為去國行禮之法。可見,在宋代,對《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原文的注解,大部分還是嚴格遵守漢唐注疏的。
到了明清,雖然還有一些傳注忠于原文和漢唐注疏,但將這句話解釋為推行禮制不更改民俗的傳注,卻還是變得多了起來,比如以下幾種。明郝敬《禮記通解》:
君子守禮,不茍同于俗,然亦當諧人情,合時宜,不必以己意輕變俗。②郝敬:《禮記通解》卷二,第3 頁。
“俗”已經徹底沒有了“故國禮法之舊”的含義,這句話也就被解讀為君子但求自己守禮不必改變民俗。姜兆錫《禮記章義》:
所謂宜于土俗也,其法即所謂國之故也,如其故則不變俗,然謹修而審行之,則亦不至以俗而違禮矣。③姜兆錫:《禮記章義》卷一,清雍正十年(1732)寅清樓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25 頁。
“土俗”“不以俗而違禮”,是在與“禮”相對的意義上使用“俗”,而不僅是在本國與他國禮制對比意義上使用“俗”,也就是轉為在禮儀和民俗意義上使用禮和俗了。汪紱《禮記章句》:
喪祭異俗,如山國麋鹿,澤國魚鱉,葛绖檾绖,魯合衛離之類,在所可從者也,此即“禮從宜,使從俗”之意,然曰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則其行之也,亦非茍同。④汪紱:《禮記章句》卷一,第26 頁。
認為這句話與“禮從宜,使從俗”(這已經是誤讀了)一樣,是在說喪祭禮儀,各地異俗,可以選擇適合的方式,“在所可從”。孫希旦《禮記集解》:
蓋禮之大體不容或異,而其儀文曲折之間不能盡一,故冢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者其所同,俗者其所不盡同者也。⑤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五,清同治七年(1868)孫鏗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8 頁。
對“俗”的理解,從故國禮法之舊,變成了與“禮”相對的“不盡同者”,“禮”是所同的“禮之大體”,“俗”就是各國不盡相同的儀文曲折。劉沅《禮記恒解》:
禮本人情而為之節文,故君子不遽求變俗,即祀喪大事亦從其俗而裁制之,但期于不違其法,曰謹修審行,則所以權其是非,去取不戾俗而亦不背禮者在焉,夫子獵較而正簿書,鄉儺必以朝服,是其義也。⑥劉沅:《禮記恒解》卷二,第2 頁。
指出君子不遽求變俗,祀喪大事也可以從俗裁制,去取不戾俗。郭嵩燾《禮記質疑》:
案不求變俗,正謂所處之地之俗,君子不求立異也,注反以去國用其故俗為言,則亦有意立異矣。⑦郭嵩燾:《禮記質疑》卷二,清光緒十六年(1890 年)思賢講舍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第6 頁。
郭嵩燾反而據此否定舊注,認為鄭注孔疏的“去國用其故俗”的解讀是錯誤,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君子行禮,不求更改自己所處之地的“俗”。
可見,明清經儒有不少無視了“去國用其故俗”的傳統注解,相當普遍地解釋為君子施行禮制,不更改民俗,與現在學術界的對這兩句話的用法大體相同。
四、誤讀史的民俗學意義
顧頡剛分析孟姜女故事的流變,說“就歷代的時勢和風俗上看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①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王霄冰、黃媛選編:《顧頡剛中山大學時期民俗學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49 頁。。新加入的分子,雖然不是故事的本來面目,但可以代表當時的時勢和風俗。對于注疏,也可以這樣看,新加入的觀點,雖然誤解了原文的意思,是對舊注的偏離,但可以代表當時學者的意見,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不同認識。通過梳理可以發現,“禮從宜,使從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本來的意義都與現代學術界的理解不同,并且在漫長的注經傳統中不斷發生著“誤讀”。傳注的誤讀史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參照證據,證明“從俗”的思想確實存在,并在不斷地演變。
在這兩句話的原文和漢唐的注疏中,“俗”主要是在空間意義上使用的,都主要是用來區分不同國別與民族的禮法,用以規定出征出使、去國遠行、治理新國時對待故國禮法的態度。
宋代注疏中,對兩句話的注解產生了“誤讀”,對“不求變俗”的理解還比較遵照舊注,對“禮從俗”的解讀更多在時間意義上展開,突出制定禮法可以因時而變,但還比較少出現要尊重民俗的注解。
在明清注疏中,禮與俗的階層對比開始凸顯,逐漸形成了與現在學術界同樣的解讀,即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幾種當代學者的觀點:君子制定禮儀要尊重民間的選擇。
必須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梳理的范圍嚴格限于傳注傳統中對“禮從俗”和“不求從俗”兩句的文本注解,而沒有考察其他使用。比如北宋程頤曾引用說:
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如法。“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②程頤、程顥:《二程遺書》卷一八,四庫全書本,第97 頁。
在這里程頤引用“禮從宜,使從俗”的時候,已經是用來佐證禮制從民俗(“河北舊俗”)的意思了。關于禮“從俗”的實際操作,出現得就更早了,比如唐代開元年間的一份制書:
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定式。”③杜佑:《通典》卷五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1451 頁。
就已經明確體現了禮制吸納民俗的實踐。也就是說,在《曲禮》傳注中,明清才成為主流的“從俗”思想,其實唐宋時期已經出現于實際操作中了。受限于經典與考據,經學傳注所體現的思想是相對滯后的,應當是已經在知識分子中成為比較有勢力的思潮之后,才能逐漸影響到經學傳注。
經儒拘于考據。在注經時,有上下文語境,有鄭注孔疏,還要依照嚴格的注經原則,也不應該出現誤讀,然而偏離還是在不斷發生。這更說明了“從俗”思想在明清已經成為相對主流的意見。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里,經學居于最核心的位置,經學思想是整體學術思想的核心,在經學傳統中演繹的思想流變,最能代表主流傳統思想,也會對其他層次的思想帶來影響。
鐘敬文先生晚年指出:
作為文明古國,它的內部有著文化層次的區別,中、下層文化是其基礎部分……這使我們民族擁有豐富的民俗文化遺產,同時也表現出民俗文化與上層文化的歷史聯系……從這種意義看,現代中國的民俗學運動,繼“五四”運動之后崛起,不過是前述歷史聯系的遞進,并帶有革命性質的表層化罷了。①鐘敬文:《民俗文化學發凡》,《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5 期。
鐘老說中國文化中,民俗文化與上層文化的歷史聯系一直存在,現代中國的民俗學運動不過是這一歷史聯系的“遞進”和“革命性質的表層化”。筆者對這一表述十分贊同。從經典的形成期,到漢唐經學、宋代經學,再到乾嘉學派,“禮從宜”“不求變俗”在兩千多年經學傳統中的誤讀史,實際上意味著,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思想演進過程中,注經的知識分子對民眾文化的態度在不斷發生變化。
如前所說,當“禮俗研究”重新興起后,有學者以“禮從宜”“不求變俗”為證,論證先秦兩漢時期就有尊重民眾文化的傳統。本文通過梳理證明,這兩句話在原文和漢唐的注疏中,主要是用以規定出征出使、去國遠行、治理新國時對待故國禮法的態度,并不是表達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的尊重,或者國家制度對民眾習俗的吸納。
另一方面,在20 世紀學術史上,一般都認為古代的知識分子是看不起中下層文化的,在振聾發聵的《圣賢文化與大眾文化》演講中,顧頡剛說:
他們(民眾)是努力創造了些活文化,但久已壓沒在深潭暗室之中,有什么人肯理會它呢,——理了它不是要倒卻自己的士大夫的架子嗎!②顧頡剛:《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王霄冰、黃媛選編:《顧頡剛中山大學時期民俗學論集》,第178 頁。
甚至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學科起點也正是基于這一判斷:
說到民眾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極了,我們要研究它,向哪個學術機關去索取材料呢?別人既不能幫助我們,所以非我們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③同上。
一直到20 世紀末,主流意見也還是如此:
在我國過去的長期封建社會中,一般出身(或依附于)上層階級的文人學者,是看不起中、下層文化的。④鐘敬文:《民俗文化學發凡》,《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5 期。
從“禮從宜”的使用與注疏來看,至少在北宋程頤引用“禮從宜,使從俗”時,已經與今天學者們的理解一樣,而在明清注疏中,更已經普遍理解為“禮從俗”了。可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關于民眾文化的態度,并不是五四一代學者認為的,幾千年來“只取‘目笑存之’的態度”⑤顧頡剛:《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王霄冰、黃媛選編:《顧頡剛中山大學時期民俗學論集》,第178 頁。,實際上至遲在唐宋時期,已經有尊重、肯定民眾文化的思想了。“從俗”思想處于不斷的歷史演進中,在明清又有新的發展,并且越來越生機勃勃、熠熠生輝,一直遞進到近現代。“某種現代學術意識從外部刺激了的他們的這種‘潛意識’”⑥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 1918—1937)》,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68 頁。,歌謠運動、民俗學運動興起,現代民間文學、民俗學學科產生,掀起了“革命性質的表層”化高潮。
當然,本文僅僅梳理《禮記·曲禮》這兩句話的經學傳注,實際上是比較局限的,無法展示“從俗”思想的整體面貌。禮俗何時開始主要在上下分層的意義使用、“從俗”思想的源流演變系統等民俗學重要問題,尚待進一步系統地發掘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