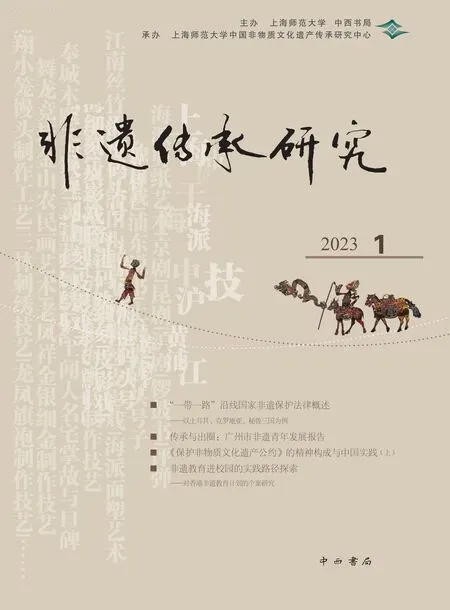上海小校場年畫春牛圖圖像特征與民俗心理研究
蒲 嬌 張麗婷
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農業國之一,農業活動與天象、氣候、季節、物候的關系密切。立春之日標志著一年中重要農耕時節的到來,伴隨如“迎春”“打春”的習俗,民間逐漸衍生出當日貼春牛圖的習慣。作為傳統年畫最后一個繁榮階段的代表,“上海清晰呈現了中國年畫消失的歷程痕跡”。[1]春牛圖作為小校場年畫中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年畫種類,真實反映了不同時期民眾的生活習慣、審美情趣和關注熱點,生動再現了清末至民國初期上海城市的歷史風貌,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
一、春牛圖年畫淵源
1.“打春”與“打春牛”
“打春”行為至遲出現于周代,《事物記原》中有“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2]的記載。每年春季時節,封建社會掌權階級通常會舉行祭田典禮,“牛”在其中是鄉土社會象征豐收的重要吉祥物,諸多禮儀風俗圍繞其展開。
明正德年間《松江府志》記載,立春前數天,官府衙門會差人扎制紙春牛,骨架為竹篾編就,肚內裝有稻谷、麥子、菜籽等農作物種子,外糊彩色紙張,芒神從本地十六七歲身體靈巧、善于歌舞的男子中挑選扮演。立春日早晨,儀仗隊伍自府衙出發,鳴鑼者行走于隊伍最前端負責開道,后隨擎依仗執事的差人及吹打演奏者,邊走邊舞的芒神扮演者及四人抬著的紙春牛位于隊伍中部,松江一府兩縣(華庭縣、婁縣)的武官佩戴盔甲、穿皂服、騎大馬緊隨其后,最后是一府兩縣的文官出場,縣官在前,府首殿后。隊伍出東門、經紫陽宮,折往西行,過北門,到菜花汀停止。在此擺開陣勢,三文、三武共六位長官手執皮鞭抽打紙春牛,待牛肚被打爛后,看是哪類種子先落地,據此占卜當年農作物的豐歉收成。禮畢,官員返回衙門,設春宴、食春餅。此習俗自明代興起,直至辛亥革命后在滬地持續近六百年。江滬一帶民間立春日祭祀芒神習俗略為簡單,民間祠堂集會祭祀完畢,飲迎春酒、食春餅、春盤,以求來年風調雨順,易于田桑。
2.春牛圖圖像溯源
“打春”“鞭春牛”作為立春日中一項重要節俗延續下來,并且衍生出各類與之相關的民間藝術形式。民間最初出現了一種用以預測當年降雨量及農事收成的雕版印刷春牛圖圖鑒,常見于通勝①又稱“通書”,舊時黃歷。或萬年歷內頁中。后被民間年畫藝人巧妙運用于年畫創作,并與生產生活廣泛結合,融入四時節氣表、十二生肖、天干地支等物候歷法元素,最終形成兼具審美性與功能性,并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春牛圖歷畫。
年畫春牛圖起源于何時何地何人無確切記載。據《中國風俗通史·宋代卷》記載:“在不搞‘鞭春’儀式的廣大農村,則盛行在墻上粘貼‘春牛圖’,以觀四時節序。”[3]以此推測,至遲宋代具有視覺圖像意義的春牛圖已在民間廣為流傳。清代道光年間顧祿所作的《清嘉錄》中,有對農歷春節期間的蘇州玄妙觀廟會描述:“賣畫張者聚市于三清殿,鄉人爭買芒神春牛圖。”[4]清代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進春》有云:“立春日,各省會府州縣衛遵制鞭春。京師除各署鞭春外,以彩繪按圖經繪芒神土牛,舁以彩亭,導以儀仗鼓吹。”[5]可見自宋至清,春牛圖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廣得民眾喜愛。另有文獻記載:“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6]45進貢宮廷的春牛圖與民間相比制作更為考究,其色彩構圖需根據立春年月日時的天干地支進行搭配,且每年均由欽天監制定。相比之下,民間流行的春牛圖雖也有所禁忌,但不似宮廷有如此多戒律,在視覺體驗上更顯活潑有趣,圖像種類紛繁多樣,更貼近民間審美與民俗生活。總之,遲至清中晚期,春牛圖類型的歷畫已在江滬一帶普遍流行,且獲得各階層廣泛認可。小校場年畫發軔于江蘇桃花塢,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清嘉慶年間已有年畫生產。這一點在春牛圖題材年畫的圖像特征及民俗心理表達方面可得窺見。
二、上海小校場年畫春牛圖的圖像特征
隨著打春習俗的歷史演進,春牛圖的圖像特征與文化內涵也發生了變化,所刻畫形象逐漸融合不同地域的民俗特征而日益生動豐富起來。各地春牛圖年畫多以“春牛”與“芒神”作為畫面主要符號,然而與北方突出春牛與芒神的主體形象不同,小校場春牛圖普遍將二者進行形象弱化、面積減小的處理,但依然將二者設置于畫面較為中心的位置。
1.“我現”與“他想”:春牛圖畫面場景的寫實與想象
某一類年畫的盛行,無疑與年畫藝人依據長期制作與文化經驗對題材體裁、內容風格、表現形式等方面的預判和選擇,以及作為欣賞者、消費者、購買者等身份的地方民眾的審美傾向與興趣喜好密不可分,二者可被認為是雙向選擇下的“互惠”結果。換言之,即是年畫創作者對消費者審美偏好加以預測后,對某一文化符號、生活場景或民俗活動進行合理的畫面再現,這其中既要滿足百姓的想象力又要兼顧呈現的真實性,縱然是將自身對事物的理解加以表現,也必須為對方提供合理化的想象空間。
年畫藝人的苦心創作與消費者審美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以春牛圖為藍本加以改造的《末代皇帝月歷圖》(見圖1)可說明問題。清宣統三年(1911 )辛亥革命爆發,次年2 月12 日,隆裕太后代溥儀頒布《退位詔書》,溥儀被迫退位,清朝統治結束。根據民眾普遍于年前置辦年歷的習俗,此圖無疑在溥儀退位前已印制完成,恰是對清廷尚未覆亡時的一曲臨終奏鳴。春牛位于畫面最中央下方醒目位置,置于華毯之上,外刻“天下太平”四字篆書。此圖中共計有28 人,時年7 歲的溥儀端坐于攝政王載灃懷中,兩旁官員根據官職依次按照秩序站立,構圖基本呈對稱布局。條案周圍繞4 人,分別為御前大臣、侍衛大臣各2 名。兩側各有11 名大臣,著補服,戴朝珠,穿朝靴,除畫面最前端2組人物略有動作變化,他人動作幅度不大,雙手或自然下垂,或手端朝珠,皆表現出肅穆恭謙的朝堂景象。所有人物均在其周旁有官職介紹,畫面左側部分為舊衙門稱謂,如大理寺、太常寺、翰林院、宗人府、光祿寺、鸞興衛①筆者并未查到有關“鸞興衛”的記載,僅根據畫面進行文字轉寫,待勘誤。另有“鑾儀衛”一詞,為清代為宮廷服務的機構,掌管帝、后車駕儀仗。清順治元年(1644)設,初沿明制稱“錦衣衛”,次年改稱“鸞儀衛”。清順治十一年(1654)厘定品級、員額,遂成定制。據清昭梿《嘯亭雜錄·鑾儀衛》記載:“本朝鸞儀衛相沿明錦衣衛之制而不司緝探之事。”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說象》:“象房在宣武門內城跟迤西,歸鑾儀衛管理。”、九門提督、內閣學士等。畫面右側為部分新衙門稱謂,如法部、郵傳部、民政部、陸軍部、度支部、農工商部、督察院、電政大臣等。另有兩處仍使用舊衙門稱謂,如吏部、侍郎等。左側前端兩名大臣互相朝向對方行打拱作揖之禮,右側前端兩名大臣行請安禮儀,兩側空白處書寫“各大臣道喜”“各大臣恭賀”等吉祥語。此外,整體畫面設置似為朝堂之上,中間人物身后有象征宮廷禮儀的華蓋、執扇、旗等,也有精致的廊柱、絹花作為裝飾,整體畫面刻畫出一派奢華的“偽繁榮”景象。

圖1 《末代皇帝月歷圖》[7]
通過此圖不難看出:一方面,小校場年畫藝人具備較高的個人素養,體現在對國家各職能部門的了解及其對時事類年畫題材的把握與篩選上。縱然不是朝堂的親歷者,卻能通過合理化想象,利用畫筆描繪的“我現”滿足消費者的“他想”,民間藝人在對服飾、姿勢、神態及構圖設色等細節把握上嚴謹工細,又與消費者甚為熟悉的春牛圖寓意結合,期望天下太平、風調雨順,從而使年畫銷量得以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作為年畫主要消費群體的民眾,雖然難以改變束縛千年的“君臣綱”思想,跳脫封建社會制約,但依舊期望通過年畫滿足自身窺探時事的愿望。無論是何原因,均體現出作為民眾的“小傳統”向國家“大傳統”靠攏的內心訴求。
2.留存與舍棄:“西化”的滲透與表達
在小校場年畫的諸多題材中,新聞時事畫、時裝仕女畫與月份牌年畫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特別是隨著石印技術的普及,小校場“月份牌畫”逐漸于清末繁榮起來。其創作與春牛圖、九九消寒圖及二十四節氣圖等傳統歷畫關系密切,在此基礎上催生出各類具有廣告宣傳作用的年畫,對新事、新物、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較高。如在1905 年以后的春牛圖中,表達歷法除使用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之外,普遍引入西方歷法的使用方式,如“禮拜”制度。
在《大清光緒三十四年》中,春牛與芒神刻畫于中心線,但位置較為下移。芒神為孩童形象,右手手執樹枝,左手牽引繩索,位于春牛右側。芒神春牛之上刻亭閣,懸“四海升平”匾額,內有武財神執元寶單腳踏于聚寶盆上。四周分刻八仙,各顯神通于翻滾海上。在《大清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春牛圖》中,春牛芒神位置也處于中心偏下,芒神身著花衣頭梳兩髻,騎于春牛背上,右手揚鞭,左手握繩,憨態活潑。身后有五路財神端坐及若干侍從站立,財神手執金鞭、如意、珊瑚、元寶等法器,侍從表情文者恬淡、武者威嚴,手執依仗及兵器。兩幅作品的創作時間均為光緒三十四年,即1908 年。此年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平靜,各地反抗舊制活動頻發,且歷經光緒帝駕崩、慈禧太后病逝、溥儀繼位等重大事件。因此,通過年畫表達對“四海升平”“國泰民安”的美好暢想,無疑是暫時麻痹對社會動蕩、時局不穩之憂慮的一劑良藥。
3.在場與疏離:符號的堆積與消逝
就目前留存的小校場年畫可見,絕大多數春牛圖題材年畫都將芒神與春牛形象作為組合符號出現,且與歷法功能結合緊密。但也有部分年畫將春牛與芒神放在較不突出的位置,甚至無芒神、春牛出現卻仍被冠以春牛圖之名,如《大清光緒三十年春牛圖》。但無論有無芒神、春牛符號,只要能傳遞“一年之計始于春耕”的信息,并將“日歷”作為圖像符號的中心,冠之春牛圖,便合乎民眾心理。受生產力發展的限制,人類對季節變化的規律并不能完全了解和掌控,大部分春牛圖會在畫面重要位置刻畫最具物候指導意義的“二十四節氣表”。其預測功能不但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能,更可對部分惡劣氣象進行一定規避。
盡管春牛與芒神總被作為標準化符號強調,其與畫面中其他具有指示性、會意性的符號以及文字(某種意義上,亦可作為符號對畫面進行補充)之間又具多重意義的組合與調節。這也解釋了符號學對于傳播學的重要意義之一,即“能夠為符號如何在主體間產生意義和誤解,提供語言和文化結構上的透視。”[8]人們對于春牛圖的認定范圍已從原來春牛、芒神的外化“圖案”狹義表達,轉變為有日歷存在就可被認定的內化“精神”廣義認可。這也從側面表達出舊時勞動人民的無奈,明明農業生產主要依靠氣候條件,卻仍逃脫不了國泰是否民安,天下是否太平的影響,因為社會動蕩、朝代更迭對身為社會底層的民眾而言依舊是掙扎于水火之痛,唯有以畫寄情,表達內心的期望與向往。毋庸置疑,春牛圖作為中國農耕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歷畫種類,無論春牛與芒神是否作為符號在場,均已內化為帶來豐收佳運的符號,與祈禱農事生產緊密連接。
三、春牛圖的文化及社會功能
雖然各地《春牛圖》在細節上的表現存在較大差異,但都反映出民眾文化心理與生活實踐之間的密切關系。從傳播學角度分析,普遍具有“反身性”特點,即“是從實踐中抽象出來,但是反過來可以作用于日常實踐,甚至改變日常實踐的理論”[9]。民眾將關于生活的思考反饋至畫面,同時通過畫面上的符號與信息反向指導農業生產,這無疑傳達出了一種人們對自然、對生活、對人生的思考和對農業、對生產、對實踐的“互構性”特征。
1.歷畫:傳遞物候智慧
“二十四節氣”是中華先民通過長期觀察、實踐,總結本土天文、地理情況而發明的,在農耕為主的農業社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體現了民眾對于物候學的深刻理解,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對促進農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春牛圖的重要實踐功能之一,便是將畫面中的“二十四節氣”物候體系作為最直觀的指示性符號指導農業生產,滿足民眾基礎的使用需求。春牛圖中所傳遞的具有物候特征的時令植物、時令動物也是其作為指示性符號對各自所代表節氣的具體表現,是民眾的物候認知對行為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即通過某種動植物直接聯想到與之相對應的節氣,如候鳥、候獸和時令植物花卉等。候鳥也稱“玄鳥”,包括燕子、鶴、鳳、雞等。古代的“候獸”主要指麋鹿,因其有按時脫角、孳茸的生理特征,故被認作可指示時間變化的候獸,民間美術中常用的“鹿鶴同春”“鹿頭花”等物候題材皆表此義。時令植物符號以桃、柳、牡丹、梅花、松柏居多,不但因為這些植物可昭示不同時節,更取其各自代表的不同文化內涵,例如,桃子象征辟邪高壽、牡丹象征富貴榮華、松柏象征萬古長青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芒神手中所執趕牛之物,北方以牛鞭為主,而在南方以象征春回大地、萬物復蘇的柳條、嫩枝居多。總之,各種帶有物候含義的指示性符號出現在年畫中,無不在提醒著人們耕作時節已至。
2.裝飾畫:祈福愿望的全面滿足
春牛圖中通常會表現出與農業生產的密切關系或對農業興旺的直接祈求,其中乞求農事生產風調雨順便是第一訴求,但小校場春牛圖還將滿足民眾精神層面的愿望與訴求作為其基本功能。這種滿足表現在兩個層面上,層面一為對全部愿望的滿足,層面二為對全部人群的滿足。前者表現為,除了對農業豐收的期望之外,民眾往往還會將其他心愿一同增添至同一年畫中,如對發財、消災、祛疾之類的美好訴求。在《光緒三十年甲辰財神春牛圖》中,畫面集合民間認可度較高的財神,如文財神、武財神,五路財神、招財、進寶等,民眾希冀來年財源廣進、富貴吉祥。通過馬生雙駒來期望畜力增加、六畜興旺,也有通過天喜星下凡送喜、利市天官送財等場景,將人們對健康、發財的期望全部納入其中。后者表現為,不同信仰、不同審美、不同階層、不同教育背景的群體在春牛圖上的選擇。如在《光緒三十五年羅漢春牛圖》中,除繪制春牛與芒神外,并繪有春官,中心位置繪阿彌陀佛,兩側有十八羅漢,并書寫“色即是空空即色”“心原成佛佛原心”字樣,此類春牛圖或與佛教信眾的選擇有一定匹配。總之,春牛圖作為一種最貼近民眾生活的文化創造,其創作的最初目的是保證其所發揮的“物”的價值,即在滿足人們對生物性的存在要求——對農業生產的指引與對豐收的良性心理暗示之上。隨著時代進步與社會意識形態的轉變,其針對“異人”對“異物”的需求又進行了完善與擴展,以此實現各自愿望的全面滿足。
3.新聞畫:參與實事討論
歷代掌權者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故而在面對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春牛圖時,官方不但將其作為傳播來年節氣、氣象、收成信息的指導手冊,同時也將自身的意識形態融入其中,以畫傳意,表達自身政治觀念。除了《末代皇帝月歷圖》《中華大漢民國月份牌》等一些反映民國末年社會巨變的時事作品之外,也有很多藝人利用月份牌畫的表現形式創作了一批表現新中國初期沸騰生活的畫作。雖然也有學者認為,小校場年畫在民國初年已經消失,但本文認為,拋開制作工藝的差異,春牛圖的影響力至少延伸至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年畫,并且春牛圖題材的年畫創作也傳承至今。在傳統年畫中,芒神以青年男性或男童為主,但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部分年畫中,有將芒神刻畫為女性,將春牛用新式生產工具“鐵牛(拖拉機)”代替的現象。如在華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新歷書》所印制的《一九五二年春牛交節圖》(見圖2)中,芒神為胸戴象征勞動光榮大紅花的女性形象,手牽牛繩引其行走鄉間,遠處隱約可見農村田舍。此時,芒神已經完成從“神”向“人”的轉變——一名社會主義新中國勞動婦女形象,體現出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圖中《春牛歌》不再局限于吉祥話語,而是傳達包括“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鞏固國防”“講究衛生”“學習文化”“除迷信”“深耕勤鋤”“挖河防災”在內的一系列指導生產生活、宣傳社會移風易俗、宣講政策法規的新時代思想。從民俗活動道具到政治動員工具,春牛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悄然改變,不僅展現了藝人們力圖以新題材、新內容改造傳統月份牌畫的可貴嘗試,也反映出努力融合于時代、渴望不被時代拋棄的良苦用心。

圖2 《一九五二年春牛交節圖》[10]
四、結語
春牛圖作為舊時農業社會的產物,應立春日“鞭春牛”習俗而生,體現了勞動人民對風調雨順、豐收太平的期盼。迫于對生活的需求,人們主動去關注自然、了解自然、利用自然,用自然變化規律服務自身生產生活,并由此形成了獨特的物候信仰觀念。民眾根據自身對歷法、神靈、天地與生活、生產、信仰的理解,通過最具典型性的農耕文明視覺符號進行表達,不但體現了民眾對物候學的深刻認知、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甚至成為不同歷史背景下政治觀念的重要載體。但歸其根本,民間美術所表現出的藝術的內涵、民俗的過程和生活的體驗等主要特征也是大眾集體文化性格的重要表征之一。對物質需求而言,主要聚焦在如何尊重天道,繼而達成生存繁衍的愿望。對精神需求而言,主要聚焦在如何抒發內心與對生活的向往上。總之,人們關于生存、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的心理表達,在春牛圖中皆有深刻呈現。與其他產地相比,上海現存小校場年畫數量并不樂觀,但仍可以反映出在晚清這一充滿裂變的時代中,上海乃至全國整體社會風貌的急速變遷,這在影像記錄匱乏的年代,無疑是保存和記錄清末上海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